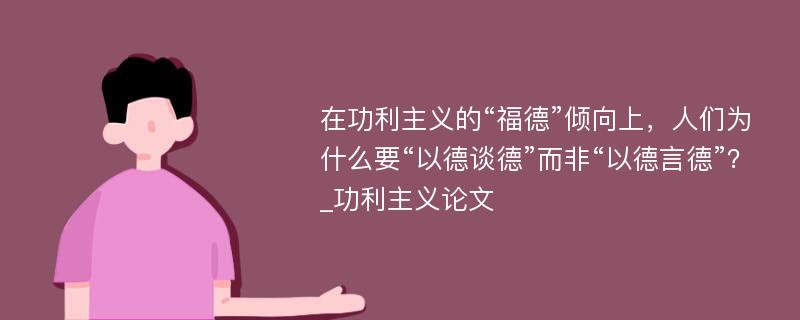
人为何要“以福论德”而不“以德论福”——论功利主义的“福—德”趋向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功利主义论文,而不论文,以德论文,福论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4)11-0015-07 功利主义是一种简捷明了而又影响深远的道德理论。[1]威廉斯指出,“功利主义的鼻祖主要把功利主义看成一个社会和政治决策的体系,并认为它为立法者和政治管理者的判断提供了标准和基础”[2]。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核心问题,是关于我们如何使得自己所追求或筹划的幸福生活成为一种道德上合理的生活。它遵循用“幸福”来衡量“道德”的基本价值趋向,我们称之为“以福论德”。这一主张,得出了与道义论(特别是以康德义务论为代表)用“道德”衡量“幸福”(我们称之为“以德论福”)之价值趋向针锋相对的观点。它更优先地强调把利益、快乐、福宁(well being)、幸福收纳、包容到道德合理性的理性筹划和论证,因而契合了一种现代性道德架构中的实践伦理趋向。 对于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各种道德主张来说,具有根本性或方向性的大问题,也是当今道德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必然遭遇到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乃是:人们为何要“以福论德”,而不“以德论福”?换句话说,人们为什么要从对幸福生活的追求出发,而不是从道德义务或道德责任本身出发,来看待和衡量道德行为的动机和标准?这个问题指向了幸福的道德性内涵,也就是指向了以幸福概念来理解行为、规则和制度的道德合理性问题。它涉及我们应当如何理解功利主义“福—德”趋向的问题。 以幸福衡量道德的“福—德”趋向,虽然古已有之,①但作为“功利主义”的根本主张则是与边沁和密尔的努力分不开的。边沁的论证基于一种哲学激进主义背景,认为人类理性必须颠覆荒谬的传统,而除“功利原则”以外的一切选择都是臆想的道德。这种“以福论德”的论证,以一种激进的修辞方式表明:功利就是幸福,就是快乐的增加和痛苦的免除,若非如此,“幸福”一词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公——快乐和痛苦——的主宰之下。只有它们才指示我们应当干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干什么。是非标准,因果联系,俱由其定夺。”[3] 功利主义“福—德”趋向的哲学论证,典型地体现在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所作的上述论断。边沁说,“功利是指任何客体的这么一种性质:由此,它倾向于给利益相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所有这些在此含义上相同),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相关者遭受损害、痛苦、祸患或不幸(这些也含义相同)。如果利益相关者是一般的共同体,那就是共同体的幸福,假如是指某一个人,那就是这个人的幸福。”[4]边沁的功利原则旨在为英国的整个法律体系进行一种法哲学的辩护和论证。他认为现代的法律、国家制度、统治体系不应该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契约实际上是一种非常含混的预设和假定;而应该建立在一些最基本的、大家都普遍接受的原则——幸福或功利原则——基础上。这种“以福论德”的“福—德”趋向的论证重点在于紧扣“道德现实性”,其目的是使功利主义成为真正系统的一种道德科学、法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奠基性的原则。密尔对边沁的功利原则的关键性修订集中为两点:一是认为对快乐的计算不仅考虑数量因素,还要考虑质量因素;二是认为作为功利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本人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也就是说,行为者个人的幸福并不优先于其他相关者的幸福。②这两条修订,使功利主义更适合用做一种“福—德”趋向的道德推理。 通过边沁和密尔的努力,古典功利主义在其“福—德”趋向的道德推理中产生了一个“三段论”(P1、P2、P3)。③第一,人性预设。这是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大前提。与17世纪、18世纪启蒙道德论证的人性预设一致——而不同于传统神学观点(趋善避恶)对人性的超验预设,人性被理解为一个趋乐避苦的本性,这是功利主义道德论证(基于苦乐原理)对人性的经验预设,即一切生物都感受痛苦和快乐,最大限度地避免痛苦、获得快乐。按照人性的经验预设,“以福论德”的三段论以幸福论为大前提: (P1)正确的行为或好的生活一定是追求幸福的行为或生活(即“追求快乐、避免痛苦”乃人性之使然)。 第二,合理性论题。这是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小前提。合理性论题涉及行为之善(好)和行为之正确的理据,并以此回应何种行为值得赞扬或鼓励。几乎所有的功利主义者都会赞同:行动的合理与否不取决于动机而取决于行动的结果。功利主义在合理性论题上往往坚持后果论,认为行为的效用或后果是权衡行为的标准,因而坚持一种重内容的合理性。按照合理性论题的内涵尺度,“以福论德”的三段论以后果论为小前提: (P2)好的结果(后果)比好的动机更适合用来衡量正确的行为或好的生活。 第三,最大化原理。这是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结论。最大化原理是将功利主义改造为一种道德理论的奠基性原理。没有这一改造,功利主义与快乐主义(主张最大化个人快乐)很难区别。边沁和密尔据此提出的原则叫做“总体最大化”,即最大化的整体的快乐。密尔的经典表述是“最大幸福原则”: (P3)凡是有利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行为或生活,就是正确的行为或好的生活。 “以福论德”的三段论奠定了功利主义道德推理的逻辑:苦乐原理、效果论和最大幸福原则。它是功利主义作为一种系统的道德理论产生的标志。这个“福—德”趋向的道德推理使道德更具现实性。因之,这一道德推理又被归结为与“衡量标准”相关的三个主要的要点(K1、K2、K3): (K1)一个行为的对或错,由行为结果衡量,其他均不相关; (K2)在以结果衡量时,依其产生幸福或不幸的总量,其他均不相关; (K3)以幸福或不幸的总量衡量时,依每个人的幸福都同等重要来计量,其他均不相关。 于是,幸福和道德的一致性,在一种“福—德”趋向中转化为以理性方式进行衡量或核算的问题。上述整理出来的“以福论德”的两类推理(P、K)可以化约为三种价值论上的强调。首先,(P1)与(K2)、(K3)内蕴幸福论观点:快乐或幸福的增加(不快乐或不幸福的减少)最重要;其次,(P2)与(K1)则表达了一种后果论观点:行为的结果最重要;最后,(P3)与(K2)、(K3)敞开了功利原则的价值维度:不偏不倚地计算每个人的幸福最重要。上述还原分析表明,功利主义“福—德”趋向问题在其奠基性的道德推理中实际上并没有脱去日常道德的“头脑简单”。不论赞成还是反对,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道德推理,实际地引发了一种持久的帕菲特式的问题:“到底什么重要?” 功利主义“福—德”趋向上的道德论证,基于三个价值论上对“通行的幸福”、“行为的结果”和“不偏不倚的测算视角”的预设。因此,它必须在面对众多尖锐批评和广泛质疑时以更具说服力的理由回答三个问题:为什么“幸福”最重要?为什么“结果”最重要?为什么“不偏不倚地计算每个人的幸福”(功利标准)最重要? 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道德推理,从其诞生时起就不断地遭到诘难和反驳。两类反驳似乎宣告了功利主义的失败。一类是从语言形式层面展开的反驳。另一类是在思想实验层面展开的反驳。 追溯历史,20世纪初英国元伦理学的兴起揭开了从语言形式上对功利主义进行反驳的序幕,从而使功利主义遭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冷落。元伦理学通过对道德语言的逻辑进行分析,指出道德术语属于一种只是诉诸人的直觉或情感才能理解的“不可定义”的直觉语言或“不可普遍化”的情感语言,它们不具备普遍性和规范性的特点。这类反驳的突出特点,是偏重形式而忽视质料,即更强调从形式上拆除功利主义“福—德”趋向的推理架构,等于从语言形式方面取消了功利主义规范论证的合法性。 英国元伦理学的奠基人摩尔(C.E.Moore)在《伦理学原理》(1903)中指出,功利主义(以密尔为代表)给出的“为什么幸福最重要”的理据是建立在“自然主义谬误”基础上的:从人们只欲求幸福或快乐,推出幸福或快乐是“唯一值得欲求的”,这等于把“值得欲求的”的价值问题与“欲求的”事实问题不加区别地混同起来,“从而犯了自然主义谬误”;[5]说“人们只欲求幸福或快乐”显然是荒唐的,使之显得合理的唯一“修辞方式”是在“目的—手段链”中将幸福或快乐处理成为“终极目的”,而这显然不再是密尔所说的幸福或者快乐了。摩尔的批评之所以重要,不在于他是否有效地驳斥了功利主义的大前提,而在于他运用的语言分析方法,即挑起了话题的转换。对摩尔来说,重要的不是质疑“以福论德”的道德推论,而是要问,当人们使用“善”、“幸福”、“正当”等语言的时候他们究竟在说什么?伦理学的重心由此转向一种更精致的学院化的道德哲学,即以语言逻辑分析为方法进路的元伦理学。这一方法轻描淡写地使“以福论德”的道德推理变得失去了意义,它认为一切道德术语无非是情感或直觉的表达,根本上没有科学意义。功利主义由此被冷落了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福利国家的实践使功利主义跃升为公众话语的主角,而英语世界专业哲学家圈子的讨论仍然有意无意地忽略它。应该说,它不是被驳倒了,而是在学院派哲学家那里让位于更优先的“元”问题——道德命题的逻辑和语言性质问题。从道德哲学主题转换中产生的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从一开始就隐蔽地容纳了某种价值态度。同样诉诸直觉主义方法,摩尔强调“理想事物”引起的愉悦具有道德意义,而罗斯(Ross)则强调“显见义务”的重要性,前者容纳了功利主义“福—德”趋向,而后者则是在道义论“德—福”趋向上运思。但把道德语言归结为一种情感语言,则是公然地将道德视为主观偏好而沦为“臆想”。 当然,功利主义之所以遇冷,除了元伦理学的勃兴带来的“忽略”外,还由于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道德推理本身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难题。尤其对于古典功利主义的论证而言,它使用的“画笔”太大,适合勾画宏大的社会和政治蓝图,但不适合用于推荐个人视角上的正确行动。而元伦理学的分析旨趣,又恰好以“零敲碎打”的个人视角锻造了20世纪上半叶道德哲学分析的理论气质。 因此,随着20世纪70年代实践哲学的复兴,当功利主义重新成为道德哲学讨论的重大议题时,对功利主义道德推理的反驳虽然不再仅仅限于一种语言形式上的反对(直觉主义反对或情感主义反对),但是各种不同价值趋向上的道德理论显示出另一种偏好:通过设计或描述一些展现具体情景的案例进行思想实验,一方面既保持分析路线上道德哲学的思想敏感性,另一方面又力图超越元伦理学脱离现实生活的形式化抽象的弊端。这种思想实验的要旨,在于暴露功利主义道德推理在价值预设中所隐含的不合理要求。这类反驳往任是从内容上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切入,进而扩展成为一般性的反对。 当代英国学者蒂姆·莫尔根(Tim Mulgan)在《理解功利主义》一书中搜集了那些用来质疑功利主义的14个经典案例。他通过分类分析后指出,功利主义的道德推理会遭遇两种关键性的反对。一种反对是“非正义反对”,是说功利主义会劝告人们对别人做不公正的事情,如把基督徒扔给狮子(基督徒与狮子的例子),杀死无辜者以平息暴动(警长的例子),谋杀一名叫玛丽的病人为五个濒死病人提供器官移植的供体(移植的例子),救“大主教”比救“女服务员”(甚至可以设想该服务员是施救者的母亲)更具价值的例子,复制一个更幸福的克隆体的例子,严刑逼供的例子,失控电车的例子,等等。另一种反对是“苛求性反对”,是说功利主义告诉人们不能做一些应该被允许去做的事情,如功利主义告诉人们在接到慈善募捐信后要立即把所有的钱都捐出,因为那样会产生更多的幸福,再如它会劝告一个人应该自愿献身30年的“慈善生活”,等等。[6]这些精心设计的案例以叙事形式(讲故事)描绘了每一种具体情景下人们在进行道德选择和道德判断时的复杂性。功利主义用幸福衡量道德的方式,在这些案例中通常都会陷入荒唐可笑的失败中。例如在失控电车的案例中,④将一个陌生人推向电车的设想已经很不对了,如果碰巧他是你的朋友的话,这种设想就更应当受到谴责。在这种情景中,功利主义的推理只考虑到了“幸福的总量”、“行为的结果”和“理想的观测点”三个抽象要素及其逻辑关联,这种极简主义的论证既不考虑幸福是如何产生的,也不在乎到底谁的幸福岌岌可危的问题。莫尔根评论说:在每一个案例中,无论警长还是医生,他(她)与所牺牲的人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中这一事实都会增加其行为的错误性;他(她)有一种特殊的义务,要求不能以这种方式伤害他人。[7] 这些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案例)吸引着研究者或讨论者不断地增加一些“非典型”情节。比如设计诸多的“碰巧”和各种不同的“版本”,以使得反对或辩护的论争更具文学色彩,也更有戏剧性和思想穿透力。⑤然而,从这种思想实验中衍生出来的针对功利主义的一般性反对,在学理上并不属于“非典型”孤例,而是具有代表性并主要集中在古典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三段论”上。我们将这些“反对”的辩论(debates)概括为如下三个驳论: (D1)功利主义“幸福论”使用了“通用价值货币”,它忽略了“人的尊严”的重要性。 (D2)功利主义“后果论”从一种“得失计算”出发支持在特殊情景下“施行不正义”,它忽略了“个体权利”的重要性。 (D3)功利主义“最大化原理”从一种“不偏不倚的理想视点”出发对人们提出了过高的要求,它看不到“个人生活完整性”的重要性。 以上三条驳论,大体上是通过思想实验反击功利主义道德推理的代表性视角。(D1)驳论的要点是说,“幸福论预设”忽视了比幸福(或快乐)更重要的“人的尊严”。诺齐克举的“快乐机”的例子是这个驳论的经典案例。[8]迈克尔·桑德尔也问道:“我们是否可能将所有道德上的善都转变成一种单一的价值货币,而在此转变过程中却不丧失某些东西呢?”[9]功利主义得失分析认为“幸福”最重要,并声称能提供一种用来衡量、合并和计算幸福的道德科学。考虑到这是一种被现代政府和现代商业公司普遍采用的决策形式,这一驳论所蕴含的矫正时弊的努力也是异常明显的。事实上,“通用价值货币”的反对,从密尔开始,就是功利主义辩护的重点。它迫使功利主义的幸福论预设变成为一种愈来愈开放性的论题。当密尔指出幸福之间有质的差别时,他意在避免“通用价值货币”的指责,但这个辩护等于承认有比“通行的幸福”更重要的“人的尊严”(更高级的快乐)。(D2)驳论指出,“后果论”没有关注到“个人权利”的重要性。例如,布兰特举的“功利主义子嗣”的例子就形象地刻画了功利主义只重结果而忽视权利的问题。[10]由于功利主义只看重行为的后果,它往往看不到“实施不正义”与“不能避免不正义”是有重大道德区别的。前者归于道德上要予以禁止的行为之列,后者则不能禁止。因此,主张通过“实施不正义”来“避免不正义”是荒谬的,它会导致赞同无视个人权利的行为。这种“非正义反对”迫使功利主义的辩护必须认真地看待“权利论”和“正义论”的道德诉求。(D3)驳论是说,功利主义“最大化原理”忽略了“个人生活完整性”的概念。每个人的生活(生命)都是独立的、不可替代的,与他的周遭世界结成牢不可破的“命运”,要求一个人从他所属的生活中脱离出来采取一种“非个人的”、“不偏不倚”的理想视点,是不现实的。因此,要求一个人为其他人的幸福做出自我牺牲,即使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也是不合理的道德要求。 无论从语言形式还是从思想实验方面,对功利主义“福—德”趋向上的道德推理的批评,都是由一种相对狭小的角度上展开的。前者指明,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道德主张,在话语形式上是一种信念、直觉和情感的表达,它不能提供完备的道德推理和道德原则的论证。后者则表明,功利主义对大众幸福、行为结果和功利标准三个道德哲学议题的价值论预设及由以展开的道德推理,存在着忽视“人的尊严”、“个体权利”和“个人生活完整性”的弊端,因而是一种失败的道德理论。莫尔根评论说,每一种对功利主义的反对都有一个简单的结构:“功利主义是不可接受的,因为(a)它说X,并且(b)没有任何可接受的道德理论会说X”(X是一些类似“警长应当杀死无辜者以避免暴乱”、“每个人应该把全部的钱都捐给慈善事业”等主张)。[11]那么,以一种“狭小的视角”或“简单的结构”进行的反驳,是否足以支持一种一般性的断言——说“功利主义是一种失败的道德理论”呢?或许,这两类反驳产生了一种“新”的历史效应,它使人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并重新审视功利主义的伟大传统,在掂量针对它的各种反对或驳论时深入思考“福—德”趋向上的核心问题——人为何“以福论德”而不“以德论福”? 不可否认,各种针对功利主义的反驳,自有它的积极意义。它们在两个层面揭示了功利主义隐含的危险:其一,在道德论证层面,元伦理学的反驳明确指出,功利主义不是一种在逻辑形式上经得起严格推敲的道德论证,它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道德劝告;其二,在价值观层面,各种思想实验的驳论揭示了功利主义的道德推理容易导致的三种疏忽,即忽视人的尊严、个体的权利和个人生活的完整性。 尽管如此,功利主义似乎并没有像它的反对者所“宣判”的那些,成了一种失败的、不值得认真对待的道德理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现代人无法避免功利主义,进而使得现代道德哲学无法避免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道德推理。一方面,由于功利主义诉诸道德现实性原则,在出发点上,从人类大致追求相同的东西(或者人们大致希望自己的孩子们能够拥有某种相同的生活)并称之为“幸福”,来权衡道德或论证道德,因而它在致力于使道德概念契合于人性欲求方面比道义论推理(“以德论福”)更贴近现代人的道德经验和道德生活直觉。另一方面,由于功利主义承诺了一种道德探究的开放性原则,即从非道德因素论证道德,这使得它不可能像道义论推理(而不是从道德因素论证道德)那样提供某种完备的道德理论,从而使得诸种“反对”和诸种“辩护”伴随着功利主义道德理论的不断改进和开放探索。以上两点表明,功利主义不是一种视野狭隘的理论,而是具有广泛现实性和实践旨趣的理论。我们当然还可以补充说,功利主义有一个无法忽视的伟大的传统,它的道德主张为一些伟大思想家(如休谟、边沁、密尔、两季威克、摩尔、黑尔、布兰特,甚至罗尔斯等)所阐发。而那些反对功利主义的道德主张,则通常从一种相对“狭小的视角”或“简单的结构”上分析功利主义,指责它的模糊性及其产生的难题。他们并不能提供某种有竞争力的道德理论的系统建构。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功利主义作为遭到广泛质疑或批评的道德理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多数时间内反而会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 功利主义并不“纯粹”,它不是某种单一的自洽的道德理论。它的现实性和开放性特点,使之混合了众多异质性的理论元素,如行为功利主义、规则功利主义、制度功利主义、双层功利主义、间接功利主义等。诸种改进的功利主义版本,往往针对不同的问题背景或道德诘难,有些理论容纳了元伦理学的理论要素(如行动功利主义或黑尔的双层功利主义),有些理论接受了契约论或道义论的理论前提(如规则功利主义),有些理论吸收了人权理论的原则(如波普尔的消极功利主义)。在这些理论中,有的坚持一元论,有的坚持多元论,有极端的功利主义,也有温和的或消极的功利主义。功利主义的各种理论探索,体现了一种包容性和开放性的理论气质。而功利主义的各种理论形态尽管千差万别,却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即遵循“以福论德”的道德推理。这是它的活力之源,是所有功利主义辩护的中心。 功利主义的最大特点是系统、清晰和简明。它所坚持的“以福论德”的道德探究路线,从幸福的道德性内涵出发,认为在任何情形下,遵循功利原则就可以做出一种合理性的抉择和判断。如行为功利主义的代表斯马特(J.J.C.Smart)在论辩中曾经明确宣告功利主义的简明态度。他接受元伦理学的批评,把功利主义理解为一种基于普遍仁爱的道德劝告:“为了建立规范伦理学体系,功利主义者必须诉诸某些基本的态度,这些态度是他和那些他正与之对话的人共同持有的。功利主义者诉诸的情感就是普遍仁爱(generalized benevolence),即追求幸福的意向,总而言之,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为全人类或一切有知觉的存在者追求好效果。”[12]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推理形式,反映了这种简明的道德现实性原则。 理解功利主义,无论在何种立场上进行,都是出于应对现时代道德现实性与道德理想性之间内在紧张的需要。如果丧失了“理想”,功利主义就会褪变成为一种“不见道德的道德理论”,一种麦金太尔式的追问紧随其后——“我们为什么要有道德呢?”如果忽略了道德现实性诉求,功利主义会走向它的对立面,即持一种超道德的主张。这在行为功利主义的道德推理中并不少见。这使它看上去与道义论的主张并无二致。然而,如果没有直觉主义和道义论的批评所形成的必要的张力,功利主义隐含的危险(忽视人的尊严、个人的权利和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就会得不到揭示和矫正。因为以幸福衡量道德(“以福论德”)的基本原则只具有相对的意义,而“以道德衡量幸福”(“以德论福”)的基本原则始终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后者不主张在道德之外寻找幸福生活的目的或标准,因而逻辑必然地将幸福排除在道德的考虑之外,形成了“为道德而道德”的“德—福”趋向的道义论。[13]前者主张从人之幸福所必备的条件或要素出发来衡量行为的道德性与合理性,认为道德的目的是“促进普遍幸福”。[14]两相比较,“以德论福”更适于理论逻辑上的论证,便于提供完备性的道德理论。但逻辑上的必然性,并不表明经验的或现实生活中的必然性。相反,“以德论福”的道义论原则,在道德现实性上并不适合用做日常道德的实践原理,它更适合作为关键时刻的伦理选项或作为圣贤道德(或道德英雄)的伦理准则:它倾向于先验地建构“德—福”趋向之理想而不是经验地实现“福—德”趋向之现实,因而适于建构道德理想而不是筹划道德现实。与之不同,“以福论德”的原则要比以道德衡量幸福(“以德论福”)的原则具有更切实的现实感,尽管它不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从一种现代性道德视角看,尽管“以福论德”的功利论原则,有着显而易见的缺欠,如它不能自洽地将说谎、强迫、拷问、背叛甚至杀人等行为纳入道德上应当绝对禁止的行为,且存在着逻辑上的自败,⑥但它却“几乎可被看成一种与政府具有密切关系的学说”。[15] 不可否认,直接以幸福为目的来论证道德或申言道德,多少会流于浅薄和“头脑简单”。[16]功利主义的“福—德”趋向,并不否认“以德论福”的道德知识,但却更为优先地强调“以福论德”的道德实践。概而言之,它是从行为、规则和制度如何有利于人之幸福或福宁的最大化的原则高度,来理解道德或论证道德的。因此,这个问题的另一种表述是:对于人们思考和筹划一种好的幸福生活而言,为什么生活提出“何谓道德”的问题与人们对生活的道德要求之间不能一致,反而与人们对生活的幸福要求之间相一致?正确的行为,为什么是最大限度地增进幸福的行为,而不是最大限度合于道德法则的行为? “以福论德”诉诸幸福之动力,而非道德之动力。它在删繁就简地将幸福之“目的和结果”等同于道德之“动机和标准”的时候,对于“人为何要讲道德”以及“何种生活要求构成了人遵循道德法则之动力”之类的问题,设置了一种“福—德”趋向上的解题路径。功利主义的理由,既非绝对正确,也非完全错误,但却在许多方面,尤其是在坚持“福—德”趋向最为强劲的制度伦理维度,凸显了现代人必须认真对待的那些紧要论题的重要性。然而,针对功利主义的驳论表明,在功利主义强调“以福论德”的地方,往往隐含着挥之不去的危险。过于现实或过于片面的功利主义,在“福—德”趋向上会陷入只见“幸福”不见“道德”的困境。因此,它需要“以德论福”的道义论予以警醒或进行平衡。因之,道义论的“德—福”趋向,与功利主义的“福—德”趋向,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的必要的张力,共同构成了规范性的来源。前者诉诸道德理想主义,后者诉诸道德现实主义。二者相反相成,互为表里,使得追求幸福生活的人们,在面对质疑和诘问时,必须得检讨“福—德”趋向上的道德推理能否顾及一种道义论的“德—福”趋向。从这一意义上看,理解功利主义的最好方式不是别的,而是认真地问一问:人为何要“以福论德”而不“以德论福”?唯有如此,在一个无法避免功利主义的时代,我们才会在坚持道德的现实性的同时不丧失道德的理想性,而在坚持道德的理想性的同时又能够兼顾道德的现实性。以这种方式,我们将功利主义理解为一种合理的“以福论德”的道德理论。 注释: ①例如,古希腊伦理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德性论视域下的“以福论德”的幸福伦理学,尤其以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为集大成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是其中具有功利主义倾向的代表。 ②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写道:行为者在自己与他人的幸福之间,“更像公正无私的旁观者那样,严格地不偏不倚”。密尔:《功利主义》,徐大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③这个三段论的记录方式P1、P2、P3以及对应的论断,与下文所述的关涉,“衡量标准”的三个要点的记录方式K1、K2、K3及其对应的论断,是笔者在对功利主义的道德推理进行概括总结的基础上以“命题”的形式提炼出来的,目的是便于清楚直观地显示功利主义“以福论德”的道德推理。 ④天桥下一辆载有10人的有轨电车失控,疾驶向一座年久失修的桥。除非有办法让它停下,否则车上10个人就会随车一起葬身悬崖。唯一的办法是把大胖子阿尔伯特推下天桥挡停电车,而阿尔伯特也会因此丧命。功利主义说,你应该把阿尔伯特推下去,因为他一个人的生命不及电车上10个人的生命重要。 ⑤例如,在哈佛公开课上,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J.Sandel)讲述了两个版本的“失控电车”的故事,既可以帮助人们澄清功利主义的价值预设,又有助于说明人们实际反对的是什么样的功利主义。[美]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是好?》,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22-25页。 ⑥从这一意义上,帕菲特称后果论是一种间接自败的道德理论,他谈到一种叫做“集体性自败”的可能,“如果几个人力图达到T设目标,而达到这些目标却将会更糟这一点为真时,我们称T是间接地集体性地自败的。”([英]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王新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9页)举例说,一个医疗小组确信对病人说谎是一种最大限度增进病人幸福的行为,于是选择了集体说谎,然而在达到说谎这一目标时,却诉诸更多、更大的谎言,且无助于病人的快乐,这使结果变得更糟。也就是说,由功利论支持的行为出现了对功利原则的颠覆或否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