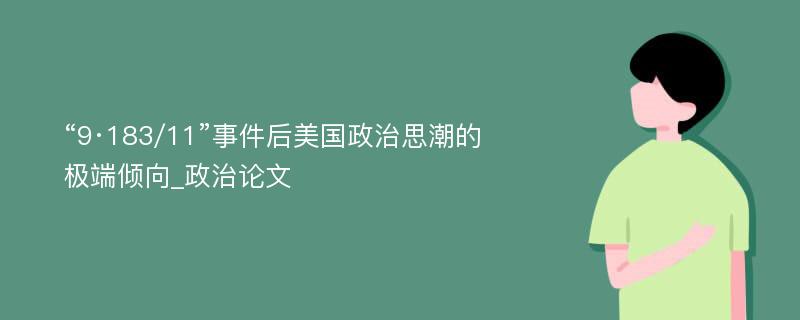
“9#183;11”事件后美国政治思潮的极端化倾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美国论文,倾向论文,政治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9·11”事件:文明间的冲突
作为政治恐怖事件的“9·11”,对现代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造成了肌体上的伤害,人们不再相信战争沿循从冲突、冲突的加剧到战争爆发的正常发展线索,战争可以是突然的、爆炸性的、非军队小规模的攻击行动,并且直接威胁平民。文明之间的冲突似乎必不可免,而负载不同文明的国家间关系也随之紧张起来。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价值系统之间、负载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间,关系得到有效协调的空间似乎骤然间缩小。
另外,从对现代化发展的影响上观察,人们看到了现代化成就的脆弱性,看到了现代化催生的社会的畸形状态——现代化既带给人们财富,也带给人们灾难,对现代化的复杂性认知更形强化。从对于社会心理的震荡来分析,人们的安全感大为下降,而不安全心理的蔓延,会瓦解人们对现代化的信心。假如对“9·11”事件的总体政治影响进行概括,我们可以说,透过各国政府一致强调反对恐怖活动的表象,现代与反现代的对峙、西方与非西方的对峙强化了。各种政治敌视由此获得了支持理由,各种政治理解的努力受到挫折。
这不幸成为我们审视“9·11”事件具有的政治思想史蕴涵的客观背景。而在这一背景条件下的审视,也具有一种紧张性。这种紧张性就是,人们对恐怖活动的紧张导致了对战争的吁求;人们对战争的信赖,导致了人们对以暴制暴政治观念的认同。而人们对以暴制暴政治观念的认同,进一步引起人们对国家间、文明间通过沟通、对话、协商来解决冲突的不信任——极端化的政治思维就潜蛰在其中了。
左翼与右翼:极端化的政治思维
首先可以从西方国家、尤其是从美国对于“9·11”事件的思想反应上得到证明。当“9·11”爆发之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相信战争是解决恐怖活动的最有效办法。——这说明美国普通民众对于“9·11”的政治认知状态。压倒多数的美国人支持发动阿富汗战争,而美国国会(众议院)在动议战争的投票中,只有一人投反对票——而且投票者还申明并不是反对战争,只是反对在不当的时机动武。这显示了美国政治家对于“9·11”事件的政治定位。而最为自由的美国传媒也受到强大民情的压力,不敢对太强的主战舆论进行批评。这彰显了美国政治健全批评空间的逼仄。当美国政府将反击“9·11”进攻的战争行动在最初形容为“十字军东征”,后又命名为“无限正义”,再更名为“持续自由”的时候,也表明了美国政府对于反击恐怖主义活动的战争的定位,偏执于它的宗教涵义,而不是政治正义。至于西方国家在类似的心理反应状态中做出的以暴制暴呼吁,对美国战争行动的支持,也都表明在紧张的政治情绪中对极端化的政治思维的借重。
行动中的政治思维容易走向极端,而判断一种政治思潮是否极端,主要看政治家和思想家的主张。“9·11”之后,具有明确政治思想、社会理念的政治家,大力地伸张一种明显是极端化的政治理念。比如,敌视共产主义的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赫尔姆斯,就在CNN的专访节目中根据不足地认定,这次恐怖活动与中国有关,并依据这一判断,认定美国就战争行动与中国、俄罗斯沟通是浪费时间。美国应当在将恐怖主义与纳粹主义联系的同时,记住共产主义的威胁,特别是共产党中国的威胁。赫尔姆斯对于“9·11”事件的这一评论,显然不是对事件本身的一个反应,而是对事件之外的某种显得极端化、排斥对话与理性的政治理念的强调。
美国主流传媒发表的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对策性论文,也是具有明确政治思想支撑和政治观念主张的,也明显地表现出极端化的特点。《华尔街时报》刊载了一篇文章,作者明确声称,只有殖民主义才是治理恐怖主义的良方灵药。他不仅认为长期的战争对于反对恐怖活动是必须的,而且认为,美国人还要承担“长期的政治义务”——“一种新形式的殖民,西方管理的前恐怖国家,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作者更从美国19世纪展开反对海盗的战争入手,定位这次反对恐怖活动的战争性质。作者指出,正是美国,以及后来介入反海盗战争的英国、法国,镇治住了海盗和庇护海盗的国家,并通过对这些国家的殖民统治,实现了这些国家的文明化。而后来殖民统治者的退出,则产生了这些国家的“肮脏和流血的事情”。作者还开出一个前国际联盟委托托管制的药方,作为管制恐怖国家的有效对策。这种主张,显然是一种反对不同国家间通过理性的政治协商和政治对话解决政治分歧的极端化主张。而且吁求的还是19世纪造成国家间、文明间政治敌对的殖民主义药方!
与这种向殖民主义低头的极右翼的政治思潮相映成趣的另一种政治思潮,则是向左走的政治思潮。在西方政治思潮的发展史上,左翼的政治思潮历来都依托在政治道义上面,它欲求的是政治公平。它的合理性也在此体现出来。但是,在“9·11”事件发生后,左翼思想家的反应似乎也打上了极端化的烙印。具有天生左翼思维的西方作家群落,对于“9·11”的反应,首先不是抨击恐怖活动,而是抨击他们所厌恶的“资本主义”,或者不为他们喜欢的美国政府。作家桑塔格故意与主流意见对峙,她认为美国媒体充斥了“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因为,“9·11”事件并不像美国媒体所说的那样“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恰恰相反,那些为了杀人连自己也一块杀掉的人不是懦夫。因此,紧要的也许不是谴责恐怖活动,倒是美国应当检讨自己的国际政策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失当。无疑,美国政府是应当从“9·11”事件吸取教训的。但是,对于“9·11”事件的关注焦点,离开了反对恐怖主义这个首要之点后,反思还有多少正当性,是值得疑虑的。离开反思的焦点问题,自诉于一己政治信念,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政治偏执。
这种表现,在著名的政治评论家(也是一个更为著名的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那里也不例外。乔姆斯基通常对于美国政府都持一种绝对不留情面的批判态度——凡是美国政府支持的,我就反对;凡是美国政府反对的,我就支持。这种极端化的政治评论立场,在“9·11”事件后对于美国政府与西方现代化主流思想的评论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美国定位在“世界头号恐怖主义国家”的位置上,因此对于美国的反恐怖战争嗤之以鼻。
从表面上看,左翼的评论要来得比极右翼的评论理智一些。但是,就左翼、右翼的评论的实质结构而言,都是一种走向极端化的政治思潮的支流而已。无疑,当极右翼评论者偏离“9·11”事件大谈殖民主义的时候,他们就丧失了理智地评论“9·11”事件的理性基础。而左翼评论者在面对“9·11”事件的时候,只是谈论以往政府政策的失当,也对于我们对“9·11”事件的理解和解决恐怖活动问题的政治思考帮助不大。
远距离政治反思
从政治思想史来看,政治的有效反思,通常离现实的政治事件有一定距离,才能保证这种反思的思想的理智程度和理解政治事件的深入全面。也许,在离“9·11”事件的发生这么近的时段上反思“9·11”事件发生的原因,这种态势本身,就将人们限定在了一个只能根据评论者自己个人喜好的政治理念,进行政治点评的狭小境地里,这就很难避免走向极端化。
同时,政治的反思,本来应当是在各种政治思想主张与政治行动方案之间寻找平衡点,以便陈述一种具有理性的政治观点,并给予这一观点以理性的论证。但是“9·11”事件是一个突发的政治事件,面对“9·11”事件,政治评论家一时慌了手脚:右翼评论家只能拿起殖民主义的破旧武器来对付突发的政治事件,左翼评论家只能以自己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感来应付局面。这样,他们都可以免除遭遇突发政治事件的尴尬的“政治失语”,但是也都不能保证自己论说的正当性——比如极右翼对反对恐怖活动提出西方殖民的政治责任,其实是一个推不出的结论;而左翼通过“9·11”事件的审视申述的反对政府、进而反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也仅仅具有宣示立场的表面意义。
本来,政治的健全活动方式不是针对像恐怖活动这样的政治事件来设计的,它一定是针对正常的政治活动需求来设计的。但是,“9·11”事件需要人们在正常的理智基础上对于突发的因而是不正常的事件进行对策设计,因此,正常的理智解释不了非正常的事变,解释就必然偏向一边,显得极端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