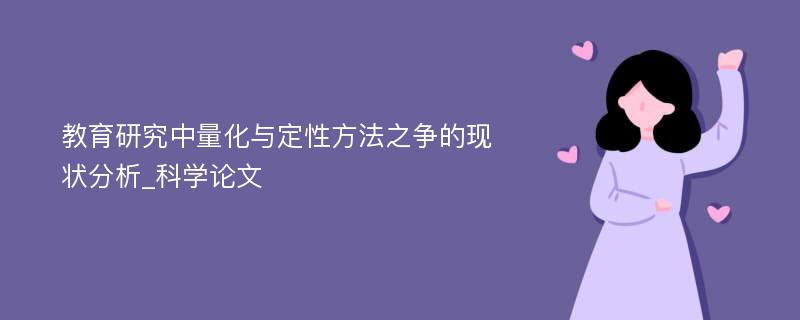
教育研究中量化与质性方法之争的当下语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境论文,之争论文,化与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整个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伴随着质性研究的崛起,关于实证的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的方法论之争,也逐渐达到了一个更为白热化的程度。然而,在这场如今依旧在持续之中的交锋当中,量化研究原来在教育研究领域的权威地位是否真正遭遇到挑战?质性研究是否如许多在该领域的学者所认为的,意味着研究方法论乃至方法的转型或转向?本文试图由这一系列疑问切入,对当下量化和质性研究方法论之争的现实语境、内涵分歧及其意义展开分析,并就两种方法论取向间的鸿沟是否存在不可逾越性进行探究。
一、量化与质性研究之争的现实语境
一般认为,量化和质性之争在本质上是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范式之争。塞尔等人认为,量化研究范式的基础是实证主义,它以自然科学为典范,断言所有社会现象都可以还原为代表真实的经验指标。外在的事实不依赖于人的客观存在,研究者完全可以以超脱对象以及具体情景的方式,利用精确的统计技术和工具获得唯一的“真值”。而质性研究范式的认识论立场则是“阐释主义”的和建构主义的,认为现实是人为建构的并永远处于变动不居之中的,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存在情境关联,对研究者而言,现实并不具有先验性,相反,没有人的关注现实就不会存在。故而,质性研究反对实证范式对量化的强调,而是尤为倚重对现实的细微描述,如深度访谈、参与观察等。① 我国学者陈向明则认为,质性范式作为传统实证主义之外的“另类”,它基于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和建构主义等理论思潮。② 而无论是“阐释主义”、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还是建构主义,究其理论渊源而言,或是来自早期维柯的“新科学”传统,或是来自博厄斯、马林诺夫斯基等的人类学实地调查研究传统,或是欧陆的诠释学、现象学以及英国后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传统,或是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费耶厄本德的非理性主义方法论传统,等等。因此,所谓量化与质性之争,尽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逐渐成为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一道令人瞩目的学术景观,但是,就方法论意义的争论而言,它可以追溯到更远,甚至从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崛起之日起,两相争锋就已经显山露水,并且在此过程之中,伴随科学与宗教、文化之间的话语歧异,两种范式之间持续紧张的内在张力始终存在,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因为各种社会思潮的涨落和语境的变迁,在表现形式上和程度差异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此,两种范式间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差异暂置不论,一个首先需要细究的问题在于:既然冲突由来已久,为何直到20世纪的80年代,两种范式间的争斗才进入白热化?要廓清这一问题,就需要对该时期特定的语境展开分析。
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的学术界可谓是一道分水岭。在经过六七十年代的文化骚乱以及平权运动之后,西方文化与政治领域的多元文化主义和平等主义的冲动也逐渐缓和,而与此同时,民粹主义、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政治上的新保守主义等思潮开始抬头。保守主义运动复兴的土壤,原本来自社会生活领域,如美国新保守主义对社会生活中个人责任、家庭责任的价值诉求。但是,它在提出这一系列文化和政策主张的同时,又把矛头指向了自60年代以来明显倾向于边缘群体利益和文化诉求的平等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如教育领域的双语教育和倾向于弱势群体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等。这无疑是对于长期以来已经在学术界成为“共识”的“政治正确性”的公然“冒犯”。正是在此语境之中,在80年代已经回归学院安静书斋的六七十年代的“反叛青年”们,当意识到自己再次受到保守主义的挑衅之时,不得不在被动之中仓促应战。由此,在英美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文化战争”在温和的自由派、激进的左派与保守派之间也拉开了序幕。
这场“战争”原本起源于为众多普通人所恐慌的社会道德危机,但是,最终却导向了学术界是认同共同文化、价值一致性还是认同多元差异的激烈论争。③ 论争双方的焦点议题在表面上是“文化”,实际上却是“文化政治”,在教育领域则进一步引申为阿普尔所谓的“知识政治”,即双方间的争执不仅仅是存在方法论立场的不同,而且还具有浓重的“政治”斗争色彩。如果说此前西方特别是英美学术界,在教育研究领域关于方法论之争还不过局限于受现象学、解释学、新史学等传统的启发,微观分析(如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拟剧论等)对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宏观分析范式的抵触,主观理解对主导的实证客观解释的排斥,强调价值、责任担当的批判理论对强调价值中立的实证研究的责难,那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原来在英美学术界并不非常瞩目的法国后结构主义,因为对微观政治分析有着独特的视角,对边缘话语合法性的认同,对理性的、实证的、中心的宏大叙述的拒斥,则很快为学术界中的温和的自由派和带有批判倾向的左派(如批判教育学)所接纳,并与英国早期的文化研究思潮结合,从而汇成一个颇有一定影响力的反保守主义阵营。换言之,也正是因为文化与政治领域中的精英论的保守主义复兴,不仅激活了此前已经存在的方法论歧异,而且更为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于,它借助后现代主义或后结构主义的话语,使原来的静悄悄的“战争”开始表面化并在学术领域蔓延,本来无关政治的方法论立场之争因为“文化战争”而成为政治立场的争锋。在此过程中,“文化战争”政治化的客观效果,实际上是放大了原来始终被边缘化的质性研究的声音。由是,在一个颇有声势的后现代语境营造中,教育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由量化到质性研究的转型说也就颇为盛行。
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何偏偏在20世纪80年代后带有保守主义“向右转”文化和政治整体语境中,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和诠释学、符号互动论、本土方法论、人类学与民族学、语言学、历史主义科学哲学和科学知识社会学等,虽然是不同的话语体系但彼此之间又存在许多交叠的众多学术资源,反而在学术界的影响日渐扩大,甚至让自然科学这样的“硬科学”都感到一种“政治”意义的威胁。1996年,在美国由索卡尔事件所引起的,关于科学与后现代主义、科学与学术界左派、科学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科学与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等诸多议题间的大对决,便足以说明学术界话语风格变化和语境变迁如何之巨。④ 一向对人文社会科学保持超脱的硬科学尚且如此,在教育研究领域内部主流的实证研究取向所面临的挑战也就不难想象。
二、量化与质性:方法还是政治之争
从以上质性研究范式崛起的语境分析中,不难看出,虽然量化范式和质性范式,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关于社会与人的存在意义、知识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等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但引发争论的导火索却是“政治”语境的变迁。因而,也正是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所有这些关于方法论的论争也就难免带有偏执和激进的色彩。
20世纪80年代后,在教育研究领域质性范式所倡导的方法包括:人种志的方法、现象学和解释学方法、历史方法、个人生活史研究方法、行动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叙事研究方法、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方法,等等。⑤ 这些方法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大多原来并不带有对实证倾向强烈排斥的立场,甚至本身就是“科学化”的结果。譬如人种志所关注的田野研究与早期试图把人类学科学化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就有着很深的渊源;行动研究则“起源于社会心理学、自然科学、组织科学和社会规划等学科”⑥,是早期美国心理学家勒温鉴于“复杂的现实的社会事件在实验室中研究的局限性”而提出的研究者应参与具体情境的主张;⑦ 当代教育研究领域的叙事研究,则最早源于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的语言学、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关于神话要素的分析,而无论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的“共时性结构”还是人类学的关于“人类精神和文化结构”,都带有典型的科学“普适性”特征。另外,还有最早由斯特劳斯、格拉泽等人提出的扎根理论研究方法,它的学术脉络可溯至实用主义和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虽然它排斥实证研究由假设、演绎到统计意义描述分析和验证的一般研究程序,但它对经验、事实和归纳方法的关注以及对因果关系探究的偏好,恰恰表明在方法上它追求的是更为严谨的科学准则。
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语境中,包括上述大多脱胎于“科学”的方法,不仅拒绝以量化研究为典范,甚至对所有实证意义的研究都带有怀疑甚至拒斥的倾向。持有质性研究范式的人们对实证研究的责难,已不仅仅是关于研究结论的“真实”与“可信”问题,而且更多的是对实证研究者立场的质疑。这里的立场包括本体论意义上的社会现实是建构性的还是结构性的,是存在确定性的本质和原则还是非确定性的“情境”局限。一言以蔽之,所有质疑所关涉的无非是现实的“可变”与“不变”、“动态”与“静态”、“线性”与“非线性”等前提假定。对“不变”、“静态”和“线性”以及结构性的偏好,显然代表了实证主义的立场,而这一立场又正好迎合保守主义的政治主张。诚如英国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罗杰·斯克拉顿对保守主义所做的诠释:“保守主义直接源于这样一种观念:个人是从属于某种持续的、现在的社会秩序,这一事实在决定人们何去何从时是最最重要的”,“个人在面对所有(共同体、教会、国家)这些事物时会感受到一种一成不变的态度。……作为保守主义之本质的‘生存意志’正是存在于个人与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之中”。⑧ 因此,在本体论意义上,与实证范式一脉相承的保守主义关于社会主张中所暗含的这种政治意味,势必引起一向坚持“政治正确性”的温和自由派和左派的警觉。
从20世纪80年代后质性范式对量化范式的质疑中,我们不难发现,该争论已经远远不是简单的方法论与方法分歧,毋宁说是一场“政治”立场的对峙。质性范式倡导者所采取的斗争策略,一是利用来自科学内部的危机,如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哲学、费耶厄本德的非理性主义科学观、英国相对主义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否定了实证典范的自然科学关于反映本质和规律的确定性真理和知识存在;二是阐发了米德、布鲁默、舒茨、戈夫曼和伽芬格尔等符号互动论、拟剧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论等建构主义的社会学传统,否定了社会的整体性、结构的客观性和先在性;三是借用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视角,否定实证、理性与科学话语的合法性;四是承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葛兰西的意识形态霸权理论、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等传统,赋予教育或社会现实以精英意识形态霸权和压制特征。因而,与经验研究和量化范式所假定的社会世界是一个“有机体”或“进化中的均衡系统”相反,它们更强调社会世界是作为文化和“剧场”的存在,或者是作为文本和语言的存在。⑨ 正是基于社会世界的这一系列反本质主义的假定,在认识论层面上,质性范式倡导者在根本上颠覆了实证范式的基础主义、约定论和工具理性观,倡导对社会世界意义的诠释而不是真理的解释,反对价值无涉而主张价值的介入。具体到教育领域,则是强调教育课程知识具有非确定性、意识形态和道德意味,而倡导建构主义乃至体现道德关怀和社会民主的知识与课程观,反对课程知识的客观性、确定性、中立性和精英霸权特征。
由此,通过对量化范式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全面解构,质性范式方法论取向中的政治立场也就凸显出来。其基本立场是:既然教育或社会现实是建构性并是变动不居的,不存在唯一先验、恒定的秩序,也就不存在量化范式方法所获得知识的普遍性、确定性以及唯一合法性;既然现实带有意识形态霸权和压制特征,研究者就不能保持一种超脱(韦伯的价值无涉),并撇开价值判断而无批判立场。从20世纪80年代后质性范式倡导者所关注的研究领域,不难看出他们与保守主义绝不妥协的态度。与量化范式关注议题有所不同的是,教育中质性范式更倾向于对社会不利和边缘人群以及边缘社会和文化的研究。除此之外,对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对学校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如消费、各种传媒、广告、青少年亚文化等也有着独特的研究偏好。这种有意表现出来的边缘对中心、弱势对强势、大众对精英对峙和抵抗的态度,以及对阶级、种族、性别和性倾向等议题的关注本身,其实就反映了一种鲜明的政治立场。
从20世纪80年代后行动研究者所倡导的教育研究“行动转向”的倡议中,我们可以领会这一立场的精神。如上所述,行动研究原本起源于二战期间勒温出于对现实情境问题关注而提出的在“实践中指向问题解决的研究”。早期行动研究在方法上更多地带有实证研究的特点。然而,80年代后,行动研究的方法论立场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瑞森认为,当代行动研究方法的起源非常广泛,除了勒温以外,如解放教育学的开创者费莱雷等解放论者、众多的实用主义者、现象学学者以及批判理论研究者,都对行动研究方法的进展做出了贡献。⑩ 怀特洛等人对当代行动研究理论资源的梳理较为全面,他们认为,当代行动研究理论资源包括在研究哲学层次上的有关反实证科学和“唯科学主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实践哲学;建立在阶级、性别和种族分析基础上的批判教育学;存在主义和人文主义;实用主义哲学、人本主义心理学和系统理论;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范式,另外还有各种具体学科领域的贡献等。他们进而从方法论角度将行动研究概括为三种类型:技术科学与实证意义的行动研究,相互合作和阐释主义的行动研究,批判和解放的行动研究。(11) 在这三种研究类型中,“批判和解放的行动研究”又是被作为任何行动研究过程中的最终目的,即通过认识个体自身受压制的条件“解放实践者”并“改变他们所处的现实处境”而存在的。(12) 显然,这种“解放”指向必定赋予了行动研究方法以强烈的政治目的和价值诉求,代表了行动研究旗帜鲜明的一种政治立场。
三、方法论多元主义:质性与量化研究能否相容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西方所谓质性与量化之争以及质性范式转向说,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向右转”语境中形成的,而在此语境中,政治立场分歧是构成两者冲突的主要成因。也正是因为敏感的政治因素介入,不仅放大了两者冲突在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而且,因为立场所导致的局限和偏见,以至于让人感到两者之间存在的范式上的不可通约性,而根本无暇顾及甚至无视是否存在整合的可能性。
的确,就本体论而言,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和量化研究所假定的前提值得商榷。如吉登斯所言,在社会学中并不存在一个“预先给定的”的客体世界,“而是一个由主体的积极行为所构造或创造的世界”。(13) 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所存在的本质区别。然而,他又指出,人的能动建构行为是受到限制的。“人类建构社会,但是他们是作为具体历史情境中的行动者建造社会,而且并非可以由他们自己选择的条件下进行。”(14) 吉登斯在此所谓的“条件”其实就是指外在于个人的“结构”。这种结构虽然不具有如孔德、迪尔凯姆、马林诺夫斯基和帕森斯等人所谓的先验主观(目的论)或客观(决定论)存在性,而同样是人们建构起来的。但是,它又构成了个体存在的条件。这种结构在文化意义上近似于布尔迪厄的“习性”,即对于特定场域的人们而言,它是一种“持久的、可转换的潜在行为倾向系统,是一些有结构的结构,倾向于作为促进结构化的结构发挥作用”,甚至是作为人的实践活动和表象的生成和组织原则。(15) 吉登斯在此用语言学家索绪尔的“言语”与“语言”作了一个形象的类比。人的行动和互动正如“言语”,它是“情境化的”,是有时空定位的,具有主体的能动性;而“结构”正如同“语言”,它是“事实上的”和“外在于时间的”。语言(结构)与言语(行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有机的联系,这就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即语言(结构)不仅是言语(行动)产生和对话(互动)的条件,也是言语(行动)产生和对话(互动)达成的无意识后果。(16)
吉登斯在此关于“结构”作为外在的条件,同时又是人行动和互动的结果的理解,实际是认可了社会现实不过是一种人为客观化的事实,它并不是一种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纯粹客观事实。譬如社会的道德伦理、文化习俗、风尚、制度等等,虽然并非是迪尔凯姆意义的纯粹客观的社会事实,但它对特定历史情境中的人们而言,的确具有不同程度和范围上的共识意义。这种共识来自人的非目的性或者弱目的性建构,同时对个体实践又具有一定的制约作用。这种本体论意义的社会现实假定,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无疑表明,在关于这种人为客观化事实的研究中,无论是实证的量化研究还是质性的研究,都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
教育以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量化范式的意义并不在于要获得普适性、确定性和一劳永逸的结论(事实上社会现实的人为历史性建构也决定了这永远是一种奢望),而是在于获得构成特定情境中不同个体行动和互动的“共识”,即结构的意义。这里的“共识”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为例。伽达默尔虽然认为每一个体是历史的存在,存在先在的“偏见”和各自不同的“视界”,然而,“偏见”之中不可能全无共同性,不同视界也不可能完全无“融合”,否则不仅人与人间的互动不可能发生,所谓的组织、社区、共同体、民族和国家乃至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量化研究的价值在于它有可能可以在偏见和视界冲突中获得共同性或者说一种统计意义的概化特征。与质性研究相比,这种概化虽然具有抽象性,且因为漠视了具体情境中不同个体行动而有损意义的丰富性。但是,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角度看,有了这种概化和共识,并不会损害质性研究意义诠释的丰富性和理论生成的多样性。相反,正是在通过与概化特征的不断比较中,才能发现个体能动性行动以及人与人间互动的更为多样化的“异”,并产生新的意义诠释和建立新的理论。
在与实证的量化研究关系上,质性研究虽然并不服务于量化研究的概化解释,但是它也未必一定与之相排斥。量化研究结论除了可以作为质性研究过程的一种参照,更为重要的价值还在于启发质性研究以更为多元的路径、素材去细化量化研究的解释,或者否证量化结论进而提供更多新的解释。与量化研究过程的技术线路、工具使用和解释方式的单一化和简单化相比,质性研究内部存在高度的非均质性。在总体上,它更关注反映“局内人”的理解,因而多采用人种志的田野考察、深度访谈、深描等方法,其研究素材极为广泛,如除了一般的考察日志外,个人传记、影像、图片、对话、故事和传奇等叙事文本都被广为采用。解释的路径也极为宽泛,包括扎根理论的编码,文化研究的叙事(图像)文本结构分析、符号的编码和解码,后结构主义的微观政治学分析,日常语言分析,等等。但是,质性研究取材的广泛性、解释路径的多样性和微观分析倾向,固然反映了它与实证研究在认识论上的整体主义倾向立场不同,但这并不表明量化研究就不能够为带有方法论个人主义倾向的质性研究所取用。“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对立。要验证循着这两者的方法论途径所发现的理论假说,就操作上可能的范围而言,都需要借助于统计学方法诉诸于众多个体或情境。”(17) 以扎根理论方法为例,扎根理论在对各种资料的编码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概念频次统计来确定范畴,在人种志、行动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特别是媒介研究)中,统计分析技术作为对意义诠释的一种验证也都有其适切性。在量化还是质性的争论中,人们要么过于强调质性研究路径在理论生成上的成效,要么强调量化研究在理论验证上的可行性,却没有想到问题就出在只关注一方所存在的偏颇。作为技术的量化工具,无论是对强调客观性的实证研究,还是更偏重主观性的质性研究,都是有用的。“研究工具并不必然就同某种特殊的方法论捆绑在一起”,“为追求效度,排斥量化的质性研究往往存在忽视信度倾向,而强调因果关系和概括性的量化研究,又频繁地为追求信度而忽视效度”。一种方法的适切性取决于它所适用的情境和研究者本人的直觉和常识,而不是一系列在先的独断性规则。(18)
四、超越“政治化”的“真实”之争
在当前教育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关于质性范式与量化范式间的不可公度性论依旧盛行,这种观点所持的基本依据就是两者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立场完全是对立的,认识路径也南辕北辙。其中关于量化研究的外在于人的客观现实与质性研究人为建构的可变化现实是构成两种范式不可通约的基本前提。故而,塞尔认为,质性和量化混合的多元研究方法也不是不可行,但即使是在对同一对象的研究中,不同研究方法所指涉的对象还是不同。两者间既不能做到三角互证也不能相互补充。因而,在他看来,或许只有形成一个建立在新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基础上的库恩意义的新范式,这一问题才能得以解决。(19)
塞尔在此所提及的新本体论其实还没有跳出教育研究中关于“存在”与“真实”的怪圈。关于“真实”,通常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实在”,一种是“现实”。前者是带有形而上意义的实在论。社会的实在论在过去、今天以及未来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悬疑的问题。保守主义与新保守主义对传统秩序的先在性假定,如美国著名新保守主义者布鲁姆所声称的,任何社会都存在一个“永恒不变、永远适应的道德准则”,“历史和社会的不平等是永恒且必然的”原则,便是这样一个带有形而上意义的“教条”。(20) 这种教条与孔德的实证主义的“人道教”、迪尔凯姆的“集体意识”、帕森斯的社会“核心价值”一样破绽百出。它与其说是代表新保守主义的一种关于社会存在的信念,还不如说是他们针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形成的相对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盛行,并带来的道德危机而发动“文化战争”的一种激进斗争策略。而也正是这种浓烈的政治挑战意味才激起了另一方同样带有浓厚政治激进色彩的回应。进而,引发了多元文化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等同样激进的反实在论反弹。各种相对主义、解构、消解、颠覆等话语本身便带有鲜明的政治立场特征。
把“真实”理解为“现实”则完全不同,任何“现实”都是特定时空境遇中的“现实”,它固然与历史不可剥离,但历史是人建构的历史,带有人的主观能动性。然而,特定时空境遇中的“现实”又的确构成人行动的条件,这种条件虽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但是,它的存在并不具有先然的合法性。也正因为如此,质性研究中后结构主义、文化研究取向关于现实中压制条件的反思,批判理论对现实的批判,现象学和诠释学对日常生活世界、文化社会学对“常人”和“常识”的关注,才体现了它们所具有的独特理论与方法论意义与价值。在此,关键的是,强调“现实”的人为建构性,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即基于激进的政治立场,否定历史与现实间的联系,甚至完全漠视现实对人的行动所构成的一定程度的客观性约束条件。质言之,“现实”是主观建构与客观建构的统一。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统一,所谓实在论关于真实(如真理)的“树干式”认识论,以及激进的反实在论甚至反“共识”的“杂多”、“游牧”和“流动”的“块茎式”认识论,都具有其各自的片面性,进而导致了质性和量化范式不可公度的对立。因此,笔者以为,既然“现实”是主观建构和客观型构的统一,所谓质性方法和量化研究间的方法论对立,毋宁说只是一种政治立场间的对立,而且并不意味着两者间存在根本的不可相容性和相互补充作用。
实证的量化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问题提出、假设建立、客观观察或问卷设计等形式,利用统计工具,以数量关系来推断各种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因果联系。这种因果推断和研究结论所反映的是社会“现实”共时性,即静态的特征。在信度足够高的前提下,它应该能够反映一个时空横断面上的现实的“真实”。但是,这种概率意义的“真实”结论对现实错综复杂情境概化,也有着它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其一,构成大概率的事件虽然能够代表人们行动或者意志的相对一致性,但是,却无法说明这种一致性背后更为复杂的多样性;其二,小概率事件(但同样也是“现实”的构成部分)往往被完全漠视;其三,简单的因果推断充其量是对有限时空中事件的一种共时解释,却不能把握在时间绵延中它与过去间的情境和历史关联,而充其量是“情境相似”的类推;其四,客观中立导致量化研究充其量回答了“是”的问题,而缺少价值和立场的反思性。质性研究的意义在于,它不仅可以对大概率事件进行延伸解释,而且可以对小概率事件加以解释以提供弥补;对历史、文化、语言、符号的关注丰富了量化研究的解释,并兼顾到情境关联;质性研究的反思性和批判性本身带有价值判断倾向,并对数字符号背后的意义提供更生动的诠释,从而赋予客观“现实”的再建构以人性化意义。
总之,正如美国学者塞科瑞斯特等指出的,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并不一定相排斥,人们过于夸大两者间的差异了,而事实上两者各有局限性。值得倡导的应该是方法的多元主义,如此不仅可以摆脱彼此的局限,而且在多种方法的共容中有益于彼此的结论互证并提供更有效的答案。(21) 在教育的质性研究家族中不仅文化研究具有这种量化与质性相容的特质,包括行动研究(解决问题的技术关注)、扎根理论(编码过程中范畴的频次)、人种志(数字档案和文本)、历史研究(计量史学)等等,都存在量化研究适用性。
注释:
①(19)Joanna E.M.Sale,etc.Revisiting the Quantitative-Qualitative Debate:Implications for Mixed-Methods Research,Quality & Quantity,2002,Vol.36.
②⑥(12)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14—16、448、452.
③(20)吕磊.美国的新保守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252—255、271.
④索卡尔,等.“索卡尔事件”与科学大战[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⑤Ronald R.Powell,Recent trend in research:A Methodological Essay,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Research,1999,Vol.21.
⑦Peter Checkland and Sue Holwell,Action Research:Its Nature and Validity,Systemic Practice and Action Research,1998,Vol.11.
⑧罗杰·斯克拉顿.保守主义的含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
⑨(18)Rebecca G.Long etc.The' Qualitative' Versus' Quantitative' Research Debate:A Question of Metaphorical Assump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Value-Based Management,2000,Vol.13.
⑩Peter Reason,Choice and Quality in Action Research Practice,Journal of Management Inquiry,2004,Vol.August.
(11)Sandy Whitelaw,etc.A Review of the Nature of Action Research,Sustainable Health Action Research Program,2003,Vol.February.
(13)(14)(16)安东尼·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277、278、232—234.
(15)布尔迪厄.实践感[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80.
(17)覃方明.社会学方法论新探——科学哲学与语言哲学的理论视角[J].社会学研究,1998,(2).
(21)Lee Sechrest and Souraya Sidani,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Method:Is There an Alternative? 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1995,Vol.18.
标签:科学论文; 行动研究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量化分析论文; 教育研究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学术价值论文; 认识论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范式论文; 保守主义论文; 质性研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