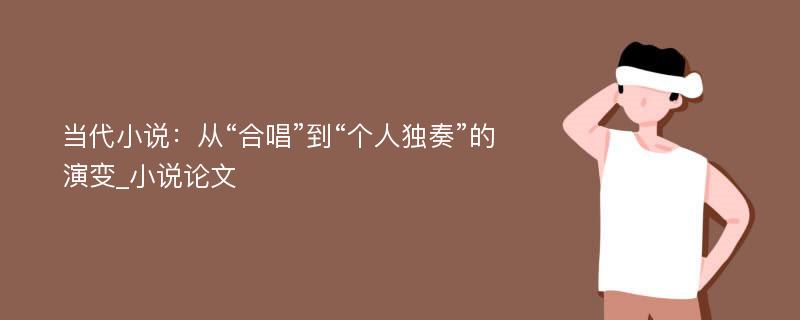
当代长篇小说:从“大合唱”到“个人独奏”的演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合唱论文,独奏论文,长篇小说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2)01-0087-04
建国后起初的七八年间长篇小说很少,20世纪50年代末才形成一个高潮。这次高潮, 作品数量也不多。据统计,17年时期长篇小说出版最多的年度是1959年,有32部。而据 茅盾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统计,仅1977年至1981年五年间就出版长篇小说406部。平均年 产80余部。但1981年就占了110部①(注:陈美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论》,上海 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5页。)。其后的发展更加令人惊讶。有人统计,80年代末至9 0年代初四五年间,长篇小说每年产量都在300来部。再以后则直线上升。1995年的年产 量已达700余部。1996年超过800部。1997年年产量接近1000部左右②(注:何镇邦:《 九十年代“长篇热”透视》,《光明日报》1998年2月26日,第8版。)。此后又有人说 长篇小说的年产量已达1100部③(注:陈鲁民:《中国文学角逐诺奖的八条理由》,《 文学自由谈》2000年第4期。)。产量如此可观,以至有“长篇泛滥”之惊呼。如今出版 一部长篇小说,如果不是特别出色或专门炒作,真的就会“泥牛入海无消息”。
出版量多当然不能说品质也好。相反长篇小说创作的泛滥还是一个问题。但它确实说 明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总体繁荣。而从艺术质地看,新时期也确实出现了不少好作品。下 面,我们就来看看中国当代长篇小说从“大合唱”到“个人独奏”的具体情形。
一、社会化操作的“大合唱”
很多评论家都提到过这样一种现象:新时期以前每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坛是 件大事,而且往往引起全社会的注目。如后来被称为“共和国长篇经典”的《创业史》 、《红岩》、《红日》、《红旗谱》、《青春之歌》和《林海雪原》等,都是数百万册 的发行量,都曾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改编成电影后更是家喻户晓。“文革”前夕出版的 《欧阳海之歌》,不到一年竟印发了两千万册,成为一种出版奇观。“文革”中也有如 此情形。除众所周知的《金光大道》是风行一时外,像《激战无名川》、《桐柏英雄》 、《征途》、《大刀记》、《万山红遍》、《春潮急》和《剑》等也是拥有众多读者的 流行作品。
长篇小说成为家喻户晓的“社会大事”,固然和有些作品不无可取处、总体出版量不 大而物以稀为贵等原因有关,但根本原因却是社会共同操作的结果。当时长篇小说创作 服从流行意识的“大合唱”,涉及到创作导向、出版规范、读者接受和作品评价等多种 因素。
由冯牧、缪俊杰主编的《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有个总序,它在评论五六十年代 长篇小说经典时曾指出:“由于政治的制约,从五十年代迭起的政治运动,以及理论上 ‘左’倾思想的发展和泛滥,文艺思想战线的‘斗争’愈演愈烈,行政上和理论上对创 作的干涉愈来愈多,这就不能不对文艺创作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④(注:冯牧、缪 俊杰:《时代的潮汐与历史的回音》,《共和国长篇小说经典丛书》总序,见《三家巷 》,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消极影响包括“从概念出发”,按概念“修改创 作构思”,把“精彩的章节或很有光彩的人物性格加以删节和修改”等等。这些问题的 出现,根本上就是服从流行意识的结果。
这里所谓“流行意识”,是指作家完全或基本按照社会流行或强制规范的思想准则和 艺术标准来创作,以集体化艺术规范马首是瞻。比如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表现 时代主流”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即是。1956年曾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并未真正落实,倒是“工具论”愈演愈烈。如1958年文艺界提出的“写中心”、“画 中心”、“唱中心”,以及柯庆施提出的“大写十三年”⑤(注:参见戴知贤《山雨欲 来风满楼》,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等口号,就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强化。 如此,作家个性意识往往丧失。17年时期和“文革”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更是深受影响 。
“流行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以“领导意志”为指导思想的社会规范。
众所周知,新时期以前的指导性文艺思想主要来自至上而下的“上级指示”。“领导 意志”甚至领袖个人意志,常常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诸如“上级指示”、“红头文件 ”、“国家政策”或“领袖语录”的“一言堂”,便成为文学创作的根本原则。
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首次高潮来说,题材的集中性、主题的相似性和艺术的模 式化就充分体现出大一统流行意识的特征。如《红日》、《红岩》、《红旗谱》、《创 业史》和《林海雪原》等都未能免俗。《山乡巨变》、《创业史》、《三里湾》等就多 按照“两条道路斗争”来设计情节、刻画人物。《风雷》、《艳阳天》这类“紧跟形势 ”的作品更是如此。上面号召“以阶级斗争为纲”,《艳阳天》便依此设计“先进人物 ”、“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百炼成钢》等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也是围绕“忆 苦思甜,赶先进,夺红旗,传帮带”等原则来进行艺术编排。主题思想口径一致,歌颂 与批判均依照特定政治要求,显然和步调一致服从“领导意志”有关。“文革”时期, 长篇小说创作意识的集体化则变本加厉。《金光大道》就是一个样板。署名“上海《虹 南作战史》写作组”的《虹南作战史》和南哨的《牛田洋》,则完全沦为“帮派文艺” 的御用工具。它们按照“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 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所谓“三突出原则”塑造人物和炮制情节,将“图解 艺术”发展到了极端。
以统一精神规范来设置情节、组织场面和刻画人物,这种脱离现实的创作造成了主题 先行、人物雷同和情节模式化。尽管当时有些长篇小说一定程度上也显示了作者个人风 格,也表现了情节清晰、结构有序、矛盾张弛、语言通俗等特点,但艺术成为“单纯的 时代传声筒”的公式化现象的非常严重则毋须置疑。
其二,以愚民意识和大批判为群体接受特征的文艺批评。
大众读者和专业读者(批评家)的接受,对创作的影响非常大。冯德英谈到《迎春花》 在1964年被改编成话剧上演时,曾说到这样的事:“我接到的读者来信和报刊转来的投 稿,一改过去的赞誉、亲切、善意的批评的文字,多是对我的小说愤怒的控诉、声讨, 对作者本人的斥责和咒骂。”⑥(注:冯德英:《关于“三花”的创作答读者问》,《 中青年作家谈创作》(上),山东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18页。)众多读者由善意批评 变为愤怒咒骂,虽然和“江青指示”与“文艺革命”有关,根本原因则是愚民政策和愚 民意识的产物。建国初的讨伐萧也牧,后来的批胡风,“反右”时期的批“毒草”,再 后来的批《青春之歌》,直到“文革”的大批判运动,我们印象最深的批评现象就是“ 工农兵齐上阵”的“口诛笔伐”。这种现象正是愚民政策的结果。那些专家们的“权威 批评”也多是对“工农兵立场”的附和。
其三,作家丧失个性以迎合时尚的创作走向。
既然是从某些既定的思想概念和时代规定出发,长篇小说创作个性意识的丧失也就自 然而然。这里不妨举个我曾多次谈到的典型例子。老作家康濯曾这样谈过“文革”前的 创作尴尬:1957年因一部作品受到冲击后,以为自己“看阴暗面”不对了;于是1958年 便“紧跟形势”而创作宣扬浮夸风的作品;待1962年大连会议召开,发现1958年的创作 路子也不对头,回去又写了篇反映现实矛盾的短篇小说《代理人》,结果又被指责犯了 “现实主义深化”和“写中间人物”的“右倾错误”⑦(注:康濯:《再谈革命的现实 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6期。)。这种左右摇摆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服从社会化流 行意识的表现。杨沫改写《青春之歌》也是著名一例。这种随波逐流,在当时长篇小说 创作中非常普遍。“流行意识”也可能含有合理看法。比如17年时期提倡作家“深入生 活”,从创作规律讲也正确,作家当然应该熟悉描写对象。左拉创作《金钱》时,就经 常跑到银行和证券交易所去观察交易活动。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竟然自备茶烟于 道旁,“见行者过,必强与语,搜奇说异,随人所知”⑧(注:邹涛:《三借庐笔谈》 ,转引自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219页。) 。此类深入生活的例子不胜枚举,关键在于“深入以后”能否独立思考。当流行意识不 让你写深入后的真实发现,再“深入”也是枉然。
新时期以前长篇小说往往引发的“轰动效应”,也和上述流行意识有密切关系。因为 当创作、出版、接受、评价都遵循一种思想规范和艺术准则时,它必然会形成一种声势 浩大的“大合唱”。毫无疑问,当长篇小说成为这种以社会宣传为目的的声势浩大的“ 社会大事”之后,人们便很少会去考虑作品是否能经受历史的检验、是否真正优秀等问 题。
二、个性意识与审美领域的拓展
新时期长篇小说尽管存在种种不尽如人意处,但获得了以往难以想象的审美自由。作 家和读者的个人审美情趣都不同,但唯有特立独行才能避免人云亦云的“鹦鹉学舌”。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个性意识的苏醒和强化,不仅成为一个革命性变化,而且有了明 显效果。首先的重大收获,我以为就是题材的解放和多样化。这种审美领域的拓展,实 际上意味着拓展了整个创作空间,显示了创作思想的解放和自由。
新时期长篇小说审美领域的拓展,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新时期初期曾有一个长篇小说出版热潮。从创作过程讲,此时出版的作品都是新时期 以前的创作,而有的已基本完成。如徐兴业的《金瓯缺》早在抗战时就有了创作准备。 以全国首届茅盾文学奖6部获奖作品即《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东方》(魏巍 )、《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将军吟》(莫应丰)、《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和 《芙蓉镇》(古华)来看,它们的创作思考都早在新时期以前。这次出版高潮的题材虽然 说不上真正的多样化,但大有扩展,具体内容也较多样而不再单调。这个阶段占有突出 地位的古代历史小说,除《李自成》第二卷继续首卷题材,刘亚洲的《陈胜》写秦末农 民起义,蒋和森的《风萧萧》写晚唐农民起义,徐兴业的《金瓯缺》展示两宋民族战史 与社会动乱,凌力的《星星草》写捻军转战九省的悲壮历程,任光椿的《戊戌喋血记》 写康梁维新运动和戊戌变法,端木蕻良出版了《曹雪芹》上卷,鲍昌的《庚子风云》和 冯骥才、李定兴的《义和拳》则描述了义和团运动。这些历史小说时间跨度大,画面较 广阔,题材含量也较丰富。
这之后尤其1985年后,长篇小说高潮迭起,题材选择也越来越丰富多彩。
历史题材方面,古代题材的长篇持续发展。凌力创作了《少年天子》、《康熙大帝》 ,杨书案则有《孔子》、《老子》、《庄子》,老作家王汝涛出版了百万字的《偏安恨 》,赵玫有“唐代女性三部曲”即《高阳公主》、《武则天》和《上官婉儿》,青年作 家吴因易埋头数年完成了系列长篇《宫闱惊变》、《开元盛世》、《魂销骊宫》和《天 宝狂飙》。这段时间还出现了影响很大的几部多卷本,如唐浩明和二月河作为后起的长 篇历史小说家,均起点很高、下笔不俗,前者的三卷本《曾国藩》和后者的《雍正王朝 》等“清帝系列”,都得好评。刘斯奋有展示晚明王室分崩离析和晚明社会风雨飘摇的 《白门柳》。熊召政的《张居正》之前两卷已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描写近现代历史风云和民族沧桑的长篇也为数不少,如《鸦片战争演义》(辛大明)、 《辛亥风云录》和《五四洪波曲》(任光椿)、《第一个总统》(黄继树等)、《危城》( 庞瑞垠)、《黄河东流去》(李准)、《战争和人》(王火)和王家斌的《百年海狼》等。 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和《血战黄沙》,则不仅填补了战争题材的空白,而且是一种艺 术开拓。
这个时期的“家族小说”也特别醒目。这些作品通过家族史、村落史或家庭史的历史 命运,借以展示民族种族的漫长岁月的历史变化。张炜的《古船》、《家族》和《九月 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丰乳肥臀》,李锐的《旧址 》,苏童的《米》,周大新的《有梦不觉夜长》,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阿来的《尘 埃落定》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等,都属此类。它们时间跨度长,历史意识和现实意 义也都非常突出。
描写中国当代社会重大变化的长篇,题材更是不拘一格。有四类题材特别醒目:
一是侧重揭示当代荒唐政治运动对人性的严重扭曲。这类作品,有古华的《芙蓉镇》 、戴厚英的《人啊,人!》、杨((的《洗澡》、从维熙的《走向混沌》三部曲、张抗抗 的《隐形伴侣》、蒋子龙的《蛇神》、老鬼的《血色黄昏》、铁凝的《玫瑰门》和张贤 亮的《我的菩提树》等。王蒙则以“季节系列”即《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 《狂欢的季节》和《踌躇的季节》坚持不懈地反思极“左”政治的危害。尤凤伟的《中 国1957》、方方的《乌泥湖年谱》和柯云路的《黑山堡纲鉴》等则是近年出版的这方面 的反思力作。
二是描述当代变革和改革者的长篇。整个80年代这是最引人注目的题材。这方面较有 影响的作品有张洁的《沉重的翅膀》、李国文的《花园街五号》、柯云路的《新星》和 《夜与昼》、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贾平凹的《浮躁》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 。
三是表现当代城市生活、都市文化和各色都市人的创作。刘心武的《钟鼓楼》和《风 过耳》、王安忆的《长恨歌》、贾平凹的《废都》、周劢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陈 染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和《玻璃虫》、邱华栋的《城市战车》、 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和王大进的《欲望之路》等都很引人注目。文学新人宁肯首发在 “新浪网”而后被《当代》转发的《蒙面之城》,则是网络文学得到纯文学刊物认可的 一个重要标志。
四是揭露新的权力矛盾和社会腐败现象。这类长篇小说创作主要出现在90年代,引人 注目的同时又颇多争议。这方面有影响的作品有:周梅森的《人间正道》和《中国制造 》,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钟道新的《权力的界面》,莫言的《酒国 》,张平的《抉择》和《十面埋伏》,王跃文的《国画》,李佩甫的《养的门》,南台 的《一朝县令》,珠海青年作家刘心武的《阿文的时代》,还有毕四海的《财富与人性 》等。
题材领域的开掘和拓展,不能不是长篇小说创作审美自由的重大收获之一。唯有审美 活动获得了自由和选择,才有可能激发作家选择题材的热情和拓展审美领域的意识。
三、艺术形式与表现手法的开放
在审美领域拓展的同时,艺术表现形式也显示了重要变化,相较以往有了重大突破。 英国著名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有个著名观点,即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也就是说艺 术形式不是外在“装饰”,而和作品内涵紧密联系。苏珊·朗格也曾指出:“所谓形式 ,就是作品内容的存在方式,包括内容的内部结构,形象的外观,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 。”⑨(注: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因此,艺术多样化不仅与形式意识有关,同时也表现为认识生活和把握世界的新的美学 形态的出现。
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的开放,主要带来了两个方面的艺术变革:
首先是创作方法的多样化。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创作方法,是现在能 够总结出的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三大创作方法。但具体情况其实远为复杂,因为这三种创 作方法,不仅每一种都可以进行新的变革和创造性运用,而且可以交叉使用,由此生发 演绎出极其丰富多彩的艺术表现。比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这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 ”代表作,实质上就是由多种创作方法融为一体而生发出来的一个奇妙艺术世界。看待 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方法的多样化,也应该持以开阔视野和灵活尺度,即应认识到很多 作品也是不拘一格而交叉性地运用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杂交体”。以《白鹿原》为例来 说,被称为“雄奇史诗”的它总体上是现实主义的写法,但同时充满了神奇的浪漫主义 色彩,现代主义的象征性也明显存在。创作方法显然不拘一格。其情节设置虽采用了传 统的纵向结构,但纵横捭阖大张大弛,并且融入了神秘传说和巫术色彩。创作方法的难 以归类,“先锋小说”创作更不用说。它们叙事视角的变换,主观感觉的大量渗入,时 空形式的变动不居,写实与写意的融合,使我们简直有些眼花缭乱。总之,创作方法改 变了过去的单一。
二是艺术表现手段和表现形式的多样化。这是创作主体意识个性化的又一必然结果。 它带来了长篇小说艺术多样化的大面积试验。一般认为,刘心武的《钟鼓楼》是新时期 长篇小说艺术形式变革的一个转化标志。但其创作,也正是张扬了主体个性的叙述。这 部作者自己说是采用了“桔瓣式”结构的作品,一改过去以一条情节主线为内容发展脉 络的传统情节模式,而是分散开来截取生活景观,从而将许多小故事组合成一幅既有联 系又相对独立的“文化生态画面”,这确实是一种大胆的艺术尝试。又如蒋子龙的《蛇 神》,也是打破了传统结构模式。它“拦腰”写起,然后在叙述中展开历史的回忆和现 实的行进,从而将人物的性格与灵魂叠印在不同时代的历史画面中予以透视。这样的创 作试验和艺术变革,在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中举不胜举。比如承前启后的一批知青作家 的作品,如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张抗抗的《隐形伴侣》、张承志的《心灵史》、韩 少功的《马桥词典》和王安忆的《流水二十章》等,都在长篇小说艺术形式上作了努力 的探索。年轻些的所谓“先锋小说家”,艺术形式的变革早已成为他们的一种创作标志 。如苏童的《米》和《我的帝王生涯》,格非的《敌人》和《欲望的旗帜》,余华的《 许三观卖血记》和《活着》,都是如此。被称为“新生代”的更年轻的作家,他们的长 篇小说创作更是以艺术变革而显示了个性化的艺术探索。
新时期长篇小说这两大艺术变革,既显示了个性化的自由,也是审美自由的必然收获 。比如1980年出版的《人啊,人!》,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视角,这在以前的当代长篇 小说中几乎不可能采用,因为那时根本不相信“我”这种个人叙述(而且还要看这个“ 我”是什么社会身份)能表现“宏伟时代”。该作中大量的人物心理活动描写,也是以 往少见的个人感觉化的体现。在上述很多作品中,我们都能明显感觉到“个人的声音” 多了,不像以往只听到规范化的“时代声音”、“上级声音”和“群体声音”。这种变 化在80年代中期以后更加明朗。一个时代的长篇小说如果只有“上级声音”,可想而知 会出现什么样的艺术。
四、关于个性意识的问题
集体意识与个性意识都是创作主体意识的不同表现。个性意识张扬的是作家的自主和 独立,集体意识强调的是服从流行意志和群体意识。审美立足点不同,实际带来创作主 体精神境界的总体差异。从最基本的创作立场讲,毫无疑问,必须提倡“个性意识”的 写作立场,因为作家坚持独立思考的创作立场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品格。
我们强调个性意识的必要,决不是说个性意识就毫无约束。比如作家创作,当然应该 关注人民命运、社会问题、时代现象等等,也必须注意大众的审美需求。只是对群体问 题的思考,应该有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能按照“长官意志”来创作。贾 平凹在谈到《浮躁》的创作时曾感慨道:“如果说,作家职业是最易心灵自在,相反的 ,也最易导致做作——好作家和劣作家就这么分野了。”⑩(注:贾平凹:《四十岁说 》,《浮躁·代序》,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这说得很有道理。“个性化”固然必要 ,但并不意味着创作的一定成功。把握不当,就会成为“劣作家”。或者说,“劣作家 ”的个性意识很容易变成“真理往前走了一步”。
比如新时期长篇小说的“个人化”写作,有些“个人化”的作品就并不怎么样,有视 野狭隘、情感琐碎、艺术矫揉、自我封闭等明显缺陷。就以创作个性意识很突出的王朔 来说,其作品应该说都具有很突出的个人特点,但有的成功有的则失败。我认为这就和 作家对“个人意识”的理解和把握有密切关系。尤其是在具体创作中,如何使“个人意 识”的思考更有价值并且尽可能出色地表达出来,就更是关键所在。又如余华,也是一 位个性特征非常突出的作家,但他的个性意识也是不断“更新”的。如《活着》就与他 以往的小说有很大差异,却获得了极大成功。这说明个性意识确实有个“优化”问题。
由此还想说说卫慧和棉棉的创作。如果说她们的出名确实带有阴差阳错的原因,她们 的作品也大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描述那样的“另类题材”,表现那 样的所谓“另类生活”,则无疑是审美自由和个性创作的结果。从文学创作的必须多元 化和允许自由来说,“另类作家”的出现应该是个进步。然而“另类作家”的个性化也 应该有所注意,应该使自己的个性意识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和更出色的艺术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