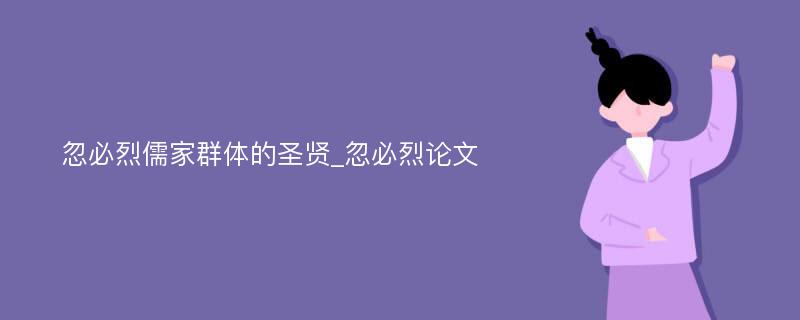
忽必烈藩府儒士群体的圣贤气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士论文,圣贤论文,气象论文,群体论文,忽必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10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87(2016)02-0034-07 元世祖忽必烈于蒙哥汗元年(1251),受命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金莲川,积极延揽藩府旧臣与四方文学之士,一时间潜邸之中人才济济,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儒士群体①,为他日后继承汗位,成就大业打下了基础。忽必烈幕府儒臣,在金元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由于背负着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对圣贤气象提出了新的诠释,更加突出了士人品格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他们所追求的圣贤气象彰显的是一种社会群体价值意识,即关怀社会、执着仁义、心忧天下的价值取向,欲借出仕而行“道”,以推行汉法、天下安泰为己任,且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经世济民的活动。同时,他们以其独特的儒者气质与人格追求凸显了儒家所追求的“圣贤气象”。这不仅是中国古代独特的一种“学者——官僚”社会阶层的精神表达,也是对宋儒所推崇的以圣贤的人格理想作为自己人生目标的继承和发展。藩府儒臣继承了宋儒所推崇的“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普遍地追求个人的身心安顿、洒落胸襟、闲适安乐及“孔颜乐处”的精神超越。 一、以天下安泰为己任 窝阔台汗六年(1234),蒙古军攻克蔡州(今河南),金朝覆亡。这对广大中原百姓来说,是一场灾难,他们命运悲惨,困苦不堪。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士人及百姓不得不再次面对蒙古代金之际华夷观念的困惑与调适。以往通过读书、科举、求仕进为生的中原士大夫也丧失了传统的优越地位,大量死亡、四处流徙、迹身民间,所受打击尤为惨重,正所谓“金季丧乱,士失所业”(王恽《故翰林学士紫山胡公祠堂记》)[1]卷40。他们作诗吟赋、科举提名、进入仕途的生活方式被彻底改变,命运同普通民众并没有多少区别。前朝经过几代人积累发展起来的文化成果,如学校,在战争中几经涂炭,“自经大变,学校尽废,偶脱于煨烬之余者,百不一二存焉”(段成己《河津县儒学记》)[2]215,典籍也在战火中焚毁殆尽,“中原新经大乱,文籍化为灰烬”(《三史质疑》)[3]卷25。面对中原这种干戈不断、百姓流离失所、文化遭受破坏的现状,他们想改变,但宋金政权已经不再给他们任何希望。 宋理学家张载认为士人应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语录中》),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身逢金元易代之际,忧世伤生,充满了对天下一统的期待,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更加突出了儒家核心价值中的关怀社会、心忧天下的精神。他们承继了宋儒普遍倡导的一种理想人格,即“圣贤气象”,历史责任感和民族忧患意识使他们更以天下安泰为己任。在这种社会现状下,如归隐田园明哲保身,执守儒家人文价值的理想,或者皓首穷经去探究性命之蕴以及人心精微的儒学理论,只能是日益脱离社会现实而无法改变现状,因而,积极出仕忽必烈藩府,辅佐忽必烈推行汉法,参加治国平天下经世济民的活动,自然和当时的社会时代背景以及北方士人心态有一定关系。其一,由于“辽金以来,以宋为正朔的观念在北方淡漠已久”[4]158,“长城一线虽然分别夷夏两个天下,但外族入居中国,不能严分内外,也是长期的历史事实。华北近边州郡的夷夏观,宜不同于中原内地,而胡汉之畛在社会上也淡于政治上。”[5]15其二,北方地区契丹、女真、汉族长期融合,“华夷同风”早已成为事实,北方文人以汉族为正统的观念相对淡化,他们的现实政治活动已经冲破了传统的夷夏观念,并不认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就不是正统。因而,藩府儒臣根据当时社会的变迁,对“圣贤气象”作出了新的诠释,发展开拓与守护了宋儒所倡导的“圣贤气象”,不偏于理论而务实际重实行,关注世事,气局雄大,继承了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 首先,儒家“身任天下”精神更多地体现在他们心忧天下,救世行道的具体实践中,他们已经认识到了空谈心性与埋头章句对国计民生毫无用处。面对漠北蒙古军队的冲击,中原地区民不聊生的现状,必须摒弃夷夏有别的狭隘民族观念,不以华夷、血统、辖地的位置及广狭等论正统,须建立新的正统观和华夷观。在正统和华夷问题上,藩府儒臣杨奂早在《正统八例总序》中已经非常鲜明地提出了“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的观点,这一说法对藩府儒臣以及北方文人产生了不小影响。继杨奂之后,藩府理学家郝经结合当时的社会实际,总结和发展了儒家“用夏变夷”的思想,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命题:“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郝经这一观点正合时宜,完全突破了“严夏夷之大防”的狭隘民族观,最重要的贡献是解决了汉族文人囿于传统的正统观及华夷界限而难以适从的困惑,为汉族文人出仕蒙古族建立的元政权提供了理论支持,也从理论上为蒙古族接受华夏文化、蒙元政权入主中原,提供了合理、合法的根据。郝经观点非常明确:衡量“中国之主”有两个标准,一是能用士,二是能行中国之道,即汉法,只要符合这两个标准,则是“中国之主”。无论汉族、女真、蒙古的统治者,只要能重用士大夫,能行圣人之道,就可以成为中国正统的君主。他在《涿郡汉昭烈皇帝庙碑》一文中进一步表明了自己对于正统的认识:“王统系于天命,天命系于人心。人心之去就,即天命之绝续,统体存亡于是乎在。”[6]卷33认为道义的体现、人心的归向才是最为根本的因素,更进一步印证了上述观点。杨奂与郝经所重视的不在于做皇帝的人是少数民族(即所谓夷),还是汉族(华),而是能否采用“汉法”,实行王道,这就超越了从前以血缘、民族、天命、德运、地域、国势等因素来论正统的思维模式,更具理性色彩和进步意义。正因为此,才能有大批文士全面性地参与辅助忽必烈以汉法治理汉地,希望以“道”为帝王师,努力将道义理想贯彻到现实的政治中,为天下制法,为建立大一统帝国的政权、王权和政教秩序服务。 许衡字仲平,号鲁斋,有《鲁斋遗书》。作为一代大儒,他在《时务五事》中说“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国朝仍处远漠,无事论此。必若今日形势,非用汉法不可也。”这里的“汉法”,即是“中国之道”和“中国之法”,他和郝经的主张一致,都强调“汉法”和“中国之道”是“北方奄有中夏”和成为“中国主”的关键所在。对华夷观,许衡是这样阐释的:人为地划分“夷”和“夏”,厚此薄彼甚或尊此贬彼,均有悖于儒家文化大义:“元者善之长也,先儒训之为大,徐思之,意味深长。盖不大则藩篱窘束,一膜之外,便为胡越,其乖隔分争,无有已时。何者?所谓善,大则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无所往而不为善也。”[7]卷2要一视同仁,不要自设藩篱,窘束一膜之外而只看到本民族的利益而不知平等对待其他民族,这本是与儒家“天下一家,一视同仁”思想背道而驰的,如天地生育长养万物之心一样,只要有爱物爱人的仁爱之心便和天地之心相似,天下本一家,自然会打破狭隘的民族观。许衡以儒家仁爱之心阐释其民族整体观,正如他在《病中杂言》之四所说:“直须眼孔大如轮,照得前途远更真。光景百年都是我,华夷千载亦皆人”[7]卷11。 夷夏一体,无论华夏还是夷狄,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本无天分高低之分,如果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那么一切障碍都会排除了。许衡之论比之郝经的华夷观,更加人性化,也更透脱。因而,他才能更好地发挥儒学的社会作用,亲身实践其经世致用、富国安民的主张,为国家、为百姓做一番大事业,为元代后来的知识分子树立典范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中国的政治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纲常解纽、礼崩乐坏的特殊时期,藩府儒士文人执著追求儒家“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并非不与世事,而是实现儒学社会价值关怀,以尧、舜、文、武、周公等圣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完成博施济众事业的理想。“以天下为己任”,这些藩府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他们摒弃了夷夏有别的狭隘观念,“华夷千载亦皆人”理论的形成,有着时代因素,也有着藩府文人共同的目标和心态,在藩府儒士看来,以蒙古族的军事实力,统一天下指日可待,而在政治、文化等方面使其“奄有中夏”,成为“中国主”则是需要付出努力的,因而,就需要突破以前狭隘的民族观,出仕而行“道”,即弘扬汉文化,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中原地区。元之立国,也即实现了藩府文人以汉法治理中原的目标,在《中统建元诏》中明确表示:“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即采用“汉法”,不单纯是蒙古民族的国家,而是大一统思想支配下的中原封建王朝的继续,依然是继承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制度,年号“中统”,意思就是中朝正统,以承接中原王朝的正统自命。 其次,因为蒙古族在灭金践宋战争中对几千年延续的中原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破坏,面临文化危亡,为适应当时形势让蒙古贵族行汉法以建立大一统帝国的需要,文人们的行道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较之以往时代反倒更为强烈。忽必烈藩府士大夫以效法圣贤为自己的榜样,忧患天下、承担道义,出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以兼济天下、拯救生民为己任。当忽必烈广泛延揽人才之时,他们认为忽必烈是贤明之主,于是乘势而动,抓住历史发展趋势形成的契机,入侍忽必烈藩府,不是为了“耀后世而垂无穷”(欧阳修《相州昼锦堂记》),而是借出仕以行“道”,辅佐忽必烈以汉法治理中原地区,以维系华夏文化。 许衡出身于农家,生于乱世,深知下层百姓生活之苦,为避兵乱,长期流离颠沛,生活无着,后又经逃难之苦,在离乱之时,“家贫躬耕,粟熟则食,粟不熟则食糠麸菜茹”[8]3717。许衡坚持北方学术重治生的精神,提出“为学者治生最为先务,苟生理不足,则于为学之道有所妨”(《通鉴》)[7]卷13的观点,非常先进,也相当深刻。他认为士人所首先应该重视的是以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为前提的,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放在第一位,不为百姓的生存和生活考虑,一味治学,而仅仅将伦理活动、政治活动放在首位,忽视经济活动,则不是儒家治国的道理。因而,许衡能“慨然以道为己任”,忧患民生,“以扶人极,振人纲为心”(《祭鲁斋先生文》)[9]卷48,居朝廷要职,凡“十被召旨”(《考岁略》)[7]卷13,为忽必烈顾问,以其学识和才能影响了元朝的政治和文化。 郝经秉承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以天下一统、生民太平、宏张纲纪为己任。他对战乱之时的百姓殷殷关注,在《劝农》诗序写道:“兵乱以来,四民失业,农病为甚。因读渊明劝农之作,感而赋此。”面对存在的社会危机,诗人充满了惆怅忧患之慨,诗中这样写:“爰自兵兴,鱼涸处陆……苛政虫胃起,纷更弗久。饥肠曷充?独耕无耦……食众农寡,安得不匮。有年无种,丰获安冀。盗贼群起,馁死并至……农为匪民,犯绳越轨。本既凋伤,政何由美?”郝经对国家民族有着很深的忧患感,读他的这首诗,顿觉一种强烈的时代感扑面而来,他对社会混乱、盗贼横行、田园荒芜、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痛心且有着清醒的认识。郝经是一个坚持儒家道德观念的人,思“大益于世”,博览群书,经历了朝代更迭,面对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战乱和动荡,常以“道济天下为己任”[6]卷首,从他的文章中常看到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的言辞。在《河东罪言》一文中他写道:“国家光有天下五十余年,包括绵长亘数万里,尺棰所及,莫不臣服,惜乎纲纪未尽立,法度未尽举,治道未尽行,天之所与者未尽应,人之所望者未尽允也。比年以来。关右、河南,北之河朔,少见治具,而河朔之不治者,河东河阳为尤甚。”[6]卷32指出汉地久未治理,困弊已极的情况。郝经出于对民生困苦的关切,又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于现实的积极态度”,在他看来,“越是乱世,越是需要士人挺身而出的时候”[10]183,这促使他入侍忽必烈藩府,辅佐忽必烈在中原地区采行汉法,而且其政见多为采纳。同时,郝经又深谙军事谋略,极有军事眼光,曾上《东师议》,力主与南宋议和。当他得知元宪宗蒙哥汗死讯后,又向忽必烈上《班师议》。郝经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赴南宋和谈,在出使南宋推动议和的同时,将入宋境,他还提出了针对南宋的布防建议及伐宋方略,多被忽必烈采纳。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其学术则贯通儒释道三家思想,涵养深厚。早年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曾做过节度使府令史、藩府重要谋士、朝廷重臣。在他的诗词中,也常体现对民生疾苦的关心,不能为民解忧是他的遗憾:“识字岂知为物忌,读书空想解民忧”(《对镜》)[11]卷1;希望平定干戈,让百姓都能安居乐业:“民人各得安家住,辞气总如平日和。箪食壶浆迎马首,汤征元不弄干戈”(《峡西》)[11]卷1;虽然他满口说“致主泽民非我辈”(《倚楼》)[11]卷3,但所作多是致主泽民之事,希望以自己所尊崇的儒家学说能够最大可能地实现其政治价值,功施于社稷,这也是从孔子以来儒家最重要的理想。 忽必烈藩府儒士发挥治国平天下经世济民的精神影响了元朝政治秩序的开端。如姚枢、刘秉忠、徐世隆、张文谦等从征大理,在元初襄赞军事的同时,不仅从战略全局谋划战争,而且用各种方法游说忽必烈,希望在战争中保全民命,并亲临前线搜救儒士,以改变蒙古族屠城政策与劫掠的本性。由于藩府儒士深谙军事谋略,了解汉地世情,在元初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又多方努力劝解忽必烈禁屠城、不嗜杀,故而逐渐改变了蒙古军队的屠戮政策,减少了战争伤亡,加快了战争进程,也为忽必烈赢得了民心。他们还保护了先进的生产力和先进的文化,在保护中原文化和文物免遭战争破坏,修复孔庙、尊孔,建立学校,推动理学的传播和发展等方面均起了很大作用。藩府儒士在辅助忽必烈实施汉法和元初的军事行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诸如以汉法治理汉地,为忽必烈争得帝位,对付阿里不哥的战争等,逐渐让忽必烈意识到以马上得天下,但不能以马上治理天下的道理。忽必烈开始以中原地区历代相沿的官仪制度和孔孟儒学的治国方略来治理国家。藩府文士为元代统治者制订立国规模,为元代多民族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帝国建立起一套适用的统治机构、典章制度与驾御权术。在社会历史变迁之际,儒士要履践自身的使命,即对道的弘扬,激发了忽必烈幕府儒臣深隐于心的儒家文化价值取向,发展开拓与守护了宋儒所倡导的“圣贤气象”,务实际重实行,深深地影响到他们的立身处世和人生追求,促使他们在社会秩序处于危机时,超越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提升为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从这一点入手,对于我们从更深层的文化心理去重新审视元初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道”的彰显与光风霁月的“孔颜乐处” 忽必烈藩府士大夫,多为当朝有影响之官员,从他们的理论阐述、文化心态以及实际行动中,都表现出了较为浓重的圣贤情结。从他们身上可以充分领略到“圣贤气象”的内在的精神境界,它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模式,如峨冠博带、规行矩步、正襟危坐、满面生春、一团和气,更是儒士的一种精神修养,一种由内而外渗透出的一种气度,即是对儒家“道”的彰显。有对社会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与道义承担的精神,还有宋儒所推崇的“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黄庭坚《濂溪诗序》)的人生境界。 姚枢字公茂,号敬斋,又号雪斋,有《雪斋集》,是忽必烈藩府群儒之首。他大体上可作为胸中洒落之儒家圣贤代表,具有统一的国家观念,提倡崇道立德、仁义为本的政治原则,主张以古之圣王之道为元朝进行制度设计。最让人钦佩的还是他的胸襟、气度,以及为人,时人评价他“天资含宏而仁恕,恭敏而勤俭,理生惟务本实,不事末作。未尝疑人欺已,有负其德,亦不留怨胸中。忧患之来,不见颜色”[7]卷13,实乃一个宽厚长者,是为孔子所谓“不逆诈,不亿不信”之先觉之贤与坦荡君子。从姚枢现有的诗中可以感受中国文化人格的大义所在,如其次刘秉忠韵而作《聪仲晦古意廿一首爱而和之仍次其韵》(其九):“夷齐顾名节,不食饿首阳。尚父应天讨,奋时清渭旁。心迹异天壤,日月同辉光。道义有如此,人惟重行藏。”[12]129其诗意在阐扬儒家精神,诗风则有圣贤气象,如混沌未开,有一股自我超越的大我之境,散发出美的光辉,用纯然太和来形容恰如其分。 许衡无疑是元代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一生风范,不仅笃学实行,且本儒家之民本爱民思想,引申孟子“民重君轻”之言,加之其敢言直谏,有唐魏征之风,辨奸批逆,浩然无畏,进退之际,又坚持原则,一丝不苟,凛然不可以利禄诱、威武屈,德望冠绝,为有元一代之楷模。其弟子姚燧《左丞许衡赠官制》有一段对许衡很精到的评价:“玉裕而金相,准平而绳直,出处则惟义所在,言动亦以礼自持。休休焉有容,属属乎其敬。人能弘道,惟朝闻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昼诵夜思之不得。行己似秋霜烈日,化人如时雨和风。来席下之抠衣,满户外者列屦。”[13]9 郝经以节义著称,人比之汉苏武。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郝经以翰林侍读学士充国信使使宋,以求两朝和平,却为宋奸相贾似道拘留真州16年。至元十二年(1275),元军渡江,始得还归,不久病故。郝经时遇难求,命运多蹇,原本怀有济世救民、匡扶天下之心,却由使臣沦为羁臣,失去了做人最基本的自由,但他以儒家忠节观自守,严守了儒家节义之士的道德操守,在被羁押的情况下保持人格道义的独立与尊严。郝经以自己的思想和人格丰富和诠释儒家道义,通过个人的自省自得把“道”落实到具体的人生实践中,和他一同使宋被拘的苟宗道称他“与人结交,始终以诚。而又喜交游,好施与,乐为善事。受人之恩,必切切思报,虽小而不忘。”[6]卷首不愧是一位至诚君子。 藩府文人不断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完善自己的人格建构,从而完成君子修齐治平的使命。张文谦,字仲谦,为人谦恭笃实,外和内刚,天性好贤乐善,而且是“人有寸美,必极口称道”。张文谦善于举荐贤才,为朝廷推举品行优良、德才兼备之士,“遭际以来,每以荐达士类为己任”。他举贤并非为了荣誉名声,完全是为了国家百姓,也从不担心为所荐举的人才连累。随着他对社会历史人生认识与体验的加深以及士人、儒士意识的强化,行事更为磊落,曾很坦然地对那些劝他应谨慎行事的人说:“人才何尝累已,第患鉴裁未明,有遗才耳,且人臣以荐贤为职,岂得避纤芥之嫌而负国蔽善乎!”[14]104一生举贤颇多,当时扬历中外者,多为文谦所举荐。藩府理学家窦默,也是一生磊落,为人朴厚,耿介贞刚,以道德模范和儒家所追求的严肃庄重、耿介忠贞的士人操守自期自律。苏天爵曾这样评价他:“乐易与人交,不立崖岸,平居不好臧否人物,时人不过以柔懦书生待,其关国家大计,则面斥权贵不少挠,虽古之汲黯、朱云无以加,盖胸中所学纯正,其志有所操守,故见于事业如此。”[15]卷8忽必烈即位后重用王文统,只有窦默上书直言进谏,他还斥责王文统曰:“此人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8]3731像这种率直耿贞的性格,很是难得。 另外,忽必烈藩府儒家士大夫也继承了宋儒洒落自得、安贫乐道、闲适安乐的精神气度,普遍地追求“孔颜乐处”。窦默虚静以守其心,与周敦颐所追求的“胸中洒然如光风霁月”境界十分接近,令同僚刘秉忠仰慕非常,敬重又加,不禁写诗赞其旷达平和、超然自得的态度和心境:“富贵不求惊见擢,田园成趣喜归闲。一心止水常平湛,万事浮云任往还。”(刘秉忠《大理途中寄窦侍讲先生二首》)[11]卷2这种超然与洒落,在畏兀儿儒臣廉希宪身上也有所体现。西域色目文人侍从廉希宪,一名忻都,字善用,号野云。廉希宪幼时基本上接受的是儒家教育,“延明师,教之以经”,师从名儒王鹗,是一个深受儒学影响的色目文人。他嗜好读书,被忽必烈称为“廉孟子”。从其词作中亦可领略其悠游之境,如其《水调歌头·读书岩》: 杜陵佳丽地,千古尽英游。云烟去天尺五,绣阁倚朱楼。碧草荒岩五亩,翠霭丹崖百尺,宇宙为吾留。读书名始起,万古入冥搜。凤池崇,金谷树,一浮鸥。彭殇尔能何许,也欲接余眸。唤起终南灵与,商略昔时名物,谁劣复谁优。白鹿庐山梦,颉颃天地秋[16]721。 显然,廉希宪追寻的“孔颜乐处”,的的确确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读书遣兴,自在逍遥,碧草荒岩,翠霭丹崖,于萧闲中享受诗书其间的乐趣,沉浸于可以陶情冶性的诗文之中,使人自然体会到词人的清静、萧闲、恬淡,大有程颢的“我心处处自优游”之意,是一种身心舒泰、从容洒落的人生境界,显示了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一种道德修养的内在自觉。 许衡所追求的也是孔颜之乐、曾点之志,他重视内心的充盈和满足,追求“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的内心愉悦,还有那种“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超越一切世俗烦恼的快乐满足。他坦言:“我生爱林泉,俗事常鞅掌”(《游黄华》),虚静恬淡,追求一种内证之乐,要达到这种境界。他乐意放弃顾影虚名,“吾道真如千里重,虚名冷笑一毫轻”,与道同在,心灵便得以滋养、充实、慰藉、安顿,即使过着“五亩桑麻舍前后,两行花竹路西东。幽人自爱幽居好,未肯埋身利害中”(《用吴行甫韵》)的清贫生活,也能深深体验回归于生活、生命本身的悦乐之中,确实是惟有乐道,才能安贫。从他的诗中,“桃溪风景写横披,浑似秦人避乱时。万树春红罗锦绮,一湾晴碧卷琉璃。饮中更听琴声雅,静里初无俗事羁。他日君侯归此隐,肯容闲客日追随。”(《题武郎中桃溪归隐图五首》其三)[7]卷11我们体味到诗人灵魂深处构建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乐园,完全摆脱了个人名利,贫富穷达与诗人无关,似乎更高于邵雍“安乐窝中事事无”的自得洒落。诗中是一种皈依自然的真乐,不在于那烂熳花千树,萦纡水一湾的美景,也不是鸡鸣犬吠,男耕女织的生活,而是那种悠闲,“饮中更听琴声雅,静里初无俗事羁”,确实是摆脱尘俗、忘情林泉。在诗中我们体验到一种简单的幸福,一种感受,一种精神的体验,对简简单单生活感到愉快的满足感。 郝经又何尝没有逍遥出世,其乐融融的欢快。如其《归园田居六首》诗:“童穉游鹿豕,野逸便深山。幽居远世尘,颢颢羲皇年。卢溪郁岩阿,缭壁涵清渊。征君始真隐,种玉开石田。幽人竞卜邻,联落崎阻间。竹木茅舍边,桑麻橘篱前。三春牡丹雨,十月梅花烟。孤云出遥岑,颓日下层巅。性与万化寂,身同天地闲。一从入絷羁,趋蹶宁复然?”(其一)[6]卷6诗人借助远离世尘深山田园,来构筑一个静绝尘氛的理想境界,足以让人超越悲情,获得灵魂的归依。精神的安宁,是一种超拔世俗的人生情态,绝非凡人所能及。郝经构建了自己独特的随缘自适、自由无待的精神天地,希冀获得灵魂的宁静与愉悦。林语堂先生曾说:“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始终是一个对人生有一种建筑在明慧的悟性上的达观”,“人生有时颇感寂寞,或遇到危难之境,人之心灵,却能发出妙用,一笑置之,于是又轻松下来。”[17]52郝经被囚居真州数载,历尽磨难,能够在对世俗的得失、毁誉、是非、生死的超脱中获得心灵自由、达到精神愉悦的境界确实不易。他渴望还乡归隐田园,去田园农村安顿他珍爱的有限生命,享受现世的欢愉,不失为传统中国儒学的理念——重视内心的充盈和满足的最好演绎,只有重视心性涵养工夫,才能达到这种对自我、对现实的一种超越。 追求事功并非以无条件地追求利益为目的,如果具有孔子之乐如“回不改其乐”和“吾与点也”的这种境界,即一种超越富贵名利而达到的精神状态,就不会在意于富贵贫贱的生存状态,就会超越感性的欲求,在理想的追求中达到精神上的满足,将精神的升华提到了突出的地位。刘秉忠居于忽必烈诸谋臣之首,谋划军政机要二十多年,其后授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为忽必烈的佐命之臣,“虽位极人臣,而斋居蔬食,终日澹然,不异平昔。”刘秉忠对名利富贵,完全能超然物外,认为“熏天富贵等浮云”(刘秉忠《守常二首》其二),“名利场中无所求”(刘秉忠《春闲遣兴》)。他闲适从容、内心平和愉悦,不为物欲所累,不为外物所累,完全超然于富贵贫贱、荣辱进退,是一种自得的心灵境界,达到了自由自觉的超然。其存心养性的工夫达到的自由自觉的境界,从他诗词中也可以领略到。如刘秉忠《秋江渔父图》一诗中:“白蘋红蓼满沧洲,江上青峰倒玉楼。出没不拘同水鸭,往来无系伴沙鸥。烟波围绕几渔舍,天地横斜一钓舟。蓑笠为渠相盖管,潇潇风雨不胜秋。”[11]卷2可见诗人心胸透脱,俯仰宇宙之间,人心与水穷云起之景的默契。只有能够洞悉世事人情的变化,获得真正的大道,超越人性欲望对自己的束缚,才能达到这种恬淡虚静,这就是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快乐。 在金元易代的特殊历史时期,忽必烈藩府儒士群体执著追求儒家圣贤气象的人格理想,不仅积极入世,将经世济民看作是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对元初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学术、文学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少贡献,而且他们把“圣贤气象”融贯到日常生活、伦理道德乃至家国天下,以希圣希贤自期自律,体现了儒家所追求的人格风范,以光风霁月或春阳和煦的特有境界,涵育成令人景仰的人格风范。同时,藩府儒臣推崇孔颜之乐,但并不过于强调个人身心的自在、闲适、舒泰、喜乐,彰显的更是一种社会群体价值意识,这是他们清醒、理性、自主、自觉的选择,也对儒者所追求的圣贤气象作出了新的诠释。 注释: ①忽必烈金莲川藩府儒士群体是一个较复杂的文人群,来源广泛,文化渊源和师承各异。他们大多是金末山东、山西、陕西、河北等不同地域的儒学、文学等领域的精英,包括:姚枢、许衡、窦默、郝经、智迂、刘秉忠、刘秉恕、张文谦、张易、王恂、赵秉温、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刘肃、张德辉、贾居贞、张礎、周惠、王鹗、杨奂、赵璧、李简、张耕、杨惟中、宋衜、杨果、马亨、李克忠、杜思敬、周定甫、陈思济、王博文、寇元德、王利用、李德辉、董文炳、董文忠、董文用、赵炳、高良弼、许国祯、许扆、谭澄、柴祯、姚天福、赵弼、崔斌、阔阔、脱脱、秃忽鲁、乃燕、霸突鲁、孟速思、廉希宪、赵良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