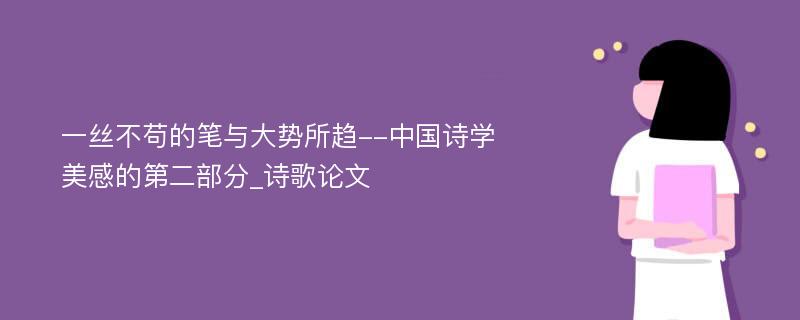
精微之笔与广大之势——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精微论文,诗学论文,之二论文,之势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4)04-0090-10 对我们这些中华民族的苗裔而言,中国古代诗歌实在是一笔硕大无比而又弥足珍贵的遗产。它启迪着我们的智慧,滋育着我们的心灵,培养着我们的美感,陶冶着我们的情操。从审美的意义上来感悟中国古代诗歌作品和诗学理论,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非常有益的裨补。审美是令人超越的,是使人们从红尘和物欲中升华出来的佳径。读着那些沁人心脾的优美而宏壮的诗篇,领悟着那些透彻的诗学洞见,不仅使我们感受到古代诗人和诗论家们的脉动,且又进入到一个莹彻而邃远的世界。我们轻吟着那些华章,被诗中那些精深微妙的意象所吸引,新奇而鲜明的内在视像如在目前;同时,我们又置身于广大无垠、深邃无比的场域。而这二者又是如此和谐地融合在同一篇什之中。中国诗学中有许多关于“精微”(或“精深”“微至”等)和“广大”(或“广远”)的论述,正是对这种诗歌创作风貌的描述。 中国古代本无“美学”一门,然体现着审美意识、审美标准的诗论却俯拾即是。美学的理论大厦要靠学者们的辛勤建构,如欲使“中国美学”不断地敞亮于世界美学之林,披沙拣金的工作应该持之以恒!关于“精微”和“广大”的话题尚未得到学界的梳理,然这些“精金美玉”恰可为中国美学和文论的丰富与提升增添资源。因为“精微”主要是指“言内”的描写,“广大”主要是指“言外”的场域,故我以“精微之笔”和“广大之势”表述之,准确与否尚待切磋琢磨。 中国古典诗学理论非常注重意境的创造,意境论成为中国诗学最为核心的范畴之一。意境是超越于意象之上的整体审美境界,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的话说,就是“境生于象外”。这种超乎于诗中有形描写的意境,不仅是“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而且具有充满生命力的势能。诗论家所说的“尺幅万里”,“广大”或“广远”,都指诗歌作品的这种品性。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第一品“雄浑”,虽是形容诗的刚健雄浑之风,其实也是揭示了这种“广大”之境:“大用外腓,真体内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荒荒油云,寥寥长风。超以象外,得其环中。持之匪强,来之无穷。”中国古代诗论中对于“广大”或“广远”的论述是颇为普遍的。《文赋》《文心雕龙》《二十四诗品》《石林诗话》《姜斋诗话》等诗论中都不乏其论;而中国诗学中在创作论上的另一种与之相关的说法则是“精微”。“精微”与“广大”是相辅相成的。“精微”是指诗歌意象描写刻画的精致入微。无“精微”无以致“广大”,无“广大”也无以显“精微”。清代思想家、诗论家王夫之论诗最重“精微”与“广大”融为一体的诗境,如他评价谢灵运《登池上楼》云:“始终五转折,融成一片,天与造之,神与运之。呜呼,不可知已!‘池塘生春草’,且从上下前后左右看取,风日云物,气序怀抱,无不显者,较‘蝴蝶飞南园’之仅为透脱语,尤广远而微至。”①评《登上戍石鼓山诗》云:“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②船山是以谢诗为标本来表达他的诗歌审美标准。本文拟对中国古代诗学中的“精微之笔”和“广大之势”这一话题加以推阐,呈现其存在,发掘其意义,阐释其内蕴。 关于精微,这在古代诗论中多有论及,却没有什么精确的界定,相关的说法还有不少,如“精深”“微至”等等。在理论上也罕有阐发,从美学角度也未尝得到足够的重视,而我认为“精微”是可以上升到一个美学范畴加以分析和建构的。中华美学传统对于诗歌的“言外之意”特别推崇,对于诗歌表现的“言内之笔”却难以得到与前者相匹配的重视。 “精微”指诗人对于物理或事态的精致而生动的表现,或者表现为对人的情感、义理的微妙呈现。“精微”是指诗人在文本中精深微妙的刻画描绘。通过文字的媒介,把所写的事物表现得栩栩如生,在读者头脑中呈现鲜明活跃的内在视像,所谓“状溢目前”是也。笔者将“内在视像”视为文学的最主要的审美特征之一,并有专文以阐述之。其中谈及:“何谓‘内在视像’?这里是指文学语言在文学作品中所描绘的可以呈现于读者头脑中的具有内在视觉效果的艺术形象,作为文学审美活动而言,这是实现其审美功能的最为关键的环节。甚至可以说,这种内在视像,对于读者来说,是真正的审美对象,至少是审美对象的核心要素。”③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精微之笔”,突出的一点便在于诗人通过诗歌意象的创造,能使读者头脑中产生充盈的内在视像。 北宋诗坛魁首欧阳修曾对当时的两个著名诗人梅尧臣和苏舜钦有这样的定评: 圣俞(梅尧臣字)、子美(苏舜钦字)齐名于一时,而二家诗体特异。子美笔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各极所长,虽善论者不能优劣也。余尝于《水谷夜行诗略道其一二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噫,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霈。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列珠玑,一一难拣汰。梅翁事清切,石齿濑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精新,心意虽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嘬。又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黄以气轹,举世徒惊骇。梅穷独我知,古货今难卖。”语虽非工,谓粗得其仿佛,然不能优劣之也。④ 欧阳修对梅尧臣、苏舜钦的诗风加以比较,以“精微”归之于梅,以“豪隽”归之于苏。而梅尧臣的诗作,是以能够生动呈现事物的情状为特征的。梅氏于此有自觉的理论意识,欧阳修转述梅尧臣论诗之语说:“圣俞尝语余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⑤《六一诗话》中称许梅尧臣者颇多,并以“精微”作为对梅尧臣诗的评价。“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适可作为梅诗精微的注脚。《诗人玉屑》引《笔谈》云:“小律虽末技,工之不造微,不足以名家。唐人皆尽一生之业为之,至于字字皆炼,得之甚艰,但患观者灭裂,不见其工耳。若景意纵完,一读便尽,此类最易为人激赏,乃诗之折杨黄花也。譬若三馆楷书,不可谓不精丽,求其佳处,到死无一笔,此病最难为医也。”⑥“造微”也即臻于精微。元代韦居安评苏轼诗:“运意琢句,造微入妙,极其形容之工。”⑦诗论家多有以“精微”“精深”赞赏谢灵运之诗,如王夫之、方东树等。王夫之有关论述后面涉及较多,而方东树亦认为,谢诗精深而兼华妙。⑧又高度评价谢诗“阔大精实,义理周足,他人所不能到”。“造语精好,如精金在镕”,“独从容细意,不可及处”⑨。明代诗论家陆时雍亦以精微评诗,其论何逊诗风:“何逊诗,语语实际,了无滞色。其探景每入幽微,语气悠柔,读之殊不缠绵之至。”⑩清人田雯评王维诗云:“摩诘恬洁精微,如天女散花,幽香万片,落人由帻间。每于胸念尘杂时,取而读之,便觉神怡气静。”(11)清人朱庭珍论诗亦云:“短章酝酿精深,渊涵广博,色声香味俱净,始造微妙之诣。”(12)中国古代诗学典籍中,诸如此类的诗论尚存许多,虽然并不都是“精微”这样的词语,但其意大致相同。 “精微”在中国诗学中体现为诗人表现事物细微变化的诗笔,又于其中蕴含着生命力的机微绽放。杜甫《水槛遣心二首》中有“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的名句,最能体现诗中的精微之笔。宋人叶梦得从这个角度作过精彩的评论: 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之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著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若无“穿”字,款款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13) 杜甫这两组诗句,把鸢飞鱼跃的物态写得惟妙惟肖,故深得诗论家们的高度赞赏。对于“精微”的重视,可以视为石林诗论的一个重要内涵。叶氏如此深入地阐发杜甫这联名句,也正是对诗歌经典中“精微”的个案有分析。 “精微”不仅是指诗作刻画精细,具有充盈的内在视觉美感,而且还蕴含着自然造化的生命力,如其所论: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使得,动无留碍,然其圆通快速,发之于手,筠亦未能尽也。然作诗审到此地,岂复更有余事。韩退之赠张籍云:“君诗多态度,霭霭春空云”。司空图记戴叔伦语云:“诗人之词,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亦是形似之微妙者,但学者不能味其言耳。(14) 叶石林极力称赏这两种境界,既见“精彩华妙”,又得“自然造化”,其实都可视为精微之笔,“岂复更有余事”,臻于极致。将所描写的事物最具特征、最富生命力的样态呈现给读者,而且创造出鲜明生动的内在视觉美感,或称之为“影写”,这是在中国诗学理论中所见的“精微”的含义。《诗经》有《卫风·氓》,其中有以“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为兴,颇得精微之旨,苏轼认为“诗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它木殆不可以当此”(15)。“写物”即是对事物最具特征、最富视觉美感的描写。 除了体物之精微,还有写情、言理之精微。诗者,持人情性,缘情而发是诗的本体特征。但诗中的情感并非是人的原发自然情感,而是赋有形式的审美情感。“精微之笔”的含义之一便是情感表现的微妙精深。刘勰认为文学之作是发于情感,其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16)但他又主张情感是要发之于文采的,因而又有“情采”之说。刘勰将“立文之道”析为“形文”“声文”和“情文”三种,其言:“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杂而成黼绂,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17)作为诗人表现在作品中的情感,不能再是那种原始的自然情感,而必须是赋有形式建构的。《情采》篇的赞语也颇有玩味的余地:“言以文远,诚哉斯验。心术既形,英华乃赡。吴锦好渝,舜英徒艳。繁采寡情,味之必厌。”(18)刘勰将“情采”合而为一个独立的审美范畴,也就是文学作品的审美形式以情感为其内蕴,而情感必以审美形式为其生成与外显的载体。述情的精微在于诗人以审美意象将情感表现得深婉动人,而非直露无遗。田同之论诗之述情云:“不微不婉,径情直发,不可为诗。一览而尽,言外无余,不可为诗。”(19)所论颇中肯綮,也即主张述情必欲出之以精微之笔方为佳作。田氏论诗特重以情为本,其诗话中多处言及情之于诗的本源作用,如说:“诗歌之道,天动神解,本于情流,弗由人造者是也。故中有所触,虽极致而不病其多;中无可言,虽不作亦不见其少。”(20)但他又述情当“兴寄深微”,“蕴蓄有味”,认为诗人欲成名家必当“造微”:“诗之为道,非造微不足以名家。”(21)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微”。具体而言,他又指出:“都必声情并至之谓诗,而情至者每直道不出,故旁此曲喻,反复流连,而隐隐言外,今人寻味而得。此风人之旨,所以妙极千古也。”(22)这是对诗中述情精微的深刻诠释。 诗中的精微之笔还有关于言理的内涵。直言义理,为诗论家所忌,斥为“理障”,因为诗歌创作有其特殊的审美规律,宋人严羽的名言“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23)。但是诗歌是与义理水火不容的吗?果如是我以为就过于偏颇了。诗中不能无“理”。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重要的美学价值之一,便是以鲜明生动的审美意象表现出诗人所体认的人生哲理。笔者对这个问题有过这样的表述:“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具有其他艺术种类所无法取代的生命强力,其间以凝练形象的语言,丰富的情感体验所呈现的人生哲理,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都是以理性的强光穿越时空的隧道,使人在受到情感的感染同时,也受到理的启示。”(24)时光已逝去十几年了,但我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观点没有多大变化。一直以来我都这样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之所以能够如此普遍地、深刻地浸润人们的心灵,开启人们的智慧,非常重要的一点便在于诗中之“理”的广泛存在。然而,理在诗歌中的存在样态不应该是如玄言诗那样的枯燥直白、毫无审美情味。钟嵘对玄言诗的批判是一针见血的:“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25)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诗中之理的价值体认。关键还在于,对于诗中之理的特质能否认识。诗中之理与哲学理念虽然都是人类思想的结晶,但其来源和内涵都殊为不同。哲学理念是高度抽象的产物,是以概念为中介的普遍性命题。再看诗中之理,却远非哲学教科书里由逻辑思维产生的结论,而是诗人通过审美感兴而获得的人生感悟。俄国著名思想家别林斯基主张诗和哲学都是表现真理的,是殊途同归的,当然他强调诗是用形象和画面来表现真理,如其所说:“诗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它的创造物是肉身化的观念,看得见的、可通过直观体会的观念。因此,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维,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绝对真理。不过不是表现在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中,而是在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诗人用形象来思考;他不证明真理,却显示真理。”(26)别林斯基有观点在中国文艺理论界的形象思维大讨论中得到了高度的认同。我却在理的内涵问题上大大有别于别林斯基的观点。别林斯基深受黑格尔的影响,他说的“真理”其实也就是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它们都指终极的抽象;而中国古代诗歌中的“理”,其内涵是远远丰富于斯的,当然也没有哲学理念的概括程度。它们是与人生、事态、物理的殊相相伴而生的,是诗人的审美感兴的产物。诗中之理以审美化的理性光芒来洞烛人心,与其把诗中之理视为一个终极性的统一概念,毋宁说它是一组意义相似的语义族。它有的时候指一种人生况味、人生境界,有的时候指客观事物变化的某种规律或情态,有的时候指社会事物的某种动态和趋向。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诗人以其独特的审美发现将读者带入一个意义的世界,穿透现象,洞悉社会。诗的精微之笔其中一个层面便是在于诗中之理。既称之为“精微”,就与那种“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理障”之作无缘。王夫之于此论说: 《大雅》中理语造极精微,除是周公道得,汉以下无人能嗣其响。陈正字(子昂)、张曲江(九龄)始倡感遇之作,虽所诣不深,而本地风光,骀荡人性情,以引名教之乐者,风雅源流,于斯不昧矣。朱子和陈张之作,亦旷世而一遇。此后陈白沙为能以风韵写天真,使读之者如脱钩而游杜蘅之沚。王伯安(阳明)厉声吆喝:“个个人心有仲尼。”乃游食髡徒夜敲木板叫街语,骄横卤莽,以鸣其蠢动含灵皆有佛性之说。志荒而气因之躁,陋矣哉!(27) 王夫之主张“理语”亦当“造语精微”,在这方面《诗·大雅》开了先河。其后唐代诗人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诗,也被王夫之从“理语精微”的层面加以认可。 清人叶燮以“理、事、情”论诗歌描写对象的几大要素,三者交互为用,而达“精微”之至。叶燮主张能将“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呈之于读者目前,方为诗之上乘。他指出: 然子但可言可执之理之为理,而抑知名言所绝之理之为至理乎?子但有是事之为事,而抑知无是事之为凡事之所出乎?可言之理,人人能言之,又安在诗人之言之!可征之事,人人能述之,又安在诗人之述之!必有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遇之于默会意象之表,而理与事无不灿然于前者也。(28) 叶氏举了杜甫的名句如“碧瓦初寒外”“月傍九霄多”“晨钟云外湿”“高城秋自落”等加以分析讨论,以“碧瓦初寒外”为例,指出:“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想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昔人云:‘王维诗中有画。’凡诗可入画者,为诗家之能事。如风云雨雪,景象之至虚者,画家无不可绘之于笔;若初寒内外之景色,即董巨复生,恐亦束手搁笔矣!天下惟理事之入神境者,固非庸凡人可摹拟而得也。”(29)叶燮此处以杜甫这几个名句为例子,阐发了精微之笔的价值尺度,亦即将那些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以文字呈现于读者的心灵屏幕之上。 在诗学中与精微成为两极而又相成的是“广大”或“广远”,它指的是通过诗的语言描绘而给读者形成的巨大张力和深远意境感。这也就是严羽所说的“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无穷”,或者说是由“在场”的语言表现而引发的“不在场”的诗歌境界。“广大”既指空间上广阔,也指时间上绵长,这里面是有一个主体的立场在其中的。陆机《文赋》中所写的“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诗人对时空的阔大苍茫的感受得以展现。刘勰论作家的“神思”时也称:“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30)作为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神思”当然是“广大”的。以我的观点来看,“神思”并非泛指一切创作思维活动,而是指杰出的文学作品的思维特征。这种思维应该是以主体的视界为出发点,超越时空局限,这也就是诗学上的“广大”或“广远”。我在论述“神思”时曾认为,“其神远矣”,就是指运思时精神世界的辽远广阔。“‘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当作家凝思时,可以想到上下千载,‘缘过去,缘以往,缘未来’,俯瞰千古,畅想无极,在时间上没有限制。神思还可以跨越空间,远远超过现实空间的阈限。”(31)这种在作家头脑中出神入化的思维过程,是将“千载”“万里”都提摄于笔下的。再看刘勰接下来对“神思”的描述:“夫神思方运,万途竞萌,规矩虚位,刻镂无形,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与风云而并驱矣。”(32)揭示了文学创作的思维特征,它不是普遍性的,而是杰出之作的思维特征。 “广大”并非是所有作品的普遍品性,也并非是具有“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作品就可称之为“广大”,而是指吸纳了宇宙生命和造化伟力、从而具有了恢张的气势和阔大的境界的篇什。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除了前面所谈及的“雄浑”一品,“劲健”也特具此种品格:“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巫峡千寻,走云连风。饮真茹强,蓄素守中,喻彼行健,是谓存雄。天地与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实,御之以终。”(33)虽是描述“劲健”的风格,同时也非常形象地表现出诗境的广大及其宇宙生命感。杜甫诗多以苍茫雄浑之境呈现给读者,如论“广大”,杜诗最为典型。清人刘熙载称之为:“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吐弃到人所不能吐弃,为高;涵茹到人所不能涵茹,为大;曲折到人所不能曲折,为深。”(34)渊深广大正是杜诗之风范。宋人叶梦得评杜诗云: 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如“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只在“有”与“自”两字间,而吞纳山川之气,俯仰古今之怀,皆见于言外。滕王亭子“粉墙犹竹色,虚阁自松声”,若不用“犹”与“自”两字,则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滕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独雍容闲肆,出于自然,略不见其用力处。今人多取其已用模仿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35) 在论杜诗的诗论中,这段论述很有经典价值。叶石林在这里称道杜甫“以一字为工”,以杜诗《上兜率寺》中的名句“江山有巴蜀,栋宇自齐梁”为例,将杜诗境界的广大雄浑揭示无遗。而且这两句诗充满动势,将“远近数千里,上下数百年”的时空纳入诗句之中,却又自然天成,得造化之妙。清人方东树论杜诗谓“杜公包括宇宙,含茹古今,全是元气,迥如江河之挟众流,以朝宗于海矣”(36)。从总体上概括出杜诗的“广大”之境。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论诗特别重视诗中的“广大”之势,如评鲍照诗《拟行路难》云:“冉冉而来,若将无穷者。倏然澹止,遂终以不穷。然非末二语之亭亭条条,亦遽不能止也。‘春燕参差风散梅’,丽矣,初不因刻削而成,且七字内外有无限好风光。”(37)王夫之最为推崇的是谢灵运的诗,他评谢诗多是从广大之境广远之势加以高度称许的,评《登上戍石鼓山诗》云:“谢诗有极易入目者,而引之益无尽;有极不易寻取者,而径遂正显然;顾非其人,弗与察尔。言情则往来动止,缥缈有无之中,得灵飨而执之有象;取景则于击目经心、丝分缕合之际,貌固有而言之不欺。而且情不虚情,情皆可景;景非滞景,景总含情;神理流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38)王夫之对于陶谢这两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诗人,相比之下他更为推重谢灵运。《古诗评选》中选评陶诗17首,选评谢诗26首。数量不是绝对的和唯一的标准,而其评价的高下亦颇见差异。在《古诗评选》中陶诗第一首《归园田居》的评语颇有总论陶诗的意味,其言:“钟嵘目陶诗‘出于应璩’,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论者不以为然。自非沉酣六艺,宜不知此语之确也。平淡之为诗,自为一体,平者取势不杂,淡者遣意不烦之谓也。陶诗于此固多得之,然亦岂独陶诗为尔哉!”(39)王夫之这里对陶渊明作了很一般的定位,并且不同意钟嵘对陶渊明“古今隐逸诗人之宗”的评价,认为即便是以“平淡”归之于陶,而能平淡者远非陶之一人。王夫之接下来又对陶诗作了贬抑性的评价: 若以近俚为平,无味为淡,唐之元、白,宋之欧、梅,据此以为胜场,而一行欲了,引之使长,精意欲来,去之若骛,乃以取适老妪,见称蛮夷,自相张大,则亦不知曝背之非暖而欲献之也。且如《关雎》一篇,实为风始,自其不杂不烦者言之,题以平淡,夫岂不可?——彼所称平淡者,淫而不返,伤而无节者也。陶诗恒有率意一往,或篇多数句,句多数字,正惟恐愚蒙者不知其意,故以乐以哀,如闻其哭笑。斯惟隐者弗获已而与田舍翁妪相酬答,故心与性成,因之放不知归尔。”(40) 历代诗论家鲜有对陶诗评价如此之低者,认为陶诗之“平淡”乃是率意冗滥。我们再看其对谢灵运诗的评价。其评《邻里相送至方山》云:“情景相入,涯际不分。振往古,尽来今,唯康乐能之。”(41)评谢之《晚出西射堂》诗云:“且如‘含情尚劳爱,如何离赏心’,心期寄托,风韵神理,不知《三百篇》如何?逢汉至今二千年来,更无一个解恁道得。”(42)评《游南亭》诗云:“条理清密,如微风振箫;自非夔、旷,莫知其宫、徵迭生之妙。翕如、纯如、皦如、绎如,于斯备。取拟《三百篇》,正使人憾蒸民、韩奕之多乖乱节也。即如迎头四句,大似无端,而安顿之妙,天与之以自然。无广目细心者,但赏其幽艳而已。”(43)评《游赤石进帆海》:“迢然以起,即已辉映万年。”(44)评《于南山往北山经中瞻眺》:“一命笔即作数往回。古无创人,后亦无继者。人非不欲继,无其随往不穷之才致故也。”(45)王夫之在《古诗评选》评谢灵运诗之论,基本上都是这种登峰造极的价值判断。船山对陶谢评价轩轾悬殊,无乃一在百尺楼下,一在百尺楼上!这其间的偏颇之处是显而易见的。但我们在这里一不作陶谢优劣之辨析,二不作船山诗论之批判,而是可以从中见出船山诗论的着眼点所在,即在于诗人通过文字所创造出的“广大”或“广远”的时空感。他的很多诗评,都出于此种角度。我们将其对南北朝之诗及对唐诗的评价相对比,可以发现,他对谢灵运的推崇远高于唐人,在《唐诗评选》中,只对李白的《古风》有“用事总别,意言之间,藏万里于尺幅”(46)的赞誉,对其他诗人很少从这个角度加以评价。翻检王夫之的《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其对诗人有如此高的赞誉者唯此一人!选杜诗的数量胜于大谢诗,但于评语却颇为“吝啬”,远没有像对谢诗这样的推崇备至!而以王夫之的评诗标准来看,何以会对谢灵运如此“情有独钟”?上推唐代诗僧皎然也对谢灵运有特别高的评价:“评曰: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夫文章,天下之公器,安敢私焉。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彼清景当中,天地秋色,诗之量也;庆云从风,舒卷万状,诗之变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哉。至如《述祖德》一章,《拟邺中》八首、《经庐陵王墓》、《临池上楼》,识度高明,盖诗中之日月也,安可扳援哉?惠休所评‘谢诗如芙蓉出水’,斯言颇近矣。故上蹑风骚,下超魏晋。建安之作,其椎轮乎?”(47)在对前代诗人的评价中,这也堪称是登峰造极的。但因皎然俗姓谢,尊谢灵运为“我祖”,其友于頔也说他是“康乐之十世孙”,因此他给谢灵运以如此高的评价时还有些心虚,说“文章之公器,安敢私焉”。但是王夫之于谢灵运毫无瓜葛,他对谢诗的高度推崇只能从他的评语中找答案了。看来看去,诗中的“广大之势”还是船山所深为看重和折服的。 诗中“广大”或云“广远”,不是仅指描写诗境的阔大,更非空洞呆板的“大”;而是以诗人的主体意识观照时空万象,并将自然宇宙的生命律动呈现于诗境之中。诗人的主体视角始终是君临万象的。恰如宋代词人张孝祥的著名词句:“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念奴娇·过洞庭》)“广大之势”,是以诗人的主体视界为阈限的,且又往往是以空间的无垠和时间的恒远相交互的。陆机所说的“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观古今之须臾,抚四海于一瞬”(《文赋》)、王羲之的“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兰亭集序》)、李白的“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诸如此类,都体现出一个“万象在旁”的主体视角。这是与其他态度都不相同的审美态度。诗人以总揽宇宙的视阈、亲和万物的情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广大之势”由此而来。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张君劢讲真善美的不同时说:“因此之故,科学以分疆划界为主,而道德以善恶是非为褒贬之准则。此二者自有其绳墨规矩为学问家、为立身行己者所不可不守者也。以云所谓美,虽出于人之感觉之主观,然其人人胸襟以宇宙与一身一心合而为一体,且超出乎世俗所谓生存常变、富贵贫贱之外,而后心旷神怡,乃能领略宇宙间种种之美,如山峙、如日出、如日落、如鸢飞、如鱼跃,为天地自然之美,惟有有道者胸襟开阔,不为物欲所蔽者乃能得之。此则美学之所以与科学哲学与道德二者迥乎各别者也。”(48)可以移之说明诗中“广大之势”的主体观照角度。 “广大”之所以与“势”相关,或者说“势”正可以表明“广大”的动态性的张力。《文心雕龙》中有《定势》一篇,刘勰论“势”曰:“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49)准确地描述了“势”的动态感与张力。皎然作《诗式》,起首便是“明势”其云:高手述作,如登荆、巫,觌三湘、鄢、郢山川之盛,萦回盘礴,千变万态。(作者原注:文体开阖作用之势。)或极天高峙,崒焉不群,气腾势飞,合沓相属,或修江耿耿,万里无波,歘出高深重复之状。古今逸格,皆造其极妙矣。”(50)皎然认为诗坛高手为诗,必当以势行之。其以起伏变化气脉连属之山川形势,比拟诗人在创作时笔意所呈现的自由流转、千变万态之势,动态与张力是势的特征。杜甫题画诗所云:“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万里。”(《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杜甫从题画的角度对作品之“势”的描述,却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夫之论“势”道:“论画者曰:‘咫尺有万里之势’,一势字宜着眼。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唯盛唐人能得其妙,如‘君家住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墨气四射,无字处皆其意也。李献吉诗:‘浩浩长江水,黄州若个边?岸回山一转,船到堞楼前。’固自不失此风味。”(51)王夫之在这里通过作品所阐发之“势”,正是笔者所论的“广大之势”,它不是一般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而是以发散性的动态和张力为其底蕴的。 精微与广大似乎是诗中两极,但它们并非是对立的,也不是不相干的“两层皮”,而是相融相即、互为彰显的。精微之笔在于诗中意象的刻画描绘,以充盈的内在视像唤起读者的审美知觉,然而,只有精微之笔而无广大之势,则诗作便无足够的韵味形成张力;反之,如果只有广大之势而无精微之笔,诗作就会使人感到空洞而缺少具体的审美感知。二者的关系可用刘勰所谓“隐秀”拟之而差近。《文心雕龙·隐秀》其言:“夫心术之动远矣,文情之变深矣,源奥而派生,根盛而颖峻,是以文之英蕤,有秀有隐。隐也者,文外之重旨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意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斯乃旧章之懿绩,才情之嘉会也。夫隐之为体,义主文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譬爻象之变互体,川渎之韫珠玉也。”(52)精微和广大,当然与隐秀并非一回事,但对应的关系却颇为相类。“秀”是在言内的,是“篇中之独拔”,近于“精微之笔”;“隐”是在言外的,是“文外之重旨”,近于“广大之势”。刘勰还以秀美的描写表现了“秀句”的特征:“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润色取美,譬缯帛之染朱绿。朱绿染缯,深而繁鲜;英华曜树,浅而炜烨:秀句所以照文苑,盖以此也。”(53)刘勰所形容的“秀”,与笔者所提出的“精微之笔”,在很大程度上相通,其以卓绝不凡的刻画呈现给读者以鲜明生动的内在视像,从而成为高光点。现在所见之《隐秀》篇是阙文,宋人张戒所引刘勰之语:“情在词外日隐,状溢目前曰秀。”(54)当为原文所存。这两句在现存的《隐秀》篇中不见,而在宋代诗话中出现,全文之失恐在元代。这两句恰恰是对“隐秀”这对审美范畴最赅恰的说明。以“状溢目前”指称“秀”的性质,正是后来梅尧臣所说的“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诗作在读者脑海中呈现出充盈的内在视像。黄侃先生试为《隐秀》补之,其中有:“然则隐以复意为工,而纤旨存乎文外,秀以卓绝为巧,而精语峙乎篇中。故曰:情在辞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大则成篇,小则片语,皆可为隐;或状物色,或附情理,皆可为秀。目送归鸿易,手挥五弦难,隐之喻也;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岸不枯,秀之喻也。然隐秀之原,存乎神思,意有所寄,言所不追,理具文中,神余象表,则隐生焉;意有所重,明以单辞,超越常音,独标苕颖,则秀生焉。”(55)从意在言外的意义讲,隐与“广大之势”有相通之处,而从篇中卓绝的意义上讲,秀又与“精微之笔”有相通之处。 “精微之笔”与“广大之势”能够冶于一炉,有机地构织于篇什之中,方为佳作。在王夫之的诗学观念中,这是作为理想的价值尺度提出来的。如其评诗时所说的“广远而微至”“大无外而细无垠”“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56)“抉微挹秀,无非至者,华净之光,遂掩千秋”。(57)“凡取景远者,类多梗概;取景细者,多入局曲;即远入细,千古一人而已”。(58)评陈子昂诗:“雄大中饶有幽细,无此则一笨伯。”(59)评李白诗:“规运广远,而示人者恒以新密。”(60)清人方东树也评谢灵运诗:“阔大精实,义理周足,他人所不能到”;“而造语精好,如精金在镕,无一点矿气烟气跃冶之意”(61),等等。这些诗论,“广远”也即笔者所谓“广大之势”,“微至”也即笔者所谓“精微”。二者融为一体,以“精微之笔”刻画的意象来辐射广大的审美势能,而又以“广大之势”烘托精微的卓绝表现。 精微之笔与广大之势,算不上是准确的诗歌美学命题,也没有更为严格的概括与提炼。但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它们仍是客观的存在,而且有着较为普遍的审美价值。篇中意象摄写刻画的精微与诗境的广大势能及张力,构成了相反相成的两极,在对中国诗学的审美感悟中,是值得提抉发阐的。 ①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版,第732页。 ②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6页。 ③张晶:《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视像之美》,《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2期。 ④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67页。 ⑤欧阳修:《六一诗话》,《历代诗话》上册,第267页。 ⑥魏庆之:《诗人玉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74页。 ⑦韦居安:《梅涧诗话》卷下,《历代诗话》,第573页。 ⑧方东树:《昭昧詹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137页。 ⑨方东树:《昭昧詹言》,第141页。 ⑩陆时雍:《诗镜总论》,《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409页。 (11)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卷二,《清诗话续编》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2页。 (12)朱庭珍:《筱园诗话》卷四,《清诗话续编》下册,第2402页。 (13)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历代诗话》,第431页。 (14)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历代诗话》,第435页。 (15)苏轼:《东坡志林》,卷十。 (16)《文心雕龙·明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5页。 (17)《文心雕龙·情采》,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37页。 (18)《文心雕龙·情采》,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38页 (19)田同之:《西圃诗说》,《清诗话续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2页。 (20)田同之:《西圃诗说》,《清诗话续编》第750页。 (21)田同之:《西圃诗说》,《清诗话续编》第753页。 (22)田同之:《西圃诗说》,《清诗话续编》第750页。 (23)严羽:《沧浪诗话·诗辨》,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 (24)张晶:《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文学评论》2000年2期。 (25)钟嵘:《诗品序》,陈延杰注:《诗品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1页。 (26)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一卷,满涛译,北京: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317页。 (27)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1页。 (28)叶燮:《原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31页。 (29)叶燮:《原诗》,第31页。 (30)《文心雕龙·神思》,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93页。 (31)张晶:《神思:艺术的精灵》,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38页。 (32)《文心雕龙·神思》,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94页。 (33)司空图著、郭绍虚集解:《诗品集解》,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6页。 (34)刘熙载:《艺概·诗概》,《艺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页。 (35)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中,《历代诗话》,第420页。 (36)方东树:《昭昧詹言》,第211页。 (37)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535页。 (38)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一,《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6页。 (39)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16页。 (40)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16页。 (41)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1页。 (42)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2页。 (43)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3页。 (44)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4页。 (45)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9页。 (46)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二,《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949页。 (47)皎然:《诗式》卷一,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8页。 (48)张君劢:《白沙先生诗文中之美学哲理》,《义理学十讲纲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4页。 (49)刘勰:《文心雕龙·定势》,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529页。 (50)皎然:《诗式》卷一,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第11页。 (51)王夫之:《姜斋诗话》卷二,戴鸿森笺注:《姜斋诗话笺注》,第138页。 (52)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32页。 (53)刘勰:《文心雕龙·隐秀》,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32页。 (54)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历代诗话续编》,第456页。 (55)黄侃:《文心雕龙札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96页。 (56)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681页。 (57)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42页。 (58)王夫之:《古诗评选》卷五,《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737页。 (59)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二,《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987页。 (60)王夫之:《唐诗评选》卷二,《船山全书》,第十四册,第950页。 (61)方东树:《昭昧詹言》卷五,第1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