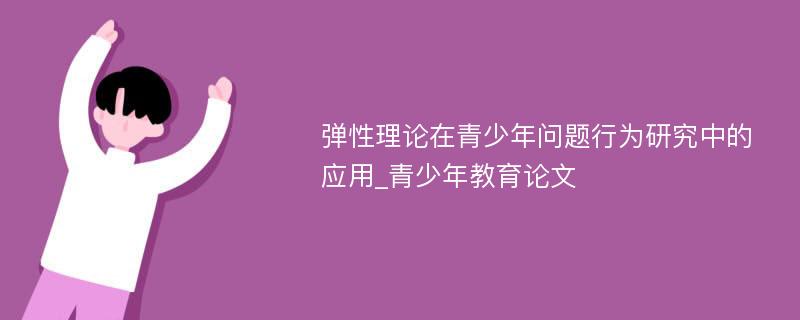
韧性理论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中的应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韧性论文,青少年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0)04-0009-05
一、引言
“韧性”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被定义为“物体受外力作用时,产生变形而不易折断的性质”,在心理学中,“韧性”指的是克服暴露在危险之中的消极影响,成功地应对创伤性经历,并避开与危险相联系的消极轨道的一种特性[1-2]。“韧性”一词最早被应用于心理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研究者采用“韧性”理论的模型研究儿童的行为。Garmezy和Masten在对儿童心理发展进行的个案研究中谈到压力、应对、危险、易感性和保护性因素之间的关联,并将“韧性”作为影响儿童发展的一项重要因素[3]。
90年代后,研究者开始关注韧性理论在青少年问题中的应用,早期研究多针对心理发展出现显著偏差的儿童,如自闭症患者,因而集中在临床心理学领域;而目前的研究却开始关注“常人”,即没有出现心理障碍但仍有问题行为的青少年。在过去30年的发展中,虽然韧性理论的框架和思路未发生本质变化,但随着不同模型的先后提出,韧性理论也日趋完善。
二、韧性理论的思路与三种理论模型
韧性理论有两个要素:一是危险因素,即来自家庭、社会环境以及自身的消极因素;二是促进性因素,即来自自身或外界的积极因素,二者缺一不可。韧性理论虽然关注发展面临的危险,重点却在于积极因素而非不足。它强调对那些处在危险中、仍能健康发展的案例的研究,这类研究既可提取出危险因素,也可指明应对的方向。
危险因素分三种:一种是长期的慢性危险,如不良的社会环境;另一种是较剧烈的短期危险,如不得不向重要他人透露自己感染了HIV病毒,其影响通常随时间推移而显著降低;最后一种是创伤性事件,如被抢劫或殴打。促进性因素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资源,即来自个体自身的积极因素,例如竞争力和自我效能感等;另一方面是资源,即来自个体外部的积极因素,例如父母的支持和某些社团组织等,韧性理论包括三种主要模型,即补偿性模型、保护性模型和挑战模型。
当一种促进性因素抵消或者与一种危险因素作用方向相反时,这就是补偿性模型。补偿性模型涉及了促进性因素对结果的直接影响,这一影响独立于危险因素之外[4]。例如在纽约市1184名初中生样本中,曾经吸烟、喝酒和吸食大麻的个体比起从未使用过的个体更容易出现药物滥用,但心理上的幸福感和社交能力补偿了该负性效应[5];并且社交能力还可补偿由于父母有药物滥用行为而产生的危险[6]。
当促进性因素缓和或减少了危险因素对产生某种消极结果的影响时,就是保护性模型。它有两种作用方式:一是稳定性保护——即当促进性因素存在时,消极结果完全不会出现的保护;二是反应性保护——促进性因素的存在不能完全阻止消极结果,但能让它出现得更缓慢,减轻后果的严重程度。Caldwell等人在对325名14到20岁非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种族歧视会增加暴力行为形成的倾向性,而种族认同感的两个维度对这一过程有保护作用[7]。
挑战模型中结果和危险因素的关系是凹形曲线形的,处于低水平和高水平的危险因素下会得到消极的结果,但水平适中的危险却与较少的消极结果相关联。该模型的关键在于水平适中的危险因素可以让个体为应对高水平的危险因素做好准备,而水平过高的危险因素会让个体感觉绝望无助而出现适应不良。例如,一定程度和频率的家庭内部冲突可以让青少年学会如何应对家庭以外的人际矛盾,而太过激烈或频繁的家庭内部冲突却可能让青少年感到无助,导致不好的结果。在挑战模型中,危险因素和促进性因素是相同的。
三、韧性理论在青少年问题行为研究中应用
青少年问题是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关注的焦点,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浪潮中,很多传统观念和教育模式都在改变。而直接受影响的就是正处于社会化最重要时期的青少年。有些青少年尽管受到消极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利用来自自身和外界的积极因素克服了这些影响,最终发展得很好。根据韧性理论,大多数青少年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消极和积极因素两方面的影响。一种危险因素可能与几类不同的问题行为相关联,而特定的问题行为往往存在着不止一种的危险因素,针对不同的危险因素又可能有几项促进性因素起保护或补偿作用。因此,应用韧性理论的模型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例如,对居住于高风险地区这一危险因素,参加亲社会性的活动对吸烟行为有一定的保护效应[8]。这说明:第一,居住于高风险地区是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它还可能是其他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第二,吸烟行为可能还有其他危险因素,如父母的吸烟行为;第三,参加亲社会性的活动间接地减少了与居住于高风险地区相关的吸烟行为,是一项保护性的促进性因素,除此之外,还可能存在其他促进性因素。
按照这一思路,研究者对青少年问题行为做了大量的研究。早期的研究偏重于寻找使青少年出现问题行为的危险因素,后来转移到探究危险因素以及可能的促进性因素之间的关系上。相当多的研究成果支持补偿性模型,研究者发现,可以用来补偿由情感上的不幸带来的药物滥用的资源包括:家庭的联系程度[9]、父母对学校活动的干涉、稳定的居住状况、压力性事件以及有支持性的同伴[10]。相邻居住环境的优势对由于被忽视或被虐待带来的药物滥用和暴力行为有补偿作用。参与课外和社团活动对同龄人使用烟草、酒精和非法使用毒品的负性效应有补偿作用[11]。父母权威的合法化、家庭的联系程度、父母的监管以及同父母公开的交流都是对同龄人药物滥用有补偿作用的资源[12]。Scal的研究发现,宗教的虔诚、学业成就、家庭的联系程度以及父母的教育期望对影响个人、同龄人群体和父母的吸烟行为的危险因素都有补偿作用[13]。Zimmerman的研究还表明,有自然导师(对青少年的成长有重大指导作用的除父母以外的成年人,如老师、邻居等)对吸食大麻或参与暴力的不良行为有补偿作用[14]。亲社会的信仰可以补偿有反社会倾向的社会化过程[15],宗教的虔诚可以补偿对参加帮派的兴趣[16]、同龄人药物滥用以及暴露于暴力行为中,控制愤怒的技能可以补偿冒险行为,父母的监管对参与冒险行为以及居住在危险地区有补偿作用[17]。Borowsky等人在对13781名初一到高三的青少年为期两年的研究中发现:学业成就、父母的存在、与父母/家庭的紧密联系、与学校的紧密联系对于曾经的暴力行为、受到暴力行为的侵害、药物滥用以及与学校相关的问题等危险因素有补偿作用[18]。
Ramirez-Valles等人对370名非裔美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发现,参加课外活动和社团组织补偿了居住于贫困地区作为危险因素的风险性性行为[19],而对药物滥用作为危险因素有补偿作用的资源有父亲的教育、老师的支持、与父母双方住在一起[20]、同龄人中性行为的规范以及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的监管和与父母公开的交流对同龄人性行为也有补偿作用。
相对于前面提到的补偿性模型,支持保护性模型的研究成果要相对少一些。在药物滥用方面,青少年的自尊[21]、内在控制、积极的情感[22]以及宗教虔诚[23]等资源都被发现对负性的或带来压力的生活事件导致的药物滥用有保护作用。Wills等人在1702名12岁到15岁的青少年中发现:积极的情感作用或感觉幸福、有兴趣并且放松,对于由情感上的不幸导致的药物滥用具有保护效应[24]。学业成就对药物滥用的保护作用在多种情境下是一致的,它有助于抵消低学业动机带来的危险和随年龄增长的药物滥用。Botvin等人发现在酒精和大麻滥用方面,决策的技能调节了有同龄人赞成药物滥用这一危险因素的影响,而宗教信仰对父母药物滥用有保护作用;作决策的技能还对青少年的父母允许其使用酒精和大麻有保护作用[25]。父母的支持可以保护青少年在药物滥用方面免受文化适应和低种族认同感的影响,同样对同龄人药物滥用和来自同龄人压力的负性影响以及随年龄增长的药物滥用有保护作用。家庭的联系程度[12]和父母的权威[26]都是可以保护青少年免受父母药物滥用消极影响的资源。对于在社区水平上的危险因素,如毒品的可得性以及社区中存在较低家庭紧密程度的规范等,父母的支持也对青少年滥用大麻有一定保护作用。可觉察的社会地位对同龄人中出现不良行为有保护作用[27]、母亲的支持对参与打斗等暴力行为和暴露于暴力行为中有保护作用,另外母亲的支持还对同龄人出现暴力行为有保护作用[28]。
四、韧性理论的局限
虽然韧性理论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成熟,但其发展仍然受到了限制,这些限制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分别是术语差异、个体/群体差异、背景/情景特异性以及对原因解释的缺乏。
首先,不同的研究者使用不同的术语,或者同一术语在不同研究中含义不同,是阻碍这一领域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这一方面,最主要的混淆就是部分研究者认为“韧性”是一种个人的、稳定的特质。而实际上,“韧性”是由背景、事件的情境、危险因素、促进性因素以及最终结果共同定义的,更类似于一种轨迹而非特质。
其次,韧性存在个体差异的问题。所谓的个体/群体差异,是指不同个体经受相同不幸事件的实际感受和最终效果可能不同,对于某个个体来说难以愈合的创伤可能对于另一个个体而言只是一次“免疫”的过程,因此很难将在某些个体身上得到的结论贸然推广。对于某个群体,由于其成员拥有某些共同的特性,或者曾共同经历过某些特殊经历,对该群体的韧性研究不能简单推广到其他群体。
第三,与个体差异的问题类似,一个个体可能在某一类危险面前有韧性,但却不能克服其他类型的危险,即具有背景特异性。一种危险因素可能由于情景不同而对个体产生不同的影响,即情景特异性。譬如父母离婚在多数情景下是一项危险因素,但在原本家庭气氛很紧张的环境中的青少年却可将其看作一种解脱,从而使得这一事件有正性效应。
最后,目前的研究往往缺乏对原因的解释,即资源或资源是怎样与危险因素交互作用以产生特定结果的。同样的结果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解释,也会对应不同的干预措施,例如弄清楚究竟父母的支持是如何与消极的同伴影响交互作用来阻止了吸烟是很重要的。
五、韧性理论在中国的应用及展望
韧性理论的提出者是西方人,之后的主要研究也基本都是西方学者的杰作,很少看到中国学者的名字。这既与中国在80以至90年代的心理学研究还不发达有关,也说明我们还未给予儿童和青少年可能产生的发展上的问题以足够的关注。
近年来,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逐渐在增多,尤其是外国学者与中国学者合作对国内青少年进行的研究,说明人们逐渐意识到了各国青少年成长环境和教育传统的不同可能导致其行为模式存在文化差异。例如,Dong在对有全国代表性的1640名平均年龄14.5岁的城市学生的研究中发现,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对不良行为有补偿作用[29]。在Jessor的研究中,当个人的易感性、有不好的榜样以及存在表现不良行为的机会作为危险因素时,来自家庭或朋友的良好榜样、家庭的控制以及家庭和老师的支持均为保护性因素,而这一结果在中国和美国样本中是基本一致的[30]。在Daniel对199名经济条件不好的中国青少年的研究中,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不幸的信念的认可对药物滥用和行为不良有补偿作用[31]。另外,胡月琴等人以访谈法编制出了针对中国青少年的心理韧性量表,分别在283名和420名中学生中进行了初测和复测,结果证明该量表有一定的结构效度和外部效度[32]。
在中国,韧性理论研究刚刚起步,未来发展余地很大。可是,如果仅在中国文化中将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重现,研究的创新性不够。我们应当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重点来研究韧性理论。详细说来,作者认为国内的韧性理论研究可以有如下几个方向:
首先就是文化差异。上文已提到,青少年的发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一影响是多方面的,可大致归为危险因素和促进性因素的不同。现今中国正在成长的青少年经历了改革开放特别是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前后的巨大变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特别是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影响。当代青少年在成长中经历更多的迷惘以及多重选择带来的压力。社会观念的改变使得中国近年来离婚率不断增高,家庭结构的变化可能成为另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而这种稳定性较低的家庭结构对青少年家庭观念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家庭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单位,每名家庭成员对家庭都负有一定的责任,“保持家族的荣誉”也是被普遍接受的。这就使得家庭的凝聚力对青少年有了约束作用,从而可能减少其问题行为的发生。然而,随着家庭稳定性的降低,青少年对“家庭”的重视程度正逐渐降低,特别是接受西方个人主义的思想以后,青少年更多关注自己的个性和权利,而忽视了作为家庭一员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是说,传统家庭观念的淡化可能成为新的危险因素。另外,很多青少年在探寻自我或者未来的职业时已不能简单地以自己的父母或亲近的成年人为榜样,因为到他们要走入社会时,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可能与上一代人已大不相同,因而对很多青少年而言,彷徨不安带来的压力也会是一项危险因素。
有一种潜在的危险因素需要特别指出,那就是目前被称作“非主流”的青少年群体。所谓的“非主流”,就是不跟随大众文化价值观、极力张扬个性、追求“另类和叛逆”,多以80后和90后青少年为主导。这些青少年摒弃并蔑视传统文化观念,常以夸张的服饰、颓废的生活方式吸引大众的注意。一方面,“非主流”群体本身就是处于高度危险中的青少年,他们推崇对传统是非观的刻意颠覆,因而其中的很多人已经出现了不少问题行为,如“一夜情”、药品滥用、酒精滥用等等。另一方面,虽然人数还不多,但他们借助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的报道,在青少年中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容易使一些还未形成正常价值观的青少年受到误导,因此他们也成为了其他青少年的危险因素。总体来看,“非主流”群体是不被社会接受的,那么为什么这些青少年会成为“非主流”?是否与媒体对个性的过分推崇有关?还是他们自身经历有一定的特殊性?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而说到中国青少年的促进性因素,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存在是不能忽略的。随着中国不断与国际接轨,与外国的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对于现在的青少年,尤其在大城市中,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目前在很多小学,几乎所有的学生无一例外都是少先队员,而这个名称对于他们只是一个称呼而已。因而,身为这些组织一员所应具有的约束力和责任感也就随之减弱。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学校观念的改变上。“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思想使得学校的约束力得到了强化,在青少年看来,在学校得到老师或同学的认可比得到父母的称赞更加有意义,这种对学校的尊崇可以作为促进性因素。但当诸如“爱读书的是书呆子”、“学校很无聊、读书很枯燥”之类的思想开始蔓延之后,这种强化的约束力也就降低了。另外,中国的某些传统观念如“男女授受不亲”、“吸烟是坏孩子”等可能对青少年在某些方面存在约束力,而这些传统观念的打破就可能使这一项促进性因素的作用减弱乃至消失。
其次,是关于性行为的研究,这在国内还很少。一方面是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青少年在“性”的问题上的开放程度还不及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青少年;另一方面,虽然现在青少年对“性”的看法有所改变,但在学校、家庭等其主要活动的场所,“性”仍是被回避甚至禁止的话题。然而,由于对性行为理解不当并且缺乏理性的认识和指导,已经有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其负性的影响。有些青少年受到媒体中“一夜情”等不良内容的影响,过早接触性行为使身体和心理受到了极大伤害。现在对于性行为的研究已非常迫切。在研究方法上,既要参考国外现有研究的方法,也要考虑到文化差异。
第三,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研究。这里是指学生就读的学校的差异——重点与一般学校。在中国,一个学校的地位和声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师资力量、生源以及校风。即使在同一地区,市重点和一般学校的学生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都相差很大。一些一般学校的学生可能刚毕业就结婚生子,而市重点的学生却为进入大学深造做准备,无暇顾及其他。可以想见,不同学校青少年的行为模式以及各种问题行为出现的概率很可能会有显著差异。在西方国家,学校之间的差异远没有中国这样明显,更多的还是地区性差异。因此,在中国进行青少年问题行为的研究时,一定要考虑样本中的青少年来自的学校,以免得出片面的结果。
总之,通过对韧性理论的研究,我们可以尝试找到一些合适的干预手段,如对青少年的父母和教师进行教育[33]、对居住于不良环境中的青少年给予更多的关注、组织并鼓励更多健康的课余和社团活动等。相信在逐渐完善的韧性理论的指导下,我们能够帮助中国的青少年更好地完成社会化[34],让他们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本研究得到北京大学心理系和美国密西根大学心理系联合资助。
收稿日期:2010-05-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