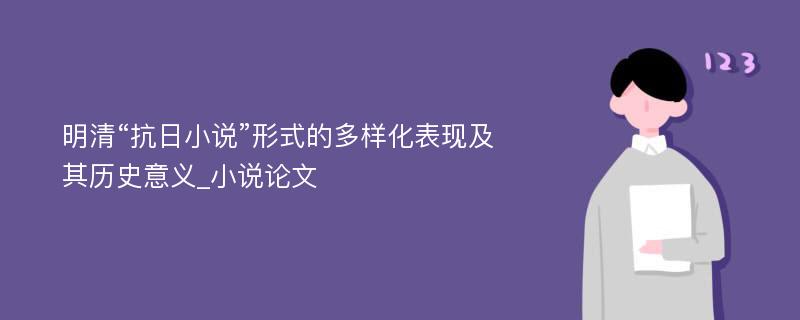
明清“抗倭小说”形态的多样呈现及其小说史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明清论文,形态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3至16世纪期间,由日本海盗、武士和浪人组成的武装集团,对朝鲜半岛及中国部分沿海地区进行了长达数百年的侵略,他们与日本国王、名主有密切的联系,有些中国海盗、奸商、无赖及失意文人等也参与其中。明代倭寇侵略时间之长,“几与国相始终”①;攻击地域之广,“裂国家幅员之半”②。明王朝“用兵以百万计,费金钱不计其数”③,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倭乱对明代社会的众多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以之为题材的文学作品难以数计,仅小说即不下数十种。对于这些小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游佐彻等早在20世纪初就展开过研究,游佐彻将这些小说统称为“倭寇小说”。他们主要是考察明清小说中的丰臣秀吉形象,或对“倭寇小说”做些考证。近年来,国内学人如严绍璗、刘勇强、张哲俊、王勇、张志彪、严美娟等也先后撰文研讨,但一般也是以文学作品为材料,论述文学中的日本人形象。鉴于此,本文拟对这些小说的历史和文学价值作初步的探讨。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小说有相当一部分是正面描写和反映抗倭斗争的,将其称作“抗倭小说”名副其实;但其中也有不少作品,只是部分涉及倭乱或平倭事件,并非主要描写抗倭斗争,而且其中多有语涉怪力乱神者,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只能算是“涉倭小说”;本文为了论述方便,一并将其纳入“抗倭小说”的考察范畴。 一 明清“抗倭小说”存在形态述略 以明代抗倭斗争为题材而创作的小说,时间上贯穿明清两朝。综观倭乱事件,以嘉靖年间最为严重,因而自万历以后,“抗倭小说”始大量出现,至晚清仍不绝如缕,其创作过程大致分为三个时期: 从嘉靖至明末为第一时期。倭寇扰边的次数,据日本学者田中健夫统计:洪武二年(1369)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计30次;建文三年(1401)至正德十二年(1517)有49次;嘉靖二年(1523)至嘉靖四十四年(1565)共543次;隆庆二年(1568)至万历四十六年(1618)为32次④。可见嘉靖年间倭乱最为集中。在当时,就有许多纪实性的文学作品产生,作者一般都是亲身参与抗倭或经历倭乱的文人。万历以后,明王朝进入多事之秋。万历二十年(1592),发生援朝抗倭战争,此后边患频仍,内乱不止。因而,“抗倭小说”相继产生,作者主要是有感于现实威胁,抒写抗击外敌的民族精神。所谓“临事而思御侮之臣”⑤,通过讴歌英雄来激励官兵。其中最著名的,是无名氏的《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小说以戚继光的“十捷”为中心,全面反映了东南沿海军民的抗倭斗争。此外,周清源《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等记述了胡宗宪剿灭江浙倭寇的故事;东鲁古狂生《醉醒石》第五回《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则以福建兴化陷落为背景,歌颂忠臣烈妇。这些小说的作者抱着“补史”的严肃态度,以写实的手法,试图全面反映抗倭斗争的过程,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从清初至清中叶为第二时期。代表作如夏敬渠的《野叟曝言》,把丰臣秀吉对朝鲜的侵略战争置换为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犯;陈朗的《雪月梅》以嘉靖三十四年(1555)张经所指挥的王江泾大捷为蓝本,描述了岑秀等平定倭寇的故事。此外,还有《绿野仙踪》、《歧路灯》等,都有关于平倭的内容。这时期,由于中日两国都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两国基本处于隔绝状态;同时,由于时过境迁,清人对明代倭乱的记忆已逐渐模糊,也没有明人深受倭害的锥心之痛,因此小说一般采用夸张和娱乐化的表现手法,抗倭英雄大多得到一本天书,有呼风唤雨、请神召将等超自然本领,战斗的输赢被曲解为法术的比试,创作风格呈现出明显的神魔化倾向,主要人物也由前期的历史人物变为虚构人物。 晚清为第三时期。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清王朝在甲午海战中败北,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之后,群情愤激,以明代抗倭斗争为题材的小说再次成为热点,如《蜃楼外史》、《载阳堂意外缘》等。这时期的“抗倭小说”延续了前一时期的写法,但由于甲午战败而导致国人的自信心挫败,小说家们常“假此发言,以慰人心”(枕流斋主人《台战演义序》),即以梦幻的手法战胜倭寇,如《梦平倭奴记》。此外,个别小说还受到女性主义之类新思潮的影响,如《载阳堂意外缘》,把一个长期与有妇之夫保持不正当关系的少妇塑造成抗倭英雄。 “抗倭小说”不仅持续时间较长,而且类型众多,几乎囊括了所有的古代小说文体和题材类别。如从文体分,有文言小说,包括传奇体《罗龙文传》、《女聊斋·查女》,笔记体《涌幢小品》中的某些篇目等;有白话小说,如长篇小说《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话本小说《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型世言》第七回《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醉醒石》第五回《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等。 从题材分,有时事小说,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主要塑造戚继光等人的英雄形象,《胡少保平倭战功》则叙写胡宗宪的战功。这些小说又以描写抗倭英雄的故事为主体;有才子佳人小说,如《玉蟾记》、《雪月梅》、《绮楼重梦》等,把抗倭斗争与才子佳人题材糅合在一起,成为清代抗倭小说的主流,通过剿倭立功抒发底层文士发迹变泰的梦想,一反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私订终身、金榜题名等俗套;有人情小说,如《歧路灯》描写纨绔子弟谭绍闻改过自新的过程,他因在平定倭寇时立下大功,因而得到重用;有道教小说,如《绿野仙踪》、《升仙传》等,作者把消灭倭寇归功于得到神仙的帮助,以宣扬道教思想。 从创作风格分,有真实反映抗倭斗争的,以《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胡少保平倭战功》为主要代表;有的虽也涉及抗倭斗争,但只是一般的概念化、模式化叙写,如《玉蟾记》、《绮楼重梦》、《花月痕》等,歼灭倭寇只是才子们功业中的一部分而已,或倭乱仅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有满纸怪力乱神,完全以夸张的手法来表现这场严肃的战争的,如上面举到的《野叟曝言》、《绮楼重梦》等。 由上可见,“抗倭小说”在不同时代、从不同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了发生在明代的倭寇入侵我国东南沿海的历史事件,以及我国军民奋起抗击倭寇的英勇事迹。这些小说虽内容驳杂,良莠不齐,但其主体部分,尤其是明代的小说,具有重要的社会历史价值。 二 “抗倭小说”的主要内容及其思想价值 抗倭小说展现了明王朝军民抗倭斗争的全貌,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抗倭前线的战斗描写,也有朝廷内部围绕倭乱事件的争斗;既有对倭寇暴行的愤怒控诉,也有对抗倭英雄的热情歌颂;既有东南沿海抗倭斗争的全方位展示,也有个别战役的集中聚焦;既有对官军正面战场的生动描绘,也有民间抗倭事迹的故事讲述;既肯定抗倭功绩,也暴露抗倭问题,具史料价值和认识意义。 揭露倭寇暴行是“抗倭小说”的主要内容之一。倭寇素以暴虐杀掠著称,曾亲自参加过抗倭斗争的郑晓和俞大猷对此深有体会,郑晓在《吾学编·四夷考》中指出,倭寇“其喜淫、轻生、好杀,天性使然也”⑥。俞大猷《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云:“倭人桀骜、剽掠、嗜货、轻生,非西南诸番可比。”⑦“抗倭小说”即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史事实,其中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即为突出表现之一。《西湖二集》中《胡少保平倭战功》写到“倭奴左右跳跃,杀人如麻,奸淫妇女,烟焰涨天,所过尽为赤地”(浙江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下同)。《雪月梅》中更具体写及倭寇入崇明,“大肆杀掠,巨商富室,罄掳一空,妇女三十以上无姿色者杀戮无存;少艾者驱使作役,青天白日群聚裸淫,少不如意,挥刃溅血。群妇股裂受污,天日为惨”(齐鲁书社1986年版,下同)。奸淫之后,又将这些妇女关闭在屋中,活活烧死,其暴行令人发指。《戚南塘剿平倭寇志》更将观照面扩展至整个闽浙地区:倭寇至泉州,“纵兵剿杀人民,死者甚众,极其惨酷,所在房屋,尽皆毁烬”;至长乐,“杀人如麻,流血若川”;至温州,“众兵屠杀,焚毁庐舍”;至福清,“纵横剿杀,人民死者相枕藉,莫可胜纪,高堂大厦,尽为灰烬”(《古本小说集成》第三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下同)。这与谢肇淛在《五杂俎》中关于倭寇“陷兴化、福清、宁德诸郡县,焚杀一空,而兴化尤甚,几于洗城矣”⑧的记载基本相同。总之,到处是一样的烧杀抢掠,这就是倭寇留给中国人民的民族集体记忆! 倭寇除奸淫妇女外,还绑架青年男子,或用他们充当炮灰,或押往日本为奴。如《杨八老越国奇逢》写倭寇若遇强壮男子,“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岳麓书社1982年版)。西安府盩县人杨复,被倭寇抓往日本十九年,作为奴隶使唤。《雪月梅》中借华秋英之口介绍倭寇道:“这倭奴狡猾凶残,大约攻破城池,先肆掳掠,把那年老者不分男女,杀戮无存,把那些少壮男人驱在一处,遇着官兵到来,先驱使冲阵,倭奴却伏在背后,有回顾者,即行砍杀。”此事在众多史书笔记中都有记载,如《皇明驭倭录》中记洪武五年(1372),高丽国两次送还被日本所掠中国海滨男女七八十人⑨。《虔台倭纂》记福清民谣曰:“怨尔倭奴性太刚,儿童掳去不还乡,分明一把无情剑,斩断人间父母肠。”⑩此外,还有受害人蔡景榕的《海国生还集》为证,作者叙述自己在嘉靖四十年(1561)十月倭寇侵占宁城时被掳至日本为奴,“则于榕髡其头,跣其足,食以糠核,寝以下床”(11),再又转卖于商人,后被僧人赎出,留在寺里抄写经文,三年后幸运地返回故乡。明人郑舜功曾两次跟随日本僧侣赴日,他在旅行记录《日本一鉴》中述及亲眼见到被掠到鹿儿岛高须地方为奴的二三百名福建男女,个个髡发跣足,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过着地狱一般的悲惨生活。 尤其让人触目惊心的是,倭寇还枪挑婴儿,剖看孕妇,以此取乐。《醉醒石》中《矢热血世勋报国,全孤祀烈妇捐躯》一回就写到倭寇“拿着男子引路,女人奸淫,小孩子搠在枪上,看他哭挣命为乐”。这种枪挑小孩取乐的暴行,在郑晓《吾学编》、钱薇《与当道处倭议》、薛俊《日本国考略》等书中都有记载。如《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中记载:倭寇“束婴竿上,沃以沸汤,视其啼号,拍手笑乐”(12)。当时辞官居家的唐顺之还亲眼目睹过倭寇用刀挑刺婴儿戏耍的场景(13)。而且,上述文献中还记载倭寇捕得孕妇,赌猜婴儿性别,剖腹验证,负者饮酒的兽行,怵目惊心,令人发指!可见,小说中所写倭寇暴行,无不有文献记载作为佐证,可谓铁证如山! “抗倭小说”在揭露倭寇罪行的同时,以饱满的笔触讴歌了历史上的抗倭英雄。历史上最著名的抗倭英雄非戚继光莫属,万历年间的长篇小说《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即以他为叙事核心。这部小说主要从戚继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实践两方面来表现他的抗倭功绩,其中军事思想又是通过他谈兵和练兵两个章节来体现,这些描写参考了戚继光的军事著作《练兵实纪》。 如在“天台观谈兵”和“统兵选士”二节中,戚继光指出: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仅要武艺精熟,胆大气豪,而且必须身先士卒,“非独临阵之际,援枹鼓之,凡件件苦处,俱要身先,所谓同滋味共甘苦此之也”。他尖锐批评明军沿袭二百余年的士兵操练方法,“通是一个虚套,其临阵的真法真令真武真艺,即却无一字相合”。他质问道:“如此就操一千年便有何用?”军事训练必须讲究实用,“岂是好看的?”对于士兵的素质,戚继光认为:“凡选士,武艺尚亦可以教,习必精,有胆量,三者兼全,方为上品。然三者之中,必以胆为主。”胆量是基础,其它皆习而能之。士兵若临阵胆怯,再好的条件也没用。在练兵即将结束时,他嘱咐士兵:“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手只执器械,脚只认进退,其余圈套、花法,俱勿习学。盖武艺中圈套、花法,上阵时不切于用,且误事。诸军晓得。” 戚继光勇于创新、出奇制胜、科学有效的练兵方法和先进的军事思想使“戚家军”拥有强大的战斗力,他也赢得了“戚虎”的威名,取得了对倭作战的一系列辉煌胜利。在作战时,他知己知彼,因时制宜,不拘于一。如台州之战,衣以贼服,智败倭奴;南湾寨之战,凿沉敌船,大破贼兵;温岭之战,趁着雾气,突袭破敌;白水洋之战,采用火攻;围剿桃渚倭贼,巧用反间计;新河大捷,借用潮汐。凡此等等,每场战斗,变化多端,精彩纷呈,令人叫绝。 作者还通过渲染对手的强大来突出戚继光的形象。如倭酋汪直熟读兵书,不仅懂排兵布阵之法,还有丰富的军事知识,并能融会贯通,灵活运用。他开始极度轻视官军,嘲笑官军“懦弱无用”。但他败于鉴湖后,仰天而叹曰:“何其神异也!”白碧之战,许朝光、哥罗王、刚杜王等欲趁暮夜袭击戚家军,谓“戚虎既擒,其余将校,皆如儿戏,何足虑也?”结果一战惨败,倭兵死者过半,倭贼皆相抱啼哭曰:“本欲共灭戚虎,今反为戚虎所屠殆尽矣。”通过这些平日不可一世的倭寇的败后表现,反衬出戚继光杰出的军事才能。总之,戚继光把军事理论和军事实践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正如他的顶头上司胡宗宪所说:“谋勇可当乎八面,胆气独雄于万夫。纪律严明而师行不扰,素优统御之才;恩威并著而士卒归心,屡收斩获之绩。此诚以武略而兼通文事者”。(14) 戚继光是古今公认的抗倭英雄,胡宗宪则是历史上最有争议、也是“抗倭小说”中出镜最多的人物。历史上的胡宗宪歼灭倭寇渠魁徐海、王直等,使一度肆虐江浙的倭寇始靖;而他立下赫赫战功,又与得到内阁首辅严嵩的支持分不开。他还贿赂严嵩,弹劾张经,陷害俞大猷,生活奢侈。严嵩倒台后,胡宗宪为人参奏,系狱自杀。隆庆年间,穆宗下旨为胡宗宪平反。万历年间,朝廷为鼓舞援朝抗倭将士的士气,为胡宗宪举行国祭。但至清代,东林党人的思想主导了《明史》的修撰,道德因素又被置于军功之上,胡宗宪再次受到非议。因而在小说中,胡宗宪的形象颇为复杂。江浙人因受惠最多,故他们笔下的胡宗宪形象一般是正面的。王士性《广志绎》卷四云:“故论浙中倭功,当首祠胡公、谭公以及俞、汤、卢、刘、戚等。而戚功在闽,其方略又出诸将之上。似此名将,又何可得而抑厄之,使愤懑死,安得不解壮士之体。为此厉阶者谁耶?”(15)茅坤、何良俊、朱国祯、郎瑛等人都发表过类似的观点。 最早以胡宗宪为主人公的小说是崇祯年间周清源的《西湖二集》卷三十四《胡少保平倭战功》,此后,钱塘渔隐叟《胡少保平倭记》、陈梅溪辑《西湖拾遗》卷四十七《胡少保平倭奏绩》皆以此为本。《胡少保平倭战功》的作者在“入话”中,就为胡宗宪鸣不平,认为他剪灭倭奴,救了七省百姓,立有大功。后来鸟尽弓藏,死得冤枉。说他日费斗金,完全站不住脚,“征战之事,怎生铢铢较量,论得钱粮?”说他是奸臣严嵩之党,但“从来道,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英雄豪杰任一件大事在身上,要做得完完全全,没奈何做那嫂溺叔援之事,只得卑躬屈体于权臣之门,正要谅他那一种不得已的苦心,隐忍以就功名,怎么絮絮叨叨,只管求全责备!”接着叙述抗倭形势,在倭寇凶猛的攻击下,官军屡败,损失惨重,形势十分严峻。这时,胡宗宪临危受命,被任命为浙江监察御史,他一出场,作者就以史传的笔法,称赞他“有倜傥之才,英雄之气,机变百出,胸藏韬略,智谙孙、吴”。他力挽狂澜,倭奴逼近嘉兴城外,城中百姓震恐。胡宗宪暗取酒百余坛,放置毒药于酒中,故意派人送往劳军,路上故意让倭寇抢去,倭寇开怀畅饮,毒毙甚多。接下来,在胡宗宪的指挥下,取得了王江泾大捷。总督张经因抗战不力,圣旨拿问,胡宗宪才堪大用,取而代之。胡宗宪上任后,根据敌众我寡的形势,制订了周密的计划,离间倭酋徐海和陈东等人的关系,使他们互相攻伐;诱降王直,使他变成瓮中之鳖。终将江浙倭寇全面肃清。最后,小说引用兵科给事中朱凤翔的奏本,作为对他的盖棺论定。显然,作者对胡宗宪怀有深厚的感情,对他依附严嵩表示谅解,甚至把史上由张经指挥而取得的王江泾大捷攘为胡宗宪所有,也隐去了胡宗宪参与排挤张经的史实。这种感情在明末江浙文人中较有代表性,如史学家谈迁评曰:“胡宗宪以倜傥非常之才,仗钺东南,鲸波就恬。值严氏柄国,情好稠密,所谓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能立功于外者。”(16)还有的小说,把胡宗宪排除在严嵩及其党羽之外,如潘之恒《亘史钞》记云:胡宗宪总制两浙时,赵文华监军,威福自恣,胡宗宪先是“迎拜借重”,继而“微诟之”,直至发展到公开冲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清浙江平湖人陈朗的小说《雪月梅》继续发展了这一观点,在写胡宗宪指挥剿灭徐海后,“因赵文华之谮,朝廷只加了胡公太子少保之衔,别无升奖”。 至话本小说《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作者既正面肯定胡宗宪的抗倭功绩,又以春秋笔法委婉地批评他的道德缺陷。胡宗宪在智歼徐海后,大宴将士,强召翠翘出席,公然对着众人称翠翘是亡国的西施。酒至半酣,拥翠翘而坐,逼之歌三诗。三司起避,席上哄乱。次日酒醒,宗宪殊悔昨日之轻率,又不顾翠翘不高兴,将她作为礼品送给彭宣慰。翠翘投江而死,胡宗宪得知消息,不觉泪下,道:“吾杀之!吾杀之!”命中军沿江打捞其尸,得之于曹娥渡。宗宪曰:“娥死孝,翘死义,气固相应也”(《型世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下同)。命葬于曹娥祠右,为文以祭之。在这篇小说中,胡宗宪虽着墨不多,但很生动,呈现出性格的多面性:既智谋高超,为国家立下大功;又有传统士人视女人为祸水和玩物的心理。但又本性善良,富有同情心。而在清代小说《绿野仙踪》中,胡宗宪的抗倭功劳被完全剥夺给了虚构的抗倭英雄朱文炜,小说中说胡宗宪与严嵩有姻亲关系,诗赋极佳,八股尤妙,但“只会吃酒做诗文,究竟一无识见,是个胆小不过的人”。第七十三回,圣旨命赵文华为兵部尚书,督师征讨倭寇,朱文炜、胡宗宪为都察院左、右佥都御史,一同参赞军务。朱文炜因曾在胡宗宪幕下献策破敌,故持名生帖去拜访他。在这一回,作者通过两人的对话,将胡宗宪迂腐、虚荣、胆怯、糊涂的性格特征描摹得惟妙惟肖。他虽然不喜欢朱文炜,但当朱文炜得罪赵文华后,又极力为他挽回,并请求赵文华将参奏朱文炜弹章中的“正法”一词改为“严处”。后来朱文炜去官,向胡宗宪辞行,胡宗宪还因未能帮上忙而“脸上甚是没趣”。可见其良心未泯。总之,《绿野仙踪》中的胡宗宪形象较为丰富、生动。而在《金云翘传》等小说中,胡宗宪则被塑造成一个奸诈、狠毒的小人。《歧路灯》更抹杀胡宗宪的抗倭功劳,把诱杀徐海的功劳安在已死去的王忬头上。而《玉蟾记》竟把胡宗宪描绘成一个通倭卖国的叛贼。可见,明代抗倭小说评价历史人物重视能力和功绩,而清代抗倭小说则充斥着道德评判和善恶观念。 除戚、胡之外,“抗倭小说”中还写到其他一些抗倭英雄,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中福建提学副使宗臣,忠君爱民,常为百姓遭受的苦难而叹息泪下,在战斗中尽全力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不受侵害。此外,沉毅有谋、为国荐贤的台州府知事谭纶,明察秋毫、谨慎有谋的巡按御史樊献科,心怀百姓、机智善谋的兵备道舒春芳和知县李炜等,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以上是抗倭战场上涌现的英雄,在民间也出现了众多可歌可泣的传奇式人物,他们或为歌妓,或是船夫、奴仆、民女和民妇,但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在抗倭斗争中立下奇功,“抗倭小说”也为我们留下了一段段传奇故事。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歌妓王翠翘,这是个虚实相间的人物,因在说服贼酋徐海投降致使倭寇瓦解中立有大功,在明末清初的文学作品中逐渐传奇化,成为“箭垛式人物”。现知最早记述王翠翘故事的有明末徐学谟《王翠翘传》,其后茅坤、胡爌、王世贞、余怀、陆次云、宋起凤、张潮等皆撰有传述,白话小说则有《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金云翘传》等。这些作品描述了王翠翘传奇而又悲剧的一生,赞美了她为国家大义而牺牲个人私情的精神,故事情节单元大体相似。《胡总制巧用华棣卿,王翠翘死报徐明山》着力突出王翠翘的“义侠”和“才女”品格。她早年卖身救父,为人做妾,流落娼家,受尽苦难。华萼为她赎身后,她谢绝客商俗子,只与些文墨之士联诗社,弹棋鼓琴。后来被徐海掳为压寨夫人,宠冠诸姬。她常劝徐海“少行杀戮,凡是被掳掠的,多得释放。又日把歌酒欢乐他,使他把军事懈怠”。后来在说服徐海投降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在徐海死后,尝怏怏,以不得同死为恨。于是尽弃弦管,不复为艳妆。后来胡宗宪将她送给彭宣慰。舟至钱塘,她大呼曰:“明山!明山!我负尔!我负尔!失尔得此,何以生为!”奋身投江而死。小说结尾,作者写华萼渡曹娥江时,梦入仙府,见到翠翘,自述因生前节烈,且有生全两浙功德,上帝特授忠烈仙媛,佐天妃主东海诸洋;并暗示胡宗宪因诛杀降人,致翠翘以死,将受到“命毙于狱”的报应。金云翘遭遇不幸,自归徐海后,徐海对她“输情输意”,“凡掳得珍宝服玩,但拣上等的与王夫人;凡是王夫人开口,没有不依的”。她对徐海心存感激,甚至不排除有儿女私情,但为了保全千百万百姓,她毅然牺牲这一切,直至最后投江殉情。为国家,她牺牲儿女私情;为儿女私情,她牺牲生命。“义侠”的品格得到了生动的诠释。 其他如《涌幢小品》卷之二十“义仆”讲述王华家仆金养,在倭贼来袭时,为掩护主人家女妇数十人逃走而英勇献身;同书卷之三十“王长年”写船工王长年被倭掳获,他机智地与贼周旋,最后杀死全船倭寇,救出同船被俘的同胞,载回被掠夺的珍宝(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又吴炽昌文言小说集《客窗闲话》卷一“查女”则塑造了一位弱女子凭借自己所掌握的医学知识,不仅成功地逃脱了敌寇的魔爪,而且药死倭王,麻倒倭将,将他们全部杀毙(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还有《雪月梅》中的华秋英,习知倭语,在崇明陷落时被掳,倭寇欲强暴她,她机智地将倭寇引到楼屋上,将他杀死,逃出重围,后与出身平民的抗倭将领殷勇结为伉俪,共同投身抗倭斗争;以及《载阳堂意外缘》里少妇尤氏在家中设下陷阱,再以石灰弄瞎倭寇眼睛,将众贼陷入地窖压毙(《古本小说集成》第四辑)。这些低层小人物虽然弱小,但他们临危不惧,机智应对,一样立下奇功。 除描写抗倭英雄事迹之外,“抗倭小说”还通过暴露明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士兵怯战、汉奸通敌、客兵害民等种种问题,以彰显抗倭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而引发读者的深思,为现实提供借鉴,具有一定的揭露和批判意义。特别是明代“抗倭小说”,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体现出作者再现历史及参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较为重要的思想价值。 三 “抗倭小说”的艺术贡献及其小说史意义 明代“抗倭小说”不仅在内容上有较高的历史价值,而且在小说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其作为明代时事小说的发端,长期以来没有受到学界应有的重视。 明代“抗倭小说”是最早描写当朝历史的小说之一,标志着一种新型小说文体的崛起及时事小说的发端。明初由于文网甚密,文人们都不敢触及时事。“靖难之役”、“土木之变”都是在一二百年后才出现以之为题材的小说。万历间文网松弛,当代人写当代事的时事小说开始出现,如万历二十八年(1600)明军平定播州之乱,万历三十一年(1603)即出现《征播奏捷传》;万历后期完稿的《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距林兆恩万历二十六年(1598)去世不过十数年;天启二年(1622)发生徐鸿儒白莲教起义,天启四年(1624)即有《七曜平妖传》的完稿;以魏忠贤为题材的系列小说面世更快,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魏忠贤自尽,次年六月即有《警世阴阳梦》出笼。可见,小说反映现实的速度越来越快。对于这类小说,郑振铎称之为“实事”小说(17),叶德均称为“今闻小说”(18),今人称为时事小说。时事小说是当代人写当代事,内容“动关政务,事系章疏”(峥霄主人《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凡例》),是从历史演义中衍化出的一个支流。目前学界一般认为万历时期的《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征播奏捷传》、《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及天启年间的《七曜平妖传》已具早期时事小说的形态,尤其是《征播奏捷传》,有人称其为第一部时事小说(19)。《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传》、《郭青螺六省听讼录新民公案》都是公案小说,前者所写故事虽托名海瑞,但其实绝大部分都是虚构的,是把民间传说的断案、折狱故事都放在海瑞身上或抄自他书;后者塑造的郭青螺形象,乃江西泰和人郭子章,曾在福建为官,先后任建宁府推官、摄延平府事、福建左布政。从现存史料看来,他对法律并无专长,对刑名断狱也没有研究,他的清官断狱形象也显然是创造出来的。《征播奏捷传》演义万历年间李化龙平定播州杨应龙之乱,其中所写有很多不经之处,情节与历史严重不符。有的情节是对《牡丹亭》、《金瓶梅》等小说戏曲的拙劣模仿;有的故事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宣扬因果报应,如把杨应龙之妻说成为龙虎山张真人之女等;战斗描写神魔化,如第七十三、七十四回敌将五知事与张真人斗法的描写。以致时任贵州巡抚、参与指挥平叛的郭子章晚年退休家居时,看到这些小说“左袒化龙,饰张功绩,多乖事实”,“乃仿记事本末之例”,写成《黔记》、《平播始末》,“以辨其诬”(20)。作者自己也在后叙中承认书中所写“未必言中款款事事协真”(21)。《三教开迷归正演义》讲述崇正里有狐精从地狱中逃出,并放出众迷魂。大儒、宝光、灵明恐迷魂到处迷惑世人,败坏世风,扰乱社会,立志外出破迷。他们一面寻访林兆恩,一面破各地的迷魂。作者把神魔和世情融为一体,别具一格。《七曜平妖传》描述北斗七星转世为明山东巡抚赵彦、登州总兵沈有容等人,魔女裴月娥、周如玉反正辅佐,荡平白莲教沈晦、高糜、洪流等妖道,剿灭徐洪儒、乜巢儿义军的神怪故事。通篇没有直接写双方军队对垒的实战场面,而是着力写双方如何在阵前斗法。可见《七曜平妖传》和《三教开迷归正演义》都是以神魔的手法写时事,时事小说的作者均以“非敢妄意点缀”(陆云龙《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序》)相标榜,上述所谓“时事小说”中有大量的神怪描写,显然不符合时事小说的基本要求,虽号称写时事,其实当时的人或事只是一个“壳”而已,总之还难以摆脱传统写法的束缚,基本可划为“神魔小说”的类型。《金瓶梅》则借宋AI写作明代事。目前虽不清楚《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成书的确切年代,但大约在万历前中期是可以肯定的,距离嘉靖倭乱的时间不长。所以,《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可能是最早一部由文人独创、全面展示东南沿海的抗倭斗争,真实地展现明中叶的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的时事长篇小说或写实长篇小说,而且叙事手法不同于说书体例的章回小说,全书分卷,回目为单句,中间穿插了不少朝廷奏议,有些章节,如有关宗臣的描写部分,乃根据宗臣的散文稍加修改而成,可见该书乃仓促成书,符合时事小说的所有特点。明代其它以倭寇为题材的小说都可归为时事小说的范畴。从现在的情况看来,明末清初的时事小说一般是在江浙书坊刊刻的,所以,大致可以断定建阳书坊是时事小说的开创者。 与题材的现实转型相适应,“抗倭小说”的创作思想与审美趣味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倭乱是明代的一件重大历史事件,促使明代小说家关注现实问题,创作思想、审美趣味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使得前期风行一时的历史演义、神魔小说开始让位于描写当代事件的小说。小说中的主人翁也由历史英雄、神话英雄变为现实中的英雄。历史演义和神魔小说中的英雄一般都是超人,他们有超强的武功,神奇的法术,人物形象呈现出类型化的倾向;战斗描写大多是双方将领大战几十回合或念念有词、呼风唤雨之类的术士斗法程序化模式,与真实的战争描写距离甚远。至《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打破了说书体的叙事视角,战争描写基本符合历史真实,不再对出场将领的装束、相貌进行冗长的描述,不再依赖极度的夸张和幻想,战争描写突出“智”的作用,更为逼真。当然,清代的“抗倭小说”重又回到神魔化的老路,但其对突破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叙事模式有一定影响。传统的才子佳人小说叙事模式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才子之“才”主要体现为诗赋之才和制举之才;而与抗倭题材结合的才子佳人小说,则变为“洞房花烛夜,平倭成功时”,小说中的才子和佳人不再是文弱书生和病态西施,既有诗赋之才、制举之才,也有军事之才,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月岩氏在“《雪月梅》读法”中说:“华秋英是第一人物,历观诸书,有能诗赋者,有能武艺者,有绝色者,有胆智者,而华秋英则容貌、才华、胆量、武勇无不臻于绝顶,当是古今第一女子。”《雪月梅》虽属言情小说,但完全突破了才子佳人私订终身、金榜题名等俗套,岑秀与雪姐、月娥、小梅的婚配主要是作为全书的贯穿线索,使众多的人物和情节得以组织起来。 审美趣味的变化还表现为作者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态度严肃,力求理性和客观,把握好分寸,重视人物性格的多面性和层次性,而不是简单地贴上正邪、好坏的标签。除了上述胡宗宪性格的多面性之外,如《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中福建都御使刘焘,既肯定他英勇能战,又鞭挞其好大喜功,轻敌冒进,甚至暴躁易怒、滥杀无辜、贪婪好钱等恶行。即使贪酷、无耻的阮鹗,作者也不抹杀他向朝廷举荐戚继光之功。此外还有徐国公、曾于拱等。这些人物的性格特点及历史功过,作者都拿捏得比较准确,与当时及后世的公私史著所述大致不差。即便如正面人物,作者也不讳言他们的性格缺陷,如曹邦辅的部队军纪败坏,戚继光在叶娘被刘焘杀害、其夫吴生向他求助时,他非但没有谴责刘焘,反劝吴生道:“何如以一女子而丧平日之英雄耶?且亡者不可复存,死者不可复生,况草堂刘公所为之事,吾不能如其万一,事在已往,言之何益!”吴生于是绝望自杀,戚继光为之恻然,于是下令“凡所夺回男女,必令人寻觅携去,不责偿也”。作者注意到这些人物性格形成的历史情境,没有故意拔高。就是那些万恶不赦的倭酋,作者也没将他们简单化、脸谱化,而是在谴责的同时表现他们的胆略和豪气。如《胡宗宪平倭战功》既说王直“少时有无赖泼撒之气”,长大后结交匪类,又说他“极肯施舍”,“极有信行,凡是货物,好的说好,歹的说歹,并无欺骗之意。又约某日付货,某日交钱,并不迟延。以此倭奴信服,夷岛归心,都称他为‘五峰船主’。”与之前章回小说中的平面化的人物形象相比,明代抗倭小说中的人物性格更为丰富,形象更为生动,更有现实感,更真实可信。 要而言之,明清“抗倭小说”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和文学创作现象,它持续时间长,品种数量多,与我国明清两代的社会、政治生活息息相关。在其身上,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历经战争磨难的历史记忆,而且镌刻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勇于抗击外来侵略者的民族基因与精神品格。在中国古代小说史上,明代“抗倭小说”还是我国时事小说的重要开端,它为小说史的发展拓宽了题材领域,注入了新的现实品格。自明代倭乱直至今日,产生了大量以之为题材的小说、戏曲、诗歌、散文、笔记、影视等作品,形成一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值得引起我们重视。 ①金安清:《东倭考》,《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倭变事略》,第206页,上海书店、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②③沈一贯:《论倭贡市不可许疏》,陈子龙:《明经世文编》第六册卷四三五,第4759页,第4759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④田中健夫著、杨翰球译:《倭寇海上历史》,第113—115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⑤⑨万历二十四年(1596)御史朱凤翔上书请抚恤于谦、胡宗宪后人中语,王士骐:《皇明驭倭录》卷之九,《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第193页,第7—8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⑥郑晓:《吾学编·四夷考》,《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2册,第710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⑦俞大猷:《论海势宜知海防宜密》,《正气堂集》卷之七,《四库未收书辑刊》第20册,第190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⑧谢肇淛:《五杂俎》卷之四“地部二”,第11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⑩谢杰:《虔台倭纂》上卷,《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10册,第249页,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11)蔡景榕:《海国生还集·上兴化太尊钱春池状》,转引自范中义:《戚继光传》,第66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12)佚名:《嘉靖东南平倭通录附录》,《中国历史资料研究丛书·倭变事略》,第59页,上海书店、神州国光社1951年版。 (13)焦竑:《荆川公传论》,唐鼎元:《明唐荆川先生年谱·附录》,民国二十八年(1939)铅印本。 (14)戚祁国:《戚少保年谱耆编》,第33、40页,中华书局2003年版。 (15)王士性:《广志绎》,第77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16)谈迁:《国榷》,第3986页,中华书局1988年版。 (17)郑振铎:《中国文学新资料的发现》,《中国文学研究》(下),第1335页,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 (18)叶德均:《戏曲小说丛考》,第603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19)傅礼军:《中国小说的谱系与历史重构》,第233页,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 (20)《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四·史部一○·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二卷”。 (21)《征播奏捷传》,第50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 (22)程毅中:《程毅中文存》,第286—287页,中华书局2006年版。标签:小说论文; 戚继光抗倭论文; 文学论文; 明清论文; 胡宗宪论文; 绿野仙踪论文; 雪月梅论文; 西湖二集论文; 倭寇论文; 醉醒石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