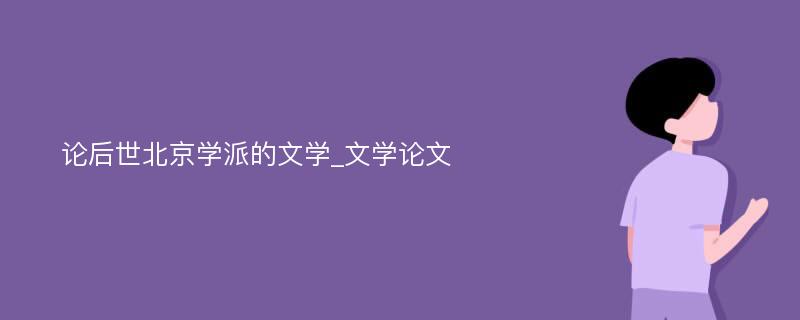
论后期京派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京派论文,后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京派:从趣味主义到审美乌托邦
一、以一场论争为起点
就京派研究的现状而言,1934年前后的京、海浪论争是京派文学的起点还是京派历史的转折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自从严家炎先生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中第一次较准确地对京派的构成作出了界定,京派的来龙去脉就激起了更多研究者的兴趣。其实,京派历史的复杂性并非只在于它所包含的成员的复杂性,如果就“自由主义”范畴内来关注和理解京派文学,我们既已看到它与海派文学的诸多区别,同时也必须看到其庞杂的作家队伍其实远非一个真正完整的统一体。在京、海派论争中,沈从文的“发难”文章《文学者的态度》缘引了一个平凡生活的“俗例”,拈出“严肃”二字欲以规范自由主义作家们的文学行为,所针对的首先便是一场由周作人、林语堂首倡,在京、海两地正方兴未艾的小品文风潮。或许正是由于他那个固执又有点不谙世故的“乡下人”头脑把这一庞杂的文学现象的历史内幕想象得过于单纯,又仅仅拈出了“玩票白相”这样一个足以惹恼上海文人的用语说明本质,由此,一场牵动八方、旷日持久的论争便不期然中拉开了序幕。论争伊始,“京派”、“海派”粉墨登场,鲁迅迅速作出了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判断。但当各方轮番上阵,口诛笔伐正酣时,鲁迅对此却有了新的认识。在《“京派”和“海派”》一文中他说:“当初的京海之争,看作‘龙虎斗’固然是错误,就是认为有一条官商之界也不免欠明白”。原因在于他已看到,上海滩上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小品文刊物,如《人间世》、《文饭小品》等,因惯奉周作人等为领袖,常有“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此番景象,映入鲁迅眼中莫不呈现一派“京海杂烩”的缭乱之势(注:鲁迅:《“京派”和“海派”》,《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2-303页。)。从而表明,一场“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席卷南北的小品文狂潮正是在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等南北呼应,合力鼓噪下成为一时风尚的。
历史地看,小品文运动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一次高潮。然而,小品文在一派“幽默”、“闲适”、“趣味”的招摇下成为时尚,正是初期京派文学误入歧途,京、海派文学在同一的消极化文学旨趣下渐趋合流的表现。众所周知,在自由主义原则下,文学的消极化个人主义姿态与积极的社会性文化追求从来就是一对矛盾。正是在这一情形下,沈从文等欲以“卫道”者的姿态挺身而出,大声疾呼的虽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严肃”,但一种欲创造于具有高尚情感和至上追求的文学的意志和愿望,已经至为清晰地昭示在未来京派文学的观念领域和实践行为之中了。
在那篇“发难”文章中,沈从文正是在要求于文学的严肃旨趣中掂出了在所谓“文学者的态度”问题上存在着的对立的两极。这也并非只是京、海派之间的区别,当时的南北文坛上显然都存在着他所谓的“玩票白相”者。他说:这些人不仅“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也在北京“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且作为“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注: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154页。)。这些批评也正印证了鲁迅当年的观察。显然,在通常所谓“海派”之外,沈从文也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北方文坛上的周作人等。
二、前期京派与后期京派:从周作人、废名到沈从文、朱光潜
在《论“海派”》中,沈从文认为:“海派如果与我所诠释的意义相近,北方文学者,用轻视忽视的态度,听任海派习气存在发展,就实在是北方文学者一宗罪过”(注:沈从文:《论“海派”》,《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160页。)。在《论冯文炳》中他认为,周作人散文“文体风格独特”处,在于“从为平常眼睛所疏忽处看出动静的美”,但“作者所表现的僧侣模样领会世情的人格”显示了并非健康的文学的“趣味”。指出:“在文章方面,冯文炳君作品所显现的趣味,是周先生的趣味”。就废名而言,“在北平地方消磨了长年的教书的安定生活,有限制作者拘束于自己所习惯爱好的形式,……情趣朦胧,呈露灰色,一种对作品人格烘托渲染的方法,讽刺与诙谐的文字奢侈僻异化,缺少凝目正视严肃的选择,有作者衰老厌世意识”(注:沈从文:《论冯文炳》,《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96-97、101页。)。将其与“海派”穆时英等联系起来,沈从文认为,“废名后期作品,穆时英大部分作品,近于邪僻文字。虽一则属隐士风,极端吝啬文字,邻于玄虚,一则属都市趣味,无节制的浪费文字,两相比较,大有差别,若言邪僻,则二而一”(注:沈从文:《论穆时英》,《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203页。)。
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史上看,“趣味主义”的小品文运动存在于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后期《语丝》向《论语》的延续。20年代末期随着鲁迅与语丝社关系的疏离,这一群体的文学倾向经历了从社会批判向文化批判的转型,继而在自由个人主义的意义上向传统知识分子的“隐逸”文化心态认同,文学旨趣趋于消极。《语丝》终刊后,在周作人的支持下,废名、冯至等1930年在北平创办《骆驼草》周刊,其《发刊词》中说:“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如斯而已”。在此,小品文不仅是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如周作人所说的,代表“文学发达的极致”,被推举到了“个人的文学之尖端”(注:周作人:《〈冰雪小品选〉序》,《周作人散文》第2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而且带着“冲淡”、“闲适”的趣味主义姿态,向小说、诗歌等其他体裁中渗透。从《骆驼草》上可以看到,周作人、俞平伯、梁遇春的小品散文,冯至的诗,废名的小说,徐祖正的文学批评等,集合着初期京派文学的基本阵容,反映出趣味主义文学的面貌。日后沈从文在谈论到它的时候,尚未免语露轻蔑,他说:“1930年,在北方,还有《骆驼草》产生,以趣味作‘写作自由’的护身衣甲,但这趣味的刊物旋即消灭,使人忘记”(注:沈从文:《〈雪〉序》,《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14页。)。
但《骆驼草》的“消灭”并非意味着小品文运动的终结,随着1932年《论语》在上海创刊,然后则是《人间世》、《宇宙风》等簇拥成了30年代上海滩上的“小品杂志年”。周作人被奉为南北文坛的领袖。于是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注:鲁迅:《一思而行》,《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此时在北方文坛,按捺不住愤激之情的不仅是沈从文,更有朱光潜等。1935年,沈从文发表《谈谈上海的刊物》一文,认为小品文的倡导者“要人迷信‘性灵’,尊重‘袁中郎’,且承认小品文比任何东西还重要。真是一个幽默的打算”(注:沈从文:《谈谈上海的刊物》,《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178页。)!1936年初,朱光潜则以回复徐訏约稿信之机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表达自己对于小品文运动的观感。他认为,小品文的泛化造成了一种“制造假古董”的萎靡世风。“滥调的小品文和低级的幽默合在一起”,阻碍了人们创造和接受严肃、高尚的文学的情趣(注:朱光潜:《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427-429页。)。
上述内容说明,在对待小品文运动的不同态度上,凸现出前、后期京派文学中存在着具有替代性关系的两极,从而在京派文学史上把由周作人、废名等所代表的“趣味自由主义”,和以沈从文、朱光潜等为代表的审美理想主义(审美乌托邦),在所依托的美学理念和所欲达到的文学(文化)目的上区别开来。以此为起点,并在后一种代表性上开启了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后期京派文学”。
联系到京派历史的实际进程,如果说前期京派正是在《语丝》解体后以周作人为中心围绕着《骆驼草》(及在向“论语派”的延伸中)所形成的集合,那么,所谓“后期京派”就必然是脱离了周作人影响力后这一群体的新的集结。从理论上说,这必然联系着京、海派论争中沈从文、朱光潜等对于周作人、废名及其小品文运动所负载的趣味主义文学倾向的批判。从历史上看,正是这一新的集结过程渐次瓦解了周作人在北方文坛上的巨大影响力,从而使京派文学在拒绝小品文志趣后区别于海派文学得到“振作”和重造。1933年9月沈从文应约主编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后,就立志使其在文坛上独树一帜。“传统之一是尽量不登杂文”,不“专在名流上着眼”,致力于培养文学新人(注:萧乾:《一个副刊编者的自白》,《萧乾选集》第3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8-439页。)。在此基础上,1937年在朱光潜、沈从文、林徽因、巴金、李健吾等主持下颁发“大公报文艺奖金”,更被视为当时“严肃”文坛的盛举,从而实现了京派文学的历史转型。同时,从以《学文》作为创办“同仁刊物”的试验到朱光潜主编《文学杂志》创刊,后期京派作家们在“自由生发,自由讨论”的宗旨上对于“艺术良心”的张扬确也给不甘沉寂的北方文坛带来了新的希望。而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朱光潜的美学理论,沈从文的创作实践,李健吾的文学批评等,在共同的审美乌托邦志趣下,常构成新的京派文学“三位一体”的重心。
时间性上的“后期京派”正是以上述文学认知和实践原则的获得为前提,活跃在从抗战前夕到40年代以《文学杂志》相维系的那个独特的“学院派”文学群体。该刊时隔十年的分聚表明这一群体的活动不是以抗战爆发为终结,而是在被迫脱离其特定地域环境后因作家的战争体验而发展和深化。从战前和战后的北方各高校,到战时的西南联大及朱光潜等任教的成都大学、武汉大学等,这一群体在自发肩负起培养文学新人的使命中也不断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其主要代表人物而言,无论是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林徽因、凌叔华、梁宗岱、李长之等,还是作为后起之秀的萧乾、芦焚(师陀)、田涛、袁可嘉、穆旦、汪曾祺等,以及在逐渐疏离周作人影响后获得新的造就的废名、冯至等,正是他们在40年代的文学实践及不同成就,丰富并完善了具有特殊历史意义的“后期京派文学”。
二、审美乌托邦:后期京派的美学世界
“后期京派文学”作为体现自由主义积极文学(文化)旨趣的独特文学形态,在既与海派文学相对峙,又与前期京派文学相区别的意义上,对于在中国新文学观念体系中确立现代美学认知原则具有重要意义。其最鲜明的特征是,在作为本体论建构的文学观念世界中,呈现出如下“乌托邦”式的美学图景:
一、直觉与“观照”:情感本体论的艺术视野与审美理想主义的艺术实践观
西方现代美学理论中,“乌托邦”的文化意象所标示的艺术自由或独立性原则,是以艺术作为人类情感自由或心灵自由的体现,使之凌驾于一切现实原则之上。由此考察沈从文等的创作活动,不难找到这一“乌托邦”情结的恰当印证。40年代,沈从文曾借《水云》一文陈述自己的创作心迹,他动情地描述道:以情感掺和着想象,映入艺术视境中的一切,“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便得以造就(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287-288页。)。
作为美学家的朱光潜,曾通过引进克罗齐“直觉”论,在对于美学和艺术理论的系统性创建中揭示出了这一艺术原则的美学认识论根源。在他作为后期京派理论家的美学创意中,他把克罗齐的“直觉”论引申为“表现”论,赋予它三重寓意:第一,艺术在于表现,表现的意蕴为象征:第二,艺术表现的本质是主观的(心灵的),而表现的手段是客观的(对象化);第三,艺术以情感为源泉,以抒情为特征,它体现的是人类心灵的自由,因而也是最高的自由。尽管朱光潜的引述并非真正依据着克罗齐的原意,但确实提供了一个合于“乌托邦”式的艺术运作方式上的普遍性原则:它把情感—表现—象征,以及“心灵的自由”作为一切艺术活动中的规律性法则并以“直觉”的美学赋意贯穿起来,显得艺术活动的本质就是以情感活动及其所获得的心灵自由为主体,达到艺术形式(审美形态)上的表现和象征。后者作为结果,就是一种在对象化的“外物”(艺术创造物)身上所显现的精神(情感或心灵)的“乌托邦”构筑(艺术世界)。
在审美乌托邦的美学赋意下,在后期京派作家们的艺术观念中,文学的情感化表达常常被看成是审美者(鉴赏者或艺术家)与审美对象之间具有一种“心理距离”的结果。朱光潜借用英国心理学家、美学家布洛(Bullough)的“距离说”欲以“辩护”中国艺术,同时也是“辩护”后期京派作家的美学观和艺术观。在“距离”说的指摄下,不仅“乌托邦”式的艺术体验被凌驾于一切现实原则之上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作家所从事的艺术活动的内在目的性与现实社会实践活动所具有的直接目的性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差异也不足为怪。沈从文把艺术中的情感活动看作是由“回忆”生成的“体验”,亦是与所把握的直接物象具有“距离”的结果。他说:现实使人心变硬,“温习过去,变硬了的心也会柔软的!”他看待艺术活动中的“我”既是情感活动的主体又是审美活动的“旁观者”。如果说“我”的情感的生成往往取决于对于现实物象的微妙关系的把握,那么,情感的美丽而具有“神性”的庄严,必在审美意识上置“我”于一种“忘我”的方式上。唯有“完全消失到一些‘偶然’的颦笑中和这类颦笑取舍中”,于“谦退中包含勇气与明智的美丽”,才能更恰当地体现审美主体的存在(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296、287页。)。这样,作为审美主体的艺术创造者就是一个纯粹的“乌托邦”式的幻想者。这正如李健吾在对《边城》的评论中所示:沈从文以“热情”达致“同情”所创造的人物,却不是情感无节制地宣泄,也并非“冷眼观世”的结果,“他知道怎样调理他需要的分量。他能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功一篇无瑕的玉石。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发见可能的美丽”。这乃得益于他“量入为出”地把握情感活动的方式。这样,“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仿佛有意,其实无意,他要读者抛下各自的烦恼,走进他理想的世界,一个肝胆相见的真情实意的世界。”(注:李健吾:《〈边城〉》,《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因此,造就出一种艺术的“乌托邦”情景,也在于通过鉴赏活动,使读者的情感世界拉开与实生活的距离。李健吾曾要求批评家如法朗士一样,把批评视若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从而期待于一场灵魂的“奇遇”。这既是艺术的“和谐”,也是体验的真实。它代表着人的情感化的内宇宙,通过艺术的方式(“直觉”的把握或“象征”的显现),在“乌托邦”的氤氲氛围中达到了默会、交流和贯通。可见,以情感化为基础,距离的美感体现了这种艺术把握和认知方式的本质。
“距离”标示了情感的生成机理,而“观照”则显示了他们所进行的“乌托邦”式的艺术活动的真实情景。在创作中,沈从文把自我的情感活动隐约在作品所包含的审美意象的背面,而以审美主体的地位凌驾于自我所造就的艺术世界之上,就是这种“观照”的方式的体现。朱光潜等的美学表达则是对于这一情态的说明。朱光潜曾借助于阐释尼采有关“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学说认为,具有日神精神的艺术家“是一位好静的哲学家,在静观梦幻世界的美丽外表之中寻求一种强烈而又平静的乐趣”。“他深思熟虑,保守而讲究理性,最看重节制有度、和谐、用哲学的冷静来摆脱情感的剧烈。”(注:朱光潜:《悲剧心理学》,《朱光潜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5页。)这既是自我的沉静,也是审美的超越。体现在艺术活动中的立场就是“观照”的立场。唯有“观照”,对象才能显示为美。“观照到了极境,真也就是美,美也就是真”(注:朱光潜:《看戏与演戏》,《朱光潜美学文集》第2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555页。)。梁宗岱在他的“纯诗”理论中,也以“冥想出神,形神两忘”来阐说这种境界。认为正是“观照”于对象的立场和审慎地对待自我相结合,使诗人(或艺术家)猝然间“放弃了动作,放弃了认识,而渐渐沉入一种恍惚非意识,近于空虚的境界,在那里我们底心灵是这般宁静,……忘记了自我底存在而获得更真实的存在”(注:梁宗岱:《象征主义》,《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这样一种情郁自守,沉静通脱,玄思妙想,物我两忘的境界就是一个真实而形象的“乌托邦”的艺术理想国。在朱光潜看来,这不仅是那些表现于“行动”,放纵于情感的“酒神”式的艺术家们(犹如“海派”)所无法达到的境界。也是与那些“滑稽”而哀怨,厌世而玩世的“趣味主义”艺术的追求者们无缘的境界。在审美的情趣上,前者表现出的“热”和后者表现出的“冷”,都不及“日神”式的艺术家们在“观照”中所显现的“静”。这一美学情趣和艺术原则上的自我定位,揭示了他们生存于艺术的“乌托邦”的世界的又一理想主义特征。
二、悲悯与“崇高”:“乌托邦”世界的生命意识和现实情怀
本质上看,艺术的“乌托邦”理念是一种反思性理念,其理念的内涵上不仅具有着一种通过“反思”使自我凌驾于现实之上的目的,并企图以同样的方式使情感化的自我与现实关系中的自我隔离,以取得一种“反省”的姿态。在“反思”或“反省”的立场上,审美主义的认知方式告诫人们:一切现实关系中的理想化假设都是虚幻之境,“现实界决没有所谓极乐美满的东西存在”。人类真正的理想,就象一根牵曳人类向上的绳索,总只能在人的精神世界或精神生活中逗留。艺术就是展现这种理想并引导人们去追寻一种理想化图景的,同时也启发人们去真正地理解现实,正视现实。从而,悲悯就成为他们涂抹在现实世界和现实人生中的真实色彩。
沈从文断言:“人生可怜。”这是他站在艺术的“乌托邦”世界里发出的由衷感慨。梁宗岱在诗的象征世界里,发见了宇宙中“一个更庄严,更永久更深大的静——死。”(注:梁宗岱:《象征主义》,《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5页。)朱光潜在他的美学理论中认为能以激发美感的“道德感”(广义的人类理想)只能是悲悯。因为以“道德”的观点看世界,一方面是“我”(或艺术)的理想,一方面就会发现一个对立于“我”(或艺术)的理想的非“道德”的世界。李健吾认为,正是作家立足现实的“悲观精神”和观照于人物的“命定论”赋予了艺术悲天悯人的“同情”。一个懂得“悲观哲学”的艺术家不会让读者(或观众)接受一种“轻而易举的下流幸福”。这正是现代艺术与传统“道学家”式的“艺术”至为深刻的区别(注:参见李健吾:《〈苦果〉》、《旧小说的歧途》,《李健吾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
反映在艺术实践上,追求表现于现实的“缺陷美”成为他们思维的一种定式。而人物的命运(卑微或伟岸),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都被“乌托邦”的艺术理念串连起来,赋予艺术家一种使命感和体现于精神的完美性。沈从文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用“坦白与诚实,以及对于人性细致感觉理解的深致”,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赞颂,在充满古典庄严与雅致的诗歌失去光辉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他以人的观念写“神”,也以神的观念写“人”。“用自己尺寸度量人事得失”。“在一种极端矛盾情形中……却感觉生命实复杂而庄严”(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294、290页。)。——在这种情调上,《水云》,恰如一个悲情者的梦呓。犹如一种同生共感的情结,梁宗岱说道:“能够从破碎中看出完整,从缺憾中看出圆满,从矛盾中看出和谐”(注:梁宗岱:《李白与哥德》,《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方是一个艺术家的才能。于是,在“震荡着虔诚,悲悯,纯洁与慈爱的祷词里,咒诅远了,怨毒与仇恨远了”。一切平凡的,偶然的,易朽的,无不“同时达到一种最内在的亲切与不朽的伟大”(注:梁宗岱:《象征主义》,《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乌托邦”艺术的内倾性及其深致高妙的外在指向于此结缡。
与一种“乌托邦”式的情感化艺术理念所共生的,除了这种贯注在普通“人事”上的感叹,乃是一派情趣抑郁中的“乌托邦”式的崇高。朱光潜认为,悲悯不是“怜悯”,作为“审美的同情”,它本身是包含着崇高的。现代艺术中的“崇高”性理念是“平等”,是生命的悲剧意识,而不是古典主义艺术和传统浪漫主义艺术中的“英雄崇拜”或“个人崇拜”(自我崇拜)。梁宗岱的观点在于,“崇高”者并不在“力”,只是“美底绝境”。就“表现”而言,在于艺术家通过“内在的自由与选择,以达到表现之均衡与集中”。是“形神无间的‘和谐’”和“天衣无缝的‘完美’”(注:梁宗岱:《论崇高》,《梁宗岱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113页。)。沈从文的“崇高”感在于“‘人’的自尊心的觉醒”(注:沈从文:《读〈论英雄崇拜〉》,《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384页。)。显然,在形式主义艺术实践和认识原则下,“崇高”作为一种以艺术人格化达到人生艺术化的内在和谐性理念,实践了“乌托邦”艺术的创造者们欲“以出世的态度,做入世的事业”的人生理想。
三、富丽悲悯的艺术之宫:后期京派的文学世界
一、梦幻“乡土”
对沈从文的《边城》记忆犹新的人们或许不会淡忘了30年代京派文学的品格和追求。就“乡土小说”而言,废名在京派文学史上的开拓性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历史地看,以沈从文、废名为代表,京派乡土小说家们正是在视艺术即梦,情感即真,亦即在朱光潜所谓“理想界”与“现实界”二元对立的观念中建构并实践着他们别具一格的艺术创造的。
但是,在周作人、废名那里,艺术即梦的象征作用往往在于它的神秘感,即自我的目的性。在废名的小说中,“乡土”总是被反复定位在作者儿时生活和见闻的狭小空间,亦因是“梦”,尽管是反复咀嚼犹未免其时时新日日新。与废名不同,沈从文在其“乡土”的世界里并不满足于梦,即不满足于一种飘忽不定的单纯的象征——他要寻觅有益于“人事”的答案。尽管在他的小说中,与废名一样,梦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常常是混和着的,但他绝不把自己笔下的精彩等同于梦的神秘离奇。一方面,他认为一味咀嚼着“空洞美好的回忆”是无益的,不能够令人向往光明。复古的趣味更其是一种吞噬自我灵魂的行为。另一方面,他看到,“现代”,如果它以“文明”所展现的只是一大堆散发着铜臭和势利气息的欲望,也不足以令人神往。于是,把自我粘附在“人事”上面的一点“小小的欲望”寄托于感兴的“乡土”及由这“乡土”所生衍的故事上面,作为“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推举出来。沈从文以为,“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用我作品去拥抱世界”(注:沈从文:《〈篱下集〉题记》,《沈从文文集》第11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34页。)。因而,他要创造一种不同于过去时代的真正的艺术。这种艺术不仅仅是寄托的,更是象征的,是隐约于“古”与“今”的夹峙中烘云托月般而出的如梦似幻的艺术之宫。作为黯然的现实的倒影,闪烁着“乌托邦”的华丽氤氲色彩。
历史上,正是由于抗战的爆发暂时打破了后期京派作家们那份对于“乡土”的沉湎,使他们重新直面人生苦难的现实。面对战争,沈从文感慨系之:“战争把世界地图和人类历史全改变了过来,同时从极小处,也重造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及这个人在那个人心上的位置”(注:沈从文:《水云》,《沈从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286页。)。战争改变了他对于“人事”的看法,在创作中把用“抒情诗”的笔调写“神”转变为用“散文”的笔调写“人”——这确乎是他从《边城》到《长河》所发生的创作倾向上的变化。在长篇小说《长河》中,作者所唱响的已不再是一曲单纯的人性美的赞歌,而包含了他面对战争的现实,对于人性问题作出的真正理性化的思考。审美化的人格理想和观照于现实的艺术趣向相结合,一方面,他把人性的纯美、自强不息、忠诚、善良、大义凛然等,仍视为反映湘西民族生活的人情风俗的本真状态。另一方面,将其放在风云变幻的大时局面前,使他感到,一切人性的“常数”都面临着“变”的考验。“这世界一切既然都在变,变动中人事乘除,自然就有些近于偶然与凑巧的事情发生,哀乐和悲欢,都有他独特的式样”(《长河·人与地》)。在老水手、夭夭、满满、三黑子这些人物身上,我们尽可以看到《边城》中老船夫、船总顺顺、翠翠、傩送二佬宛若相亲相识的面貌,但是,随着对立面的出现(保安队长、师爷等代表的社会邪恶势力),加上“新生活”、外敌入侵等外在压力的来临,一场历史性的正义与邪恶的争斗必不可免,其中必然蕴含着更真实而深刻的人性善恶之争。
战争所造成的苦难的现实使后期京派作家们暂时放弃了对于“乡土”的精神品格的塑造,转向对于人的真实生存境况的“观照”。这不啻使他们笔下的“乡土”多了一种源于现实的苦难况味,凸现出“流亡者”自我难于割舍的故土情怀。在芦焚笔下,现实的故乡——尽管是那块使人不得不背离的贫穷的土地和一群生息无趣的愚弱的乡民,一旦被笼罩在外凌内辱的巨大的苦难阴影下,它就使人更多了一种牵肠挂肚的情愫。从30年代的“百顺街”到40年代的“果园城”,一种“恋土情结”所由生的爱恨交加的情绪,使作者重又沉湎于那份对于北国故土的“缠绵”。然而,与一个迷醉却又清醒的怀乡病者的梦境极不相称的是,这里生活着的却是一群值得埋藏的“古董”,单调生活的蛀虫和不合时宜的“事业家”——芦焚所怀念的“果园城”就是这样一个美丽而凄艳的所在。在“嘲讽”的外表下,作者奉献给故乡的却是一颗更真切地感受着苦难的心。在《果园城记》中我们看到,沉浸在“同情”和幻想中,作者更象一个真正的果园城人,“多么善用夸大的言辞和天赋的想象力”以满足他的怀乡梦。就象那个受人诅咒的水怪“阿嚏”,为了不想再让倒霉的果园城人碰到时一样,一旦不声不响地离开了这个令人气闷的“鬼地方”,反过来,“当他高兴或有所怀念的时候”,却隐忍不住要再去看看那片故土,甘冒再受诅咒的危险。从而,“一种极自然的情感,……我们只有在闲着的时候才会想到往昔的种种……破碎的冷落的同时又是甜蜜的旧梦,在我们心里,每一个回想都是一朵花、一支香味、云和阳光织成的短歌”(《果园城记·阿嚏》)。
二、悲悯人生
在受到过沈从文引导的北方作家中,田涛在40年代的创作中表现流亡和苦难的主题堪称孤绝。无论是《流亡图》和《潮》中那些空有救国抱负而无救国本领的青年学生男女们,沉浮在民族苦难的潮汐中所遭受的灭顶之灾,还是作者在《灾魂》、《饥饿》,以及长篇小说《沃土》等之中对于北方人民在战争和灾荒中的苦难生活的直接描述,其情景无不令人惊心动魄。其中,田涛用一种看似“纯客观”的描述,却使自己如啼血杜鹃般的故土情怀,在作为苦吟诗人的漫长的流浪行旅中,无时无刻不以精神的目光深情而又沉痛地注目于那块灾难中的土地和上面的受难的人们。无庸讳言,作者在作品中所展现的特定的悲悯情怀,乃是出自京派作家们惯常的对于生活的悲剧观念,但正因如此,一种悲天悯人般的博大的“同情”的力量贯注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它把有关“人”的命运本质的问题,通过表现于战争中个人、家庭、民族浑然一体的“苦难”,朴素而真切地揭示出来,从而产生了一种超越作者艺术表现能力的永久的艺术魅力。
芦焚的长篇小说《结婚》更直接地提供给我们一个透视战争年代卑微人物苦难命运的范本:在战争中做着发财梦的“小人物”胡去恶,他忘记了作为人,善良并非真正只是累赘和苦难的根由,而要在民族的炼狱或受难的母亲的肌体中去过一种吸血鬼似的生活,在没有真正把自己由人变成鬼之前,他的命运就只能攫在那些真正的鬼之手中,
与沈从文、芦焚、田涛等悲悯人生的立场相对应,在冯至、废名的创作中,透过其隐晦奇崛的自我化艺术表达,却使人看到了面对灾难的现实,在不同的思想轨迹中寻觅着各自的拯救与解脱之道。抗战前数年的留德生活,使冯至不仅从里尔克(Rilke)那里领略到了以艺术凝固思想而显示的巨大的“象征”的力量,也使他在整个西方存在主义哲学的思想背景下,从雅斯贝斯等存在主义大家那里,领会了通过澄明自我的“实存”性摆脱“形而上”意识的束缚,获得现实的“自我拯救”的思路与途径。小说《伍子胥》中那个不甘象父兄一样以身饲虎的逃亡者伍员(子胥)的形象,他的关于自我的“存在”感显然不是纯精神性的;对于死亡,他没有恐惧,所谓“镞矢之疾”、“飞鸟之影”,生命之然矣。但是,即如一道当空画出的“美丽的弧”,其中却有“无数的刹那,每一刹那都有停留,每一刹那都有陨落”。——“停留”和“陨落”都是两种“存在”的形式,通过自我“克服”达到“自我拯救”或是走向自我消亡。出走后的伍子胥就是在各种连绵不断地“克服”中获得了一个被拯救的自我。于是,作者也和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渐渐脱去了浪漫的衣裳,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炼着的人”(注:冯至:《伍子胥·后记》,《冯至选集》第1卷,四川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370页。)。自我的被拯救无疑等于获得了一种“存在”的新形式。所以,面对溧水边上那个美丽善良如神明的浣衣女郎,伍子胥才恍若重获新生般欣喜。一切对于自然和命运的感觉都顿然改变了性质。正是为了这样一个美丽动人的结局,小说中一切所谓“幽郁”和“神秘”的色彩才不仅折射出诗化的自然本色,也成了那个被“克服”的命运所焕发的瑰丽色泽。
在40年代,如果说冯至通过在艺术中获得“自我拯救”所展现的心路历程昭示了他的新的人生经验,也标示了以一种艺术化的人生感悟向现实的人生理想发生迁移的思路或途径,那么,对于废名而言,他的一如既往的“人生理想”无疑是向往着那种古典式的“逍遥”。他是周作人的真正的学生。而且,他的朴素的生活方式和超脱的人生志趣使他有效地克服了周作人式的享乐主义。表现在艺术和生活上,则是一如既往地孤绝超拔和悠游娱世处变不惊。只不过,战争带给废名的,已既不是“五柳先生”的理想,也并非杜子美式的忧虑。而是面对被铁血浸染的“文明”,以一个劫后余生的自我思虑着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将来。在小说《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中,废名笔下(也是莫须有先生眼中)的“飞机”犹如唐·吉诃德眼中的风车。象唐·吉诃德大战风车关乎骑士的行侠仗义,莫须有先生对飞机的恐惧关乎一个自由个人主义者所理解的民族和人类的幸福。因此开宗明义,废名说:这部小说“是莫须有先生坐飞机以后有心写给中国人读的”,“他怕中国读书人将来个个坐飞机走路,结果把国情都忘掉了”。然而它又是一部“避难记”,其中作者所发抒的对于人类文明史的理解联系着他对于战争生活的观察与体验,从而使一个类似于《莫须有先生传》的极端个人化的文学文本,以其独特的内省视角和特有的心理体验,把一种至为高远而又不无偏执的社会(文化)忧患意识凸现出来。尽管,其中民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观结合着道德犬儒主义的个人文化心态,使作者在对于社会和文化的终极理想上未免逃避现实,遁向虚无,但仍执着地从心灵上呼唤着人类回归自然,真诚地向往着充满原始情趣的人类大同,显然并未根本违逆审美理想主义的艺术认识规范。
三、新诗“现代化”:“严肃”文学的至上追求
对于新诗的热衷是后期京派文学活动的一个显著特点。从朱光潜在北京的居所慈慧殿三号的“读诗会”发源,它不仅使卞之琳、何其芳、林庚、孙毓棠等成功登上中国新诗的高雅殿堂,更在新诗“现代化”的道路上催生了杰出的西南联大诗人群。沈从文曾在为《大公报·文艺副刊》附载“诗特刊”所写的发刊辞中认为,虽说在“文学商品化”的时代,一味要求于新诗的精巧雅致难免沦于孤芳自赏,但因其体现着“严肃”文学的至上追求尤其未可偏废。且认为,“要建设新诗,得有个较高标准”(注:沈从文:《新诗的旧账》,《沈从文文集》第12卷,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1984年版,第182页。)。朱光潜更倾向于以“曲高和寡”来理解他所谓“好诗”的含义,他说:“如果文艺的价值不应取决于多数,则这一部分嗜好难诗的人也有权说他们所爱好的诗是好诗”(注:朱光潜:《心理上个别的差异与诗的欣赏》,参见商金林:《朱光潜与中国现代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97页。)。40年代,朱光潜的《诗论》更是在现代诗学的认识论意义上,通过“用中国诗论印证西方诗论”,借区别“谐”、“隐”阐释了一种中西合璧的审美理想主义诗歌实践原则。他认为,“谐”代表着“豁达超世”的境界,“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注:朱光潜:《诗论》,《朱光潜全集》第3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诗的表现也必然地联系着作家审美态度上的“距离”感,犹如说话不能直接成为诗,散文化决不是中国新诗的正途。进而,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理论一则要求在对于“好诗坏诗”的区分上“诉之于纯粹的文学标准”,以摆脱“庸俗浮浅曲解原意的‘散文化’”所造成的新诗创作的“无政府状态”(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2页。)。一则在“间接性”的美学赋意下,把“在啼笑皆非之中深寓悲悯”,“严肃轻松的相反相成”视为新诗“现代化”的基本品格(注: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再分析》,《半个世纪的脚印——袁可嘉诗文选》,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61页。)。从“纯诗”的提倡到探索新诗“现代化”之路,后期京派的新诗实践继承并发展了新月派和30年代“现代派”的新诗传统:以合于“朗诵诗”的要求规范新诗的节奏和韵律,以“间接性”表达求取意境的高妙,以“玄学的思维”体现思想的深邃。这代表了他们对于文学的至上追求,寄寓着他们造就于中国新文学的崇高梦想。
冯至和穆旦,在不同的代表性上把后期京派的新诗实践推向高峰。朱光潜说:冯至40年代的新诗“学德国近代派,融情于理,时有胜景”(注:朱光潜:《现代中国文学》,《朱光潜全集》第9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28页。)。情本自然之趣,理者生命之忧。就其《十四行集》中所见,他不啻是以诗的形式串连起了里尔克和雅斯贝斯。面对生命,他“忧患重重”:“我们的生命象那窗外的原野/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之十八)。“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象树木“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伸入严冬;……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未来的死亡,象一段歌曲”(之二)。感觉着,融合于自然,也象里尔克一样,冯至拥有了一颗“谦逊的心”。一种对于自我和自然的“新的发现”,不仅在存在主义的观念上,也在审美主义的意义上,把创造于艺术的自我与现实世界的关系凝定。从里尔克式的“崇拜自然”到艾略特式的感悟苍凉,正是冯至诗中的“沉郁”之气培植了穆旦诗歌的“沉雄”之慨。如在长诗《隐现》中我们读到的,那番真正“悲天悯人”的沉重感慨:“枉然:我们站在这个荒凉的世界上,/我们是廿世纪的众生骚动在它的黑暗里,/我们有机器和制度却没有文明/我们有复杂的感情却无处归依/我们有很多的声音而没有真理/我们来自一个良心却各自藏起”。无论其自我化的表达多么令人“陌生”,但这必然是真正的现代新诗,凝聚着中国新诗人半个世纪中对于诗的崇高理想和至上追求。
标签:文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西方美学论文; 海派风格论文; 朱光潜论文; 李健吾论文; 读书论文; 水云论文; 边城论文; 梁宗岱论文; 语丝论文; 小品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