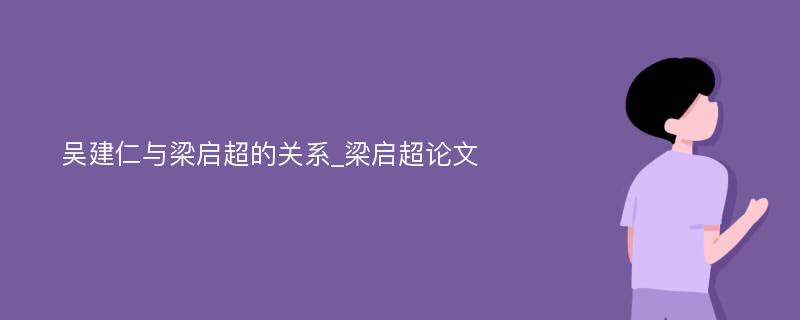
吴趼人与梁启超关系钩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钩沉论文,人与论文,关系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435(2002)06-0636-05
往往有这种情况,一篇已酝酿多时的考据文字,直待关键史料发现,才犹如一地散钱,忽然得到贯穿的线索;又如堵塞的河道豁然贯通,顺流直下,即可领略两岸的旖旎风光。原先零落的材料与缺乏验证的预感,便可在此一史料的统领下,自然整饬成篇。而对于吴趼人与梁启超这个题目来说,霍坚(俪白)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就具有这样的作用。
此前,论及二人关系,最先也会最多谈到的,应该是列名于“四大谴责小说”的吴趼人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向被视为由梁启超倡导的“小说界革命”代表作。该书以及吴氏的不少小说,也是在梁启超主办的《新小说》杂志上开始连载。至于二人之间是否有过直接的交往,则基本不在考虑之列。因为吴趼人以办《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娱乐性小报成名,与先后主编《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政论杂志的梁启超不在一个层次;而友人记吴氏“以小说名家,诙诡玩世,不可方物”[1](P20),也与政治家兼学者的梁启超形象大异其趣。“道不同,不相为谋。”二人虽曾有戊戌变法前二年同寓沪上的经历,但此后天涯暌隔,要见也难。如断言其未曾往来,也绝不出人意外。
意外地倒是在编辑《追忆梁启超》时,我读到霍俪白的《梁任公先生印象记》,在这篇副题标为“为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作”的回忆文章中,居然提到了吴趼人曾招待过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弱冠游学沪滨,适值先生自日本潜赴香岛,路过上海稍事勾留,偶于乡前辈冯挺之先生席上一遇之,初见平易无异常人。次日复于吴趼人先生(即我佛山人)座上再瞻丰采,趼人先生固淳于髡之流,多方为余揄扬,并谓是君虽少,曾居印度有年,深知印度国情,熟谙梵文等语。实则余虽曾随父执旅印三年,略操印度流行语,他非所习也[2](P163)。
就所述情景看,梁启超与吴趼人并非初见,且已有相当交情,吴氏才会在梁为清廷通缉的亡命客时,无所顾忌地接待他。
需要考证的是此事发生的年份。查检丁文江与赵丰田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可以知道,自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到1910年10月21日吴趼人去世,其间梁曾三次往来上海。依照上文“自日本潜赴香岛,路过上海稍事勾留”的条件,第三次即1907年阴历四月间的回沪,显然应该排除,因有梁启超六月八日《与南海夫子大人书》自述,“数月来奔走于上海、神户、东京之间”[3](P409),此次显然未至香港。
另外两次行踪,一在1900年,梁启超《三十自述》[4]中曾道及:
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义和团变已大起,内地消息,风声鹤唳,一日百变。已而屡得内地函电,促归国,遂回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闻北京失守之报。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留沪十日,遂去,适香港。
这次梁启超的仓促回国,本是为策应唐才常、林圭等筹划的“自立军”起义。此役乃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维新派集中最多精锐与财力、寄予厚望的武力行动。其迅速惨败,对于作为组织者之一的梁启超,所受心理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且梁氏此行,在沪不过十日,虽曾见过后任《时报》编辑及《新新小说》主笔的陈景韩(即陈冷血),当时陈氏却是以“同志”而非小说作者的身份与梁秘密会见(注:这一情节在当年负责接待梁启超的狄葆贤(楚青)所述《任公逸事》中有记述:“庚子七月任公曾在上海虹口丰阳馆十日,任公以日本料理不甚佳,由余家日日送小莱以佐餐。任公到之第三日,陈景韩在丰阳馆与谈二小时,乃初次见面也。”(《梁启超年谱·长编》255页))。因此,以情理推之,梁启超似无心情与余暇和尚处于编小报生涯的吴趼人会面。
1904年的情况就不同了。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于该年项下所记:
先生以正月杪返国,往香港开会。二月末旬由港至沪,留数日,与狄楚青、罗孝高筹画开办《时报》各事。三月,复返日本[3](P336)。
既要办报,自然须联络同仁,与在报界已颇有影响的吴趼人见面,也属顺理成章。何况,吴氏此前已开始在横滨出版的《新小说》上发表作品,与梁并非陌路人。还有一个细节,可从侧面证明吴、梁沪上相见是在此时。根据后来进入《时报》馆做编辑的包天笑回忆,那时《时报》除总主笔罗普(孝高)外,“另外有两位广东人”担任主笔,其一即是冯挺之[5](P318)。
那么,梁启超在赴吴氏之约前的会见冯氏,应该也是为筹办《时报》事。并且,霍坚记此次会面后,接下来又说到,“顾是时立宪论与革命论激战甚烈”。而就时间言,1906年发生的这场论战,也更接近于此时而与1900年隔远。
从会面情形看,因在座尚有多人,可知是吴趼人邀约梁启超,而非梁之主动求见;否则,梁氏也不便为照顾霍坚,“遂舍众客侧席独与”霍淡。由此亦可推知,吴趼人与梁启超此前应已相识。这里,用得着吴氏生前挚友周桂笙的一段追述:
趼人先生及余,皆尝任横滨新小说社译著事,自沪邮稿,虽后先东渡日本,然别有所营,非事著书也[6](P16)。
吴、周二人为《新小说》撰稿,起始于1903年10月印行的第八号杂志。吴趼人在该期一口气发表了历史小说《痛史》、社会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写情小说《电术奇谈》,并在“杂录”栏刊出《新笑史》,其文字占了那本刊物的大半篇幅,并由此一跃而为《新小说》的第一写作主力。关于吴氏赴日时间,魏绍昌推定为1903年冬,即在最初“自沪邮稿”横滨《新小说》社之后。而吴趼人与周桂笙加盟后,《新小说》在第八号与第九号之间,仍有10个月空前绝后的长时间停顿。虽然在此期间,《新小说》社连同承担其印刷的《新民丛报》社活版部,正从横滨市山下町152番迁至160番,可能会造成刊物的脱期;但其延误时间之久也让人疑心,吴、周二人大约正在此时“后先东渡日本”。查梁启超1903年踪迹:正月应美洲保皇会之邀,游历美洲;十月二十三日(西历12月11日)复返横滨[3](P309-333)。
据此而论,梁氏应该有机会与吴趼人碰面。这大概就是吴在沪上邀约梁启超的前因。
至于吴趼人去日本所营何事,周桂笙未作说明。魏绍昌在《鲁迅之吴沃尧传略笺注》中曾提供了一个说法:
据其堂弟吴植三在一九六二年说,趼人在沪曾助理广智书局业务,此去与《新小说》社联系出版发行事项有关[7](P6)。
魏绍昌虽然谨慎地表示,“姑录此说待证”,但这多半是事实。从1905年2月出版的第二年第一号(第十三号)起,《新小说》的发行所已正式由先前的横滨新小说社,标明改为上海广智书局。或许是为了表示与“国事犯’梁启超撇清干系,以掩人耳目,这期刊物上还故意刊登了被梁氏一再痛骂的“清太后那拉氏”的照片。而《新小说》的移师上海,应该就是吴趼人东渡商谈的结果。
1901年于上海开办的广智书局,是维新派在国内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主要由梁启超在日本遥控。初期经营状况一直不佳,这在梁与同人的书信中屡有述及。即使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游美归来,十二月十八日(西历1904年2月3日)致书蒋智由时,梁氏仍在为“今年广智亏累不少”[3](P335)而苦恼。在此情况下,吴趼人将多种小说交由该书局出版,无疑是对这一维新事业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根据魏绍昌与日本樽本照雄先生著录的吴趼人小说版本(注:见魏绍昌编《吴趼人研究资料》与樽本照雄编《(新编增补)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济南:齐鲁书社,2002年)。),可以看出,吴氏清末刊行的小说单行本,一大半出自广智书局(有争议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与《瞎骗奇闻》、《糊涂世界》不计在内(注:1909年,吴趼人在《中外日报》发表《(社会小说)近十年之怪现状》(后改名《最近社会龌龊史》)时,撰有《自序》一篇,清点其历年所作小说,一向为研究者所重视:“计自癸卯始业,以迄于今,垂七年矣。已脱稿者,如借译稿以衍义之《电术奇谈》(见横滨《新小说》,已有单行本)。如《恨海》(单行本),如《劫余灰》(见《月月小说》),皆写情小说也。如《九命奇冤》(见横滨《新小说》,已印单行本),如《发财秘诀》,如《上海游骖录》(均见《月月小说》),如《胡宝玉》(单行本),皆社会小说也。兼理想、科学、社会、政治而有之者,则为《新石头记》(前见《南方报》,近刻单行本)。……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部分百回,都凡五十万言,借一人为总机捩,写社会种种怪状,皆二十年前所亲见亲闻者,惨淡经营,历七年而犹未尽杀青。”(1909年4月20日《中外日报》)郭长海据此而将署名“抽丝主人”的《海上名妓四大金刚奇书》与署名“茧叟”的《瞎骗奇闻》与《糊涂世界》排除在吴作之外(见氏之《吴趼人写过哪些长篇小说》,日本《清末小说》17号,1994年)。)。现举示如下(包括长篇小说与笔记):
《电术奇谈》24回,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108回,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二月,至宣统二年(1910)八月,陆续分八卷出版;
《中国侦探案》,光绪三十二年(1906)三月出版;
《九命奇冤》36回,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至同年八月,分三册出版;
《恨海》10回,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出版;
《劫余灰》16回,宣统元年(1909)出版;
《最近社会龌龊史》20回(未完),宣统二年(1910)九月出版;
《趼廛笔记》,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出版;
《痛史》27回(未完),宣统三年(1911)出版。
其中原在《新小说》连载者,版权固然可保留在广智书局,但《恨海》乃直接以单行本面世,《劫余灰》与《最近社会龌龊史》(初名《近十年之怪现状》)分别初刊《月月小说》与《中外日报》,最终也花落广智,可见吴趼人与广智书局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而除《新石头记》与《上海游骖录》,吴氏最重要的小说已尽包括在内。
从1903年10月与《新小说》结缘,到1906年11月《恨海》的出版,可以算是吴趼人与梁启超所主持的杂志及书局的第一度“亲密接触”。其后的中断,显然是因为由吴趼人担任总撰述的《月月小说》在1906年11月创刊。这不仅导致了《新小说》的停刊(注:《月月小说》第二号(1908年11月)广告曰:“本社……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译述。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又,郭浩帆在《〈新小说〉创办刊行情况略述》(日本《清末小说から》66号,2002年7月)中,对此说作了考证。《月月小说》第一号(1906年11月)刊有《声明版权》,称:“本社所登各小说,均得有著者版权。他日印刷告全后,其版权均归上海棋盘街乐群书局所有,他人不得翻刻。特此先为预告。”至第九号,《月月小说》改由群学社经办,也曾刊登过类似声明(见《月月小说》第十号封三之《特告》)。),也使得吴氏随后的几部小说,如《胡宝玉》、《俏皮话》、《上海游骖录》与《发财秘诀》,改由承担《月月小说》发行的乐群书局与群学社出版。而1909年1月《月月小说》停办后,吴趼人又立刻恢复了与广智书局的联系,虽然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考察吴趼人小说的署名,除常用的吴趼人及由其化出的趼人、趼等,“我佛山人”应是最通行的名号。其他如“岭南将叟”只偶而一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老少年”或“中国老少年”之署,首见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开始在《南方报》刊发的《新石头记》,再现于1906年出版的《〈中国侦探案〉弁言》。此笔名之使用,显然与梁启超写作《少年中国说》,并自署“少年中国之少年”有关。视其为对梁氏维新理想的呼应,应该不算太离谱。
更值得考究的是吴趼人的小说创作与梁启超的内在联系。以前的研究者讨论“四大谴责小说”时,虽也将其纳入“小说界革命”的框架中,并认定其在结构、笔墨上受《儒林外史》影响甚大,但这只属于精神上的契合,而缺乏确凿的证据。1997年,笔者到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时,在《新民丛报》第十九号(1902年10月)的初版本上,偶然发现了一则《新小说社征文启》,才自认为找到了“谴责小说”文体发生的由来。这一在《新小说》出刊之前登载的征文启,应该是出自刊物创办人梁启超之手,其关于来稿要求的说明,对作家的写作自然会产生诱导的作用。而其中特别强调:
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又如《儒林外史》之例,描写现今社会情状,借以警醒时流、矫正弊俗,亦佳构也。
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与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这两部最接近《儒林外史》风格的小说,会不约而同在1903年出现;而吴作写情小说《恨海》与《劫余灰》开卷发论,也总要在儿女之情外,说出另一番“情”之理。
追索吴、梁遇合,大概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吴趼人的作品中,与梁启超本人的著述关系最密切、形迹最明显的,竟是其最不能被人理解的《胡宝玉》。先是1926年,有署名“稗史氏”者,在《我佛山人之赝品》中,指认收入《我佛山人笔记四种》中的《上海三十年艳迹》“乃假托也,原为一小册子,名曰《胡宝玉》,出自另一人之手笔”[8];后有王俊年在《吴趼人年谱》中颇为疑惑地提及: “作者和当时的广告都把《胡宝玉》列为‘社会小说’,其实它只是一部写上海妓院生活的笔记而已。”[9](P297)将《胡宝玉》从吴趼人的著作中剔除出去,或者否定作者本人冠之以“社会小说”的定义,都是因为无法想象,已经显示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的吴趼人,何以会为一名妓女立传,为腐败社会肌体上的毒疮妓院浪费那么多的笔墨。
我起初也未尝不抱有同样的疑虑。迨熟读过梁启超的《李鸿章》,此次再重读吴趼人的《胡宝玉》,便突然有新的发现:二书在题目、构思以至章节设计上是如此的相似。
《李鸿章》又名《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是因为梁启超认为:“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故为李鸿章作传,不可不以作近世史之笔力行之。”[10]而《胡宝玉》正题下也径直署有“一名《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吴趼人也是希望通过此书,“乃得见此胡宝玉为上海数十年间冶艳历史中之旋涡中心点”[11](P2-3)。
篇章布局上也好有一比:《李鸿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李鸿章之位置》分述“中国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及“本期历史与李鸿章之关系”;第三章题为《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以下各章分别从“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李鸿章之末路”,论述了李鸿章一生行事。最后一章即第十二章为《结论》。而《胡宝玉》第一章名为《发端》,末章即第八章也称《结论》。中间从第二章到第四章依次为《胡宝玉以前之北里》、《胡宝玉以后之北里》、《胡宝玉同时代之北里》;第五章笔端拉开,写《上海游客豪侈之一斑》;以下才言归本传,是即第六章《胡宝玉本传》。而传主之迟迟登场,更显示出作者意在借胡宝玉,写出晚清上海妓院史,进而透显出沪上奢靡风气的形成与变迁。
而上文漏过的第七章《胡宝玉之比拟》,又是明显脱胎于《李鸿章》一书《结论》中的第一个子题目“李鸿章与古今东西人物比较”。梁启超将李与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俾斯麦、格莱斯顿、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16位中外名人相比,以确定李鸿章的历史定位。《胡宝玉之比拟》则分列“与诸妓之比拟”、“与诸鸨之比拟”、“与群盗之比拟”、“与神怪之比拟”四节,所比之人近至稍后成名的妓女林黛玉,远至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孙行者,看似杂乱。但如果因此认为,这是吴趼人的游戏笔墨,故意将《李鸿章》一书庸俗化、妖魔化以取悦读者,则属误读与失察,不会为吴氏所首肯。
其实,在《胡宝玉》的《结论》一章,吴趼人曾特意为此书之撰著作了一番辩白。其说先以发问引出:
或曰:胡宝玉一妓女耳,其传不传何足道,其得若失更何足以撄吾人之心?顾乃费纸费墨费日月费精神而为之传,又复罗列各妓女之历史以实之。金圣叹有言:“世间笔墨匠,造成笔墨,乃遭如此人如此用!”毋亦可以已乎?且今之时,何时也!识时之士,方且竞出其新思想新学问,著书立说以饷国人;不足,又翻译西书,取材外族。今不从事于此,而独浪费笔墨,为此无益著述,纵不为人所齿冷,宁不自恧耶?
这一责备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可谓义正词严。但吴趼人并不认可,且辩称其著作实有深意。按照他的说法,胡宝玉虽不过一妓女,却能“转移风气”,“维持典型”,足以作“知改良风俗之为急务”的“英俊少年”与“知保全国粹为要图”的“老成持重者”的示范:“呜呼!以一妓女能为之者,顾如许之英俊少年、老成持重之流皆甘放弃其责任,滔滔天下吾将安归?此《胡宝玉》之所由作也。”这便是《胡宝玉》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同列为“社会小说”的原因,在吴趼人,本是以庄重、严肃的态度写作这部笔记的。
此说还可得到一个证明。为撰此文,近日重翻《吴趼人研究资料》,才发现吴之挚友周桂笙早在《胡宝玉》出版不久,即已在书评中揭示了其有意模仿梁启超“全仿西人传记之体”[9]而写的《李鸿章》一书之底牌:
此书之作,即所以传宝玉者也,故名之曰《胡宝玉》。仿《李鸿章》之例,其体裁亦取法于泰西新史。
接下来,周氏正面阐述了此书的意义:
全书节目颇繁,叙述綦详,盖不仅为胡宝玉作行状而已,凡数十年来上海一切可惊可怪之事,靡不收采其中,旁征博引,具有本原,故虽谓之为上海之社会史可也。……盖中国自古至今,正史所载,但及国家大事而已。故说者以为不啻一姓之家谱,非过言也。至于社会中一切民情风土,与夫日行纤细之事,惟于稗官小说中,可以略见一斑。故余谓此书可当上海之社会史者此也。[12]
而这一评价思路,也有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发明在前。所谓“前者史家,不过纪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13],这一主张为国民作史与关注国民史的新史学宗旨,在当时激起了巨大反响。而吴趼人《胡宝玉》之撰著与周桂笙书评之阐发,其实正是对梁氏首倡的自觉应和。
如此,梁启超1901年撰写、出版的《李鸿章》,1914年由中华书局改题为《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14](P54)重新出版,尚符合作者之本意;而《月月小说》创办人汪庆棋(号惟父)1915年将死友吴趼人之《胡宝玉》更名为《上海三十年艳迹》,编入《我佛山人笔记四种》中印行,而放弃了吴氏自拟的另一书题《三十年来上海北里怪历史》,则使其影写上海社会史之深心隐而不现,趼人先生于地下当亦不能心安。
以上对于吴趼人与梁启超从行迹到心迹的相遇钩沉,正好写在《新小说》创办与“小说界革命”口号提出一百周年之际,谨借此表达对先贤事业的一份敬意。
2002年10月20日于京北西三旗
收稿日期:2002-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