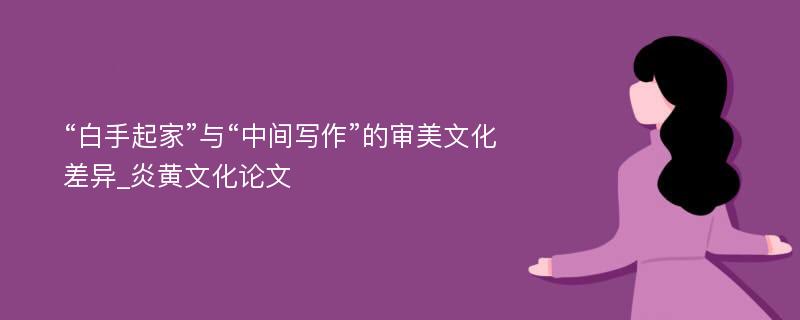
“从头写起”与“从中间写起”的审美文化差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写起论文,文化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两种不同的叙事时间方式
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论及叙事与故事的“时间倒错”问题时这样说:“我们(西方)的文学传统却以明显的时间倒错为开端,……从中间开始,继之以解释性的回顾,后来成为史诗题材形式上的手法之一,大家也知道小说的叙述风格在这点上多么忠实于远祖。”① 又说,“从中间开始”是整个古典时代的“惯例”②,还说“从中间开始”是“通常做法”③。显然,热奈特关于西方叙事文学“从中间写起”的说法并非漫不经心之言,而是对一个确定的事实的描述,或对某个规律深思熟虑的揭示。
诚如热奈特所言,从中间开始叙事,是西方文学叙事的经典手法。这种手法滥觞于荷马史诗,盛行于希腊戏剧。荷马史诗《奥德赛》就是“从中间开始”叙述的第一个典范。史诗叙述的故事是奥德赛从特洛亚回返故乡伊塔刻岛的漂流过程。但史诗却是从奥德赛返乡途中被女神卡吕蒲索强留长达七年,引起雅典娜女神不满,恳求宙斯干预写起。奥德赛此前近十年漂流中种种离奇冒险和不幸遭遇,是他终于离开卡吕蒲索,在法伊阿基亚国王的宫廷里讲叙出来的,这就是倒叙——热奈特所谓“解释性的回顾”。荷马的这种时间倒错方式在希腊戏剧中成为高超艺术技巧的标志之一。亚里斯多德在《诗学》中极力标举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王》,主要就是因为该剧最成功地运用了“从中间开始,继之以解释性的回顾”的时间手段。此后,西方文学叙事大行此道,终至形成一种惯例。无数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精于此道,无数小说杰作与戏剧精品都展现此种技艺的艺术魅力。可以这样认为,尽管不是全部西方作家全部西方叙事作品都是“从中间开始”,但“从中间开始”的确是处理叙事与故事关系最盛行的手段,而且,这种手段进入20世纪仍然经久不衰,在有的叙事文学品种中甚至还被发扬光大,例如意识流小说和运用意识流手法的小说。
但中国传统小说的叙事时间方式与西方截然不同,它不是从中间开始而是从头开始。所谓“从头开始”,是说叙事从故事发生的那个时刻开始,叙事之始即故事之始,例如中国传统小说的最高成就明清小说的四大名著即是如此。《三国演义》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成功写人的长篇小说,小说的审美阅读效果几乎全集中于小说中刻画的主要人物形象上。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三国时的英雄,智术武勇,非常动人,所以人都喜欢取来做小说的材料。”④ 而后来人品评《三国演义》,也基本上以其人物形象刻画成就议论之。但就是这样一部叙事作品,作者却紧紧追随魏蜀吴三个国家的兴衰始末从头说起:从东汉末年桓灵二帝昏庸,宦官弄权坏政,激起黄巾起义开始叙述,于是有镇压黄巾,诸侯募兵,由此引出刘关张入伍;继而为诛宦官方有董卓进京,董卓擅权招致诸侯结盟讨伐;在伐董战争中曹操孙坚初露峥嵘,刘备兄弟小试身手;如此下去,叙述三股势力成长成型,经营势力范围,终于建国立号,形成鼎足之势,最后结束分立,“三国归晋”。整个叙事依据故事时序,不错不乱,如果仅从时间角度看的确是一部严谨的讲史之作。中国小说史上以刻画人物性格成就而负有盛名的长篇小说《水浒传》也是“从头开始”的,小说的主旨是再现以晁盖宋江为首的梁山泊英雄聚义“替天行道”的事迹。如果按照西方的叙事时间方式,这个叙事最可能“从中间开始,再继之以回顾”。但《水浒传》作者却坚定地走中国的路——从头写起。小说先写一个和梁山泊八杆子搭不着的“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下延安,途遇史进传艺,史进惹官司奔延安寻王进,在延安结识鲁达;鲁达打死郑屠逃至五台山出家,被遣至东京大相国寺,结识林冲;林冲获罪于太尉高俅,发配沧州牢城营,风雪山神庙,月夜上梁山;林冲剪径遇杨志,杨志东京途穷卖刀,杀死泼皮发配大名府,得梁中书信任押送生辰纲。这才引出晁盖等七人智取生辰纲,晁盖于此才上得梁山形成一个中心,吸引各路英雄来结义。神话小说《西游记》亦复如此,这部长篇大可如《奥德赛》般写来:唐僧带着三个徒弟西行,历经磨难,某处顺境时,回顾初始,叙述三个弟子之非凡出身及非常事迹。但中国小说叙事就绝不这样叙述,《西游记》一定要先从孙猴子的出世讲起,而后是他获得超凡技艺和不死之身的闹天宫经历,以此为他皈依唐僧后屡败妖魔鬼怪的神奇本领做好铺垫;《西游记》也一定要从唐玄奘的出世讲起,也要说清楚他何以要去西天取经,为此不得不扯出唐太宗死而复生尊善果的缘由。此后则依时按事道来,直至到达西土,人人修得正果,顺利返回。《红楼梦》也自不待言,小说开篇除过以超叙述甚至超超叙述方式“预叙”了“石头”所载故事,从而造成一种阅读的神奇效果外,一切还是中国式叙述:从头开始。先叙述林黛玉家世(其父林如海中断世袭改从科举,官禄和人丁两不荣盛,中年方得一女黛玉,偏又年仅六岁其母即“仙逝”扬州城),再叙黛玉被送回母舅贾家,以及从此与宝玉青梅竹马耳鬓厮磨渐长渐大情随岁进的过程,而不是像西方那样先从二人情事开始,再回顾年少之时。总之,中国传统叙事文学很少有“从中间开始”的例子。无论是对“二十四史”的诸般演义,还是种种神魔或世情小说,“从头说起”是极少破例的叙事惯例。
“从头开始”与“从中间开始”造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叙事时间景观。虽然这两个不同景观乍看起来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叙事技巧使然,但深层地看,它却从一个方面显现了中西审美文化的差异和特色。因为正如詹姆逊所说,“形式自身是一种内在的固有的意识形态”⑤,即他所称的“技术的意识形态”⑥。就是说,叙事方式可以见出意识形态来,甚至受制于意识形态。西方叙事文学的“从中间开始”和中国叙事文学的“从头开始”的时间方式,显然表现出不同的审美意识形态,或者说受制于不同的审美文化。我们可以这样说:刻意进行“时间倒错”的“从中间开始”的方式,显然是西方“改造自然”说这一审美意识形态的强大传统的一个表现形式;而“从头开始”则是中国“顺从自然”审美文化的反映。
二、改造自然:“从中间开始”的审美底蕴
西方美学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就为“从中间开始”确立了一个极为显著的地位,也为这样的“改造自然”建立了第一个美学依据。在《诗学》中,亚里斯多德明确褒“从中间开始”贬“从头开始”。他说,叙事作品的情节“显然有简单的和复杂的之分”。所谓“简单的”,“指按照我们所规定的限度连续进行,整一不变,不通过‘突转’与‘发现’而到达结局的行动”;“复杂的”则是指“通过‘突转’或‘发现’,或通过此二者而到达结局的行动”。⑦ 亚里斯多德所说的“连续进行”的情节,其实就是指从头开始并按时序而行进的情节;他所说的通过“突转”和“发现”到达结局的情节,也正就是“从中间开始,继之以解释性的回顾”的情节,例如他奉为典范的荷马史诗《奥德赛》和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俄狄浦斯王》。亚里斯多德高度评价这两部作品在叙事中成功运用的“突转”和“发现”这两种手法,并在短短的〈诗学〉中不惜用三章(十,十一,十六)的篇幅讨论“突转”和“发现”的技巧及其美学意义。认为这两种叙事手法不仅是艺术性的标志,更是“创造性的模仿”的标志。亚里斯多德文艺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高抬技艺而轻视想象,认为艺术之所以是艺术,就一定要人的“技艺”显现其中,否则就只是自然,而非艺术了。亚里斯多德对“突转”和“发现”的充分肯定,是西方美学以艺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这一审美理想的典型话语。它的表层意义是开创了西方叙事时间的主流方式,形成了“从中间开始”的强大惯例,其深层意义则是开启了艺术(技艺)征服自然的审美思潮,使之始终鲜活地流淌于西方文学艺术史,绵延不绝。于是有了文艺复兴时期狂热探讨艺术手法和技巧的《艺术论》热潮。⑧ 正如朱光潜所说:“文艺复兴时代的文艺,无论是在实践方面还是在理论方面,重视技巧是一个特色,而且还可以说,这是西方艺术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⑨ 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达·芬奇著名的“第二自然”说和卡斯特尔维屈罗的“准三一律”。前者提出,“画家不只是模仿自然,他在其创造过程中与自然竞争”,从而提交出高于自然的“第二自然”。⑩ 后者则第一次提出戏剧应当把演出的故事情节处理在一天一地之内,(11) 这表明他意识到了叙事与故事在时空上的巨大差异。后来在波瓦洛影响深远的《诗的艺术》中,它就被固化成为法律:“要用一地一天内完成的一个故事,从开头直到末尾维持着舞台充实。”(12) 到18世纪天才论盛行的时代,对天才的一个主要解释就在表达的技巧和手段方面。例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康德首先指出,“人们只能把通过自由而产生的作品,即通过一个意图,把他的诸行为筑基于理性之上,称为艺术”,“艺术只能意味着是一创造者的作品”。“人们根本上所称为艺术作品的,总是理解为人的一个创造物,以便把它和自然作用的结果区别开来”。(13) 因此,“美的艺术是天才的艺术”(14)。天才有多种表现或才能,而在艺术中,“天才不仅见于替某一确定概念找到形象显现,更重要的是见于能替审美意象找到表达方式或语言”(14)。朱光潜对此如此评说:“康德的重点不在审美意象的形成而在审美意象的表达,即不在胸有成竹而在把胸中成竹画成作品。”(15) “寻找表达方式”也好,“把胸中之竹画出来”也好,它们都存在两个情况:一是必定经过天才的手法技巧这一关,否则不可能有艺术作品存在;二是经过天才的手法技巧而获得的作品必定不全等于原来的“表象里的意象”或“胸中之竹”了。正如郑板桥所言,“胸中之竹不是眼中之竹,手中之竹不是胸中之竹”(17)。因为经过手法和技巧,“创造”的目的得以实现:自然已经被改造过了。
如果说从亚里斯多德起,西方一直涌动着一股要通过人的技艺潜能改造自然的审美理想的话,那么这种理想却一直有一重要的附加条件,那就是运用了人为的手法技巧还不能被看出来人为因素,自然被改造过了还要看得像似自然。用康德的话说就是:“美的艺术须被看作是自然,尽管人们知道它是艺术。……(艺术的作品)使我们在它身上可以见到完全符合这一切规则,却不见有一切死板固执的地方,这就是说,不露出一点人工的痕迹来。”(18) 然而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艺术远离自然”和“艺术自律”的呼声越来越高,“展露手法”说在创作和理论两个领域都日益扩张,大有占据中心之概。俄国形式主义关于通过“艺术手法”“使事物陌生化”(19) 的理论广泛传播,加之从本雅明以来西方美学对艺术中技术决定论的日益强化的肯定,康德为代表的观念过时了。强调改造自然创造自然必然重视技艺与手法,但过于强调技艺与手法就必然走向技术决定论,技术决定论的结果是使艺术日益远离自然。试看今天西方艺术那种仿像盛行的现状和《侏罗纪公园》、《星球大战》之类的技术型艺术昂首阔步的情景吧,自然,你在那里呢?
西方这种根深蒂固的改造自然的审美理想,有其深刻的文化背景,那就是从古希腊开始确立的人本主义。古希腊人一方面对人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要求,一方面又自我回答:“人是万物的尺度。”从此以后,尽管西方有一个漫长的基督教会统治精神文化时期,教会力图贬低人的主体性,但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整个欧洲人本主义反而如决堤之水汹涌澎湃,蔚成西方思想的主潮。人本主义有种种主张和观念,其最主要的一条就是认为人作为主体,可以而且能够对自然行使主宰权,而且正是在对自然行使这种主宰权时才显现人是主体。如后现代理论家大卫·格里芬所指出,在西方,“占有和统治自然的欲望一直是现代公民的驱动力”。(20) 西方人一直强调“能动性”,这个“‘能动性’也就只剩下占有和支配自然事物这一层意思了”(21)。西方思想认为,人能够而且应该征服自然,它表现在一切领域,当然包括艺术。征服自然的理想培育了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在艺术中就表现为种种技巧和手法。“从中间开始”只不过是文学叙事中改造时间的手法之一罢了。
三、“从头开始”:顺应自然审美理想的产物
与西方叙事“从中间开始”的美学追求正好相反,“从头开始”则是中国贵重生命、顺应自然审美文化在文学叙事中的一个表征。
中国古代意识形态素来崇奉生命。孔子说“天地之大德曰生”,扬雄说“天地之所贵曰生”(22),程颐说“天只是以生为道”(23)。诸如此类关于贵重生命的“天籁之音”响彻数千年中国文化之中。中国人认为,万物惟生,因而人必贵生。生命即自然,贵自然即是贵生命,于是极为崇奉自然。崇奉自然有两义,一是要求顺应自然而不违逆自然。庄子说要“依乎天理,因其自然”(《庖丁解牛》),王弼说“万物以自然为性,故可因而不可为也。……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也”(《老子道德经注》29章)。嵇康更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著名命题张扬贵自然的思想。顺应自然还被引申到社会政治,形成“顺”文化。《左传》已阐释“顺”的“六义”,指出“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隐公三年);“顺成为臧,逆为否。”(宣公十二年)《管子五辅》:“人道不顺,则有祸乱。”《吕氏春秋·顺民》:“先理顺民心,故功名成。”董仲舒《春秋繁露·卷十》说:“逆顺自著,其几通于天地乎。”还说:“见天数之所始,则知贵贱顺逆所在,知贵贱顺逆所在,则知天地之情者。”(同上,卷十一)把顺自然的道理说得最为令人服悦的是柳宗元。他在寓言小品《郭橐驼传》中描述并评论了只有“顺木之天”、“不害其长”才能使所种之树根深叶茂硕果累累这一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二是反对人为改变自然。庄子《秋水》提出“无以人灭天”:“曰:‘何谓天?何谓人?’北海若曰:‘牛马四足是谓天,络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在《骈拇》中进一步要求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认为得之于天的自然本性就是它的“至正之情”,甚至片面地反对一切人为的改造和修饰:“合者不为骈,枝者不为跂,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斫之则悲。……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钩,直者不以绳,圆者不以规,方者不以矩,附离不以胶漆,约束不以墨索。”
顺从自然既要顺其“性”还要顺其“时”。所谓“顺时”,就是遵守自然时序和顺序。中国古代思想特别强调事物的顺序和时序,这是由《周易》“生生不已”和“生生之谓易”思想推导而来的。生命从初到终从小到大从幼到长,后继于前生继于死,这个过程是有顺序的,正如唐代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所阐发的:“生生,不绝之辞。阴阳变转,后生次于前生,是万物恒生,谓之易也。前后之生,变化改易,生必有死。”(24) 生命有顺序,这已经被中国古代文化符号化。例如《说文解字》解释“天干地支”,就自觉地将年月律历与方位、季节联系起来,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生命时空顺序的符号系统。如“天干”:甲 位东方之孟(春),阳气萌动,以木载莩草之象。乙 象春草木冤曲而生,……丙 位南方,万物成炳然,……丁 夏时万物皆丁实。……庚 位西方,像秋时万物庚庚有实也。辛 秋时万物成而熟,……壬 位北方也,阴极阳生,……癸 冬时水土平可揆度也,……“地支”亦复如此,不再赘述。简而言之,中国古人认为,作为自然的生命有其方位顺序(东南西北)。但古人更强调生命的时序(春夏秋冬),中国人看重方位而尤重四时。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庄子说:“春夏先,秋冬后,四时秩序也。”(《天道》)董仲舒说:“天之道有序有时。”(《春秋繁露·天容》)《周易》说:“变通莫大乎四时。”其一是指四时变化: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再从秋到冬,时光变化,生命迁徙;其二是指流通:四时运转,始则有终,终则有始,顺时延展,无穷尽也。总之,无论是四方还是四时,都强调两个字:顺序。因为正是这四方与四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生命模式,也是一个完整的生命过程,即:春孳生、夏生长、秋收获、冬蕴藏,这个顺序是不可也不能移易的。遵守这个时间顺序,就是契合了自然节奏和生命节奏,就“生生不已”;违逆了这个时间顺序就等于强折生命有机体,就是毁损生命。正如《管子·四时》所说:“春行冬政则凋,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雨。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春种夏长秋收冬藏,四时各守其功。若只按人的主观愿望行事,彼此颠倒替换,违背自然和生命的节律与顺序,则欲速反不达,处处事与愿违。真是顺时者倡,逆时者亡啊。
总之,中国思想要求顺从自然,顺从自然的要义就是要遵时守序。这种生命观决定了中国古人的艺术审美观。庄子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道》)“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刻意》)梁漱溟先生说孔子美学:“孔家没有别的,就是要顺着自然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他以为宇宙总是向前生发的,万物欲生,即任其生,不加造作必能与宇宙契合,使全宇宙充满了生意春气。”(25) 可以说中国文艺美学的伟大传统就是鼓吹“自然”。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说:中国传统有两种美,一种是“错采镂金雕缋满眼”的美,一种是“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美,但后者一直被认为是一种更高的审美境界。(26) 这个结论论据非常充分。如李白提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认为“雕虫丧天真”。程颐也说:文应如“化工生物”,“且如生出一枝花,或有剪裁为之者,或有绘画为之者,看时虽似相类,然终不若化工所生,自有一般生意。”(《二程遗书》卷十八)李贽也认为,“画工虽巧,比之化工,已落二义矣”(《杂记》)王国维评元杂剧称:“元曲之妙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27) 显而易见,中国叙事文学“从头开始”的传统正是这种顺自然、遵时序思想传统的必然结果和必然方式。有人说,“中国小说情节事件的叙述有明晰的时序性”,是因为“佛学因果观念渗入小说思维”,“强化了小说家的思维逻辑意识”。(28) 这显然是舍近求远、“数典忘祖”的说法,不足取。中国小说万事从头说起,有根有源,然后逐步发展,终于形成高潮,最后叙事结束,而事件结局亦是清楚明白,决不混乱,这不正对应着中国思想反复强调的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和时间顺序吗?宗白华先生曾充满感情地评论陶渊明现象说:“空间时间合成他的宇宙而安顿着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有节奏的。对于他空间与时间是不能分割的。春夏秋冬配合着东南西北这个意识表现在秦汉的哲学思想里。时间的节奏率领着空间方位以构成我们的宇宙。所以我们的空间感觉随着我们的时间感觉而节奏化了、音乐化了!”(29) 应该说,宗白华正道出了中国小说“从头开始”即按照时空顺序进行叙述的美学依据。
四、“开头”审美情趣应在自然变异中
我们确认中国文学叙事有“从头开始”的惯例,并不意味着中国叙事的情节结构“线条”也和时间“线条”一样是笔直的“直线线条”。因为正如解构主义叙事学家希利斯·米勒所说:“叙事根本就不是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根直线。倘若是那样的话,就不会引起读者的任何兴趣。叙事之趣味在于其插曲或者节外生枝。”(30) “从头开始”作为叙事的时间方式,它代表着追求自然的审美理想,但遵守时间的自然顺序不等于叙事情节结构也不求变。恰恰相反,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讲变易。《周易》书名即是此义。不过中国人所讲的变化不是人为之变化,而是事物自身的变化,要求人们观察、分析事物自身内部的变化,总结其规律,并在实践中按照自然规律办事。所以中国小说虽在时间顺序上似乎表现出直线线条,但在这条时间之直线上运行的“事”,却和事物本身的面貌一样千变万化,纷繁复杂,形之于小说则显现为龙缠凤绕,云遮雾障,似断似续,变化无穷。例如《水浒传》:虽然小说的时间线条是直线,但“从头开始”这个“头”字,就蕴藏着千变万化。光是众英雄上梁山就有多少趣味啊。每一个人的特殊经历,每一个人的特殊性格表现,每一个人的特殊上山之路,都自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像一条条有源头的小溪,汇入梁山这条大河;也如一条一条吸足养分的须根,从四面八方滋养梁山这棵大树。《水浒传》这样的“树根式”或“溪流式”叙事线条在中国几乎全部传统长篇小说中都有呈现,而这两种叙事线条的比喻义就是生命的自然开始。生命开始当然不等于生命的全部历程。正是生命历程自身的复杂变化而不是人为改造决定了中国传统叙事的复杂变化。可以说,中国传统叙事文学的审美诱惑完全在于生命本身的“自然美”。
但是,以“改造自然”为指归的“从中间开始”的西方叙事惯例却遇到了理论麻烦。这麻烦来自当下的西方理论界,其关键就在于人们发现,“从中间开始”的技艺对读者来说原来是个“骗局”,对作者来说原来是自寻烦恼。制造麻烦的理论家之一就是希利斯·米勒。他在其《解读叙事》中“解构”西方叙事的“开头”理论时,引用了当代著名作家安东尼·特罗洛普的一段否定“从中间开始”惯例的议论。特罗洛普说:“作家经常采用‘从中间开始’这一技巧,有时一写就是一两章之长,但迟早得折回去,再次从开头写起。然而,在极其精彩地写下了数页之后,再折回去,这显得有些笨拙。读者这时可能已被源远流长的家族史或长篇的乡土风情描写所吸引。当作者再折回去时,读者难免会产生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就像一个人在吃了山鹬、鱼子酱和奶酪通心粉之后,又要让他吃炖羊肉。我的看法是,倘若炖羊肉是必不可缺的一道菜,就应该先上……。应该把上百个细小的事件点点滴滴地输入读者的大脑。我希望这种输入通常是在读者无所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的。”(31)
米勒评论并发挥特罗洛普的意见说:“倘若小说家突如其来地开场,描写一个人物把另一个人物扔到了窗外,他迟早需要解释是谁扔的谁,为何这样做。正如斯特恩所悉知,这种解释会导致无穷无尽的回退,……它意味着故事不可能真正地开始。”(32) 这两人的话让人分明感到对西方叙事传统的反讽, 感到他们实际上是在否定“从中间开始”的惯例。而且这种简单的解构思维确实有道理:既然改变了自然以后又得没完没了的“回退”到自然原貌,又何必做此种“创造”?我们很难理解,西方理论家何以直到今天才进行这样简单的思维。但若从西方文化转向的高度看问题,我们就能理解这两人的反思。因为随着后现代思潮的兴起,随着对技术至上的“极度现代化”的普遍反感,西方思想文化领域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回归意识,即“回归自然”、“顺应自然”的意识。这不能不在审美文化传统上留下阴影。正如大卫·格里芬所总结的:西方人对自然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太长的“世界的祛魅”阶段,现在终于回到“世界的返魅”工作中来了。“世界的祛魅”是由于认为自然自身“无魅”,而必须人工赋“魅”,它建立在一种“掠夺性的伦理学”之上,其后果之一是“人与自然的那种亲切感的丧失”,“对满意感的寻求也越来越多的借助于‘人工’手段,借助于对技术产品的占有。”(33) 而现在要对世界“返魅”了,就是说要返回自然自身的魅力上面而不屑于“人工”和“技术”了。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回返。说不定从现在起,“从中间开始,继之以解释性的回顾”真的要靠向叙事顺从自然的“从头开始”了。这并不奇怪,文化全球化何必一定是西方文化全球化,而不能有一点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呢?
注释:
① 热奈特《叙事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② 热奈特《叙事话语》,第23页。
③ 热奈特《叙事话语》,第39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历史的变迁》,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4页。
⑤ 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2页。
⑥ 陈永国《文化的政治阐释学》,第127页。
⑦ 亚里士多德《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页。
⑧ 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第19页。
⑨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62页。
⑩ 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11) 《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94页。
(12) 《西方文论选》(上),第297页。
(13)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48—149页。
(14)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第152页。
(15)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388页。
(16)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第388页。
(17) 《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下),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0页。
(18)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第152页。
(19) 《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
(20)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21)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223页。
(22) 《太玄·大玄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23) 《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页。
(24) 《二程集》。
(25) 梁漱溟《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27页。
(26)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27)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85页。
(28) 吴士余《中国文化与小说思维》,第88—90页。
(29) 宗白华《美学散步》,第89页。
(30)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6页。
(31)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54—55页。
(32)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第55页。
(33) [美]大卫·雷·格里芬《后现代精神》,第220—221页。
标签:炎黄文化论文; 文化论文; 叙事手法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判断力批判论文; 文化差异论文; 西方美学史论文; 读书论文; 奥德赛论文; 诗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