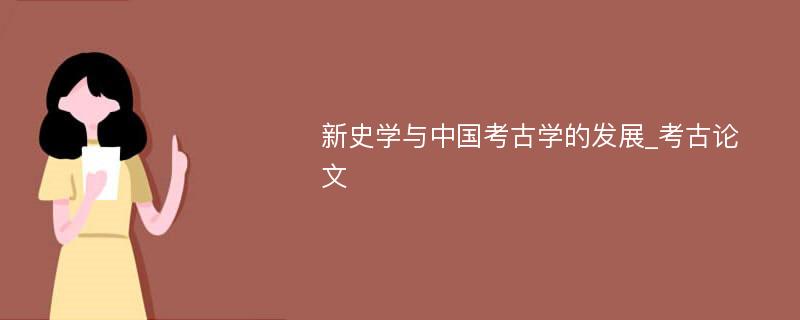
新史学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古学论文,史学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现阶段中国考古学面临的问题
中国人的科学考古,当从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算起,至今整整70年。以这年为基点,5年前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unnar Andersson)发掘仰韶村,创造中国第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概念;3年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展开大规模、有计划的殷墟发掘,揭露3000多年前的王都。总而言之,20世纪的20年代可以说是中国科学考古发轫的时代。
启动中国考古列车的安特生和李济,他们的学术背景皆非考古。安特生专长地质学,故仰韶发掘的层位以距离地表深度机械地划分,缺乏考古学的层位概念(Andersson,1947)。李济研习人类学,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eople)副标题作“一个人类学的探讨”;虽然那时他的眼光已触及考古学领域(李济,1992;《选集》7页),但与西方考古专业到底有些区隔。借用张光直的话说,他不是以一个狭隘的考古专家的地位出现的(张光直,1988b)。这两位考古开拓者的学术背景虽非严格意义的考古学,但地质学与人类学皆与考古学紧密相关,加以他们的出身和学历、经历,对尔后中国考古学的走向应有所影响。中国虽然有将近千年的金石学传统,但20世纪初发展出来的考古学却是一条崭新的西方之路,这从当时领导人物的背景来看,毋宁是极其自然的事;不过我们还是要从中国考古学萌芽滋长的学术环境,从李济所服务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新史学的发皇地的学风,以及该所创办人傅斯年的学术思想来综合分析才可能贴切。这些问题下节将有所论述,这里先说考古学。
在欧洲,近代意义的考古学之开放,首推1800~1840年丹麦发生的古物学革命,C.J.Thomsen提出石器、青铜和铁器的三期说,J.J.A.Wo-rsaae从地层加以证实,Seven Nilsson透过比较,归纳出人类四期进展的生存模式:蒙昧、畜牧或游牧、农业和文明。1840年以后石、铜、铁三期说推广到全欧,像一道清光照亮幽暗的史前世界,近代考古学于焉诞生(Daniel,1978,38~56、77页)。其后西方考古学随着大学术环境的激荡,虽有进化论派、文化历史学派和功能学派等差异(参Trigger,1989),但在所谓“新考古学”(New Archaeology or Processual Ar-chaeology)看来都有其一致性,统统归入“传统考古学”之列。所谓新考古学是60年代美国的突起异军,其领袖Lewis Binford承袭Walter T-aylor在40年代对考古学的批判,而揭橥新方法与新目标,强调生态研究,把考古学材料作系统关联性的解释,效法人类学,以成为人类学做为考古学的终极目的(Binford,1962)。基本上他们认为传统考古学着重特定时空的文化特质,具有历史学倾向,重视个别性超过普遍性,故难以对人类行为提供普遍的原因和法则;而今他们要探讨社会文化体系和文化过程,解释人类行为。如果考古学还和历史有一点关连,那只不过因为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存在于过去而已。于是考古学遂告别历史,转而拥抱人类学,这在西方考古学史上,遂称作“考古学革命”(Martin,1971)。
中国科学考古虽然可以分出几个阶段,使用的方法和关注的问题是有发展的,不过就与历史学关系的密切程度来说,从20至80年代,甚至到现在,基调大体一致。在新考古学思潮传入中国以后,号称“黄金时代”的中国考古学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84)也重复60年代西方发生过的历史,产生“新”“旧”的分歧,中国考古学遂面临严峻的理论与方法的挑战。大体而言,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中国考古学界新旧杂陈,处在矛盾中,尤其年轻考古工作者普遍引起苦恼(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编委会,1995,43页),而领导的一代对新考古学也出现倡导和批判两种截然的态度(俞伟超、张爱冰,1992;张忠培,1993、1994,143~149页)。
西方学术传统重视创新,但往往喜欢把过去的“旧”推到极端,强调与自己的差异,以增显自己的特点。新考古学是不是真那么新(Dan-iel,1981,178页),传统考古学是不是那么陈旧不堪?60年代当时似无疑义的问题,二三十年后的看法却不同。譬如Gordon Childe,应该是所谓传统考古学的代表了,但根据新近的研究,新考古学所标榜的鹄的——通则化,也正是Childe要做而且已经做的工作(Renfrew,1994);甚至有的学者认为新考古学和后新考古学(post-processual archaeology)的争论,都可以从Childe的研究获得启发(Trigger,1994)。80年代末至90年代被美国新考古学所震撼、所感动的中国考古工作者,有些人也难免犯了西方极端化的毛病,就像张忠培批评的,把新考古学描绘成巨人的时候,先得把传统考古学打入小人国(张忠培,1994,145页)。但提倡新考古学最力,也许也是最有影响的俞伟超并不否定所谓传统考古学的看家本领: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甚至可以说他还是以这两根支柱来架构中国“新考古学”的理论的(俞伟超,1996),俞氏想要努力的是如何透过实物资料来了解历史的原貌,所使用的方法便有见仁见智的差别。
作为一个中国考古学者,面对这种分歧的学风的确两难,是要继续当一个具有“历史癖”的考古家呢,还是断然易帜,投奔人类学阵营,或是寻找独立自主的第三条路?解铃还是系铃人,问题出自Binford,我们还是从他检查起。Binford那篇革命宣言《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Archaeology as Authropology")开宗明义所引Willey和Phillips的话,其实有清楚的范围,他们说:“美国考古学是人类学,此外什么也不是”(American archaeology is anthropology or it is nothing)。虽然美国考古学的方法、理论源自旧大陆,不过就历史的延续性和古今连属的文献来说,Willey等人不能不承认美国无法与欧洲、中东、亚洲的考古相提并论(Willey and Phillips 1958,viii)。所以应该变成人类学的考古学,是像美国那种没有历史文献只有民族志的地方,但换到B-inford的手中,无限推广,“美国考古学”只剩下“考古学”,而“我们作为考古家”者就是要在“我们的园地扛起完成人类学目标的重责大任”(Binford,1962)。
在我看来,资料可以规范学术的性质,自然与人文的大分野且不说,即使在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域内,虽同样以人或人群做为探讨的对象,不同资料可能造就五花八门的学科,范围缩小到考古学也是不同样的道理。一般讨论考古学方法论都离不开资料、技术、方法和理论4个重要概念,诚如张光直所说,资料是研究历史的客观基础,技术是取得资料的手段,方法是研究资料的手段,理论是研究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的总结(张光直,1988a,61页)。然而对于“人类历史的规律性认识”也是以资料做基础的,所以考古因资料之不同自然产生不同的技术、方法和理论,于是形成不同的考古学。美国考古的资料性质,至少在历史延续性方面不同于中国,中国考古学借他山之石以攻自己之错时,岂可毫无别择地照单全收?下文我们在新考古学和传统考古学之间有所取舍去就,基于资料规范学术性质即是一项重要的考虑。
学术发展往往有其传统,不论批评或继承,皆有特定对象和特定义涵,异地移植,同样名词的指涉或内容并不一律,这就像越淮两种的橘,其实已是枳了。美国新考古家所批判的传统考古学,大部分对象是西方的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e-historical archaeology),而中国提倡新考古学的人,批判对象之一也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性。这两方面的“历史”是否雷同?不能不分辨。在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急遽转变,亦有学派和阶段的差异,不能简化为“中国历史学”,更不能混淆地称作“传统史学”。这个划分认识不清,即使睥睨Binford “教主”的人(张光直1994;1995,132页)也难免走Binford的老路,把历史学当作“旧”,西方传来的考古学当作“新”,而号召中国考古学家脱离“传统史学”的窠臼,投入人类学的阵营(张光直1981;1992;1995a,1~24页)。俞伟超不否定考古学重建历史的功能与任务,但对历史学的理解也同样定位在传统的史学(俞伟超,1996,56、62页)。这是由于对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尤其是傅斯年所倡导的新史学的陌生而造成的误解。
尽管60年代兴起的新考古学在欧美已经过时,但他们提出的考古新路径以及后来风起云涌的更新的各种考古学派,如象征、结构或批判等考古学(Trigger,1992,339页),在中国恐怕还没过去。它们留给中国考古家的问题依然是:中国考古学应该是“历史的”还是“人类学的”,或者其他的方式?这个困扰当从20世纪中国新史学(不是所谓的传统史学)与考古学的交涉情形来考察。
二 中国考古学基调的形成
不论新考古学家怎样把考古学拉进人类学的圈子,总不能不承认考古学和人类学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即在于它的“古”字。考古学的资料是过去的遗存遗物,不像人类学绝大部分取材于当今之世。所以考古学的时间领域便接近历史学而远离人类学,历史悠久的地区,如埃及、近东、中国、印度等地,考古家所处理的绝对年代固然古老,即使新考古家在美国的发掘研究,相对年代也都属于史前阶段。
在新史学风气下成长的中国考古学,其基调是历史重建,与美国新考古学所批评的文化历史学派不尽相同,反而含有一些新考古家所提倡的成分,这和它成长的温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学是有密切关系的。当西方考古学引入中国之时,就和当时中国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古史研究结合,其交涉点是在史语所。史语所的史学是中国20世纪的新史学,绝非传统历史学。这话要从疑古学派说起。
1923年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引起疑古和信古的辩论,李玄伯(1924)和陆懋德(1926)先后都主张只有考古学或借助于考古证据才是解决古史疑难的科学方法,但真正付诸实行的则推始于1928年成立的史语所。史语所创办人傅斯年原来也是疑古派,留学欧洲7年,于1926年底返国,深以疑古为不足,改走重建之路(杜正胜,1995)。疑古和重建都是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疑古派证成古人认定的古史其实只是春秋战国秦汉人的古史观而已;重建派则在楼台拆毁后的空地重拾一砖一瓦,以建构新的楼台,其所依凭的材料大部分是考古的证据。所以中国考古学一开始便担负起历史重建的任务。
这里历史重建的“历史”是和新考古学所批判的“历史”有所区别的。傅斯年认为“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故他揭示的治学宗旨是不断扩张研究材料和工具(傅斯年,1928;《全集》四,253~266页)。创所规模,据他手写的第一期报告书的规划共分八组,即汉语、人类学民物学、汉字、民间文艺、史料学、文籍考订、敦煌材料研究、考古学(“史语所档案”元198-1,No.2896)。尔后续有修订,1929年迁移北平乃合并为三组,第一组史料学与敦煌,第二组汉语、汉字和民间文艺,第三组考古与人类学(“史语所档案”元203-2,No.2920)。可见当时所谓的“历史”,范围是很广的,与大学科系划分所谓的历史不同。从傅斯年、李济到夏鼐都说考古学就是史学之一部分(傅斯年,1930;《全集》四,289~299页;李济,1936;夏鼐,1984),也都是这种广义的历史学的概念。这是新史学的历史概念,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要放在这种学术结构以及发展过程来看,如果不之此图,而硬以“传统的中国历史学”来突显与近代考古学之不搭调,并不符合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的实情。
在傅斯年受命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大约半年之后,李济便离开清华国学院,加入史语所的行列。他对“历史”和“重建”的认识,可以说是傅斯年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李济的安阳考古,一开始就抱定希望在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基本材料上“能渐渐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1930a;《选集》232页)。新历史植基于新资料,而新资料的取得则靠田野考古。李济说:“田野考古工作……是一种真正的学术,有它必要的哲学的基础、历史的根据、科学的训练、实际的设备。田野考古者的责任是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整理出来供给史学家采用(李济,1936;《选集》53页)。”田野考古者和狭义的史学家只有分工之不同,其追求历史重建的终极目标则无异,而且二者合则双美,离则两伤。他们的学问即是广义的历史学,李济故说:“这本是一件分不开的事情,但是有些有所谓具现代组织的国家却把这门学问强分为两科,考古与历史互不相关,史学仍是政客的工具,考古只能局部的发展。如此与史学绝缘的考古是不能有多大进步的(同上)。”缺乏以科学手段获得资料作基础的历史学的确容易流为政客的工具,不过在学术能独立自主的环境中,考古学若脱离历史,有可能沦为只是提供资料的工具,没有弘大的发展性。他显然寄望田野工作者不要仅满足于从田野发掘资料,还要进一步成为考古学家,也就是和狭义的历史结合,从事历史重建的工作。考古与史学原本分不开,换句话说是共同成为广义历史学的一部分。
从研究方法说,傅斯年新史学重建历史的方法论是用尽可用的材料,联系所有可以联系的工具,他说的工具即是学科;而且对于“史料赋给者以内,一点也不少说”(傅斯年,1927、1980,68页),也就是把各个材料的内涵、各种材料间的关系讲透彻(杜正胜,1995)。此一原则性的宣示随着世界学术的发展,工具的精神和概念的更新,可以不断扩充,最终目的是要把研究对象完整深入并且彻底地呈现。即使像新考古学家Binford所悬揭的目标(1962),从出土文物讲到生态环境(technom-ic)、社会文化系统(sociotechnic)以及社会体系内的意识成分(ideotechnic),也不出“把材料说尽”的范围。所以傅斯年新史学的方法论可以吸纳学术界不断创发的新方法。我们固不宜夸大20年代的先见,但也不必乐观相信后代方法一定和前人对立。
中国考古学萌芽伊始所表现的浓厚史学倾向,早在李济与傅斯年合作之前,他发掘西阴村的动机就很明显了。民国14年冬至翌年春,李济先在山西南部汾河流域做考古调查,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终于理出头绪,部分以历史遗址,部分以可能的史前定居点作为他前进的路标,历史遗址包括传说的舜陵和夏陵(李济,1927a;李光谟,1994,19~28页)。西阴村的史前遗址是在寻访夏代陵墓的途中发现的,他所以决定发掘,部分是这位置正处在传说夏王朝——中国历史开创时期——的王都地区的中心(李济,1927b;李光谟,1994,29~30页)。发掘结束后,李济给清华国学院师生解释他选择山西工作的原因,因为《史记》讲到“尧都平阳,舜都蒲阪,禹都安邑”,这些古代名城都在山西。据当时的学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在场,也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戴家祥,1989;李光谟,1994,170页)。民国17年11月李济应聘为史语所考古组主任,他继董作宾之后在小屯发掘,计划以小屯为中心彻底工作,“不但极可靠之三代史料可以重现人间,且可借此训练少数后进,使中国科学的考古可以循序发展”(“史语所档案”元25-3,No.348,民国17、12、20李济致傅孟真函附致蔡孑民、杨杏佛函)。可见他看重的是三代史料,而这里后来证实的确就是殷都。30年后徐旭生调查豫西,也是抱着寻找夏墟、夏文化的态度到田野去的(徐旭生,1959)。
从王国维、李济、傅斯年到徐旭生,不论涉及考古领域深浅,都有以考古学解决历史问题的倾向。新考古学家或许要归咎于中国人无可救药的“历史癖”吧?然而在中国土地上,尤其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铲子下去,非经宋唐汉周各层无法达到新考古学所赖以建立理论的史前阶段,硬叫中国考古家不理会历史问题也难,这就是上文所指出的,资料不同会产生不同之考古学的道理。当然中国考古学的浓厚历史兴趣连带把史前部分也建立历史的秩序,最近几十年中国最主要的考古领导人如夏鼐或苏秉琦,不是说史前史等于史前考古(夏鼐,1984),便以复原古代历史的本来面目为考古学之终极任务(苏秉琦,1991)。
自傅斯年揭举古史重建,李济以考古学来实践,历经夏鼐、苏秉琦前后70年,中国科学考古皆以重建历史为基调,这期间李济主编《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夏鼐参与和主编《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与《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苏秉琦主编《中国通史》第二卷《远古时代》,大抵都把考古学当作历史学看待。即使在美国学风中成长而且参与新考古学革命的张光直,前后四版的《中国古代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基本上也是一部上古史。即使以提倡著称的俞伟超,他从事的楚、羌等“历史民族区”的实证研究(俞伟超,1985),无一不是历史的著作。然而不论新考古学家或者更新的后新考古学家,凡想给中国考古学注入新生命的人,该怎样看待过去这70年的考古学史呢?
三 以科学工具重建历史的考古学
检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应深入其发展过程,发掘它所强调或忽略的地方,再分析其中的长短优劣,而不是以后世的概念或理论作批评的准绳。譬如上文提到新考古家企图熔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系统和社会意识成分于一炉,这些概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成为学术的主流课题,李济的考古学因时代的限制,未突显这些概念是很自然的,但并不表示所谓中国“传统”考古家的成果就是一些零星文化现象的拼盘而已。
大家都知道傅斯年的新史学特别重视史料,他那句“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1928)的宣言,能同情地了解的人并不多(许冠三,1986,215~216页)。上面已说过,在新史学的体系中,史料之所以占居绝对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史料可以塑成学术的方向,可以规范治学的方法。那么在中国这种不重视理论的学术传统中,对李济这种不喜欢徒托空言,而宁愿实证研究的学者,他提出的史料范围就含有方法学的意义了。李济考古学的方法论见于他申论古史重建的7类材料范围中(1962;《选集》,90~92页):
1.属于人体解剖学与生物学的古人类化石,以及东亚现代地形尚未形成以前的地文、地理、气候和动植物;
2.与东亚地形有关的科学资料,包括地质、气象、古生物等研究成果;
3.人类文化遗迹,史前古器物;
4.属于体质人类学的遗骸;
5.“狭义的”考古发掘品(青铜时代及以后的文物);
6.民族学和民族志的资料;
7.文献史料。
这7类材料可以归纳为4门:生态学(1、2)、民族学(4、6)、考古学(3、5)、狭义的历史学(7)。从新考古学来说,第三、第五是他们批判的传统考古学,也是现在有些人对中国考古学不满的所在。第五、第七属于历史时期的资料,基本上是新考古学未触及的领域,倒是关于生态学、民族学的材料和新考古学颇有相通之处。不过李济考古学涉及生态和民族的部分,意涵仍与新考古学有所差别,单论时空范围似比新考古学悠远宽阔,这是与傅斯年强调“科学的”学风息息相关的。
傅斯年的新史学以自然科学为师,他肯定顾亭林研究历史事迹要观察地形的方法,但惋惜如果能有现代一切自然科学的工具,亭林的成绩必更卓越。他相信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所以现代科学如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术无一不是供给研究历史之工具,史语所的目标也想把历史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地精确,在中国建立起科学的东方学(傅斯年,1928)。当时中国能发挥这类工具效应的机构,尤其和我们这里要讨论的课题有关者,首推民国5年(1916)成立的地质调查所。大约半世纪后,李济总结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写成《安阳》(Anyang)一书,第三章标题作“田野考古方法”(field method),却专讲地质调查所及其科学家——美国人葛理普(A.W.Grobau),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达生(Davidson Black),德国人魏敦瑞(J.F.Weidenreich)和法国人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正反映李济(或史语所)考古学方法上的兴趣。
地质调查所这5位外国专家,不是地质学家就是古生物学者,后来从他们的专业领域伸入考古而成为考古学家。上述李济7类材料范围属于生态和民族者,都和地质调查所有过密切的合作。先说民族学。
心理学和人类学(尤其是体质人类学)出身的李济,他的学术有两大课题,一是中国民族的原始,一是中国文化的原始,二者合成为李济考古学的核心(李济,1954;《选集》81~87页)。李济考古学把民族和文化等量齐观,恐怕是有更基础的历史学考虑的,也就是说,他以追究民族的起源和流变作为解答他的历史观的方法。他在博士论文中把现代中国人分作五大民族单位,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勾画他们的迁徙情况,公元3至6世纪及11世纪两次移动的规模最大,促使中国的民族变化比任何其他单一原因造成的后果都更剧烈(李济,1922;《选集》6~7页)。李济虽然根据多项标准划分民族,最基本的则是人体测量,如身高、头形、鼻形、肤色等,终其一生不曾忘情于地质人类学(李光谟,1996,150~152页)。我们发现民族一项在傅斯年的史学同样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他最主要的学术著作几乎都是环绕中国古代民族这个课题。有趣的是傅斯年大学时代就提出与流俗迥异的中国历史分期法,秦汉是纯粹汉族的“第一中国”,隋唐是汉族为胡人所挟、另成系统的“第二中国”,他认为研究一国历史不得不先辨其种族,种族一经变化,历史必顿然改观,故宜据种族之变迁升降为历史分期之标准(傅斯年,1918;《全集》四,179~182页)。于是史语所人类学组乃有地质人类学之研究,这不但是李济考古学的特色,也是傅斯年新史学的特色。
探索民族的原始主要是把人体测量方法应用于考古发掘的人骨资料上,李济致力的“北京人”研究即凭借上述地质调查所步达生和魏敦瑞的成果(李济,1965;《选集》98~127页);步达生也曾利用安特生提供的出土人骨材料研究华北史前居民和现代居民的体质特征(Black,1925a、1925b、1928)。像这样把古生物学、古人类学等工具引入考古学,不但构成李济考古学的重要成分,也成为中国考古学不可分割的一个部门。考古发掘重视人骨资料遂亦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传统。首先是史语所殷墟发掘的人骨,50年代以后累积的资料时空范围更广,时间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到青铜时代或更晚,空间遍布中国各地,研究的目的也不外想阐明人种起源和发展,了解史前各地居民体质特征以推定其种属,进入历史时期则想印证文献所记载的各种民族(韩康信、潘其凤,1984),基本上还是沿袭李济的传统。
傅斯年也认为考古学与人类学的关连应该特别注意人骨测量(1930;《全集》四,294页),故史语所设有人类学组研究田野考古所得的人骨资料,李济在台湾大学则创办考古人类学系。但这两个机构的考古学却没有走上民族考古学(ethnoarchaeology)的路子,不像Binford根据阿拉斯加Nunamiut Eskimo 、南非Bushmen或澳洲土著等民族学调查研究而解释考古遗址之结构功能(Binford,1983,144~192页)。李济考古学的民族学成分虽然也理论性地包含原始民族的风俗习惯,但对现代民族志的运用是相当谨慎而节制的,深怕超过比较参考的范围太远而引出荒谬可笑的议论(李济,1962;《选集》97页)。因为基本上他认为民族学家调查公布的材料,可靠度的差异甚大(李济,1941;《选集》37~45页),比起古生物学、体质人类学,是够不上称作“科学”的。
科学工具应用到考古学,第二个领域是鉴定动物骨骼以推断当时的生态环境。李济这方面的工作也和地质调查所分不开。他主持殷墟发掘,一开始就关照到生态的层面,即使在西方也算先进的。参与鉴定的古生物学家有德日进、杨钟健和刘东生,先后认辨出安阳29种哺乳动物(de Chardin and Young,1936;杨钟健、刘东生,1949),它们有的野生,有的家养,有的外地引入,就全群动物观之,与现在安阳之哺乳动物分布大有出入,显示当时黄河中下游的生态与今日颇不相同。这些动物同时包括有习于寒带生活和热带生活的种属,譬如以竹子为主食,只生存在海拔3000米以上之寒冷山地的扭角羚(Budorcas taxicola lichii)(杨钟健,1948);但也有南方热带的象、水牛和竹鼠。印度象(Elep-has indicus L.)即使是南方的贡品,放生供商王狩错,当时黄河中下游也要有适宜它生存的气候生态,何况水牛是最为普遍的动物之一,而生于南方森林地区的竹鼠(Rhizomys cf.troglodytes Matth.and Gr.)在安阳也不算罕见。另外殷墟出土的鱼骨发现鲻鱼(Mugil sp.),此种鱼产生于中国东南沿海江河入海之处,安阳地处内陆,不可能出产。学者遂推测,若非贡品,殷商时代安阳的地理环境与现代必不相同,可能有盐分较高的内地湖泊,或者有直接入海之川流,鲻鱼得以溯江而上抵达安阳地区(伍献文,1949)。
1949年以后,继承史语所考古学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4年发掘西安半坡,同样注意兽骨,并及于孢粉分析(《西安半坡》附录),应该也是史语所传统的延续。半坡之后比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都不忽略生态考古的资料,如临潼姜寨和白家村、宝鸡北首岭、南郑龙岗寺、淅川下王岗、宁阳大汶口、兖州王因和西吴寺、泗水尹家城、胶县三里河、上海崧泽、南京北阴阳营和余姚河姆渡等等,不烦备举。可见中国考古学注意生态资料不但有悠久的传统,而且也蔚成风气。
生态考古学是把生态区域、人群结构和文化特征合在一起考虑,以探索人群为适应生态环境所引发的文化变异。Barth说考古家如能在三者的关系回答“为什么”的问题,就可以对人类学的一般领域有所贡献了(Barth,1950)。这种研究推到极端,认为生态塑造产业形态、制约人口结构而形成文化特征。新考古家便千方百计想以有限的生态和人口的变数证明它们对社会文化体系之形成占有关键的角色。相形之下,中国“传统”考古学的生态研究遂显得保守,只停留在动植物遗存所反映的自然环境和气候的变迁(贾兰坡、张振标,1977;柯曼红、孙建中,1990),以及环境因素对经济类型或经济成分的制约而已(高广仁、胡秉华,1989)。回顾30年代史语所与地质调查所合作分析殷墟动物骨骼以来,中国考古学利用生态资料重建历史的传统并无太大的改变。不过像Barth 的论证,从北极区的狩猎采集经森林区到Mississippi谷地的农业和半游猎形态,研究的对象甚为原始,生态决定的成分固可能比较大。即使如此,生态系统派的考古学者在变化过程上所作的解释,经常是建立在一连串的假设上,没有明确地证实(参Change,1975;张光直,1983,141~142页)。而且从文明发展的进程来看,新考古家的持论反而有失偏颇,他们那么强调生态、人口或技术决定论,轻忽个人才智之创发,漠视人类有效控制自然以增进生活品质的方法,对一切文化的改变似乎认为与人的主动性可以完全无关(Trigger,1992,289~290页)。这是缺乏说服力的,所以李济浅尝即止的生态研究反而给中国考古学树立一个“不及于乱”的规范,作为重建历史或古代社会的基础,但不至于发展成体系性的环境决定论。
四 重建过程中对外来思潮的回应
傅斯年矢志把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统移到中国,不论吸收的人才或交往的学者,都是通达学术行情,占据世界学术主流的人物。他倡导的治学态度是留心世界学术思潮,对这些思潮作出回应,但又坚持走自己的路,不轻易盲从。史语所的中国考古学便在这种气氛中逐渐茁壮的。
当史语所创立之时,欧美考古学流行的思潮是文化历史考古学(cu-lture-historical archaeology),目的在重建过去的生活,对于文化来源和发展的解释,采取1880年以后的传播论,而不是更早流行的进化论。也就是说,他们相信文化动力受自外来更甚于发乎内在的因素(参Trigger,1989,104~206页)。就文化历史学派而言,考古学整合入庞大的历史学,与傅斯年新史学的宗旨正不谋而合;但从当时世界主流的传播论来说,中国文化成为西方文化的余绪,则非傅斯年、李济等人所能接受,至少在民族感情上如此。其实文化历史学派的研究取向就像民族主义史学一样,有可能造成民族主义考古学(Trigger,1989,174页),不过由于傅、李笃信科学,而且强调客观的治学态度,他们既不愿诉诸情绪以哗众取宠,又想据理服人以进军世界学术主流,这条自己的路走起来便倍觉艰辛。
世界古文明不论像Glyn Daniel 所分的六区或像Henri Frankfort分的三区,夏鼐指出只有中国这一区成为传播论派和独立演化论派争论的交锋点(夏鼐,1986,85页)。当1921年春天安特生在仰韶村南的深沟发现细致的彩陶竟然跟石器一起出现,他无法解释,备感沮丧。等他回到北平地质调查所,查阅Raphael Pumpelley 在中亚Ashkhaba附近之绿洲Anau 的发掘报告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Prehistoric civilizations of Anau,遂有所体会,同年秋天再赴仰韶村从事系统发掘(Andersson 1947,1~4页),于是提出仰韶彩陶西来之说。安特生比较仰韶与Anau 和乌克兰Tripolje 的彩陶,采取英国考古家Hobson等人的断代,认定河南彩陶是西方的彩陶经草原带东传而来的(Andersson,1923,34~40页)。安特生的说法,尤其关于西方彩陶的考古发现,很快获得T.J.Arne的补充(1925)。根据Arne的研究,自Anau以西,经外高加索(Transcaucasia)、伊朗西南Elam地区的Susa、Tepe Mussian ,两河流域下游的Abu Shahrain,至Tripolje这一横贯东西的路线上,另外伊朗南方的Baluchistan和印度的Deccan等都有彩陶发现。这些遗址加上1923~1924年安特生在甘肃的发掘调查,一幅洋洋大观的东西彩陶分布图就出现了(参Childe,1926,176页)。
Arne 比较陶器的色致、形式和纹饰,断定仰韶彩陶与Anau一、二期同时(1925)。Anau遗址分南北两个大土堆(kurgan),北堆早于南堆,第一、第二期在北堆,第一期属于石器时代,第二期属于铜石并用时代(Pumpelley,1908,50页)。仰韶时代与Anau孰为先后,安特生曾请教负责Anau 田野发掘的Hubert Schmidt,Schmidt的态度比较保留,不如上述Hobson等英国考古家之坚定(Andersson,1923,39~40页),也不像Arne把未见金属器的河南彩陶当作西方第一次传入,而出土金属器的甘肃彩陶则排在第二次(Arne,1925,23~24页)。中国考古家在这种学术潮流中,则想找出既为世界学术所接受,但对自己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又觉得是合理的解释。
1926年春天李济发现西阴村史前遗址,当年秋天从事发掘。发掘的报告开宗明义就提安特生在中国境内西自甘肃,东至奉天发现多处类似西阴村的文化遗址,李济认为安特生“所设的解释好多还没有切实的证据”,我们急需要做的,“不是那贯串一切无味的发挥,而是要把这问题的各方面,面面都作一个专题的研究。”西方考古家根据东西相距数千里的零星彩陶就建构自西徂东的传播路线,这种贯串的大理论,李济认为是“耗时无益的工作”;而且西阴彩陶若与别处的“对照”比较起来,并没有显著的抄袭痕迹,如果说彩陶原始于西阴村,其实也举不出反证的(李济,1927b,5、30~31页)。然而1929年秋季的安阳发掘,却在未经翻动的地层发现一块带彩的陶片,李济把它放在当时对彩陶所理解的时空架构中,回应Andersson、Arne 等人关于Anau与仰韶关系的论断。李济采取H.Frankfort比较审慎的态度,图案花纹偶尔的相似不一定是传播造成,有些毋宁可以独演得到。而且Anau与Susa的年代尚有疑问,“所以仰韶文化的时期并不能因为它与中亚、西亚共同有带彩的陶器缘故而得到什么准确的程度”(李济,1930b;《选集》239页)。今日这个考古学与人类文化史上的大课题虽然有比较明确的见解,唯在70年前中国考古学萌芽之初,像李济采取这种保留的态度,固然是他严谨学风的展现,但似乎也不能完全排除带有民族主义的成分吧。
对于强大的文化西来说的浪潮,史语所的新史学不会全盘否定,只采取审慎的态度;然而城子崖黑陶文化的发现,给傅斯年和李济的学术找到出路,可以合理地安顿他们的情感,好像久困重围的孤军忽获外援,而杀出条路。他们在史语所出版的考古报告集《城子崖》的序言分别这样说,这个遗址“不但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田野考古的工作也因此得了一个可循的轨道”(李济,1934);或说“中国史前及史原时代之考古,不只是彩陶这么一个重大问题,”也不应“以这个问题为第一重心”(傅斯年,1934)。支持这个理念的即是城子崖这个与西方彩陶截然有别的新端绪。所以在传播理论流行的时代,傅斯年的新史学能摆脱一元论倾向,确认“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之上的”(傅斯年,1934)。这是文化起源的多元论,从一个以上的文化起源中心复原古代历史、社会与文化,中国考古学遂开展了自己的前程。
Raphael Pumpelley中亚探险,Anau 的发掘是要解答他长年以来有关亚利安(Aryan)民族、文化、语言与欧洲之关系的问题,所以 Anau彩陶及其他动植物的文化遗存被解释成两河古文明的来源,从中亚到两河,一种由东而西的传播(Pumpellet,1908,xxv,67~75页)。但 Anau及其以西的彩陶资料放在安特生的架构中就成为近东与远东的比较了(Ande-rsson,1925)。且不说Pumpelley的假说能否成立,近东或中亚,对中国而言皆是“西方”,后来俄国学者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976、1989 中译本),便受到更带有民族感情的批判(邵望平、莫润先,1989;杨育彬,1976)。瓦西里耶夫把中国文化西来之“西”放在西藏一喜马拉雅山地带的北部,这里他推测可能曾是人种或民族的核心,其中一部分分化出来成为“原中国人”(中译本作“原始中国人”,疑当是步达生所谓的proto-Chinese),给中国带来新石器文化(瓦西里耶夫,1989,168~170页)。这和安特生等人的理论一样,同样很难证实。经过几十年考古资料与研究的累积,中国境内的考古系列自然比李济时代的认识更加清楚,中国文化本土起源说已有更多客观的证据,不是只靠民族感情而已,但对东西彩陶的“相似性”似乎也不能存而不论。严文明便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彩陶不但不同源,发展过程亦未曾有重要的联系,因为相似的自然条件和文化水平是可以独自发展出相似的彩陶的,所以彩陶可以有多元的中心(严文明,1987)。这反映50年代以来中国一些考古学者的意见,即相似的生产水平和自然环境会导致类似文化面貌,而非依赖文化传播不可(俞伟超,1996,103页)。这些看法活像德国民族学家Adolf Bastian的翻版,他说:类似环境面临类似的问题可能创造出类似的方法来解决(Trigger,1989,100~101页)。
中国考古学者反对文化西来说,主张中国文明本土起源和发展,是有附带条件的,即使在弥漫民族主义的中国,夏鼐并不排斥在发展过程中可能加上一些外来的因素(夏鼐,1985,84页);大多数古史学者和考古家都承认有不少中国文化的源头非在现代中国疆域以外追查不可,如果以传统汉文化的区域为范围,即所谓中国本部,外来的成分则更多。对实证研究者而言,如何发掘或认识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外来因素,才是重要的课题。李济在这方面给中国考古学立下一个规模,他是把中国的历史文化当作全人类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来看待的,因此他不止一次地提醒学者要突破秦始皇给后人设定的界线,要我们北越长城以寻找中国文化的源流,南方也要走到太平洋诸岛上去(李济,1954、1962;《选集》80~97页)。所以李济讨论殷墟出土的5种兵器和工具便放在横亘欧亚大陆的青铜文明中来分析,推测带銎或带环的兵器与工具应有中国以外的因素。不过对于殷墟和南西伯利亚Minussinsk盆地的青铜文明,谁是传递者,谁是接受者,李济在保留存疑之中多少带有自东徂西的倾向(李济,1933、1929;《选集》530~546、317~319页)。
古人并没有现代的国界,文化交流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如果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传播论以人类文明出于西亚是谬误的,那么强调文化的自发性,中国学者既排斥西来说于前,却宣扬中原文化一元中心论于后,遥远的周边接受中原文化,在逻辑上显然是矛盾的。中国考古学经过60、70年代盛行的典型中国传播论“龙山文化形成期”(Lungshanoid Cul-tures),此一直到80年代初苏秉琦提出“区系类型”理论(苏秉琦,1981)才寝息。区系类型以多元中心建构中国本部文化的根源,但又不忽略其间的交流,比较能全面解释现有的考古材料。区系划分法虽因人而异(参严文明,1987;苏秉琦,1991),但现在提出的说法尚限于中国本部。如果说青藏高原、戈壁沙漠真的产生阻隔作用,那么区域类型所勾划出来的蓝图是可以支持中国文明独立起源于东亚的理论的;可是如果中国本部与外界仍有交通孔道,它在整个亚洲地区“区系类型”的位置,与其他区系的关系是重译而来,还是直接传递?这些问题至今犹缺乏比较清楚的看法。现有的理论架构仍达不到李济的视野——以欧亚大陆做为中国考古学的基盘。
从亚洲或世界看中国并不意味中国文化没有本土的成分,史语所发展出来的中国考古学毋宁是更肯定后者的。傅斯年说西洋人治中国史多注重外缘的关联,其所发明多在“半汉”的事情上;他虽承认这方面的重要性,但同时觉得有些更重要问题却是“全汉”的。他说,如果按照传播论,先秦文化“只是西方亚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个分子,我们现在已有的知识已使我们坚信事实并不如此”(傅斯年,1934;《全集》三,207页)。这是史语所寻找东方黑陶文化的思想动力,从后来中国文化的特质逆推,应有相当大的成分是独立发展成功的,李济曾举骨卜、丝蚕和殷代的装饰艺术,即使外国人也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李济,1954;《选集》87页)。所以中国考古学成立之初,即具有一种倾向:在自己的文化系统内寻找文化演变的轨迹。基本上这个倾向和Binford从内在观点考察文化变化(Trigger,1989,295~296页)颇有相通之处,虽然他们采取的手段并不相同;但如果从兼顾外来因素这点来说,中国考古学又比60年代的新考古学更具先进性,像Ian Hodder所主张的,带着世界体系的要求,在更宽广的领域内了解考古文化的内在质素(Trigger,1989,350页)。所谓世界体系,傅斯年提倡的新史学除研究大家习称的“汉学”外,毋宁更看重非汉文化的“虏学”(傅斯年,1928;《全集》四,258页)。在考古学方面,李济则把中国放在乌拉尔山、喜马拉雅山和印度洋以东的亚洲大陆,环太平洋的各群岛,从北极到南极,包括南北美洲,这一个大区域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以寻求殷商文化的来源(李济,1954;《选集》81页),这样可能反而比“闭关自守”式的研究更容易看清楚真相。
由于时代风气的影响,李济考古学探索文化内在发展轨迹显然带有进化论的色彩,有些地方难免陷于单线进化论之弊。人类学进化论把各种不同文明安排在一个普遍的进阶程序上,考古学进化论也不例外,把物质文化纳入一张进化表,根据几个简单的原则解释形制异同的变化。如Henry Balfour所举竖琴的例子,会古今异地诸例于一堂,近代非洲、南美、几内亚等后进民族简单弓弦的乐器是竖琴的早期形态,古代埃及、叙利亚、希腊和印度的复杂竖琴是进步的形态,不问民族有无迁徙,文化有无交流,假定凡成为人类使用之竖琴,必经过如此的阶段。事实上进化论者如Balfour不能不承认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所谓“真正的”(actual)连续并不能获得历史和考古证据的充分支持,他们甚至不预期事实的发展序列必会出现,不过根据形制的相似性,认为掌握住所谓的主流(main stream),就可建构它们的进化程序(Myres,1906,viii-xiv)。说穿了这是一种理想形态,不是事实。但考古进化论派健将Gen.A.Lane-Fox Pitt-Rivers 即以这种方式建立他的进化理论,一根最简单的棍棒,可以演化出无数的形制:据我初分,第一种发展方向或是蘑菇头棒(Mushroom club),或是鸟头棒(bird club),第二种方向或是棍棒回飞器(waddy boomerang),或是回飞器(boomerang);第三种方向成为盾牌(shield),第四种方向抛置棍(throwing stick),第五种方向或是鹤嘴战锄(war pick,malge),或是称为leangle的战锄;第六种发展方向则是长矛(lance)(Pitt-Rivers,1875,Myres,1906,pl.Ⅲ)。然而这张兵器或工具的发展系谱只是形态学的关系图,没有历史或考古的根据,也可能不是真实的进化表。
这种古器物进化论对李济影响颇深,他研究小屯出土的各式青铜小刀,即本着由简而繁的原则建构一幅系谱(李济,1949,插图26;《选集》647页),大抵采用Pitt-Rivers研究澳洲土人棍棒系谱的方法。他不但把凹背凸刃的北方式刀和凸背凹刃的中原式刀共属一族,也把环柄与兽首柄的北方式刀与中原刀列为同科。我们今日已清楚地认识环柄刀和兽首刀、剑是北方民族文化的标识(参杜正胜,1993;陈芳妹,1992),它们在殷墟出现,显示彼时北方文化对中原的影响。但李济却认为殷商的兽头刀都由较简单的开始,经其长期孕育发展而成,以兽头装饰的风气则系商人接近动物群之故(李济,1949,36页;《选集》650页)。这种解释显然完全排斥外来的因素,与他之对待有銎兵器的态度(李济,1933;《选集》522~546页)截然不同。强调科学考古的李济建立古兵器系谱当然不会像Balfour所说,只掌握器物发展“主流”而不追究历史与考古的证据,他研究豫北青铜句兵自殷商到战国大约1000年的历史,遂依地区分成小屯、侯家庄、辛村、琉璃阁和山彪镇五组,由以测铜戈上下刃线的比率,以建立胡穿由无而有,由少而多的进化史(李济,1950;《选集》686页)。他得出的发展序列虽然大体上符合事实,但殷代无有胡戈的结论便被西北冈1003大墓所出的铜戈所推翻(参梁思永、高去寻,1967,123~125页)。这是器物形态学建立发展史可能经常会遭遇的难题,不是李济一个人所能解决的。
李济治学素以严谨著称,而仍不免发生这样的错误,可见器物形态的发展如果没有精确的地层根据加以约束,充足的资料呈现其全貌,恐怕很难避免上述进化派论的流弊。苏秉琦以较多的资料作基础,在这方面有比较进步的贡献,他不但坚持地层学是形态学的基础,“运用器物形态学进行分期断代必须以地层叠压关系或遗迹的打破关系为依据”,而且把器物与人以及社会的因素结合一起,“不能把器物形制变化理解为如生物进化”的模样(苏秉琦,1982;1984,254~255页)。这样,器物类型的系谱才可能比较接近真实,而器物所代表的人们和社会的历史也才可能重建。虽然中国考古学的器物类型系谱不会再蹈百年前进化论派的覆辙,但如果我们没有忘记二里头一至四期文化归属、划分的争议,卑之无甚高论的形态学,最困难的恐怕是具体的实践吧。它做为考古学的一大特色,考古学的看家本领,担负建构长时段演变的任务,但比之百余年前的Pitt-Rivers,Oscar Montelieus,或50年前的李济,现在的精密度又长进多少呢?这似乎是中国考古家不能不省思的问题。
五 中国考古学的前景
这个问题系于各人对本文开篇所提问题的看法而有所差异,是要做一个历史学倾向的考古家,还是人类学倾向的考古家?当然不一定非采取排他性的抉择不可。而且根据各种客观条件,拾长避短,对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仍然可能有比较一致的共识。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多少可以掌握中国考古学自萌芽以至茁壮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些特质,一方面回应过去新考古学输入中国所引起的争议,另方面也指出不能无视于学术发展脉络,而只机械地抄袭西方新旧考古学的划分。其实就西方考古学的发展而言,新考古学者截然区分新旧也不见得是正确的。Binford自许站在西方考古学进化改变的主要转折点上(a major point of evolutionary change),英国考古学家Gl-yn Daniel则评论说:“考古家总是谈论进化改变和文化进程,1960年代美国此一宗派的考古家似乎忘了考古学史,也许我写这本《考古学小史》(A Short History of Archaeology还有一点价值,让他们读读或再读Thomsen,Worsaae,Montelieu和Childe”(Daniel,1981,191页)。这话对现在中国考古家,不论是否宣扬新考古学,恐怕都还有意义。
果不其然,70年代以后愈来愈多的考古学家相信史前文化相当歧异,有人且暗用历史特殊性来解释文化歧异性,所以备受“新考古学”批评的文化历史学派又隐然复活。大体上再度肯定历史复杂性中的特殊相,而文化的发展除物质因素外也连带注意意识形态、信仰和文化的传统。于是不多久就产生新历史学派和新进化论派(Trigger,1989,329~369页)。最近20年西方考古学思潮的启示,未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应恢复其传统精神,抱着兼容并蓄的态度,收集各种可能的资料,运用各种可能的工具和方法以建立中国考古学的内容。原则上仍然沿袭傅斯年的方法论,发扬李济的考古学,但辅以台湾过去三四十年新史学的发展经验,追求整体性和有机性。60年代许倬云把社会科学一些方法引入史学研究(许倬云,1966;1982,619~645页),二三十年后我提倡新社会史学,都可算是新史学传统的进一步发展。根据我们的理解,历史可以分为物质的、社会的和精神的三个层面,研究者可从任何一点入手,寻绎多层面的关联,再从各层面的关系建立研究对象的有机性,最后完成其整体性,使重建的历史不但有骨骼而且有血肉、灵魂,这样的历史也才可能和现实人生接榫(参杜正胜,1992a)。这种新史学的方法同样可以应有到考古学上,而弥补被新考古家所批评的不足之处。苏秉琦要把史前考古学升华到史前史,不但具备“硬件”的骨肉还具备“软体”的灵魂(1991;1994,15页),恰与我们的史学见解不谋而合。显然,到90年代,虽然经过新考古学的冲击,中国考古学还是沿着新史学的道路前进,资料、方法、观念、课题固然大为丰富,但历史学取向的基调还是一以贯之,不至于像新考古学偏重生存模式而轻忽社会组织与精神现象。
考古学主要的研究对象是经过科学发掘所获得的物质遗存,但考古学不限于物质文化,考古学也不等于物质文化史。美国新考古学家批评传统考古学只研究“物”,不研究“人”,这样的论断是否公允,我们该怎样理解,都可以再讨论,至少中国的考古学自萌芽以来,以它具备历史的基调,从未放弃透过物质以探求古人活动的尝试。张忠培所谓“透物见人,研究历史”(1993;1994,143页),即是科学考古引入中国以来就揭举的奋斗目标。尤其50年代以后,有些考古家在这方面更有意识地进行探索,新石器时代的研究成果较著者可以张忠培和严文明为代表。张忠培推测元君庙仰韶墓地反映的社会组织(1980;1990,34~50页),排比半山—马厂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齐家前期等三阶段的墓地而建构中国父系氏族制的发展(1987;1990,148~179页);严文明从姜寨一期村落遗址重现社群聚落(1981;1989,166~179页),从仰韶房屋基址透视家庭结构(1987;1989,180~242页)。他们的研究方法我曾撰文商榷(1992b),在理论层次上,也只是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注释而已;不过这都是透物以见人的尝试,有些甚至早到50年代末,即使放在世界考古学史中,也算相当先进的。
我们肯定经济因素影响人类文明的重要性,但属于社会层次的家庭生活、政治组织、法律规范、财产观念以及精神层次的宗教信仰、人生观与美学哲学等方面的追求则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就可塑造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Eric Hobsbawn认为马克思本人已指出每个社会各有其独特的历史,其反映于经济的变化也各有特殊的方式。因为不可能以一些通则来解释所有文化转变的具体实情,所以Hobsbawn判断马克思倾向于采取多线进化论(multilinear evolution),至少在短程或中程的时间内如此(Trigger,1989,222页)。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西方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Neo-Maxism)普遍地采取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别的看法,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非经济因素才是决定社会转变的主宰,而意识形态的复杂度对人类行为和考古资料的解释也愈来愈占重要的成分(参T-rigger,1989,341页)。夏鼐说考古学要研究的是一个社会或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传统,研究人类的古代情况,横的方面是每一时期人类各种活动及其之间的互相关系,纵的方面则是各种活动在时间上的演化,进而阐明这些历史过程的规律。但他知道不能把这种历史过程写成简单的社会发展史,而在探求一般规律之外也要分别各国家、各民族历史进程的特异点及其客观原因(夏鼐,1984)。
教条主义考古学讲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普遍原则,另一方面,美国新考古学之批评传统文化历史考古学,强调它自己具有人类学的倾向,追求普遍化,而非历史学的特殊化。表面上看来,这两种思潮,似乎可以合流。不过夏鼐反对新考古学,因为新考古学家一直没能拿出一条大家公认的新规律来(1984)。如果新考古学能在普遍规律的领域内有所建树,信奉历史过程之规律的夏鼐就没有反对的理由了吗?夏鼐过世之后,新考古学才在中国普遍发展,尤其进入90年代,新考古学以及后新考古学的理论和方法大力冲击青壮考古学者,重要著作相继译述流传。举其著者,如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编的《当代国外考古学理论与方法》(199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的《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1996)、以及南京博物院发行的《东南文化》等,中国考古学应该怎样面对此一风潮,似乎不是夏鼐引证Daniel一句权威的话“新考古学变老了”就可解决的(1984)。
然而中国考古学家所要资取于过去四五十年西方考古之经验者是什么?这是关系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重要问题。根据过来人张光直的现身说法,他认为美国新考古学对中国有用的地方是日新又新的技术和方法,以及借此技术、方法获取资料、解释资料而发展自己的看法(张光直,1994;1995,137~138页)。所谓方法应该是多样的,原则上大概不外从考古遗存见当时的社会情状,从零碎无生机物见整体的、有机的社群和人的活动。以新石器时代来说,我曾提议根据人骨的年龄、性别作人口学的分析,以了解聚落人口结构;从人骨病变推求人的健康状况、劳动习惯和饮食文化;由聚落遗址的动植物资料重现当时的生态环境和生活资源:总之,综合地建构古人生活的面貌(杜正胜,1992b)。我进而提出复原“村落共同体”的主张,就现有资料的性质分成五个层次:自然生态、聚落型态、社会组织、人群结构与人际伦理。动植物遗存告诉我们当时的生态环境,保存完好的聚落遗址使我们如亲临其境之感,聚落内家屋的大小和墓葬的排列也许可以透视当时的社会组织,人骨遗存或可反映人群结构,至于房屋的格局大概也能传达伦理变化的讯息(杜正胜,1994a、1997)。这种研究取向所得结论是精细或者粗疏,端系于田野考古资料之多寡和解释工具之精粗而异,终极目标都不外追求理论既整体又有机,与新史学的目标契合。
新史学的观念和方法注入考古学不限于整体性和有机性的历史重建,还想对文化变迁提出解释,许倬云之探索良渚文化的衰落(1997)即是一例。辉煌的良渚文化何以消失呢?计倬云从后世帝国崩溃的经验知道“报酬递减”的边际效应和复杂系统的不稳定是导致社会崩解、文化式微的重要因素,用来检视良渚文化的考古资料,发现统治阶层过度消耗资源,投下更多劳力,所得不如所失,终于拉垮原有的复杂社会体系。就良渚文化这个个案来说,当然可以再更细密地验证,但大体上这种研究方式将使Binford所批评的“历史的”考古学失去依据,Binford之流的新考古家一向批评历史倾向的考古学不能对文化改变和进化增益任何解释(Binford,1962),显然不适用于新史学影响所及的考古学。
中国考古学家在汲取美国新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时,有一点基本差异恐怕不能不注意,美国新考古学所研究的社会多很简单,以Binford对考古遗址结构的解释而言,他所涉及或参证者不是南非的Bushman、澳洲中部的原住民,就是阿拉斯加的爱斯基摩人(Binford,1983,144~192页)。中国考古学处理的资料和课题则远为复杂,70年的中国考古学一直带有浓厚的历史倾向,不全是萌芽时期确定下来的特性,也不能归咎于考古家的惰性,恐怕和资料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
历史倾向的考古学本身具有观察文化长期演变的特色,然而上文说过,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一生探索的两大课题是中国民族的原始和中国文化的原始,以他重建中国上古史的规划来看,时间拉得很长,空间推得很广,但演变的观念并不明显。李济似乎没有受到与他并世的大考古家Gordon Childe(1892~1957)的影响;Childe揭举人类文明进化的规律,从新石器革命到城市革命(Childe,1936、1951),几乎成为史前史或史前考古学的通则,但在李济考古学中却看不到类似的痕迹。80年代以后中国考古学理论的主要引导人苏秉琦基本上继承李济而有所改善,苏秉琦回顾他一生的考古志业,斗鸡台瓦鬲墓的研究打破他的大一统“怪圈”,泉护村和元君庙的仰韶文化遗址打破“硬套社会发展规律教条的怪圈”,他说,于是找到了新起点,知道中国古代文化多源,必须按实际存在的不同系统寻其渊源、特征及各自的发展道路(邵望平访问整理,1977)。这是他有名的“区系类型”理论形成的剖白,后来他概括中国考古学发展目标有三:中国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苏秉琦,1981a;1983;1984,270、301~305页)。第三项主要是研究夏商周三代,即青铜时代,李济在方法上虽未明白揭示,但在实证方面,规划《中国上古史》(待定稿)即是具体的落实。所以到这阶段,苏秉琦大抵仍在李济的余荫下经营;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他把属于方法学的区系类型理论和课题取向的古文化古城古国结合起来,中国考古学的新时期才算诞生(苏秉琦,1981、1986、1990),于是超越李济的藩篱,而对西方考古学的大理论提出一些回应。
苏秉琦将以前构想的考古学大目标进一步系统化,构成“重建中国古史”的框架:(一)从氏族到国家,(二)方国——中国,和(三)中华统一实体三阶段(苏秉琦,1992;1994,139页),这样才达到社会长程发展理论的层次。他的说法,尤其去世之前不久接受《明报月刊》的访问(邵望平访问整理,1997),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发展三部曲,与我的古史研究架构不谋而合。我把从新石器时代、三代到战国大约6000年的历史,分成从村落经邦国到帝国三大发展阶段(杜正胜,1990、1992a),过去多年的学术研究,大抵利用考古资料重建这三阶段的历史(杜正胜,1994b;1996,9~30页)。如果Gordon Childe的两次革命可以做为西方考古学理论的一种典范,那么村落——邦国——帝国的三阶段,或说“三次革命”,是否也可以供研究人类长程历史之参考呢?中国考古家似乎应多利用中国历史绵延发展的庞大资产,从本身的资料出发,尝试建构理论,才不致于捧着金碗沿门要饭。
以历史为基调的考古学并不是专为解答远古历史的个别问题而存在的,也不是专门为撰写远离现代又只局限在黄河到长江一片土地的历史而已。不论考古或历史,最终目的都是要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所以“三次革命”的理论虽为历史发展建一架构,它的价值则系于课题与结论有没有普遍的意义。像文明的起源、国家的形成都是普遍的课题,中国考古学提出的解释能不能有更大的效用?张光直的文明起源新说(1986)即是中国考古学走自己的路又回应世界考古学主流的一种尝试。西方主流思想认为文明始于人类之创造环境,并把自己与原始的自然环境隔开,因此文明的起源即宣示与前此时代之破裂。张光直从另一种方式思考,受亚洲与美洲之萨满式意识形态的启发,以人与自然连续的宇宙观做为文化底层,发展出相关的政治程序、社会体系、祭仪信仰和美学等文明。这种看法告诉我们文明的开始是人与自然结为一体,与以前的时代关系是连续不断的。张光直认为亚美萨满式的连续性比犹太基督教式的破裂性更能解释世界多种文明发展的过程。
张光直透过青铜器动物纹饰、古代美术人兽母题、亚琮、“亚形”和商巫的研究,建立他的“萨满论”(1990)。他所研究的课题都属于中国文化的“礼”,而萨满或巫只是礼的一部分,但为能够与世界主流学术对话,遂取“巫”而舍“礼”。除非我们能证明巫文化是古礼的核心或底层,否则回应式的研究恐怕还是未善用中国资料以建立一般原则吧?中国考古学界有“中国学派”的口号(苏秉琦,1981a;1983;1984,269、305页),什么是中国学派呢?除了本文论述的具有历史倾向的基调外,是不是也该从中国资料开发出关系人类文明发展的课题,经过实证研究以供其他文明体系参考,而不只是对西方之课题和结论的回应?
六 结语
60年代初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李济领导下开始编撰《中国上古史》,“编辑缘起”说:近代的田野考古学为中国新史学奠定稳固的基础,开辟建设的资源(中国上古史编辑委员会,1972)。而今在20世纪即将结束、中国考古度过70春秋之时,这门学问已累积庞大的资料,号称是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84),满怀自信,前程似锦。但资料不等于学术,如果没有方法学或理论的贡献,是不能成其为学术的。因此也有考古家对于中国考古学是否进入黄金时代抱着保留的态度,号召同志,学习西方考古学的新成果。任何学问若要维持不断的创造力,往往要靠外来刺激,或注入新的生命,所以提倡新考古学的俞伟超无疑有其一定的贡献(俞伟超,1991)。不过“黄金时代”这顶桂冠是不是要等到中国“传统”考古学汲取了新考古学的“合理内核”(俞伟超,1989)才能戴呢?恐怕是见仁见智的问题。
本文分析70年来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说明它虽一向以历史学为基调,但不能完全抄袭美国新考古学派批评西方传统考古的论调,把它理解为文化历史学派。自中国考古学萌芽之际,研究的方法和资取的工具已含有后来美国新考古学的要求,这是因为中国考古学的史学性格是20世纪引入并且发扬的新史学,不是中国的传统史学。有些考古家不明此理,也仿效美国新考古学家的呼吁,宁近人类学,而远离史学,遂产生另一种混淆。
考古家“应该”当个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家?虽是西方的问题,但给中国年轻考古工作者带来相当的困扰。人类学家研究的对象是人或人群,新历史家亦然,但与传统史学的“英雄式”个人有差别,所以在新史学脉络中发展出来的中国考古学,以对象而言,其实无历史学或人类学之分。
标签:考古论文; 傅斯年论文; 中国考古学论文; 历史学专业论文; 新史学论文; 文物论文; 史前时代论文; 地质年代论文; 历史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李济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