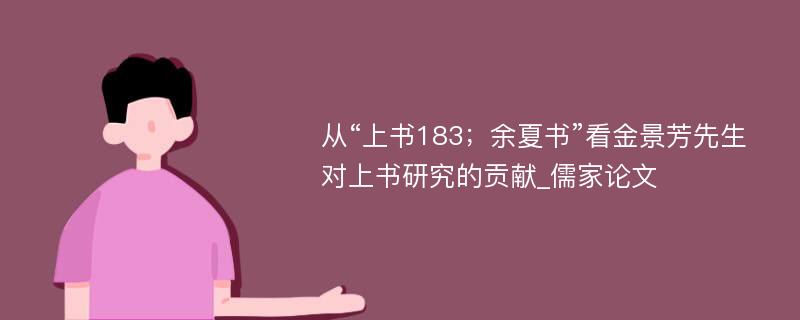
从《〈尚书#183;虞夏书〉新解》看金景芳先生对《尚书》研究的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尚书论文,贡献论文,新解论文,虞夏书论文,金景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们以“浩如烟海”赞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之丰富,而在这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尚书》则是最古老、最珍贵的一部典籍。它记载了自尧舜以来到春秋之时的为政大事和旨要,可以算是我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说中华民族的文明悠久,《尚书》所载便是这悠久文明之始;说我国的传统文化辉煌,《尚书》便是这辉煌文化的开源。
《尚书》之所以占据如此重要地位,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经过了大思想家孔子的光顾。在孔子光顾以前,它是存放于官府的尘封故档;在孔子光顾之后,原来的尘封故档经过整理编次,遂列为六艺之一,成为学子必修的课程,是社会领袖以及政治家、思想家的为政典范。
不幸的是,这部光辉典籍在秦始皇统一天下后,遭到了秦始皇的严厉禁毁,几乎销亡。秦亡之后,虽得秦博士伏生传授,但劫难之余已是残缺不完,仅保存下来二十八篇。这二十八篇,内容属夏代及其以前之书者四篇,为《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属商人之书者五篇,为《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西周包括春秋之文者十九篇,为《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尽管伏生传留下来的这二十八篇文献,并非原来《尚书》的全貌,但先圣开创文明的举措以及三代哲人为政治要的大纲,还是保存下来了。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中华民族之光照耀世界的人类文明遗产。
然而自汉代以后,对《尚书》的传治虽代不乏人,但由于汉代惑于五行灾异,六朝以后又受《伪古文尚书》扰乱,真伪掺杂,则《尚书》之精义隐晦丧失就自属难免了。逮清代学人,虽用力超于前人,但缺点是注意于文字的训诂考证,而对全句全章全文的了解却很不够。本世纪以来,因为疑古风兴,于是目《尚书》为战国之物者有之,甚或指为秦以后产生的作品之说亦接踵而出,更使《尚书》蒙尘而治者寥然。虽间或有人问津,但要旨精义的阐明就更艰难了。
王国维曾说过:“于《书》所不能解者,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不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1〕以王氏学问之搏大, 对《尚书》尚且有如此之慨叹。那么,在当前为宏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而进行的古籍整理工作中,要阐明这部古奥难懂、佶屈聱牙之典籍,揭示其精义的大任,将落于谁人之身呢?
十年前,我曾耳闻到一个消息,说于省吾先生说:“九十岁以前暂不动《尚书》,九十岁以后专力攻治《尚书》。”于省吾先生是名扬中外的学者、著名的古文字学专家,其《泽螺居诗经新证》一书,于《诗经》文字、成语、诗义的阐明,实使三千年之诗复增光辉。所以,彼时我听到于老将治《尚书》一事,曾欢欣鼓舞,拍手称快,专俟书成。遗憾,于老于九十之年不幸作古,让我惘然失望。
其后,又聆知一消息:我师金景芳先生于1989年(时年八十有八)在完成并出版《周易全解》一书之后,亦以攻治《尚书》,整理这部最古奥、最艰涩的典籍,阐明其精义为己任;也要在九十岁之年致力于斯,把其一生积累的学识献给当代、传遗后人。1991年在先生九十华诞席上,我见先生虽耄耋遐龄,但意气不衰;虽苍颜白发,但精神有加。可谓“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觉暗暗庆幸,天赐先生高寿,必能使《尚书》精义光辉于今朝。又两年之后,金老与其助手吕绍纲先生合著之《〈尚书·虞夏书〉新解》书稿便告成功,并于1996年6月由辽宁古籍出版社出版问世。
《尚书·虞夏书》是指《尚书》中的前四篇——《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其中,《尧典》记载的是尧舜治理天下和尧舜禅让之事,《皋陶谟》记载的是皋陶同禹在舜前谋划讨论为政之事。这两篇文献载记的资料,据说是舜当天下时掌史事者所录,舜为有虞氏,故后人称之为《虞书》。《禹贡》记载的是禹平治水土划天下为九州及任土作贡之事,《甘誓》是夏后启讨伐有扈氏的誓文。夏后启是禹子,他凭借其父禹平治水土的功业和影响,破坏了禅让制而把公天下变为传子制的家天下,从而建立了夏王朝。所以关于禹启的事情,当是夏代史官所传录,故传史事者称《禹贡》、《甘誓》为《夏书》,并将其与《尧典》、《皋陶谟》合起来总称之为《虞夏书》。
《尧典》是《尚书》的首篇。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这是说孔子编次《尚书》是以《尧典》作中国信史的开篇。然而金景芳先生通过对古史的全面研究后,则认为孔子列《尧典》为《尚书》首篇取义远非仅此,而是“有极深远的意义,”并指出:“孔子‘论次’《尚书》取《尧典》作第一篇,尧以前事不取,还有更深一层意义。从《尧典》的内容看,有三项是主要的,一是制历,二是选贤,三是命官。而第一项制历是划时代的大事。这件大事是尧完成的。”
说《尧典》载记的尧完成制历工作是“划时代的大事”,“有极深远的意义”,这是金景芳先生治学的精采发现,是金景芳先生学术研究的卓越成果,将遭秦火焚烧而沉沦丧失了两千余年的《尚书》精义再度揭示出来,从而使我国传统的天、天下、天子概念的形成和含义得到了历史的、实际的阐明。对于这个问题;不仅自汉以来的历代学人为之懵懂不明,即使“五四”时期以后的新史学家们亦率皆未能给以阐发。可以说这是金景芳先生在历史研究工作上的一大贡献。而这个发现,这个成果,这个贡献,来之实属不易。金老自弱冠读书治学,至八九十岁高龄之后,才得到明确的认识和把握。据我所知,金老在1956年的《论宗法制度》、1959年的《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几个问题》中,就都曾对为什么天子要祭天的问题做了历史根源的探讨和阐述;而1981年在《中国古代思想的渊源》一文中,更详细地论证了古人对天的认识过程和尧时产生的天概念的实际意义。通过这些论文,可以见到金老的治学是锲而不舍,是一以贯之。故能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得其大成而发前人之所未发或未能发。
金老在《〈尚书·虞夏书新解〉·序》中说:“我们认为帝尧制定新历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我们开始对于制定新历的重要性并没有明确认识,只是首先我们读《论语·泰伯》‘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感到惊异。孔子平生不轻许人,为什么独对尧这样称颂,简直把最美好的词句都用上了。为什么提到天大?‘则天’是什么意思?及与《尧典》对照,才了解到这个天固然是自有人类以前就有,但是人的认识,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例如在尧制新历以前,据《左传》襄公九年说,是‘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即视二十八宿中的心宿二纪时。心宿二当然不能代表天。而制新历是‘历象日月星辰’,日月星三辰就能代表天了。尧历象日月星辰制历是‘则天’,制历以后,依历行事也是‘则天’。《尧典》说‘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就是依历行事,从而达到‘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又,尧制新历以前,长时期以火纪时,人们知有春秋,不知有冬夏。《尚书·洪范》说:‘日月之行,则有冬夏。’不知道日月之行,怎能知道有冬有夏呢!即还不知道有四时,不知道有闰月,不知道一岁是三百六旬有六日。又,以火纪时之时如《国语·楚语》所说:‘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即在以火纪时时期视天为神的世界。而制定新历以后,不同了。了解天是以日月星为主体,在天上起作用的是日月星,特别是日。《礼记·郊特牲》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是其证明。正因为这样,人们知道天的主体是日月星,特别是日,而不是神。这在无形中人们的观念悄悄地就改变有神论为无神论了。由此可见,尧的废弃旧历,改制新历,是何等重要!无怪孔子论次《尚书》以《尧典》居首,而以最美好的词句来称颂尧了。”——这不难看出,金景芳先生治学不是以一书一文之章句讨论历史,而是全面掌握材料,融会贯通,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依历史实际去揭示阐发问题。
在中国哲学史上,自然天概念是尧时的实践产生的,经孔子总结而发扬。这种思想认识,对中华民族来说,其意义远远超于意识形态。范文澜在论孔子及儒家学说时曾指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中国,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从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并无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2〕为什么儒家学说能抵抗宗教毒, 范文澜仅仅以“孔子也用中庸思想来看人与鬼神的关系”和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的主张作立论基础。然而从孔子编次《尚书》以《尧典》为首篇来看,不正说明儒家学说,其根源在尧时的社会实践吗?故金景芳先生在对《尧典》做全面解释之后,又做出如下结论:“古代中国人自然之天的天概念从此形成,唯物论世界观的基础从此奠定,构成了以孔子学说为主流的传统思想文化的理论骨干。自尧及尧以后上层人物及知识界在天与天人关系上绝大多数人持理性的态度。对天神地祇人鬼的祭祀不过出于实用或政治的目的。”那么,范文澜说的“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的问题,不就不答自明了吗!
关于《尚书》的第二篇《皋陶谟》,金景芳先生在对该篇进行研究和考察后,肯定了是当时人意识形态的真实记录,是极宝贵的史料。又根据《尚书大传》记孔子说:“《皋陶谟》可以观治”,而指出《皋陶谟》是“谈政治的”。对这篇要旨的发掘,金景芳先生指出说:“我们认为这篇作品的中心内容是‘在知人,在安民’六字”〔3〕。
安民自不必说,何谓知人?《皋陶谟》文中提出了“宽而栗,柔而立,原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九德。对皋陶说的这九德,金景芳先生极为看重。在《〈皋陶谟〉新解》中,金老与吕绍纲先生从训诂到文义,从社会属性到历史作用,对此“九德”进行了详细认真的解释和阐明。不仅纠正前人的误解,而且还提出了三点想法:第一,《皋陶谟》所谓九德,如宽、如柔、如愿、如乱、如扰、如直、如简、如刚、如强,无非是人之性格、心理以及行为能力方面的特点,尚不具有后世如仁义礼智信忠孝等道德范畴的意义。第二,宽而栗、强而义的句式,反映出一种过犹不及的思想,与后来孔子表述的中庸之道一致。第三,此经之九德与《尧典》之“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似有渊源关系。而《洪范》三德正是此经九德之概括。“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相当于《洪范》的“柔克”;“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相当于《洪范》的“正直”;“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相当于《洪范》的“刚克”。《吕刑》亦有三德之说。这说明《尚书》各篇内容是贯通的。以上三点共同证明《皋陶谟》“九德”的早期和真实性。
关于第二点,我们从皋陶所说的每一德的两方面看,是既制约,又相辅。这和《论语·先进》篇中孔子对子路或哂之,或退之,而对冉求则进之,以及说子张过,子夏不及,而指出“过犹不及”的记载,实相若而又贯通。都有防止过度而导致走向反面的意义。由是可知,孔子及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实渊源于尧舜之时;儒家所主张的人的最高修养境界的“中庸”,并非如批孔者们把中庸说成是调和、是左右逢源那种不负责任的误人之论。九德是知人选贤的要旨,所以《皋陶谟》文中又一再说“日宣三德”,“日严祗敬六德”,“九德咸事”。前人对此的理解颇误。金老与吕绍刚先生解释说:“前人之所以把‘九德咸事’讲成‘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要害在于他们不懂得原始社会与后世阶级社会之不同,以为最高层领导只能做知人、官人的主体,而不会是对象。殊不知尧舜禹这样的领导人是被推选出来的。尧选择舜、舜选择禹,无不经过长期的严格考察。他们既要知人、官人,又同时自身也是被知、被官的人。而且要求的条件要更高,别人‘日宣三德’、‘日严祗敬六德’即可,他们则须‘九德咸事’”。——这是发聩震聋的讨论,无论对以住,对现今,还是对将来,都是负责任的解释,是具有超时代意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
《禹贡》是《夏书》,这是就资料的归属性而言,并不是说《禹贡》所载之事晚于《虞书》。实际上禹治水事,不仅见于《尧典》,也见于《皋陶谟》,是尧舜当天下时所要解决的一件大事。所以在时代上,《禹贡》与《尧典》、《皋陶谟》所记为同一时代的事情。但把关于禹治水土的历史资料归属于《夏书》,即夏史,把它看作是太祖高庙的业绩而着实地予以记录存档,则是合情合理的。
因此,金景芳先生在对《禹贡》作解时,指出篇首“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十二字是全书纲领,又大量引证了先秦时人包括诸子对禹敷土、甸山、陂泽的讲述,证明了大禹确有其人,平治水土是确有其事。又根据《禹贡》记载的黄河下游已非春秋中叶以后的黄河河道和“震泽三江”是太湖水域而非长江入海水道等,批驳了把《禹贡》指为战国时人地理观念或秦统一中国以后伪作的说法之非。又在考察《禹贡》所载的九州地域山川河海纯系自然地理区划时,同柯斯文《原始文化史纲》对原始人熟悉自己的乡土的论述相对照;而对《禹贡》篇八州言赋言贡而冀州只言赋不言贡的问题,与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说的“阿兹忒克联盟并没有企图将所征服的各部落并入联盟之内”,“有时有一个贡物征收者留驻于他们之中”的情况相比较,印证了《禹贡》一书资料来源的古老,从而肯定了《禹贡》篇的历史学意义。
正是因为有禹平治水土之功。所以才能有禹子启改禅让制为传子制,从而变公天下为家天下之举,故接下来的《甘誓》篇就正是这个转变事件的文献,即开创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记录。
新事物的产生是对旧事物的扬弃,即既有否定也有继承,而不是全盘废除。因此,金老与吕绍纲先生在对《甘誓》篇中最难解的两句话“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作解时,是把“威侮五行”与《洪范》“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合看,把“怠弃三正”与《尧典》“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合看。《洪范》篇是商箕子向周武王讲述禹治天下的大法。禹父鲧堤障洪水,违反了水润下的性质,因而犯了大过被殛死。这是尧舜时发生的事,是彼时引以为戒的事。即在当时来看,谁办事不顺五行之性,谁就是罪人。“以齐七政”是舜代尧主事,勤于政事。七政为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三正则为天地人,即七政之省,则“怠弃三正”即荒废政事。因此“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就是说既违背自然规律又搞糟政事。这在任何时代都是莫大的罪过,而在当时尤为令人痛恨,从而使难解之文以浅显明白之语给以释通,而夏后启讨伐有扈氏也就义正辞严了。
请读者注意,《尧典》记载的尧是“历象日月星辰”,是掌握“日中”、“日永”、“宵中”、“日短”、“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这是“天工人其代之”,把先前目为神人的天拉回到自然界的认识,是尚处于原始社会公天下时代先民的大进步。而《甘誓》篇中的夏后启则是“天用剿绝其命,予恭行天之罚”,天又变成神圣权威了。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但仔细琢磨,夏后启说话尽管威严,但也只是代天行罚,无疑,这是传承于“天工人其代之”而来。所以天始终是那个时代的社会观念核心。即当人们认识了天的自然性,把握自然天的规律行事,是人代天工;而当把这种观念用来抢夺天下时,则又把天推到神秘莫测的位置上去。于是天、天下、天子这种最具权威的观念便在社会中酝酿出来,文明社会的大门也就从此敞开了。所以《甘誓》篇虽仅88字,但文中所载的主人公已不是“允恭克让”的民众领袖,而是站在社会之上的“赏杀孥戮,行天之罚”的君王了。
通过金老与吕绍纲先生对《虞夏书》这四篇文献的新的诠解,即可使读者不难理解,《虞书》的内容是孔子所说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而《夏书》则是大同之世转为天下为家的小康时代的文献。按现代社会的人类历史分期来看,《虞夏书》所反映的正是我国从原始社会末期的军事民主制向阶级社会的君主制过渡时期的历史内容。即《虞夏书》是中华文明曙光喷薄而出时期的历史文献记录。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尚书》之《虞夏书》四篇,都曾被说成是战国甚至更后时期编撰出来的东西。于是在史学界就出现了要把中国古史缩短二千年,从诗三百篇作起的观点;或仅仅相信殷墟甲骨卜辞可作我国文明史研究材料的史学家了。因此,金老与吕绍纲先生这部《〈尚书·虞夏书〉新解》就尤有意义、尤显功力了。
注释: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二《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
〔2〕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第四章第九节第203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3〕金景芳、吕绍刚《〈尚书、虞夏书〉新解》金序, 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