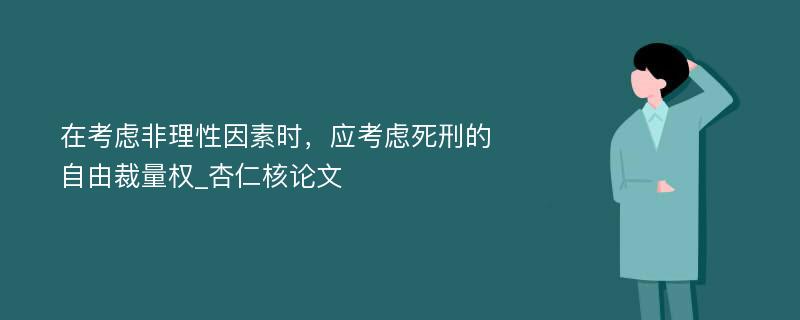
死刑裁量应介入非理性因素的考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死刑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非理性因素对量刑的影响
非理性因素在我国现行立法中不是法定的量刑情节,该因素对量刑的调控作用要么体现在总则的一般性指导原则上,要么隐含在分则的具体罪名之中。如中国《刑法》第61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刑罚。”这里的“情节”暗含着非理性因素的价值判断,通常情况下,案件的非理性因素与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成反比,从起因上看,被告人或受害人方面的非理性因素越大,案件的偶发性越大,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便越小。此外,我国刑法关于死刑的裁量制度也对犯罪主体和犯罪情节有明文的限制,具体而言,“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能适用死刑”,“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里的“罪行极其严重”也包含有非理性因素的考量,至少在犯罪动机上,情感因素的作怪是某些犯罪的直接起因,在一般人的价值判断上是“情有可原”的。再如,我国《刑法》分则第232条杀人罪的量刑标准为“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这里所谓的“情节”也应当包含非理性因素的价值判断,大义灭亲杀人、激情杀人等等都属于“情节较轻”的情况。
近年来情感因素在司法环节上也逐渐成为量刑的酌定情节。1999年10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全国法院维护农村稳定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故意杀人犯罪是否判处死刑不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结果,还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全部情况。对于婚姻家庭、邻里纠纷等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犯罪,适用一定要十分慎重,应当与发生在社会上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其他故意杀人犯罪案件有所区别。对于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从轻情节的,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解释中所列举的“被害人一方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一般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规定充分体现了非理性因素对死刑裁量的重大影响。不可否认,被害人过错导致矛盾激化恰恰是犯罪人产生非理性因素的直接原因,情感因素对量刑的介入也是现代刑事法治逐渐善解人性、延展人权的必然结果。
情感因素对量刑的影响反映在域外一些国家的刑事立法中,俄罗斯联邦《刑法》把激情杀人与一般的杀人犯罪区分为两个罪名,在量刑上也有很大的不同,“由于受害人的暴虐、挖苦、严重侮辱以及其他违背法律或道德的行为(或不作为)使行为人长期处于精神损伤的情境中,所导致的突发的激情状态下的杀人罪,处3年以下限制自由或剥夺自由刑。”相比而言,激情杀人的量刑幅度相对一般杀人罪的6年至15年剥夺自由刑显然轻得多。
德国《刑法》第213条规定,由于被杀者的严重侮辱所激怒引起的故意杀人属于较轻的情形,处1年以上10年以下自由刑。瑞士联邦现行《刑法典》第113条也把激情杀人作为从轻处理的依据,即“根据当时的情况,行为人因可原谅的强烈感情激动或在重大心理压力下而杀人的,处10年以下重惩役或1年以上5年以下监禁刑。”
在英美法系中也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行为人虽然具有恶意预谋而杀人,但他是在法律视为可以减轻罪责的情况下实施的,就应定他为非自愿的非预谋杀人罪。这种情况是指按自杀契约杀人或激愤杀人的行为,可以减轻被告的责任。”①
我国刑法理论界一直以来受“唯意志论”影响较重,认为“人的情感是可以为人的认识所左右并最终为人的意志所控制......情感、情绪乃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对于刑事责任能力并无影响……刑事责任能力只需研究人的意识和意志能力,无须考虑其情感问题”。②还有学者把情感因素降低到认识因素与和意志因素的下位概念,主张“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决定着主观恶性的有无,而情感因素只决定主观恶性的大小”。③因而,情绪因素在犯罪主观方面没有获得应有的地位,鲜有人深入研究情绪因素对犯罪的影响和作用,这不但是刑事立法的不足,也是刑法理论的缺憾。
二、情感或情绪因素是考量犯罪人主观恶性的风向标
(一)哲学依据——非理性因素对人的行为具有能动作用
非理性因素这一概念虽然在哲学理论界没有形成通识性定义,但是非理性因素的如下三个特征在哲学界是有共识的:其一,非理性因素是与理性因素共存的人类思维形式之一;其二,非理性因素是以非逻辑思维形式而存在的人类思维;其三,非理性因素的思维形式表现为情感、动机、兴趣、幻想、想象、顿悟、灵感、直觉、潜意识、信念等。④由此,非理性因素是指,直接影响人的行为及其方式,以情绪为主导并与理性相对应的非逻辑性人类思维活动。
人类对非理性因素的认识早在古希腊和罗马先哲们的著作中就已经初露端倪,但是,受宗教思想所左右,最初人类认为非理性因素来自于神的力量,如柏拉图认为:“凡是高明的诗人……都不是凭技世来做他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附着。”⑤亚里士多德也坚信“上帝的思维是直觉的,他于瞬息之间明察一切,明察其整体。”⑥直到在19世纪初,以康德为首的德国哲学家把非理性因素看成是一种先天具备的直觉。现代西方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叔本华和尼采构筑了“唯意志论”的非理性理论,将非理性主义推向了极致,他们危险地认为通过逻辑和理性的方法无法得出真理,甚至主张“自我”决定客观世界,“自我”或“自我意识”是完全不受理性制约的,人的意识是一种心理本能的要求,即权利意志的实现过程。正是由于他们将非理性因素推向非理性主义的极端,导致非理性理论的衰微。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合理地解决了非理性因素与理性因素在人类思维和行为中的辩证关系,在明确理性对行为起到支配作用的前提下,承认人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能动性。马克思主张:“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人类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或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为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⑦“没有‘人的感情’,就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⑧由此,非理性与理性一样也是人类行为的动力来源。我国哲学理论界在摈弃极端非理性主义的前提下,明确承认非理性因素在人类心理与行为中的影响和支配作用。有学者主张,在认识活动中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而发挥作用的。没有理性因素的认识是盲目的,没有非理性因素的认识是僵死的。⑨总之,理性和非理性都对人类的行为具有调控作用,犯罪行为也概莫能外。
(二)心理学依据——非理性因素能够支配和控制人的行为
1.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动定型破坏说——情绪的生成机制
人类的神经活动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巴甫洛夫认为,心理活动的机制是反射,即“刺激——反射”是人类和动物共有的神经活动模式。强度不同的各种情感是在大脑半球皮质活动的基础上产生的,而不良情绪的产生源于外界刺激对神经活动原有定型的破坏,其机理在于:人的神经在原有的平衡状态下是定型的,“皮质机能作用的变化首先可引起大脑半球的抑制状态,这时抑制过程阻止兴奋过程,然后这些变化引起非习惯性兴奋代替习惯性兴奋。这就使已形成的高级神经活动的定型受到破坏,对皮质活动提出新的、非一般的要求。皮质的兴奋过程和抑制过程之间的正常相互关系在此情况下受到破坏,这就产生消极色彩的情感。”⑩情绪型犯罪的产生过程是负面刺激所导致的神经联络转换障碍,好比“我已经激起了一种兴奋过程,而现在又想以一种抑制过程来限制它,……这是因为我造成了一种兴奋与抑制之间的不平衡……如果忽然有人要求我做另一件事,这对于我是不愉快的。因为这意味着我必须抑制我所处于其中的强烈兴奋性过程。”(11)于是,消极情绪随之而来,其强烈程度要看刺激物的性质及其对行为主体的社会意义,如果刺激属于有悖伦理道德或者将会给行为主体带来重大消极影响的,则不良情绪反应必然加强,行为的暴力程度也必然加大。
虽然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证实,“暂时联系”的接通部位并不局限于大脑皮层,海马、基底神经节以及脑干网状结构甚至小脑都参与条件反射的形成与巩固。但是总的看来,巴甫洛夫提出的暂时联系学说原则上是正确的。(12)它用神经定型破坏理论合理解释了消积情绪产生的生理机制问题。
2.“杏仁核”激活说——激情的发源地
与传统的神经活动学说不同,这一学说认为,人的情绪性行为是由大脑皮质以外的神经胞核团“杏仁核”所控制的。处于“杏仁核”控制下的情绪被称为“激情”,这是一种突发的短暂而强烈的情绪,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处于激情状态下的人会产生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变化,比如心跳和血流速加快、体温升高血清素减少、肾上腺功能增强、意识模糊且认识范围狭小而失去理智,直接的行为反应就是疯狂地毁物伤人,直到激情消解之后才会冷静下来而停止攻击行为。
纽约大学神经科学中心神经学专家约瑟夫·勒杜(Joseph LeDoux)第一个发现“杏仁核”在情绪中枢中的决定性作用。人脑“杏仁核”是形似杏仁的神经细胞核团,位于边缘系统圈的底部的脑干上端,专司情绪事务。该理论突破传统观念,认为情绪系统可于新皮质之外独立进行反应。某些情绪反应、情绪记忆的形成可不需意识、认知的参与。因为从丘脑到“杏仁核”的捷径完全绕过了新皮质,“杏仁核”可储存记忆并促使我们还不知所以就已作出反应。因而,借这旁门左道“杏仁核”可储存一些我们完全不曾有意识觉察到的情绪印象或情绪记忆。(13)
勒杜及其同事们的研究认为,过去一直视为边缘系统核心部位的海马回,其主要功能并非是情绪反应,而是登记与弄清知觉模式的认知功能。……当情绪唤起带有某种特别的力量时,“杏仁核”最倾向于把这样的时刻印在记忆里……这意味着,大脑有两套记忆系统,一套记普通事物,一套记忆有情绪意义的事物。(14)“杏仁核”的工作机理是由刺激人生气的想法或感受促使“杏仁核”分泌出新的儿茶酚胺激素,刺激越强烈激素分泌越多,前一次受刺激产生的激素还未减退,第二次的又紧追上来,接二连三地迅速使肌体处于高水平的生理唤起状态。在这积累过程中,情绪中枢急速加热,终于摆脱理性而大发雷霆。此时,人的行为已经不经过大脑皮质的控制,受情绪动机的指挥满脑子都是发泄情绪的攻击性想法,对其行为后果全然不顾,因而激情状态下的犯罪往往会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果。同时,也正因如此才会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乃至在法律上减轻罪责(其前提是受害人的过错引发了犯罪人的激情)。戈尔曼把这种激情状态称为情绪短路,当人们的神经已经绷紧的时候,一点点小事就会导致情绪短路。这时,无论是生气还是焦虑情绪都非常强烈。人们情绪的突然暴发正是短路所致。达尔文对此描述如下:“在非常愤怒,大喊大叫要对手滚开的时候,手臂能够控制住不打对方或者不使劲把对手推开的人就很少了。想要打人的欲望,往往非常强烈,其程度常常至于捶打没有生命的东西或把东西摔在地上。但这种体态又常常成为全无目的的或者像疯了一样。”(15)可见,非理性因素是客观存在的,并时刻会激发人的不良情绪进而引发攻击性行为的发生,这种从不良心理到暴力行为的转换过程极其短暂且难以控制,因而便成为减轻犯罪人罪责的一项重要理由,当然,其前提是被害人存在过错并激发了犯罪人的不良情绪。
三、死刑裁量中非理性因素的权衡与考量
(一)被告方的非理性因素
被告方的非理性因素体现在两个层面上,其一是犯罪起因上的非理性因素,即由客观刺激导致行为人大脑出现情绪短路,非理性占据整个心理并支配人的行动。其二是判决结果对被告人的刺激而产生的非理性因素,当然,这种刺激较犯罪起因上的刺激程度较轻,因为行为人事先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犯罪起因上的非理性因素由于来源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处理结果。其一,由于被告人自身的不正当行为首先激发了被害人的过激行为,转而又引发被告人的非理性行为的,不能由此而减轻被告人的罪责,防卫挑拨当属此种,如果犯罪行为极其严重可以考虑判处死刑。其二,如果由于被害人的不正当行为而导致被告人当场产生激情而引发暴力犯罪的,应当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而不易判处死刑。例如,2004年2月28日8时许,被害人的妻子与被告人在集市上因摊位问题发生纠纷,经市场管理人员调解平息后被害人又同被告人发生争吵和厮打,还将被告人摊位上的食物踩碎,随后双方被人拉开。被告人见自己的食品被踩碎无法销售而顿生愤怒,便到旁边卖肉摊位上拿了一把杀猪刀朝被害人左肋部刺两刀,造成被害人胃破裂致血气胸大失血死亡。案发后,被告人自首,法院以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其三,如果被告人并非当场在激情支配下实施暴力攻击行为,而是事后伺机报复的,应该按有预谋的故意犯罪处理,应当判处死刑不易减轻处罚。例如,2004年7月16日17时许,被告人与被害人在随同渔船返城时,因玩扑克引发争执及厮打致被告人前门牙外伤性松动。因此被告人怀恨在心并产生杀人之念。当日20时许,被告人趁被害人睡觉之机持刀捅刺其数十刀,致其左肺、右心房和肝脏破裂,急性大失血死亡。被告人威逼渔船停靠岸边离船跑走,后自首,法院以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执行。
比较上述前后两个判决,与民众的预期不会有出入,但是我们认为,前一案件的刑罚与国外激情杀人的刑罚相比还是失之过重。从另一角度,如果对这一案件的判决超出被告人及其家属对审判结果的预期程度,比如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立即执行,都可能激发被告亲属对受害人一方的仇恨产生报复动机,甚至惹起社会对被告人的广泛同情,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法律效果,而且还会引发不良的社会效果。
(二)被害方家属的非理性因素
“杀人偿命”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积淀和延续。通常情况下,杀人案件被害方家属对刑事判决结果的期待都是较重的刑罚,如果实际的判决与期待的刑罚落差很大,也会激化矛盾而导致被害方的情绪短路,从而引发新的报复性犯罪。因而,对被害方家属的抚慰也是死刑裁量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处理不好死刑判决与被害人亲属预期判决结果的关系将会使生效判决成为另一起犯罪的起因。例如,2006年5月21日凌晨,35岁的丁某在宣武区一处拆迁房内被四个出于戏谑心理的少年(最大的19岁)折磨而死。死状惨不忍睹,头发被烧掉一半,身上伤痕累累,被抢走了100多元钱和一部小灵通电话机。由于四人之中最重的判决是17年有期徒刑,听到法官宣判后被告方和被害方的反应截然相反,被告人失声痛哭悔不当初,而被害人的妹妹则感到极大的不满,认为没有人被判处死刑就等于自己的姐姐冤枉死了,于是哭喊着:“姐,你怎么就这样无缘无故地走了,你死了也不能放过他们啊……”由于双方对判决都不能接受,后续的隐患难以预则。
(三)民意中的非理性因素
由于民意反映的是民众对案件事实的心理评价,其对判决结果的期望往往将非理性因素掺杂其中。这便要求刑事司法环节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既不能置之不顾,也不能盲目顺从。人民法院审理刑事大案要案一定要在定罪量刑上把握好“宽严相济”的尺度,要做到宽严并用、宽严有据、宽严适度,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法外开恩;也不能因为有社会舆论压力增大就人为拔高,不是越重越好,更不是不分情节轻重一律顶格重判。
处理民意与死刑的关系应当把握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民意不能代表政策和法律,审判结果不能完全附随民意。
政策导向只代表一种倾向,可以引导法官形成宏观上的司法理念。而罪刑法定原则和公正司法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求有明确可靠的政策和法律为依托。
第二,民意不能强行压制,死刑裁量也要考虑民众的感受。
第三,民意不能迁就和忽视,正确引导民意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环节。
总之,典型案件的民意问题应在理论上加大研究力度并逐渐立法化,如大义灭亲而为民除害的案件、因长期受迫害而反抗中杀人的案件等等,都应当从立法上考虑情感因素的影响作用并在量刑上从轻或减轻处罚,不宜适用死刑。
注释:
①[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②曲新久:《刑法的精神与范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0页。
③转引自李兰英:《探问“意欲”为何?——对故意概念中希望和放任的新诠释》,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
④何颖:《论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载《学术交流》1989年第3期;绍六:《非理性》,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赵东海、牛婷《论非理性因素在认识中的作用》,载《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权立枝、肖安邦:《非理性因素在主体选择过程中的作用》,载《甘肃理论学刊》1999年第2期。
⑤泰勒:《柏拉图文艺对话》,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⑥梯利:《西方哲学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
⑦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43页。
⑧摘自《列宁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第1958年版,第255页。
⑨何颖:《论认识中的非理性因素》,载《学术交流》1989年第3期。
⑩转引自[俄]M·雅科布松:《情感心理学》,王玉琴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1-102页。
(11)巴甫洛夫:《条件反射演讲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4年版,第271页,转引自[俄]M·雅科布松:《情感心理学》,王玉琴等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2页。
(12)参见http://www.spe-edu.net/info/6268.htm,访问日期:2009年10月19日。
(13)参见[美]丹尼尔·戈尔曼:《情感智商》,耿文秀、查波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1-24页。
(14)[美]丹尼尔·戈尔曼:《情感智商》,耿文秀、查波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版,第26-27页。
(15)[英]查尔斯·达尔文:《人与动物的情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