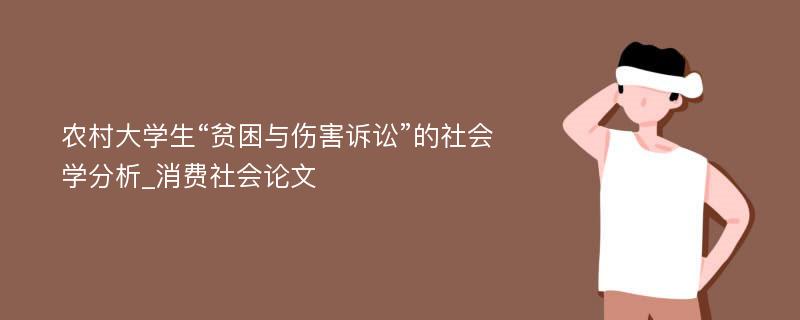
农村大学生“诉贫伤害”的社会学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农村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最近,社会上广泛而热烈讨论农村大学生申请助学金过程中“诉贫伤害”这个议题。事件缘起如下:某高校全班同学围坐在一起,听一位申请助学金同学“述贫”并评分,以确定助学金等级。该同学面对诸多师生说:“我家在农村,爸爸务农,妈妈生病长期卧床,弟弟上中学,还有一个妹妹在上小学。”①有人评论说,这是对本已因贫寒而自卑的同学的再度伤害:“公开述贫迫使贫困生不得不牺牲隐私、自揭伤疤,极可能让自卑者更加自卑,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 从高校方面看,“诉贫”举措有些无可奈何,因为助学金须针对贫困而亟待接济的同学,而在高校眼里,几乎所有学生都是无知之幕下的陌生人,只得以自我诉贫来确定助学金资格。基于是,诉贫是“不信任假设下的信任”。一方面,缘于彼此是陌生人关系,故需“诉贫”以确定救济对象;另一方面,高校在成本上着眼不可能亲往贫困生所自的农村调查其真实性,故而又以自诉为实情,这是信任。至于诉贫所以成为对贫困生的伤害,须将此问题置于当代农村大学生面临的结构压力及其自我评价的合力下看待。笔者认为,“诉贫伤害”具有一定的现代性。首先,中国古代穷书生面临的结构压力低于当今大学生的困境,另外,古代清贫书生缘于其占据的文化资本而一定地免于心理伤害,甚至可凭借其“精神贵族”②的出身而傲视王侯。其次,进入工商化的现代社会以来,“以农为本”曾经占据的社会基础地位逐步让位给城市工商为本,农村人被视为“贫困、落后以及封闭”等消极形象的化身,因此亟待被消灭或城市化。与此有关,现代社会价值观金钱化趋势影响人们的自我评价观念:德让位于富,富成为自我尊严感的基础或最后的救赎,而贫似乎是一种罪错。惟其如此,客观的贫困处境才会伤害本已脆弱的农村大学生的敏感神经。最后本文从减弱结构压力与自我内在尊严重建的修身角度提出化解诉贫伤害的举措。 二、君子固穷——传统读书人的家族支持及其德识尊严感 (一)诗书传家——传统士大夫教育的乡土特质 1.光宗耀祖——为家族的保世兹大而读书 传统社会的基础在农村,而农村基本上是血缘与地缘的重合:地缘只是“血缘的空间投影”[1]。古代人务必面向“列祖列宗”而为家族效劳,家族之“保世兹大”或“传家”乃家族子弟共有的使命。与此有关,古代读书人的心灵归属在家族及所属社区,而非其他地方。其中,“诗书传家”或“耕读持家”是家族继承乃至光大的最重要手段:耕是相对“保守”的传家方式,而“读”或“诗书”则是家族“发展”之路经。故而,任何读书人都不是单纯出于个人的求知之热情或世俗目的而读书,而是为了“光宗耀祖”而读书。 古代重私学,家族(而非家庭)往往以族田或其他经营的公共收益兴办私塾。族内子弟皆有资格免费享受家族置办的学校,这是族内教育之公有制。若“祖上有力”,且“文曲星高照”,有朝一日幸而中举,他也是整个家族的光荣与骄傲。古代读书人发迹后要反哺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而是整个家族:“只要他的收入增加,大量远亲就会纷纷要求他提高对他们的赡养费。”[2]甚至当其衣锦还乡后还尽可能造福于家族所在社区,因为社区往往不过是他的家族之扩展。即便社区里那些家族成员之外的人,也是相互守望的邻里。基于“里仁为美”的桑梓情感与现实生活的合作性,一个人对于邻里也存在一份——根植于报恩之情感基础上的——义务。例如,费孝通的父亲一贯的事业在本乡,在地方上。他留日归来,“第一件事在本乡建一所中学……接着组织县议会。”换言之,当古代读书人一旦不在家乡,他便免不了身在异乡的愁苦与有朝一日还乡的热望。 2.不患寡而患不均——农村社会分化小,书生家庭间差距较小 古代社会承认公开的实质不平等,号称形式平等的现代社会却充溢着实质不平等。相对于重视“进步”的现代社会,古代社会更加看重的是秩序或教化。为了这一目的,社会必须相对均衡。中国古代社会尽管也有分化,但较之于形式平等的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为运作中心的现代社会,古代社会就要均衡许多。古代社会往往通过“非专业化生产、限制工商、节制资本、限制过分的土地流动、分家析产”等方式而免于过度分化。其中,男耕女织是典型的非专业化生产,其生产更多是为了家庭自给自足的使用价值。再如,四民中工商的地位较后于士农,这与古代对于工商的限制性作用认识有关。工主要是手工业,而非今日意义上的大工业生产。传统的工的作用在于补充狭义上的农业之不足。至于商,总体地看,古代并不绝对禁止,而是有所限制,其作用重在“互通有无”之交易,而非谋取差价为目的。所以容许商,因为其可以互通有无而互利。所以限制,因为谨防商可能造成的分化及无情逐利。以上基本上是“以农为本”的前提下的“无工不富”以及“无商不活”的古代经济部门设置及其根据。此外,如“盐铁官营”的节制资本、财产家族共有、限制过分的土地流动以及诸子均分家产等都是防范社会过分差别或旨在追求“均”的社会设施。因此,古代家庭之间不会存在天壤之别的贫富差距。与此有关,古代的读书人的家庭或家族也不会像当今“断裂”。③ 3.清贫书生——私塾、家学、义学、书院及寺庙等地皆可节俭读书 中国古代社会尊师重教,存在一定意义上的教育机会的平等。另外,教育等方面尽可能由社会自我应对之,而非由政府解决:“秦汉以下,领土大,而政府干涉之范围狭,教育事业诸要政,任民间自为,蔚然称盛,其自营之力,诚有足多。”[3]理论地看,一个人,哪怕生于农家,只要天分好,又勤苦,命也不坏,都有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梁漱溟曾指出:“从前人读书机会之容易,非处现在社会者所能想象。……一个人读书是否中秀才……就全看你是否寒灯苦读;再者看你资质如何。”[4] 为教育平之目的,社会设置各类学校以满足聪慧而又贫寒的读书人的求学之需。潘光旦与费孝通曾以950份明清时期科举的硃卷(试卷)为样本,调查生源地的城乡分布及考取的比例情况,将分析结果与苏俄及美国比较。结论是,中国底层社会书生的就学率及考取率远高于俄,而与自诩平等的美国社会的20%的向上社会流动率不相上下。 下面我们看看古代那些提供给清寒之士的教育场所。先看私塾。办私塾的成本不高,很多设馆的教师不过是长期参与科考的“兼职人员”,他们以教书那点收入以自立,今后还要一再参加考试,直到考取或不能考为止。再看义学。义学始于宋。范仲淹少时家贫,父死后母再嫁朱氏以便使其有可能读书。范仲淹做官后在家乡办义学,使族内贫寒子弟免于其少时之苦。再看书院。书院本是自由讲学之所,客观上提供给读书人跻身所在。另外,社会上还提倡“耕读持家”。许多人一边种田,一边读书。这就是中国古代之书香社会,甚至穷苦人家也充满诗书以及礼仪。总之,古代社会具有较多的就学机会,古代书生一直具有清贫、上进而又勤奋的形象。最后,我们以唐代各类学校的盛况以证明古代贫寒之士的教育机会的相对普遍的境况:“书生少年寻师访学于深山古刹,博学的鸿儒和致仕的官员广招门徒……点拨少年。士大夫的家学注重诗文,佛教寺院亦开办儒经讲学。”[5] 4.精英教育——相对于现代平等社会,古代读书人少 古代实行精英教育,而精英教育的数量总体上受制于人性差异及古代的官的数量。一方面,天资优良的人该求学。儒家教育思想认为“人性不齐”,即人的天资上存在类型和程度的差异。旨在培养社会治理精英的教育机会应赋予那些优秀资质的人。人群中天资优秀的人毕竟少数。此外,古代教育存在着职业教育与士大夫教育的分流。一般所谓的古代教育指的是旨在培育社会精英的士大夫教育。韦伯认为,中国古代的儒家教育旨在培养闲情逸致的“文士”。韦伯注意到传统士大夫“文”的一面,而未能注意到与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史”的方面。与其说是文士们追求闲情逸致之情趣,倒不如说他们超越于一般职业或现代专业知识的视野之约束,这才是古代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背景下读书人的重要特点。另一方面,古代社会的官员数量限制精英教育者的数量。古代社会官学一体,学而优则仕。理论地看,学者趋向于做官,从而尽其服务社会之理想。譬如,孔子一直试图做官之目的,不是贪恋做官的权势或利益,而是试图以权力实现其治理的愿望。另一方面便是官员必须是读书人出身。隋唐以降的科举制就是选材进而为政府选拔官吏的制度化。可是,鉴于中国古代社会权力之“皇权止于郡县”之结构特征,县以下不存在“吃皇粮”的官员,因此,古代对于官员的要求的数量远远低于今天的官员数目。而官员数目之少也自然会限制读书人的数量。尽管如此,中国传统时期的识字率约为5%,这个数字远高于同时期的西欧社会。 (二)士志于道——传统读书人基于“德识”的内在尊严感 无论中西,传统社会都具有一定的阶级性。西方阶级社会的根据长期为“血”和“土”,也即以是否为贵族血统或占有土地与否划分阶级。中国的阶级根据自先秦后便由血统让位于德或学。至于学识,中西也存在本质差异。西方中世纪的知识掌控在神学人士手里,那些“用拉丁文写成的神学或历史著作,关于礼拜仪式的知识,甚至商业公文的阅读”,均由“少数受教育的人”[6]也即神学人士掌握。社会功能上看,古代中国的读书人有几分相当于西欧封建时期的教士。只不过,西方教士们掌控彼岸之神学知识而成为此岸的精神领袖,而人文主义的中国传统读书人所接受的是韦伯所谓的“高雅的俗人教育”,[7]他们是世俗领域的“圣”而神明之士。圣人者,人伦之至也。而基于这种圣而具有感通、感召、感化之力量,此乃中国式“由圣而神”的力量的根据。这与中国传统人文性知识的“认识你自己”的人自身以及人伦有关。梁漱溟指出,读书人追求人伦“情理”,而非“物理”。在中国文化语境下,礼、情、理或教不过是人的情感能力及其处置规则的不同领域的表现。“情理出于人情好恶,偏于主观;物理存在于事物,经人考验得来,偏于客观。”[8] 孟子的“劳心者治于人,劳力者治人”之论,亦可视为分工的理据。士以劳心者自居,士与其他平民之不同,可以“士以弘道”或“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为区分的标准。《论语》云:“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凭“德识”而非“金权”获取远远高于其他人群的社会声望。从四民关系看,士为农工商的领袖。“旧日中国社会的成分,为士农工商之四民,而士为四民之首。士人不事生产,却于社会有绝大功用。便是他代表理性,主持教化,维持秩序;夫然后若农、若工、若商始得安其居、乐其业。”[9]从价值上看,士是社会共奉的具有内在价值的理性的化身,从而达成四民一体的秩序,而非如今日阶层或阶级对立的无休止的紧张与冲突。 总之,君子或士人以其经由教育所得的“德识”取得社会的尊敬,不仅不以金钱或权力为尊严的基础,甚至还傲视金权。缘于上,基于教育的内在德性便足以支撑读书人。与此有关,读书人若有钱,但他不会因此骄傲。譬如,子贡尽管是个跨国经营的富可敌国的商人,但他依旧出自于内在的虔诚而尊敬且长期赞助长期郁郁不得志的老师孔子。与内在德性基础上的尊严感有关,古代读书人不以贫为耻,而以自己的德识落后于人而羞。例如,春秋齐桓公之相管仲说,当年与鲍叔一起经商,分钱时自己拿多的一份,鲍叔并不认为我贪心,因为他知道我家贫,且管仲每次都心安理得:“分金多与,鲍叔独知管仲之贫。”[10]缘于“惟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或“士志于道”之故,古代读书人志不在富,而在于德,因此不患贫而患德落后于人。例如,孔子得意的门生曾子与子路等都是清寒之士,“曾子捉襟见肘纳履决踵。子路衣敝缊袍,与轻裘立,贫不胜言……总之,饱德之士不愿膏粱;闻誉之施奚图文绣。”[11]当然,尽管士以德识为内在尊严的基础,但从未轻视或禁止财富,而是从道与财的不可分裂的关联看待合理致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此外,与儒家“爱物”及“通财”观相应,君子珍惜财货,且用之有道。 三、“诉贫伤害”——当代农村大学生生存压力及其与自我尊严感的外在化的紧张 (一)孤独的救赎——当代大学生的生存压力 1.自由而脆弱——家庭核心化所致的弱承担力 现代大学生较之于古代读书人面对愈加强烈的生存结构压力。几乎可以说,在极为市场化的教育环境中,对于相当孤弱的当代农村家庭及其子弟而言,教育改变命运的理想已变得像一条孤独而狭隘的救赎之旅。下面我们依次从家庭核心化、市场冲击、高等教育扩张以及基本消费奢侈化等方面看待农村大学生面临的结构性压力。 相对传统的扩大家庭或家族,现代小家庭具有较高的个人自由及流动性等优势,但也脆弱许多。刘易斯在《经济增长理论》中指出,处于温饱发展阶段的经济状况下,大家庭制度具有较高的承受力。实际上,群体化的社会结构或较高的社会团结利于人们对抗环境的挑战。传统中国家庭不仅名声好听,也与其实际的强势力量对于家族的生存价值有关。基于上,传统社会一般作兴大家族或合作性较强的家庭联合。此外,“亲戚通财”等互助制度也加强人们的抗风险能力。可以说,古代不存在个人脆弱,而只存在家族的强弱。 然而,近代以降,中国大家族被作为和皇权一样的专制制度而被打倒或日益弱化,并且代之以现代核心化的家庭。核心家庭的内在逻辑是个体主义。现代个人所面临的自由而孤独问题也渗透到现代核心家庭中。从家庭人口数量看,费孝通1936年进行江村调查的时候,平均家庭人口大约为5口人。此外,从民国期间的社会调查看,中国家庭人均人口也基本集中分布在5人左右。解放后中国家庭人口数目在70年代末期之前一度增加。但是,解放前后有一个根本的不同是,解放前各家庭虽然分立,但是家庭联合而成的家族依旧存在。而解放后家族基本沦为不合时宜的陈年旧事。更为根本的是,无论家族或家庭,其曾经的社会基本单元的地位,皆让位于已经行政化了的生产队。70年代以后,农村缘于计生政策使得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人口减少。总之,现代家庭相对于传统家族要脆弱许多。中国农村大学生的经济水平几乎直接就是其家庭的情况,因此,与农村家庭核心化的脆弱化相伴的几乎是农村大学生的集体贫困化。 2.沉默的大多数——市场化加剧农村家庭经济的边缘化 一方面,解放后,中国社会政策一直存在城乡二元分立局势,巨大的剪刀差造成农村日益落后于城市。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进一步加大城乡差距。无论是强制的不平等,还是号称形式平等或机会平等的市场化,都不断造成农村家庭经济的边缘化。如果说前后有什么不同的话,前阶段是农村家庭的集体性“均贫”,而后一阶段不仅造成城乡的差距加大,还致使农村内部家庭日益分化。我们即便承认市场化可能生产出日益增加的社会财富,但这里的财富是个总体概念,并且这种繁荣并不能掩盖市场化内在逻辑所致贫富不均。另外,当收入市场化而极其分化之际,消费也面临市场化的无差别对待。也即,市场要价一个样,不管你是富人或穷人。市场化的必然结局是,即便它制造了几个富可敌国的富翁,同时制造出更多的穷人。以当今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尽管东部地区的很多农村确实很现代化了,但是,由沃勒斯坦所说的资本主宰下的“世界体系”可知,当中国面向外部市场开放之际,其市场化的内部也难免“中心”与“边缘”的分化。由此,东部的富裕之梦恰伴随着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进一步落后。以上是中西部农村大学生家庭贫困的市场化环境分析。 3.相对贫困——大学生消费过程中“奢侈必要化”所致的压力 在消费方面,当代农村大学生面临的主要不是温饱压力,而是“奢侈品逐步必要化”所致的经济压力。凯恩斯认为,人类行为受制于需求(need)和欲求(wants):“必不可缺的绝对需求,另一种是相对意义上的,能使我们超越他人,感到优越的那类需求…即满足人的优越感的需要,很可能永无止境。”[12]凯恩斯正确区别了两类需求,且指出与奢侈有关的“优越感”需求的永无止境性。但未能揭示旨在奢侈或炫耀的优越感需求逐步向必要需求转化的现代社会机制。因为自然经济解体后,人的需求越来越受制于工商业的“社会制造”,并且工商业以先富阶层为社会需求的模板,且逐步将上流社会的需求扩展至贫民阶层。换言之,在工商时代,自然经济早已成为明日黄花,人们的生活越发依赖于市场而不自足。即便愿自给自足,但再也没有小富即安的闲适生活机会,而不得不踏上致富的疲惫之旅。然而,作为总体的底层即便日夜勤奋,他们还是难免相对贫困的窘境。 与此有关,农村大学生更多面临社会制造的日益必要化的奢侈需求。市场化的教育使得学生的用费,尤其是生活费,大大提高了。当代大学生的合理消费范围大致为800元到1500元,其中73.5%用于吃喝。其中,实际消费数据在500元到1000元的人群占55.83%,④可见贫困大学生比例之高。分析如下:第一,基本消费额偏高,而无论哪个城市,500元当能满足温饱。这说明,大学生中消费包含许多已经必要化的奢侈。例如,电脑、手机等曾经的奢侈品如今逐渐变为学生的必需品。第二,与总体大学生消费日渐增多伴随的是贫困大学生的比例增加,其中大多数势必来自农村。这与农村总体上的边缘化有关。第三,如今大学生中存在诸多请客吃饭场合及其对“品牌”的追求。例如,有人指出“90后青年人缺乏节约意识”。[13]反过来看,这说明仍有可以削减的非理性的消费空间。总之,除了少数极端贫困家庭所致的绝对贫困大学生外,大多数贫困实际上属于“相对贫困”,而这种相对贫困是无限制的教育市场化所致的奢侈必要化的产物。 4.过度教育——高等教育去精英化所致的高校的人满为患 市场化导致的不均衡,既有不足,也有过度。与教育机会不足相伴的是教育过度,农村也不例外。一方面,缘于近20来年的无节制的教育市场化之故,高等教育投资越来越超出一般农村家庭的承受力,许多农家子弟没读完中学便辍学而涌进民工潮。这是教育的机会之不足。另一方面,高等教育普及化造成大学生人数剧增。高等教育人数剧增势必造成高等教育低等化。与此同时,接受了高等教育的人还面临着职业期望与现实职业机会的心理差距。其中,很多大学生被迫从事远远低于社会或自身的期望的职业,甚至有很多大学生无奈接受纯粹毫无知识含量的劳动机会。鉴于此,有人便提出,教育远甚于职业所需的技能的现象是教育过度。我们承认这种现象的客观性。不过,我们进而指出高校逐年扩招所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教育过度。也即,越来越多远高于一个人天资的教育机会。直白地说,很多人接受由于过分扩张的高等教育均等化所致的教育机会。卢梭认为,每个人的机会决定于其自然而然的地位。反之,若教育机会超过个人资质,会有如下后果:其一,高等教育低等化,教师不得不降低标准去满足大多数;第二,天资较差的学生因为高等教育本不是适合于自己的事情而焦虑;第三,就业期望与今后职业机会的差距及其所致的不满。第四,加剧家长的教育负担,因为高等教育就读年限长于一般教育。在上述教育机会扩张的所谓福音中,就包含很多本不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农村学生,也因此包含他们的——不堪日益增加的市场化教育“投资”之压的——家庭或父母。 (二)自我空心化——当代大学生人格尊严的外化 1.隐含鄙夷的同情——以防作难的现代救助制度的心理预设 古代社会对于贫弱者的救济,更多的是出于同胞情怀。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慈爱观念是古代共同体关系下的公益的心理基础。 与之相对,理论地看,现代制度的人性基础更多是恶。起码现代市场制度的根据在于人性的恶,而非基于人性之善。而现代社会不过是市场之扩张。恶是现代社会的动力,然而现代社会也受困于人性之恶。现代社会的穷人,并非民胞物与的对象,而是“内部的外人”:“这种外人虽然可以说实质上处在群体之外,可又逗留在群体之内。”[14]与此有关,现代救济制度,与其说是同情心,不如说是防范穷人变得穷凶极恶,以至于大家——尤其是金权者——都过不上好日子。即便是现代社会也似乎在做一些善事,而其初始动机则至多不过是尽可能减少制度崩解而已。在现代条件下,对穷人的救济“并非为个别穷人的利益,而是为社会整体——政治、家庭的、某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特殊群体——的利益。”[15]因此,现代社会的救助制度潜含着对于弱势群体的兼含一丝鄙夷的同情。尤其是在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视野下,那些被救助的人往往有一定程度上被视为懒惰或愚蠢之辈。基于上,现代救助制度,一方面是对穷困者的救赎,另一方面,被救助往往又被视为穷人的耻辱之印记。 2.与人生分离的教育——现代大学生自我价值的他者化 当代农村大学生所以会遭遇“诉贫伤害”,是因为外在的贫困遇上了内在的人生教育的缺失所致的自我孱弱。 古代读书人起码理论上可以几近傲慢地宣称“士志于道”、“士以弘道”、“君子喻于义”,因而“君子固穷”。因为,基于道义之内在价值及其赋予读书人的尊严感,读书人可以不富裕,甚至很穷。但由于他有内在的德与识,当他面对权贵,丝毫不怯懦。譬如,孔子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应该是颜回与子路,二者皆穷困不已。对颜回,孔子欣赏地赞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然而,对于身处于极度市场化环境中的现代人而言,他的价值往往定义于其所占有的财富。而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若说他“身价数千万”的话,与其说是赞美他,倒不如说是在羞辱他。然而,当几乎无孔不入的现代市场逻辑侵入到现代教育领域中,越来越多的读书人开始以各种功利的外物来定义自己。这也便是现代教育目的的外在化的必然结果。手段沦为目的之逻辑势必招致读书人以——外在于内在人格的——条件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钱穆说,现代教育的病症之一是“学问与人生分成两橛”。[16]也即,现代教育一方面存在功利主义的趋势,另一方面便是对于内在人生修养的忽视。 从个人心理角度言之,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一个征象是,人们的价值观从有关于人生的内在德性(virtue)逐步让位于各种外在的条件(conditions),这势必造成现代人自身的条件化以及价值的相对化。曾经,做一个“耕读持家”的读书人是许多书香之家的家训之词。然而,近代以来,中国一直纠葛于外在的富强之梦,并且这种富强梦很大程度上牺牲了文化人曾经享有的基于德识的尊严。于是,当内在的修身之学被遗弃,而仅仅留下外在的功利之学的时候,读书人先是成为“国家的人”,再成为“市场的人”,却削弱了作为人生根本的人格尊严之自我。总之,古代自命“士志于道”的读书人会清贫而骄傲,而缺乏内在尊严感的现代读书人则往往因为穷困而深感某种罪错之羞耻。这是当代大学生遭遇诉贫伤害的社会心理学基础。 四、结构与自我的重构——化解“诉贫伤害”的思路 (一)均贫富——以伦理限制市场 充满风险的现代市场经济是造成贫富极度分化的重要原因。与现代风险社会(risk society)不同,古代社会设置上通过家族制、多样化生产、低市场化等措施尽可能减弱风险。这些措施也是实现古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理想的手段,而“均”又是重视“治”或“秩序”(order)而非“进步”(progress)的古代社会制度宗旨之必需。当然,需要说明,均不是机械平均,而是均衡,以免社会分化过大而导致“乱”。然而,当前,中国缘于市场的分化效应,以至于贫富差距悬殊。这是造成诸多贫困生的重要经济原因之一。基于上,宜以伦理适度限制过分的市场经济,尤其是严防教育文化等部门的过分市场化,是创造均衡的社会发展以及减少贫困生或贫困家庭的必要举措。 (二)折中家庭——加强家庭支持能力 中国大学生的贫困之实质是其家庭的贫困。而其家庭的贫困与当代家庭核心化所致的脆弱有关。折中家庭是传统大家庭与现代小家庭的中道地取舍的产物。一方面,传统大家族抗风险能力较高,但其抑制国家意识的产生,也抑制个人存在感。另一方面,现代核心家庭以其方便的流动性及其个人主义而适合于工业化、市场化经济之需,但是,家庭过于弱小,又势必造成面对国家与市场的个人之孤弱之境。基于此,潘光旦等学者提出“折中家庭”设想,“我们需要一种家制,左不至于抹杀个人,右不至于忘却社会,上对得住以往,有相当的留恋,下对得住未来,有充分的愿望。”[17]总之,较之于现代核心家庭,折中家庭具有相对较高的抗风险能力,也是化解大学生贫困问题的一个向度。 (三)救助在地化——将大学接济体系纳入地方民政 古今皆有救济,然而背后的心理机制不同。古代救济的心理根据是民胞物与之互为恩情,而现代社会救济则不过旨在使边缘人群不危害社会。现代社会一方面制造贫富差距;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又试图以救济掩饰其制度的内在的不平等的机制。另外,普世性现代救济的去地方化或抽象性也削弱了曾经的社区性互助体系的情谊基础。基于上,公益必须在地化(localization)。 公益的情感应基于人与人的同胞意识之互为恩情。在乡土化的中国,救助体系基本是由地方乡绅带头进行的基于差序格局情感基础上的义务感的社区里的抗风险系统。近代以来,缘于社区国家化⑤之故,社区公益功能日渐式微。另外,缘于市场化以及家庭核心化等故,现代社会的风险愈加强烈,势必造成许多弱势人群。现代社会的公益组织很大程度上就是以上述弱势群体为服务对象。但是,和传统救助的社区化相对,现代公益存在超社区特质,它所针对的是“公民”,而非熟人。再者,国家救助的抗风险体系也远离这些弱势人群。总之,现代救助——无论是国家的,还是社会上的——带有如下问题。第一,陌生化而可能存在信任危机;第二,距离远而运作成本高;第三,专门化或职业化;第四,陌生化所致的非需求导向,因为陌生化会加剧对弱势群体需求的认知难度,同时,职业化也会造成从业者自身的利益导向,及其所致的忽视社区需求的问题;其中,仅以其“陌生化”来看,它所导致的“诉贫”就可能成为对弱者的再度伤害。鉴于上,救助宜在地化:一方面,基层社区上报亟待救助的大学生指标;另一方面,上级政府将助学金下放到基层民政。例如,有人指出诉贫是“想让学生证明自己有多穷?那你干嘛不走其他途径?比如去村委、街道办开个家庭状况证明,何必让学生承受这种屈辱?”再由基层行政或社区针对贫困生的家庭进行救助。这将利于认知救助对象的贫困状况之实情,促进地方社区意识,同时也一定地减免了心灵敏感期的大学生的心理伤害。 (四)因材施教——扩大职业教育,让学生分流 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应该各就其位,各尽其职。传统儒家精英教育偏于道,而相对忽视器。这种取向在社会上造成的消极后果是,与应用有关的职业教育不为上流社会所重视。此外,最近二十来年,高校一路扩招,无节制的“普及大学教育”趋势造就出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大学生总量的增加,以及工厂化教育,一方面缘于这种不当的“普及”,⑥造成生源的水平逐年下降,而教育过程必须照顾“大多数”。结果不免是,尽管大学人数逐年增加,但水平每况愈下。基于上,笔者以为,理应因材施教,宜扩展职业教育。一方面,加强已有的职业院校,将许多不特别好的高校改为高职院校;另一方面,将来自于农村的成绩不特别优秀的学生分流到职教系统。毕竟,职业教育更加符合他们的智力水平,另外,职教读书年限较少,花钱较少,且挣钱早,这可以减少助学金的必要,也相应减少诉贫伤害。 (五)节俭读书——教育环境的去市场化 从Parsons的现代社会制度上看,社会与文化体系应该与讲究效率的经济系统分开,以便保证教育的相对超越性。然而,当代中国教育也被无限制地市场化,办教育与开工厂几乎没有什么本质差别。与此有关,市场化不仅根本上影响教育应该具有的相对超越价值,也造成学生生活环境的市场化甚至赤裸裸的金钱化。为改变上述情况,首先理当限制教育的市场化趋势,尤其该禁止校园的奢侈倾向,创办公益性的教育环境,争取让穷苦家庭的孩子也上得起学;其次,对于学生本人而言,主观上提倡节俭意识。毋庸讳言,即便是许多农村大学生身上也带有许多奢侈之风,这是亟待改观的。第三,勤工俭学。学校以及社会皆尽可能为大学生提供一些暂时性的力所能及的就业机会,以便使其减少家庭的负担,从而也减少需要救济的必要性。 (六)重塑精英价值——把“修身”带回高等教育的中心 古人治学内外兼修,并且认为作为内在素养培养的修身是一切德行与行为的前提条件。近代民族危机激发引发的教育现代化的后果之一是人格的政治化:良知之学让位于政治意识。近代以降的教育相对忽视了修身之学,这是人格教育之缺失。早在1948年社会学家孙本文便指出这种症状:“现代青年无不关心政治,而却往往忽视个人的行为;现代青年无不热心于运用政治手腕,而却不注意人与人之间的伦理法则。这是青年教育常被忽视的重要问题。”[18]而“国家的人”确实人自身当内在固有的修身之学,只会造成抽象的国族主义。而近来三十来年无限制的教育市场主义进一步造成青年人格的市场化。无论人格的政治化,还是市场化,都是内在人格的掏空,其结果难免是内在自我的缺失。上述缺失也与当代学生的人格危机及其所致的诸多困扰有关。 在上述情况下,宜超越狭隘的专业化、市场化的职业主义教育,应该在现代条件下重塑社会人才观。而现代人才务必在传统的君子不器的“文化人”与现代“专业人士”之间求得均衡,也即,现代人才必须是具有人文关怀的专业人士。为达到这一目的,除了坚持以往的理智化的教育之外,应该将内在人格教育的“修身”之学带回现代教育的中心。具体言之,宜从如下几方面着手。首先是,教育的人文化。其次是,教育过程的本土化。再次,重塑教师的道德感召。第四,加强反省教育。古人云,君子三省吾身。这在今天依然有其不可或缺的价值。第五,教育环境的去功利化以及去市场化,营造相对超越的教育环境。第六,将培育少数人的精英教育与大部分一般人的职业教育分开。 注释: ①“高校要求贫困学生公开‘述贫’被指二次伤害”,登录自中华网http://edu.china.com/new/edunews/jy/11076178/20151022/20606625.html。 ②传统社会都存在其特有的贵族,只不过其形式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对于中国而言,先秦是贵族时代。秦汉已还,随着封建社会的瓦解,基于血缘和土地的贵族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这并不表示中国从此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平等社会,因为,读书人或士大夫从此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他们凭借其身体化的文化资本成为社会的精神贵族。始于隋唐而终结于晚清的科举制是读书人精英化的制度保证。 ③“断裂”一词,指的是孙立平《断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一书中揭示的社会极度分化,尤其是许多弱势群体被抛出现代化发展的轨道的境况:“被甩出的人,甚至已经不在社会结构的底层,而是处在社会结构之外。” ④以上数据来自上海交大《2014年中国大学生消费行为与品牌认知调查报告》。 ⑤社区国家化与国家社会化,是近代以降中国国家权力集中化的表现之一,二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一方面,国家权力日益下降至乡镇乃至村或街道;另一方面,本该具有适度自治的基层越来越因为国家权力之触角的渗入而“他治化”。 ⑥大学教育必须“高等”。在古代,作为主流的儒家教育旨在培养“大人”或管理社会的精英,这必然是天赋较高的少数人的权益。而“普及”大学的必然结果是:高等教育的低等化。人性不齐,人的天资的类型及其程度都有很大差异。教育机会最主要应该决定于的人的天资。因此,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于高等教育。而普及的结果是,本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去接受日渐工厂化的大学教育,造成学生与高等教育的两不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