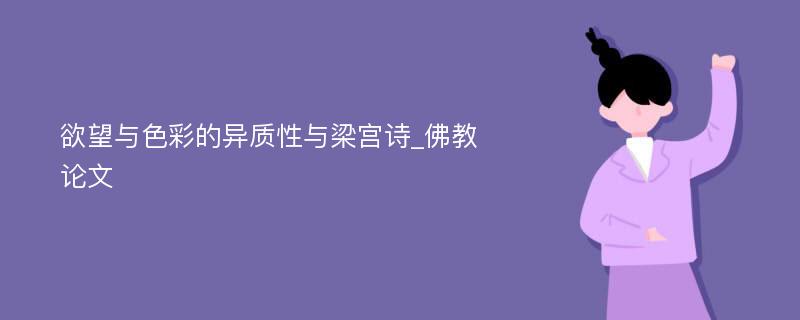
欲色异相与梁代宫体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相与论文,欲色异论文,梁代宫体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佛经中的欲色异相描写深深地影响了宫体诗,宫体诗的内容因此而与以往的言情之什有了很大的不同,这已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发现。就佛经与宫体诗的这层关系来讲,我深表赞同,并无异议。但是,在回答宫体诗的作者们为什么敢于这样大胆仿佛经而极写欲色这一问题时,论者似乎都把它归结于作者的低级趣味上,认为这种摹仿完全是为了满足他们作为腐朽、无聊文人的变态心理、感官刺激。而鼓起其创作胆量的又恰恰是“不晓空观,是作色观”[(1)]、“于五欲中生大不净想”[(2)]的经教所给予的权宜、方便。对这一解释,我则深感困惑,多所不解,窃以为有再进行讨论的必要。
首先要辨明的问题是,梁代君臣对现实中荒淫放荡的声色生活是持赞成还是否定的态度。
应该说,出于国家治乱的需要,历史上的多数开国之君对风俗教化是十分重视的。南朝诸帝也显然没有例外。宋武起自匹夫,“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未尝视珠玉舆马之饰,后庭无纨绮丝竹之音。”[(3)]即位之初,就曾下令惩治“赃污淫盗”,“伤化扰俗”者,冀“一皆荡涤”[(4)]之。齐高即位,其整齐风俗的措施也一如宋武,而自身节俭,甘于清苦。尝言:“使我临天下十年,当使黄金与土同价。”[(5)]欲以身率天下,移风易俗。然而,宋武建元不过三年,齐高建元不过四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二帝是不可能建立一国风俗规范而立奏其效的。另一方面,二帝于诸子“顾有慈颜,前无严训。”[(6)]使诸子养成了“所欲必从其志”[(7)]式的骄横。因是之故,诸子孙继统者非但不能生美教化、移风俗之意,反倒有心于行伤风败俗之事。上行下效,终于酿成了宋齐之世荒淫的世风,朝野上下演出的荒诞故事不绝于书。梁武帝享有天下达四十七年之久,相比之下,他就有更多的时间在宇内推行风化。虽然由于积重难返和措施不力等方面的原因,他未能十分有效地抑制和扭转荒淫、腐败的社会风气,但他不倦地推行风化的行为却有力地表明了他对现实的荒淫生活是持否定而不是赞成的态度。具体表现在:
一、梁武帝身经宋齐两世,对当时腐朽、荒淫的世风自是颇多感触,梁台未建时,作为朝廷重臣的他就对齐东昏朝的“骄艳竞爽,夸丽相高”表示了不满,下令“掖庭备御妾之数,大予绝郑、卫之音。”[(8)]梁台既建,他对宋齐之主的荒淫误国更是引以为教训。天监元年诏曰:“宋氏以来,并恣淫侈,倾宫之富,遂盈数千。推算五都,愁穷四海,并婴罹冤横,拘逼不一。抚弦命管,良家不被蠲;织室绣房,幽厄犹见役。弊国伤和,莫斯为甚。凡后宫乐府,西解暴室,诸如此例,一皆放遣,若衰老不能自存,官给廪食。”[(9)]此后不久,他又令改曾为皇家荒淫之所的华林园为弘法道场。陆云公《御讲波若经序》述其事云:“华林园者,盖江左以来后庭游宴之所也。自晋迄齐,年将二百,世属威夷,主多奢替。舞堂钟肆,等阿房之旧基;酒池肉林,同朝歌之故所。自至人御宇,屏弃声色,归倾宫之美女,共灵囿于庶人。重以华园毁折,悟一切之无常;宝台假合,资十力而方固。舍兹天苑,爰建道场。”这一系列措施,虽难有“草偃风从”之效,但却是他“在上化下”[(10)]的统治思想的认真贯彻。
二、梁武帝深知“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1)]的道理,故特别注意人君形象的树立。史称其“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五十外便断房室。后宫职司贵妃以下,六宫祎三翟之外,皆衣不曳地,傍无锦绮。不饮酒,不听音声,非宗庙祭祀,大会乡宴及诸法事,未尝作乐。”[(12)]可谓身体力行,为世作则。他不仅自己恭俭庄严,而且还严于庭训,善教诸子。昭明太子的“孝谨天至”、“不蓄声乐” [(13)],梁简文帝的“实有人君之懿”[(14)],及梁元帝的“性不好声色,颇有高名”[(15)],都显示了其庭训之效。而观简文帝《诫当阳公大心书》所言“立身之道”及梁元帝《金镂子》之立《箴戒》、《戒子》二篇,则知立身实已为萧梁家训。有梁一代人君中少荒淫之主,显然与其多得立身之教不无关系。
三、梁武帝的整齐风俗,除用上述措施外,还更多地倚仗佛教这一法宝。他早年在齐竟陵王萧子良门下时,就接受了以佛法化成民俗的思想。称帝之后,这一“遣方便之说,导化城之迷”[(16)]的思想也就自然地成为其王化方略。梁简文帝《大法颂序》就对此作了披露。“若夫眇梦华胥,怡然姑射,服齐宫于玄扈,想至治于汾阳,轻九鼎于褰裳,视万乘如脱屣,斯盖示至公之要道,未臻于出世也;至于藏金玉于川岫,弃琴瑟乎大壑,卑宫菲食,茨堂土阶,彤车非巧,鹿裘靡饰,此盖示物以俭,亦未阶于出世也;解网放禽,穿泉掩胔,起泣辜之泽,行扇暍之慈,推沟之念,有如不足,纳隍之心,无忘宿寤,盖所以示物以为仁,亦未阶乎出世也。”以佛法化俗,最重要的是以佛教的观点来思考、认识现实人生,把人们对现实利益的关心引向佛教宣传的彼岸和来世。在这一点上,萧子良之作《净住子》为梁武帝做出了榜样。《净住子》以佛教的观点猛烈批判、否定现实享受,就是想借此以医世,获齐家治国之利。梁武帝的《净业赋》即脱胎于此文,其文略云:
观人生之天性,抱妙气而清静,感外物以动欲,心攀缘而成眚。过恒发于外尘,累必由于前境,若空谷之应声,似游形之有影。怀贪心而不厌,纵内意而自骋,目随色而变易,眼逐貌而转移。观五色之玄黄,玩七宝之陆离,著华丽之窈窕,耽冶容之逶迤。在寝兴而不舍,亦日夜而忘疲。如英媒之在摘,若骏马之带羁,类白日之丽天,乃历年之不亏。观耳识之爱声,亦如飞鸟之归林,既流连于丝竹,亦繁会于五音。经昏明而不绝,历四时而相寻,或乱情而惑虑,或耳而堙心。至如香气馞起,触鼻发识,婉娩追随,氤氲无极,兰麝夹飞,如鸟二翼,若渴饮毒,如寒披棘。舌之嗜味,众尘无有,大苦咸酸,莫不甘口。食众生,虐及飞走,唯日不足。长夜饮酒,悖乱明行,罔虑幽谷。身之受触,以自安怡。美目清扬,巧笑蛾眉,细腰纤手,弱骨丰肌,附身芳洁,触体如脂,狂心迷惑,倒想自欺。至如意识攀缘,乱念无边,靡怀善想,皆起恶筌。如是六尘,同障善道,方紫夺朱,如风靡草,抱惑而生,与之偕老。随逐无明,莫非烦恼。轮回火宅,沈溺苦海,长夜执固,终不能改。迍否相随,灾异互起,内怀邪信,外纵淫祀,排虚枉命,蹠实横死。妄生神祐,以招福祉,前轮折轴,后车覆轨,殃国祸家,亡身绝祀。初不内讼,责躬反已。皇天无亲,唯与善人。
从中可以看出,梁武帝指出人们以眼、耳、鼻、舌、身、意“六识”追逐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为非,并把它上升到“殃国祸家,亡身绝祀”的高度来认识,这就极其鲜明地显示了其批判现实,借此以劝谕警世、淳化风俗的用心。从现存材料来看,梁武帝的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产生的影响是极大的,其臣下莫不禀承其意旨广为弘扬。《广弘明集》所载简文帝《六根忏文》、沈约《忏悔文》及梁君臣同作之《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就集中地体现了他们以佛教的观点对现实的声色生活作出的反省和思考。简文帝忏悔六根,冀“一切众罪悉灭”,“归之真域”,沈休文觉今生“罪业参差”,“庶罪无所托”,“永息来缘”,都表示了对现实享受的批判和否定态度,而《八关斋夜赋四城门》诗更是这一主题的大合唱。如《第四赋韵南城门老》云:“盛年歌吹日,顾步惜容仪。一朝衰朽至,星星白发垂。已伤万事尽,复念九门枝。垂轩意何在,独坐镜如斯。”
总上言之,出于巩固封建秩序的需要,萧梁君臣父子对荒淫的社会风气是表示了强烈的批判态度,并有了切实的整齐措施和行动。这就使我们很难想象,以移风易俗自任的上层统治者居然会出尔反尔地以文字形式去欣赏、赞成现实的声色生活;一面以佛教的观点否定现实享受,一面又超越佛教的观点去忘情地赏玩佛经中的女色及男女性爱描写,以助其在文字上的追情逐声之趣。作为封建最高阶层,又作为文章领袖,他们应该想象得到,专门倡导这样一种极写欲色的诗体对天下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其正在努力推行的风化又将要造成多大的危害。更何况,“不妄语绮言”[(17)]正是这帮菩萨弟子的严持之戒。如简文帝作《菩提树颂》,武帝就斥其“不无绮语过也。”[(18)]沈约更以此戒来反省己之文行。其《忏悔文》云:“性爱坟典,苟得忘廉取非。其有卷将二百,又绮语者众,源条繁广,假妄之愆,虽免大过,微触细犯,亦难备陈。”此文字细犯,究不过为华而不实,作巧佞之辩,而犹念念不忘以自责,那么,超越于宗教的目的而专事于描写欲色的污杂之语对他们来说就要视为更大的犯戒了。
二
然而,宫体诗“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19)]确实能给人一种“非好色者不能言”[(20)]的感觉。仅就宫体诗本身来讲,其为好色者之言似乎倒是让人置疑不得,但是,研究有关宫体诗的背景材料我们发现,事情其实并不如此之简单。
先从北齐颜之推所观察到的一种现象说起,这就是古乐府《三妇诗》内容在梁、陈时代的变更。《颜氏家训·书证篇》云:“古乐府歌词,先述三子,次及三妇,妇是对舅姑之称。其末章云:‘丈人且安坐,调弦遽央。’古者,子妇供事舅姑,旦夕在侧,与儿女无异,故有此言。丈人亦长老之目,今世俗犹呼其祖考为先亡丈人。……近代文士,颇作《三妇诗》,乃为匹敌并耦己之群妻之意,又加郑、卫之辞,大雅君子,何其谬乎?”卢文駋注曰:“宋南平王铄,始仿乐府之后六句作《三妇艳》诗,犹未甚猥亵也。梁昭明太子、沈约,俱有‘良人且高卧’之句。王筠、刘孝绰尚称‘丈人’,吴均则云‘佳人’,至陈后主乃有十一首之多,如‘小妇正横陈,含娇情未吐’之句,正颜氏所谓郑、卫之辞也。张正见亦然,皆大失本指。”其实,在梁代,古乐府的改作象《三妇诗》这样情形的还很多,实不止《三妇诗》一首。颜之推所指出的这一现象表明,梁代宫体别为新变,在内容上的确是与以往言情之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其特征正如陆时雍所指出的那样,“梁诗妖艳,声近于淫。倩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21)]梁代宫体内容上的这种别为新变,颜之推大为不满,指为郑、卫之辞,但宫体诗的倡导者梁简文帝萧纲对此却表示了不同的态度。其《答新渝侯和诗书》云:“垂示三首,风云吐于行间,珠玉生于字里,跨蹑曹左,含超潘陆。双鬓向光,风流已绝;九梁插花,步摇为古。高楼怀怨,结眉表色;长门下泣,破粉成痕。复有影里细腰,令与真类;镜中好面,还将画等。此皆性情卓绝,新致英奇。故知吹萧入秦,方识来凤之巧;鸣瑟向赵,始睹驻云之曲。手持口诵,喜荷交并也。”按文,新渝侯所为诗三首正是所谓“倩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者,其为宫体已自无疑,萧纲对它们却充满了赞赏之情。这说明宫体诗的倡导者并不认为宫体诗与诗教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是以泰然为之,泰然言之,而无不安之状。
说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以“倩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为特征的宫体诗究竟是凭什么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接受并提倡,得以在这个并不贱视风教的国度里盛行,以至于到了《南史》所说的“且变朝野”的地步?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不得不回到有关宫体诗的两条最重要的,也是最直接的背景材料上来。一为《梁书·梁简文纪》所载:
(帝)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
二是《梁书·徐摛传》所载:
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号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
根据这两段材料,宫体乃太子家令徐摛首创,后来则为太子为首的东宫文人所赞成、效法,于是名声渐起,梁武帝知此事大为震怒,召徐摛责让,只是由于徐摛的“应对明敏,辞义可观”,梁武帝才气平意释。这里需要追究的问题是,徐摛是以什么样的应对内容使盛怒之中的梁武帝气平意释的?很显然,对待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徐摛是不可能仅仅靠饰其华辩博取武帝欢心以塞责的,文中言其应对“辞义可观”,就表明他还是据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以此才平息了这场风波。然徐摛所持又是什么样的理由和依据呢?文中虽然没有透露,但是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萧纲在为晋安王时,梁武帝曾托周舍为其求友,条件是“文学俱长兼有行者”[(22)],而徐摛正是以此“而堪此选”[(23)]。徐摛既充其选,本应以良好的文行与太子游处,而他却“属文好为新变”[(24)],创为“轻艳”之宫体,使得包括太子萧纲在内的东宫文人递相仿习,务为妖艳。就梁武帝看来,徐摛所作所为自然是毁坏宫教,有伤风化,他之所以怒而召徐摛加以责备,盖即由于此。因此,徐摛应对内容就必须是说明他所创立的宫体为不妨害风化之体或者说正是关乎风化之体。只有让梁武帝理解他创为宫体的这一番用心并赞成他的做法,其愤怒才能平抑,徐之罪才能被开赦,而宫体诗此后也才能见容于天下而“且变朝野。”
但是,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又与其体现风化的意图有什么关系呢?换句话说,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又将要表现什么样的教化内容,达到什么样的风化目的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能从宫体诗摹仿佛经中的女色及男女性爱描写这一事实本身来求得答案。一般说来,佛经中极写女色与男女性爱,实际上并不是在有意表现什么,它只是要通过人间的欲色异相来体现“真如”(“空”),一方面告诫世人对女色作不净观,明白女人“譬如革囊盛屎,有何可贪”[(25)]的道理;一方面说明人间的爱欲欢乐既虚幻不实而又充满罪业和痛苦,希望人们登彼慈航,脱离苦海。其劝谕醒世、教化世俗的目的是相当明确的。所以,徐摛的宫体仿佛经而极写女色和男女性爱所要体现的教化内容及所要达到的教化目的,只可能是一如佛经而非其它。
上面我们曾提到,梁武帝针对腐朽荒淫的社会风气,企图以佛法来教化、整齐之。为此,他在意识形态领域亲自倡导了以佛教思想对现实荒淫的声色生活的批判和否定,群臣影响附和,造成极大的声势。这就表明,徐摛的这一做法并非出于偶然,他实际上是响应梁武帝以佛法化俗的号召,用诗歌的形式来为之鸣锣呐喊。徐摛所创宫体正是迎合了萧梁天子在政治上的这种需要,所以其先才被作为太子的萧纲接受并作大力提倡,其后也才为梁武帝理解和接受,任其在宇内风靡。
三
徐摛创为宫体既是为以佛法化俗,那么,宫体诗的实际是否真正体现了他的这一创作思想和意图了呢?下面我们来作一些具体的考察。
《广弘明集》卷第二十四《僧行篇》载有徐陵《谏仁山深法师罢道书》,其文略曰:
仰度仁者,心居魔境,为魔所迷,意附邪途,受邪易性。假使眉如细柳,何足关怀;颊似红桃,讵能长久?同衾分枕,犹有长信之悲;坐卧忘时,不免秋胡之怨。洛川神女,尚复不惑东阿,世上班姬,何关君事?夫心者面焉,若论缱绻,则共气共心,一遇缠绵,则连宵厌起。法师未通返照,安悟卖花?未得他心,那知彼意?呜呼!桂树遂为豆火所焚,可惜明珠乃受於泥埋没。
在这段材料里我们可看到,徐陵为谏仁山深法师罢道,其所用譬喻并不取自经载异相,而是取用史传故事和文学作品。“同衾分枕”句用汉成帝班婕妤事,“坐卧时”句用春秋鲁大夫秋胡事,而“洛川神女”句则用曹植《洛神赋》事。这一情况表明,古老的情爱题材这时实际上已化为了弘教者借以说法的人间异相,用它们可以说明“眉如细柳”的不足关怀,“颊似红桃”的不能长久,男女性爱的恨别离苦。值得注意的是,秋胡、班婕妤之类史传故事在当时社会广为流传,并不是得之于历史知识的人力普及,而是好事文人热衷于摹仿前代咏史乐府的结果。所以,徐陵用以说法的这些异相,很大程度上已不能说就是取自史传故事和旧有的文学作品,而应该是俯拾流咏于文人笔端的咏史乐府。作为宫体诗人的徐陵象这样做,就说明文人仿乐府一度也曾演欲色异相以说法,寓有劝谕醒世的目的在内。至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我们在上文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就是象古乐府的《三妇诗》那样的言情之什,为什么到了梁代的内容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趋于妖艳、淫靡,女主人公形象都是“倩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以前,我们似乎都把原因简单地归于文人因情感的贫乏、病态而导致的摹仿失败,这显然是不准确的。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佛经中演欲色异相,以说法的做法启发了佞佛之文人,因此文人们在化俗目的的驱使下也就易于产生取前代史籍中、古乐府中较有影响的情爱题材以为异相而仿佛经以极演之的想法。很显然,改作中的欲色描写愈类于佛经,它就愈利于体现它“背后的意义”[(26)]。据此,可以这样说,梁代改作乐府的这种情况与其说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失败的摹仿,倒不如说是出于以佛法化俗目的的一种强彼以就我的行为。
那么,在具体的一首诗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到其仿佛极演欲色异相以说法的创作目的呢?试看《玉台新咏》中的三首诗。先说卷八汤僧济《咏渫井得金钩》诗。
昔日倡家女,摘花露井边。摘花还自插,照井还有怜。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宝钩于此落,从来不忆年。翠羽成泥去,金色尚如先。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传。
所谓咏渫井得金钩,并不是作者真正的作意所在,它只是要通过一个事件的追想,一个女人华颜消歇的命运思考,来表现“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传”的人生无常,说明尘世中人们实无法摆脱与生俱来的生老病死之苦。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还可以发现,僧济此诗无论立意还是作法,都是以《佛所行赞·离俗品第四》中众采女对太子的色诱及太子的攻破为蓝本。“太子在园林,围绕亦如是。或为整衣服,或为洗手足;或以香涂身,或以华严饰;或为贯璎珞,或为安枕席;或倾身密语,或世俗调戏;或说众欲事,或作诸俗形,规以动其心。菩萨心清净,坚固难可转。闻诸采女说,不忧亦不喜,倍生厌思惟,叹此为奇怪。始知诸女人,欲心盛如是。不知少壮色,俄顷老坏死。哀哉此大惑,愚痴覆其心。尝思老病死,昼夜动勖励,锋刀临其颈,如何犹嬉笑?见他老病死,不知自观察,是则泥本人。”僧济诗中的那一个“窥窥终不罢,笑笑自成妍”的女性形象,实际上就是经中“锋刀临其颈,如何犹嬉笑”的众采女形象,而他“此人今不在,此物今空传”的人生无常之叹,也显然是从经中的“不知少壮色,俄顷老坏死”化出。再说卷六王僧孺《为人述梦诗》:
已知想成梦,未信梦如此。皎皎无片非,的的一皆是。以亲芙蓉褥,方开合欢被。雅步极嫣妍,含辞恣委靡。如言非倏忽,不意成俄尔。及悟尽空无,方知悉虚诡。
此诗仿佛经极演欲异相以说法的意图与前诗是同样的明显,而表达之直接则过之。《维摩诘所说经》云:“是身如梦,为虚妄见。”僧肇注曰:“梦中妄见,觉后非真。”[(27)]看得出,王僧孺诗整个就是一个“是身如梦”之喻。其极写梦中女子的柔情绰态,用心根本不在于骄淫,而是用此为异相以说空无,以此达到对现实欲色的否定。最后说卷十王金珠(一作梁武帝)的《欢闻歌》其一:
艳艳金楼女,心如玉池莲。持底报郎恩,俱期游梵天。
梵天,今人似均解作寺庙,谓与欢幽会、交欢之所,此实大谬。按,诗云“心如玉池莲”即是说此女心性清净,不为六尘所染。梁武帝《净业赋》即持此以喻心性之清净,文云:“外清眼境,内净心尘,不与不取,不爱不嗔。如玉有润,如松有筠,如芙蓉之在池,若芳兰之在春。淤泥不能污其体,重昏不能覆其真。雾露集而珠流,光风动而生芬。”如此,则梵天不得解为寺庙甚明。梵天乃色界之初禅天,此天离俗界之淫欲,寂静清净,故名梵天。欲界在梵天之下。“男娶女嫁,身行阴阳,一同人间”[(28)]。诗云“俱期游梵天”,其义则如王少卿所谓“方欲除五累,长辞三雅卮”(《八关斋夜赋四城门更作四首》),梁简文帝所谓“愿能同四忍,长当出九居”(《望同泰寺浮图诗》),王训所谓“愿托牢舟友,长免爱河深”(《奉和梁简文帝望同泰寺浮图诗》),实际上是表达了佛徒希冀超脱人间欲界苦海而入清净梵天的美好愿望,包含了对尘世淫欲、情爱生活的彻底否定。又考佛典,知此诗之立意和作法原也是有其所本的,这就更加证明此诗之写异相乃不为极欲宣淫。《法句譬喻经》卷二述“五百婆罗门女闻法开悟”异相云:“舍卫国东南海中有台,上有华香,树木清净。有婆罗门女五百人奉事异道,意甚精进,不知有佛。时诸女自相谓曰:‘我等禀形生为女人,从少至老,为三事所监,不得自由,命又短促,形如幻化,当复死亡。不如共至香华台上,采取花香,精进持斋,降屈梵天,当从求愿;愿生梵天,长寿不死,又得自在,无有监异,离诸罪怼,无复忧患。’即赍供具,往至台上,采取花香,奉事梵天,一心持斋,愿屈尊神。佛见其心应可化度,即与大众飞升虚空,往至台上,坐于树下。诸女欢喜,谓是梵天,自相庆慰,得我所愿矣。时一天人语诸女言:‘此非梵天,是三界最尊,号名为佛,度人无量。’诸女白佛言:‘我等多垢,今为女人,求离监检,愿生梵天。’佛言:‘诸女善利,乃发此愿。世有二事,其报明审:为善受福,为恶受殃,世间之苦,天上之乐;有为之烦,无为之寂,谁能选择,求其真者。善哉诸女,乃有明志。’”通过对以上三首诗的实际考察我们不难发现,宫体诗极演欲色异相以说法的创作目的在作家们的创作中确实是得到了体现,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它们的确是寄寓了仿佛经极演欲色异相以说法、化俗的深刻用心。宫体诗正是以有助于风化的这一实际功用,大体就是徐摛的辩解,而为萧梁父子所承认与接受。
四
以上的论述确立了我们对宫体诗极写欲色异相以说法的基本看法,但在实际的解读过程中,大量的宫体诗却使我们有难以印证其创作目的的感觉,原因主要是这大量的宫体诗仿佛只留意于欲色的极力铺写而无任何明显的攻破之言。所以,找出解读这大量的宫体诗的关键所在,使我们的结论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就显得大为必要。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曾经指出,梁代宫体别为新变,在内容上与以往言情之什有了很大的不同,用陆时雍的话来说就是,“梁诗妖艳,声近于淫。倩妆艳抹,巧笑娇啼,举止向人卖致。”陆时雍的概括可以说是抓住了梁代宫体欲色描写最为重要的一方面,这就是极力铺写女性的淫欲恣态,但究宫体诗的实际,陆氏的概括也还稍嫌不完整。事实上,宫体诗除了着力描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外,还特别留心于女性妒性的表现。所以,宫体诗在内容上总的特征就应该是极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下面我们进行一些具体的考察。
宫体诗写女性的淫欲姿态和妒性,通常是采用两种方式,一是概括描写,直接在字面上提起。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如梁简文帝《夜听妓诗》云:“留宾惜残弄、负态动余娇。”《美女篇》云:“密态随流脸,娇歌逐软声。”《娈童诗》云:“足使燕姬妒,弥令郑女嗟。”《咏舞诗》云:“逐节工新舞,娇态似凌虚。”《春闺情诗又三韵》云:“珠帘向暮下,妖姿不可追。”武陵王萧纪《同萧长史看妓》云:“回羞出曼脸,送态入嚬蛾。”萧子范《罗敷行》云:“城南日半上,微步弄妖姿。”萧绎《半路溪》云:“先将动旧情,恐君疑妾妒。”江洪《咏舞女》云:“发袖已成态,动足复含姿。”刘令娴《和婕妤怨诗》云:“只言争分理,非妒舞腰轻。”沈满愿《戏萧娘诗》云:“因风时暂举,想像见芳姿。”何逊《离夜听琴诗》云:“美人多怨态,亦复惨长眉。”王训《应令咏舞诗》云:“笑态千金动,衣香十里传。”吴均《三妇怨诗》云:“小妇多姿态,含笑逼清卮。”刘遵《应令咏舞诗》云:“举腕嫌衫重,回腰觉态妍。”刘缓《敬酬刘长史咏名士悦倾城诗》云:“夜夜言娇尽,日日态还新。”二是展开描写,这一方式主要用于表现女性的淫欲作态,并不作字面上的强调。如邓铿的《奉和夜听妓声》,整个就是在写女人以语言音声作态。“烛华似明月,鬟影胜飞桥。妓儿齐郑舞,争妍学楚腰。新歌自作曲,旧瑟不须调。众中俱不笑,座上莫相撩。”刘孝威的《南苑还看人》也整个在写女人的以形貌自矜之态。“春花竞玉颜,俱折复俱攀。细腰宜窄衣,长钩巧挟鬟。洛桥初度烛,青门欲上关。中人应有望,上客莫前还。”而邵陵王纶《车中见美人》中的“关情出眉眼,软媚著腰肢。语笑能娇美,行步绝逶迤”之句,则是写女人以其威仪作态。梁简文帝《美人晨妆》中的“散黛随眉广,胭脂逐脸生”句,则是写女人以其色相弄姿。其《咏内人昼眠》中的“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之句,则是写女人以其睡态慵媚、肌肤细嫩而呈欲态。
对宫体诗内容上的总体特征有了这样具体而实际的把握,事实上也就找到了解读宫体诗的关键所在;进而我们也就可以在此基础上印证其创作目的了。
考察佛经我们发现,宫体诗集中体现的女性的淫欲作态和妒性,其实正是佛教所赋予的女子丑恶天性的两个最主要的方面,很多经书都对此提出谴责和批判。《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云:“有阿罗汉,以天眼彻视,见女人堕地狱中者众多,便问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缘故。一者贪珍宝物衣被欲得多故;二者相嫉妒;三者多口舌;四者作姿态淫多。以是故堕地狱中多耳。’”《佛说七女经》云:“女人所以堕泥犁中多者何?但坐嫉妒姿态多故。”《佛说长者法志妻经》云:“亿世时有所堕女人身中者何?淫欲姿态在于其中,不能修身,放心姿意,嫉妒多口,贪于形貌而自恃怙。”《六度集经》卷第六云:“弥勒为女人身经:女情专淫,心怀嫉妒。”相比较而言,经书中对女子淫欲作态的批判揭露要比其妒性为甚,其表现可以说是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佛说义足经》卷上《摩因提女经》第九云:“女见佛形状端正无比,以三十二相,璎珞其身,如明月珠,便淫意系著佛,佛知其意如燃。”《五分律》卷第四云:“是日诸比丘尼竟夜说法,疲极还房,仰卧熟眠,于是婆罗门从床下出,作不净行,此比丘尼即踊升虚空。时婆罗门便于床上生入地狱,莲花色因从空中往诣佛所,头面礼足,以是白佛。佛问:‘汝当尔时,意为云何?’答言:‘如烧铁烁身。’佛言:‘如此无罪。’”《大智度论》卷四云:“阿难端正清净如好明镜,老少好丑容貌颜状,皆于身中现,其身明净,女人见之,欲心即动。”
很显然,宫体诗着意展示女子的淫欲作态和妒行,并不说明这个时代独多淫妒之妇,文人愤而以诗疾之,所说明的只能是接受了佛教妇女淫妒观念的文人自出于弘法化俗的目的较之前代更刻意地关注和研究现实中女子的淫欲作态和妒行,以诗的形式对之进行揭露和宣传。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妇女的淫欲作态和妒行其实是当时社会普遍注意和研究的焦点问题。关于女子的淫欲作态,由于它是“牵人入罪门”的“惑人之具”[(29)],妨害治化的主要因素,故当时推行佛化时是作为中心问题提出来的。文人们一旦述及佛化,无不以其为言论轴心。从上引梁武帝《净业赋》、梁简文帝《六根忏文》、沈约《忏悔文》中我们即可见其情形之一斑。至于女子的妒行,也被提到破家弃产、杀亲害子的高度来认识。由梁武帝《慈悲道场忏法传》叙郗皇后自述其“以生存嫉妒六宫,其性惨毒。”沈约《俗说》之有“车武子妇大妒”、“荀介子妇大妒”[(30)]之类的专文以及张缵专为《妒妇赋》,我们就能感受到此问题在当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尤其是张缵的《妒妇赋》,可以说是以佛教的观点来观照和批判现实中女子妒性的代表,集中反映了统治者在推行佛化的过程中对此问题的高度注意。“惟妇怨之无极,羌于何而弗有。或造端而构末,皆莠言之在口。常因情以起恨,每传声而妄受。乍隔帐而窥屏,或觇窗而瞰牖。若夫室怒小憾,反目私言,不忍细忿,皆成大冤。闺房之所隐私,床第之所讨论,咸一朝之发泄,满四海之嚣喧。忽有逆其妒鳞,犯其忌制,赴汤蹈火,摛目攘袂,或弃产而焚家,或投女而害婿。”如此看来,宫体诗刻意展示女性的淫欲作态和妒行就不是一种偶然,而是对萧梁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以佛教的观点揭露和批判现实中女性的淫欲作态和妒性的密切配合,其创作目的是相当明确的。
然而仅就诗本身来讲,其铺写女性的淫欲作态和妒性似乎并不如佛经那样表示了相当鲜明的攻破态度,这一点曾使我们以前的读解走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认为宫体诗人完全是出于病态的心理在欣赏和玩味女人的淫欲作态与妒性,给以其方便的正是佛教“于五欲中生大不净想”、“不晓空观,是作色观”的观法。这一读解看似合理实则大谬。此观法作为修炼方法之一,虽提倡于五欲中修不净想,但强调的却是修不净想以“制服贪欲”[(31)],并不是教人恋迷于不净而不返。如此,它怎么能给宫体诗人欣赏和玩味女人的淫欲作态与妒性提供方便呢?事实上,只要我们对佛经的欲色描写有一定的了解,对宫体诗的这一情形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在佛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攻破所谓女人丑恶的天性并不停留在几句空洞、枯燥的说教上,围绕其攻破之辞,都有那么一段极铺张的、“简直要搅乱我们的羞耻感”[(32)]的欲色描绘。如《方广大庄严经》卷第九《降魔品》叙述到波旬魔女以淫欲迷惑佛陀时,就一气描绘了她们的三十二种“绮言妖姿”,她们或“涂香芬烈”,或“媚眼斜眄”,或“露髀膝”,或“现胸臆”,乃至“递相拈掐”,以“恩爱戏笑、眠寝之事,而示欲相”。上举《佛所行·离俗品第四》中写众采女对太子的色诱也曾让我们见识过这样的情景。象这样铺张的欲色描写,也难免不给我们以作者是在欣赏和玩味欲色的感觉,但究其实际却不容我们作如是观。佛经之所以要极欲色描写之能事,主要是佛教认为女人美之所在,就是欲之所居,而欲又能导致诸种人世罪恶的产生,从这点上来讲,女人美之所在又是众恶之所居。因此,为了充分展示女人的丑恶,就得要不遗余力地体味女性的客观美。所以,宫体诗的大肆铺写欲色从根本上来说是承袭了佛经的这种极写之、力破之的写法,至于为何不见其攻破之辞,这可能一方面是由于这攻破之辞是当时人人心中都明白的常识、口号,另一方面是由于宫体诗的女色及男女性爱描写诗人们本来就把它视为可体现真如的欲色异相,故无须再在诗中提出。也许正是这一点,它给人们带来的误会也深,给后来文学创作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大,这大概是创为宫体的徐摛始料不及的。
注释:
(1)《经律异相》卷第十九《比丘失志心生惑乱十七》。
(2)《自在王菩萨经》卷下。
(3)(4)《南史·宋本纪上》。
(5)《南史·齐本纪上》。
(6)(7)《南史·宋本纪上》。
(8)(9)(10)(11)(12)《南史·梁本纪上》。
(13)《梁书·昭明太子传》。
(14)《梁书·梁简文纪》。
(15)《梁书·梁元帝纪》。
(16)《大法颂序》。
(17)《智度论》十三。
(18)《答菩提树颂手敕》。
(19)《隋书·经籍志》。
(20)《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梁元帝集题辞》。
(21)《诗镜》卷十七。
(22)(23)(24)《梁书·徐摛传》。
(25)《法句譬喻经》卷第四。
(26)黑格尔《美学》第二卷57页。
(27)《注维摩诘所说经》。
(28)《经律异相》卷第一《三界诸天一》。
(29)萧子良《净住子净行法·在家从恶门》第十。
(30)《玉函山房辑佚书》第八函卷七十五。
(31)《成实论》卷第十四《不净想品》。
(32)黑格尔《美学》第二卷5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