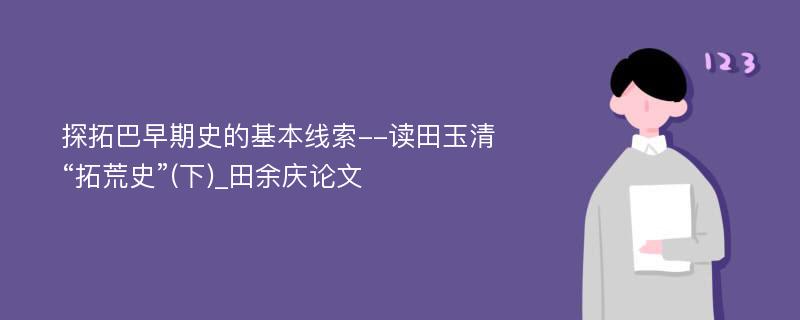
探讨拓跋早期历史的基本线索——田余庆先生《拓跋史探》一书读后(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拓跋论文,之二论文,一书论文,线索论文,读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也正是在这样的起点上,我们才可以把献帝以来君位传承之际的种种波澜和事件,放到传子制的建立亦即专制君权逐渐形成的过程中来加以认识和评价;(注:如神元帝末年之事变而身死,如果仅仅归因于西晋护乌桓校尉卫雚借附于拓跋部之汉人卫操和乌桓王库贤而施离间之计,那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晋人用间的得逞,是以拓跋君长和各部大人本已围绕传子制而尖锐矛盾为其前提的。)才可以较为完整地解读《序纪》所载献帝以来的有关世事,包括那个著名的“天女传说”;因而也才可以拉出献帝以来君位传承从推举制转为传子制,经重重波澜至章帝以来进入父子相继在兄弟相及中曲折发展的阶段,再到昭成帝以来传子制方渐稳定而并未巩固的完整线索;并使从属于此的各种头绪,包括母、后之族介入和影响君位传承过程的头绪在内,真正与“拓跋部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主线索”紧密地啮合到一起。
二是结构问题。在考虑拓跋部专制皇权逐渐形成和族际关系不断融合这两大主题时,后族问题和乌桓问题,确是相互关联而极具影响的重大因素,这也正是田先生此番研究洞察幽微之所在。那么这些因素是处于一个怎样的结构中,又怎样来评价其作用和地位呢?
据《魏书·序纪》和《官氏志》所载,献帝“七分国人,使诸兄弟各摄领之”而传子诘汾,以帝室拓跋氏为首的部落联盟,不仅形成了七加一(稍又扩展为九加一)部的核心或中坚,形成了七部和九部共奉拓跋氏子孙为其君长的格局,而且也明显地变革了各部原来的大人推举和统领体制,这无疑是拓跋部为首的部落联盟结构的一次重大转折。(注: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1962年版)内篇第一《宗族十姓》以为八姓之纥骨氏、十姓之乙旃氏皆属高车之部落。此或献帝任檀石槐联盟之“西部大人”前后依附拓跋氏之部,从而透露了献帝“七分国人”之前,以拓跋氏为首的联盟构成之况。因而献帝以兄摄领纥骨氏,以叔父之胤摄邻乙旃氏,自必改变了这两个高车部落原来的大人推举制,同时也表明“七分国人”之举,确为各部融入“国姓”,联盟进一步巩固的过程。)在此基础上,神元帝以来先后聚散于这个联盟,或发生过一定附属关系的“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又分别构成了联盟的一般或外围成员。(注:马长寿先生《乌桓与鲜卑》第四章《拓跋鲜卑》二《拓跋部和以拓跋部为中心的部落联盟之形成》,兼采姚薇元先生《北朝胡姓考》的有关研究,述神元帝时七十五个内入诸姓族源可考者三十一,属匈奴者六,属丁零包括高车者六,属柔然者三,属乌桓及东部鲜卑者九,属其余东西各族姓氏者七。这反映了拓跋部为首的联盟在族属上的一种更为具体的构成状态。)这样一个构成状况,直接就是道武帝建国以前拓跋部族际关系的基本结构。而当时情势下,既然是族际关系的基本结构,也就不能不是决定各重大事件和政治过程的基本结构。故神元帝后不久,其相关内容已被时人概括为“旧人”和“新人”之间的关连。(注:见《魏书·穆帝长子六修传》及《卫操传》附《卫雄传》。《资治通鉴》卷八九《晋纪十一》孝愍帝建兴四年述六修事胡注云:“旧人,索头部人也;新人,晋人及乌桓人也。”盖从《卫雄传》概括而来。)所谓“旧人”亦称“国人”,指拓跋部人,献帝以来自然是指宗室十姓成员,而“新人”则指“乌桓”和“晋人”。由于“乌桓”在当时也是来附“诸方杂人”非鲜卑者的泛称,故旧人与新人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宗室十姓与来附各部和汉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把帝室拓跋氏单列为一极,也就有了拓跋君长与宗室九姓大人以及来附各部大人和汉人豪宗之间的关系。(注:《魏书·官氏志》述内入诸姓乃“神元皇帝时,余部诸姓内入者”,四方诸姓则“岁时朝贡,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与《序纪》所载相参,内人诸姓有可能只是神元帝盛乐祭天大会的参与者,四方诸姓则是自来与拓跋部发生某种附从关系者。但以神元帝以来史实而论,前者常有叛散疏离者,后者亦有关系紧密者,故两者界限恐非甚明,盖有所区别而未可截分为较早或较晚融入两大势力。)应当说,这就是主导和牵制着神元以来至道武前后专制皇权逐渐形成和族际关系不断融合的基本结构。
为什么说其主导和牵制了族际关系的融合过程呢?前面指出,魏晋以来北方地区民族关系从趋异走向趋同的过程,是与一个新的强势中心的形成,因而也是与专制君主秩序的形成和巩固相辅相成的。在当时,拓跋部族际关系走向融合的过程,与拓跋为首的联盟走向专制国家的过程,实际上是交集在拓跋君长与宗室九姓及内入诸姓、四方诸姓和汉人豪宗的关系上了。故其各族融合的最终进程也就可以一言以蔽之:是匈奴余部或高车之部也好,广义或狭义的乌桓之部也好,是东部鲜卑如宇文氏或慕容氏也好,都先后并入了拓跋部治下,又终于成为了其所建专制秩序和封建国家的臣民。由此再看乌桓各部与拓跋的融合过程,那么很清楚,作为泛称的“乌桓”,其中相当一部分,如田先生此番研究所明确的,在屠各匈奴趋异过程中衍来的铁弗乌桓和独孤乌桓,其种族文化背景与拓跋部的差异相对较大,故须晚至道武帝建国称帝后方得兼并和完全融入拓跋部治下。而作为部族专称的乌桓,范晔《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和《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注引王沈《魏书》既已述其言语习俗与鲜卑同,则其与拓跋部的融合过程也就与东部鲜卑一样,主导因素并不是种族文化问题而是政治关系问题。当然无论是广义还是狭义的乌桓,其与拓跋部之间,一在农耕化或汉化过程中部落组织越益松散乃至于消弭,一则在农耕化过程中逐渐建立了适应于此的专制秩序而组织越益强固;其间共生互补乃至于融合的基础,也正是走向专制的权力中心与走向定居的小农经济之间的关系。
现在再把传子制所浓缩的专制君主秩序的建立过程放到这个结构中来观察,则各种势力的可能角色、反应和作用、地位实已大体可知。首先,《官氏志》载“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而拓跋旧俗,君长必祭天而登位。就是说,在拓跋部的传统中,有权推举或被推举为君长的,只是宗室十姓成员尤其是八姓成员(因为另二姓本非兄弟,一为叔父之胤,一为“疏属”)。因而相对于他族各部,宗室十姓无疑是拓跋君长最强固的支持力量:而在宗室十姓内部,他们又是变革种种传统包括废止推举而建立传子制的最大阻力。其次,内入诸姓及四方诸姓时附时散,其态随联盟之况变动不居,《官氏志》谓为“兴衰存灭,间有之矣”。但大体说来,在建立传子制和从部落酋长向专制君主的发展过程中,当君长与宗室九姓矛盾尖锐时,自须拉拢和亲信内入诸姓或四方诸姓大人;(注:《序纪》载神元帝晚年之变,乌丸王库贤“亲近任势”,在庭中磨砺斧钺谓诸部大人“上欲尽收诸大人之子杀之”,俨然以刽子手自任。便反映了作为内入诸姓的乌桓诸部在当时颇受神元亲信的事实。)倘其势转强危及君权,自然又须依靠宗室来限制或打击他们;而若宗室九姓与之矛盾突出时,君长亦可左右逢源:其间种种攻守平衡纵横捭阖,皆在情理之中。(注:“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从》所收《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一文,已经勾勒了旧人和新人与君长利益的这种关系格局,田先生在“共生关系”一文中,更以相当篇幅勾勒了新、旧分野及其逐渐走向融合的过程。但两位先生都未详论其要,特别是他们对新人和旧人的界定,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第三,《官氏志》载宗室“十姓百世不通婚”,故而后族倘非汉人,就是内附诸姓或四方诸姓成员,而其中非鲜卑者皆可泛称“乌桓”。即此已见,母、后之族在传子制和专制君权建立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新人”、或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利益的体现者。所不同的,只是其依附君权的一面尤其突出,君权强大时母、后之族常因此而强,及其过强威胁到君权而须削弱时,又多一重亲情血缘的牵扯罢了。
也正是这个早期拓跋史中客观存在着的,以拓跋君长为一极,宗室七姓或九姓贵族为一极,内入诸姓和四方诸姓贵族为一极,或者再加上依附拓跋的汉人豪宗为另一极的关系结构,不仅可以帮助解读《序纪》所载早期拓跋史的种种问题,也可以帮助恰如其分地认识母后之族或乌桓各部在早期拓跋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正是这个结构,直接在专制君权建立和族群关系融合的总格局上,决定了子贵母死、离散部落、史官命运,以及其他种种早期拓跋史和北魏史重大事件和制度的基本背景。
三是《序纪》解读问题。揭示《序纪》的史源为拓跋早期的叙事歌谣,及其编撰为《国记》的脉络线索,从而使这份珍贵史料价值愈显,求索有门,这正是田先生此番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国记》来源的真实,显然并不等于其所记内容的真实,“国史之狱”更为之遮上了重重迷雾。那么我们又当如何解读《序纪》的有关记载并辨识其可靠与否呢?
我们知道,《序纪》记载的主要内容和发展线索有三:一是拓跋族源及迁徙事项,这当然是各族口述史歌谣共同的重要话题。二是部落的聚散盛衰及其与魏晋的关系,其很明显是在维护道武帝凝聚部众和“图南”大业的政治资源。三是拓跋早期帝系,包括君位传承之次(君统)及其前君与后君的世系关系(宗统),这一部分比重最大,并且是《序纪》当之无愧的主干和轴心。详观《序纪》的叙事体例、内容安排、笔法详略等项,其绝大部分行文,都是在依据道武帝登位后“追尊成帝以下及后号谥”的精神而梳理历史,以明确献帝以来拓跋君位传子制的发展历程(注:《序纪》记成帝以下君位传承惟书“崩、立”二字,记献帝传子圣武帝诘汾后方有世系关系,意寓此前乃部落推举制时期,此后才是传子制辅以兄终弟及的发展期,故其君长方有父子兄弟世系之可言。继而《序纪》记圣武帝事惟天女传说一事,旨在说明神元之“神”及传子为天意。其记神元帝事除德化服众、盛乐祭天大会并与曹魏和亲外,大半篇幅皆述其欲传位长子文帝沙漠汗而事变身死之波折,以为此后神元子章帝、平帝、昭帝、文帝子思帝、桓帝、穆帝交叉登位的传子制发展期张本。),尤其是理出道武帝所承神元帝、文帝、思帝、平文帝、烈帝和昭成帝、献明帝父子七人五帝相承之脉(注:《序纪》记桓、穆帝事以其与西晋的关系为中心,是因为这种关系极大促进了拓跋部的发展,又构成了道武南向争统的一宗重要资源,也是因为桓、穆与思帝皆文帝之子的缘故。继而《序纪》记事仍围绕文帝三子思、桓、穆帝后代的帝位之争展开,穆帝身后,先是桓帝子普根及普根幼子在位,然后思帝子平文帝登位,接着普根弟惠、炀帝兄弟相及。再到平文长子烈帝翳槐争位成功,传位其弟昭成帝什翼犍,是为献明帝之父,道武帝之祖,这才成就了道武帝所承神元帝、文帝、思帝、平文帝、烈帝和昭成帝、献明帝父子七人五帝相承之脉,而烈帝实为拓跋君位传承稳定到平文帝一脉的关键或枢纽。),从而凸显神元以来君位传承之次以父系直系关系为其内轴的事实,建立起旨在巩固传子制秩序的君统服从宗统的原则。
但也正因为如此,就更要对《序纪》内容的可靠性提出疑问了。人们会问:即便从《国记》到《序纪》未有波折,这难道就是准确可靠的史实吗?且不说南北史籍载道武帝身世的出入和史界的怀疑,也不说婚姻关系的复杂使早期拓跋的父子兄弟关系含混不清,随便从流传至今的各族史诗中拿一部来看,君长世系部分占的比重都不是太大啊!显然,这里面的删繁就简,取舍选择,讲究大了。再者,道武帝于开国之际撰修《国纪》,难道真是在戎马倥偬中忽发奇想,要想留下本族早期的一份实录信史,而不是因为有其迫切需要总结历史开辟未来,不是想要通过历史来巩固自己及其子孙“世为帝王”的地位?事情很清楚,就现有条件而言,除个别点上的是非外,要总体地说《序纪》准确度高可信性大,或者总体地反对这种判断,最终仍需要从《魏书》所载道武帝开国规模的一系列举措入手,来弄清《国纪》编撰的用意和原则,寻找《序记》所示基本内容的佐证或反证,从而得以相对跳出太武帝以来北魏国史系统的种种纠葛来做出判断。
在这篇书评中,当然是完成不了这个任务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序纪》所示基本内容的佐证,的确是大量存在着的。即就天兴年间所建庙制而言,田先生此番研究早期拓跋君位传承过程时,就已经涉及了庙制问题并作了深刻论断。(注:如“子贵母死”一文二《拓跋部早期君位传承中后妃的作用》谈到天兴二年宫中“五帝庙之立,从庙制上确立了拓跋大宗的地位,排除了兄终弟及的传承秩序。”然田先生于此条脚注曰:“《魏书·太祖纪》同年同月载此事,缺思帝一庙,当为史文之漏。”显然是忽略了《太祖纪》所载乃为“太庙”之制,其与宫中五帝庙本是两套并列的制度。)循田先生的提示加以考察,便可以发现《魏书·礼志一》载天兴二年所建整套宗庙祭祖之制,正好展现了道武帝对自己所承拓跋氏帝系的四种考虑。其一是太庙四庙,是为始祖神元帝、太祖平文帝、高祖昭成帝和皇考献明帝庙。(注:田先生“共生关系”一文五《东木根山地名的来历》有一条脚注说到道武帝尊平文帝为太祖时,以为“孝文帝改尊道武帝为太祖,而以平文帝为烈祖。”误。因为《魏书·礼志一》载孝文帝太和十五年四月尊道武为太祖诏,明明称平文为“远祖”,故有“平文既迁,庙唯有六”之语,已明尊道武帝为太祖后,平文庙已迁,并无更改庙号之事。)其所遵用的,显然是《礼记·丧服小记》及其郑玄注所述的五庙制(注:见《礼记·丧服小记》“王者邀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之文,特别是郑玄注,《丧服小记》不提五庙的昭穆内涵,而是强调“始祖感天神灵而生……高祖以下与始祖而五”一段。),又据《礼纬》和《孝经纬》之义而虚一庙(注:《礼纬·稽命徵》:“夏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孝经纬·钩命诀》:“禹四庙,至子孙五;殷五庙,至子孙六;周六庙,至子孙七。”俱《玉函山房辑佚书》本。),以为道武帝身后地步;而其所强调的,则无疑是始祖神元帝以下,平文帝——昭成帝——献明帝——道武帝父子四代相承的宗脉。其二是宫中五帝庙。所谓五帝是在太庙四帝的基础上增加了平文帝父思帝弗之位,从而勾勒了思帝——平文帝——昭成帝——献明帝——道武帝父子五代的宗脉。其三是云中盛乐祖宗旧游之地祀神元以下七帝。这七帝当是在宫中五帝的基础上增加了思帝之父文帝沙漠汗和昭成之兄烈帝翳槐,从而又完整地建构了神元帝——文帝——思帝——平文帝——烈帝和昭成帝——献明帝——道武帝父子七人五帝相嗣的宗统。四是端门内祖神之祀,其所祀当为道武帝登位时追尊的成帝以下诸帝,甚至包括所有拓跋口述史系统中的祖先;然其重点似仍应放在神元以下诸帝,尤其是不列于上述宗统而在拓跋早期壮大史中极具地位的桓、穆二帝身上。由此可断,与《序纪》所载的情况高度一致,天兴整套庙祭之制的基本宗旨,也是要清理拓跋早期帝系,梳出道武帝所承神元以来父子七人五帝相承之统,同时兼顾此外诸帝尤其是在神元以来拓跋发展史中地位重要的桓、穆二帝的历史地位和与之相应的政治资源,从而达到总结历史开辟未来,通过建立君统附从于宗统的原则来巩固传子制的目的。
关于天兴二年这套祭祖之制与《序纪》所载拓跋早期帝系的关系,当然还有不少具体的考证可做,但仅是上面所列举的,两者之间在基本用意和内容上的紧密啮合,特别是在道武帝所承神元以来父子七人五帝的宗统上的全面匹配,已足够令人印象深刻了。这当然决非偶然,因为在道武帝开国之际,《国记》的撰作和庙制的构思本身就是相互配合的。《魏书·邓渊传》:“太祖诏渊撰《国记》,渊造十余卷,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未有体例。”这里虽未明言《国记》始撰于何时,但邓渊自道武帝初拓中原被招揽即“擢为著作郎”,可以推知《国记》当自皇始以来始撰。(注:《魏书·高允传》载其对太武帝曰:“《太祖纪》,前著作郎邓渊所撰。”据《魏书·邓渊传》,渊皇始时为著作郎,后出为蒲丘令,“盗贼肃清”,约天兴元年十一月稍前人为尚书吏部郎,天赐三年蒙冤而死。则允之此语,盖就邓渊为著作郎时受诏始撰《国记》而言,且其撰道武帝时期的编年史,下限不会晚于天赐三年。又《崔浩传》:“初,太祖诏尚书郎邓渊著《国记》十余卷,编年次事,体例未成。”与《高允传》所述相参,此当就《国记》十余卷撰成之时邓渊为尚书郎而言。)而《太祖纪》载道武帝初定中原,便大肆招徕士大夫与之“宪章故实”,至登国十年七月建天子旌旗,改元“皇始”,两年后“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表明庙制之酝酿亦正在皇始以来,而《国记》对拓跋氏早期君长世系的清理,到天兴元年七月“建宗庙”时必已大体完成;当年十二月道武帝登位之初追尊成帝以下号谥并定其中若干帝的庙号,也只能在这种清理已大体完成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注:道武此举,似亦汲取了石赵的相关故事。《晋书·石勒载记下》:“太兴二年,勒伪称赵王……改称赵王元年,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命记室佐明楷,程机撰《上党国记》,中大夫傅彪、贾蒲、江轨撰《大将军起居注》,参军石泰、石同、石谦、孔隆撰《大单于志》。”此《上党国记》与《大将军起居注》及《大单于志》相并,似亦为羯人之“早期史”,《史通》外篇亦列之于《古今正史》中,是为拓跋氏撰《国记》之先河。然其时所建宗庙不详其制,至赵王十一年勒自称赵天王时,“尊其祖邪曰宣王,父周曰元王”,旋即帝位,“改元曰建平,自襄国都临漳,追尊其高祖曰顺皇,曾祖曰威皇,祖曰宣皇,父曰世宗元皇帝”。此世系亦当据《上党国记》而来。)
也正是在如此紧密的匹配关系中,除可以看出《国记》编撰和庙祭建制在基本用意和宗旨上的一致外,还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推论:一是只要《礼志一》所载天兴庙祭之制未经太武帝以来大幅删改,那么从魏收书《序纪》内容与天兴庙祭之制的高度啮合,可以推断《序纪》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国记》的基本内容。(注:这方面的佐证还有不少,如《魏书·邓渊传》载《国记》内容“惟次年月起居行事而已”,简直就是《序纪》以道武之前二十八帝传承世系为墓本内容的写照。又如《序纪》述拓跋氏远承黄帝之裔昌意至始均一脉,积六十七世而至成帝,也正是《魏书·太祖纪》及《礼志一》载天兴元年十二月帝登大位,“追尊成帝以下及后号谥”,崔玄伯等奏“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数用五,服尚黄”的产物。又《魏书·高佑传》载太和十一年佑共李彪上奏:“惟圣朝创制上古,开基长发,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足以史弗能传。”似亦可证《序纪》一笔带过的成帝以前六十七世,乃是《国纪》本未叙次。至于《国记》当初篇幅十余卷远多于今见《序纪》的一卷,亦不难解释为其续经改编部分内容确被删削;尤其是太和十一年以来国史从编年改为纪传体,有关内容许多都散入了诸纪传表志。)既然如此,关于北魏国史系统的波折对于《国记》所记早期拓跋史的影响,就不宜作过高的估计了。二是从四套庙祭之制的出入和互补可以推断,恰恰是神元以下父子七人五帝相嗣的世系,并非是《序纪》中最为可信的部分。这倒不仅是因为其刻意营构之迹颇显,令人联想刑事证据学关于受益者即作案者的推理原则;更是因为道武帝将祭祖之制分为四套办法,除去其兼顾旧俗与汉制的意味外,恐怕也是因为拓跋早期婚姻关系颇为紊杂,致使君位传承世系不次而昭穆难讲,尤其是文帝、思帝、烈帝、道武帝前后君统和宗统关系不甚明朗之故。换言之:承袭了《国记》基干的《序纪》,其最有可能曲笔之处,恰恰是直接与神元至道武父子七人五帝相嗣之脉相关之处;倒是距此宗统越远的内容(注:渲染祖宗“图南”事迹以维护道武帝与南朝相争的政治资源的部分当在其外,因为这一部分也是较易曲笔之处。具体如《序纪》述平文帝功业“西兼乌孙故地,东吞勿吉以西,控弦上马将有百万”,《资治通鉴》九○《晋纪十二》太兴元年载平文击破刘虎后,“西取乌孙故地,东兼勿吉以西,士马精强,雄于北方”,盖从《序纪》之说。胡注则界定“勿吉以西之地,未能兼勿吉也。徒何慕容、令支段氏及宇文部、高句丽亦非郁律所能制服”。是《序纪》此处文似夸饰。《序纪》又述平文帝闻晋愍帝噩耗而拒刘曜、石勒、东晋之使,“治兵讲武,有平南夏之意”。《拓跋史探》所收曹永年先生《补充与讨论两题》以为平文帝“图南”之举,实是进兵离石而为石虎大败,遂被桓帝祁后加害而身死。然则《序纪》于此又隐晦矣。),才越有可能保留拓跋早期口述史系统中“世事”的原貌,即有荒诞离奇也当归于这个口述史系统的问题,而很难归咎于天兴以来的成文史系统。
四、关于模糊区域问题
最后,我还想简单谈谈“模糊区域”的探讨问题,也是有些好意的读者对田先生此书抱有不必要遗憾的地方,以此来结束本文。
首先要明确,所谓“模糊区域”的存在,与史料的多少并不必然相关。史料少会有模糊区域,史料多就没有了?换个角度还应当说,史料多了,清晰区域扩大了,模糊区域也就随之变大了。就是说,正是因为我国古代史料之多、之系统,为世界史上所仅见,才会有如此大量的模糊区域;而对文档和物品遗存很少甚至根本没有文字遗存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史来说,肯定不仅会鲜有清晰区域,连模糊区域亦必罕见了。由此看来,所谓模糊区域,正应是黑暗与光明的过渡地带,完全没有史料的黑暗地带是无法研究的,史料中已非常清楚的光明地带是无须研究的,只有存在着史料又不甚清楚的模糊地带,才是研究和探索可以纵横驰骋的广阔园地。但我们注意到,在《拓跋史探》一书《前言》中,田先生一方面谈到了模糊区域的研究对于整部中古史研究的重要性,提到了“但开风气不为师”与学术进步的关系,这实际上已经从史学史和史学学角度明确了模糊区域探讨的必要。而另一方面,田先生又在反复地说明此番研究的资料稀少而结论难下,旨在提供思路和头绪以引起共同探讨,甚至说了“戒惧愚诬”的重话。这些话很明显并不是讲给外部,而是讲给史界同人听的。这不免让人感慨于我国史界的现状:如果连田先生也要在探索模糊区域时如此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那么我们目前的史风,是一种并不拘谨甚至是开阔大气的史风吗?我们目前的史界,是一个让人们大胆探索推陈出新的史界吗?在这里面,我们这二十多年来的发展又有些什么经验和教训可以总结呢?
无数学术史经验和教训都表明,特定清晰和模糊区域格局的停滞不前,通常也就是旧的研究范式和框架,非调整或改变已再难推动该学科和领域前进的标志。当此之时,若要推进认识,就须充实或修改研究的范式和框架,这才会有新的问题、新的事实、新的理论,也才会有新的模糊和清晰格局。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陈寅恪先生为代表的文化史学的研究路子(注:此当以3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开讲《魏晋南北朝史》为标志。),主要通过诸种族文化背景来透视门阀社会的种种问题,为这个领域的清晰区域和模糊区域划出了一个大的格局。到40年代以来,以唐长孺先生为代表的社会史学路子(注:此当以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大部分文章的写作年代为标志。),主要以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来透视各种社会问题包括种族文化问题,为这个领域的清晰和模糊区域划出了又一个格局。50年代以来,后者愈长而前者渐消,至田先生《东晋门阀政治》出,才构成了这条路子的一个转机。继而田先生《拓跋史探》正面切入早期拓跋史这个深关中古史演变枢纽和东北亚民族关系转移的模糊区域,围绕着拓跋部从部落社会向专制皇权国家发展的总线索,主要通过政治问题来探讨这个多民族时期的多元发展过程,以此涵盖了以往魏晋南北朝史各重要命题又形成了新的研究框架。就其内涵和方向而言,田先生所开启的这种研究,似已在开始形成一个同时接续陈寅恪先生和唐长孺先生所代表的学术路子的合题,因而也已在区划着又一个清晰和模糊区域格局的轮廓。
对模糊区域的探讨,必须有较深的材料榨取功夫,亦必有赖于较高的理论素养,两者缺一不可;故高明为之必胜义叠出而发人所未发,庸手为之必画虎反成犬而惨不忍睹。此理甚明,无庸赘述。但这里仍有必要强调理论和材料相为发明的问题,因为转辗递嬗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史坛正处于有史以来理论和材料关系最为乖张的一种氛围,处于两个极端互不接头通气的状态:一头是那些偏好理论的史家以心学式的易简法门,接连抛出了各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理论”——在这里材料永远是挥之即去的配角;另一头是那些酷爱实证的史家做着朴学式的密实功夫,不断辨证着那些从事实到事实的“事实”——而赋事实以意义的概念框架早已成了先验之物而不再被审视。也正因为久处于这种乖张的氛围,田先生探讨早期拓跋史这个模糊区域的艰苦工作,竟然会变得易于受人误解了!人们似乎已经忘了史料学上的一个基本现象和原理:大匠眼里材料多,小才手下少证据。某一领域和专题的材料范围,不但是由有关文档物品等遗存的总量决定的,更是由研究的观念和范式来划分的。因而在有关观念和范式不变的前提下,材料的多少,就会由遗存总量的增长与否来决定;而反之,在这种遗存总量不变的前提下,材料的多少亦可以由有关观念和范式的变化来决定。由此看来,从陈寅恪、唐长孺到田余庆等先生所以能见人所常见,发人所未发,在史料总量并未大幅增长的地方极大地推进有关研究的发展,原因端在其研究观念和范式较以往更切合于事理,也就能发现和利用更多隐晦又关键的材料和线索。(注:曾见有人把“一代材料必有一代学问”之说的合理处无限夸大,甚至把陈寅恪先生和唐长孺先生归结为敦煌叶鲁番文书再现人世所催生出来的杰出学者。这不仅严重低估了陈先生和唐先生的成就和学问,且有违于“人能弘道”的哲理,也是对陈、唐三先生治学经历和路子的无知。)当然他们的研究观念和范式,并不是现成地得之于书本,而是先在大量缭人耳目的记载和现象后面发现问题纽结和脉络之所在,以之指导研究并涣释其他各相关问题,又验证和修正其结论,从而才建立起关于该领域和事态的特定诠释体系的。
其实在科学史、科学学和哲学认识论上,模糊区域的价值及其与清晰区域的界域和相互关系,大概可以认为是一个从理论到实际都有了若干定论的问题。不仅史学,任何学科和领域的研究工作,其基本的设定总是最考量学者的洞察力和创造力,也具有最为根本的意义,在此前提下,新的拓展和发挥当然也还是需要洞察力和创造力,但大量问题其实已是勤奋、毅力问题和语言、逻辑问题,而这种基本问题的设定,正发生于模糊区域,也只发生于模糊区域。质言之,有问题或问题很多的地方,就是模糊区域;没有问题或问题较少的地方,就是清晰区域。模糊区域就是学术领域的前沿,是所有原创工作的密集地,也是学术探索不断向前推进的关键所在。因而任何时期、地区、领域、专题历史的研究,无论其史料多么翔实多么丰富,只要有探索,就会有模糊区域,就会有模糊区域与清晰区域的关系问题,两者其实是任何学科和领域的一对密切互动的侧面:特定学科范式下形成的清晰区域的格局,势必导致相应的模糊区域,而模糊区域探讨的成果,又必然导致清晰区域的种种变化或位移,乃至于学科范式的改写,这也就是学科发展的一般过程。
学术史上常常可见,一方面,模糊和清晰区域的研究,都为学术发展所必需,乃是学术领域和学科进步相辅相成的两个侧面;另一方面,尽管所有史家都会不同程度地面临模糊区域和清晰区域的关系,具体到个别史家,却仍然会有选择和志趣的不同。笔者相信,像田先生这样的史家,毋宁说是不喜欢、甚至是不屑于清晰区域的研究,而一定要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放在模糊区域的种种问题上的。很显然,有洞察力和没有洞察力的史家,穷其枝叶的研究和明其要津的研究,消除了问题的著述和提出了问题的著述,都是史学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发展所必要的部分;但要我说,英雄在群众基础上发挥的作用,总还是要比群众重要一些吧?
编后记:《拓跋史探》一书由三联书店提供,由本刊编辑部约请作者,撰写书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