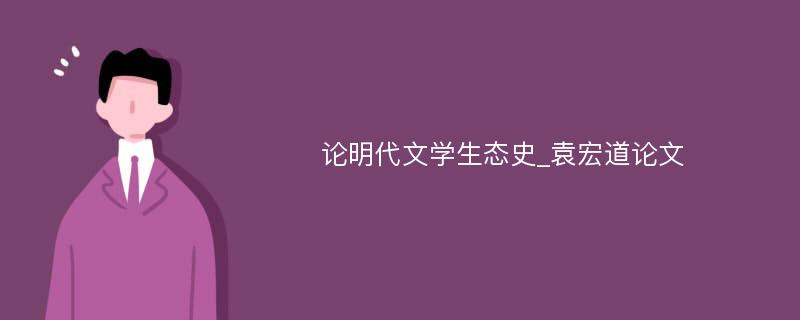
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史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论论文,生态学论文,明代论文,文艺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封建社会,在唐宋达到鼎盛而在明清时期走向衰退和没落。在封建自然经济逐步解体的同时,顺应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规律,资本主义因素艰难而曲折地开始在中国萌发并不断增长,商品经济得到新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变革,也必然引起文艺美学观念的变化。明代中期开始兴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引发了文学解放思潮的出现。这种思潮,一反旧的传统文学观念,摒弃封建主义文学的敦厚礼义色彩,鼓吹自由的市民意识,使市井人物开始走入文学作品中,并成为文人创作中歌颂的重要对象。张扬人性的觉醒与个性的解放,追求与时代相扣合的美学风格与观念,成为新的文学潮流。而西方新学的输入,又极大地促进了文学的进步与发展。在这种情势下,明代的文论家们,于总结前人文学理论中纷繁学说与博杂体系的基础上,大胆借鉴和创造,力图建立具有新的时代特征的文艺美学体系。又由于时代呈现着复杂的矛盾、激烈的斗争和日益下滑的态势,促使文论家们对文学做开放性与多维性的社会学思考,令文艺生态学思想获得了新的发展。
对社会自然外物与创作主体内在情感关系的思考,是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出发点。祝允明、李梦阳、王廷相、谢榛、王世贞等人的文艺生态学思想,都显示了这一特征。揭开明代文艺思想史册,最先走入我们视野的,是著名文学家和书法家祝允明。“身与事接”是他的主要论点之一,祝允明在《送蔡子华还关中序》中这样写道:
身与事接而境生,境与身接而情生。尸居巩遁之人,虽口泰华,而目不离檐栋,彼公私之憧憧,则寅燕酉越,川岳盈怀,境之生乎事也。至于蛮烟塞雪,在官辙者聂聂尔,若单行孤旅,骑岭峤而舟江湖者,其逸乐之味充然而不穷也,情不自境出耶?情不自已,则丹青以张,宫商以宣,往往有俟于才。夫韵人之为者,是故以情之钟耳,抑其自得之处,其能以人之牙颊而尽哉。(注:祝允明:《送蔡子华还关中序》,《枝山文集》卷二。)
在《姜公尚自别余乐说》中又说:
情从事生,事有向背,而心有爱憎,由是欣戚形焉。事表而情里也。(注:祝允明:《姜公尚自别余乐说》,《枝山文集》卷二。)
祝允明的话,很有辩证的意味。他首先认定,“身与事接而境生”。外在事物或使人欣喜,或令人悲戚,而形于面色,这就强调了人对外界环境与事物的某种有赖性;“境与身接而情生”,则表明美感亦当“自境出”。但是,文艺创作不仅仅以此为唯一必备的条件,而又“往往有俟于才”。创作者只有具备了创作才能,又在特定的环境下产生出某种感情,才可能创作出优秀的作品。祝允明的这一文艺生态学思想主张,无疑是放射着唯物主义之光的卓见。
与祝允明生活在同一时期的李梦阳,也十分看重文艺创作中的艺术情感,主张要表现发自作者内心的真情。而且他对艺术情感与客观外物关系的认识,也与祝允明有相似之处。李梦阳认为:
情者,动乎遇者也。幽岩寂滨,旷野深林,百卉既痱,乃有缟焉之英媚枯缀疏,横斜嵚崎清浅之区,则何遇之不动矣?是故雪益之色,动色则雪;风阐之香,动香则风;日助之颜,动颜则日;云增之韵,动韵则云;月之与神,动神则月。故遇者,物也;动者,情也。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梅月者,遇乎月者也。遇乎月则见之目怡,聆之耳悦,嗅之鼻安。口之为吟,手之为诗。诗不言月,月为之色;诗不言梅,梅之为馨。何也?契者,会乎心者也。会由乎动,动由乎遇,然未有不情者也。……身修而弗庸,独立而端行,于是有梅之嗜。耀而当夜,清而严冬,于是有月之吟。故天下无不根之萌,而子无不根之情,忧乐潜之中而后感触应之外。故遇者因乎情,诗者形乎遇。(注:李梦阳:《梅月先生诗序》,《空同集》卷五十。)
李梦阳在这里十分鲜明地道出了“诗者,感物造端者也”(注:李梦阳:《秦君饯送诗序》。)的意义。面对“幽岩寂滨,旷野深林”之壮美景色,焉有不动情者。然而,遇物动情,只是创作过程之始,随之便“情动则会,心会则契,神契则音,所谓随遇而发者也”。同时,“耀而当夜,清而严冬”与创作者的“月之吟”,“身修而弗庸,独立而端行”的品德与创作者的“梅之嗜”,在李梦阳看来,都有着某种必然性和因果关系。物→情→文,是李梦阳对文艺创作活动走向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李梦阳在《结肠操谱序》中做了进一步的展示:“天下有殊理之事,无非情之音。何也?理之言,常也,或激之乖,则幻化弗则,《易》曰‘游魂为变’是也。乃其为音也,则发之情而生之心者也。《记》曰:‘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起物而动,然后心求形焉。’是也。”这里,李梦阳将文艺创作与理论探讨进行了对比,从而得出前者是“感物而动”、“乃其为音也”的结论,这一观点,与先秦时期音乐美学著作《乐记》中的“物感”说是大体一致的。总体说来,李梦阳这里所言之“物”,大致还是指自然界的一景一物,对宏观自然与文艺之关系的思考,尚有所欠。当然,李梦阳是在表述文艺创作过程时说明“物”在文艺创作流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仅揭示了“物”在创作中的使动作用,而且指出了创作过程中“动遇”结合的反复性特征,不乏新颖之处。而且,李梦阳对文艺创作与地域之关系也曾有所思考,尽管这种思考在当时看来并不显深刻。例如,他在《题东庄饯诗后》中说:“夫既东西南北人也,于其分不有怅离思合者乎?于是筵于庭,祖于道,觞于郊,嬉于园,不有缱绻踟蹰者乎?斯之谓情也。情动则言形,比之音而诗生矣。”(注:李梦阳:《题东庄饯诗后》,《空同集》卷五十八。)在《题明远楼诗后》曰:“情以地殊,音由感发者也。”(注:李梦阳:《题明远楼诗后》,《空同集》卷五十八。)李梦阳意识到了不同地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情愫,其为此所动,发而为诗。但他对文学作品因地域不同所显示出的差异却研究不多,所论自然显得肤浅了一些。倒是明代的其他一些学者在这方面有很好的补充。以李东阳为例。他认为:“汉魏、六朝、唐、宋、元诗,各自为体。譬之方言,秦、晋、吴、赵、闽、楚之类,分疆画地,音殊调别,彼此不相入。此可见天地间气机所动,发为音声,随时与地,无俟区别而不相侵夺。然则人囿于气化之中,而欲超乎时代土壤之外,不亦难乎?”(注:李东阳:《麓堂诗话》。)又说:“世殊地异而人不同,故曹、豳、郑、卫,各自为风,汉唐与宋之律,代不相若,而亦自为盛衰。”(注:李东阳:《赤城诗集序》,《怀麓堂集》卷四。)表明了地域、时代对文体与声调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
李梦阳在考察文艺创作与外物关系的同时,自然地对艺术与社会关系有所思研。他曾说过这样一段话:“襄予有内之丧,亲睹厥异。伤焉,惊焉,吟焉,永焉,于是援笔而布辞。疏卤荒鄙之音,聊泄愤愤闷闷汶汶焉。”(注:李梦阳:《琴操谱序》。)李梦阳在这里阐述的是作家创作的过程。由于“内之丧”的刺激而伤、惊,又由这种伤、惊之情产生吟、咏的创作欲望,终而诉诸笔端。社会事件对作家产生创作的驱动力,促使他通过援笔布辞以宣泄情感,李梦阳所揭示的这种创作活动现象,显然具有社会生态学的内涵与意义。当然,李梦阳以情为枢展开的艺术理论阐述,一定程度上拘制了他的文艺生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所论也极为有限,将这时代其他文论家的这方面言论列录如下,其可与李梦阳所言相得益彰。胡翰认为:“诗系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辞义不同,由世而异。”(注:胡翰:《古乐府诗类编序》,《皇明文衡》,卷三十八。)高棅指出:“文章与时高下,与代终始。”(注:高棅:《五言古诗叙目》,卷二十二。)王祎则提出,从“词翰细事”中“可观世变”(注:王祎:《书徐文贞公诗后》,《王忠文公集》卷十七。)。他们的一个共同点,即认为文事之兴衰率随时代之变迁。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显示了比李梦阳更为开阔的视阈。
与李梦阳同为明代“前七子”的王廷相,其文艺生态学思想同样贯穿着情感的主线,与李梦阳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他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心理学家,所持感知论是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基础:“故神者在外之灵,见闻在外之资,物理不见不闻,虽圣哲不能索而知之”,“人心与造化之体皆然。使无外感,何有于动?故动者,缘外而起者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倘无与客观外界相接触,没有对世事的“实历”,即使圣哲也无以为知。人的思维、情感盖“缘外而起”。王廷相的这种唯物主义的心理学理论,融渗在他的艺术审美情感论中,显示出鲜明的艺术生态论的蕴味。在他看来,情感是人在外界事物的刺激下产生的,所谓“憎爱哀乐,外感之迹”,“喜怒者,由外触者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但是,情感又不仅仅是人对外物的简单反映。王廷相指出:
喜怒哀乐,其理在物;所以喜怒哀乐,其情在我,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在物者感我之机,在我者应物之实。不可执以为物,亦不可执以为我,故内外合而言之,方为道真。(注:王廷相:《雅述上篇》。)
大千世界,人的各种状况不同,心理素质、接受状态有异,因此对外界的体验也不尽一致。情感的产生,既有外物影响作为前提,又有自我感应条件相作用,“合内外而一之道也”,即应当为主客观相统一。也就是说,人的知觉运动产生情感,而人产生情感也须具备产生情感的主观素质,其才成为可能。王廷相的观点,显然更符合艺术思维的规律,更具有合理性和广泛的意义。而他同时认为,由外物引发出的情感,对艺术格调的确立,具有重要作用。他所言“任情漫道,畔于尺渠”,被文学史家视为“因情立格”说的标志。这表明,王廷相起码在这一点上超过了李梦阳的认识,使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得到了深化。
列为明代“后七子”的谢榛、王世贞,生活在明代中期,其文艺生态学思想同样表现出缘情特征。谢氏认为:“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虽幽寻若索,不易得也。”又说:“作诗本乎情景,孤不自成,两不相背。凡登高致思,则神交古人,穷乎遐迩,系乎忧乐。此相因偶然,著形于绝迹,振响于无声也。夫情景有异同,模写有难易,诗有二要,莫切于斯者。观则同于外,感则异于内,当自用其力,使内外如一,出入此心而无间也。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胚,合而为诗,以数言而统万形,元气浑成,其法无崖矣。”(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谢榛认为作诗的奥妙在于特定的时空之引发,这无疑是特别强调和重视了诗歌创作的社会与自然外物的影响。同时,他也认识到,在关乎诗歌创作的景与情两者间,它们既相对立,又相统一,即所谓“孤不自成”,“两不相背”。诗歌作品是作家观于外而感于内的成果。谢榛把客观外物视为作诗“媒介”,将由外界感刺而来的情感目为诗之胚胎和魂魄,是十分恰当的,是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形象概括和归纳。
谢榛对文艺的生态学思考,还表现在外在环境与作家审美心理相互关系方面。其曰:“自古诗人养气,各有主焉。蕴乎内,著乎外,其隐见异同,人莫之辩也。熟读初唐、盛唐诗家所作,有雄深如大海奔涛,秀拔朔漠横雕,清逸如九皋鸣鹤,明净如乱山积雪,高远如长空片云,芳润如露蕙春兰,奇绝如鲸波唇气。此见诸家所养之不同也。”(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外在环境的影响,构成了作家特定的审美心理(养气),而这种不同的审美心理,也就决定了作家作品的独特风格。谢榛以唐诗为例所论证的这一观点,展示了东方生态诗学的特有魅力。也许,谢榛的这样一段话更令人回味:“作诗譬如江南诸郡造酒,皆以曲米为料,酿成则醇味如一。善饮者历历尝之曰:此南京酒也,此苏州酒也,此镇江酒也,此金华酒也。其美虽同,尝之各有甄别,何哉?做乎不同故尔。”(注:谢榛:《四溟诗话》卷三。)这一比喻说明,作家受外在环境影响所得不同的创作赋性,使作品的“醇味”必然殊异。谢榛所言各地方风味之酒,既是虚言指喻,又有实义含藏,展示出谢氏的文学地域意识。
王世贞是“后七子”的理论代表,其诗学具有以情论诗的特征。虽然也主张“感物而动”、“形之于声”,如其曰:“心之精神发而声者也。其精神发于协气,而天地之和应焉;其精神发于噫气,而天地之变悉焉。”(注:王世贞:《金台十八子诗选序》,《四部稿》卷五十六。)但其落脚点更为切近文学本体。他说:“自楚、蜀以至中原、山川莽苍浑浑,江左雅秀郁郁,咏歌描写须各极其致。吾辈篇什既富,又需穷态极变,光景常新。”(注:王世贞:《与徐子与书》,《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一八。)可以见出,王世贞对自然的观察,远比他的同时代人视境更为阔大。作家置身于这样的外在环境中,在接受自然作用的同时,还要更多地从中引发出富有新意的创作。这是王世贞的独到之处。然而,王世贞的高远见解,更表现在关于南北曲的论述中。他对南曲北曲的不同风格做了这样的分析:
凡曲,北字多而调促,促处见筋;南字少而调缓,缓处见眼。北则辞情多而声情少,南则辞情少而声情多。北力在弦,南力在板,北宜和歌,南宜独奏。北气易粗,南气易韵。此吾论曲三昧语。(注:王世贞:《曲藻》。)
王世贞以地域角度观察北曲和南曲,从字词用调、情感表征、板弦运用、演奏方式、气度强弱等多方面,对南北曲因地域不同而形成的风格,做了相当中肯、颇具才情的论述,在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领域中是最具特色的。
在明代,堪称文艺生态学思想大家者,当为思想家、文论家李贽。在他的艺术理论中,童心说是最著名并为人们所熟知的主张。童心者,真心也。李贽认为艺术应表现人的“童心”,表明了市民阶层要求思想和个性解放的呼声,在中国文学理论和美学史上有重大意义。在关于童心说的表述中,李贽指出:“然童心胡然而遽失也?盖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注: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在李贽看来,人的“童心”的失却,童要的一点是“有闻见从耳目而入”,“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闻见和道理“主于其内”便造成了“童心失”。李贽这里所言“闻见”与“道理”,虽然并非指耳目所能感知的一切外物,和目力所及的一切识见,但李贽仍是指认其为某种特定的社会人文环境,即对人产生影响的人为设定之虚假社会环境。这就使李贽童心说这一重要美学论说,内含了社会生态学的意义。
基于“满场是假”的社会环境,李贽提出“发愤著书”说,其成为其文艺生态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他说:“古之贤圣,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注: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李贽所论,揭示出社会事件的刺激对作者进行创作有巨大的激励作用。他还曾这样说道:“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一旦见景生情,触目兴叹,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注:李贽:《杂说》,《焚书》卷三。)这里,李贽指出了社会环境对艺术创作影响的两种形态。其一是“蓄极积久”的影响。客观社会的各种事物,对作者的思想与心灵日积月累地产生作用。这是一种量的堆积。其二是见景生情的触发。经年积累于心之物,必然届时造成“势不能遏”的倾吐之状。然而这种宣泄,必以某一种社会物状为媒介,得到触发后方能尽情倾泻,乃至“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注:李贽:《杂说》,《焚书》卷三。)。李贽的蓄愤成诗说,细腻深刻地描述了社会环境影响文艺创作的基本点和过程,比起他前辈的同类观点,显得更为透彻、精炼和全面。
与“发愤著书”说相联系的,是“感时”说。就文艺生态学的题旨而论,后者有更鲜明的直指性。李贽说:“文非感发已,或出自家经画康济,千古易者,皆是无病呻吟,不能工。”(注:李贽:《复焦漪园》,《续焚书》卷一。)所谓“感时”,即作家对所置身的社会环境的感受,从这种感受中孕育而成文旨,点示了社会人文背景对文学创作的前提作用。那么,李贽“感时”说的蕴义何在呢?我们且看他这样一段话:
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记,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注:李贽:《童心说》,《焚书》卷三。)
李氏此言意在批评当时文坛盛行一时的复古文学思想。但从中却表露出一个极为重要的文艺生态学观念,即文学作品的样式与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形态的;新的社会,新的时代,新的生活,必然有反映和表现它的作品产生。而这些被称誉为“古今至文”的作品,又作为人文环境的组成部分去影响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李贽所论透露出的带有生态规律性的文论主张,值得我们格外重视。
李贽就此又从具体作品入手进行分析。他认为,《水浒传》便是作者“感时”之作。有那样的“时”,必然有反映那样的“时”的作品:“宋室不竞,冠屦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致驯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君相犹然处堂燕鹊,纳币称臣,甘心屈膝于犬羊已矣。”(注:李贽:《忠义水浒传序》,《焚书》卷三。)《水浒传》的作者正是面对宋明以来这样一个黑暗、腐朽、多难的社会态势,感而发之,执笔为著的。文撰至此,很容易令人想起李贽同时代人怀林的与其相类的言论。他从对《水浒传》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切入,做了更为详深的阐发:“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妇人,然后以扬雄之妻、武松之嫂实之;世上先有马泊六,然后以王婆实之。世上先有家奴与主母通奸,然后以卢俊义之贾氏、李固实之。若管营,若差拨,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陆谦,情状逼真,笑语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呕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浒传》之所以与天地相终始也。”(注:怀林:《卷首·〈水浒传〉一百回文字优劣》。)怀林认为,《水浒传》中的各类人物虽系作者“捏造”,但确是社会生活中“先有”,若非如此,作者即使倾尽心血、闭门苦思,也是写不出来的。这就极其鲜明地指出了现实环境对小说创作的重大作用,是对李贽所论的更明确具体的补充。
深受李贽影响的公安派,其文论具有鲜明的生态学特色。这一流派的领袖人物袁宏道,是当时文坛主张趋时的新派人物,因而理论上极力强调时代对艺术创作的影响。“时道既变,文以因之”,便是他提出的著名论点。他说:“古不可优,后不可劣,若使今日执笔,机轴尤为不同。何也?人事物态,有时而更,乡语方言,有时而易,事今日之事,则亦文今之日文而已矣。”(注:袁宏道:《与江进之书》。)在他看来,“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注: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古今相异,时代有别。而世运既变,则“文随时转”。当今之人“事今日之事”,也必“文今之日文”。因此,“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厚不可以优劣论也。”(注:袁宏道:《叙小修诗》。)
袁氏的《雪涛阁集序》,在文艺生态学思想史上堪称重要之作。此文提出了若干重要论点。其一,他认为,“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妍媸之质,不逐目而逐时。”这也就是说,文章不是凭空而降,而是由古自今随社会历史发展演变而形成,因此,文章品格的高低,也就为时代情势所决定。袁宏道在这里指出文章批评的价值尺度受社会时代所制约,而绝非取决于纯粹的个人好恶。而他批评拟古主义“彼不知有时也,安知有文”(注:袁宏道:《诸大家时文序》。)之说,又表明了文艺批评要知世论文的意向。其二,袁宏道认为:“法因于敝而成于过者也。”这就揭示了文之变化的某种规律。诗文的章法、风格必然经历由兴起、流盛、衰敝进而被一新的章法、风格所替代之过程。而新的章法与风格仍然会经受由盛而衰的历程。在这种由世运变化所引起的诗文演变的交互更迭的历史改革中,新的风格与章法当在“矫枉过正”中确立。这是确有见地之论。
此外,袁宏道对地域与文学之关系,亦有思考与论析。他指出:“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他认为地区不同而导致民风有异,由此造成了楚地诗风的独特性。这种分析显示了文艺生态学的新颖视角。
袁宏道的文艺生态学思想,在这一领域历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对世运与诗文关系的思考和有关规律的总结归纳,具有极高的价值,若将袁宏道视为继刘勰之后对“时变文因”说论述得最为充分者,并非过誉之辞。
总观明代文坛,在其论著中表达出文艺生态学思想的文论家,还不仅仅只限于上述文论家。袁宏道之弟袁中道,对其兄的“时变文因”说持赞同态度,认为“天下无百年不变之文章”。一方面,他感到“诗莫盛于唐”,其“览之有色,扣之有声,嗅之若有香,相去千余年之久,常如发硎之刃、新披之萼”(注:袁中道:《宋元诗序》。),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体。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唐诗固有高格,但宋诗亦有“精采不可磨灭处,自当与唐并存于天地之间”,所谓一代有一代之风格。而这种不同,皆因时所致,“有气行乎其间”(注:袁中道:《宋元诗序》。)。从而由文之外部和内部两方面将致变原因觅见,这就在某种程度上比宏道所论更加细腻深入。李维桢指出:“格由时降而适于其时者善,体由代异而适于其体者善。”(注:李维桢:《亦适编序》,《大泌山房文集》卷二十一。)胡应麟认为:“四言不能不变而五言,古风不能不变而近体,势也,亦时也。”“诗之体以代变也”,“诗之格以代降也”(注:胡应麟:《诗薮》。)。冯时可言道:“西汉简质而醇,东京新艳而薄,时之变也。”(注:冯时可:《雨航杂录·两汉文章》。)屠隆论曰:“虞夏之书浑浑尔,商书灏灏尔,周书噩噩尔,汉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质木,元文轻佻,斯声以代变者也。”(注:屠隆:《诗文》,《鸿苞节录》卷六。)比较一致地表明了时世对文学体制、风格具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此时的文论家,对地域与文学的关系问题,与前述的李梦阳、王世贞、袁宏道等也有一致的看法。唐顺之说:“西北之音慷慨,东南之音柔婉,盖昔人所谓系水土之风气,而先王律之以中声者。”(注:唐顺之:《东川子诗集序》,《荆川先生文集》卷十。)屠隆说:“周风美盛,则《关睢》、《大雅》;郑、卫风淫,则《桑中》、《溱洧》;秦风雄劲,则《东邻》、《驷驖》;陈、曹风奢,则《宛丘》、《蜉游》;燕、赵尚气,则荆、高悲歌;楚人多怨,则屈骚凄愤。斯声以俗称。”(注:屠隆:《鸿苞集》卷十八。)王骥德说:“剧之与戏,南北故自异体”,“北南二调,天若限之,北之沉雄,南之柔婉,可画地而知也。北人工篇章,南方工字句,工篇章,故以气骨胜;工句字,故以色泽胜”(注:王骥德:《曲律》。)。许学夷说:“诗文与风俗相为盛衰”(注:许学夷:《诗源辩体》卷十一。)。他们认为民风民俗对文学创作影响深远,这无疑大大丰富了明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内涵。至于晚明黄宗羲所持诗原本论——人在“天道之显晦,人事之治否,世变之污隆,物理之盛衰”的环境中,“推荡磨励”,必有不平,发而为诗(注:黄宗羲:《朱人远墓志铭》。),基本上是昌黎所论及明代李贽“发愤著书”说的复述,已显得新意无多了。至此,中国古代文艺生态学思想的历史,开始步入自己的最后一个朝代。
标签:袁宏道论文; 李梦阳论文; 文艺论文; 生态学论文; 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水浒传论文; 焚书论文; 王世贞论文; 四溟诗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