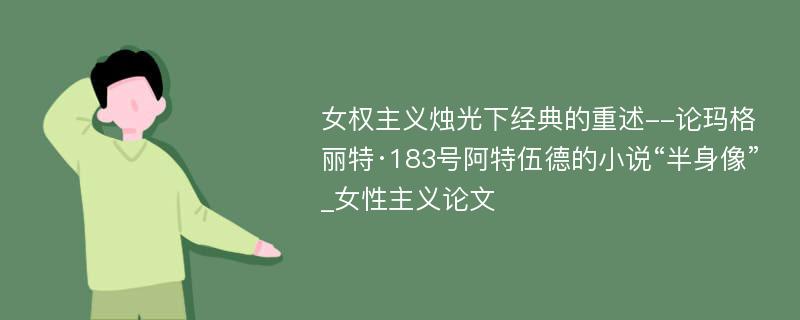
女性主义烛照下的经典重述——评玛格丽特#183;阿特伍德的小说《珀涅罗珀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伍德论文,阿特论文,玛格丽特论文,女性主义论文,经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中后期,西方文学中多有重述与再造经典的文本出现。这些作品往往在原作人物关系与情节框架的基础上大胆发挥,通过叙述视角和言说方式的转换,对旧有故事进行重述。如英国作家简·里斯(Jean Rhys)作为《简·爱》前篇的长篇小说《藻海无边》(Wide Sargasso Sea,1966)、美国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Donald Barthelme)戏仿格林童话和迪斯尼版动画片的中篇小说《白雪公主》(Snow White,1967)和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挑战莎士比亚经典悲剧《哈姆莱特》的长篇小说《葛特露和克劳狄斯》(Gertrude and Claudius,2000)等,均为这一重述与再造序列中的佳作。2005年,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推出了重述希腊神话的小说新作《珀涅罗珀记》(The Penelopiad,2005)①,亦再一次引起了人们对这位宝刀未老的作家创作才情的关注。
作为20世纪下半叶西方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学现象,经典重述与西方文学由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过渡,与后现代主义重估传统价值、消解既定权威的潮流之间,隐含着许多微妙的联系。女性主义作为后现代思潮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以揭露历史传统与现行文化中的父权中心本质和弘扬女性价值为旨归。它认为历史是一种建构、是“他”所讲述的“故事”,体现了权力拥有者的话语暴政。而作为加拿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女作家和女性主义文论家的阿特伍德,则通过《珀涅罗珀记》讲述了一个“她”的“故事”,使其成为女性主义烛照下重述经典的一部力作。
《珀涅罗珀记》是2005年3月正式启动的全球重述经典、重造神话的大型出版合作项目之一。全球共有30余家出版社、数十位作家参与,其中不乏诺贝尔文学奖和布克奖获奖作家。中国著名作家苏童也参与了对孟姜女故事的重构。神话之所以成为重述的首选对象,首先是因为它作为绽放于人类童年时代的花朵滋养了无数人的心灵,具有其他文类无可比拟的得天独厚的历史辐射力;同时,神话作为人类祖先旺盛想像力的产物,往往又以变形的方式折射出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体现出母系社会向父权制社会过渡的历史印痕。比如希腊神话中俄瑞斯忒斯杀母为父复仇的故事,以及埃斯库罗斯以此为题材创作的著名悲剧三部曲,均反映了“女性富有历史意义的失败”;希腊神话中以奥林匹斯山上的天父宙斯为中心的新神谱系体现的一夫多妻制,显然也表现了现实生活中男女地位的差异;在小亚细亚一带民间短歌基础上形成的荷马史诗,同样有很多实例显现出地中海沿岸诸国以父权制为中心、并向私有社会形态过渡的痕迹。女性要么被处理成弑君篡位、心狠手辣的荡妇,如阿伽门农的妻子克吕泰涅斯忒拉,要么被理解为男性竞相争夺的尤物和引发战争的祸水,如珀涅罗珀的表妹海伦。这位众神和凡人的宠儿轻佻而虚荣,天生为男性的追逐而活,是一朵在鲜血浇濯下盛开的玫瑰。而奥德修斯的妻子珀涅罗珀则以二十年的孤灯独照为代价,换得了忠贞的好名声。因此,借用西蒙娜·德·波伏瓦“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文化生成的”观点可以发现,神话作为一种变形的历史,是渗透了父权制物化与妖魔化女性的历史观的;而对神话进行重述,则具有了正本清源的文化还乡意义。
基于此种原因,阿特伍德爽快地加入了重述神话的行列。早在20世纪中期求学于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期间,阿特伍德即深受神话原型理论的代表人物诺思洛普·弗莱的熏陶,随后在长期的文学实践中,亦表现出对神话经久不衰的浓厚兴趣。她的很多诗歌均涉及神话题材,比如1974年的作品《你很幸福》即从希腊神话中的女怪喀耳刻的角度,重述了奥德修斯故事,表现女性作为战利品,只能被动地面对男性欲望的主题,探索了两性关系中的权力政治;1995年的诗集《焚毁之屋的早晨》更是涉及了多样化的神话题材。②《珀涅罗珀记》则是阿特伍德在女性主义价值观的烛照下反思既定历史叙述的扛鼎之作。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首先在于以重述神话为突破口,经由人物叙述视角的转换,通过女主人公打破数千年的沉默,以第一人称向当代的我们叙述“她”的故事的巧妙构思,体现了女性主义的文化观与历史观。
在荷马史诗《奥德修纪》中,珀涅罗珀是英勇的伊塔刻国王奥德修斯的妻子。她以对丈夫忠贞不渝的典范形象而出现,她的事迹也成为各个时代训诫妇女的教科书。海伦与帕里斯私奔后,奥德修斯随即踏上了去特洛伊的征程,一走便是二十年。在此期间,珀涅罗珀一边操持着伊塔刻的政务,一边抚养倔强不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同时还得抵挡一百多个求婚者的纠缠。当奥德修斯历经艰险、战胜各种妖魔、钻出了诸多女神的寝帐而最终返乡后,他杀死了所有求婚者,同时也没有放过妻子身边的十二个女仆。
在史诗中,珀涅罗珀只是一个副线人物。至于她在20年等待中的痛苦与绝望,不仅在史诗中付诸阙如,也是丈夫奥德修斯和儿子忒勒马科斯不屑一顾的。卷一中,忒勒马科斯当众粗鲁地责备母亲:“你还是回到自己房间里做你的事去吧,回到你的织机和纺梭那边,命令女奴们干她们的活;讲话是男人们的事,首先是我的事,因为我是这家的主人。”③ 珀涅罗珀听了这番话居然也不敢再辩,反而认为儿子的话有道理。但阿特伍德却以女性作家天然的理解与同情,以及女性学者理性的价值立场勘破了这一既定历史叙述背后的暗影,将那位终日在家绩麻、以泪洗面的女性推向了历史的聚光灯下,并投注以人文主义的温情关怀。这才有了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女性叙述视角,对“以前不知道的几条印在书上的仿真陈述”(第2页)、“他所讲述的版本”(第2—3页)、“官方的说法”(第3页)进行补充与修正。小说第一部分《低俗艺术》中,珀涅罗珀说道:“我已是死人,因而无所不知”(第2页)。她不再甘于自己只是“一个训诫意味十足的传奇。一根用来敲打其他妇人的棍棒”、“一个或一系列故事”(第3页)的主人公。过去的日子里,在奥德修斯的“圆滑”、“狡诈”、“狐狸般的诡秘”和“狂妄”面前,“我三缄其口;或者,若要张嘴的话,说的都是他的好话。我没有和他作对,没有提出难堪的问题,没穷追不放。在那些岁月里我只要善始善终,而要善始善终最好就是把该锁的门锁好,在一片喧嚣狂暴中安然入眠。”(第3页)“而今既然其他人都气数已尽,就该轮到我来编点儿故事了。”“所以我要讲自己的故事了。”(第4页)这种女性主体的自我言说,正是美国女性主义文论家埃莱娜·肖瓦尔特所倡导的“她们自己的文学”。
小说《珀涅罗珀记》还使第一人称单数“我”和复数“我们”的叙述交相辉映、彼此补充,进一步将个体女性命运的呈现拓展而为对女性集体命运的沉重反思与诘问。阿特伍德采用了别致的艺术形式,使王后珀涅罗珀的身世回忆和她最为信任的十二位贴身女仆诉说自身悲惨命运的合唱歌咏彼此穿插应和,创造出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小说中,王后的回忆由《我的童年》、《我的婚事》、《望穿秋水》、《奥德修斯和忒勒马科斯杀了女仆》等十九个片段组成,女仆的歌咏则包括《小孩儿的哀歌》、《理想爱人》、《奥德修斯的审判》等十组合唱歌词。这一形式戏拟了希腊悲剧的表演程式,通过对古希腊圆形剧场中悲剧演出场景的还原,仿佛使读者真切地看到了那位哀怨而不失庄重节制的珀涅罗珀,听到了围绕在她身边的女仆的哀诉。
关于被吊死的女仆,史诗中是这样描写的:奥德修斯先是残杀了所有求婚者,背着珀涅罗珀叫来女奴,要她们搬走求婚者的尸体,用水和海绵把椅子和餐几擦洗干净,然后准备用长剑砍杀她们:“叫她们全部丧命;那样她们就不能再去想怎样顺从求婚人,同他们私通的一切欢情了”④。而儿子则更有创意:“可不能让她们痛痛快快地死掉”。“他把一根黑色船上的绳索绑在大柱子上,把绳子另一头扔过亭子,把女奴们高高挂起,让她们的脚碰不到地。就像修翎的画眉或鸽子在寻找地方栖宿的时候,陷入深藏在榛莽里的网罗,落到苦痛的卧床上;正是这样女奴们排成一行仰着头,让绳扣拴到每人颈上,遭到惨死;她们用腿挣扎了一会儿,时间没有多长就断气了。”⑤
阿特伍德在“前言”中明确交代了小说与史诗不同的叙述角度:“我选择了将故事的讲述权交给珀涅罗珀和十二个被吊死的女仆。这些女仆组成了齐声咏叹的合唱队,其歌词聚焦于在仔细读过《奥德修纪》后便会油然而生的两个问题:是什么把女仆们推向了绞刑架?珀涅罗珀扮演了何种角色?《奥德修纪》并没有把故事情节交代得严丝合缝,事实上是漏洞百出。一直以来,这些被绞死的女仆便萦绕在我心头”《前言,第2页》。
究竟是什么把女仆们推向了绞刑架?这些女仆自小从做农民、奴隶的双亲那里被买走或拐走,在宫中服务。她们没有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无论是主人还是来访的贵族都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她们。小说第一组合唱歌《跳绳式韵律》中,被吊死的女仆唱道:“我们在空中舞动/我们的赤足在抽搐/诉说着您行事不公”(第6页);第四组合唱歌《忒勒马科斯的诞生》中,她们又唱道:“我们的生活被编织在他的生活中;他是孩子时/我们也是孩子/我们是他的宠物和玩具,假扮的姐妹,他的微不足道的同伴/我们跟着他生长,跟着他嬉笑,跟着他奔跑/尽管我们没有着落,我们饥饿,晒得满脸雀斑,几乎没有肉吃/他理所当然地视我们为他所有,不论是为了/做什么:照顾并服侍他吃饭,为他洗澡,给他逗乐/摇着他睡觉,虽然我们自己的小身子已快散了架/我们哪里知道,当我们在沙地里陪伴他/就在这岩石和山羊遍地的小岛的港口旁边玩耍时/他已注定要成长为屠杀我们的少年冷血杀手……”(第57—58页)她们也有自己的梦想,也渴望“穿亮闪闪的红裙子”,“和所有爱恋着的男子睡觉/奉献给他们无数的亲吻”。然而,从梦中醒来,她们却不得不“重新又开始辛苦劳碌/还得听从命令撩起衣裙/忍受所有流氓无赖的凌辱”(第104页)。
阿特伍德清晰地向读者暗示了女仆和珀涅罗珀命运的联系以及她们本质上的一致性,因为她在把女仆写成月亮女神阿耳特弥斯身边的十二位月亮少女时,是把王后写成月亮女神的化身、月亮少女们的女祭司长的。十二女仆“被奸污以及随后被吊死可能象征了母系的月亮文化遭到了颠覆,颠覆者便是一个正在崛起准备夺取权力,崇拜父神的野蛮人群体”(第138页)。所以,女仆们后来又化身为蛇发、犬首、蝙蝠翼的十二位复仇女神,开始了对奥德修斯的追逐。
因此,珀涅罗珀“我”和十二位女仆“我们”在幽冥中穿越了千年雾瘴向当代读者直接言说的构思,使得小说成为一部真正的“女书”。话语权的转移造成了价值取向、道德评判以及爱情观的深刻逆转,体现了边缘话语对主流话语、“野史”对“正史”的挑战。
作为一部重构经典之作,小说体现出鲜明的互文特征。除了以女仆组成歌队戏仿希腊悲剧的演出形式,⑥ 对地狱冥府的具像化描摹体现出作家对维吉尔史诗《埃涅阿斯纪》和但丁《神曲》的继承,女仆对奥德修斯的追逐令人真切地想起萨特境遇剧《禁闭》中令人不寒而栗的地狱图景之外,作品还和荷马史诗一样,遵照故事发生的自然顺序展开,并通过主、副线的交织营造出一种双重叙述。只不过和史诗不同的是,珀涅罗珀的身世和婚姻生活,以及与女仆共同构筑的友爱世界上升为主体,而奥德修斯所代表的暴力、杀戮和阴谋则下降为由断断续续的道听途说连缀起来的副线内容。这种呼应与对照既使小说与史诗密不可分,又巧妙地实现了价值的转换。
如果说,《奥德修纪》呈现的是动荡、好斗、注重武力的男性世界,那么,《珀涅罗珀记》展示的则是安宁、平和、充满温馨的女性生活。小说叙述中心的变更,有着作家自觉的历史反思意识为支撑。弗吉尼亚·伍尔夫早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已质疑了传统历史叙事虚伪的“宏大”性,认为“现在所有的历史全时常好像有点奇怪,不真实,侧重一面”⑦。她在评价垂维利安教授的《英国史》时批评他的历史无非是“十字军……大学……下议院……百年战争……蔷薇之战……文艺复兴之学者……寺院之解散……田地均分与宗教之争……英国海上霸权之缘由……西班牙无敌舰队……等等”,⑧ 偶尔能进入历史的几个女性不是女王便是贵妇。在福柯的历史谱系中,无论是疯癫、疾病、犯罪还是性等边缘文化因素,亦并不是确定不移的“客观事实”,而是“观念”、“知识”、“话语”的建构。他认为历史是由无数点点滴滴、血肉丰满的个体生活组成的,其中充满了矛盾、断裂、空隙和不连续性。在《知识考古学》中,他这样呼吁:“要重建一种话语,重新找到那些从内部赋予人们所听到的声音以活力的、无声的、悄悄的和无止息的话语。”⑨
由此角度观之,阿特伍德笔下的女性生活,体现的正是女性主义的历史意识,私人生活场景被赋予了不下于攻城掠地的文化意义。珀涅罗珀15岁时即被作为交易对象从一个男人之手转入另一男人之手:“像一袋肉似的被交给了奥德修斯。请注意,是一袋金子包装的肉。一种镀金血布丁。”(第36页)而婚礼则高度仪式化地表现了男性对女性实施掠夺与征服的实质:“床上花团锦簇,门槛洒过了水,祭酒也准备停当。守门人立于门外以防惊恐的新娘夺门而逃,同时也阻止她的亲友闻其尖叫时破门而入。所有这些只是在演戏:仿佛新娘是被拐骗来的,而婚姻的美满就该是一种被认可的掳掠。应该是一种征服,一种对敌人的蹂躏,一次戏仿的杀戮。是应该见血的。”(第39页)
在荷马史诗中,除了珀涅罗珀之外,其他寥寥几位女性如海伦和安德洛玛格同样只是点缀性的配角。然而,阿特伍德的小说却充满诗意地抒写了女性世界的温情,充满了家居细节的种种描摹和女性情感的细腻刻画。珀涅罗珀和十二位贴身女仆合力破坏求婚计划中的配合与默契,使得读者产生了她们既亲如母女、又情同手足的印象。她们虽然“不得不非常小心,说话声压得很低,但那些夜晚却有一种过节的气氛,甚至,有一种欢闹的意味。”(第94页)她们共同品尝夜宵、拆织布、讲故事、猜谜语、编笑话。“在火把摇曳的光线中,我们白天紧绷的面孔变柔和了,举止也有了变化。我们简直成了姐妹。到了清晨,我们的眼眶因缺少睡眠而发黑,我们交换着同谋者会心的微笑,还时常飞快地捏捏彼此的手。”(第104页)
相反,特洛伊的暴力世界却被消解了价值与意义。在《望穿秋水》部分,作家仅以一页左右的篇幅,将倾国倾城的特洛伊之战简约成为毫无意义的非理性荒诞:“街道被血染得殷红,王宫则火光冲天;无辜的童男被扔下悬崖,特洛伊的妇女被作为战利品瓜分,国王普里阿摩斯的女儿们也在其中。”(第69页)由此,阿特伍德通过重述奥德修斯故事,既与史诗形成互文,又对之实行了解构。
小说不仅通过重述神话表现了新的历史观与价值观,这一文化还乡之旅还清晰地呈现出发人深省的现实意义。因为珀涅罗珀的时代虽已远逝,但我们深知:以父权制为中心的社会文化并未随着科技的进步而发生根本的改变。当今世界中,海伦所代表的取悦、依附男性,自我客体化的审美观依然广有市场。作家通过珀涅罗珀之口说道:“正是通过她我才知晓了美人斑、遮阳镜、裙撑、高跟鞋、束窑、比基尼、有氧锻炼、身体穿孔以及吸脂术。然后她便侃侃而谈自己是如何的调皮,引起了多么大的骚动,还有毁了多少男人。有多少帝国因她而崩溃。”(第156页)而奥德修斯也脱胎转世,“做过法国将军,曾是蒙古入侵者,曾是美国的企业巨头,曾是婆罗洲猎取人头的蛮人。他当过影星、发明家、广告商。”(第158页)虽然历史已经走过了近3000年,但两性真正和谐平等的理想还远未实现。在许多国家,性别平等已然是无可更改的法律事实,但男性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却依然以或公开或隐蔽的形式存在着。所以阿特伍德通过珀涅罗珀之口这样感叹道:“世界仍然和我的时代一样凶险,只是悲惨和苦难的范围比以前更深广得多。而人性呢,还是一如既往的浮华。”(第157页)由此,穿越时空的珀涅罗珀提示我们:只要平等和谐的人类理想尚未实现,阿特伍德及其他诸多思想家、文学家等所倡导的女性主义文化观便有其存在的理由。
不难看出,《珀涅罗珀记》通过历史与当下、凡人生活与幽冥世界、真实与荒诞、男性世界的暴力和女性世界的温馨等多重因素的映照与冲突,赋予古老的神话以新的生命,呼应了后现代主义重估价值、让边缘的“他者”发声的趋势。由于重述经典使原定的价值失去了无可置疑的确定性,文学经典因而成为一种可供再生产的丰富资源。经典重述为读者提供了在不同的历史观与文化观之间创造对话的可能性,亦使文本生发出了新的意义层面。多元、异质文化的并存与狂欢,也许正是后现代语境下经典重述的部分意义所在。《珀涅罗珀记》正是由此角度,为我们理解大量涌现的当代重述文本提供了启示。
注释:
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珀涅罗珀记》,韦清琦译,重庆出版社,2005年。本文所有涉及小说内容的引文均来自此版本,以下不再作注,只在文中标明页码。
②傅俊:《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研究》,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第356页。
③④⑤《奥德修纪》,杨宪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第10页,第290页,第290—291页。
⑥有关阿特伍德对古希腊合唱团传统的改写已有专文讨论,参阅陈榕:《阿特伍德〈帕涅罗帕记〉中对古希腊合唱团传统的改写》一文,载《当代外国文学》2006年第3期,第138—146页。
⑦⑧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王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55页,第54页。
⑨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