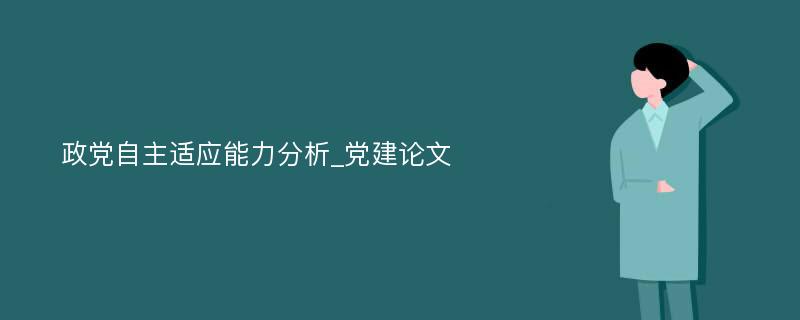
自主性与适应性视角下的政党自我革新能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适应性论文,政党论文,视角论文,自主性论文,自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件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426[2014]04-0058-03 “自我革新”能力堪称决定政党的核心竞争力。对于处于大幅度社会转型的国家而言,政党的“自我革新”能力更为重要。如果执政党僵化,旧的政治体制极可能使国家的发展和社会转型受滞。尤其对于以强大政党组织起来的后发国家而言,政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不仅关系到政党的兴衰,还关系到国家的发展前途和命运。因为作为支撑性主体力量的政党决定着政治体系转型的成败,肩负现代化重任政党的强大往往就意味着国家的强大。在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整体布局中,党的建设不是一项孤立的行动,党的建设绝不是为党建而党建,执政党建设与国家建设是有机一体、相互促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通过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认识,革新了传统理念,将市场经济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改变了传统的将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捆绑的陈旧理念。邓小平同志将之称之为又一次革命。为了更加深刻地认识坚持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在党的十八大上,将“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写入党章。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新时期要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将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要目标,是对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本文从“自我革新”的内涵与目标分析出发,阐述了“自我革新”的主要原则,并提出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的若干建议。 一、自主性与适应性:对于政党“自我革新”的重要分析视角 “自我革新”无疑是政党体现自主性和适应性,使国家发展保持在平稳改革轨道上的关键能力。作为“自我革新”的两个重要的变量,一方面自主性是政党展示适应性的重要前提,如果政党在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的确定中丧失了自主性,迷失了自我,就会成为完全从属或依附于特殊利益或个别社会群体的工具性组织,由此必然会缩小自身原有的社会基础,削弱其对于社会的组织动员能力,而弱化的政党必然无力领导和展开革新,去适应社会的需求。另一方面,有效的适应性也是体现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基本要求。如果政党对社会的适应性下降,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过于脱离社会现实,无法迅速适应环境变化、满足社会需求,负面政治压力也只会越来越大,日益坐大的党外势力和尖锐的社会需求最终也会瓦解政党的自主性,削弱其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政党自我革新的关键在于形成自主性和适应性的相互促进与良性互动循环。由此可见:既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依靠自身力量,主动地解决所面临的意识形态、组织队伍以及党的社会基础等各方面的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问题,提高政党的适应性;又要通过积极有效的改革的成效,来呼应和满足社会需求,提高政党权威,反过来巩固政党自身的自主性。政党必须时刻保持游走于自主性与适应性的双轨之中,使二者相互促进、良性循环、保持平衡。 事实证明,在数百年的政党政治历史变迁中,目前能够活跃在各国政坛上的老牌政党,无一不与时俱进地在自己的社会基础、运行机制、政党政策乃至干部队伍中不断革新。特别是20世纪末期,作为西方政党的发源地,欧洲政坛发生了重要变化:一些传统的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民主党,而以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纷纷打出“第三条道路”、“新中间”的旗号,调整理论政策。不少在剧烈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阶层变化中没有做出自我革新的政党在大浪淘沙中或者消失影踪,或者被边缘化了。另一方面,政党如果盲目地改革,失去了自主性,在变革中迷失了自我,随波逐流,就会被社会冲突撕裂。对于政党中心主义①国家而言,极度危险。即使社会依靠自身内生性动力侥幸成功转型了,但是执政党在社会结构变化中的地位被削弱,被边缘化,甚至沦为在野党,乃至消失。这种政治体制转型也意味着执政党发展的失败。我们看到苏共自从进入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长期停止不前之后,“自我革新”的路径实际上被封闭了。而苏共后期所谓新思维指导下的政治改革已经不是适应性改革,而是自上而下的政治革命。在对政党与政治、经济、社会关系的强制性调整所导致的震荡中,不仅苏共解体,前苏联的国家体系也瓦解了。从某种程度上看,这次政治革命的到来,正是僵化的前苏联体制适应性调整失败,或者说长期“自我革新”失败的结果。从某种程度上看,政治革命的到来正是僵化的前苏联体制适应性调整失败的结果,而并非是我们拒绝“自我革新”的理由。这反过来更是说明,“自我革新”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干可能不犯错,但要承担更加严重的历史责任。 二、“自我革新”的内涵与目标指向 如果说政党的“自我完善”是政治资源的存量开发,那么“自我革新”则重在政治资源的增量开发。对此执政党的“自我革新”经常会遭遇两种类型的风险:一是发展的倒退。例如,有一种观点把当今中国社会种种负面现象归罪于市场经济,认为要回到革命时期党和群众之间密切的党群关系状态,就必须把体制全面回归过去,无视党“自我革新”所取得的显著成绩。这种观点实质上就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成果,无疑会使政党发展置于倒退的风险之中。二是发展的停滞。改革停滞作为一种苟且的态度有时候容易被人忽视,不能及时引起足够的警惕。很显然现在重新回到计划经济的传统体制已然不太现实,而精神懈怠和利益固化的藩篱却无时无刻不在威胁着党和国家的安全。长期一党执政的国家容易存在政党发展停滞综合征,在当前主要表现为看不到新的社会领域和经济领域内党的建设的相对滞后,把政治停滞幻视为社会稳定。对于执政党而言,将自己最初的成功看做是永久的保障无疑是短视和危险的,尤其是在社会表现出表面上稳定的时候,这种政治上的停滞对政党来说很可能就是致命的。同时,精神懈怠背后往往还有利益固化的原因。对此,孙立平认为,当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②党的建设关系全局,只有通过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为党的建设不断注入新的要素,提高党的活力,才能顺利地迈过长期执政和市场经济转型这两道门槛。 作为增量改革,“自我革新”对党员干部、组织设置以及制度建设等多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首先,对于党员干部的角色要求是不断变化的。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员干部需要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能够表现出一定的能力,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发动动员身边的群众带头致富,体现党的先进性。随着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而构成改革阻力的情况下,党员对于信仰的忠诚显得更加重要。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但是,党的纯洁性要求党员干部必须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自己对自己开刀,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其次,对于组织设置而言,党的建设要与经济生产与社会活力相适应,在原有的行政权力为依托的党组织建设基础上,还需要不断加强对非行政权力依托的组织资源的发掘和整合。党组织设置不仅要有比较长远的发展规划,还要有拥有落实规划的基本能力,能够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结构流动,吸纳各方面的积极资源。最后,对于制度建设而言,党的观念、制度与体制需要具有开放性,通过制度建设的方式提高政党质量,使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创新推动成为党的建设的增量资源而非异己力量。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增量改革的“自我革新”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是针对政党改革的前进方向,即党的建设既不能倒退也不能停滞,新的改革要素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党的建设中来;还意味着改革方式的增量调整,即要对既有的改革路径和方式进行大胆突破,找到新的发展路径。例如,在“不争论”、摸着石头过河的增量改革开放阶段,党建探索采取的也是基层创新,高层总结的策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始终摆脱不了“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改革碎片化状态。如果仍然对此津津乐道,不思进取,不做突破,仍然将其作为未来改革唯一依赖的模式,就有可能会造成党的建设的停滞。经过30多年改革后,党的建设需要整体思考、系统推进,不能从单一的具体问题去看问题,而是要求从发展的规律性上、从一般性意义上、从系统上去看问题。例如,党内民主的分层改革,必须保持一定的平衡,离开了党内高层对于民主探索的良好支持氛围,党内基层民主空间是有限的。即使是对于党内基层民主的探索,也需要系统发展的眼光。民主是由授权、决策、管理、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组成,是一项系统工程,所有环节环环相扣,共同构成一个体系。在改革攻坚阶段,也要防止党的建设走向“碎片化”,需要有统筹全局的设计机构,不断总结各地的探索经验,把改革的成果通过一定的形式固定下来,构建党的建设发展的完整体系。要把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开发党的建设增量改革的两种有效手段,实现两者互为补充、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执政党必须有明确而坚定的自我规定性才能引领国家的整体进步与发展。从现代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共产党增强“自我革新”能力的重要战略目标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推进国家的现代化。也就是要使执政党逐步从利益和权力过于集中的体制中抽身出来,通过政治结构中的政党权威来加强国家结构的自主性。从目前改革开放的目标来看,中国共产党增强“自我革新”能力的目标指向,可以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去分析:一方面,增强“自我革新”能力,要有很强的政党忧患意识、战略意识和理想追求。如果说1978年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穷则思变”的无奈之举,那么今天已经不再是一穷二白。目前改革所寻求的进步与发展,更多地不是从摆脱危机出发,而是从避免或防范危机出发,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缺乏强烈的心理动力与精神力量。因而,增强“自我革新”能力的主观目标,在于破除当下小富即安和精神懈怠的心理与精神状态。这意味着中国要创造新一轮的深度改革和有效发展,就必须破除缺乏进取精神的心理格局。③ 另一方面,增强“自我革新”能力的客观目标,是要通过加强执政党建设,为改革输入源源不断的动力,走出各种陷阱,防止改革进入停滞与倒退状态。目前,中国的发展与改革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转型陷阱”的双重考验。前者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这就意味传统的增长方式必须要有革新,党员干部要有本领恐慌感和学习紧迫感,各级党组织要努力开发自身的潜能,把学习作为一种组织的使命和责任来对待,通过科学发展来实现突破,实现党建资源的增量开发。而后者则是“在改革和转型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利益固化的格局,尤其是像我们这样渐进式的改革,就更容易形成既得利益格局。这样的基本利益格局形成后就要求不要往前走了,要维持现状,然后希望把我们认为所谓过渡型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体制。”④“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是利益固化的藩篱,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这种陷阱就更加需要党通过增强“自我革新”的能力,开发新的增量改革来避开。为此,需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益均衡机制,防止社会力量的失衡和利益关系的失衡;需要促进公民意识和社会组织的发育,形成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方式;需要促进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等等。同时,还需要通过党的组织机制的“自我革新”促进社会流动,防止社会结构固化;通过党的工作方式的“自我革新”最终重建社会的基础秩序。 三、“自我革新”的主要原则 经过三十年的实践,中国政治体系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治理经验,也具有了更强的抗风险与抵御危机的能力。这些资源在提升中国政治的有效性的同时,自然也累积起比较扎实的“自我革新”能力的基础。但是对于超大规模社会的执政党的“自我革新”所要处的环境和要考虑的因素是极为复杂的。从整体上看,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关系仍然是对于执政党自我革新的所要处理的基本问题。一言以蔽之,既要大胆探索,有所突破才能推动发展,但是还必须防范风险,要实现存量优化和增量增长的统一,凝聚社会合力,减少革新的冲击力。为此,“自我革新”必须保持以下三个“统一”: 1.大胆探索与防范风险的统一 风险并不完全是政党的自身革新所带来的,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借助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人类社会应对风险的能力提高了,但同时又面临着治理带来的新类型风险。因此,对于任何执政党而言,对于由不可控的力量引发的风险和危机,都要有体制、机制、人才以及心理上的充分准备。党的“自我革新”过程,由于新的资源整合往往是一种试错的过程,因此会在短时间内增加原有体制的不确定性,所以风险系数会被变革放大。为此,要更加重视忧患意识和风险观念,要有处置危机的方案、体制与物质准备。一个善于“自我革新”的执政党,必须将改革与改革中的风险统一起来,综合考虑,有能力驾驭风险,预防和抵御危机,在处置危机中赢得社会的支持和民众的认同。中国共产党历来把抵御风险、预防危机作为其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努力不断地加强和提高。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各个方面所带来的风险与危机,既有来自自然的,也有来自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由于中国政治体系具有内在的稳定性和强大的领导力,这些风险和危机不但没有动摇党的领导,相反使得党在有效抵御风险和危机中获得了巩固和发展,改革的成果获得了有效的累积。这不能不说是执政党“自我革新”能力的体现。这种能力一方面来自党的功能与结构的有效;另一方面来自党所拥有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以及比较丰厚的领导人才的储备。 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当前有些风险需要给予高度重视:一是党组织出现信任危机的风险。二是党内政治局面出现混乱的风险。三是党发生分裂的风险。这些风险的主要表现有两种:一种是思想上发生分裂;另一种是组织上发生分裂。四是党发生质变的风险。⑤在对一些基本问题的判断上,党内的中层与基层,以及党内高层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各种不同意见的分歧。不过党对于这种风险已经有一定的准备措施,例如十八大提出的通过党代表提案制度、进一步深化党代表大会制度对于解决党内不同意见的制度化表达有着深远意义。从当前“自我革新”的风险控制与自我创新动力源角度看,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内部已经有了一定的默契,也可以说是有了一定的大致分工,中央组织更加注重维稳、控制风险,地方和基层组织更加重视创新活力。这种模式的长期存在离不开良好的上下互动,如果上级党组织费力地抓住权力不放,不支持创新探索,那么地方和基层组织的改革就无法提供更多的自由、责任和参与权,只能是维持谨小慎微、零碎、浅层次政治改革,这显然不利于增强党的“自我更新”能力。 2.存量优化与增量提升的统一 如何处理好党建资源的存量优化和增量提升的关系,是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必须要重视的问题。因为,如果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不能有效整合,“自我革新”就会带来资源的分裂与浪费。有人认为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是无法解决的。例如,美国学者亨廷顿就认为,倘若政党领袖试图将新的集团吸收进入一党制的框架内,那么,虽然他们的队伍扩大了,但其代价是政党团结、纪律和热情的削弱。⑥确实这些年来人们不断在提问,执政党的规模在逐年扩大,政党能力是否获得同步提高?这一问题甚至已经被纳入了新一届中央的议事日程。中共中央政治局在2013年1月28日召开会议,要求强化党员管理,严格党内组织生活,严明党的纪律,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努力建设一支规模适度、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员队伍。”我们认为党员的数量与规模问题是对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的一次重要考验。所谓适度的党员规模的合理标准就是,党员数量的增加必须是边际效益递增,而非递减的。而单纯的存量优化或者增量提升都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如果只是简单地控制党员发展速度,降低党员数量,那么表面上看似臃肿的党员规模会得到控制,但是现有党员队伍人员老化、管理体制僵化等问题仍然无法解决。关键是要通过有效的“自我革新”,使党员管理体制建设能够把党员队伍的存量优化与增量提升结合起来。通过严格规范党员管理制度,按照党章要求,清除不合格党员,不能让一小部分不合格党员绑架全党;要对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开放入党渠道,通过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形成党员队伍有序流动的格局。 3.凝聚合力与减少冲击的统一 在跌宕起伏的社会变革浪潮中,无论是确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还是建立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每一次突破都有一个凝聚共识的过程作为思想准备。没有共识,不可能从改革开放激荡的30多年走到今天。执政党在增量改革中的共识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凝聚共识,减少改革的阻力,任何时候都是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的关键要素之一。由于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的调整变革,人们的价值观念呈现多元、多样、多变的复杂局面,这自然会影响到党内,影响到对党的建设共识。我们认为保持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统一,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就会形成党的建设的最大共识。党的历史经验说明,只要人民群众真心拥护,党的建设就会获得源源不断的资源,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是形成这种共识的思想保障。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郑重告诫全党:“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检验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任何时候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只有党将人民利益置于最高的地位,才能形成共识,才能保持充沛的“自我革新”动力,才能形成强大的“自我革新”能力。坚持和创新群众路线,保持和群众的密切联系,是增强党的“自我革新”能力的最为关键的途径。 注释: ①以英国和美国的经验为基础而产生的“社会中心主义”以及以法国、德国和日本经验为基础的“国家中心主义”完全无法诠释清楚近代以来政党在中国制度变迁路径与当代中国政治结构中的轴心地位。因此杨光斌等学者提出政党建构政治秩序进而创建国家结构使得中国的国家建设总体上更多地体现出“政党中心主义”的色彩。但是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概念,政党中心主义概念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参见杨光斌.政治变革中的国家和制度[M].北京:中国编译出版社,2011. ②孙立平.“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J].开放时代,2012,(3):125-127. ③林尚立.党与人民关系决定中国的未来——基于中国自我革新能力的考察,[J].当代世界,2013,(3):2-3. ④孙立平.转型陷阱:中国面临的制约[N].南方都市报,2012-1-1. ⑤许耀桐,赵麟斌.关于发展党内民主防范风险问题研究[J].新视野,2009,(7):52-53.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356.标签:党建论文; 日本政党论文; 美国政党论文; 英国政党论文; 德国政党论文; 政治论文; 自我分析论文; 中国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风险社会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社会资源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