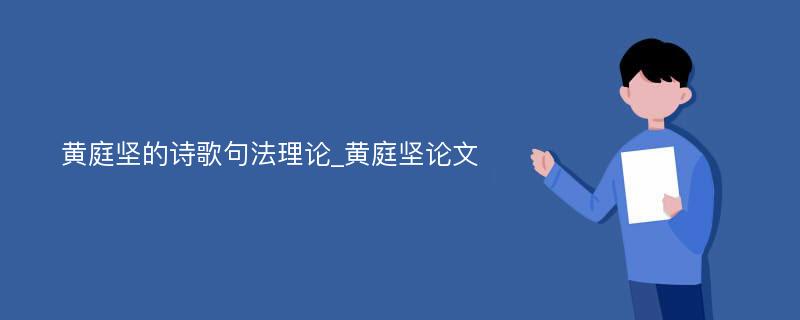
黄庭坚的诗歌句法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庭坚论文,句法论文,诗歌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从古到今,黄庭坚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但在有关的研究中,黄庭坚关于诗歌句法的看法却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注意到了,也没有作系统的论述。实际上,诗歌的句法问题是黄庭坚诗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仅据《山谷老人刀笔》、《豫章黄先生论文集》统计,句法一词就出现了不下20次,这还不算与句法基本同义的句律一词。如再加上诗话中的有关材料,黄庭坚对句法的论述就相当可观了。虽然宋代最先提“句法”一说的不是黄庭坚,但是,在宋代,黄庭坚我句法理论无疑是最丰富、最系统、影响最大的。
一
说到诗歌的句法,我们首先要弄清黄庭坚所说的句法指的是什么。黄庭坚始终没有对句法一词下过定义,但是,从他的一些具体论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出他所说的诗歌的句法至少包括了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1.指诗句中的拟人一类的修辞手法。《观林诗话》载:“山谷云:余从半山老人得古诗句法云:‘春风取花去,酬我以清阴。’”黄庭坚所说的句法,就是以春风作句子的行为主语,“我”作被动的接受者。这种手法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拟人。黄庭坚的这种句法,就是吴沆后来在《环溪诗话》卷中所说的“以物为人”法。吴沆说:“山谷诗文中无非以物为人者,此所以擅一时之名,而度越流辈也。……如‘春至不窥圆,黄鹂颇三请’是用主人三请事;如咏竹云:‘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是用正事……又如‘残暑已趋装,好风方来归’、‘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谓残暑趋装,好风来归……”吴沆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黄庭坚的这一手法,可见黄庭坚是将这一手法看作是诗歌普遍的句法的。
2.指诗句安排节奏的方法。范温《潜溪诗眼》载:“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昔尝问山谷‘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山谷云:不如‘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此专论句法,不论义理,盖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也,此句法出《黄庭经》。”这里的意思说得很清楚,黄庭坚之所以认为“千岩无人万;壑静,十步回头五步坐”比“耕田欲寸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好,是因为“千岩”一联更能鲜明地体现“七言诗四字三字作两节”的特点(注:杜甫《秋夜》云:“露下天高秋气清,空山独夜旅魂惊。疏灯自照孤帆内,新月犹悬双杵鸣。南菊再逢人卧病,北书不至雁无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银汉遥应接凤城。”方回评论道:“此诗中四句自是一家句法‘千岩无人万壑静,三步回头五步空(原文如此)’是也。‘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亦是也。山谷得之,则古诗用为‘沧江鸥鹭野心性,阴壑虎豹雄牙须’亦是也。盖上四字下三字本是两句,今以合为一句,而中不相粘,实则不可拆离也。试先读下三字,则句法截然可见。”(《瀛奎律髓》卷十二)方回的这段话对我们理解黄庭坚的看法不无帮助。),因此范温认为黄庭坚是“专论回法,不论义理”。由此也可以看出,在黄庭坚看来,诗句的节奏是句法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观点在别的材料中也可以得到证明。如《紫微诗话》载:“或称鲁直‘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此乃可言至耳。鲁直自以此犹砌合,须‘石吾甚爱之,勿遗牛砺角。盾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以为极至耳。”黄庭坚颇为自负的这四句诗,其主要的特色在于第一句和第三句打破了五言诗句通常的上二下三作两节的惯例,代之以上一下四、上三下二作两节的新节奏。联系上文,可见黄庭坚所谓的句法,诗句节奏变化,打破常规的方法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黄庭坚的其他一些诗句,如“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邀陶渊明把酒碗,送陆修静过虎溪”等也是属于这类句法。
3.指持句的对仗方法。《潜夫诗话》载:“山谷教人云:‘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可以为律诗之法。”所谓律诗之法,实际上就是律诗的句法。法在何处?就在借对。九方皋之“九方”在这里本为姓,但其字面为数量词,于是借以与上句“千里”的数量词相对。他的“青春白日无公事,紫燕黄鹂俱好音”(《次韵盖郎中率郭郎中休官二首》其二)等也是这一句法的运用。
4.指诗句声律的变化方法。《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十五“山谷上”引《禁脔》云:“鲁直换字对句法,如‘只今满坐且尊酒,后夜此堂空明月’、‘清谈落笔一万字,白眼举觞三百杯’、‘田中谁问不纳履,坐上适来何处蝇’……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欲其气挺然不群,前此未有人作此体,独鲁直变之。”这种通过上下句平仄的变化来达到“欲其体挺然不群”的效果的方法,我们现在称之为拗救。黄庭坚对这种改变诗句通常的平仄来取得特殊的艺术效果的做法是颇为得意的,并视之为独得之秘。《王直方诗话》载:“山谷谓洪龟父云:‘甥最爱老舅诗中何等篇?’龟父举‘蜂房各自开户牖,蚁穴或梦封侯王’及‘黄流不解涴明月,碧树为我生凉秋’,以为绝类工部。山谷云:‘得之矣’。”洪龟父所举的两联诗,就是今天常说的拗律。这两联完全打破了一般七言律诗的平仄规定,两个下句都是先四仄后三平,故意犯三平调之忌,字面上也似对非对。这种句法就是“以律而差拗,于拗之中又有律”,从而可以取得“健而多奇”的艺术效果。
5.指诗句的语言风格。黄庭坚在《与甥驹父九首》之九说:“作省题诗,尤当用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诗也。”黄庭坚没有具体指明杜甫省题诗句法上的特点,但是,熟悉杜甫省题诗的人使会知道,杜的省题诗的主要特点是平正典雅。黄庭坚所说的句法,可能就是指这种风格。这种说法,与深受其影响的葛立方在《韵语阳秋》卷二中所说的“应制诗非他诗比,自是一家句法,大抵不出于典实富艳尔……若作清癯平淡之语,终不近尔”的意思差不多。黄庭坚自己也直接说过这样的话:“驹父外甥推官:得来书并寄近诗,句甚秀而气有余,慰喜不可言。甥风骨清润,似吾家尊行中有文者。忽见句法如此,殆欲不孤老舅此意。”(注:《与洪甥驹父九首》之五,《山谷老人刀笔》卷一。)黄庭坚在这里所说的句法显指诗句的风格。
以上五个方面是黄庭坚诗歌句法的最基本内容,这些内容是我们根据诗话著作和黄庭坚本人的作品中明确或间接透露出黄庭坚句法思想的资料归纳出来的。实际上,黄庭坚未作说明,现存资料没有直接也没有间接说明黄庭坚句法具体所指的肯定丰富得多。他在诗文中二十多处说到的句法,肯定有不同所指,但由于他没有一处加以说明,因此,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他所说的句法到底有多少具体的含义。不过,仅从上面我们所能基本确定的几方面的内容来看,黄庭坚所说的句法,含义是很广的。
虽然黄庭坚所说的句法含义甚广,但有一点是比较明确的,即它是指对诗句的艺术处理,是诗歌运用语言的艺术,并非笼统指作诗的方法。他所说的句法与诗法并不能同日而语。何以见得?陈师道《后山诗话》载:“黄庭坚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尔。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从这几句话可以明显地看出,在黄庭坚的观念中,诗法与句法是不同的。那么这种区别是什么呢?黄庭坚对此未作直接的说明,但从一些间接的材料中,我们推测他所说的诗法可能指的是诗的篇章布局等,不同于对诗句的艺术处理。既然黄庭坚说“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那么,知道了“韩之文法”,也就知道了“杜之诗法”指的是什么了。范温《潜溪诗眼》中有一段话刚好可以作为黄庭坚“杜之诗法,韩之文法”的注释:“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如杜子美《赠韦见素》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此诗前贤录为压卷,盖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室,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由此可知,黄庭坚所说的诗法,指的是诗的立意布局,而不是诗的语言。黄庭坚在《论作诗文》中说:“但始学诗,要须每作一篇,辄须立一大意,长篇须曲折三致焉,乃成文章耳。”这也说的是诗法。作为诗法概念意指命意曲折的另一佐证是曾季貍《艇斋诗话》中记载的一段话:“人问韩子苍诗法,苍举唐人诗‘打起黄莺儿,莫叫枝上啼。几回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黄庭坚所说的诗法与句法的区别,于此可见。
二
在黄庭的观念中,诗的句法在诗的创作与评论中是具有特殊地位的。
首先,句法是黄庭坚认识诗歌,进行诗歌评论的一个独特角度。作为宋代一位具有特殊地位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黄庭坚对诗歌的评论角度无疑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是独特的,他的一些评论角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便如,他从无一字无来处来评论杜诗,不仅超越了杜诗集大成、每饭未尝忘君等传统说法,而且也开辟了认识杜诗的新角度,成为宋代最著名的论杜观点之一。而从句法的角度来广泛地论诗,也是黄庭坚在论诗角度上的一个新开拓。《紫微诗话》说:“渊明、退之诗,句法分明,卓然异众,惟鲁直为能深识之。”可见黄庭坚对诗的句法是别有会心,独具只眼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认识诗歌的独特性。
在黄庭坚的诗歌评论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言论:
诗来清吹拂衣巾,句法词锋觉有神。今日相看青眼旧,它年肯作白头新。(《次韵奉答少微纪赠》)
句法俊逸清新,词源广大精神。建安才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再用前韵赠高子勉》其三)
(梅圣俞)此篇是得意处,其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它人无此功也。(《跋雷太简梅圣俞诗》)这些话都是从句法的角度来评诗的。那么,黄庭坚在从句法的角度来评诗时,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回答是肯定的。其具体的标准是:
第一,诗歌是否有句法,这是衡量诗人作品是否优秀的重要尺度。黄庭坚在《答何静翁书》中说:“所寄诗,醇淡而有句法。所论史事不随世许可,取明于己者,而论古人语约而意深。文章之法度盖当如此。”说何静翁的诗有句法,显然就是说他的诗写得不错,有法度。这就对他的诗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实际上也肯定了他是懂句法的。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二载:“鲁直谓东坡作诗未知句法。”在一般人看来,作为宋代最杰出的诗人苏轼竟然不知句法,这岂不是胡说八道?金人王若虚就说:“东坡,文中之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而其所谓法者,果安出哉?”(《滹南诗话》卷二)王若虚的这一段话不一定是针对葛立方说的,但它可以说明,在宋代,黄庭坚认为苏轼不知句法的说法是相当流行的,不然王若虚就不会如此大动干戈了。这也就同时说明黄庭坚的这一说法恐怕是事出有因,不大可能是无稽之谈。(注:黄庭坚的这一说法在南宋中后期流传极广,但又是与黄庭坚自己的说法有出入的。黄庭坚曾在他那首有名的《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中明确地说苏轼“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对苏轼推崇备至。这种流传的说法恐怕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诗人不知句法,诗歌就不可能有句法,这是理所当然的。上面一正一反的两条材料说明,黄庭坚对诗人知句法和诗歌有句法是多么重视。他评价陈师道“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答王子飞书》),认为梅尧臣的诗“用字稳实,句法刻厉而有和气”(《跋雷太简梅圣俞诗》)等,都是肯定他们的诗有句法,是优秀之作,而不是随便写出来的。那么,怎样才能算是有句法?当然就是广泛地掌握了造句的技巧,对上述所举的句法内容的各个方面都有较深入的体会。
第二,句法简易,是诗美的最高境界。有句法,固然是优秀诗歌必备的条件,这反映了黄庭坚对技巧的肯定,但这并不是诗的最高境界。黄庭坚认为,诗歌的最高境界是句法简易。他在《与王观复书三首》其二中对王观复说:“所寄诗多佳句,犹恨雕琢功多耳。但熟观杜子美到夔州后古律诗,便得句法简易而大巧出焉,平淡而山高水深,似欲不可企及,文章成就更无斧凿痕乃为佳作耳。”什么是句法简易?从他的话中我们不难看出,就是指诗句表面上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山高水深,不可企及。也就是说,诗句已看不出技巧来,但正是在这无技巧的地方是大巧的所在。据《王直方诗话》载:“洪龟父言:山谷于退之少所许可,最爱其《南溪始泛》,以为有诗人句律之深意。”这很有点奇怪,黄庭坚对韩愈诗一向是颇有微词的,但为什么偏偏认为《南溪始泛》“有句律之深意”呢?其实,读一读韩诗就不觉得奇怪了。韩愈的《南溪始泛》共三首,是韩晚年的作品。现录一首,可见一斑:
南溪亦清驶,而无楫与舟。山农惊见之,随我观不休。不惟儿童辈,或有杖白头。馈我笼中瓜,劝我此淹留。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幸有用余俸,置居在西畴。囷仓米谷满,未有旦夕忧。上去无得得,下来亦悠悠。但恐烦里闾,时有缓钯投。愿为同社人,鸡豚燕春秋。(其二)
韩诗一向是以“横空盘硬语”、“险语破鬼胆”著称的。但在这首诗中,硬语与险语不见,难字与离奇全无,诗句平易单纯,平淡自然。《蔡宽夫诗话》说:“退之诗豪健雄放,自成一家,世特恨其深婉不足。《南溪始泛》三篇乃末年所作,独为闲远,有渊明风气。”至此,我们就不难明白黄庭坚为什么认为《南溪始泛》“有诗人句律之深意”了。
有句法与句法简易,是黄庭坚对诗歌艺术两种境界的认识与评价,前者是对一般优秀诗歌的期望,后者是对诗歌极品的要求。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黄庭坚的这种句法思想是与他的整个诗学思想一致的。他曾说过:“宁律不谐,而不可使句弱;用字不工,不可使语俗。此庾开府之所长也。然有意于诗也。至于渊明,则所谓不烦绳削而自合者。”(《题意可诗后》)有法,就可以做到句健不弱,这是有意为诗,虽为佳作,但不是最高境界;陶渊明的诗“不烦绳削而自合”,不讲法而法自在,从必然王国走向了自由王国,这才是诗的极致。
其次,黄庭坚认为,对于初学者来说,句法又是学诗的重要途径。正如吕本中所说的那样:“前人文章各自一种句法……学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辈。”(《童蒙诗训》)黄庭坚自云他年轻时学诗“自往见谢公,论诗得濠梁”(注:《奉答谢公静与荣子邕论狄元规孙少述诗长韵》,《豫章黄先生论文集》卷二。)。谢公就是谢师厚,得濠梁就是得句法,《艇斋诗话》“山谷诗妙天下,然自谓得句法于谢师厚”的话可证。有了这样的经验,再加上后来对诗歌句法的进一步认识,因此,他希望后辈一定要在句法上用功,尤其是对杜甫诗的句法,更应该加以精通,这样才能在诗歌创作上取得成绩。当后辈孙克写信向他求教时,他说:“请读老杜诗,精其句法。每作一篇,必使有意为一篇之主,乃能成一家,不徒老笔砚玩岁月矣。”(《与孙克秀才》)在《与洪甥驹父九首》之九这封信中,他说:“作省题诗,尤当老杜句法,若有鼻孔者,便知是好诗也。”杜诗的句法是学诗的津梁,学到了杜诗的句法,成为诗歌创作的高手自然也就不难了。所以他说:“(陈师道)作诗渊源,得老杜句法,今之诗人不能当也。”(《答王子飞书》)
黄庭坚之所以特别注重对杜甫句法的学习,固然与宋代尊崇杜甫的风气有关,同时也与他的家传的密切的关系。《洪驹父诗话》说:“山谷父亚夫(黄庶)诗自有句法……山谷句法高妙,盖其源流有所自云。”如前所述,黄庭坚也从谢师厚处得句法,而谢是黄庭坚的岳丈。《后山诗话》说:“唐人不学杜诗,惟唐彦谦与今黄亚夫庶、谢师厚景初学之。鲁直,黄之子,谢之婿也。其于二父,犹子美之于审言也。”这段话就把黄庭坚重视杜诗句法的家学渊源揭示出来了。
诗的句法固然重要,但在诗歌创作中,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人品。《潘子真诗话》中的一段话就鲜明地表明了黄庭坚的这一观点:“山谷尝谓余言: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发而然。”在黄庭坚看来,杜诗之所以能做到“句律精深”,句法非凡,不是单纯的艺术修养深厚的问题,而是他内心“未尝一日不在本朝”、“忠义之气”作用的结果。“忠义之气”是因,“句律精深”是果。这两者的轻重不言而喻。黄庭坚在《跋东坡书》中的另一段从反面表明了这一观点:“往时许昌节度使薛能能诗,号雄健,时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辈,高自贤至,乃云:‘我生若在开元日,争遣名为李翰林。’此所谓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也。”时得前人句法,这当然是薛能的长处,按照黄庭坚对诗歌的一般看法,似乎可以算是优秀之作。然而,以为得句法就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其结果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由此看来,有人品,往往可以做到句律精深;无人品,有句法也可能成为诗人中的败类。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会发现以前学术界将黄庭坚斥为形式主义诗人的观点是多么可笑。
由上可知,黄庭坚在学习句法上已建立起了一整套内外兼修的理论,这套理论既是他对前人创作经验的总结,又是他自身的创作体会。由于有了具体理论的指导,黄庭坚的诗在句法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赢得了宋人的普遍称赞。《豫章先生传赞》云:“山谷自黔州以后,句法尤高,笔热放纵,实天下之奇作。自宋兴以来,一人而已矣。”(注:《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引。)“山谷老人……至中年以后,句律超妙入神,于诗人有开辟之功。”(《五总志》)
三
在中国古代诗歌句法理论史上,黄庭坚是有特殊贡献的。
黄庭坚对句法思想的贡献在于,一是将句法视为一种认识诗歌的新角度、进行诗歌批评的新尺度,这就为认识诗歌、批评诗歌找到了新角度、新标准,这使他的句法论远远超越了一些以启蒙为主要目的的诗学著作(如晚唐五代北宋初的诗格),而更具理论色彩。二是更加明确、更加突出地将学句法看作是一种教育后学的方式和手段。三是确立了以杜甫为句法理论的中心话题的地位。在黄庭坚的影响下,宋人谈句法蔚然成风,出现了诸如惠洪、吕本中、吴沆等句法名家。所谓“句法之学,自是一家工夫”这样独特的诗学思想,正是黄庭坚直接影响的结果。翻开《诗人玉屑》卷三、卷四专录句法资料的两卷,到处都可以看到黄庭坚句法思想的影子。
黄庭坚对诗歌句法的重视,表明了他对诗歌语言的高度敏感,也表明了他是真正把诗作为语言艺术来看待的。他强调句法,侧重点多在于语言的变异,以造成一种语言陌生化的效果。从他对诗歌句法的强调来看,在他的观念中,似乎隐含着这样的诗学思想,即诗歌的意义一定程度上存在于诗歌的句法中。句法在诗歌中有着一定的独立的存在价值。他所说的句法,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某些构造规律的总结,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的指导意义,但又并非一成不变的公式。他强调有句法,但更强调无句法(句法简易),并且强调诗人的品德修养。这应该说是符合诗歌创作的规律的,同时也使他与一般将句法看作是单纯的艺术技巧的看法区别开来了。他强调诗歌的句法,并没有把诗歌简单地看作是表现道德思想的工具,而认为诗歌由于句法的存在而变得具有独立的艺术价值。这种思想又是与文以载道的观念大异其趣的。这样,他实际上已将“形式主义”与言志派调和起来了。
当然,黄庭坚强调句法也不是没有偏颇之处,正如王若虚所说:“东坡,文中之龙也,理妙万物,气吞九州,纵横奔放,若游戏然,莫可测其端倪。鲁直区区持斤斧准绳之说,随其后而与之争,至谓未知句法。东坡未知句法,世岂复有诗人?而深所谓法者,果安出哉?……鲁直欲为东坡之迈往而不能,于是高谈句律,旁出样度,务以自立而相抗,然不免居其下也。”(《滹南诗话》卷二)王若虚把黄庭坚的“高谈句律”理解为与苏轼对抗,这固然是受了南宋以来苏黄对立论的影响,不足信,但从他的这段话中,我们倒可以看出,黄庭坚如果单纯以句法论诗,有时会失于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