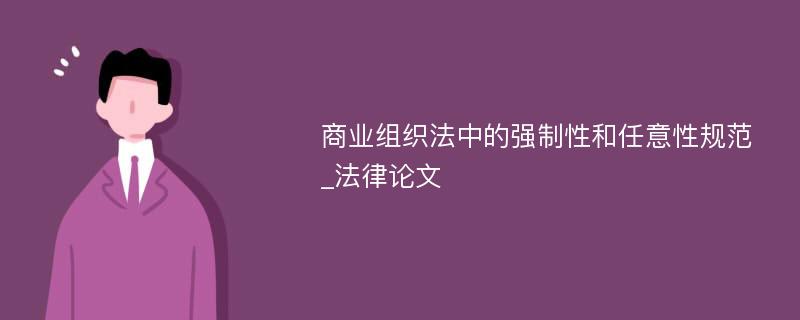
商事组织法中的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组织法论文,商事论文,强制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公司法立法的相关学术讨论中,学界常把减少强制性规范的数量看作衡量立法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准。例如,2005年公司法修订得到学界盛赞,其中一主要原因是学者看到该法律修订“处处虑及公司参与方之谈判空间,大大拓宽了任意性规范之适用范围。”①在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国家对社会的严格管控到市民社会自主发展的语境下,这样的认识当然不无道理。但是,从学术研究与立法讨论互动的角度看,这种认识显然失之粗略。②上述认识有一个重要前提尚需澄清,即任意性规范是促进自由的、而强制性规范则相反。迄今为止的理论探讨,学者仍然把任意性规范看作是公司法等商事组织法立法最合适的工具——既然商事组织法要促进自由选择,那么任意性规范最大限度地允许当事人设定商事组织内部治理的方式,自然是最能促进自由选择的规范类型。换言之,讨论各方共享一个假设,即任意性规范是促进自由选择的、而强制性规范则相反。③本文的重点是反思上述假设,即讨论是否可以将任意性规范一律看作是促进自由选择的、而强制性规范则相反。 法律规范依其强制程度可以分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是当事人必须遵守、不能依当事人意志选择变更或拒绝的规范;任意性规范则允许当事人选择变更或排除该规范中设定的内容。后者因其强制程度弱、鼓励当事人设定其权利内涵而被看作是赋权性(enabling)规范。④学界通说认为公司法同时包含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⑤不少研究对立法采纳强制性规范持怀疑态度,对采纳任意性规范支持鼓励。⑥但是,是否任意性规范可以一律看作是促进自由、而强制性规范则相反?商事组织法——特别是那些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他组织形式和确定内容的任意性规范——是否体现强制、如何体现强制? 对上面提出的问题,本文结合公司治理理论和法律现实主义研究的相关讨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并以我国《公司法》确立的董事会制度为例展示了允许个人选择变更或者排除的任意性规范恰恰体现了强制。事实上,打破任意性规范和促进自由选择之间虚假的对应关系、让妨碍自由选择的原因显明出来,在立法、司法过程里直面这些问题,商事立法才更有可能促进自由。更一般性地讲,如何配置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问题应从关注规范类型的形式分析拓展到对法律的实效进行分析。 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先回溯了公司治理已有的对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研究,特别是公司的合同理论;第二部分引入法律现实主义理论和当代批判法学理论来深入讨论任意性规范的强制效果;第三部分以我国公司法上的董事会制度为例,讨论任意性规范何以导致剥夺中小股东的强制性后果;第四部分以探讨立法如何从形式主义的规范类型划分转向依赖法律效果的实质分析为依据作结。 一 公司法中的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 (一)法律经济学语境中商事组织法的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 法律经济学理论强调:商事组织法最终的目的是为人们提供合作的模板,故而应允许当事人对商事组织的形式自行决定而不是以立法代替个人的自由选择。减少法律强制性规范、增加任意性规范故此常常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的的理想工具。公司法学者甚至因此将公司法性质认定为赋权法——法律限制人们选择公司治理内容的强制性规范自然只能当作例外。 对公司法应促进自由选择的考察,来自法律经济学者对商业组织历史的认识和法律学者对经济学者提出的企业理论的反思。按照法律经济学者的考察,从最早的合伙到后来以现代公司为主的形形色色的商事组织,反映了人们在商业领域的自由选择的诉求。学者将股份公司的兴起看作是现代工业生产条件下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因为股份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展示了在大规模工业生产条件下的高效率。而直接规定该商事组织形式的商事组织法,则被认为是尊重自由选择。不少研究者试图展示迄今为止的欧美商事组织法变迁实际体现了自由选择的实现。⑦罗曼诺教授考察美国公司法发展历程,着重指出美国公司法赋权法的特征与联邦体制下的州际竞争的关联。这种思路更把公司法的发展看成一种类似在生物互相竞争中进化的过程,而是否促进自由选择则变成了某个具体的公司立法是否能够胜出的检验标准。⑧从这个角度看,商事组织法作为市场得以存续和发展的基础之一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促进自由选择为目的。⑨ 法律在商业组织中保护个人的自由选择,在经济学的企业理论中对应的是把商业组织看做是个人通过合同的方式来组织合作,也就是公司合同束(nexus of contract)理论。简而言之,公司被看作是一系列被反复遵循和履行的合同,而公司法和其他类型的商事组织法的实质是一系列当事人自由同意并选择的默示合同条款。如耶鲁大学的汉斯曼教授和哈佛大学的克拉克曼教授在讨论商事组织法的功用时所言:“在每个市场经济体中,法律都会规定一系列标准形式的法律实体。在美国,这些实体包括商业公司、合作社、非盈利组织、市政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合伙、有限合伙、私人信托、慈善信托和婚姻等。这些法律实体大体是标准形式的合同,为所有人、经理人和债权人等当事人提供默示合同条款。”⑩在经济学领域,自从阿尔奇安和登姆赛茨把公司定义为“在团队生产过程里的集中化的合同代理人”后,詹森和麦克林在《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一文中正式提出了合同束这一术语。公司合同束理论早期的这些研究是实证性的,企业理论研究者观察到公司治理结构的很多制度可以降低代理成本,故而把这些制度看作是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公司的股东和经理人事先看到了代理成本的问题,公司治理结构则是双方主动选择的最小化代理成本的结果。(11)这种看法的基础是制度经济学对效率的基本认识:若制度保障人人都可以自由选择,则可达到最优效率。保障自由选择的制度,既包括公司治理的一些基本架构,例如保障投资者对管理者进行监督的董事会制度,也包括法律对相关各方的管制和干预。(12) 公司合同束理论后来的研究逐渐出现规范性的指向。法律经济学学者伊斯特布鲁克和费舍认为,公司不仅可用合同束来描述,而且法律应该保障公司按照相关各方自由选择的方式来运作。他们进而提出,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裁判,其内容最好是反映相关各方默示同意的合同内容,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相关各方的交易成本。(13)合同束理论下的理想公司法包括下列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公司法应该体现相关各方没有交易成本情形下的谈判结果;二是公司法应作为相关各方的一份默示合同,亦即公司法规定可供其选用但并不强制选用。前者的目的是节约交易成本:有了公司法,相关各方就不必每次都重新谈判公司应遵循哪些规则;后者的目的,则是在公司法的规定在特定情形下并非最有效率时,相关各方可以选择更有效率的规则。两者均强调自由选择应是法律干预的目标:相关各方可拒绝公司法提供的规则另选其他。公司立法若以上述理想公司法为目标,则任意性规范无疑是理想的工具。 在上述理论影响下,传统法律理论中用以证明国家对企业组织进行强制立法的理论被重新表述。传统理论着眼于公司对公众利益的影响。在公司的合同理论中,公众利益被看作是个人利益的集合,或者重新被定义为是促进经济效率本身。按照这样的分析,组织法所包含的强制性条款,或者应被修正,或者得以证成期经济效率而得到保留。现有公司法的强制性规范,如果属相关各方默示同意的合同内容则有效率可以保留,因为强制性规范剥夺了当事人自由选择的机会,从效率的角度讲并不值得推荐。相应地,任意性规范允许自愿退出(opt out),以便相关各方按照具体情况定制符合自身需求的公司治理规则。故此立法者如有可能应把强制性规范转化为任意性规范,即允许当事人自行设定规则来替代以促进效率。 按照法律经济学理论的观点,公司法中那些允许当事人通过另行约定修改的示范条款应属任意性规范,在公司法立法中应占较大比重;那些直接规定商事组织关系的内容、不允许当事人修改的规范,立法应占较小比重。这一思想对公司立法和司法影响深远,以致今天公司法学者有时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既然当事人的自由选择是公司法作为默示合同的基础,是否应当将公司法全部都变成任意性规范。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登教授(Jeffery Gordon)写道:“例如,立法是否应在公司法每一条规定前都加上‘除非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这样的限定语,以便当事人自由更改其内容?”(14) (二)强制性规范的采纳和限制 法律经济学对强制性规范的全面排斥让学者开始反思强制性规范的必要性究竟何在。起初,学者看到公司相关人特别是股东在信息方面的弱势是公司法采纳强制性规范的合理理由。(15)在《公司法的强制性结构》中,高登教授进一步细化了任意性规范应让位于强制性规范的诸种情形:为保护投资者、面临不确定情形、为保护公共利益、为实现公司治理的创新和对付投机行为。他的结论是,美国公司法中有些强制性规则的存在实际让当事人可以更有效率地选择商事组织形式。(16) 法律经济学之外对强制性规范是否应存在的反思,则力图揭示效率并非公司制度形成的唯一因素、在很多情况下也不是决定因素。既然公司法所规定的制度并不必然是人们追求效率的结果,那么当然不能说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作为开创公司法的政治理论的一位学者,哈佛大学的马克·罗教授(Mark Roe)对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过程中的金融管制变迁做了详尽探讨,他认为是美国民众对大银行的敌意导致政府立法限制金融机构扩大规模,而大型企业的兴起带来了这些金融机构无法满足的融资需求,最终形成了向公众发行股份的公众公司模式和股权分散化的公司治理特征。(17)与马克·罗教授的方法类似,社会学家罗依(William Roy)教授则考察了美国股份公司从公立机构向私人企业转化的历史过程,发现股份公司形成并非追求效率的驱动,而是一系列政治变迁引致的结果。(18)此外,在比较公司治理研究领域,斯坦福大学的青木昌彦对日本主银行体制的研究、马克·罗教授对欧洲和美国公司治理模式的比较以及德国工人董事的研究也都揭示了政治环境的巨大影响。(19) 在司法界久负盛名的美国特拉华州衡平法院前大法官爱伦则认为强制性规则适度存在的理由是国家有必要、也有权力对公司进行管制。在对“什么是公司的本质”这一问题作了历史的考察之后,他认为学者和法官没有办法将公司仅仅看作是帮助人们经商的工具,因为它对政治、社会都有巨大影响,故此国家必定要对公司进行管制,而为特定管制目的存在强制性规范自然也是必要的。(20) 上述批评固然揭示了法律经济学理论解释公司制度形成的局限性,但并非对该理论的直接回应。公司治理的形成是公司法直接作用的结果,如果公司法是一系列供当事人选择的默认合同条款,那么应该对当事人没有强制作用:即便特定政治环境直接决定某些公司法条款,若不体现当事人的自由选择,当事人应当有机会拒绝接受,从而可以排除特定政治环境的影响。上述经济社会学、商业史和公司治理研究所论述的政治环境对公司治理的巨大影响,若不在当事人是否受到强制问题上作出回应,作为理论就难以圆满。 二 法律现实主义视野中的任意性规范与强制效果 人们对法律强制的通常理解是法律对个人自由选择的直接约束。这一点在政治自由主义传统中尤为突出,柏林对“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区分无疑是这一传统的最好阐释。个人自由只有在必要的限度内才能被法律约束,这一点经由《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论述为当代民主政治实践所接受,并成为对政府和法律本身合法性进行评判的基础。(21) 法律现实主义理论家对理解强制作出的一大贡献就是提出强制不仅包括约束人的选择行为本身、还包括型塑可供行为人选择的范围。这一理论贡献大大深化了我们对法律强制的理解。在法律现实主义理论视野中,约束选择行为的法律强制除了法律的直接禁止之外,更重要的是赋予权利;对行为人可供选择的范围型塑,则出现在约束选择行为的法律强制成为行为人做出选择的前提条件之后。 从1930年代开始,霍菲尔德、黑尔等学者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为分析法律强制作用贡献了基础性理论。(22)对法律强制,学者的通常理解是法律对个人行为的禁止性规定,特别是那些市场管制方面的法律;保护合同、财产权利的法律,被认为是尊崇自由选择的法律,学者并不认为它们属于法律强制的范畴。黑尔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认为,法律不仅可以通过禁止性规定来实施强制,而且可以通过赋予合同、财产权利等来实施强制。“政府在‘保护财产权利’之时到底做了什么呢?”黑尔设问,并从两方面给出分析。在消极意义上,是政府不干涉财产所有者对财产的处置;但在积极意义上,则是政府强制财产所有者之外的他人不得染指,除非得到所有者同意。黑尔提及法律实践中该积极意义上的保护要远为全面。黑尔的洞见让法学界对法律强制的理解进入一个新领域。 与黑尔同代的法学家杰非(Louis Jaffe)对合同权利作了类似分析。在评论第三方侵犯合同权利的案例时,杰非观察到不仅合同当事人受到合同的约束,而且他人也受到约束:合同当事人提供约束的内容,而法院则予以强制执行。杰非讨论了一系列以合同权利实施强制的情形,如雇佣合同、行会协议、加入股票交易所的协议等等。 霍菲尔德对权利的微观分析为理解法律强制提供了清晰的理论框架。在《论应用于司法推理的某些基本法学概念》中,霍菲尔德将权利指出,“权利”一词包含四个方面的含义,即“要求”(right or claim)、“自由”(liberty or privilege)、“权力”(power)和“豁免”(immunity);与以上四类相对应的承担义务的四种情形是“义务”(duty)、“无权利”(no-rights)、“责任”(liability)和“无权力”(disability)。(23)法律上具体的权利和义务,总是这些含义的特定组合。当法律赋予一方当事人要求、自由、权力或者豁免时,对方当事人就相应地有义务、无权利、责任和无权力。在这个意义上,霍菲尔德的分析佐证了黑尔论述:当立法者规定了权利,就等于为权利行使者影响的相对人设定了义务,从而客观上构成法律强制。 霍菲尔德的分析在两个方面推进了约束行为人的选择行为本身的法律强制的研究:第一,就法律上的强制而言,看似保障自由的赋予权利的规定和为个人或者组织设定义务的禁止性规定实际效果类似;第二,政府机构、司法机构等执法机关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构成法律上的强制。后者尤其对理解发展中国家的法律强制有启发意义。在发展中国家,常常有研究者认为某些领域没有立法或者司法消极不作为,是法律力量所不及的“真空”地带,故而不存在法律强制。(24)按照霍菲尔德的分析,立法、司法的消极不作为,实质上是为现有条件下的某些行为人设定了“豁免”,并为他们行为影响的相对人强加了“无权”。故而即便没有立法、司法明确设定的权利义务,法律强制仍然是存在的。例如,立法和司法对修建高层建筑的不作为,也明确相邻土地所有人无权就采光受影响要求得到赔偿。当法律赋予土地所有人修建高层建筑、不受到他人权利主张的豁免,也就是强制相邻土地的所有人接受采光影响的结果。(25) 当代批判法学理论家邓肯·肯尼迪在法律现实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还有一类强制的类型,即由于某些规则成为人们行动时考虑的前提,这些规则也可以带来强制的结果。这些规则就是肯尼迪教授定义的“基础规则”(ground rules)。肯尼迪教授就工人罢工过程中受到法律强制的例子来说明基础规则的效用。罢工的持续性取决于工人在罢工期间能否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在无法得到薪水的前提下,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受到财产权利的基础规则限制,工人于是不得不缩短罢工期间,接受较为苛刻的条件回到工作岗位。(26)在这里,某些法律规定,例如政府是否有义务在罢工期间支付最低生活保障,可能会极大改变双方的博弈过程。尽管该规则本身有可能被规避,但一旦该规则被社会广泛接受成为常识,就会型塑行为人的选择范围。这些规则因而可能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基础规则而实际表现出强制性。上述通过赋予权利、政府不作为或者支持“基础规则”的法律来实施强制,在现实中非常普遍且往往不容易为人察觉。法律强制不易察觉的原因很简单:当立法者无所作为,人们往往就认为法律对结果没有任何影响。但霍菲尔德的分析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即使只是给出自由行动空间的赋予权利的法律,实际上仍然发挥了强制作用。 上述法律现实主义学者所开创、批判法学运动进一步发展的分析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商事组织法——特别是那些允许当事人选择其他组织形式和确定内容的条款——如何体现强制的问题。既然法律强制可以表现在约束行为人行为本身和型塑行为人可供选择的范围两个方面,公司合同束理论所主张商事组织法是默示合同条款或应是默示合同条款一说,就需要重新斟酌。从法律现实主义对法律强制的分析出发,现存公司治理结构与其说是股东和经理人双方主动选择的最小化代理成本形成的制度,不如说是法律强制带来的结果。法律强制的形式,较为明显的是某些强制性规范对个人自由选择的直接限定。就这类强制而言,行为人并无选择。(27)大部分商事组织法上的规定是任意性规范。在任意性规范中,如果自由选择体现在商事组织法的规定本身是行为人的自由选择和这些规定并不对行为人表现强制力,那么法律强制表现在商事组织法的具体规定上,也可从行为人可否选择其他规则和行为人可拒绝遵循示范规定两个方面来看。 商事组织法上的任意性规范实际构成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商事组织法上的任意性规范实质没有给行为人选择的余地;第二,任意性规范作为行为人做出选择的依据成为最终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学者研究指出,尽管可以利用任意性规范,自行修改公司组织形式的困难程度仍然对行为人处处掣肘,故而这些规定本身并不体现行为人的自由选择。例如,公司管理层在多大程度上要直接对股东负责,是可以由章程自行设定的内容。但具体到法律问题,则是到底多大范围内的事务管理层(董事会)需要股东大会的批准,该任意性实际上给了管理层极大的自由空间。例如公司经理层的报酬,Bebchuck教授就认为任意性规范实际上给予为了谱子了经理层自我交易的空间。(28) 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司法立法尤其需要关注任意性规范带来的强制,是因为这些强制需要处理种种利益冲突,如果失败则带来经济和社会的负面效果。近年的比较公司法成果表明,包括俄国在内的众多移植英美公司法的立法努力都归于失败。对发展中国家公司法立法而言,立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需面对的众多利益冲突的解决都无法通过移植英美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的公司法来完成。 立法不应仅仅着眼于是否采纳、采纳多少任意性规范,而应当关注任意性规范的实际效果是否促进个人从事商业方面的自由;类似地,针对某一任意性规范带来的实际强制,立法采纳强制性规范予以处理,则当为可取。立法者要促进自由,必须得拆解已有的强制——无论这种强制是通过强制性规范实现还是通过任意性规范实现。拆借强制的方式,往往要使用强制性规范的方式。比较公司法在过去二十年的实践表明,包括俄国在内的众多移植英美公司法的立法努力都归于失败。对发展中国家公司法立法而言,立法失败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需面对的众多利益冲突的解决都无法通过移植英美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的公司法来完成。在考察司法环境不佳、政府管理缺失、本地习俗不同等等原因以后,比较法学者发现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法立法而言一种实用的做法是:发展中国家不应复制美国公司法的规定,而应采纳“自我执行模型”。所谓采纳“自我执行模型”的公司法,就是对照英美公司法的规定依照当地法院、政府是否有能力配合任意性规范行事而把许多任意性规范替换为强制性规范,以应对公司法在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挑战。 三 董事会制度:任意性规范如何导向强制性后果 中国公司治理研究中为学者和媒体广泛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损害中小股东权益。学者论述和立法回应关注投票制度、股东诉权等,(29)而公司法的相关任意性规范为学者研讨和立法、司法所忽视。根据2005年修订后公司法,股东大会同时拥有修改公司章程和按照公司章程规定行使职权的权利,董事会则依照公司章程规定确定其职权。对公司股东而言,公司法的规定意味着股东可以通过章程规定股东会、董事会及经理职权,上述规定当属任意性规范。按照法律经济学的理论,该规定属以任意性规则促进股东及经理层的自由选择。公司章程列出的董事会职权,类似某种默认合同条款,股东可以在章程中规定特定的授权和限制,故而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股东的自由。然而,现实中出现的情形却是这些按照任意性规则行使自由选择权利的中小股东权益屡屡为大股东通过董事会决议所侵害。而难以得到救济。 对任意性规范的深入分析应可帮助我们理解侵害何以发生。上述规定就大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关系而言,择其要者,包括下列内容:(1)大股东有要求按照既有章程召开股东大会提出任免董事、修改章程的权利,中小股东有义务接收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2)中小股东无权利要求大股东提出任免董事、修改章程;大股东有决定是否提出任免董事、修改章程内容与否的自由;(3)大股东有通过股东大会任免董事、修改章程的权力,修改后章程内容自动对中小股东发生法律效力,也就是说中小股东有受任免董事、章程修改结果的约束的责任;(4)中小股东无权力通过股东大会任免董事、修改章程,大股东有不受到非法定程序提出的章程内容修改的豁免。按照霍菲尔德提出的理论框架,大股东任免董事的权利、修改章程发生法律效果的权力和不受到中小股东相反主张约束的豁免尤其体现法律强制。由大股东所主导的董事会由于有就公司事务做出决议的权力,该决议内容直接对公司产生效力,同时自动对所有股东发生法律效力。结合上述两点,当大股东通过章程选举董事并设定董事会职权,中小股东不得不接受董事人选和该董事会职权设定;当选任的董事依职权做出决议,中小股东不得不承受决议的法律效果。法律强制在此表现为,设大股东通过设定董事会职权、选任董事决议一项公司事务,实际可以强制中小股东接受该决议的法律约束力。在当前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情形下,大股东派遣董事主导通过的决议屡屡损害中小股东利益,而中小股东也不得不接受这个结果。(30) 任意性规则在理论上可能解决上述问题,但不乏障碍。理论上,中小股东通过章程中设定防范“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大股东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规则是可能的。例如,投资者可以通过章程设定董事会对中小股东承担保障其利益的信义义务。但是,任意性规则作为解决方案的麻烦在于,若信义义务来源于章程设定,则意味着它随时可被大股东撤销,中小股东无法依赖其保障利益。中小股东除了上述章程规定之外,还需要一套复杂的限定大股东修改章程的法律应对方案来真正达到目的。在当前公司上市的立法给予大股东绝对主导权的前提下,这样的方案在上市公司章程中还从未出现过。也就是说,该任意性规范并没有让小股东获得更多选择的余地。 我国学者对《公司法》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的分析也展示了任意性规则的不足。按照我国《公司法》第16条和第149条第(四)项,章程在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公司订立合同或进行交易等问题上有自治的权力。施天涛教授指出:“封闭公司一般由控制股东把持公司管理,或者根本没有董事会,或者只有几个由控制股东管控的执行董事。真正的‘非利害关系’董事在封闭公司中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即便有,控制股东在安排公司治理时也不可能把控制权拱手交出。所以,封闭公司中的股东同意,则完全可能就是控制(或多数)股东的同意。”换言之,法律虽然规定了在关联交易的投票表决中有利害关系的董事要回避,公司法的任意性规则仍然允许大股东左右公司最终决定。 公司法上关于董事会的任意性规范非但没有促进合作,实质上还增加了股东之间合作的困难。法律经济学分析任意性规则,看到的往往是权利,而不是相应的义务。研究者往往因公司法允许当事人任意设定权利内容而认定其保障自由,而没有看到该允许之下对权利相对人的强制。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中,大股东常常利用董事会损害小股东利益,而由于股东派生诉讼极少被法院受理,中小股东无从对抗大股东。董事会权力有什么样的特征、法律应当设定什么样的约束,是中国公司法立法、司法必需面对的问题。申言之,看似体现股东自由选择的公司法规定,实质上体现了损害小股东的法律强制。从这个角度看,以任意性规范回应上述问题,实属不得要领。 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的董事会制度在实践中支持了“一股独大”的持续存在。当上述任意性规范所带来的法律强制成为人们选择投资的前提时,它变成了基础规则起到型塑选择范围的作用。一家大股东主导的上市公司,即便中小股东权益受到大股东侵害,还是会比没有大股东主导的上市公司更易于成为中小股东更中意的选择。这是因为在没有占绝对优势大股东的上市公司中,由于存在少数股东通过增加股份而控制董事会、进而对全体股东施加强制的可能性,且该少数股东由此获得的收益极大,出现股东恶性竞争的可能性更高;这样的恶性竞争对中小股东的损害甚至超过大股东主导的上市公司里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侵害。实践中,这样的公司往往陷入控制权争夺的斗争而经营瘫痪。例如,一度被列为“大股东制衡”思维下公司治理典范的上市公司东北高速,在股东中并无占绝对优势的单一大股东,前三大股东持股比例及董事会席位比例均为任何两方相加大于第三方。但该公司董事会换届屡屡沦为股东互相恶意竞争的机会,中小股东利益因为大股东之间恶意竞争而受损。相比这样的公司,对中小股东而言,大股东主导的上市公司反而成了更优的选择。公司法关于董事会的任意性规范非但无法帮助中小股东防范大股东通过董事会侵害其权益,反成为大股东侵害中小股东的有力工具。合同束理论假设任意性规范可以保障股东的自由选择,却忽视了在一股独大的条件下该任意性规则成为强制股东的工具。已有的公司法董事会制度的实质,是通过任意性规范授权大股东对公众股东(小股东)的强制掠夺——对小股东而言,这些任意性规范所实现的实际上的强制性,与公司法直接采纳限制小股东权利的强制性规范无异。 在中国现实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的条件下,公司法在董事会制度建设方面采纳强制规则效果未必不佳,因为只有通过法律强制才能减少强势大股东对中小股东的实际强制,从而真正促进自由选择。近些年中国学者关于董事会的法理反思,也在从形式主义转向实质分析的方向上作出了有益的尝试。(31)邓峰教授对中美董事会制度的比较研究表明,中国董事会职权设定以任意性规范为特色,而美国公司法则明确董事会作为公司管理的最高权威并不得以章程加以修改,同时以信义义务来防范董事会对中小股东权益的侵害。董事会因获得对抗股东决议的权利和法院的约束,受到大股东操纵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大大减少。这固然有股东派生诉讼制度和高效率的司法等其他原因,但公司法关于董事会的强制性规范并未妨碍对中小股东权益的有效保护却是不争之事实。同时,美国公司法在董事会制度上采纳的恰恰是强制性规范,但在促进股东合作方面却明显更为有利。(32)借鉴美国公司法的规定,立法者在改革中国董事会制度时,至少不应拒斥强制性规范。转换思考的角度,看到任意性规则也有法律强制的作用,立法、司法机构或许可以从一些并不真实的前提中解脱出来。 笔者认为,立法者如在下一轮公司法修改中改进我国董事会制度,当有针对性地解决任意性规则仍然允许大股东左右公司最终决定的问题。具体而言:第一,以强制性规范确立董事会在日常运营和并购语境中的职权与对应信义义务,并对股东会以多数决修改与董事会职权相关的章程条款予以限制;第二,以强制性规范对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及自我交易的董事会或股东会投票作出限定决议必须绝大多数票通过;第三,以强制性规范限定董事会或股东会投票决议影响某一类别股东时赋予其否决权。这些建议得到了相关比较公司法学研究成果的支持。(33) 四 商业组织法的规范配置:从形式主义到实质分析 对于在法律上属于后发国家的中国而言,现有商事组织法理论的约束在于:欧美公司法模式既然本质上体现当事人自由并会促成高效率的公司治理,那么移植这样的公司法就是顺理成章的选择,故而任意规则被一般性地认为体现自由,强制规则自然被排除在立法、司法选择的范围之外。但在现实中,一些从欧美既有公司法中移植到中国语境中的制度并不体现当事人自由,相反实质上导致强制。更严重的是,这些名为自由、实则强制的法律,使立法、司法对真正限制当事人自由的制度问题无从回应:中国公司法上的董事会制度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我国立法大量移植国外法律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注意:即便移植的是在其他国家语境下体现行为人自由选择的规范,它在中国语境下也可能有强制的效果。例如,方流芳教授1996年对中国刚刚完成的公司立法进行评价时认为,一个立法者认为为代表促进自由选择的“规范化”公司法,恰恰是强制相关当事人接受政府强制安排的工具。(34) 在明确任意性规范与促进自由选择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之后,法律还有能力促进自由选择吗?中国学者常常担心如果法律不能有一个清晰的、区别于政策制定的标准,就难免为政治所影响。这样的担心固然有历史和社会原因,但制订法律时依据任意性规范和促进自由选择之间虚假的对应关系,却对实现法律的自主性这一目的根本上有损。打破任意性规范和促进自由选择之间虚假的对应关系,让妨碍自由选择的原因显明出来并在立法、司法过程里直面这些问题,法律才更有可能促进自由选择。 立法放弃增加任意性规范这一虚构的目标之后,应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进行规范配置?对董事会制度的法理分析实例告诉我们,立法应在实质分析的基础上考虑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的配置,而不是把规范配置建立在任意性规范和自由选择的虚假关联上。为着促进自由的缘故,立法不应仅仅着眼于是否采纳、采纳多少任意性规范,而应当关注任意性规范的实际效果是否促进了个人自由;类似地,针对某一任意性规范带来的实际强制,立法采纳强制性规范予以处理,则当为可取。在决定是否采纳强制性规范的时候,我们必须首先知道立法所处理的真正冲突是什么,把冲突展现在公众面前、让立法选择强制的目的凸显,如此才能真正保护个人权利、促进个人自由。从形式主义转向实质分析,应是立法合理配置强制性和任意性规范的前提。 比较公司法的研究中,从对公司法规范类型到底属于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的形式主义考察转向考察规范的实际效果是导向强制还是促进自由,是从形式主义转向实质分析的典型例子。这种转向的实质是公司法法理研究从依赖新古典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向传统制度经济学的回归。(35)与新古典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强调作为对个人行为约束的规则和组织(新制度经济学定义的“制度”)相比,传统制度经济学更强调人与人之间互相冲突的利益关系和这些冲突的解决。(36)在传统制度经济学的代表巨著《资本主义法律制度》中,上文使用的霍菲尔德对权利的微观分析是作为其制度分析的基础性理论出现在论述中的。(37)传统制度经济学可以帮助实现对中国公司法效果的实质分析,进而分析其背后的利益冲突问题。对中国法学界而言,之所以应当关注比较公司法研究成果和从传统制度经济学中汲取智慧,是因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公司法的立法需要处理种种利益冲突,这些未必是移植一个已有公司法模型能够胜任的。 当代法理学对权利问题的讨论,让我们在立法权衡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时受到启发。当保护一种个人权利要牺牲另外一种个人权利的时候,立法或司法不得不作出选择。“是谁的、什么样权利?”继续追问下去的时候,在保护权利的华丽辞藻背后就出现了国家强制的身影。既如此,所谓保护权利和赤裸裸的国家强制之间又有什么区别?既然都需要强制,权利话语还有必要在立法和司法中继续使用吗?如哈佛法学院院长玛莎.米诺教授所言,在这样的时代里,权利话语的意义在于揭示权利背后的冲突:“权利”可以理解成一种公共话语,它代表的是“即便在冲突和争斗之中仍然存在的共处的承诺”。(38)在权利的话语中,那些让社会分裂的根源才有可能被揭示出来,从而真正的权利保护才可能实现。正是那些为解决个人自由之间的冲突而制定的强制性规范,才让我们知道立法应保障的个人自由到底是什么。如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赠言所讲,一个人在此学习法律有成,意味着从此有能力参与设定和管理那些“为得着自由而必须首先设定的行动界限”。(39) 面对复杂的利益关联中的恃强凌弱,立法者如果拒绝强制性规范,不啻自缚双手。在采纳强制性规范后立法者就其合理性向公民阐明理由,则是一个真正良善的国家治理所应体现的明智和谨慎:毕竟对公民施加强制从来不是法律能轻率跨过的红线,只有为了真正促进自由才如此的立法者才有底气面对本国公民和文明世界的正当责问。 ①相关讨论参见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的描述,《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 ②在大陆法系成文法传统中,关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讨论源远流长。对这个传统的回顾和综述,见王轶著:《民法原理与民法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英文文献中这种区分更早的渊源,参见Calabresi & Melamed,Property Rules,Liability Rules,and Inalienability:One View of the Cathedral,85 HARV.L.REv.1089,1093(1972)。 ③学界在过去几年相关作品主要集中在分析在何种情况下强制性规范有其必要性。学者应用法律经济学理论对公司法的目的和功能的分析,加深了我们对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认识。例如,罗培新教授参考法律经济学的公司合同理论提出,商事组织法中强制性规范存在的合理性在于法律针对公司长期合同的不完备性提供的合同漏洞补充机制。故此,提供这种机制的公司法内容如信义义务相关规范应以强制性规范来规定。限定公司治理的权力配置和内部利润分配为调整对象的相关内容,则应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罗教授在考察了已有的研究后得出结论,认为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适用范围应考虑以下三类情形:区分结构性规则、分配性规则和信义规则;区分闭锁公司和公众公司;区分初始章程与后续章程修改。见罗培新:《公司法强制性与任意性边界之厘定—一个法理分析框架》,《中国法学》2007年第4期。罗培新教授更早的讨论,见罗培新:《论章程“超越”公司法的合理界限——以合同为研究视角》,载沈四宝、丁丁主编:《公司法与证券法论丛》,第1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5-80页。 ④关于“赋权法”(enabling law)的讨论,见Hansmann & Kraakman,What is corporate law?,The Anatomy of Corporate Law:A Compara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By Reinier Kraakman* et a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⑤就公司法体现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交织的相关讨论,参见赵旭东著:《公司法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4页;孙晓洁著:《公司法基本原理》(第二版),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另外,施天涛认为,公司法规则的分类与公司的性质密切相关。公司的性质有法人说和契约关系说两种观点。其中契约关系说主张任意性规范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导致对强制性规范合理性的探讨。见施天涛著:《公司法论》(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4页。蒋大兴认为,公司法具有自由因子和管制因子,在公司设立、运营、终止和责任方面均有体现,“无论如何自由主义,中国的公司法很难超越这种国家管制的立场。这也是准确理解和解释中国公司法立法构造的一个基本的理论前奏和文化前提”。蒋大兴著:《公司法的观念与解释Ⅰ:法律哲学&碎片思维》,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34-86页。赵万一从股东构成的变化解释了两种规范同时存在的原因:“同质化”使得公司内部权力配置可以通过更多任意性规则来规定,而股东“异质化”使得公司内部权力配置需要更多强制性规则来规定。赵万一著:《公司·商人·经济人》,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205页。 ⑥一般而言,在公法领域立法采纳强制性规范所受到学界和公众的批评较少,因为公法本身就蕴含着国家对某些社会关系强行管制的政策目标;在私法领域,立法采纳强制性规范的正当性总是易被拷问,因为强制性规范往往拒斥了个人自由。关于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在公法与私法语境下的讨论,见苏永钦:《私法自治中的国家强制——从功能法的角度看民事规范的类型与立法释法方向》,《中外法学》2001年第1期;解亘:《论违反强制性规定契约之效力》,《中外法学》2003年第1期;苏永钦著:《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孙鹏:《论违反强制性规定行为之效力——兼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理解与适用》,《法商研究》2006年第5期;谢鸿飞:《论法律行为生效的“适法规范”——公法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及其限度》,《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⑦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著:《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Easterbrook,Frank H.and Daniel R.Fischel(1991)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⑧Roberta Romano,The Genius of American Corporate Law,AEI Press,1993,Chapter 5,page 85-118. ⑨经济学家弗里德曼认为强制在市场经济出现之前是达成合作的主要方式,而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合作是通过自由选择达成的。科斯的企业理论认为,生产可以通过市场和企业两种方式,前者体现自由,后者体现强制。科斯之后,许多制度经济学研究者表达了对企业内部关系体现强制的不同观点,提出公司合同理论的威廉姆森和哈特是其中的主要人物。见米尔顿·弗里德曼著:《资本主义与自由》,张瑞玉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科斯:《企业的性质》,陈郁译,载科斯著:《企业、市场与法律》,盛洪、陈郁译,格致出版社2009年版。 ⑩Henry Hansmann and ReinierKraakman,The Essential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aw,110 Yale Law Journal 387-440(2000). (11)迈克尔·詹森、威廉姆·麦克林:《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载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编:《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2)例如,Jensen认为,代理成本高低取决于成文法、普通法以及人们以合同来解决问题的创造性。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有降低代理成本的强烈动机。而现有法律和与公司相关的合同设计,都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不断降低代理成本的结果。迈克尔·詹森、威廉姆·麦克林:《企业理论:经理行为、代理成本和所有权结构》,载路易斯·普特曼、兰德尔·克罗茨纳编:《企业的经济性质》,孙经纬译,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年。 (13)弗兰克·伊斯特布鲁克、丹尼尔·费希尔著:《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张建伟、罗培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Easterbrook,Frank H.and Daniel R.Fischel(1991)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4)Jeffrey N.Gordon,The Mandator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89 COLUM.L.REV.1549,1556.(1989). (15)Melvin A.Eisenberg,The Structure of Corporation Law,Columbia Law Review,vol.89(1989),pp.1461,1464-70. (16)Jeffrey N.Gordon,The Mandatory Structure of Corporate Law,89 COLUM.L.REV 1549,1556.(1989). (17)Mark Roe,Strong Managers,Weak Owners,The Political Roots of American Corporate Finan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 (18)William Roy,Socializing Capital:The Rise of the Large Industrial Corporation in America.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19)Masahiko Aoki and Hugh Patrick(ed.),The Japanese Main Bank System,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 Ronald Gilson and Mark Roe,Understanding the Japanese Keiretsu:Overlaps between Company Governance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Yale Law Journal; V.102-4,871-906; Roe,German Codetermination and German Securities Markets,in Blair and Roe eds,Employees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4-205; Mark Roe,Some Differences in Company Structure in Germany,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Yale Law Journal; V.102-7,pp.1927-2003; Roe,Political Determinan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2003. (20)Allen,William,Our Schizophrenic Conception of the Business Corporation,14 Cardozo L.Rev.261(1992-1993). (21)“没有什么能比这更明确:政府是必须的,这点不可否认。而且无论它怎样建立,人民必须舍弃一些他们在自然状态中所有的权利,从而使赋予政府所需要的权利。”见约翰·杰伊:《联邦党人文集》第二篇,汉密尔顿、杰伊、麦迪逊著:《联邦党人文集》,程逢如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2)Robert L.Hale,Coercion and Distribution in a Supposedly Non-Coercive State,38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23); Hohfeld,Wesley.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Legal Reasoning,23 Yale Law Journal 16(1913); Hohfeld,Wesley Newcomb,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26 Yale Law Journal 710(1917). (23)沈宗灵先生在国内最早介绍霍菲尔德的理论,王涌教授详尽介绍了霍菲尔德的学说并将其应用在民法基本概念的分析上。见沈宗灵:《对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学说的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王涌:《寻找法律概念的“最小公分母”——霍菲尔德法律概念分析思想研究》,《比较法研究》1998年第2期。 (24)David Kennedy,Laws and Developments,in Law and Development:Facing Complexity in the 21st Century,edited by Amanda Perry-Kessaris and John Hatchard,Cavendish Publishing,2003. (25)在法律没有规定权利或者义务的时候,司法过程通常是厘清权利的一个必要过程。 (26)Duncan Kennedy,The Stakes of Law,or Hale and Foucault!,15 Legal Studies Forum 327(1991).肯尼迪教授明言上述分析是对法律现实主义学者对强制探讨的推进。 (27)学者指出,即便有强制性规范,当事人也会采取策略规避不利结果,从而最终形成的公司治理结构并不因这些强制性规范而改变。例如,布莱克认为现代美国公司法上的强制性规范(州法部分)实际上并不对当事人的合同选择有实质性影响,故而这些强制性规范实际上“无关痛痒”。见Black,Is Corporate Law Trivial?:A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nalysis,84 Nw.U.L.Rev.(1990)).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无关痛痒”并不能说明法律缺乏强制力。即便强制性规范是可以规避的,它们仍然可能作为“基础规则”构成强制。 (28)Pay Without Performance:The Unfulfilled Promise of Executive Compensation By Lucian Arye Bebchuk,Jesse M.Fried,pp.15-19. (29)通过修改投票制度保护中小股东权益,认为旧《公司法》中的直接投票制度导致小股东的表决权很难达到选举董事所需要的法定数额,故而董事会受到少数大股东操纵,其通过的决议也会侵害小股东利益。新《公司法》对股东的表决权制度进行了修改,规定股东可以通过公司章程规定表决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新《公司法》第43条)。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可以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的决议(新《公司法》第106条)。 (30)中国当下缺乏司法救济手段,中小股东难以挑战董事会的决定;即便增加救济途径,考虑到董事会决议对中小股东权益的广泛影响,中小股东难以事事通过司法救济,权益仍然难以保障。见Deng,J.,Building an investor-friendly shareholder derivative lawsuit system in China,46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347-385(2005). (31)在商事组织法领域自由选择的障碍,既有政府或者立法机构通过制定法形式将强制性规范强加于公司的问题,也有法律对诸如大股东滥用其地位问题的不作为。对此,有学者提醒立法者“重新认识董事会制度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认真对待公司的政治属性,在董事会权威中心、合议和共管制度上继续不断学习”,从政治、社会、文化的角度对中国公司法的制度安排提出了有见地的质疑;也有学者呼吁公司法修改的首要问题就是要重新确立公司法的自由主义精神,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其制度规则。邓峰:《董事会制度的起源、演进与中国的学习》,《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施天涛:《公司法的自由主义及其法律政策——兼论我国〈公司法〉的修改》,《环球法律评论》2005年第1期。 (32)邓峰:《董事会制度的起源、演进与中国的学习》,《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33)美国学者豪森教授认为,在公司法以任意性规范确立董事会制度的大框架下,中国证监会作为监管机构采纳了不少必要的强制性规范来解决公司法中强制性规范不足的问题,这些规范有:(1)规定在公司日常运营和并购语境中高管和控股股东的信义义务的规范;(2)赋予公众股东权利的通过及否决投票机制的规范;(3)对控股股东关联交易及自我交易的董事会或股东会绝大多数票通过的规范;(4)规定独立董事制度的规范;(5)规定某一类别股东否决权的规范。笔者认为,这些强制性规范原本应体现在公司法中,尽管目前通过证券管制已经实现,从改进公司法的角度立法者应将其纳入公司法规范中。Nicholas Howson,"Quack Corporate Governance" a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the Securities Regulation Cannibalization of China's Corporate Law and a State Regulator's Battle Against Party State Political Economic Power,37 SEATTLE U.L.REV.667(2014)(hereinafter,Battle Against Party State Power). (34)Liufang Fang,China's Corporatization Experiment,Duke Journal of Comparative & International Law,149,181-85(1995). (35)传统制度经济学兴起于20世纪初,经由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在20世纪中期罗斯福新政期间达到鼎盛,后因新古典自由主义制度经济学兴起而逐渐影响减小。对传统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的对比,参见钱弘道:《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法学研究》2002年第4期。 (36)公司的合同束理论重视公司法规范类型属强制性规范还是任意性规范,原因在于不同类型的规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程度不同。而对规范是导向强制还是促进自由的考察,则秉承传统制度经济学对制度实际效果的重视。参见约翰·R.康芒斯著:《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寿勉成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五章。 (37)约翰·R.康芒斯著:《资本主义的法律基础》,寿勉成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四章。 (38)在分析保护权利所依赖的暴力时,玛莎·米诺教授写道,因为法律涉及国家控制这一有组织的暴力,法律解释与暴力之间的关系盘根错节。因为人们总是力图强加于权利他们所认为的意思,以便有组织的国家暴力对此加以实现,故此法律中包含人际冲突或者组织之间的冲突总是与暴力相关。Martha Minow,Interpreting Rights:An Essay for Robert Cover,Yale Law Journal 96(1987):1860-1915. (39)John MacArthur Maguire,LL.B.Harvard 1911,Professor of Law 1923-57,Royall Professor of Law 1950-57,composed this declaration,which has been used by Harvard Presidents when conferring degrees at Commencemnt since the late 1930s:"You are ready to aid in the shap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ose wise restraints that make men free."见哈佛法学院图书馆网站:http://asklib.law.harvard.edu/a.php?qid=37313。标签:法律论文; 组织法论文; 合同管理论文; 股权论文; 公司治理理论论文; 法律规则论文; 规范分析论文; 公司法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