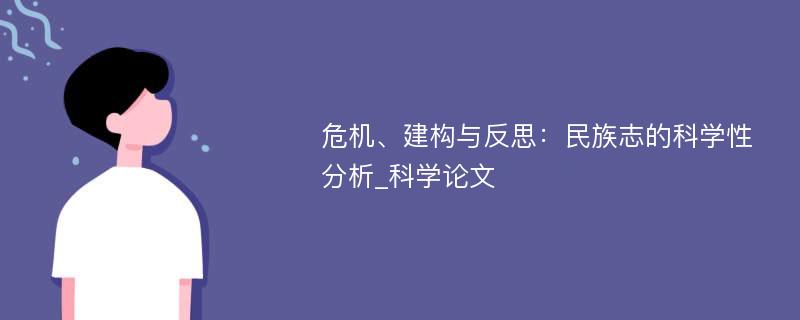
危机、建构与反思:民族志科学性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科学性论文,危机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16)03-0093-07 目前,在人类学内部,范式权威的缺失和多重范式的并存,印证了“当代人类学的发展反映出一个中心问题,即关于在一个急剧变迁世界中的社会现实的表述。在人类学内部,民族志田野工作和写作已经成为当代理论探讨和革新中最活跃的竞技舞台。民族志的注意力在于描述,而就其更广阔的政治的、历史的和哲学的意蕴而言,民族志的写作就更富于敏感性,因为它将人类学置于当代各种话语(discourses)中有关表述社会现实的问题争论的漩涡中心。”①在西方,有的人类学者致力于复兴诸如民族语义学、英国功能主义、文化生态学和心理人类学等旧的研究范式;有的致力于综合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其他的象征分析方式;有的致力于建立像社会生物学那样更具涵盖性的理论解释框架,以便实现更为“科学”的人类学之理想;有的致力于将有影响的语言人类学研究与社会理论所关心的问题结合起来。②在中国,诸多学者也提出了众多的民族志范式,比如,主体民族志③、关系民族志④、影像民族志⑤、线索民族志⑥、感官民族志⑦、自我民族志⑧、实践民族志⑨等。除此之外,很多学者还从宏观视角对民族志书写进行了探析,其间不乏当今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翘楚,比如何星亮、朱晓阳、蔡华、彭兆荣、高丙中、张小军等。对于中西方学者而言,在民族志书写上所做的诸多实践,很好地说明了“我们不是从参与观察或(适合于阐释的)文化文本开始的,而是从写作、从制作文本开始的。写作不再是边缘或神秘的一维,而是作为人类学家在田野之中及之后工作的核心出现”⑩。“他们都被民族志的实践所鼓舞,并且反过来激励着民族志实践,民族志实践是它们在分化时期的共同的标准。”(11)从总的意义上来说,学者们的这些民族志实践对于民族志发展是健康的。但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中外学者,特别是国内学者对于当代民族志写作态势产生的缘由、民族志实践场中的种种“幻象”、科学民族志的诉求等问题还没有从学理和事实等方面进行深入、系统的探讨。基于此,本文在关注民族志种种危机表现的基础上,着力去探讨民族志书写危机背后的本质,进而辩证地去看待人类学界解决民族志书写危机而采取的种种民族志实践,最后提出对于民族志科学性的看法,以就教于大家。 一、民族志危机表象和意指实践 从自发性的、业余性的与随意性的业余民族志肇始,民族志走过了科学民族志强调行为与社会结构的“社会的自然科学”阶段,迈向了追求微观意义、符号象征、语言权力等为特征的社会生活的意义认识的进程中。在民族志发展历程中,其范式的不断转换、理论关切点的不断转移、方法视野上的不断延展及价值目标上的不断升华,这些都使以民族志为核心和主要标志的人类学学科得到了长足发展。无独有偶,在民族志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也是险象环生、危机重重。 1.修辞问题引发表述危机 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中,通过凄苦的土著人和浮躁而机械的圣保罗与里约热内卢去展现古老悠久的文明在西方殖民入侵下的惨状,以此去思考和批判西方殖民主义和西方文化中心论。保罗·拉比诺用“一个人把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让自己失去或显或隐地选用小说家方式对具有魔力的经验进行创造的机会,并且破坏对于异国情调的幻想;他把解释者的角色转变为针对他自己,针对他的解释——这是要把通常被建构为秘密和什么所包围着的、作为人类学职业的入行仪式的田野作业转化为它的适当维度:一种对社会现实的表征进行建构的工作”(12)。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则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民族志作者如何将自己关于人性和人类社会的观点与身处其中的世界的诸多问题联系起来思考的真实行为。奈吉尔·巴利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则用反讽的方式去解剖自我,看到了民族志作者在田野工作前后的“天真”的一面,令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陷入了对民族志书写的深深思考。以上文本中表现出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将对对象的研究作为研究对象、民族志作者自我解剖等指向,都和以往的民族志,特别是与科学民族志的表述有着巨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引起的民族志危机主要体现在民族志表述方式上,即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展示社会事实、伦理价值和社会环境等相关问题。 2.争议问题引发民族志表述危机 在人类学一百多年发展史中,争议问题贯穿其中。但就人类学研究重点的亲属称谓来说,就存在亲属称谓是生物的还是社会的、心理的还是社会的、结构的还是功能的争论;亲属称谓语义上联姻对血统的争论;模式的历史变迁所表明的亲属称谓等相关问题。而涉及这场争论的人类学家则更多,麦克伦南对摩尔根、里弗斯对克罗伯、拉德克里夫—布朗对里弗斯、马林诺夫斯基对布朗、默多克对列维—斯特劳斯,甚至有些不知名的学者也参与其中。当然,当时所发生的这些争论还没足以引起一场民族志危机的到来。真正使民族志危机到来的则是近代四场引人注目的争论:德里克·弗里曼与玛格丽特·米德在《萨摩亚人的成年》中引发出来的“人类学家做什么”的思考,促使人类学内部如何去捍卫民族志权威问题出现;加纳纳思·奥贝塞克里批评马歇尔·萨林斯关于夏威夷群岛上谋杀库克船长的叙述以及萨林斯的反驳,引发了人们对同一问题采取不同思维模式的思考;大卫·斯图尔揭露危地马拉的玛雅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丽格伯塔·孟朱所撰写的著名纪实性著作中的失实之处,再次说明了在民族志表述中,“谁去表述”是个利益攸关的重要因素;记者帕特里克·蒂尔尼对拿破仑·沙尼翁关于雅诺玛玛族的民族志及生物医学研究的大背景所作的批判和曝光,引发了人们去思考民族志作者如何更好地去保护被研究者的问题。最后,“这些争议尚未使得人类学家绞尽脑汁设定的复杂议题和各种当代研究陷入严重的混乱,但是它们已经让人类学在尴尬面对学科在它的主要公众当中继续拥有的形象和理解”(13)。 3.学理问题引发的民族志表述危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两本有关民族志理论的著作——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的相继问世,民族志的“表述危机”在学理上得到了确认。在《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中,两位作者把人类学以往的作品和现时代的作品拿来对比分析,并从诗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入手去分析民族志,以此来关注民族志文本的撰写。而在《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中,两位作者在关注人文学科的表述危机之后,更是大胆地提出人文学科实验时代的到来。同时,在著作的大部分篇幅里,他们阐释了实验时代的民族志样态。正如克利福德和马库斯所言:“本书要击打出一种强有力的声音,在所有那些目睹民族志和文化批评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的领域引起争论。”(14)正如他们所言,人类学最近30年的发展实践恰恰证明了他们理论的正确性。 综上,修辞、争议及学理问题是引起民族志表述危机的三大缘由。但如果从更深层次探究,它们仅仅是引起危机的表层原因及现实表现而已。究其根源,民族志表述危机的出现有着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认识论基础及价值诉求。 首先,在时代背景上。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以往那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民族志书写方式,不但受到第三世界人们的反对,也引起了西方人类学家自身的反省。格尔茨说出了“西方道德和智力自信的动摇”(15)的话语,而萨义德在《东方学》中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科学民族志的书写目的:“它的意图在于理解和在某些例子中控制、操纵,甚至吞并与西方不同的世界。它的discourse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不是直接的,但它在与不同的权力的交换之中存在。作为一种政治知识文化,它的存在与西方的关系比它与东方的关系更大。”(16)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现代潮流下的多元话语主体影响民族志书写的方式和价值诉求的变革。 其次,在认识论基础上。民族志书写本身就是一个实践和认识活动,其间主体与客体、写作与事实、田野与写作、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关系交织在一起。而对这些关系本身的梳理,历来就是整个人类认识过程中不能缺少的一环。以往的民族志认识也许过于片面或者简单,如今只是需要在全面把握事实的基础上,更为客观真实地反映“他者”而已。这本身就是人类学认识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环,但正如格尔茨所说的,有些人类学者过于矫枉过正了。“认识论疑病症”(17)妨碍了人类学者从事更好的民族志写作,甚至出现了“现代认识论的观念于是便转向了对主体表征的澄清和判断”(18)的过激倾向,拉比诺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这也许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深刻的西方思想史渊源,而这种渊源就是西方思想史上根深蒂固的怀疑主义传统。(19) 再次,在民族志的价值诉求上。随着时代背景的变迁,人类学界理所当然地应该对“为什么要写民族志、怎么去写民族志及民族志写作的意义何在”等相关问题得到新的认识。因此,建立在新时代基础上的民族志书写价值也得到了人类学家们广泛的关注。作品本身应该为现时代服务,只有这样的作品才会有生命力和活力。可以说,价值诉求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导致了这场民族志书写危机的出现。当然,除此之外,也不排除一些人类学家为了哗众取宠,故意夸大和以非常规方式撰写民族志,进而引发民族志危机现象出现的情形。无独有偶,后现代下的“没中心”“无根基”“流浪生活”等理论倾向也是促成民族志写作方式多样化的理由之一。 通过对于上述民族志危机表象和危机出现缘由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民族志危机的本质来。因为无论是民族志危机表象、还是民族志危机出现的缘由,其背后都存在一个如何去表述异文化、彰显人类学特有功能的问题。基于此,笔者认为民族志危机实质上就是来自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的危机,也就是民族志在达致求真至善上出现的危机。因此,只要这两个问题得以解决,民族志书写危机也就随之会消除,因为文化描述本身就是一个求真的历程,文化批评本身就是一个求善的过程。真善之间,民族志就能做到和谐之美。那么,通过什么途径才能达到民族志的求真至善?“只有通过提高传统人类学的异文化的描述功能,我们才能提高人类学的本文化批评功能。”(20)因此,把描述和批评、学理和实践、实验和创新结合于一体的实验民族志,或许就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法之一。 二、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结构和反结构 人类学学科出现危机并不可怕,它反而是学科发展的一次契机。在人类学学科之前,号称基础学科的物理学、数学和哲学也相继发生过危机,这些危机甚至还直接关涉到学科的生死存亡。比如,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量子力学的产生使经典物理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失效,由此引起了物理学上的危机;数学的基础在20世纪初被成功地转向逻辑,但随着逻辑悖论的出现,数学的基础也发生了动摇;哲学传统的研究主题——上帝、物质和灵魂,面临着宗教学、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冲击,哲学存在着失去自身研究对象的危险。在危机之中,经过三门理论学科的科学家们的不断努力,相对论的出现、自然数的重新定义及语言逻辑化分析,使得物理学、数学及哲学成功化解了危机,获得了新的发展。这些学科在面临危机时所表现出来的应对危机的方法,确实值得人类学界借鉴。实践证明,人类学界也是如此去做的,一大批实验民族志作品的出现,正是应对危机的最好办法和举措。但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种种实践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结构,应该如何去分析这个结构,是如今寻找民族志科学性的根据。 危机影响下的民族志书写,总体结构呈现出以下特征:范式多样化、修辞文学化、视角微观化及价值人性化等。首先,范式多样化。“范式”是个较为模糊的概念,主要是把一个科学理论作为范例去表示一个科学发展阶段的模式,范式是一幅关于世界整体的图式,以范式改变为标志的科学革命的实质是人们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范式的作用在于去解决科学理论中的问题。(21)民族志实验阶段出现的范式多样,是解决科学民族志危机的产物,也是人们面对世界政治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的产物,同样是科学理论的更新。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到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相对论到认知科学、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的并存等为民族志书写范式的多样性产生奠定了基础,对于大家去理解诸如现代主义民族志、新现实主义民族志、心理动力学民族志及线索民族志、主体民族志、影像民族志等分支学科的内涵大有裨益。在心理动力学民族志的三本代表作中,罗伯特·莱维的《塔希提人:岛民社会的心智与经验》强调的是人观思想;奥德·柯累克的《力量与劝服:一个亚马逊印第安人社会的领导权》关注梦境中人们的思维结构关系;奥贝耶斯科尔的《马渡莎的头发:关于个人象征符号与宗教经验的一项研究》看到了思维模式在社会变迁中的形成与转化。在中国“主体民族志”倡导者朱炳祥教授的众多民族志理论研究中,对主体民族志形成、范式特征、多重主体及实践个案都有阐述,特别是在《“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22)中,把其提倡的范式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给读者一种全新的认识视野。总之,这些民族志理论及作品,都成为了今天范式多样化的表征。 其次,修辞文学化。随着罗兰·巴尔特和福柯思想的广泛传播,民族志书写也深受其影响,一股号召民族志诗学和政治学的潮流涌起,很多学者甚至发出了民族志书写进入了一个文学的时代,修辞多样化应成为当今民族志书写一大特色的呼吁。比如,在有的学者称为开启了实验民族志写作先河的《忧郁的热带》中,作者采取了自白、人观及文学语言去书写民族志。保罗·拉比诺认为克利福德把民族志分为经验的、对话性的、解释性的和复调的四种写作方式,其中心论题是人类学写作一直以来都在压制田野工作中的对话因素,它把对文本的控制权交给了人类学者。(23)另外,《写文化》的其他作者,比如,雷纳托·罗萨尔多、玛丽·路易斯·普拉特等都表达出了在民族志写作中重视修辞的必要性想法,他们认为《努尔人》里面体现出来的没有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法律及没有领袖的那种缺乏维持政治秩序的制度的表达方式让人难以接受。 再次,视角微观化。从理论上看,在人类学古典时代,以进化论、功能主义及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宏观理论追求,成为当时民族志撰写的出发点和归宿;而在民族志危机出现前后,更加关注微观层面的象征主义、政治经济学派、实践论、解释学等,预示了当今时代理论多样化和小理论盛行的局面已经形成。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转向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这在人观思想及其相关作品中得到了体现。正如学者所说:“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的提出,部分原因在于为了在政治上对抗具有危险性的种族主义以及浪漫的集体思维理论。”(24)比如,肖斯塔克的《尼莎:一个昆丹妇女的生活与言语》、罗莎尔多的《知识与激情:依龙哥特对自我和社会生活的看法》、克拉帕扎洛的《回归的礼仪:摩洛哥人的割礼》等作品,都充分展现了这种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主题的多样化造就了描写的细致化和深入化。比如,格尔茨对巴厘斗鸡的深描展现了鲜血、家族及权力等关系系统;而在保罗·韦斯利的《学着劳动》中,读者看到了民族志作者对于本文化的批评以及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性经验。从异文化到本文化、从边缘到中心的主题变换,表征了民族志主题的多样性。而在这种主题选择下的民族志作品,显得比经典民族志更为精细和丰富,避免了以往民族志那种单调乏味、无厘头的描述弊端。就像格尔茨所说的,民族志描述有四个特点,除了它是解释性的、社会性会话流、把会话解救出来和固定术语固定下来之外,民族志还有第四个特点,即它是微观的。(25) 最后,价值人性化。民族志作品体现出来的人性化,不仅仅是指对研究对象的尊重,也能显示出民族志作者的真实个性,更能彰显出人类学追求人性普同的目标。格尔茨的“深度描写”和“当地人的立场”的“经验相近”、民族志的对话式文本的出现、依龙哥特人的“心灵地图”,都是尊重调查对象的产物。而《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公开,正如雷蒙德·弗斯所说的:“一旦它得以面向大众读者出版,作者必然会同时招致批评与赞赏;所以公正地来讲,他即使不被同情,至少也应该被理解。”(26)王铭铭也认为:“他以少见的勇气,表达了他对人类学家与他的‘活人材料’之间关系的阳光与阴暗面,他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不控制自己的笔触,这一做法几乎是一种美德,源于马氏对待自我最真实的自省,展现出一位对社会科学之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十足又耐人寻味的魅力。”(27)人类学是对人性进行探寻的学科,文化多样与人性普同本应是其永恒不变的价值追求。西方中心主义和为殖民主义服务的书写目的早已得到遏制,人类学公众化和公众人类学,“对于人类学家来说,任务仍然是重新整合或重新发明他们在当前从事人类学的意义,从而使公共人类学的根本愿望在对此学科的目的有清晰理解的大众中得以实现”(28)。 对于民族志实验场中出现的以上结构特征,我们应该从辩证的视角去看待和分析它们。既要看到它们对于民族志发展的贡献,也要看到它们背后展示出来的不足。欧内斯特·盖尔纳说:“后现代人类学是相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主观性和自我放任。归根到底,后现代主义人类学的实际意义好像是这样:拒绝(实践上有很大的选择性)承认任何客观事实和任何独立的社会结构;反对调查对象和调查者不对多重意义进行寻求。”(29)虽然盖尔纳对民族志实验的总结看起来有些过激,我们不应该否认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种种实践确实带给了我们一些好的田野工作方法和撰写民族志的进路。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美国人类学家诺曼·邓金眼中的民族志书写给民族志发展带来的危害。他说田野民族志作者对各民族的描述应该超越传统的、客观的写作方式,写作出更具实验性、更具经验性的文本,其中包括自传和基于表演的媒体;更多地表达情感;文本要小说化,借此表达诗意和叙述性的事实,而不是科学事实;同时还要面向活生生的经历、实践,采取多视角进行写作。(30)如此看来,盖尔纳对后现代人类学特征的总结也不为过,后现代人类学的随意性、混合性、边缘性等特征确实存在。那么,就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实践场中的结构,恰恰预示了一种新的反结构文本的存在。 同时,民族志实验场中的结构与反结构态势并存,又一次再现了格尔茨讲的那个乌龟驮乌龟的寓言故事,好像永远找不到解决危机和问题的办法。诚然,人类学是对异民族的研究,研究主体本身就带有一个两难的困境:如果异族与我们不同,那么研究他们对理解我们有什么意义?如果异族与我们相同,我们研究自己好了。然而,我们不可能不去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人类学,短短的一百多年历史已经证明了它存在的必要。“实验潮流对民族志实践的探究和质疑,只能被视为是健康的。实验潮流应该被当作过程来理解,因为它展示了人类学的变迁。”(31)因此,民族志实验从正反两方面打开了把握民族志科学性的大门,带给了我们诸多启迪和思考。 三、民族志科学性探析 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的研究工作已经表明:我们(现代文化群体)所接受的逻辑规律并非具有普遍性,某些边远地区土著居民具有与我们不同的逻辑。(32)格尔茨也说:“人类学,或至少解释的人类学,是一门科学:其进步不以达于观点的一致为标志,而是以辩论的巧妙为标志。使我们在争论中彼此激怒对方的精确性才是最上品的。”(33)我们不禁要问:文化志的描写以及其研究方法到底能否阐释文化,它们在方法论上是否还有指导意义?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在理论上到底有没有可能性?(34)当然,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还是首先来弄清楚何为科学?科学是指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物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从这个定义上去看,科学至少包含三个基本的要素:事实、规律和实践,以事实为基础,以规律为对象,以实践为标准。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也要具备以上三个基本要素。同理,作为人类学标志的民族志要追求科学性,则要在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下工夫。而要达到文化描述的真实性和文化批评的至善性,则又需要我们弄清楚真实和价值的互相关系、真实的本质、获得真实的方式、价值的评价标准等相关问题。知识性问题的真实在一定条件下只有一个,而评判性问题的价值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多元。在两者关系中,真实是基础,价值是核心,真实和价值有机统一。把以上理论和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诉求结合起来,我们能很清晰地得出民族志危机问题的解决和民族志科学性的建构,不外乎就是如何获得真实和彰显主流价值两个方面的问题。 民族志真实是指民族志主体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民族志要达到真实,会涉及谁去写、写什么、怎么写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以及调查者与被调查者、被调查者与文化、调查者与文化、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和文化等一系列相互关系。在如此众多的问题和关系中,归之一点,就是如何看待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民族志要书写真实,简单地说就是要找到联系主体和客体关系的途径和方法。综观民族志书写历史,从表面上看,业余民族志既非客观又非主观,经典民族志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后现代民族志做到了主客观的统一。这样去看,民族志书写危机应该得到了解决,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我们可以从西方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和中国人类学家朱炳祥的研究中去发现端倪。克利福德在《写文化》中这样说道:“本书中的作者没人认为任何文化描述都一样好坏。如果他们支持一种如此无足轻重和自我拆台的相对主义,他们就不会花那么大的力气去写作详尽的、有承担的批评研究文章了。”“承认民族志的诗学纬度并不要求为了假定的诗的自由而放弃事实和精确的描述。‘诗歌’并不局限于浪漫的或现代主义的主体性;它也可能是历史性的、精确的、客观的。当然,它也像‘散文’一样为惯例和制度所决定。”(35)那么,在克利福德眼中,什么样子的民族志文本是尊重事实和好的?他认为民族志的写作至少以六种方式被决定:语境上的、修辞上的、制度上、一般意义上、政治上的及历史上的。这些决定因素支配了内在一致性的民族志虚构的铭写,他因此认为民族志的真理本质上是部分的真理。(36)从克利福德的论述中,我们能看到他也承认民族志写作是有一套制度和规范的,文化描述还是要追求一定规律性,不是追求绝对的相对主义,现实的历史和权力等因素使民族志书写只能达到部分性真实。而在朱炳祥的研究中,他借用福柯的话语和权力理论,在民族志书写中主张多重主体,第一主体即田野对象、第二主体即民族志作者、第三主体即评审者,通过三重主体的叙事而形成文本,用以去解决后现代民族志的困境。(37)再结合他有关民族志书写理论的其他文章,我们能够看到他提出的多重主体的民族志看到了主体间、主体与客体、田野的关系,确实解决了民族志撰写中诸多问题。比如,他在文章中用了一个后现代词语“互镜”(38)作为连接不同主体的纽带。但是他也在文章中这样说道:“‘主体民族志’是对科学民族志的颠覆,但这种颠覆并不在于用一种范式去取代另一范式,而是对各种范式意义的根本性质疑,进而达到对不同民族志作者及作品的相对性真理的认可与平等性地位的确立。‘主体民族志’消解了民族志作者建立话语霸权的雄心。既然所有的民族志都是主体的建构,那么所谓的客观真理就不再存在,某一个或者某一派人类学者的话语霸权就显得滑稽可笑。”(39)自此,我们知道了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是部分真实,而朱炳祥则认为民族志没有真实可言,有的只是不同的主体。笔者不禁要问:民族志的目的如果不是对真实的追求,人类学还是人类学吗?部分真实和真实的区别何在?一门学科存在的主旨何在?一门学科成熟的标准是什么?究其根源,其实在于研究者还是没有找到连接部分与整体、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真正纽带。 民族志真实来自实践,实践是检验民族志真实的唯一标准。基于此,笔者认为解决民族志危机、树立民族志科学性的唯一方式则是建立“实践民族志”。实践本身具有主观能动性、客观规律性和社会历史性的特点,因而能够很好地把民族志书写中的主体、客体联系起来;实践检验真实的标准是确定的,也是不确定的,因而实践中的真实就具有绝对真实和相对真实两个属性;实践本身就是不断运动、发展的,这是对于以往民族志种种实践的认同和批判;实践离不开田野,这就奠定了民族志书写的根基。因此,实践民族志的建构,能奠定民族志书写的实践本体论基础、认识论基础和价值观取向。当然,在实践民族志建构过程中,还需要具体的方法和策略。作为一门不断走向成熟的学科,人类学要在发展战略层面上,即理论和原则上具有一定确定性,同时在发展策略上,即具体方法和路径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也就是说,民族志书写中必须要有一定的“硬核”和一定的“保护带”。在硬核中,田野是基础,田野工作是动力,整体观、尊重、理解“他者”、保护文化客体是原则,求真至善是目标。在保护带中,民族志体裁、修辞、主题、具体范式,则随着实践情景可以不断变化。只有这样,民族志书写才能得到继承和发展,民族志描述的真实性才能得以保证。 民族志科学性不仅仅指在文化描述上的客观,也指文化价值上的至善,价值上的至善是其真实性的指向和目标。人类学学科是十分注重历史的,在对历史理论和实践的认识和批判基础上,一种新的文化批评才能产生。今天,人类学已走过了为殖民主义服务和西方中心主义的阶段,正迈向新的阶段,这是人类学本质的回归。比如,当代人类学的两种文化批评方法,即认识论的批评法(epistemological critique)与泛文化的并置法(cross-cultural juxtaposition),都把批评的矛头指向自我,也就是采取“变熟为生”(defamiliarization)策略。这也说明随着对原始部落和异族研究吸引力的下降,人类学有回归本土的研究趋势,这就拓宽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和主体,当代公共人类学随之呼之欲出。人类学历来具有公共关怀,正是学科内在的文化批评的纬度构成了推动它研究其他社会的根本动力。公共人类学的呼唤反映出影响到学科自身实践的跨学科参与以及各种学术共同体和实践的多样性;映射出过去人类学开展学科探索的背景的真实变化;显示了把当代作为将在不远的未来浮现的最近的过去而理解势不可挡的时间方向。因此,在公共人类学建构的背景下,人类学的公众应该是指当代民族志研究自身的复杂路径所触及的公众。同时,人类学这门学科将在它的研究努力上更关注它的责任、伦理和对各种他者的义务,而不是关注它作为一门学科进行推动的行会似封闭的,对辩论、模式和理论传统的痴迷。(40)只有在公共人类学下,文化多样、人性普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科理念才能充分展现。尊重、理解、平等、公正、反思、人文、和谐本应是人类学的应有之义。 综上所述,笔者主要从民族志表述危机的三种表象入手,看到了产生民族志危机的缘由,并在此基础上认为民族志危机是文化描述和文化批评上的危机。而在人类学界试图解决民族志危机的种种“幻象”中,呈现出结构和反结构两种民族志书写态势。在对以上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要真正地把握民族志书写的科学性,则应从文化描述的真实性和文化批评的至善性入手。只有这样,民族志书写危机和实验民族志的种种实践才能被充分认识,民族志书写才能达致求真至善的目标,人类学才会是真正关于人类,进而为人类服务的学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志危机是民族志科学性探寻的引爆点,实验民族志的种种探索是民族志科学性建立的基础和出发点,而民族志科学性则是解决民族志危机和理解实验民族志的最好途径和目标诉求。 注释: ①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8页。 ②参见[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35页。 ③参见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④参见王铭铭:《民族志:一种广义人文关系学的界定》,《学术月刊》2015年第3期。 ⑤参见朱靖江:《虚构式影像民族志:内在世界的视觉化》,《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 ⑥参见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事的新范式》,《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⑦参见张连海:《感官民族志:理论、实践与表征》,《民族研究》2015年第2期。 ⑧参见蒋逸民:《自我民族志:质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⑨参见李银兵:《批判与反思:实践民族志建构的必然性探析》,《云南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⑩[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30页。 (11)[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35页。 (12)[美]保罗·拉比诺:《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高丙中、康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55页。 (1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4页。 (14)[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27页。 (15)Geertz,Clifford.Works and Lives: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149. (16)Said,Edward.Orientalism.New York and London:Penguin,1978,P.12. (17)Hylland Eirksen,Finn Sivert Nielsen.A History of Anthropology.Pluto Press,2001,p.148. (18)[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高丙中等译,第286页。 (19)李清华:《民族志文本生产与话语剧场创造——格尔茨〈作品与生活〉的文本现象学》,《广西民族研究》2013年第4期。 (20)[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21页。 (2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6-207页。 (22)朱炳祥、刘海辉:《“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23)[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296~297页。 (24)王铭铭:《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8页。 (25)[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27页。 (26)[英]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卞思梅、何源远、余昕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页。 (27)[英]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中文版序第8页。 (28)[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21页。 (29)Gellner,Ernest.Postmodernism,Reason and Religion.London:Routledge.1992.p.29. (30)转引自阿兰·巴纳德:《人类学的历史与理论》,王建民、刘源、许丹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184页。 (31)[美]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E.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第227页。 (32)Levy-Bruhl.The Notebooks of Lucien Levy-Bruhl.trans.P.Rivere.Oxford:Blackwell.1975.p.43. (3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第37-38页。 (34)[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煊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导读第16页。 (35)[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54-55页。 (36)[美]詹姆斯·克利福德、乔治·E.马库斯:《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第34-35页。 (37)朱炳祥、刘海辉:《“三重叙事”的“主体民族志”微型实验》,《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38)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39)朱炳祥:《反思与重构:论“主体民族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40)詹姆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第25页。标签:科学论文; 人类学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民族志论文; 科学性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范式论文; 民族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