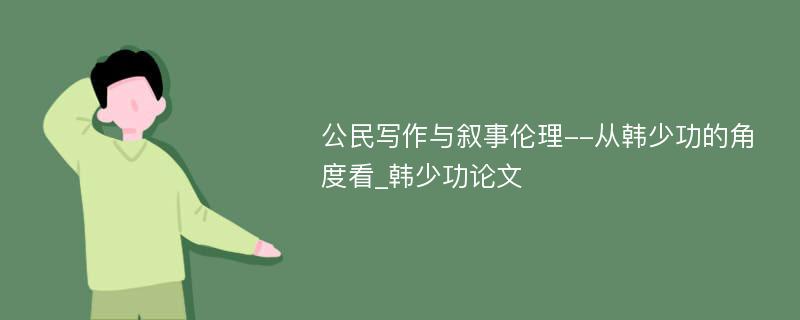
公民写作与叙事伦理——由韩少功的一个主张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公民论文,韩少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公民写作”,是韩少功在答记者问时的一个提法:
我也有兴趣参与一些基层的生产创收和制度改革的活动,近年还顺手写过一些有关社会经济事务的文章,一篇在乡镇干部座谈会上关于全球化的文章,还引起过一些经济学专家的讨论。有个记者问这是不是“知识分子的写作”,我说这是“公民写作”,因为公民都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
(2002年10月18日《中国文化报》)
这个说法就我所知,此前似乎没有人提及,少功提出后也没有引起文学界的关注。我觉得这个提法很有意思,具有比较大的解释空间,而且与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学批评的现状有某些深层关联,值得进一步探讨。
从韩少功的本意看,他所谓“公民写作”,是指文学创作以外的写作;在他看来,这些写作本身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写作。那么我们可以提出的问题是:
如果说他的非文学写作是“公民写作”,那是否意味着,他的文学写作就是非公民写作?
如果“公民写作”与非公民写作是内容与形式均有根本不同特征的两类文体,那么其实质性区别是什么?
假如作家写一篇有关全球化问题的文章,是以公民身份参与一项公共事务,表面上看当然与文学无关,但这文章是否能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彻底区别开来?也就是说,一篇谈论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问题的文章,是否没有任何文学性?
同样的逻辑,作家在写小说或诗歌时,我们是否可以说,其身份肯定不是公民,其心态思维与公民意识无关,其作品之意义与价值,也绝对与公共事务无关?换言之,从事文学创作时的作家,可以没有公民的身份和公民的意识,他只是一个超离于公民社会之上,或存在于公民社会之外的一个另类,异数?文学理论的常识告诉我们,并非如此。
本文不打算对上述问题逐一作思辨讨论。为了简明,我只从对韩少功的理解出发,对当代中国部分作家在社会中的自我定位和角色意识略作考察,进而谈谈我对批评家喜欢谈论的所谓“叙事伦理”的看法。
一 韩少功的公民意识与“公民写作”
根据我对韩少功本人和他创作的理解,我认为,韩少功有非常明确而强烈的公民意识,自从成年以后,他始终都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现代的公民:遵纪守法,敬业乐群,具有高度道德自觉意识,在文学创作以外,不断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奉献,尽己所能帮助一切可能帮助的贫困弱者。韩少功是一个相当低调的人,他在这方面的德行善举一般当然不为人知,只有极少数接近他日常工作和生活圈子,了解他行事准则和为人风格的朋友,才略知一二。其中又只有很少能见于文字记载,孔见所著《韩少功评传》、廖述务著《仍有人仰望星空——韩少功创作研究》、廖述务编《韩少功研究资料》这三本书中,约略可见一点这方面的记载。
把韩少功定位为公共知识分子是比较确切的,虽然他本人未必认可。道理很简单,他在创作之外,对社会始终保持高度关注与批判性思考。且不论他早期对社会政治文化活动的关注与参与(他所作《文革为何结束》一文最能看出这方面的蛛丝马迹),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诸如人文精神讨论、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环境与生态问题、“三农”问题、现代性、发展主义、恐怖主义、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等当代世界和中国的这些重大问题上,韩少功都有自己的思考。他通过演讲、对话、接受媒体采访、策划选题编组文章、主持召开学术会议、组织系列读书讨论活动、出席国内外各种会议等方式,鲜明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对思想文化界乃至全社会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韩少功曾经领导创办了当代中国最具社会影响的综合性新闻杂志《海南纪实》,该杂志在1988-1989年短暂存活期间创造的社会影响与发行量两项纪录,迄今国内同类杂志未有超越者。他曾经主持的新版《天涯》,是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思想界一面灿烂夺目的旗帜,后起效仿者不乏其人,同样未有超越者。他这些创作外的“事功”,足以媲美中国当代任何公共知识分子。
从韩少功的写作看,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从早期的小说到近些年的散文随笔,都能体现他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对世界与中国的政治现状,经济问题,社会文化,世风人心的强烈关注和严肃思考。这是积极介入的一面。他还有保守、传统的一面,那就是,他在创作中始终坚守文学的纯洁境界、高尚理想,我们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暴力叙事、色情描写,看不到对丑恶世相的津津乐道,他拒绝粗鄙的语言、下流的文风。而这种坚守,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已经很罕见了。他的立场和原则很鲜明,那就是,文学不能给读者以假、丑、恶的不良影响。他对那些以流氓加才子自居的当代走红作家相当蔑视,鄙而远之。在我看来,这乃是一个有良知作家所应有的职业道德,是公民意识和公民责任在文学专业领域的具体体现。而这种职业道德与文学界流行的所谓叙事伦理之说,截然不同。
简单说,我认为,韩少功提出的公民写作主张,体现了作家与社会最为合理之关系定位。他既不自外于、孤立于社会,又不完全认同、融化于社会,他与社会保持可贴近观察体验而又超然物外的微妙距离。他既是有坚定人生信念、具普世情怀与全球视野之“世界人”,又是蕴涵强烈民族情感与国家意识之中国人;他是怀疑人类终极价值之虚无主义者,又是珍重个体道德品质之理想主义者;他是从内心深处超越了世俗羁绊,蔑视人生功利目标与物质实惠的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又是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尽其所应尽、所能尽义务之优秀公民。
二 当代作家的角色意识
我首先要设定,现在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公民社会;即使它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比较纯粹的公民社会,也已经具有了公民社会的基本雏形;至少中国的部分人群,已经具备了比较成熟的公民意识,韩少功所言所行,就是证明。
但总体上看,中国作家们对自己的作家身份可能相当在意乃至敏感,而对自己的公民身份则可能未必有自觉认同。他们中很多人是把两者对立起来看的,他们当然喜欢前者而漠视乃至鄙视后者,甚至于,他们可以声称以当作家为耻,可以真假难辨地、矫情地以反文化、反文学的流氓自居,但很少人乐意做一个普通公民。因为,公民与平民百姓实在相差无几,而平民百姓的身份大致就是平凡平庸的同义语,故这样的定位,是极难为他们接受的。
近三十年来的中国作家,其自我角色意识的发展演变有迹可寻。70年代末那些“重放的鲜花”们(五十年代右派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从维熙等),其中很多人把自己定位为苦难承受者,他们的作品(所谓大墙文学)是苦难的结晶。这种意识与他们所接受的中国苦难诗学理念(司马迁:诗文乃贤圣历尽苦难而发愤所为作)、俄罗斯文学中的承受苦难和忏悔救赎精神高度契合:诗人作家既是不幸的时代受难者,更是替全民族承担苦难的悲情英雄。他们曾经的文学地位确实与此有关。80年代中期,年轻一代作家受19世纪以来欧洲浪漫主义、现代主义的深刻影响,以张扬个性,反叛传统,探索尖端形式的文化先锋、艺术精英自居。这些中国的艺术精英在心理上与平民社会的距离,大体约等于纽约、巴黎到中国内地那些中小城市的距离。上世纪90年代开始,作家开始从社会文化的中心位置逐渐退居边缘,先锋精英“堕落”为普通人,作家成为被嘲讽的对象(如王朔),从正面意义上,则有人(如王蒙)特别强调文学应当回归自我,他们在反对将文学地位神圣化、文学属性政治化、文学作用夸大化的同时,也一并反对文学当中的英雄情结和理想主义,从而开启了文学世俗化直至低俗化的时代潮流。最为极端的情形是,部分人以反体制的姿态倡导文学的流氓化,我是流氓我怕谁、下半身写作之类肆无忌惮的宣言,把作家的神圣光环彻底摧毁,流氓诗人、流氓作家的说法因此而被合法化,堂而皇之地招摇于文学世界。90年代中期以后,市场经济的狂潮再一次对文坛进行全面清洗,流氓化文学被冲刷殆尽的同时,市场化巨浪又催生了新一代靠“码字”致富的作家,他们成了商业意义上的文化英雄,近年作家富豪榜的推出,表明写作这一行当成功的价值标准已经转化为金钱的数额。诚然,没有几个作家站出来表示以富豪为荣,但也没有谁站出来表示不屑或反对。在传统中国,君子固穷,文人潦倒本是常态,蔑视金钱利禄更是传统文人的基本价值准则,但这一切,在商业化大潮中彻底改变了。潦倒的文人肯定不是成功的文人,而成功的标志不是文章的水准而是稿酬的标准。郭敬明、于丹们成为千万富翁的同时,也成了著名的作家学者。
早期的悲情英雄,中期的先锋精英,稍晚的流氓作家,最近的文学富豪,不同时期的这四类作家,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公民意识或平民意识,他们似乎是有权超越道德禁忌,不负社会责任,具有绝对思想自由和行为自由的独特群体。张贤亮透过章永璘等人物表达的落难者高高在上的心态,不过是作家本人自我意识的文学表达罢了。先锋派的诗人和作家在世俗生活中的各种反常规、超常规行为,常常会得到反常、超常的理解和宽容,顾城杀妻之举当年获得很多人的同情与理解,其中一些人为顾城辩护的理由是,因为他是一个有才华的诗人,所以应该拥有超越人伦法律行事的特权。至于王朔走红时代一些人对流氓合法化的辩护,就更为普遍,他们的理由是,流氓行径可以成为瓦解压抑人性的陈旧体制、颠覆不合时宜的迂腐道德的有效力量。顺着这个进程看下来,我们就不会奇怪,何以郭敬明明目张胆抄袭而且敢于拒不认错,却能得到王蒙的推荐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王蒙著名的辩护词是:加入作协又不是选举道德模范!在王蒙看来,写作者只要才华足矣,道德?干他何事!这种立场和主张并不新鲜,翻阅19世纪以降的欧洲文学史,类似主张乃至更为极端的见解触目皆是。
三 公民道德与叙事伦理
可以设问:一个普通公民有杀人的正当权力吗?有做贼而不受惩罚反受奖赏的权利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作家是否可以无视公民社会的法律和基本道德准则,成为不受任何约束的无法无天之徒?
诚然,真正杀人做贼的诗人作家毕竟是极个别人,绝大多数作家仍然循规蹈矩生活在世俗社会中,仍然接受这个社会的法律和基本道德的约束。但这不等于,在他们内心深处,没有杀人做贼的冲动和欲望。当他们把这种冲动和欲望通过作品宣泄出来时,他们的意识就被合法化了,而且经常会得到赞扬和鼓励,因为他们表达了人类意识深处的黑暗和邪恶。而这,正是一些批评家所强调的应该给予肯定与支持的作家的“叙事伦理”。
中国自古就有“文人无行”,“一为文人,便不足观”的说法,小说家从一开始,就与街头巷尾的流言家,与宫廷的弄臣戏子,联系在一起。到了清末,大力提倡新小说企图刷新国民精神的梁启超,没多久,就对新小说家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大加挞伐了:“近十年来,社会风气一落千丈,何一非所谓新小说者阶之厉?循此横流,更阅数年,中国殆不陆沉焉不止也。”他愤怒地诅咒道:“公等若犹是好作为妖言以迎合社会,直接阬陷全国青年子弟使堕无间地狱,而间接戕贼吾国性使万劫不复,则天地无私,其必将有以报公等:不报诸其身,必报诸其子孙;不报诸今世,必报诸来世。”(《告小说家》)百年前的小说家在相当开明的梁启超看来竟然如此不堪。不知那些毫无道德意识的当AI写作手看到这些陈旧议论会作何感想。从接受西方影响一面看,19世纪以来,特别是浪漫主义以降的西方文艺思想,一直有如此主张:要求艺术家道德,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歌德),诗人就是这个世界的匿名立法者(雪莱),超越世俗社会的伦常道德,乃是诗人作家的最高道德。“作家唯一该做的,就是对他们的艺术负责。只要是好作家,就会胆大妄为……为了写作,荣耀、自尊、体面、安全、快乐等都可以牺牲,就算他必须去抢劫自己的母亲也要毫无不犹豫,一篇传世之作抵得上千千万万个老妇。”(福克纳)当代批评家谢有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作家要把文学驱赶到俗常的道德之外,才能获得新的发现——惟有发现,才能够帮助文学建立起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属于它自己的叙事伦理和话语道德。用米兰·昆德拉的话说,“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乃是小说惟一的存在理由。一部小说,若不发现一点在它当时还未知的存在,那它就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知识是小说的惟一道德。”(《中国作家的道德陷阱》,2005年12月20日《南方都市报》)
这里涉及一个对小说功能的认识与定位。小说的社会作用究竟是什么?是用来发现人内心世界的未知领域的吗?如果是,那么发现的最终目的又是什么?是了解人性之恶以学习模仿之,还是警醒教化之?很显然,没有谁愿意承认,文学展示人性之恶是为了大家学习效仿,虽然实际效果常常如此;几乎所有表现人心黑暗道德沦丧的作家,都和《金瓶梅》作者一样,声称表现邪恶就是为了警醒读者,因此他们的动机是纯洁高尚的。但我们看看欧洲19世纪以来那些著名乃至伟大作家的生活形迹,就知道这样的表态是不可信的,倒是那些赤裸裸肯定、赞美人性的邪恶,肯定作家一切放浪形骸为合法光荣的人,反倒更可爱一点。当他们站在社会通行道德对立面,主张另一种彻底自由、解放的个人道德时,其实客观上也在肯定他们反对的东西,因为这些人毕竟是另类、少数,多数人必须按照世俗社会的庸常标准来生活,否则这个世界早就被人欲彻底毁灭了。而多数人的社会必须有自己的道德标准,这就是为什么欧洲浪漫主义新风尚与所谓维多利亚时代“虚伪道德”同时存在的根本原因。现在看来,19世纪的浪漫主义后来固然日益占了上风,但20世纪初期欧美新人文主义的兴起,最近几十年基督教保守势力的复兴,包括伊斯兰宗教的复兴和中国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抬头,正说明,被近两百年来的现代性艺术理论奉为永恒正确的那些反伦常道德也就是反世俗社会价值标准的叛逆姿态和极端主张,已经受到了最强有力的挑战。
四 还我一个干净的公民社会
没有教育功能的小说是不存在的,差别只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从古代的柏拉图、孔子到今天的美国和中国,人类社会对文学艺术的负面教育功能有基本共识:过度渲染的色情和暴力对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极为有害,因此必须对文艺作品的相关内容给予限制直到禁止。面对这个铁一般的事实,无限制的否定任何道德前提的所谓叙事伦理能够成立吗?
如果事情仅仅如此,那倒也罢了。因为叙事伦理毕竟也是一个“学术问题”,倡导尊重叙事伦理的批评家,当然不是在鼓吹社会的道德败坏。但问题在于,不少人把无所约束的“叙事伦理”贯彻到实际生活中来,为了成为作家,不妨先做流氓;创作是否成功尚未可知,流氓行径已然先行,而且美其名曰体验生活!所以,在客观上,肯定作家的无限制的叙事伦理特权,实际上给一些人抛弃内心的道德约束提供了理论依据。假如这种体验的后果和效应仅仅局限于作家个人或小团体范围内,那倒也罢了,因为初看起来,这也是所谓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无法干涉,也不必干涉。但问题在于,这样的体验常常演变为社会化的行为,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经典性的现象莫过于20世纪后半叶以来盛行于西方,近几十年传播到中国的行为艺术。美国当代作家哈里·克罗斯认为,为了成为天才艺术家,必须先达到疯狂境界,或者干脆成为疯子;而要达到这种境界,必须借助于酒精、大麻、性爱、鸦片。他放浪形骸,纵欲狂欢直到以自杀结束三十岁的年轻生命,难道仅仅是他个人的选择、个人的利害得失而与社会无关吗?梁启超当年对小说家的诅咒,我看也可以移赠给哈里·克罗斯及其在中国的追随者和信徒。
因此,我认为在当代社会,应该提出一个主张:一个人首先是公民,其次才是作家。作家应该有高尚的道德,而不是相反。历史上特别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历史上,无视道德乃至生活颓靡到彻底腐败程度的诗人作家确实大有人在,他们确实写出了伟大的作品。但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逻辑:为了创造伟大作品,我们应当鼓励、至少要容忍作家的道德沦丧,如克罗斯那样。作家个人出于自己的考虑,要按照克罗斯的逻辑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那是他的自由,文明社会也很难干预。
问题还在于批评家。批评家们是站在培养作家的立场上,以作家导师自居,给他们出主意,指方向,寻找成名捷径,还是站在维护公社会大众根本利益的立场上,要求作家必须承担他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现在的批评家更多是与作家结成同盟,相关的难听一点说就是沆瀣一气,以“阬陷”国民、尤其青年一代为能事。很少有批评家站在社会良知和大众读者立场上说话,这正是文学批评日益堕落的根本原因之一。
写作何为?如果我们承认作家无法自外于社会而存在,无法否认作品总要成为社会文化产品之一类而对读者发生影响,那就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你可以不是英雄,你可以坦然做平民,可以自封为流氓,可以坦然做富豪,成明星,但你不可以不对自己的社会身份有一个基本的定位与认识:你是不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假如你承认这个身份,那就意味着这是你发表作品所应该坚守的身份“底线”——公民要遵纪守法,公民要有基本的社会责任和义务,公民的写作自然也应该如此。
以摧毁人类基本伦理为无尚光荣的后浪漫主义世纪应该结束了。我们在持续性的是非混乱、人性肮脏、行为邪恶、文化丑陋的世界里已经呆得太久了,我们渴望一个平静、祥和、理性、干净的公民社会。
作家艺术家,请你们理解并掌握人类那些最基本的词汇吧:
天道,菩萨,性命,良心,良知,德行,善恶,美丑,诚伪,真假,敬畏,同情,怜悯,悲怆,自省,忏悔……
标签:韩少功论文; 文学论文; 公民权利论文; 艺术论文; 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作家论文; 道德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