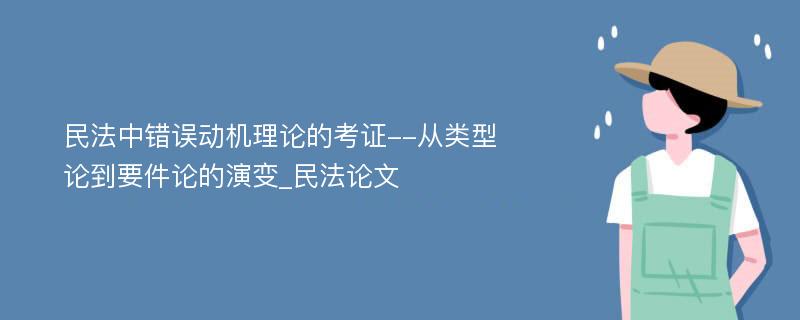
民法动机错误论考——从类型论到要件论之嬗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要件论文,民法论文,动机论文,错误论文,类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错误代表了非正常意思表示之典型,在传统大陆法系诸国特别是德国和日本,有关其法律构成、法律效果的学术论争长盛不衰,而在错误的诸问题中,最耐人寻味的当属动机之错误。围绕动机错误之法律意义特别是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关系,各种学术观点竞相争妍,但基本上可以归置于两大理论阵营,即严格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原则上将动机排斥在法律评价之外,仅仅在例外条件下才给陷入动机错误者一定救济的“类型论”或者说“二元论”立场,以及不特别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通过设定统一的错误构成要件,对所有符合构成要件的、包括动机在内的错误表示进行保护的“要件论”或者说“一元论”立场。从总体上看,目前已经开始并仍在继续着从类型论到要件论的嬗变过程。我国对错误的立法是通过“重大误解”概念来完成的,不仅条文内容笼统,对动机错误只字未提,而且,在主要大陆法系诸国构成理论聚集的错误论,在我国似乎从来都没有成为民法研究的中心议题,特别是对于动机错误,除蜻蜓点水般地陈述“除非表示于外,动机错误原则上不影响法律行为效力”这一类型论思想外,学界呈现出高度的默然,专题研究成果尚付诸阙如。有鉴于此,笔者写作本文,期图能唤起学界对错误研究的重视并将该问题逐步引向深入。
一、类型论:表示错误、动机错误之严格区别
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的区别,在德意志前期普通法学即已初见端倪。(注:关于前期普通法学的错误论,参见〔日〕野田泷一《萨维尼错误论之形成》一文。(〔日〕原岛重义.近代私法学的形成与现代化理论[C].九州大学出版会,1996.229-268.))作为后期普通法错误论的源流,Savigny以自然是德意志观念论的“自由”哲学为基本视角,努力实现早期普通法传统中所蕴涵的思想的体系化[1]。Savigny从法律行为论的意思主义原理出发,将当事人之“意思”作为通过法律行为变动权利义务的根据,在他看来,表示错误是“不真正错误”,其本质为“意思欠缺”,表意人此刻之所以受法律保护,不是因为其陷入错误,而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与表示相对应的意思[2](故不能按表示行为发生效力)。与表示错误相反,动机错误属于“真正错误”(而非意思欠缺),除非动机以“条件”或“前提”的形式构成法律行为的内容,否则即便该动机表示于外,原则上也不受法律的保护。因为,在动机错误,构成法律行为的基本事实要素——“意思”已经存在,而且该意思与表示完全吻合,动机坏过是该业已存在并表示于外的意思形成过程中的缘由而已。如果将动机错误纳入法律保护范畴,则交易将陷入无边的肆意与不安,交易安全也难以维系。事实上,基于交易安全之价值判断,将动机置于法律评价之外,也是德意志概念法学思想的产物。诚如Egger所言,19世纪的法律学,为推动产业资本主义社会交易的安全,追逐法律行为理论的“技术化”(Technisierung),特别是通过所谓“分离法”(Isolierungs-Methode),使特定法律行为事项独立化、抽象化(Abstraktheit),最终从基本行为以及原因(Causa)中解放出来,在这一点上,不能不说对动机的无视与抽象物权契约理论、票据行为无因性理论一脉相承[3]。Savigny的上述认识构成了后期普通法错误论的机轴,并对那一时期的立法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民法(第一草案)》几乎是Savigny错误论的直接翻版:一方面规定(表示)错误无效(第98条);另一方面也明文强调,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动机错误不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第102条)。尔后的《德国民法典》第119条规定意思表示“内容错误”的法律行为可撤销,法条文言虽未触及动机错误问题,但若考虑民法典作为后期普通法沉淀物之属性,在其错误法的底流中,对普通法上支配性立场的继受应毫无疑问[4]。
日本“旧民法”即《普阿索纳德草案》第309条原则上否认动机错误对法律行为效力的影响。现行《日本民法典》第95条规定“要素错误”的意思表示无效,并未明确将动机排斥在法律评价之外。的确,单就文义解释而言,动机错误或许可能包含于第95条所规定的错误之中。但若结合体系解释,由于《日本民法典》第101条将意思欠缺、诈欺、胁迫并列为影响意思表示效力的因素,错误显然只能包括于意思欠缺之中(除错误外,意思欠缺还表现为真意保留、虚伪表示)。特别是,《日本民法典》规定意思欠缺→无效,而因欺诈、胁迫所为的意思表示→可撤消,更是凸显了其错误法上的意思欠缺构成。在因欺诈、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存在与表示行为相对应的效果意思,只不过该效果意思的形成过程(动机)中存在瑕疵,故可统称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在通常的动机错误,与表示行为相对应的效果意思也客观存在,故充其量将其归入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之范畴。可见,区分意思欠缺与有瑕疵的意思表示,构成了日本法律行为体系的基本框架,动机错误从属于意思表示之瑕疵,而《日本民法典》事实上又未将其作为有瑕疵的意思表示予以明确规范,乃因传承了《德国民法(第一草案)》,代表着立法对动机错误的公然无视[5]。为了实现立法无视动机之原则,通说力图对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的区别予以明确地把握,通过“表示行为的错误”概念指称表示错误,并将“表示行为的错误”进一步细化为“表示上的错误”和“有关表示行为意义的错误”即“内容的错误”[6]。在通说看来,意思表示的形成过程可以归结为:(1)动机(或缘由);(2)意欲发生一定私法效果的意思即效果意思;(3)通过一定表示行为发表效果意思之意思,即表示意思;(4)表示行为。动机错误为(2)之形成阶段即从(1)到(2)的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例如误以为将铺设铁道而高价购买附近土地的意思表示,误将劣马作为受胎的良马而购买(劣马)的意思表示(与表示相吻合的、购买土地或劣马的效果意思客观存在);有关表示行为意义的错误(内容的错误)为表示意思形成阶段即从(2)到(3)的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如本意为购买甲马,误以为甲马为正在马厩中的马匹,作出购买“现在马厩中的马匹”之意思表示,而事实上该马为乙马(购买甲马的效果意思,与购买乙马之表示不一致);表示上的错误为表示行为形成阶段即从(3)到(4)的过程中出现的不一致,包括表意人自身和表示中介人行为引发的不一致,前者如本欲书写为100英镑出售(表示意思并无瑕疵),却不小心写成100美元出售;后者如邮局误将100英镑出售的电报译为100美元出售(效果意思与表示显然不一致)[7]。
二、类型论框架内对动机错误的例外保护
德、日两国民法典维持错误论的意思欠缺之构成,原则上将动机错误排斥于法律评价之外,通过切断法律行为与原因之关系以图交易之安全。尽管鼓吹交易安全为“近现代市民法最高理想”者不乏其人,但法学界也一直没有停止对交易安全至上主义的质疑与批评,追求交易安全保护“正当性”(Richtigkeit)和“相对性”(Angemessenheit)的呼声亦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律行为领域,基于交易类型的不同,特别是在消费者与事业者的契约关系中修正交易安全保护的绝对性,将动机适当地纳入法律评判视野,不仅代表了对冲突利益的合理调节,甚至也意味着对市民法中基本人性的回复[8]。时至今日,彻底闭塞对陷入动机错误者的法律救济之门的不妥当性,已然成为法界共识。其实,就连动机错误、表示错误类型论的最忠诚捍卫者Savigny本人也认可动机错误的例外受保护性,认为动机以“条件”或“前提”的形式植入法律行为内容时,类型论的原则不再适用。此外,关于对象性质的错误,即便其不构成《德国民法典》第119条2项的“本质性错误”(error in substantia)而仅仅停留在动机错误的层面,Savigny也主张通过瑕疵担保责任对买主提供保护[9]。但在德国,为抑制民法典无视动机之弊害,竭力实践动机法律价值的当推Windscheid的“前提理论”和Larenz的“行为基础论”。Windscheid指出,对意思的自我限制,除了通常所谓的附条件、附期限外,还包括通过“前提”对意思进行限制。例如,以嫁资形式进行的赠与,就是以婚约的存在为前提。如果前提不存在或事后灭失,若债务已经履行,则发生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而在债务尚未履行的情况下,则产生针对履行请求的前提不存在的抗辩权。虽然Windscheid并未言明前提缺失的意思表示无效,但其所谓履行内容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和针对履行请求的抗辩权与意思表示无效的后果如出一辙[10]。Larenz一方面承继了前提理论,同时又对此作出了一定程度的改良。其将被当事人作为契约基础的前提事实称为“行为基础”,当行为基础不存在或灭失时,将导致契约的解除或者契约内容的调整。尤应注意的是,Larenz将行为基础二分为主观的行为基础和客观的行为基础,以嫁资形式进行的赠与,其行为基础为主观意义上的婚约;而不动产买卖契约缔结后发生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以致等价关系的破坏,则表现为客观行为基础的丧失。尽管行为基础构成要件暧昧不明,特别是主观行为基础的构成无法限定,但不能否认的是,正是通过该主观行为基础概念,使得动机具有了法律意义(而客观行为基础理论渐次演化为日后的情事变更原则)。虽然按行为基础理论,基础的缺失仅导致契约的解除或契约内容的调整,但如同前述前提理论一样,其在客观上践行了(动机错误)意思表示无效之效果。事实上,德国的大量判例也是借助前提理论和行为基础理论,对陷入动机错误者提供法律保护的[11]。
日本通说一方面维持错误法的类型论构成,严格区分表示错误与动机错误;但另一方面,也积极探寻法律例外保护动机错误的途径。富井政章将《日本民法典》第95条规定的“法律行为的要素错误”概念置换为“有关法律行为(意思表示)内容的重要错误”。而是否构成法律行为内容的重要错误,并非以错误发生在行为的哪一阶段来(客观地)确定,而只能根据表意人的意思来(主观地)判断。若当事人“将动机作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则动机错误也可能构成要素的错误。至于何为“将动机作为意思表示的内容”,即便在富井的论述中也暧昧不明,其本来密切维系于当事人意思,但也不排除通过交易习惯对该意思作出推定的可能[12]。鸠山秀夫也将民法典上的“法律行为的要素错误”还原为“意思表示的内容或目的之错误”,认为在确定意思表示的内容时,只能以具体的表示行为为基础进行解释,即从外部的、客观的表示行为中合理推断出的当事人意图,构成意思表示的内容。关于何为动机错误,仅以心理学的基准是难以判断的,动机是否构成意思表示内容的错误也应以具体的表示行为为基础进行解释[13]。不能否认,鸠山说与富井说之间有一定的连续性,但在动机如何成为意思表示内容这一问题上,富井从表意人的意思中寻找答案,而鸠山则注重从外部表示行为去探知,而这种客观化立场也为动机被法律更广泛地评价提供了可能。我妻荣比鸠山更为重视表示在法律行为中的作用,主张以表示行为为本体对意思表示内容进行纯粹客观的观察。就动机而言,如果其仅秘而不宣地存在于表意者的内心,则不能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而其一旦表示于外,使对方知悉其内容,则动机错误转化为法律行为内容的错误,这就是构成日本通说内容之一,并对我国法律行为理论产生过重要和持续影响的“动机表示必要说”。日本的判例也大体上维持着“动机表示必要说”的立场。其中,既有以动机未表示为理由否定法律行为“要素错误”的判决(如最判昭和38、2、1民集64、377),也有以动机表示为理由肯定法律行为“要素错误”之判决(如最判昭和39、9、25民集75、525)。针对通说、判例的立场,也有学者认为,无论动机怎样地表示,都不会导致意思与表示的不一致,依然仅为意思形成前阶段的错误。但这些学者也主张在动机表示的情况下,类推(而非适用)错误无效的规定[14]。另有学者指出即便存在动机之表示,动机错误也不构成意思欠缺,而依然从属于意思瑕疵,应类推适用民法有关意思表示瑕疵(欺诈、胁迫)之规定[15]。但在例外地保护动机错误这一点上,上述观点实际上与通说、判例的立场较为接近[16]。
三、从类型论到要件论
通说、判例所持的严格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立场,遭遇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异常猛烈的批评,在批评过程中渐次形成了以动机错误、表示错误一元化为前提、实行统一的错误构成的要件论观点,并取代通说而成为现在的多数说。多数说的批评主要围绕着后述几个方面展开。
首先,类型论以对意思表示形成过程的心理分析为前提,然而事实上,从心理学的角度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特别是内容错误至为困难。根据通说,将劣马A误认为良马B而作出购买A马的意思表示为内容(客体)的错误即所谓“同一性错误”(购买A马的意思表示与购买B马的效果意思不一致);但若误信劣马A为良马而作出购买A马的意思表示,则仅构成有关A马性质的动机错误(在购买A马这一点上表示与效果意思相一致)。在前例中,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无非是观念上的一纸之别,难怪学者指出,有关表示行为意义的错误即内容错误与动机错误根本就无法区别,将错误理解为意思欠缺的通说之观点,仅仅在表示上的错误(如误记、误传)才具有合理性[17]。有趣的是,在力倡错误类型论的德国后期普通法学,对动机错误范围的认识也并不统一。例如,Savigny不仅将客体错误(error in corpore)即“同一性错误”归于内容错误,而且“本质性”的性质错误也被作为内容错误的形态之一,只有“非本质性”的性质错误才停留在动机错误的阶段(《德国民法典》第119条也持该立场);而Zitelmann则认为,只要实现了客体的个别化和特定化(如已经作出了购买A物的决定),不独该客体的性质,甚至对该客体同一性的错误,从意思形成的心理过程来看,都应视为动机错误[18]。
其次,即便能从心理学上区分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这样的区分在法律上也毫无意义。为了消除前述动机错误和表示错误认定上的分歧,日本学者川井健特别使用了狭义动机错误与广义动机错误的概念,并认为日本民法学没有充分研究动机的概念,没有把握动机概念的广、狭两种含义,正是导致判例和学说纷争之根源。在川井看来,动机是狭义的动机,即常识意义上的、纯粹心理学上的、作为生活事实的行动原因、要求、动因、诱因,动机错误是主观的理由错误或者与目的物没有任何关联的错误。“之所以买帽子,是因为去年买的帽子丢了”,在该意思表示中,“去年买的帽子丢了”是动机。相反,“之所以买,是因为该帽子质量好”,则属于意思表示对象性质的错误,该性质已经形成了意思表示的内容。判例和通说将性质错误也作为动机错误,无非是对动机错误的扩张,使其包括并不当然构成“要素”的一切内容,从而,法律上的动机与生活上的动机出现了不一致,动机也因此成了“非要素”的同意语[19]。(注:在动机法律效果问题上,川井主张回到类型论的原点,即狭义动机即便表示于外,也不受保护;广义动机即便未表示于外,也受保护。)姑且不论狭义动机和广义动机的区分在心理学上能否成立,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狭义动机错误,还是广义动机错误,或者此外的其他内容的错误,在表意人“真意”(真意与效果意思是不同的概念,关于二者的关系,可作如下的理解:误将A马作为B马,而作出购买A马的意思表示(同一性错误、内容错误),此刻效果意思为购买B马,真意也是购买B马,真意与效果意思一致,但都与表示不一致;误以为劣马A是良马而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有关性质的动机错误),效果意思为购买A马、真意为购买良马,由于真意与效果意思不一致,虽然效果意思与表示一致,仍不影响“真意的欠缺”)欠缺这一点上,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动机错误甚至构成了“真意”欠缺的典型[20],其在形式上是错误的“继子”,实际上是错误的“实子”[21]。而综观日本判例,被作为错误处理的几乎所有事案其实都不过是动机的错误[22]。不仅如此,以“真意欠缺”为视点,基于错误的意思表示与因欺诈、胁迫而为的意思表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二者在适用上完全可能出现重合,因此,《日本民法典》所固持的意思欠缺与意思表示瑕疵的法构造也失去了合理性。
再次,类型论从意思主义的立场出发,谋求表意人保护和交易安全保护的平衡点是不成功的。如前所述,类型论一方面将表示错误理解为意思欠缺,本着“没有意思即没有义务与责任”之原则,对陷入错误的表意人进行救济;另一方面,又将实际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动机错误排斥在错误保护之外,结果大大限制了意思表示无效(被撤销)的范围,从而兼顾了交易安全。殊不知,只要法律将重心置于表意人真意、使错误影响意思表示的效力,不仅动机错误、其他错误也一样会危及到交易安全,错误制度自身就是作为交易安全的对立面而存在的[23]。仅在动机错误的情形寄予对交易安全的热情,而在其他错误则沉湎于意思主义的思考,不能不说有些精神分裂。事实上,从表示主义的立场,也完全可以对错误制度进行理论上的说明,也就是说,基于一定的要件(而非区分错误的类型)对错误无效(可撤销)的规则进行限定,通过保护对表示的信赖以图交易之安全。多数说主张,除了通说、判例所肯定的表意人重过失、要素错误等要件外,还应特别考虑相对人对错误的认识可能性,只有相对人明知错误(恶意)或因过失而不知时,错误无效(可撤销)的规则才能适用。
最后,动机“表示必要”说缺乏根据。考虑到动机的千差万别,通说一方面不得不例外地承认对动机错误的保护,但同时又以动机的表示为条件。其实,错误的本质即意味着其对表示不具有亲和性,这在动机错误和表示行为的错误并无差别。对于表示行为的错误,通说并未特别要求以表示为错误保护的条件——即便要求恐怕实际上也不太现实,因此,惟独要求动机的“表示”失去了理论上的连贯性[24]。通说要求动机表示于外,乃立足于动机本非法律行为内容之判断,认为只有通过“表示”动机才能转化为法律行为的内容。然而,何为法律行为的内容,从属于法律行为的解释问题。法律行为内容的确定,旨在确定可以从行为者有意识地选定的外部行为态样以及其他外部事情的总体中推断出的行为者的真意。因此不能否定对方可以认识的、从表意人行为过程中能推断出的真意也可以成为法律行为的内容。故无论动机表示的有无,只要具备预见可能性,就可以作为法律行为的内容。从外部事实总体(特别是预备交涉)推断,若能客观认定意思表示以一定事实为前提,则以该事实为前提也构成了意思的内容,动机也可包括于该事实前提中[25]。其实,动机的表示无非是为判断相对人的认识可能性提供了有益的认定参数。在通常情况下,相对人应当认知表示于外的动机,但也绝不能说相对人了解表意人动机的同时就了知该动机的错误,因此,在日本也存在动机虽然表示于外,依然拒绝适用错误规则的判决(如最判昭和37、12、25民集63、953)。相反,如果相对人已经洞察到了表意人的动机错误,或者有理由判断其应当知道表意人的动机错误,即便动机没有表示于外,也有认可错误无效的判决(如最判平14、7、11判时1805、56)。此外,还有一些判例虽然形式上固守“动机表示”,但对表示作极其广义之解释,不仅认可默示之表示(如最判平成元9、14判时1366、93),甚至有判例(如东京地判平元8、21、判时1349、70)就动机表示的认定,纯粹采拟制的构成,与其说是基于契约缔结过程中的具体事实直接认定动机之表示,不如说是因为契约当事人的特殊性、契约的性质和目的,从客观上认为动机是契约缔结的当然的前提,即相对人对动机错误的认识可能性显而易见。也就是说,通过对动机表示的认定方法之活用,在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方面,判例已经相当程度地融入了多数说的思想,从而与多数说的立场业已非常接近[26]。
四、一元化的错误构成要件
综上,动机错误与表示错误的区分不能成立,不仅一律将动机错误排斥在错误法之外流于武断,而且以“表示”作为动机受保护的条件也大有疑问。但在采行统一的错误概念后,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错误要件应如何构成,在多数说也未必统一。较为普遍的看法是通过表意人无重过失、相对人的认识可能性、错误的重要性三项指标对错误法的适用进行限定。在有关错误要件的形形色色的议论中,舟桥谆一教授所倡导的“阶段性”要件论尤为引人注目。在舟桥看来,错误要件论的实质,是平衡错误者保护与交易安全,故错误要件构造的最终落脚点,也就是谋求该种平衡点。具体而言,其错误要件的内容为:(1)存在错误(包括动机错误)的事实;(2)错误与表示之间的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不仅表现为如果没有错误表意人不至于作出该意思表示,而且更表现为一个通情达理的“理性经济人”同样不会作出该意思表示,即对因果关系采主、客观相结合的构成;(3)相对人的认识可能性。如果相对人明知表意人陷入错误,或者因过失而不知,则已无保护相对人的必要,交易安全与表意人保护的平衡问题不会发生,可直接基于意思主义的立场,使错误影响法律行为的效力,而无须继续考虑后述要件是否成立;(4)表意人对错误是否存在重过失。但这并不是表意人错误主张的要件,而是相对人对抗错误主张的手段,故重过失的举证责任存在于相对方。如果证明了表意人的重过失,考虑到相对人的善意无过失,已不存在特别平衡表意人保护与交易安全的必要,应直接基于表示主义之立场,肯定法律行为的效力,也无须继续考虑后述要件之成立否;(5)错误是否为法律行为要素的错误。在前述要件全部满足的情况下,表意人利益和交易安全利益陷入了直接而尖锐的对抗中,此刻,作为双方利益的平衡点,是否构成法律行为要素的错误至为关键。舟桥指出,不能将法律行为的要素错误,简单地等同于错误与表示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意思主义和表示主义的调节器,要素错误具有与诚实信用原则等一般条款相似的特征和功能,其内容只能在法官结合具体的案件事实,针对个案作出自由裁量后才能探明。但法官在进行自由裁量的时候也应遵循一定的基准:第一,不能仅依表意人对错误程度的主观认识来判定;第二,应结合具体交易的性质或条件。如在古画、古董买卖中,很难鉴别商品的真伪(卖方也不知真伪),通常奉行“买主当心”的原则,如买主以为是真品而购买,即便日后鉴定为赝品,一般也难以认定为要素错误。再如,将劣马误以为良马而购买,但该买卖的价格与劣马相当,也不大可能作出要素错误的认定;第三,表意人、相对人或者第三人受非难或同情的事实的有无。例如,相对于保证人误信主债务人谗言而债权人全然不知的情形,若债权人对保证人受骗也有一定的过失,则更容易认定要素错误。需要指出的是,此刻作为判定要素错误的参考因素,相对人方面的受非难因素不应达到恶意或因过失而不知表意人错误的程度;而表意人方面受非难的因素也不应达到重过失之程度,否则如前所述,已无通过要素错误之认定去平衡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之必要;第四,因意思表示的有效或无效对表意人、相对人或第三人造成的影响。以表意人和相对人的关系为例,在赠与等单务无偿行为,相对于买卖等双务有偿行为,赠与人的意思表示更容易被认定为要素错误[27]。
但多数说强调相对人认识可能性的错误构成也存在颇多疑问。例如,A古董店标价1万出售的瓷器,B以为其时价应在2万以上,而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实际上该瓷器并不值钱,就连1万的价格也显得过高。在该例中,即使A认识到了B的错误,也很难认容B之错误主张。因为在此等完全仰赖自身鉴赏力而选购商品的交易中,如果商品价值与B的判断吻合,B可以保有盈余利益,法律通常并不支持来自A的错误主张,与此相对应,B自身错误评价的风险也应自行负担。但若对前例稍加调整,情况将大不一样。设B并非从古董商店A,而是在百货商店C的瓷器专柜购买,考虑到B作为普通消费者在专门知识上的欠缺,其与作为事业者的C百货公司存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关系,在认识到B的错误时,C负有订正该错误的契约上义务,而绝不能主动利用消费者的错误获利。事实上,基于特别保护消费者的法意识,已有学者主张针对消费者设定较一般错误构成更为宽松的要件[28],并且出现了反映该种见解的相应立法。(注:日本《电子消费者契约法》第3条规定,消费者通过电脑等画面为要约或承诺的意思表示时,虽然因重大过失而发生意思表示错误,其错误主张也不受影响。但若事业者在电脑等画面上准备了确认消费者意思的设置,或者消费者自行放弃该设置,其重过失将影响错误之主张。)如此看来,在错误要件论中应受重视者,并非相对人方面单纯的知或不知(恶意、善意),而表现为相对人能否利用表意人之错误(利用可能性)。若要对此作出准确的判断,不能仅仅关注表意人的意思表示过程以及相对人的主观认识状态,更应回顾交易的前前后后,并充分把握隐藏在交易背后的习惯以及各种社会“关系”[29]。那么,除了事业者不能“利用”消费者的错误之外,又是否意味着其他普通当事人之间,一方对另一方错误的利用都是合理的呢?为了解答该问题,加藤雅信教授主张引入诚实信用这一一般条款,通过禁反言原理进行判断。也就是说,错误构成的中心,不在于相对人的认识可能性,而在于对相对人的非难可能性,如果相对人以过失或者其他方式“关与”了表意人错误之形成(但并未达到欺诈、胁迫之程度),通常可以认定其非难可能性。例如,甲女向乙男赠送并交付订婚礼品,乙男在接受礼品时并无与甲女缔结婚姻的意思(且其行为不构成欺诈),甲女发现该事实后提出错误之主张,此刻,法律认可甲女之错误请求并不是单纯地基于乙男对甲女错误的认识可能性,而是因为乙男的暧昧促成了甲女的错误并积极利用该错误,乙男的行为违反了减实信用原则,根据禁反言法理,不能使其获得额外的利益(订婚礼品)[30]。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在普通的当事人之间,若相对人并无违反诚实信用原则之行为,在其对表意人的错误存在认识可能性时,表意人的错误主张是否也都不能成立?例如,甲收集到某地段将修建高速公路的情报,打算在该高速公路入口附近建加油站,为此购入位于该处的乙之土地,但事实上该地段并无修建高速公路的计划。或者甲女误以为能和丙结婚,为准备结婚在乙家具店购入大量家具,而丙根本无与甲结婚的意愿。此刻,甲仅仅是为自身的利益追求而购买土地,而追求利益必然伴随着风险,本着风险与利益同在之原则,即便乙对甲之错误存在认识可能,似乎也没有理由使乙负担因甲的错误主张而导致的不利益。甲女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和丙结婚并购入家具,尽管甲女的处遇非常令人同情,但这毕竟属于其个人私事,与乙并无特别关联,即便乙有可能认识到甲女之错误,使其负担该错误产生的不利益也不近情理。为了使前述两例中陷入错误的表意人受保护,在意思表示的相对人方面,于认识可能性之外,还应附加某种要件。加藤雅信教授将该要件表述为“前提的合意”(“深层意思”)与“内心效果意思”(“表层意思”)之间存在不一致。如果甲乙二人都误信在某地段将修建高速公路,甲购买乙位于想象中高速公路入口的土地,此刻,“甲购买乙位于未来高速公路入口处的土地”是双方的“前提的合意”(尽管其并未明确表现出来,但的确是客观存在的“合意”),而“甲购买乙的这块土地”则是“表层的合意”,由于事实上该地段修建高速公路纯为空穴来风,乙的土地并非高速公路入口的土地,“前提的合意”与“表层的合意”显然不一致,故应认容甲之错误主张。相反,即便表意人以特定的事实为自身意思表示的前提条件(通常表现为默示行为),但并未与相对人就该前提形成合意,纵然该前提破裂,也不能简单地承认表意人的错误主张[31](正是在这一点上,加藤教授的“前提的合意”论区分于Windscheid的“前提”论)。虽然,加藤教授的“前提合意论”可谓匠心独运,但就其实质而言,无非力图将错误主张限制在共同错误之中。由于共同错误中双方都陷入了错误,并不存在相对人对意思表示的信赖问题,从严格意义而言甚至也不涉及相对人对错误的认识可能性问题(尽管多数说的不少学者认为共同错误中,相对人当然构成恶意[32]),故全然超越了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对立,与其说加藤教授是在认识可能性要件上附加了前提的合意之要件,不如说是通过前提的合意要件对认识可能性要件的取代。需要强调的是,前提的合意与表层合意不一致即共同错误时,不仅不应(事实上也无法)考虑相对人的认识可能性问题,而且表意人的重大过失也不妨碍其错误之主张,否则相对人将获得意想不到的利益。毕竟,相对人也陷入了错误,其并不具备通过使法律行为有效而获保护的正当利益[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