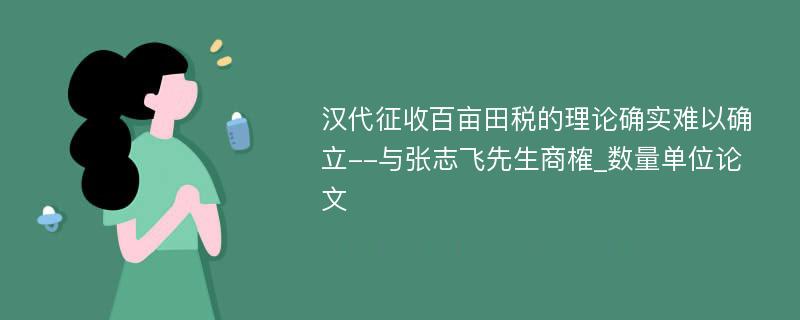
汉代田税百亩征收说确难成立——与臧知非先生再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代论文,百亩论文,臧知非论文,说确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 (2001)04-0113-08
臧知非先生在《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与农民田税负担新探》(以下简称《新探》,刊于《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一文中, 对汉代田税征收方式提出了新观点:汉代田税是以百亩为单位,而不是以亩为单位、按实耕亩数计征。我在《也谈西汉田税征收方式问题》(以下简称《也谈》,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 期)一文中提出了商榷意见,认为《新探》的观点难以成立,相反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看,汉代田税是以亩为单位、按实有亩数征收的。为此,臧先生在《再谈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问题》(以下简称《再谈》,刊于《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一文中对笔者进行了批评,并运用一些新材料对其观点进行了补充论证。笔者仔细拜读《再谈》后,觉得这个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故撰此文,以就教于臧先生和学界方家。
第一,关于战国秦朝田税征收方式和对“汉承秦制”的理解问题。
(1)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实行授田制。 这种观点目前已为多数学者认可。一些材料反映秦似乎是以顷为单位授田,如云梦秦简《田律》云:“入顷刍稿,以其授田之数,无垦不垦,顷入刍三石,稿二石。”[1]据此,《再谈》认为,“入顷刍稿”就是征收刍稿, 以顷为单位计算征收,其余谷物当然是按顷征收。进而又认为,战国以顷为单位授田,农民都要交纳一顷良田的国税。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难以成立的。
首先,刍稿征收方式并不等同于田税征收方式。刍稿与田税都属于土地税,但刍稿并不是田税。云梦秦简《仓律》规定:“入禾稼、刍、稿,辄为癐籍,上内史。刍、稿各万石一积,咸阳二万一积,其出入、增积及效如禾。”[1]又云:“禾、刍、稿积索出日, 上赢不备县庭。出之未索而已备者,言县廷,廷令长吏杂封其癐,与出之,辄上数廷。其少,欲一县之,可也。”[1 ]云梦秦简《田律》规定:“禾、刍、稿撤木、荐,辄上石数县廷。勿用,复以荐盖”。[1 ]此处“禾”即谷物,是田租征收的对象,与刍稿的区别很明显。《汉书·贡禹传》:“已奉谷租,又出稿税。”《汉官仪》:“田租稿税,以给经用”。在《后汉书》诸帝《纪》中,屡见“勿收田租、刍、稿”或“勿收租、更、刍、稿”的诏令。这些记载表明:刍稿与田租(田税)是各不相同的税种。《再谈》认为“刍稿之征是田税的一种”,则显然有误。战国各国对谷物即田税的征收都要考虑实际产量,这与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条所规定的不管土地耕种与否,农民都要按顷交纳定额刍稿有明显不同,如《商君书·垦令》曰:“訾粟而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之“量入修赋”,《孙子兵法·吴问》有:“范、中行是(氏)制田,……而伍税之。”《管子·大匡》云:“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岁饥不取。”另外,秦简之《法律答问》曰:“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口口匿田。”[1]这段话的意思是, 部佐对已收取田租的土地不上报为匿田,对未收取田租者则不为匿田。这说明政府对农民的土地,并不是统一以百亩为单位收取田租,也不是不管耕种与否都要按授田数征收,而是有较大的合理性和变通性,否则,就不会存在“匿田”的问题。这与刍稿征收方式的不同是很明显的。实际上,云梦秦简《田律》之“入顷刍稿”只规定刍稿的征收方法,而没有规定田税的征收方法,这本身就已说明田税征收与刍稿征收是不同的,决不会是法律条文的疏漏。
其次,秦国授田以顷计,但田税征收并不是以顷计。云梦秦简《仓律》云:“种:稻、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答大半斗,叔(菽)亩半斗。利田畴,有其不尽此数者,可也。”[1 ]这条材料一方面说明秦国谷物征收的多样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秦国农民所拥有的一顷之地并非单纯种植某一种谷物,否则,政府对谷种的规定就应是顷用多少,而不是亩用多少了。既然农民谷物不是以顷为单位种植,那么,谷物征收当然不可能以顷计征。实际上战国时期统治者往往鼓励农民几种谷物并种,以便在灾害和不测时自我调剂。如《管子·牧民》记载:“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通典·食货二》亦云:“魏文侯使李悝作尽地力之教……必杂五种,以备灾害;力耕数耘,受获如盗寇仇之至。还庐树桑,菜菇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授田百亩的农民,其土地也被分割成几块,以种植不同的谷物。这样,田税就不会按顷征收,而只能以亩为单位,按谷物实际种植的面积征收。《孙子兵法·吴问》有:“范、中行是(氏)制田,以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而伍税之。……[智是(氏)制田,以九十步为畹,以百八十步为亩,而伍税之。]……韩、魏制田,以百步为畹,以二百步为亩,而伍税之。……赵是(氏)制田,以百步二十为畹,以二百四十步为亩,公无税焉。……”[2 ]这里明确说明田税以亩为单位计征。《管子·君臣》:“有道之国,发号施令,而夫妇尽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功农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此处的“一亩之赋”反映了当时田税按亩征收的现实。
最后,战国时期有些国家不是以顷为单位授田。如《庄子·让王》记载:“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此处所引是否为孔子与颜回的原话当然可以考证,但其中田亩数是基于当时的现实,正反映当时有的农民土地远低于百亩。《管子·禁藏篇》亦曰:“食民有率,率三十亩而足于率岁。岁兼美恶,亩收一石,则人有三十石,果蓏素食当十石,糠秕、六畜当十石,则人有五十石。布帛麻丝,旁人奇利,未在其中也。”此处的三十亩田不管属一人或一户,都无法得出每户农民有田百亩的结论。实际上,战国各诸侯国各自为政,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不平衡,统一以百亩为授田单位是根本不可能的。《再谈》认为战国“制土分民之法,都是以五口之家、百亩之地为标准”,显然不符合史实。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农民怎么可能又“都要交纳一顷良田的国税”?
故此,我认为,战国时期各国授田的标准具有多样化特征,即使像秦魏以顷为单位授田的国家,其田税征收也不是以顷为单位,而是以亩为单位,按实有亩数计征。
(2)关于“汉承秦制”问题。《再谈》认为, 西汉在对待六国贵族和地方豪强的处置的方式、分封宗室为王、工商业政策各个方面确实是“变通”秦制或改变秦朝的政策,但是就土地制度和田税征收方式而言则继承了秦制。其根据是刘邦称帝伊始所发布的“复故爵田宅诏”。
对该条诏令,《再谈》认为“对于普通农民来说则是恢复其原来所占有的土地。所恢复的爵位当然是秦朝二十级军功爵所规定的爵级,田宅自然是秦政府所授予的田宅”。同时认为,汉初之《九章律》,“其基本内容也是承秦而来,‘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无疑和秦朝的军功赐田一致,‘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之‘法’很可能就是指秦法而言。‘行田宅’就是授予田宅,有功劳者按功劳大小增加授田数量,没有功劳者则耕种原来官府授予的份地。”这种理解仍可商榷。
其一,“复故爵田宅”是针对“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的脱籍流民,所恢复的并非秦政府授予的田宅。众所周知,公元前216 年秦王朝颁布的“使黔首自实田”令,是对农民土地私有权的法律承认,而在此之前,农民土地私有权事实上已普遍形成。实际上,在战国末期,各国因直接控制的土地越来越少,授田已逐渐废止,农民对土地的私人占有权已被事实上的私人所有权所代替,土地买卖已经出现。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记载:“今括一旦为将,东向而朝,无敢仰视之者,王所赐金帛,归藏于家,而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3 ]土地买卖必然促使土地在占有者之间转移,导致土地占有不均,有的甚至完全丧失土地,这在秦朝后期已不罕见。如《史记·陈丞相世家》谓陈平和他的兄嫂只有三十亩地,远少于百亩。当时还有一些身为“编户齐民”的雇农,如阳城人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3 ](《陈涉世家》),可以肯定他们的土地更少或没有土地,否则没有必要为人佣耕。《再谈》认为“秦朝农民实际占有土地和纳税土地是一致的”,其意思是说,秦朝农民最少都还有百亩土地,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在授田早已废止,土地私有制确立和土地频繁转移的情况下,秦末汉初农民的田宅怎么可能是秦政府授予的呢?“复故爵田宅诏”所要恢复的田宅不是授田制下的国有土地,而是农民的数量不均的私有田宅。实际上,“复故爵田宅”也并非是恢复战争前私有田宅的原状,因为由于战争的破坏和流民的逃逸,房屋的损毁和田园的荒芜是必然的,加之人口的死亡和相互迁徙在战争中都是巨大的,所以,以前的秩序被破坏殆尽,根本无法恢复。这样,“复故爵田宅”应当理解为让流民重新回到土地上,重建家园,进行农业生产,恢复原来的生产生活秩序。
其二,“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很明显是针对立有功劳的人,与无功劳者无关,《再谈》以“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推断“没有功劳者则耕种原来官府授予的份地”,是没有根据的。“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实际是一种赐田,不同于授田制。汉代的赐田是私有性质,可以说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史籍记载的汉代赐田很多。如《汉书·苏武传》:“(赐苏武)秩中两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4 ]此处“公田”指赐田来源于国有土地。《汉书·卜试传》:“上乃召拜式为中郎,赐爵右庶长,田十顷,布告天下。”汉武帝时赐其姐修成君田百顷。[4](《外戚传》)《汉书·王嘉传》:“诏书罢苑,而以赐(董)贤二千余顷”[4]。这是西汉赐田数额最大的一次。这些赐田来源于国有土地,但赐出后即为占有者私有。《再谈》将“行田宅”作为授田制无疑不符历史真实。另外,“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之“法”不可能是秦法。《汉书·高帝纪上》载刘邦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在此情况下,“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之“法”怎么可能是秦法?《再谈》本身对此也不敢确定,而只说“‘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之‘法’很可能就是指秦法而言”。那么,由此而推出的结论当然是不可信的。
总之,秦朝的基本土地制度是私有制,不是授田制形式下的土地国有制,如果说汉代在土地制度上继承了秦朝,那继承的是土地私有制,而非土地国有制。仅仅以“复故爵田宅诏”和“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令,根本不能说明汉代是否继承了秦朝的土地制度。
第二,如何理解晁错所说的五口之家、百亩之田问题。
《汉书·食货志》载晁错一段话:“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新探》认为此处的“百亩”是汉代以顷计税的证据。我在《也谈》中认为“晁错所说,只是以汉代‘能耕者’,即拥有土地较多的自耕农家庭为例,来说明汉代农民的一般负担,并未涉及国家计算田税的土地面积,这里的‘百亩’只是一个概数,犹如‘五口之家’是指一个家庭大约的纳税人平均数。”《再谈》认为,“如果明白了上文所指出的战国秦朝的授田制是以顷为授田单位的话,对晁错的这段话就不会作出上述解释了,更不会把‘能耕者’解释为‘拥有土地较多的自耕农’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战国实行授田制,有的国家虽是以顷为授田单位,但其田税并不是以顷为单位计征,而是以亩为单位,按谷物实际种植的面积征收;秦朝实行土地私有制,很多农民的土地远少于百亩,其田税征收也是以亩为单位。晁错所云的五口之家、百亩之田仅仅是举例说明问题,因为举例论证总要选择具有代表性、常见的事例,否则就缺乏说服力,汉代农民家庭显然并非都只有五口,也不都只有百亩土地,只是五口之家、百亩之地在当时较为常见而已。臧知非先生对此未加详察,见到“顷(百亩)”,辄以为是授田和纳税单位,似乎过于敏感,殊不知在先秦到两汉的古文献中,“亩”字也是随处可见的。
第三,对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的6 号木牍记载的平里、稿上两地征收户刍、田刍和田稿的情况,其所征刍稿都精确到“升”或“半升”,这只有以“亩”为单位征收才会出现。
其一,《再谈》认为,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就实行名田制,其根据是商鞅变法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汉代也实行名田制,如《汉书·食货志》所引董仲舒的一段话:“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兴,循而未改。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由于商鞅的名田制是授田制,故汉代的名田制也是授田制。对于商鞅变法之法令,《再谈》认为,“其含义就是先明确爵级的高低差别,授予不同数量的田宅,以‘名’占田,不得逾越等级限制,也就是所谓的‘名田制’”。我认为,以上解释未必妥当。因为如果把“名”解释为“授予”,那么其宾语应是“田宅臣妾衣服”,授予田宅尚可讲得通,授予臣妾衣服则在逻辑上和史实上都行不通。实际上,此处的“名”是“名籍”即户籍,“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意思应是“户等、田宅、臣妾、衣服各有一定等级,不得逾越。”《商君书·徕民》:“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此处的‘名’也是指名数、户籍。可见,秦根本不存在汉代的“名田制”。
汉代“名田制”的“名”是自行度计申报之意,这一点不同于作为户籍解释的“名”。《说文解字》:“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对汉代的“名田”,颜师古注曰:“名田,占田也。”[4](《食货志》颜师古注)关于“占”字, 郭璞云:“占,自隐度也。”汉武帝“算缗钱”,下令“各以其物自占”,就是令物主自行度计财产申报之意。[4 ](《食货志》)云梦秦简《傅律》有“匿敖童,及占癃不审,典老赎耐”[1]。意思是隐匿成童, 及申报废疾不确实,里典、伍老应赎耐。所以,“名”、“占”,都是自行度计申报之意。可见,颜氏将名田释为占田是有根据的。名田,就是通过自行申报土地数量,从而取得对土地的合法占有,这实际是秦朝“使黔首自实田”的发展。“名田”与“自实田”一样,一方面说明国家对土地私有制的法律承认,同时也反映当时国家无法掌握个体家庭所拥有的土地数量及农民土地不均的事实。百姓申报土地是与户籍联系在一起的,故“名田”又是“籍名田”。《史记·平准书》谓汉武帝时曾规定“贾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属,皆无得籍名田,以便农。敢犯令,没入田童”。司马贞《索隐》注曰:“谓贾人有市籍,不许以名占田也。”“若贾人更占田,则没其田及童仆,皆入之于官也。”“籍名田”从字面解释就是“以籍名田”、“以籍占田”,“籍”是指户籍。由于户籍还可称为“名籍”、“名数”、“户版”、“名”等,故“以籍占田”又是“以名占田”,“以籍名田”又是“以名名田”,前一个“名”指户籍,后一个“名”是自行度计申报之意。“以名占田”就是说,户籍是占田的基础,是“占田”、“名田”合法化的一种要求,这说明了户籍与土地的密切关系。如果说在授田制情况下,户籍是授田的基础,那么,在“使黔首自实田”以后,户籍就是申报并合法占有土地的基础。《史记·平准书》所引汉武帝时的法令,说明在此之前商人是能以户籍占田的(商人名田主要以购买获得),即合法占有土地,同时也反映“名田”是私有土地,而非国家授田,因为“敢犯令,没入田童”的处罚是针对再“名田”的商人,若是授田制,则处罚应主要针对负责授田的官吏。
实际上,上文所引董仲舒的一段话已明确说明了名田制的私有性质。董氏认为从商鞅变法至汉,土地买卖和兼并频繁,这显然是土地私有制的特征。董氏对战国土地制度的认识是否准确,当然值得讨论,但他对汉代土地制度的描述是真实的。正因为董仲舒对引起当时土地兼并的名田制不满,所以才提出“限民名田”的主张。何谓“限民名田”?颜师古注曰:“名为立限,不使富者过制,则贫弱之家可足也。”而在此之前是不存在“限民名田”,可见,“限民名田”就是对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数量加以限制,使之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这就是汉武帝问事六条中惩处“强宗豪右,田宅逾制”[4 ](《百官公卿表上》)者的原因。但是,这里的“制”,是指一定等级所能拥有土地的最高额,而不是都必须拥有这个最高额的土地(也就是必须低于或等于这个最高额),更不是国家授田制下的授田标准。“限民名田”作为对私有土地拥有量的限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很小的,这是因为私有制本身具有很强的突破能力。此外,汉代土地买卖非常盛行,也说明了名田的私有性质。如《汉书·食货志》引贾谊的一段话中有“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尝债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汉书·霍光传》:“大为中孺买田宅而去。”甚至汉成帝亦“置私田于民间”。[4](《五行志》)《再谈》认为,“名田制、 授田制是一制异名,传统称谓是名田,今人谓之授田,其本质是以课促垦,保证税收。”这显然是错误的。造成这种错误,除了对“名”字的理解错误之外,还因为混淆了“名田”与“限民名田”的概念。
另外,关于秦汉的土地制度,《新探》认为“授田制又是国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的过渡形态,土地一经授予就不再还授,长期固定于私人名下,久之即归私有。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土地更成为私有财产的主体,土地兼并必然发生”。而《再谈》又认为秦朝和战国一样实行授田制,进而认为汉代的“名田制”也是授田制。这种前后抵牾的认识让人费解。
其二,《再谈》认为,木牍所载的“田刍、田稿数量甚微,是否是平里、稿上两村农户所交的田税的一部分,虽然无法肯定,但颇值得怀疑。因为按秦汉社会结构,其乡、里一直存在着一定数量的公田,这些公田并非全部处于抛荒状态,有一部分是被垦种的,其收入主要用作基层政权的运转费用;这些土地是否交纳一部分刍稿?虽然因资料限制目前无法确知,但交纳的可能性要大一些”。我们认为,汉代“公田”是确实存在的,但其主要经营形式是“假名公田”(因屯田与我们要论述的问题无关,故此处从略),其办法是国家将控制的可耕田租赁于百姓(主要是贫民、流民),收取高额地租。《汉书·元帝纪》:“在位诸儒多言盐铁官及北假田官、常平仓可罢,毋与民争利。”这说明国家经营“假名公田”带有牟利的目的。学界一般认为“假名公田”自汉武帝始,并且有专门的官吏管理和负责征税,郡县都不能过问。[5 ]如《汉书·食货志下》:“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太仆、大农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再谈》以为公田之税由乡里征收并用于基层政权之运转费用,是缺乏史实根据的。同时,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的年代是景帝四年,当时内地郡国尚不存在可耕之公田。所以,6号木牍之刍稿只能是征于私田。
其三,《再谈》认为,“据凤凰山汉墓出土4号、5号木牍所记的算赋征缴情况来看,算赋是分多次征收的,从正月到五月,每个月都在征缴,……算赋如此,刍稿田税亦然”。我们认为以算赋征收方式推导出刍稿田税征收方式,是一种简单比附的错误。算赋征收有多次记载,刍稿田税却仅一次记载,正说明刍稿田税已一次征收完毕。实际上,算赋与刍稿田税征收方式的不同是由其各自特点决定的,刍稿与谷物的生产与收获是有季节性的,政府向农民征收刍稿田税只可能在庄稼收获之后征收,过期很难收缴,更不会在农民青黄不接时候征收,怎么能与货币征收方式的算赋一样呢?
其四,《再谈》认为,“按顷计征田税,是指国家制定财政预算,确定田税总额而言的,即国家根据土地和人口数量,本着‘一夫百亩’的原则,层层分解给地方各级政府,中央对郡、郡对县、县对乡、乡对里只依次要求完成税收总额就行了。至于郡分解给县,县分解给乡,乡分解给里的具体数字是否按中央标准执行,基层政权如何计算,怎样征收,实收多少则不予过问,以一乡一里一时一次的刍稿统计数字自然很难找到按顷计征的印记”。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令人吃惊的假设。可以肯定,任何一种税收方式都必须通过乡里基层政权来具体实施,但乡里基层政权在征收时也是要按国家制定的政策来具体执行,不可能随意而为,虽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基层官吏舞弊的情况,但这是国家不允许的违法行为,最高统治者怎么可能对“是否按中央标准执行,基层政权如何计算,怎样征收,实收多少则不予过问”呢?而《再谈》赋予这种行为以合法化,更是惊人之论,如若这样,整个社会秩序就要乱了套,即使最愚蠢的统治者也不会这样做。秦律《法律答问》:“部佐匿者(诸)民田,者(诸)民弗智(知),当论不当?部佐为匿田,且可(何)为?已租者(诸)民,弗言,为匿田;未租,不论口口为匿田。”[1]其规定,部佐已向百姓收取田赋而不上报,就是匿田,要论罪。 可见,战国对基层征收田税已有严格规定,汉代只会更为严密,怎可对基层官吏征税没有具体政策而由官吏任意为之?同时,假设事实如《再谈》所云,即百亩征税是体现在中央预算总额上而非基层官吏具体实施上,那么“以百亩为单位征收”的说法还有什么意义?以亩为单位和以顷为单位在中央制定预算总额时难道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此外,不知《再谈》这种说法的依据何在?
第四,关于《盐铁论·未通》所载文学和御史争论的实质和“顷亩”释意问题。
臧知非先生认为,两人对话中的“顷亩”应解为“百亩”,而不是以往的“田亩”,因为如果“‘顷亩’解为田亩数的多少”,则“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在史实上都不能成立。……因为无论亩积大小,都交纳三十税一的田亩,有多少地交多少税,每亩不过数升,即使凶年,这个数量也是微不足道,按剥削率来说都轻于‘什一而籍’,有什么理由恢复什一而籍制?”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弄清文学的原意,弄清文学对“什一而籍”、“什一而税”及“初税亩”的理解,而不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很明显,从对话可看出文学有两重意思:一是从制度上比较“什一而籍”和“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的优缺点。文学认为“什一而籍”的优点是“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己不独衍;民衍,己不独勤。”而“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有“乐岁粒米梁粝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的缺点。在这里,文学并不是比较两种赋税制度的剥削率大小。请看《孟子·滕文公上》: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籍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较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兮兮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孟子认为从税率来说,贡、助、彻皆为什一之税,但赞同“助”、“彻”,反对“贡”,其原因是“贡”有缺点,即“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这显然是从两种税制的特点上来比较的。孟子借龙子之口反对的“贡”,实际就是西周井田制破坏后,各国普遍实行的“履亩而税”即按田亩征收田税。鲁国“履亩而税”从“初税亩”开始,故“初税亩”也成为以孟子为首的儒家弟子抨击的对象。如《谷梁传》云:“古者什一,籍而不税。初税亩非正也。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己悉矣。”《公羊传》:“何讥乎始履亩而税?古者什一而籍”。这两段话明确地赞同“什一而籍”,抨击“履亩而税”的“初税亩”。
崇尚儒家思想的文学,虽然认为西汉“三十税一”的田税较轻,但田税仍然是“以顷亩出税”即“履亩而税”,就还带有“乐岁粒米梁粝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的缺点,故大加抨击。实际上,孟子、春秋三传和文学之所以赞同“什一而籍”,抨击“履亩而税”,真正目的是要恢复久已远去的井田制。在他们心目中,井田制下是“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这种先公后私、人人互助的做法,正符合儒家们“仁爱”的道德观念和理想追求。所以我说,文学将“什一而籍”与“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相比较,不是从税率上,而是从制度的特点上进行比较的,臧先生从税率上比较两种税制,当然就曲解了文学的原意。
文学的第二层意思是汉代“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虽轻,但“加以口赋更徭之役”,农民的负担就很重,甚至达到“中分其功”的程度,这比“什一而籍”重得多。臧先生认为井田民的境遇很悲惨,负担很重,除了“什一而籍”外,还有其他劳役,其目的是说井田民的负担比汉代农民重。我认为,臧先生的说法是否正确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无关,因为很显然,文学认为井田民的负担仅仅是“什一而籍”,汉代农民的负担就是远比“什一而籍”重,这就是文学的原意和逻辑,臧先生关于井田民负担的看法即使比文学更正确,恐怕也无法改变文学对井田制的赋税制度的美好想象。正因为臧先生不是从文学而是从自己对井田民和汉代农民负担的理解上,来探讨这个问题,所以他才会曲解文学的原意,把“顷亩”解为“百亩”。
此外,《再谈》认为,“‘顷田’为一顷之田,‘顷亩’为一顷之亩,二者词例相同,释‘以顷亩出税’为按一百亩交税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训诂上都不存在‘误解’的问题”。我认为把“顷亩”释为“百亩”在语法和词意上都是错误的,因为“顷田”和“顷亩”的词例是不同的,“顷”、“亩”是量词,而“田”是名词;“顷田”是偏正结构的词组,“顷”修饰“田”,而“顷亩”是并列结构的词组,指土地,是借代用法。若“顷田”释为“一顷之田”尚可说得通,那“顷亩”释为“一顷之亩”即“一百亩亩”是什么意思?实际上,在古汉语中,“顷亩”从来都释为“田亩”,此处仅举几例。《后汉书·光武帝纪》:“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后汉书·刘般传》:“郡国以牛疫、水旱,垦田多减,故诏种区种,增进顷亩,以为民也。”《后汉书·秦彭传》:“每于农月,亲度顷亩,分别肥瘠,差为三品,各立文薄,藏之乡县。”
第五,对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7号木牍和10-34 号竹简所记郑里农户占田数字的理解问题。
7号木牍云“市阳租五十三石三斗六升,其六石一斗当米物……。 ”笔者在《也谈》一文中认为“这里市阳租的‘租’当指田租(田税)。如果亩收三升,按百亩为单位而不是按实耕亩数征,则百亩之税为三石,田税的统计数应俱为3倍数,而不会出现‘斗’、‘升’等零头, 因为不足百亩也要按百亩计税。”关于这一点,《再谈》有两种解释:“一是基层官吏所征之税是因地制宜的数字,二是木牍统计的仅是一年之中,某一次所收之税的数字。”其所谓“因地制宜”即中央预算总额,层层向下分解,对基层如何征收,上级不予过问。其实,这两种假说都不能成立,其原因我们前文已经论述,此处不予重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