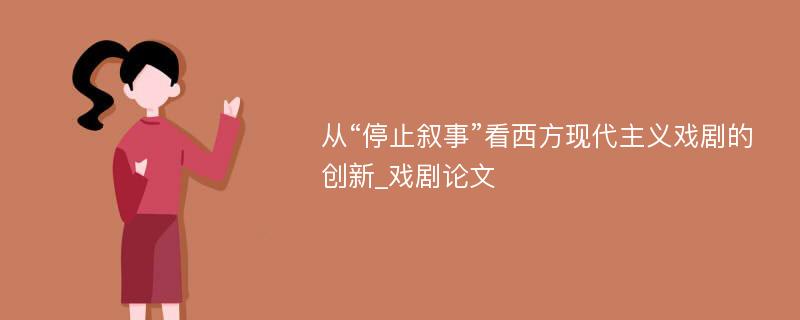
从“停叙”视点看西方现代派戏剧之创新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派论文,视点论文,戏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令人难忘的20世纪行将过去,21世纪正在向人们翩翩走来。值此世纪交汇之际,回眸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历程,对其经验得失作出客观公正、恰如其分的回顾、反思和总结甚有必要。这样既有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与把握20世纪西方文学尤其是现代派文学的状貌及其特征,又可帮助人们来更好地瞻望未来文学发展的趋势。20世纪西方文学中存在的疑惑点最多、引起歧异乃至责难非议最大的,恐怕非现代派文学这一支脉莫属。褒扬称颂者有之,贬斥毁损者亦不乏其人,真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那么究竟该如何恰当地评说现代派文学的功过是非?正像认识某一事物必须要看其主导方面,力戒避免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狭片面性那样,对待西方现代派文学自然也理应采取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科学眼光与辩证态度。笔者以为,现代派文学最最根本的特征即在于其处处标新立异、反拨传统的大胆探索创新精神。尽管这种探索创新常常失之偏颇,难免走到极端甚至误入歧途,然而就其积极有益的主导方面来讲,却暗合了新的内容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表现形式这样一条文学发展内在规律。现代派文学的崛起及其繁盛为20世纪西方文坛吹入一股清新气息,带来一种全新景致。清代诗人赵翼《论诗》咏得好:“李杜文章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们不妨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倘若没有了现代派文学这一部分,那么20世纪西方文学虽不至于顿然黯淡失色,但无疑总会明显给人一种缺乏“新鲜感”的体味。(这种“新鲜感”,若借用西方形式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个理论术语,亦即所谓“陌生化”)。因篇幅所限,本文在这里仅借助引入的西方叙述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术语——“停叙”,以此为视点,透过对现代派戏剧与传统戏剧之间的纵向比较,试图描述出西方戏剧创作的某种嬗变轨迹,藉以探究西方现代派戏剧创作的艺术创新性之所在。
叙述从广义而言,即是一种交流或通讯,指传送者通过某种媒介向接受者传递某种信息。文学叙述的媒介则是语言文字,其传递的信息即为文学作品中具体描绘的许多大大小小的虚构性事件。由此我们可以说,通常人们所谓的“故事”便是由从叙事性作品中提取出来、并按照一定逻辑关系(如因果律等)和时间顺序重新排列组合的一系列事件构成的。根据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与文本(即作品)叙述故事所用篇幅多少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理论上划分出三种叙述类型:其一为均速叙述,指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与文本叙述故事所用篇幅在单位上均称对等。例如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为十小时,文本便分出十章(或节),各章(或节)叙述每一小时内发生的事件内容。其二为加速叙述,指文本以较少篇幅叙述发生、持续时间较长的故事。如人物几年乃至几十年的生活经历、遭际,被寥寥数行概介性语言一笔略过。加速叙述若加速至极限点,就会变成“零叙”,亦即某些故事因微不足道、不足挂齿而在作品中被略而不提。其三为减速叙述,指文本耗用较多篇幅来叙述发生、持续时间较短的故事。如人物不过须臾瞬间的意识闪念,文本却耗费了数页甚至几十页篇幅深挖精掘、细细道来。减速叙述若减速至极限点,便成为“停叙”,意即停下来叙述,此时故事时间完全滞固不动,惟有文本在花费篇幅进行叙述。这里我们不妨打个比方:如同一辆正在行驶中的汽车因有人搭车或交通堵塞之故戛然暂停;虽然汽车已不再移动,但它又显然不是完全静止(停止)的。因为司机并未熄火,汽车发动机仍在“笃笃”运转,故而必定还在消耗着一定数量(公升)的汽油,就如同文本还在花费一定的篇幅仍然在进行叙述那样。“停叙”是与本文内容密切相关的重要概念。当然,无论是使用均速、加速还是减速叙述,在剧作家那里都应当是依循所表现内容的具体需要而定的。
事实上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上述所谓文本篇幅的多少,其实也就是语言文字的疏密约繁问题。因此加速叙述与减速叙述又分别可以用“约叙”与“密叙”相称谓。在“密叙”区域内还存在一种“平叙”,即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与文本叙述所用篇幅达到吻合日常生活时间节奏的协调一致性,特指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言语”(具体就戏剧而言即包括独白与对话的所谓“台词”。这是因为尽管舞台上的人物对话虽带有一定的表演成分和色彩,而与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言谈不能完全等同,但大体说来一个人在舞台上说“台词”同他于日常生活中谈话在时间节奏上还是协调一致、相差不大的)。当然我们不能绝对化,因为人物之“言语”只有处在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进程中,方可属于“平叙”;倘若它处在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中断为零的阶段,那么就不能再笼统地称之为“平叙”,而只应算作“停叙”了。
叙述是叙事性作品中最重要的艺术手法、技巧之一,而戏剧既为叙事性作品中最主要的种类、体裁之一,其必然也就离不开叙述。戏剧通过舞台人物的行动与对话搬演世态人情,台词一般说来在剧本中占据着大部分篇幅(当然通常要求这些台词应尽量富有某种“动作性”)。所以说戏剧总体上采用的是一种“平叙”。剧本中还常有简短的舞台提示、布景说明、“话外音”、剧情概介和出场人物介绍等,则属于“约叙”;而篇幅较长未被打断的人物独白,则可算作“密叙”。以上几种叙述手段、技巧在西方戏剧创作中被经常性地使用,并不给人以多少陌生感。那么,“停叙”在西方戏剧创作中是否也得到使用?其使用情况又如何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西方传统戏剧。众所周知,西方传统戏剧的创作原则,是经希腊先哲亚里斯多德理论归纳、被后世共同认可并高度自觉地予以遵循的:第一,极其强调对人物动作(尤其是外部形体动作)的摹仿,对人物内心活动总是借助于相应的外部动作或颇富有“动作性”意味的台词,做外化式的显现。正像亚氏所指出的,“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悲剧中的人物借动作来摹仿,……悲剧是行动的摹仿”,“情节是行动的摹仿”。(注: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六章”和“第九章”,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58页。)从亚氏不厌其烦的强调中我们不难看出,在亚氏那里,“情节”即经过布局的行动,情节与行动其实乃是同义语,一出戏的情节就是一个完整的行动体系。此即传统戏剧“情节”的要义和精髓!第二,特别推崇故事情节中因果关系的重要性,即人物的言与行、事件与事件之间都必须严格依据必然律或可然律来串接贯通。恰如亚氏特别申辩的那样:“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经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如果一桩桩事件是意外的发生而彼此之间又有因果关系,那就最能(更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依据上下文联系,系指引起观众恐惧与怜悯之情的戏剧表演效果——笔者注);这样的事件比自然发生、即偶然发生的事件更为惊人,这样的情节比较好。”(注:亚里斯多德:《诗学》“第六章”和“第九章”,引自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由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虽不乏巧合的机缘,但在最普遍意义上讲,却往往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之间的顺承或碰撞,并非一定受因果律的牵系和制约。所以传统戏剧理论注重的“因果律”,在很大程度上不啻为一种理想化的艺术建构,意在使原本繁杂无章的现实生活显得井然有序、合乎规律。
受上述戏剧理论的“导向”作用,传统剧作家们在其创作时,一般都非常注意筛选、滤取存在因果联系的一些事件,苦心孤诣地将它们串接成为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组构出包括开端、发展、高潮和结局的严密推演的完整情节。亚里斯多德为何如此这般地推重因果律在戏剧情节中的重要性呢?推究而论,或许主要是基于对引起审美效果的观众心理方面的审慎考虑,同时也是对异于“史诗”创作(“史诗”类似于现代长篇小说,大体上可视为一种小说创作了)而要求“戏剧性”的古希腊戏剧(主要指悲剧)艺术特征的精辟概括、准确把握与科学界定。戏剧既然被限制在几个小时内演出,又主要得依赖摹仿人物动作而非像荷马史诗那样的语言叙述;还须想方设法让观众始终保持浓厚的观赏兴趣,其局限性与困难度显然要远比“史诗”创作大得多。故此,剧作家们才格外讲究事件之间紧密联系、环环相扣的因果关系,以便令观众信服,不至于觉得有悖情理而产生“厌看”心理;同时借助于层层设置悬念的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来确保观众观赏兴趣的稳恒持续性。
严格说来,任何叙事性作品中的故事情节都须或多或少带有悬念成分;但相比之下戏剧中的故事情节对设置悬念的要求尤其高。故而我们会清楚地发现,设置悬念的“延宕”手段在传统戏剧创作中倍受重视并因此得到大力使用。所谓“延宕”即指剧作家在叙述所发生事件、安排故事情节和设计人物言行时,抓住观众急于获知内情的“破谜”心理,故意放慢叙述节奏,延缓事件进程。如刚刚叙述至某一件事件的“兴奋点”时转向对另一事件慢条斯理的追溯;在中心情节发展过程中穿插其他次要情节线索以造成“戏中戏”;在矛盾冲突难分难解的高潮阶段设计上一段人物的抒情性独白,或者以出人意料的滑稽行为来冲淡、缓解紧张的戏剧氛围等等。藉此强化观众迫切期待的情结,从而巧妙设置出戏剧悬念。从某种程度上讲,延宕起到了近似于“停叙”的叙述功能,但它本身并不能与“停叙”划上等号。这是因为延宕虽拖延了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干扰了剧情发展的直线式嬗递,却并未使故事时间戛然中断、停滞不动。而且由延宕扩充出来的篇幅,其实都是与剧情有着内在因果联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整个封闭式“圆环”情节结构上不可分割的某一段“圆弧”。因此可以说,延宕乃属于介乎“停叙”与“平叙”之间的一种密叙。
我们不妨举例具体说明之。象《哈姆雷特》中“伶人演戏”一场,其戏谑性与全剧沉重压抑的气氛不相协调,同剧情的联结似乎也不怎么紧凑。然而它正是哈姆雷特所能利用的,试探国王、确证鬼魂所言“杀兄篡权”真相的最有效途径。缺少此环节,哈姆雷特坚定的复仇心理(尽管在采用何种复仇手段上犯踌躇)就难以解释清楚。莎士比亚使用独白的延宕手法也很成功,他运用内心独白展露人物的隐秘灵魂,可谓达到卓绝可叹的艺术深度。其笔下人物的内心独白往往不是三言两语,而是篇幅很长,常常单独构成某一场景。譬如哈姆雷特身处与国王剑拔弩张的严重对立态势,可莎翁偏偏让他深陷于抒发忧郁乃至近乎癫狂的独白的神思恍惚之中,迟迟拿不出复仇的具体行动和举措。乍看那些大段大段的内心独白,抑制了剧情发展的急骤节奏,隔开了事件之间环环相扣的“时间”纽带,观众仿佛一下坠入到只需以耳聆听剧中人物痛切肺腑或愤嫉若狂的灵魂鸣响的心境,沉缅于其中而忘记了自己是在看戏。然而实际上,那些独白恰恰是全剧情节发展结构中一条非常重要的因果链,它标示出哈姆雷特面对复仇任务,由疑惑、痛苦到踌躇以至决断的完整心理流程。而若从实际演出的观赏效果来讲,那些内心独白则无疑成为剧情中最扣人心弦、撼人心魄的精彩场面。
传统戏剧一般在人物对话上力求简约得当,视台词的臃长拖沓为创作之大忌。但也有人敢用延宕手段闯此禁区:对白篇幅极多,几乎将人物动作淹没掉,似乎明显缺乏戏剧性动作。莫里哀的《丈夫学堂》就是一个例证。该剧几乎通篇为一对情人(奥拉斯与阿涅斯)向第三者(阿尔诺耳弗)分别讲述自己恋爱经过的对白,舞台动作甚少,却仍被人们公认为一部喜剧佳作。推究起来,莫里哀的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巧妙设置的特殊喜剧情景,赋予了对白(语言叙述)以强烈的戏剧性动作。具体说来就是,奥拉斯把恋情透露给父亲的朋友阿尔诺耳弗,并请他帮助对付那个纠缠阿涅斯的“讨厌的老头”;阿涅斯同样也将自己的私情告诉了自己的监护人阿尔诺耳弗(她已没有任何其他的沾亲带故、关系更密切的亲属)。令人忍俊不禁的是奥拉斯根本不知道阿尔诺耳弗正是那个“讨厌的老头”;而阿涅斯全然不知监护人既有娶她之念则必定会想方设法从中作梗(倘若她知道这一点,是决不会那样丝毫未加戒备的吐露心机的);阿尔诺耳弗本人则更是陷入知情又不能明言、被迫煞有介事地装作蒙在鼓里的尴尬境地。这一特定喜剧情境便把剧中那些解说恋爱经过的大段大段叙述转化成“语言”动作:不知内情的两个年轻人叙述愈是认真详尽,对阿尔诺耳弗的刺激愈是强劲有力,由此反弹力激发出的人物动作性(指阿尔诺耳弗采取的种种阻拦举措)也便愈发强烈。在这里,使用延宕手段同样取得了巧妙设置悬念、引人入胜的良好喜剧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戏剧虽然竭力推崇基于因果关系之上的情节,但并未由此就否认存在那种由一系列缺乏因果联系的事件所组成的情节。在亚里斯多德那里是把它称作“最差的情节”的。在这类被传统戏剧理论家、剧作家们看来乃属于败笔的戏剧作品中,因为事件之间缺乏因果性的衔接,所以在叙述时很可能有意无意地使用了“停叙”。正是鉴于传统戏剧刻意追求由因果链串接连缀的封闭式情节结构,遂决定了传统剧作家们在其创作中对“停叙”手段高度自觉地讳避、漠视以至鄙弃,使得他们对“停叙”的使用仅仅达到微乎其微、微不足道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从总体范围内和在一般意义上作出这样的推论:“停叙”在西方传统戏剧中并不存在。
那么,西方现代派戏剧情况又如何呢?纵览整个西方现代派文学,它的一大鲜明突出特征,就在于其对传统的大胆反拨——亦即反传统性,戏剧创作概莫例外。传统戏剧的一切固有模式受到冲击,剧作家们不愿再把由“因果链”串接成的理想化艺术建构硬行套加在现实生活之上;而力求再现日常生活中的偶发性事件。偶然性代替了因果律,因而打破了包括开端、发展、高潮、结局的封闭式情节结构,营造出事件不连贯完整、故事无明显结尾的开放型情节结构。由于深受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等西方现代非理性主义哲学、心理学思潮的影响,加之对两次史无前例、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导致现代西方人传统道德规范、伦理价值观念发生极大动摇的严重精神危机的身感体同,现代派剧作家大都将艺术视域、焦点投向人物的心灵世界,认为戏剧性主要应当在于人物内心而非外部形体动作。如象征主义戏剧最重要的代表作家梅特林克就认为,“真正的悲剧通常是内在的,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几乎很少外部动作。心理活动要无可比拟地高于纯粹外部的动作”。因而他主张剧作家应当着力刻划人物隐秘的内心活动,将内心生活称之为“静态的生活”,并创造出一种“静态戏剧”予以展现。相比之下,表现主义剧作家们更是强调描写人物的心理变化,展示人物的主观情结。像美国现代戏剧之父——奥尼尔的表现主义剧作(甚至包括他的大部分现实主义剧作),均侧重于对人物心灵世界和精神状态的细微剖析。从主要表现人物内心活动的内容需要出发,人物外部动作必然受到弱化,内心独白跃升为戏剧情节的主要内容和刻划人物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现代派剧作家笔下的主人公一般都是些忧郁型、内向型或变态型人物,他们的性格较模糊,感情不轻易外露,多耽于沉思默想,甚至思维紊乱。所以现代派剧作家与传统剧作家使用的内心独白已经具有着某些质的差异:着重描写人物的某些无意识、潜意识、直觉和梦幻等,完全依照这些人物非理性心理活动本身实际带有的非逻辑性、不合正常时序的随意跳跃性的自然模式予以披露;因而人物心理活动所呈示出的轨迹往往是一幅杂乱无章、繁复多变的“心电图”。这种内心独白较之传统戏剧中的内心独白能更恰当而真实地反映出人物忧郁型、内向型或变态型等复杂诡秘的心灵世界。现代派剧作家们所注意选取的事件,往往只是展现人物日常生活的某些片断,仅仅成了引发人物心理反应和意识流动的偶然契机。由这样一些琐碎零散的事件构成的故事,已不复为剧本的骨架,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零零碎碎、断断续续,惟有人物意识流动所持续的心理时间依稀可辨。现代派剧作家对故事事件的安排、组合也只能构成迥异传统戏剧情节的另一类“情节”:其特点在于“无变化”和“偶然性”;以展示人物(处于特殊精神状态中的)为目的,无法构成任何演变,(而不像传统戏剧那样总有基于因果关系之上的完整连贯的某一推变过程);如果说有戏剧高潮,那也不再是传统戏剧那样以故事情节的转折点为标志的逻辑高潮,而只是以人物情感的强烈表现或渲泻为置高点的感情高潮。剧作家仅仅用人物生活中偶然发生的一些琐事,来引发人物内心的活动,展示人物的性格。
西方现代派剧作家们正是以这种毫不遮掩的反拨传统的大胆创新精神,挣脱了戏剧创作传统模式的羁绊。他们不再循规蹈矩、亦步亦趋地精心选用一个首尾连贯的完整故事串接全剧,围绕事件之间顺承因果关系的嬗递设计情节;而是依赖人物的心理活动总揽全剧,凭附人物心理的衍变轨迹组构情节、安插场面;顺应戏剧表现内容所发生的由外在故事情节转到人物内心活动的偏移,在创作中尽量淡化事件本身的戏剧性,使故事情节的发展变化时有时无、若隐若现,退居到舞台一角,只构成为人物心理活动的某种淡远背景。由此,在他们的剧作中,很少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事件、有头有尾的故事,整个剧情由一连串大都互不相关的生活事件、场景片断、人物之间难以沟通的对话,或者人物莫名其妙、不知所云的自我呓语乃至沉默寡言等等组成。尽管从实质上看,剧作家们乃是以人物的某种思想情绪、精神意念或特殊内心动作为线索,来选取事件、编排情节和刻划人物的。所以,那些貌似互不相关的事件、缺乏因果联系的情节场景、不合情理的人物关系与近乎荒唐的人物台词,也并非东拼西凑而成的一盘散沙,而都统一在人物情感意识这条深层、内隐的结构线上;何况人物心理意识的流动严格说来同样需要经历一个时间过程。但因心理意识活动(特别是非理性意识活动)本身具有的不规则性、间断跳跃性和不合因果的非逻辑性,造成了由人物心理意识活动构成的那种“心理时间”难以整合,决定了心理意识活动这根情节线索只能是一条“虚划”的间断工曲线,故而给读者的感觉便是: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经常停留在某一点上滞固不动,剧本只在花费篇幅让人物自身作“内心意识的流动”而已。如此说来,在现代派戏剧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故事发生、持续时间出现间断跳跃,只存在展示人物内心意识活动的大量篇幅的独白的情形,非常符合我们在文章开头对“停叙”所下的定义。这也就是说,“停叙”存在于西方现代派戏剧作品中。例如奥尼尔的表现主义剧作《琼斯皇帝》,全剧共八场,其中有六场全是主人公琼斯一人的独角戏。剧作家并未将笔墨付诸展现黑人造反——琼斯皇帝出逃——最后饮弹身亡这一惊险“追捕”的外在事件的发展变化过程,(若换了一位传统现实主义剧作家,很可以按部就班地在此方面泼足笔墨、大作文章,而且亦完全可能写出一部扣人心弦的相当出色的戏剧佳作);构成该剧最主要戏剧性的便是琼斯的大段内心独白,剧作家藉此凸现琼斯深陷绝境之中苦苦挣扎的恐惧、绝望心理。而在他的另一部剧作《奇异的插曲》中,几乎就没有什么动作,全部都是女主人公的内心独白。该剧上演需耗时5小时, 被评论界称为“戏剧形式的意识流小说”。很显然,奥尼尔笔下所使用的内心独白,类似于现代派“意识流小说”对人物心理意识活动所作的描述,篇幅很长,不构成情节上某种明显的起承转合、演变推进,故事发生、持续的时间完全停顿下来,惟有主人公沉醉于“自我意识的流动”之中。毫无疑问,诸如此类的剧作都是使用“停叙”手段的有力佐证和成功范例。
由于西方现代派戏剧品种繁杂,艺术手法多种多样,所以对“停叙”的使用情况自然也会各有不同。但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在那些多采取类似“意识流”手法描写的以人物内心独白为主要内容的剧作中,使用“停叙”的情形最为多见。总的说来,“停叙”这一独特叙述手段到了西方现代派作家手中,才开始受到特别重视与格外青睐,并且有被愈来愈广泛使用的创作态势。这种态势就从一种崭新视角——叙述学角度向人们清晰地透示出,西方戏剧创作从注重外在动作表演(摹仿)到刻意追求表现(呈示)“内心生活”的由“外”转“内”的重大嬗变轨迹。可以说,西方现代派剧作家的一片苦心孤诣并没有枉费,其创作的成功便是对他们艺术尝试最好的回报;他们的不拘一格、大胆探索的艺术创新精神亦略显一斑。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认识、肯定乃至赞叹。
收稿日期:1999—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