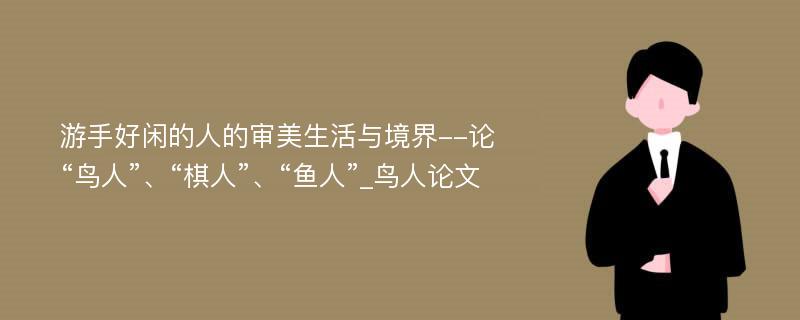
闲人一族的审美人生及境界——谈《鸟人》、《棋人》、《鱼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闲人论文,鸟人论文,境界论文,人生论文,鱼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3年《鸟人》在剧坛出现可以看作中国话剧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在这出剧中,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代中国作家共同恪守的价值预设被轻轻置换,过士行以他一批率性而为不计功利的闲人形象取代了第一代作家进取的理想者形象。他在正统人生之外发现了一线新的生命的熹微,在对闲人生活的观照中发现了同尼采、本格森生命学说的对接点。它毅然舍弃了人生的形而上学层面(终极关怀),而直接在芸芸众生的感性生命中寻找大欢喜。经由过士行,一种花鸟虫鱼具有审美特性的闲散人生开始在世纪末戏剧舞台悄然上演,并以其滑稽的戏仿和放肆的笑声解构了载道戏剧的神圣与庄严。过士行给持续了近二十年的理想主义话剧划了个句号,也为单调的人生舞台增添了别样的戏文。为此,过士行作为本世纪“为人生戏剧”的最后一位作家,同时成了新世纪戏剧多元人生的倡导者和开山作家。
一、鸟人:受挫人生的代偿及焦虑的自疗
《鸟人》是闲人三部曲的开篇之作。幕一拉开,过士行便把我们带入了一个鸟的世界——鸟市。鸟市是由鸟与人构成的江湖。这里不但有三爷胖子之类的帮主及帮众,也有“南路”、“北路”、“北京画眉”、“天津画眉”的门派区别,更有“秋西呼垛单,抽颤琢滚翻”等行家讲究,以及“肮口”“净口”等诸多禁忌——如果哪只鸟不经意叫错了音,便会遭到当众摔死的帮规惩罚。鸟人奇异的文化语码不仅令金发碧眼的老外瞠目,连北京之外的中华百姓也大开眼界。
打破笼罩在鸟市上的神秘光环,便会发现鸟市的主体实际仍是人。只是这是些病态的人,一些在现实人生受挫的人。鸟市是受挫人生病理投射的一个代偿世界,是受挫人生的避风港治疗所。正如许多国人自己考试不及格拼命强迫孩子读书一样,各式各样的鸟人把自己在现实人生中受挫的焦虑投射到鸟身上,并通过鸟的闪转腾挪哗众取宠寻求一种精神补偿,来完成他们在世俗人生的未竟之梦。因此,在熙来攘往的鸟市中,你随意掀开一位气度悠闲的鸟友的后襟,都能从其身上找到在现实人生中受挫的印痕。三爷是鸟人族族长,曾经是京剧名角,但“不知哪一天演砸了,就像点颏叫了两声蛤蟆”,从此一蹶不振,沦入鸟市,养红子,当帮主;胖子一生都想成“角”,超越那位坐在母亲身边身着戏装的父亲,可惜老天没给他好嗓子,因此,他只能跟在三爷后面起哄,他养画眉,因其“势大声宏,能把别的鸟声音都‘压下去’”;百灵张在火葬厂工作,职业使他的嘴变成了报丧的乌鸦嘴,所以他养百灵。这种代偿机制不仅适用于视鸟如命的养鸟者,也同样适用于那位满世界寻找珍禽的鸟类专家,以及那位漂洋过海的鸟人精神分析专家等所有“与鸟生生死死的人”。在鸟的大旗下,实际上聚集了京城脚下后文革时代各式各样的神经病患者,只是症状稍有不同。鸟市的这种属人性质使鸟市成了人世的投影。细细观察,鸟市实际上是世俗权力和价值趣味的一种转移,鸟市外表松散和平,实际内部等级森严,帮派林立,并以世俗的好恶为尺度。百灵张之所以空有十三套也当不了帮主,不仅因为他的百灵不如三爷手中的红子更具贵族品味,同时也因为他本人是火葬场工人,而三爷则是所有鸟人族票友中唯一一个专业国剧剧团的导演,是一个真正见过金少山的人。鸟人实际是把人生冷落的竞技场转移到鸟市上来,延续人世上未能演完的人生戏剧。
在《鸟人》人物谱中,三爷的形象最为成功。三爷人格是太监人格和师爷人格的混合体。他烙印着太监文化中所有的故弄玄虚、狐假虎威、装派拿大的大内作派,也烙印着色厉内荏指手划脚好为人师的师爷癖性。他既是一个受挫者,又是施虐狂。受挫给他生存留下了永恒的耻辱,他去当导演,但观众走出了剧场,没有演员再听他说戏。于是他到鸟市在鸟众和票友的双重身份中享受名角和导演的荣耀。作为施虐者,他在鸟人族一言九鼎,指鹿为马,捆绑学徒,颐指气使,在鸟人的簇拥和欢呼声中重享权威的荣耀。三爷最有意思的是他同胖子的关系,这是一对典型的被虐/施虐的共生关系,胖子作为师爷的业余跟班,在对三爷的吹捧和辉煌的过去中享受着权威认同的荣耀、喜悦,他“甘愿属从于他人的支配、命令、保护,沦为他的一部分,他的微未尘土,借此……分享他的伟大、权威、恒定”(注:弗洛姆:《美的艺术》,349页。)。而三爷对胖子及黄毛及鸟众的施虐中,则享受着“无情盘剥”,“完全主宰别人,使别人在我的意志下完全屈服,使自己成为真神”,“享受施虐者的快乐”(注:《逃避自由》,77页。)。三爷和胖子成为彼此不可分割的共生体,双方均失去了人格的独立性和完整性。施虐/被虐两种对立人格不仅体现在三爷和胖子身上,更体现在鸟人族中每个个体的人格中。鸟人族都同时扮演着受虐/施虐的双重角色。首先,每个人都是受虐者,他们共同匍匐于族长三爷的麾下,任其呼来喝去,赶场扮角,忙得不亦乐乎;同时也是残忍的施虐者,其施虐对象便是他们笼中的鸟。对他们行使发号施令生杀予夺大权,鸟人族在把鸟儿囚于笼中发号施令的同时,也把自己囚于一个更大的笼子里,接受着一个更大的牧者的拘役。
陈博士和丁保罗又是一对欢喜冤家。他们在剧中的身份一个是鸟类研究专家,一个是精神分析学者,其实他们更是鸟人族中两个沉疴更重的患者。在剧中,陈博士很快被丁保罗识出假学者真患者的身份,指出使他涉及鸟人世界的真实动因是窥淫癖而不是鸟的研究。这种一语中的的分析令陈博士胆战心惊,很快不打自招,并将其引为知己。而丁保罗之所以具有如许功夫,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精神分析专家,而是因为他自己和陈博士一样,也是一个窥淫癖,正因为感同身受,才能成为解人。他这条狐狸尾巴是他对陈博士进行诱供式分析时,被旁观者的三爷看出了端倪,并一语道破的。作为另一种解人,聪明的三爷看出丁保罗免费治疗同自己免费教人学京剧一样,在冠冕堂皇的理由下都有不能告人的卑下目的,以后便来了一次三堂会审,审出了丁保罗因为窥淫导致妻子离去,而后窥淫成癖,进而通过建立精神分析疗所,从而有更多的机会窥淫的病史,从而审出了丁陈两位真患者假医生(学者)的真面目。
鸟市作为克服焦虑的生存方式,还体现在它的类聚性上。中国文化没有孤独个体。传统的中国人或者在君臣父子的人际中共存,或者到儒道佛的神仙世界与神共倚,文革之后,现代中国人失去了“万朵葵花向阳开”的和谐圆融心境,焦虑就产生了。于是,各种形式的气功、铺天盖地的大秧歌,以及盛行京都的鸟市,都作为缓解个体孤独焦虑的类聚方式得以流行。鸟市的类聚缓解了精神幻灭的个体生活沦为散沙的痛苦。鸟人通过鸟市互相构筑一个彼此认同的世界,通过相濡以沫的互相肯定达到自我肯定的目的。因为鸟市不仅给鸟人提供了参予空间也提供了表演空间,进入鸟市可使鸟人获得观众与演员的双重身份,这表现在给别人站脚助威的同时也为自己换得了表演的权力。鸟的表演是鸟人人生竞技的延续,是自我肯定的重要形式。中国人讲究“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受挫使“留名”已不可能,鸟人就通过鸟儿的“留声”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百灵张一鸟进林独坐石桌开始表演的时候,那是鸟人生命重新展现的时刻,在这种貌似悠闲的气氛中,有一种看不见的刀光剑影。鸟人生命的最高赏赐是他人对于鸟的技能的肯定,从而达到一种“一鸟进林,百鸟无语”的最高境界。因此,每个人都绝不能放过任何表演和炫耀的机会。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成就了本剧最后一场天衣无缝的“三堂会审”。在会审中,三爷抖足了花脸的威风,众鸟友也喊足了堂威,他们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众星捧月之中当了一回“角”,这对他们来说是生命的最大节日。
鸟人的生命虽然具有“代偿”和克服焦虑的双重功效,却不能说是一种健康的积极的人生。作为人生代偿,养鸟颇类于一些丧失肠胃功能的患者,用外置瓶管完成代偿排泄功能一样,这种行为虽为壮夫不屑为,却有一种聊胜于无的无奈。作为对分离焦虑的克服,又以审美的形式出现,有合乎人类本性的一面,但因其受病态心理的支配,又以牺牲其他生物的自由为代价,因此是健康人性的扭曲状态。正为此,过士行对这种病态的审美虽不乏怜悯,又同时给予无情的嘲讽和戏谑。
二、棋人:天才的生命模式及人生宿命
如果过士行通过对鸟人族的发现误打误撞地进入了非功利生命形态的观察渠道的话,那么,在他经由此渠道进入闲人生命的其他空间之后,又看到了鸟人喜剧性以外的生命状态。那是一种具备了生命的严肃性庄严性的状态,这便是棋人的生命。对于这种生命,他收起在鸟人中的调侃和戏谑,而以一种真诚的眼光审视这种人生的机理和局限。
《棋人》不是闲适,不是琴棋书画,不是玩。《棋人》是一种战斗人生,是一种投入全部生命能量“连骨头都不剩”的生死搏弈。这里具备人生的全部悲剧性和庄严感。只是棋人的战斗人生不同于世俗领域受功利驱使而是一种性情的需要,因此仍是一种审美的人生。棋人的人生不是在人生舞台上而是在棋盘上实现的。棋坛不仅是竞技场所,同时也是人生舞台的缩微。阴阳、四时、三百六十周天构成了他全部的时间和空间场。棋人用生命为燃料,以智慧为能量,通过黑白二子模拟厮杀,体会人生的种种境界与滋味。棋人的人生除了不受人间烟火和各种七情六欲滋扰之外,其他紧张、玄妙变化并不比实际人生稍逊。甚至因了他的智慧的单纯性,显得比实际人生更富跌宕变化之姿。比如,实际人生永远是一次性的,不能重演的,而棋上人生可以无数次复盘,无数次重新开始。每一次复盘和开棋都为生命展示了新的机遇和可能。因此总能令人留连忘返,具有无限迷人的风光。
《棋人》首先要表现的是天才人生轨道的宿命性、超常性。在作家看来,任何一种天才都是作为某种特殊的生命而生。为之而生的人,他只能以某事物为生命形式,来展开自己的生命和消耗自己的生命能量,并在这种展开和消耗中获得全部的生命快感。何云清就是一个为棋而生的人,他最适合下棋,只能下棋。在下棋中,他体会生命的真实与快意,并获得人生的价值——“整整倾倒了一代人”。为了表现和探讨这种效应,作家故意选择了棋人老年和战斗松弛时的人生破绽,试图为棋人的人生论证另一种出路。当棋人过了六十大寿,发现这一辈子都在棋上度过,而自己又不能下对手棋的时候,他产生了落寞感——后悔,他撵走了棋友,烧掉了棋盘,表示再也不下棋了。然而当聋子把一个围棋天才领到他眼前时,他不但重新下起了棋,而且一发而不可收,进入了欲罢不能的发烧状态。后来他先后接到鬼魂和昔日情人的警告和求助,请他放过这个孩子,也许为了赎罪,也许为了给自己一个机会,他答应了司慧的请求。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局中,他朦胧中有两层考虑:一是最后了却棋缘;二是通过对一个新的围棋天才的强行改道,重新修改棋人的人生——离开棋。但是意想不到的结果发生了,司炎自杀了。通过死亡,司炎找到了人生自由的方式——“我终于找到一个自由的世界,我可以下我的棋了”。司炎以“不下棋,勿宁死”甚至死后阴魂还要下棋的执拗行为论证了棋人生命与棋的同构。从而推翻了何云清的改道设想,说明了谁也不能改变棋人的人生轨道。因为棋人是为围棋而生的,改变棋人轨道,就如同改变上帝的程序一样。何云清的人为改道之举和晚年惧悔除了说明棋人也不免有“围城情结”(里面的想出来,外面的想进去),更说明了棋人对围棋深层的执着和眷恋:他不能容忍周围的人那样轻描淡写地下棋,那是对棋的亵渎;不能容忍自己不能下对手棋的状态,那是棋人的耻辱。《棋人》除了揭示了天才的人生轨道,作家还揭示了天才的生命个性,以及由此个性注定的人生得失——棋坛上的辉煌和世俗人生的冷落。棋人在收获搏弈喜悦的同时也放逐了世俗的幸福。棋人除个性乖僻、孤傲、自我中心外(同其天才同构的),最突出的一个特点便是无情、专注,“真正的棋手下棋时内心里是一种古井无波的状态”。棋人如同高僧,要明心见性,去掉俗人的各种贪染、旁鹜,能抗拒人生的各种与棋无关的诱惑,包括情爱。为此,何立清在年轻时失去了他“一生最美好”的司慧的爱。因为痴迷于棋,司慧走时他甚至连头都没有抬起。结果一个人才在棋盘上度过一生。一抬头,发现伙伴“头也白了,背也驼了”,这才想起青年时的恋人,才知道嫉妒徒弟们的男欢女爱,然而为时已晚。这是棋人的生命代价。“整整倾倒一代人的辉煌”,本该用老年的孤独为代价的。棋人的代价就是天才的代价,历史上许多天才——尼采、卡夫卡、贝多芬、康德——都是独身,摘取王冠进入人生的巅峰这些高难的人生,不是拖儿带女的俗人能做到的,所谓高处不胜寒。天才的代价体现了上帝的公道,当你一旦成为上帝的选民、宠儿,成为天才的时候,某种程度上你就被从常人的幸福中除名了。这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1.你不能随便消耗上帝给你的高原子能量(尼采的见解);2.常人的幸福成了不堪承受的东西——何云清喝醉了酒,在雪夜错把媛媛当成年轻时的情人试图来点缠绵情调时,这个在他眼里纯若天使的姑娘告诉他,“导游是清白的,但我不是”。多一分自由,亦多一分点染。于是何云清马上抽身退步,“下棋下棋”,回到棋上。
棋人的另一生存特点便是人生的机遇对其命运的涂写。《棋人》似乎告诉我们,并不是每个具备下棋才分的人都能成为国手。一些才华横溢的人过早夭折体现了人生机会的不均等,即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良好的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作为一个一生下来便被剥夺了下棋机会的天才,司炎始终处于一个对围棋充满敌意环境,他从来没有机会在摊开的棋盘上以真实的棋子与人对弈,而唯一的两次实战都是决定一生下棋权力的生死之战。生活没有给他充分演练和提高的机会,他一出手便被推到生死战场。在这个意义上,司炎过早地遇到国手于他不是幸事而是大不幸,他因为走近了太阳而被刺盲了双目,他的可以原谅的失着成了他被剥夺下棋权力的口实。在司炎的短暂的下棋生涯中,生活充分地表现了对年轻天才的生存空间的掠夺和不公。这种人生的残酷性也许只有真正下过棋的人才能体会到。
三、鱼人:游戏人生及生命沉醉
如果说《鸟人》是一种代偿的人生,《棋人》是一种搏弈的人生(战斗),那么《鱼人》就是一种游戏的人生。鱼人是游戏者,是大玩家,鱼人的生命快乐及其实现都在钓鱼的游戏中。
钓鱼之所以具有游戏性质首先在于它的非功利性。鱼人并不以钓鱼盈利,鱼人之于钓鱼只有投入没有产出。鱼人不停地变换鱼竿、鱼食,不但老婆离开了他,而且还搭上了幼子的生命。鱼人在钓鱼中所收获的只有游戏的快乐。比之棋人,鱼人的审美特点更为鲜明,就像运动员要讲究风度和仪表、演员要讲究派头一样,鱼人举手投足都有迥异常人的风范。他往那一坐,“像关老爷似的”,“风不敢刮,浪不敢起”,走路的时候,“碰不着一粒石子,也踢不着一根草”,像草上飞一样。打鱼的时候,两目放光,半长头发迎风飘摆,看他钓鱼,就如同在看一场精彩的艺术表演,用老于头的话说:“他抡竿甩线,还是提竿上鱼,加上锣鼓,那就是唱戏呀”。
钓鱼的游戏性还体现在对游戏规则的遵守和对游戏内容的痴迷上。在钓神开场之前,有一场老于头与钓神之间的关于钓鱼的问难,这个问难从钓鱼的缘由、目的、历史、规则、机关、诀窍、禁忌以及对钓鱼的形上学意义全都问遍,这种问难就像是体育竞赛中的一种资格审查和级别的检定,又像儿童游戏过关时的答辩,只有拆解了谜语和熟谙游戏规则者才有资格参与。有了这个规则,就连反对钓鱼的老于头也不能阻止钓神钓鱼,虽然老于头是一方老大,大青鱼是一方的守护神,但对于一个用儿子作鱼食,用三十年的光阴作鱼饵线的钓鱼人,爱鱼如老于头者也无话可说,只能认同规则——“我就成全了你”。当然,这些之于游戏还都是预演和前奏,真正体现游戏性质的是钓神真正施钓时的那种生命状态。那是一种生命的欣悦,一种生命能量倾力投射中体会到的沉醉。如果说何云清(《棋人》)在焚香洗手中还保留着一种日神的梦幻,那么在钓神同大青鱼生死的搏斗中,则体现了生命的最高快感——酒神的沉醉。作为钓鱼场上一个真正的大玩家,钓神以儿子为饵,以岁月为线,以身体为钓钩,拼尽残年之力,全力一搏,特别是在即将得手时表现的特殊的精神状态:抑制不住的狂喜,兴奋、喝酒、神经质、手舞足蹈断断续续的噫语……明知死亡在即,却不肯松手,一种飞蛾投火的痴迷,一种将生命付之一炬的狂喜,全部表现无遗。钓者由其对生命的抛舍和投入达到了生命释放的最高境界。此时的钓神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钓者,他同死在舞台上的盖叫天、倒在冰场上的叶乔波,以及讲演中遇刺总统肯尼迪并无二致。这种状态使我们想起了尼采对于酒神沉醉的绝妙分析:“我们置丰盈于事物,赋予诗意,直到他们反映出我们自身的快乐。这些状态是……克敌制胜,嘲弄、绝技、残酷,它们都属于人类最古老的节日之庆典。”
在这种难得一遇的生命庆典之中,生与死,胜与负均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反映自身的力量。钓神生怕对手能力得不到发挥,从而影响自己竞技水平的发挥,乃哀告大青鱼“咱们三十年才得见一次,你要是……不使真劲……让着我,可就辜负了我一片心”。因为“咱们不过是玩”,因此就一定要玩透。据钓神所知,鱼也是愿意玩的,“就是玩死,他也心甘”。在整个惊心动魄的人鱼搏斗中,你看到的是钓神全部精神的闪光,这里有“哀鸣思战斗”的渴望,有“刑天舞干戚”的疯狂,有“醉卧沙场君莫笑”的视死如归。在钓神同大青鱼的搏斗中,克敌制胜、嘲弄、绝技、残酷,真是一样都不少,这个等了三十年的游戏者,可谓过足了瘾。
酒神式的沉醉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在其高潮时可达到一种对立面的消失,主客体的和解的境界。钓神钓大青鱼的最后阶段就进入了这种境界。当老于头听到大青鱼咬钩,即将撞线并看到大青鱼山一样的身影时,曾哀求钓神不要钓了,“玩玩得了”,但钓神已经欲罢不能。他答应老于头“我不伤你的大青鱼,我……见个面……就让他走”,并哀求大青鱼“我等了30年,你等了300年,咱们总得见一面”。在这里, 搏斗变成了交友,老对手成了老朋友。这时候,主体与客体、你和我、棋手和对手、人和鱼的对立完全消除了,大家都是一个游乐场的玩客,是朋友,我因你而兴奋,你为我而存在,共同构成快乐人生的圆融状态。正为此,钓神才安慰老于头,虽然我现在钓它令你很难堪,而钓完之后我就死了,我的生命也就耗干了,等我耗干了之后,烧成灰扔在湖里,“生前钓他们,死后喂他们”,“鱼吃了我,我也就成了鱼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与他、人与鱼、人生与自然的界限完全取消,钓者和鱼都归入一体,归于太一。
游戏人生的另一证明是钓与被钓均遵循同等的原则:公平。在老于头同钓神问难的时候,曾提出一个问题,谁钓谁的问题,这就好比决斗时的生死合同。用老于头的总结就是“本事小的鱼,你钓它,本事大的鱼,它钓你”,“一根线,一头是你,一头是他,你在岸上,他在水里”。这就是所有钓者(渔者)和鱼(利)的全部人生寓言。从更高的人生层面上,对此世界有所欲取的芸芸众生无一不是钓者,名声、财富、学业、功勋、掌声、鲜花无一不是鱼。图小利者和小钓者如猴子和鲫瓜子之流,想出人头地夺冠夺魁者便是钓神类的大玩家。但是,只要你在人生的湖中垂钓,你就得接受竞技的公平,你就得接受“你钓它,或它钓你”的对立选择。在“你钓它,或它钓你”的对立选择。在“你钓它”的记载里,我们可联想到凯撒大帝、秦始皇、范思哲、毕加索、迈克尔·乔丹、杰克逊、比尔·盖茨;在“它钓你”的分册里,我们则看到数不胜数的如过江之鲫的失败魂灵,从股票大王到房地产商人,从下野的政客到黑社会老大,当然,此中更不乏钓到了鱼却不懂得“见好就收”,最后终因太贪被鱼钓的玩家——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钓到了整个欧洲,但是他们对远东的俄罗斯这个大雅马哈鱼全都垂涎三尺,准备了全部钓钩鱼食去钓,一个把自己钓到科西嘉岛上,一个把自己淹死在反法西斯战争的汪洋大海里。在过士行为我们建立的垂钓寓言中,我们不难做出以上的人生联想。
三部作品《鸟人》、《棋人》、《鱼人》表达了三种不同的人生态度,有三种不同的人格和三种不同的人生境界,虽有诸多不同处,但却有共同的东西,即三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放弃了人生的功利,放弃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拯救苍生等终极关怀。他们都是逸出有为的社会主流话语的边缘人物——人生的江湖客。这种人物在近代文艺作品中已很陌生,但稍稍往远追溯一下,便可在中国古代狷狂人格中找到原型。
狷狂人格是孔子所认同的由其弟子曾点所倡导的那种春日郊外击水唱歌(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先进》)的人生。狷狂“有耻且格”,“有所不为”,实际就强调超越功利讲究美学品味和随心所欲。孔子说“中行不达”,“必也狂狷”,中行是指子路的齐治平的有为理想,而狂狷就是曾点的闲人人生。在孔子心目中,闲人人生是高于中行人生的上行境界。孔子之所以不能放弃中行,是因为他士的责任感(“士不可以不弘毅”《泰佰》)。因此,狂狷人生是一种舍弃功利关怀直指性情的审美人生。是中国古人从竹林七贤到陶渊明到李白都在追求的潇洒人生。因此,过士行对这种人生的发现,即可看作作家对上帝死后理性贫困乌托邦幻灭的一种精神梳理,也是对中国古文化的一次蓦然回首。
值得一提的是:过士行通过他的“闲人三部曲”表现了一种戏剧思维的转变。在这些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试图把握生命两极以及多极的复杂性的努力,一种对终极价值之塔的怀疑和落入言荃的小心规让,一种朦胧的冲绝传统的冲动和探索的狂喜。经由过士行,话剧终于有了不那么清晰的主题和可称之为“一言多符”的东西。过士行以他学者的虞智和敏感为精神盛夏送来了秋讯。有关过士行的思维方式和美学思想因为十分复杂,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里专文论及。
标签:鸟人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