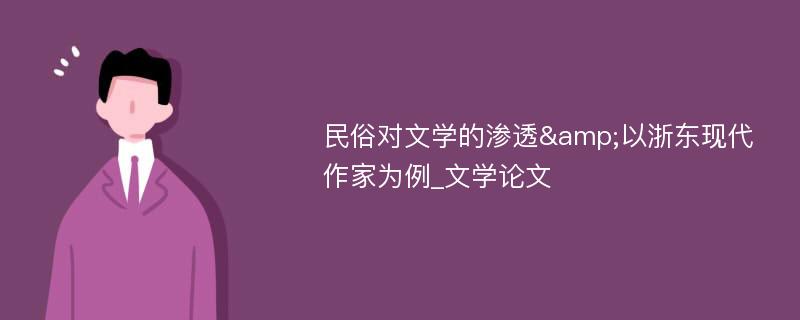
民俗对文学的浸润——以浙东现代作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浙东论文,为例论文,民俗论文,作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2)05-0121-05
美国民俗学家阿切尔·泰勒在谈到民俗与文学的关系时,提出了“民俗学和文学实属 相通的领域”[1](P52-54)的观点。泰勒的观点强调了文学源于民间,民俗与文学的相 通性,民俗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力。但这一观点又忽略了文学自身的创造性,作家,特别 是现实主义作家,不仅是模拟民俗,更是在自觉与不自觉中表现民间风情,反映存在于 现实生活中的地域风俗。浙东现代作家的作品中有许多有关民俗的描写,在这些作品中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中国现代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同时也看到了一幅中国现代社会的 风俗画。
最早注意到浙东现代作家作品中的乡土性,或说是民俗性的当是鲁迅。鲁迅在《<中国 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评述了许钦文、王鲁彦、台静农、魏金枝等人的作品,将 他们对于乡土的描述集中于对家乡、对于童年记忆中民俗的留恋,或是“回忆故乡的已 不存在的事物”(许钦文),“或是描写着乡下的沉滞的氛围气”(魏金枝),在这种留恋 中表现出作家对于乡村中原始信仰、民俗的关注。
一
文学对民俗的关注首先表现在作家对“农事”与“人事”的描述。浙东作家的作品多 与“农事”相连,更多地以“农事”为表述内容,反映着“农事”对于“人事”的制约 ,民风对于民性的影响。
地域是决定“农事”的首要条件,又是形成民俗的主要因素。不同的地理环境形成了 不同民风,也便有着作家对“农事”与“人事”不同的关注。周作人说:“风土与住民 有密切的关系……一国之中也可以因了地域显出一种不同的风格。”[2]对于浙东民风 ,鲁迅曾说过:“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驿,展其殊才; 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世俗递 降,精气播迁,则渐专实利而轻思理,乐安谧而远武术。”[3](P39)在这里,鲁迅概括 了浙东民风由古至今的转变。同时,鲁迅还说:“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 岳地带之民气相同。”[4](P156)陈方竞认为,由于“奉禹为祖先”,因而浙东民性中 具有“禹墨遗风”,即周作人所概括的“安贫贱,敝恶食,终岁勤劳”,以及“食贫” 、“习苦”的生活方式,所有这些构成了浙东民俗的特性[5](P113)。鲁迅、周作人散 文中有关家乡民俗的描述无不表现出农事的琐碎与人事的艰辛,如鲁迅的《朝花夕拾》 集,周作人的《花煞》、《回丧与买水》、《关于送灶》、《关于祭神迎会》等,在描 述家乡那些耳熟能详的民间风俗中,表现着“农事”与“人事”相互牵连的关系。
王鲁彦是浙东作家中较多地描写民俗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更多地表现出生活于社会 下层的农民、普通市民的生存状况,及他们精神上所赖以寄托的民间信仰。《鼠牙》是 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以流行于民间的鼠信仰、鼠婚习俗形象地表现出“农事”与 “人事”的关系,表现了潜移默化的风俗习惯对人的心灵的约束。作者将“农事”中的 鼠疫带入“人事”中的纠纷,以民俗反映出民性中的狭隘、自私;在表现“农事”与“ 人事”的同时,作品也反映着民俗中的诙谐与幽默。《岔路》描述了民间求雨过程中隆 重壮观的仪式,在反映“农事”中的民间风情时表现出农民丰富的想像力。《菊英的出 嫁》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乡村中的“冥婚”风俗,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出浙东农村的风习 。王鲁彦另一篇作品《关中琐记》,几乎是民俗、民风的调查记。篇中记述了关中郃阳民间送穷鬼、招魂、逐雀、老鼠嫁女等习俗,这些风俗与浙东风俗有着很多相似 的地方,作者以家乡习俗为参照,对南北方的习俗做了比较,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由 于王鲁彦对浙东民俗环境、乡土生活方式的描述,“使早期乡土小说获得了民俗学的价 值”[6](P68)。
作为鲁迅的同乡,许钦文的小说《疯妇》、《石宕》等都是乡土文学中的优秀之作, 后篇被鲁迅称为“活泼的写出民间生活来”。而在《鼻涕阿二》中则更多地表现出民风 与民性。在浙东作家中,许钦文的作品颇具鲁迅遗风,在他的《一首小诗的写就》、《 鼻涕阿二》中都有着对鲁迅作品的刻意模仿,然而在对民俗、民风的描写上则突出了自 己的风格。他的《步上老》、《老泪》对浙东婚俗的现实的描述,使作品具有独特的民 俗学的意义;《鼻涕阿二》虽然明显地带有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思想,但所表现出的民 风却又与《阿Q正传》迥然不同。鲁迅曾将许钦文和王鲁彦加以比较,认为二者是“极 其两样的”,许钦文的作品“冷静和诙谐”;鲁彦的作品“太冷静了”,因此“失掉了 人间的诙谐”[5]。也许是由于许钦文更加注重人的生存环境,注重民俗对人的品性的 影响,也可以说是注重民性;而王鲁彦的作品则更多地注重于民俗的形式,注重于人所 生存的环境中的民俗。因此,许钦文的作品更具有热情,而王鲁彦的作品更多了客观的 描述。
鲁迅最为赞赏的乡土作家台静农的小说以描写乡村落后的风俗见长,将民俗融合于农 民的悲惨生活之中。小说集《地之子》既表现着乡土中国的民间风俗,又反映出普通农 民的悲剧。《红灯》讲述的是农村鬼节放红灯的习俗。得银因“下水”(当强盗)被杀, 得银娘守寡多年又失去了惟一的儿子,她没有能力办丧事,为他糊了一只小小的红灯。 “当天晚上,便是阴灵的盛节。市上为了将放河灯,都是异常轰动,与市邻近的乡人都 赶到了恰似春灯时节的光景。……他们已经将这鬼灵的享受当作人间游戏的事了。”得 银娘在昏花的眼中,看见得银得到超度,“被红灯引着,慢慢地随着红灯远了!”整篇 作品在描写民俗的过程中,也写出了中国农民的命运。
二
20世纪初的中国仍是以原始农业为经济基础的宗族社会,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是维系 这一体制的基础。重宗族、重血缘是农业民族的典型特征。血缘形成了宗族,地缘决定 着宗族在社会中的地位,血缘与地缘引发了世世代代因地而争的宗族间的血战。浙东现 代作家在表现浙东民性时,更多地反映着这一主题。
王鲁彦的《岔路》,许杰的《惨雾》,都描述了血淋淋的宗族之战,表现出宗族利益 的至高性,特别是《惨雾》更突出了山地居民的原始与荒蛮。《岔路》描述的是为乞雨 ,两个村落的人联合一心求关帝神,但为关帝神轿先到哪村,大打出手,以至酿成血案 。《惨雾》讲述的是,为了争夺两个村落间的沙渚而发生的惨案。如果说《岔路》仅仅 表现着宗族间的利益之争,那么,《惨雾》不仅表现出两家族之间的血腥残杀,同时还 展示了介于两家族间的女性的悲剧:一方是自己的娘家,一方是自己的夫家,在两家族 格杀中,女主人公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弟弟,将两家族的悲剧集于一人的身上。
在这类作品中,引人注意的是表现在作品中的“祠堂”意识。祠堂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是神圣的。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又称宗祠。《说文解字》对“宗”的解释为:“宗 ,尊祖庙也。”《礼记·大传》说:“尊祖故敬宗。”《白虎通·宗族》也说:“宗, 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祠堂”意识的根源是“祖先崇拜”,对祖先的 崇拜是以血亲关系的延续为纽带的,是维系家族、氏族、宗族稳定的保障。祠堂是一个 家族精神上的归宿,通过对祖先的祭祀,沟通家族成员之间的精神联系与情感交流,形 成宗族内部的亲和力和对外战斗的凝聚力。《岔路》、《惨雾》中描述的对外血战,家 族的凝聚力来源于“祠堂”,特别是在《惨雾》中,家族成员几次聚集于祠堂,每次聚 集都会再一次引发出更惨烈的杀伤,其精神来源正是祖先崇拜的“祠堂”意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祠堂”不仅是家族内部沟通、亲和的场所,同时又是家族内部 分裂的爆发处。祠堂有独立的经济来源,这就是“祭田”,它是维持祠堂、家族活动的 经济基础。祠堂设有专人管理,负责修缮祠堂、保存家谱、筹备祭品等事宜。正因此, 形成了宗族中各个家庭之间的矛盾。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描述了表现在祠堂中的家 族内部的争斗。
《一千八百担》的副题为“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写”,明确地表示记述的是家族 内部的事务。宋氏家族有八大分支,一百八十多房,两千多家,宋氏家族曾有过“五世 同堂”、“百岁齐眉”的辉煌,而今却已走向末路,内部矛盾日趋尖锐。作品集中表现 了因共有的一千八百担存粮而引发的宗族内部的争斗。
宗法制度要求在本家之内财产相通,同宗兄弟“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 资之宗”[7](P247-249)。宋氏祠堂在“余则归之宗”上各房都有自己的打算,每个子 孙都想独得公有财产,对此互不相让。正在吵得不可开交之时,一千八百担粮被愤怒的 村民们一抢而光。
三
与宗族观念紧密相连的是“子嗣”,为了家族血统的延续,“典妻”以及相关的婚姻 形式,成为制度民俗中重要的一部分。“典妻”是流行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民间习俗 ,“典”即“租”,即将自己的妻子租与别人。吴越地区的典妻之风在宋代已经开始流 行,元代以后此风更为盛行,《元典章》中记载“吴越之风,典妻雇子成俗久矣,前代 未尝禁止”。明清之际沿袭成俗。清人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记述:“在浙江的宁、绍 、台各地,常发生典妻之事,有妻与人,期以十五年,满则纳资取赎。”
作为一种民俗,20世纪30年代的浙东“典妻”之风仍很盛行,柔石《为奴隶的母亲》 和许杰《赌徒吉顺》所描写的都是发生在浙东的“典妻”习俗。“典妻”是典方与被典 方双方利益的互为,作为被典方,更多的是为生计所迫,不得已而为之。而典方的目的 则是为了子嗣。中国人以家为本位,“家”的扩大是以父系一方单系发展为原则的,这 就决定了“子”的意义大于“妻”的意义,子的延续是第一位的。“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在无子的情况下,以各种方式、手段得子便成为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于是“典 妻”成为相当普遍的一种辅助性的婚姻,既解决了无子的问题,也免却了妻妾之间的纠 葛,同时也使夫妻感情得到了巩固,从另一方面说,也避免了“出妻”悲剧的发生。
柔石《为奴隶的母亲》不仅写出了“典妻”的原因,描述了被“典”妇女的典期生活 ,及解典后的悲惨结局,更重要的是作品揭示了在“典妻”过程中“子嗣”的重要意义 。费孝通在考证中国人的婚姻观时认为,父母双方对子女都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生物 性是由血缘关系决定的,社会性则可以不以血缘为标准。在《为奴隶的母亲》中,我们 可以看到父母的社会性对于被典妻子的意义。春宝妈为秀才家生育了秋宝,三年后,孩 子断了奶,典期也到了,“于是孩子和他亲生的母亲的别离——永远的别离的命运就被 决定”。春宝妈又回到了自己的家,春宝妈与秋宝的关系也就此结束了。在“典妻”行 为中,这种婚外生活所生的子与其母亲的亲子关系被抹杀了,春宝妈与秋宝之间生物性 的母子关系被社会性母子关系所取代。费孝通以《红楼梦》为例,对这种关系做了形象 的论述。他说:“读过《石头记》的人自然记得探春为了赵姨娘那种使人讨厌的劲儿, 在她当家时,明白地向她说,要她不要弄错,自己是王夫人的儿女。意思是赵姨娘不过 是替王夫人怀次胎,并不是赵姨娘用自己名义生的。王夫人尽管心里疼她自己所生的元 春和宝玉,可是她对于探春和贾环等在名分上依旧是母亲。在社会关系上,她得公平地 对待所有的儿女,不论是自己生的还是别人替她生的”[8](P90)。在《为奴隶的母亲》 中,秀才的大妻不也说:“这个儿子是帮我生的,秋宝是我的”;“我会养的,我会管 理他的……”。对于她来说,秋宝虽然是别人替她生的,但由于他们之间所具有的社会 关系,从而提高了她在家族中的地位,她是由儿子,而不是由丈夫来巩固其位置的。
“典妻”不仅剥夺了亲生母亲对于儿子的权利,同时也赋予了典方妻子不可推卸的做 母亲的职责,不管她是否愿意,她都必须平静地接受这一切,否则她将不能在这个家中 生存下去。家庭是以父子为主轴的,子女是父亲的财产,是父亲血脉的延续,夫妻、母 子都不过是配轴,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礼教中最残酷的一面。
在描述“典妻”现象的同时,作家们也涉及到与此相似的“卖妻”现象。如,罗淑的 《生人妻》、台静农的《负伤者》和《蚯蚓们》,表述的都是卖妻行为。“卖妻”现象 的出现,普遍是由于经济的困顿,更直接地是为了生存。《负伤者》、《蚯蚓们》不仅 写出了在“卖妻”行为中女性的悲剧,同时也描写出在这一行为中男性所受到的屈辱。 “典妻”同“卖妻”一样,是一种男性行为,而在这一行为中,女性都是被作为商品任 意处置。
在浙东不仅有“典妻”习俗,同时还有“入赘婚”和“叔嫂婚”,目的同样是为了“ 子嗣”。旧婚俗中的入赘婚既有着“家贫无有聘财,以身为质”的还债之意,同时也有 “以承炫祀,守丘墓”[9](P629)的传宗接代之意。许钦文的《步上老》和《老泪》中 所描写的浙东入赘婚,反映出不同的内容。家贫出赘是《步上老》的主题,为了夫家血 缘的延续而招赘则是《老泪》所表现的内容。
未婚女子招进丈夫称为“入赘”;已婚妇女招进的丈夫称做“步上老”。做“步上老 ”的人多是由于生活的艰难,没钱娶妻,于是不得不到女方家去。《步上老》中的主角 长生由于家境的贫寒而不得不做“步上老”,而他的儿子同样因为贫寒,也将面临这一 境况。《老泪》描述了彩云黄老太太——一生婚姻的悲剧。先是两次订了婚,还未过门 就死了新郎。后嫁给黄麻子做三填房,儿子不到周岁又死于天花,随后黄麻子又病死。 黄麻子临死前留给彩云的话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要她向人“借种”,说成是他 的“遗腹子”。以后,彩云有了女儿明霞,为续夫家香火,招女婿入赘,“明霞从此改 称妈妈为婆婆,她的丈夫叫彩云做妈妈了”。不久女儿又死了,于是彩云又为女婿—— 儿子续弦,“堂堂皇皇的讨进填房儿媳妇”。几年后,入赘的儿子患传染病死了,彩云 又为儿媳妇招了一个“补床老”,“一方面日日夜夜堂堂皇皇的为她的填房儿媳妇做丈 夫,一方面做她的儿子”。彩云——黄老太太的一生都是为了夫家子嗣的延续。篇中的 “补床老”也就是“步上老”,也许这一叫法能更形象地说明这类人的身份。
台静农的小说《拜堂》和许钦文的《难兄难弟》都反映了“叔嫂婚”这一婚姻形式。 《拜堂》描述了乡村中“叔嫂婚”的全过程,表现出在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这一婚姻习 俗的渐趋衰落。这种婚俗之所以能存在的原因更多的是子嗣和经济的考虑,是为死者生 子接嗣,以防死者的祭祀斩绝。同时,也是为了保存死者的遗产于本族之内,不被分散 于外。
四
如果说“典妻”更多的是为了“子嗣”,为了宗族血脉的延续,那么,“再醮婚”则 表现出对妇女精神上的约束。表现寡妇再醮是历代文学作品的一个主题,作品大多表现 妇女丧失及再嫁后的艰辛。在现代小说中也不乏这类作品,浙东作家的作品中也描写了 这一风俗。妇女再醮本来只是一种风俗,“自有史直至宋初叶,寡妇可以再嫁是一贯的 风俗”[10](P370)。但自儒家提倡寡妇守节的理论,并逐渐成为礼教以后,“再醮”就 已不仅仅是风俗,而已成为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的《祝福》展示的不仅 是礼教吃人的主题,同时,也表现出民间风俗对于人的心灵的束缚。祥林嫂的“不事二 主”,以死相抵,并非在于她对礼教的认识,更多的是民间关于妇女再嫁的习俗对她的 束缚。她相信柳妈所说的“你将来到阴司去,那两个死鬼的男人还要争,你给谁好呢? 阎罗大王只好把你锯开来,分给他们”。这些她在山里不曾知道的习俗使她陷入绝境, 于是乞求解脱。解脱的办法是到土地庙里去捐一条门槛,当做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 ,以求赎了这一世的罪名。许钦文的《老泪》中“妇人重婚,在松村算是堕落五百劫, 死去的时候在阴间要走‘火砖头’”;《鼻涕阿二》中再嫁妇女死后将在地狱里“捧火 廊柱”、“赤着脚走火砖头”、“用锯把身子锯开来”等等说法,都是对妇女再醮的精 神压力。鲁迅在《我之节烈观》中引用《壶天禄》和《右台仙馆笔记》中记载的不愿守 节的妇女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人唾骂,做了乞丐, 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为鼓励妇女守节,从宋代到清代的法律规定了寡妇对财产享有继承权。宋代《户令》 规定:“兄弟亡者,子承父份;兄弟俱亡者,则诸子均分。……寡妻妾无男者,承夫份 ;若夫兄弟皆亡,同一子之份。”明代《户令》规定:“凡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 夫份。”清代《条例》写明:“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份,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 之人继嗣”。按此规定,寡妇要享有丈夫的财产必须做到:无子;立志守节;日后须择 子立嗣。这实际上也是要求寡妇必须为丈夫守节,否则寡妇也不会得到财产继承权。节 烈带来的是对人性的束缚与压抑,对于年轻守寡的妇女来说更是如此。许杰的《台下的 喜剧》中松哥嫂五服内的堂嫂“守寡已经五年,但是春情还没有灭杀,很可以在她的服 饰和举止上见得出来。因为她还有一个六岁的儿子,按照习惯,不能随意去改嫁”。这 里所遵从的“习惯”,也正是“夫死从子”。鲁迅认为,节烈之事是由儒家孔孟之道鼓 吹的,“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 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 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此后皇 帝换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11](P121) 。男人要女人守节,既是由于子嗣的关系,也是由于财产的原因。由于经济上的不能独 立,女人也甘于守节,班昭在《女诫》中就写道:“夫有再娶之义,妇无二适之文。” 女人的不争也使节烈之事成为一种风俗而延续。
社会一方面主张妇女“节烈”,另一方面又鼓励“再醮”。妇女在没有经济权的情况 下只能依靠男人生活,丧失后在无子的情况下便被逼迫改嫁,祥林嫂如此,鼻涕阿二如 此,许杰《改嫁》中的启清嫂亦如此。19岁的启清嫂方死了丈夫,留下一个女儿。在她 还沉浸在丧失的悲伤中时,婆婆已在劝她改嫁了,“她说她手中捧着的小东西若是个男 孩子呢,那么张姓的香火,还可以不绝;便是做娘的,在年轻时守了寡,把他养育成人 ,——现在苦了几年之后,将来儿子大了,还可以过老,还可以享几年的儿孙福;—— 总算还有一点希望。只是现在——”。启清嫂没有儿子可以依靠,只能改嫁到别家。“ 节烈”、“再醮”都是为了男方的利益,妇女在这一过程中只是作为商品被买被卖,失 去了自身独立人格的价值与意义。
同样,以妇女牺牲为代价的婚姻习俗“冲喜”,在浙东现代作家作品中也可以读到, 台静农的《烛焰》描写的就是这一民俗中女性的悲剧。“冲喜”是未婚男子因病娶妻, 以求以喜事冲去附着的晦气,达到治病的目的。故事起于办丧事——吴家少爷的出殡, “冲喜”并未带来转机,娶媳妇未能挽救他的性命,新过门的媳妇当上新娘就成了寡妇 。“冲喜”虽然是男女双方生前的约定,但更多的是为了死人。在得知吴家少爷病重时 ,母亲希望婚事能迟一迟再说,父亲却说:“女儿毕竟是人家的人,你不答应也不成话 。”因为许了字,就是人家的媳妇,死亡断不了婚姻的契约,所以仍得嫁过去。说是“ 冲喜”,实际上与“抱主成婚”、“归门守孝”没有差别。
周作人曾说,要了解一国的文化,非从民俗学入手不可。又说:“我常觉得中国人的 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12]。在此,周作人强调了民 俗对于文学、对于改造国民性的重要意义。民俗是一个时代,一个地域的人群共同的生 活方式,是决定着人的命运、性格的一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对民俗的关注,也是对 国民性、对民族文化的关注。同时,民俗作为一种文化,对作家的审美观、创作倾向有 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浙东现代作家所处的地域环境,民间信仰习俗对他们的浸润,都使 得他们在有意无意中将民俗作为关注和描述的对象与借鉴,他们对浙东民俗的描画与书 写使民俗学和文学成为相通的领域。
收稿日期:2002-07-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