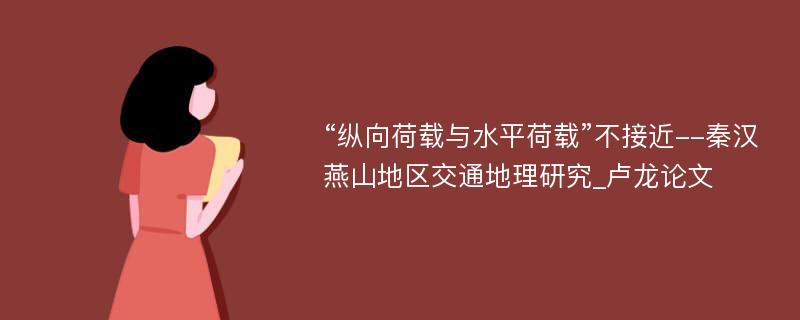
“载纵载横”与无远弗近——秦汉时期燕蓟地区交通地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时期论文,地理论文,交通论文,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0)08-0105-14
《史记》、《汉书》谈及燕蓟地区①战国秦汉社会经济状况时,都称之为勃、碣间都会。都会的形成,除一定人口和城市规模、异常活跃的贸易等条件外,便是无远弗近的道路交通。秦汉统一王朝的交通建设,大有成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毁城郭、平险阻、修驰道,交通便利;两汉时,交通发达。“汉并二十四郡、十七诸侯,方输错出,运行数千里,不绝于道,……陆行不绝,水行满河”②。交通道路深入偏僻地带,道路筑建标准、水平都较高③。
学界对中国交通史已有不少研究④,秦汉交通研究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⑤。但既往成果在区域交通研究方面,存在畸轻畸重情形⑥。就秦汉交通而言,研究多集中关中、关东,对朔方衢处的燕蓟关注不够;虽有部分成果对秦汉燕蓟交通有探讨⑦,然总体不够深入、详尽与系统。
一、东和东北向
主要通往东北及朝鲜北部。战国末,燕昭王攻驱东胡,置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⑧;秦仍燕旧,以四郡部勒东北;两汉时,东北疆域扩展,四郡外,增置玄菟、乐浪郡。军事、行政和经济文化交往的需要,秦汉燕蓟通往东北的道路,在继承历史交通网道基础上,又有进一步发展。燕山山脉横亘北京北部。北京通往北和东北地区,多依横穿燕山的潮河、滦河及支流河谷,以及山海间滨海平原(今辽西走廊)的道路,古北口、喜峰口和山海关分扼三道咽喉⑨。经过后二者或喜峰口以东道路,基本通往东北一带;经古北口者,虽亦可达东北,但尚通今内蒙一带。为便于叙述,本文把从古北口通往内蒙的道路视作北向,这里只言通往东北的道路。
根据记载和有关研究,秦汉时燕蓟通往东北的道路,主要有卢龙、无终、傍海道。
1、卢龙道。因道出古塞“卢龙”(今河北喜峰口一带)而得名。历史上较早言及卢龙道者,为东汉田畴。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征乌桓。五月,畴随军至无终(今天津蓟县)。七月,大雨水,原定行军路线傍海道“洿下,泞滞不通”,军不得进。太祖患之,以问畴。畴回云:
旧北平郡治在平冈,道出卢龙,达于柳城。自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而尚有微径可从。今虏将以大军,当由无终,不得进而退,懈弛无备。若嘿回军,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备,蹋顿之首可不战而禽也。⑩
白檀县,西汉置,东汉废,治今河北滦平东北;旧北平郡即西汉右北平,治平冈(刚或岗),今辽宁凌源西南(11);柳城系西汉辽西郡辖县,今辽宁朝阳南。田氏所云道径,就是从今蓟县出发,东北经喜峰口,沿滦河河谷西北行,至滦平东北,复折向东北,到达凌源西南,顺大凌河上游而下,抵辽宁朝阳。田畴列陈的卢龙道,和《三国志·武帝纪》所载基本一致:“(曹操)将北征三郡乌丸,……傍海道不通。田畴……引军出卢龙塞,塞外道绝不通,乃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经白檀,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八月,登白狼山”。
《传》、《纪》记载田畴所云道路和曹军实际出兵线路,基本一致。异者惟《纪》有“登白狼山”。白狼山即白鹿山,在今辽宁喀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东境。该山位处凌源、朝阳间,由凌源至朝阳,必经白狼一带。但《田畴传》又言:“太祖令畴将其众为向导,上徐无山,出卢龙,历平冈,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余里”。文无“越白檀之险”、“经白檀”。或认为《武帝纪》载“经白檀”有误,“白檀之险”乃卢龙塞外平冈、白檀间的大片“空虚之地”。卢龙道当为出卢龙塞沿滦河左岸北行,再沿滦河支流瀑河北上,至老哈河上游西岸折而东去,沿大凌河趋向东北(12)。此说和《辞海》所云一致。其实,对《武帝纪》“经白檀”,早在清初,《热河志》编者既质疑并予以解释:“若从旧说,以汉白檀为今滦平县地,是魏武既出卢龙塞之后,乃反折而西行,几于南辕北辙,此固势之必无。且田畴所谓‘路近而便’者,义又安在耶?故以魏武师行之道言之,当日军次无终,本欲从东道傍海至柳城,既因道泞回军,上徐无山(今河北遵化一带,西汉置有徐无县)。山在今遵化州西,乃自无终北行之路,继‘出卢龙塞’、‘堑山堙谷五百余里’,皆指塞外之路,而言其曰‘经白檀’者,乃总计自无终回军后所历之地”(13)。该解释未使人尽服,因为它忽略了《武帝纪》关于军队实际行进“经白檀”的记载,此次行军,不存在所谓的“自无终回军”的问题,而是一往直前:历平刚,涉鲜卑庭,东指柳城。但其“白檀之险”的解释,为我们理解问题有所启示。其文云:“田畴熟悉道路,而于白檀独称为‘险’者,盖自今密云一带,崇山峻岭,其东与卢龙塞相接处皆为‘白檀之险’。在田畴之计曰:‘从卢龙口越白檀之险,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明言自卢龙越过白檀之险也。”可见,“白檀之险”和行政建制的白檀县并非同一概念。“白檀之险”的白檀,是指今密云-古北口至喜峰口一带绵延崇山峻岭构成的交通障碍。因此,“白檀之险”是针对密云-古北口至喜峰口间崇山峻岭而言的(14)。如此则《武帝纪》、《田畴传》中的卢龙道即清晰显现:从今北京(燕故都蓟)出发,东行经天津蓟县(无终)、河北遵化(徐无),出喜峰口一带(卢龙塞),沿滦河北行,越白檀之险,再沿滦河支流瀑河河谷北上,经河北宽城、平泉,东向经凌源西南(西汉平冈),顺大凌河北源河谷而下,经辽宁喀左(大城子),由大凌河河畔东指朝阳(西汉右北平郡属县),并通往辽宁阜新(西汉辽西郡治所)(15)。
卢龙道很早即今北京一带通往东北的交通要道(16),秦汉时是燕蓟连接东北的重要道路之一,秦时期的右北平郡治所,西汉右北平郡、辽西郡,都位处该道上。东汉以来,北方乌桓等部族逐渐强大、南侵,右北平郡内移土垠(今河北丰润东南),卢龙道因阻塞而荒废(17),田畴“建武以来,陷坏断绝,垂二百载”之语,就道出了该道自光武帝以来渐遭荒废的情况,东汉末曹操东征乌桓时,仅“有微径可从”。尽管如此,此道仍为燕蓟通往东北的主要道路:其一,曹操讨伐乌桓,所行路径即为该道;其二,后汉灵帝时,赵苞出任辽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18)。表明尽管卢道在东汉末通行条件较差,且鲜卑部族频繁出入,而辽西郡长赵苞仍冒险让家人行走此道,可见该道当时在沟通中原与东北交往方面的地位。隋唐时,卢道仍为中原通往东北的主干道(19)。
2、无终道。无终,春秋时国名,因都无终而名;秦时为右北平郡治所,汉时为右北平郡辖县。因道经无终交通枢纽,故名无终道。据载,春秋前期,该道可能就为华北进入东北的要道。《史记·匈奴列传》:“秦襄公伐戎。……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又《国语·齐语》: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史记·齐太公世家》:二十三年(前663),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孤竹还。《汉书·郊祀志》、《史记·齐太公世家》也载桓公北伐山戎、离枝、孤竹。《史记》、《国语》所记,涉及两个问题:山戎、令支、孤竹部族所在地,令支部族等与山戎的关系。
首先,山戎部族所据地。对于《史记》文,司马贞、裴骃引服虔语云:山戎、北狄,盖今鲜卑也。后世基本沿袭服说。据《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鲜、乌均系东胡,因各依鲜卑、乌桓山而得名。因均为东胡,学界或将二者混谈,甚或伦绪其先后(20)。根据《国语》、《史记》及诸家注疏,我们可知山戎、东胡关系密切,或为同一民族,山戎只是其“别名”;或山戎为“东胡”之一支;或为毗邻的两民族。在谭其骧的两种历史地图集中,春秋、战国时的东胡和山戎,均分别标注,为毗邻部族。其中山戎,春秋战国时地处今大凌河流域(21)。这一标注从胡注《资治通鉴》秦王政三年(前244)“燕北有东胡、山戎”云“自汉北平无终、白狼以北,皆大山重谷,诸戎居之,春秋谓之山戎”(22)文得到较好的印证;但战国后期,大凌河地区为东胡所据。《史记·赵世家》: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前273),取东胡。“正义”云“今营州也”。唐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即田畴所讲的柳城,辖管大、小凌河等地。可见,春秋战国时的山戎,主要活动在辽西大凌河一带,山戎为中原对当时这一地域诸部族的统谓。
其次,令支部族的地理位置。令支或作离支、令疵等,古部族(国)名(23)。裴注《史记·周本纪》“伯夷叔齐在孤竹”引应劭语“在辽西令支”;韦注《国语·齐语》齐桓公“刜令支”:“令支,今圉县,属辽西”。辽西郡主体处于东北,故令支又称“东北夷”(24)。但两汉令支治所何在?《中国历史地图集》标注为今河北迁安西(25)。清代江永却云:令支,今直隶永平府抚宁县,故令支城在卢龙县(26)。今卢龙距迁安约30公里。可见,谭图与江说的令支治所有明显差别,但学界基本采用谭图标注(27)。
再次,孤竹部族的地理位置。孤竹亦作“觚竹”,先秦古部族(国)名。齐桓公北伐山戎、斩孤竹后,孤竹之城存焉(28)。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辽西郡令支县内有孤竹城;颜注《汉书》引应劭语亦可证之(29)。那么,孤竹究竟在何处?《史记·周本纪》“正义”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注《尔雅》“四极”,均引唐初《括地志》“孤竹故(古)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30)。卢龙,唐代平州治所。但江永却说“孤竹,今永平府滦州”(31)。清代滦州治今滦县。江氏之说,恐怕有误。今天的卢龙,位于滦河支流青龙河入滦河口处(32),在滦河东岸;滦县则在滦河下游西岸,二者相距约20公里。关于桓公北征山戎等部族,《说苑·辨物》曰:“齐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溪中十里,闟然而止,……行十里,果有水曰辽水。表之,从左方渡至踝;从右方渡至膝。已渡,事果济”(33)。据此可知桓公北征孤竹,曾渡辽水。《管子·小问》等对此事也有记载,然未载齐军所渡是辽水;《水经注》援引《管子》文,却把此事记入“濡水”,齐军在进攻孤竹前,曾渡濡水即滦河(34)。对《说苑》之辽水,有学者认为当作濡水(35)。这样,齐军要攻孤竹,需先渡滦河,证明孤竹城即卢龙在滦河东、滦县在滦河西,故江永“孤竹,今永平府滦州”之说不确。
最后为令支等部族(国)与山戎的关系,即究竟是被山戎占领,还是彼此为联盟。此事涉及令支等部族(国)与山戎所在地间的交通问题,其间有数百公里之遥,山戎是通过何一交通路线控制令支,或与之形成联盟的。对山戎与令支等部族(国)间的关系,《热河志》称令支、孤竹之地皆为山戎所据(36),不确。因为韦昭注《国语·齐语》时就指出:令支、孤竹,“山戎之与也”。“与”,或谓“党与”、“同盟者”。高诱注《战国策·齐策二》“韩齐为与国”曰:“相与为党与也,有患难相救助也”。杨倞注《荀子·王霸》“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云“与,相亲与之国”;或谓“亲附”、“附从”。如韦注《国语·齐语》“桓公知天下诸侯多与已”云“与,从也”。据此可知《热河志》所谓“令支、孤竹之地皆为山戎所据”不确,令支等部族(国)与山戎间是联盟或附从的关系,或以联盟为主,《北京历史纪年》称之为“部落联盟”(37),恰当。而彼此联盟或附从关系的形成,主要在于:第一,都为边远部族,在生产方式、文化和生活习性等方面具有相似或相同或相通性;第二,彼此交通便利,来往方便。
那么,令支等部族与山戎间的交通路线怎样?山戎居大凌河一带。限于生产力水平,古代开辟道路,常依山傍谷,在山谷低缓处翻越分水岭。居于大凌河一带的山戎,要到达令支、孤竹所在滦河下游一带,首先要逆大凌河而上,经今喀左大城子,然后向南,顺大凌河南源支流而行,再于白狼县折向西南,经黑山与七老图山-努鲁儿虎山间谷地行进,越过刀尔登,进入滦河支流青龙河上游,顺河而下至卢龙(孤竹),由卢龙渡滦河(濡水),沿滦河北上至迁安西(即旧令支)。反过来,桓公出军令支、孤竹,即从今北京出发,向东经华北平原北端的河北玉田、丰润(秦汉土垠),然后沿燕山东南北上,至迁安西(即春秋令支),“刜令支”后,再顺滦河西岸而下,至青龙河(玄水)入滦水处渡滦水,至卢龙。这样,以令支、孤竹为中介点,因山戎侵燕、齐桓公伐山戎的军事活动,一条燕蓟通往东北的道路被打通了(38)。
与卢龙道相比,无终道相对曲折,里途略远,但因通过地区为平原或河谷,无崇山峻岭,故道路状况要好。顾祖禹曾说:“春秋时,山戎尝为燕患,齐伐山戎以救燕。盖其地控据高深,直走燕都,六驿而近,方轨并辔,无山溪、关隘之阻也。”(39)1955年以来,沿此道的青龙河谷和大凌河谷地区,出土了大批商周青铜器和兵器,表明当时其地已是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孔道(40)。秦汉时,无终道仍为东北诸民族与中原频繁往来的陆路要道,是通往东北“较为便捷”的道路,特别是右北平郡内移后,“卢龙之途遂渐阻塞,仅无终一道尚为往来于塞内外者所必经”(41)。
3、傍海道,即依傍近海的道路。颜注《汉书》武帝元封五年(前106)武帝“北至琅邪并海”:“并读曰傍。傍,依也。”故“傍海道”又称“并海道”(42)。史念海曾指出,秦汉东北诸郡濒海之处,地势平衍,易修道路,故由广阳(今北京)到东北之途最方便。自碣石循海东行,可达辽西、辽东,并远抵朝鲜。武帝时,楼船将军杨仆从齐浮渤海而东征朝鲜,左将军荀彘出兵辽东以佐之,荀氏之师所行即为并海道(43)。
傍海道名始见于《三国志·武帝纪》曹操北征乌桓“傍海道不通”。由此初知傍海道从今蓟县出发,然具体路径,文献载之不详,学界研究结论也彼此纷纭(44)。但可以肯定:傍海道是秦汉时华北通往东北交通道路之一。该线从蓟县出发,经卢龙和山海关等要塞,可达辽西、辽东乃至朝鲜半岛(45)。否则,曹操不会把它作为北征的首选行军路线。但因傍依大海,每逢雨季,该道积水严重,通行状况极差;加之沿途人烟稀少,四野荒芜,该道在秦汉时并非通往东北的主道(46)。
二、北去方向
主要指西北和北偏东向。由北京通向北方道路,一般经军都山、燕山间峡谷山口,主要乃西北方的南口-居庸关和偏东北的古北口。人们通常把经过该二关口的必经之路,各称居庸关道和古北口大道(47)。
1、居庸关大道。南口位于北京小平原西北隅军都山、西山交接处。由小平原出发,从南口入山,穿峡谷,经居庸关,翻八达岭转向西北,沿今洋河(秦汉于延水)而上,经宽阔山间盆地,可上内蒙古大高原(48),是为居庸大道。
秦汉时,居庸道路线基本不变:从北京出发,经南口、居庸关,在延庆南越八达岭,顺今官厅水库所在谷地西南行,在河北内桑干河(秦汉治水上游)、洋河入官厅水库处,沿洋河西北行,迭经怀来、宣化、万全、怀安、内蒙兴和等地,进入内蒙高原。该道是秦汉燕蓟通往北方的要道。秦时上谷郡治所沮阳(今河北怀来东南)位处居庸道上;西汉幽州刺史部上谷郡的15县中,有沮阳、昌平、军都、夷舆、居庸、泉上、涿鹿、且居、下落、潘县、茹县、广宁、宁县(西部都尉治所)等13县,并州刺史部代郡所辖马城(东部都尉治所)、延陵、且如(中部都尉治所)等县,都处在该道上;东汉幽州刺史部上谷郡所辖8县中,有沮阳、居庸、涿鹿、下落、潘县、广宁、宁县(护乌桓校尉治所)等7县,幽州代郡马城和广阳郡辖县昌平、军都等,也处该道上(49)。上述秦汉郡县在居庸大道及附近的分布情况,基本上反映了该道在燕蓟交通北方方面的突出地位,说明该道在保证秦汉政府对上述边远县域的行政管理上拥有不可小觑的意义。
由于居庸道北通蒙古高原,南连华北平原北端,秦汉北方异族部落欲进入中原,只要沿今永定河支流洋河东南下,即可攻略沿途县城,侵扰上谷郡所。该道同时也是秦汉政府抗击异族入侵的要道之一。笔者粗略统计,两汉时匈奴、鲜卑、乌桓等北方异族部落入侵幽燕和两汉政府出击活动中,至少一半涉及上谷(50)。由于来去交通便利,异族军队不仅入侵频繁,且有时南下甚深,如安帝元初五年(118)和建光元年(121),鲜卑军队就曾寇犯居庸险塞。和平年代,居庸道又是汉夷商贸往来的纽带。汉代在塞上宁城(今河北万全)设“胡市”(51),允许汉夷民间贸易,幽燕因而成为国内一商贸活动频繁地区。由于来往道上的人员众多和成分复杂,为加强交通、贸易管理,秦汉政府还在居庸险隘设有关卡(52),出入者需要出示地方行政机关发放的通行凭照(53)。
2、古北口大道。该道因由密云东北古北口出而得名。因道经秦汉重镇平刚,故道又名平刚道(54)。古北道的存在,所据有三:(1)自秦在东胡置渔阳、右北平等5郡以来,几郡秦汉并存。右北平、渔阳郡相邻,按秦汉惯制,彼此间当有道路相连。(2)据两《汉书》等,秦汉北方异族频繁寇边,屡攻右北平,入渔阳,也表明二者交通便利。同时,汉军多次出击入侵者,通常由渔阳出发,从右北平迂回北上,对之形成包抄之势(55),也说明渔阳、右北平间有道路可通。(3)《太平寰宇记》引《冀州图》: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惟有三道。其中“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日(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56)。表明从今北京出发,可达右北平所在地平冈,并抵达匈奴左贤王行在。
古北道具体路线怎样,传世文献直接线索甚寥。学者较多引用者,为《冀州图》所载。但在理解上存在问题,即将其所载看作一条线路,似不妥。因为既然“经北平、渔阳,向日(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又从何谈起,白檀和卢龙塞,西北与东南,南辕北辙。实际上,《冀州图》记载的入塞东北,为泛言,可能包括两条路线:一是北平—渔阳—白檀—平刚—匈奴左地,二是北平—卢龙塞—辽西—匈奴左地。后者当为卢龙道,前者则为古北道即平刚道。
关于秦汉古北道走向,学界也有分歧,根源在于右北平郡治所何在。不少研究认为右北平治今内蒙宁城附近,古北道线路为:由今北京东北行,经密云西南(渔阳县),出古北口东北向前进,经河北滦平东北(白檀县)渡滦河(濡水),由平泉(西汉字县)北上,抵内蒙宁城附近(右北平郡治所)(57)。对右北平郡治宁城说,这里略作辨析。宁城处老哈河上游,作为右北平郡治所,西汉时,平刚在抵抗或出击异族入侵上,具有重要的地理价值和军事意义。鉴此,古北口道肯定经过平刚;同时,沟通渔阳的平刚,自然与其时的辽西郡有道相连。辽西郡治所(秦、东汉治今辽宁义县西,西汉在今阜新西南)地处今大凌河流域,横亘辽西郡治所与宁城间的,是与大凌河平行的努鲁儿虎山,宁城与辽西治所各处努山西北端山麓和东南丘陵。如右北平治宁城,则古北道在从平泉向东北行近200华里到宁城后,又翻越努山,进入大凌河流域;或由宁城向西南返回,从凌源附近的大凌河北源进入大凌河流域。不论由何一路从宁城进入辽西郡,或翻山或绕道,都有悖常理。而平刚若在凌源西南,则由平泉向东北行,可直接进入大凌河流域,绕道、翻山之苦自不存在。所以,笔者认为西汉右北平治所位于凌源西南的说法较为合理。
综上,笔者以为古北道走向应是:自广阳蓟县出发东北行,经渔阳出古北口,东北行经白檀,渡濡水,循水东南行,于今承德折向东北,趋字县,再由平泉抵平刚(今凌源西南),与卢龙道合。两汉时的渔阳、右北平郡特别是前者许多辖县都处该道上或附近。据《汉书·地理志下》,西汉渔阳郡12县中,渔阳、狐奴、路、安乐、厗奚、犷平、要阳(都尉治)、白檀、滑盐等9县位处道上或附近;右北平郡已知故址者,有平刚、字县等位于道上。另据《后汉书·郡国志五》,东汉渔阳郡9县,渔阳、狐奴、潞、安乐、傂奚、犷平等6县位道上或附近。东汉时,北方疆域萎缩,右北平内迁,古北道西汉时所达地区基本为鲜卑所据,所辖县无一与该道相近。
古北道开拓较早,至少春秋战国时该道就承担着沟通华北与东北的任务。战国时,由燕都东北行,经后来的渔阳郡治所,沿大凌河谷至于辽西治所,再东渡辽水而至于辽东郡治襄平(58);另有研究指出,尽管古北道早见通行,但因险狭崎岖,去往东北方向极为不便,一直没有成为经常性通途,迄唐为止,在交通东北方面,古北道的作用难匹于卢龙道(59)。不过,该道西汉时在出击北方异族武装入侵方面具有他途无法取代的作用,则从另一侧面表明它在秦汉时的价值(60)。
三、西往方向
包括西线北边道和西南飞狐道两条道路。
1、北边道。北边道因地处秦汉北陲得名。兴筑此道,与古长城关联甚密。战国时,赵、燕等国为抵御外族内侵,于其北境修筑长城,并修建了几与长城平行的北方道。因此,燕蓟通往西部的北边道,至少战国时就存在。《战国策·燕策一》载苏秦游说燕文侯:“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踵道数千里”。《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说燕“西有云中、九原”。“索隐”:“《地理志》云中、九原,二郡名,秦曰九原,汉武帝改曰五原郡”;“正义”:“二郡并在胜州也。云中郡城在榆林县东北四十里,九原郡在榆林县西界”。云中始置于赵武灵王,在今内蒙托克托东北;赵邑九原,在今包头西;赵国代郡,在今河北蔚县东北;燕郡上谷,秦治今河北怀来东南(61)。苏秦所说表明,在今包头—托克托—蔚县—怀来一线,燕、赵两国为防匈奴,其间有道路相连。该道为当时燕国通往西部的一条主要道路(62)。
秦汉时,北边道仍为幽燕通往全国的重要道路之一(63)。秦时为防御匈奴,大修长城;为控制国内各地,“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64),大筑道路。秦代经营的交通大道,多利用战国原有道路(65)。其“东穷燕齐,南极吴楚”(66)的驰道建设,自然也充分利用战国时的北边道。有关文献没有载明驰道的具体走向,但学界根据秦皇汉武的巡狩活动,已有繁多成果问世。
《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二年(前215),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始皇巡北边,从上郡入”。上郡,秦治肤施,今陕西榆林东南。这一记载说明秦皇东从碣石出发,大致经行了北边道的大段(67),然后南下由今榆林回咸阳。另有学者据此描绘了北边道的部分线路(68)。还有研究者指出:北边道在秦国统一后、未设九原郡之前,是由上郡北上、经云中而至辽西的(69)。据此推断,在设九原郡前,秦北边道西端可能止于云中;置九原后,其西端则延至九原一带。《史记·秦始皇本纪》可证之:三十七年七月,始皇崩于沙丘平台,辒凉车载棺回京,行遂从井陉,抵九原,行从直道至咸阳。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井陉,在石家庄西。有人据此而拟出秦皇棺回咸阳的路线:从井陉经石艾(今山西阳泉)、马首邑(今寿阳)到太原郡(治晋阳,今太原南),再经娄烦(今宁武)、马邑(今朔县),到雁门郡而至云中(70)。实际可能未经太原,而是由井陉向西北,逆今滹沱河(秦虖池河)而上,由今山西原平县西北行,经轩岗至宁武,北上经朔县到右玉,再沿浑河河谷而下,至今托克托附近,最后由河套平原行至包头西,即秦九原郡,经直道抵咸阳。表明九原郡设置后,秦汉时的北边道得以向西进一步延伸(71)。
两汉时,北边道仍是燕蓟通往西部的要道。《汉书·武帝纪》:元封元年(前110),武帝为讨伐匈奴“巡边垂”,“行自云阳,北历上郡、西河、五原,出长城,北登单于台,至朔方,临北河”,到达了北边道西端;《史记·武帝本纪》:同年四月,武帝登封泰山,随后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至甘泉。由驰道东端向西,舆历北边道全程。可知武帝时的北边道,有适于浩荡的帝王乘舆车骑队列通过的规模(72)。而且,北边道还是两汉处理北方异族事务的重要道路。汉夷构衅时期,北边郡县作为出兵异族的基地,北边道在军队调遣、辎重运输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北边道又是交通内郡与东北等边地的道路,自西向东,北边道先后和直道、上郡云中道、太原雁门道、邯郸广阳道、居庸道、平刚道、卢龙道、无终道,以及沿黄渤海岸的并(傍)海道等至少9条道路相连(73)。因此,秦汉时的北边道对王朝的兴衰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燕蓟与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文化交往的主要路线。如顺帝阳嘉四年(135)冬,乌桓寇犯云中,一次便“遮截道上商贾车牛千余两”(74)。当时北边道上来往商旅众多、商贸繁盛的情景由此可知,折射了北边道是一比较繁忙的民用运输线。
北边道的通行状况与长城的作用联系甚密。尽管东汉时的北边道依旧发挥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东汉以来北方游牧族的南下和北边居民在政府组织下的内徙,以及由此而导致的长城防卫作用减弱、北边地区农业经济的衰落,由燕蓟通往西部的北边道部分地段通行状况逐渐恶化(75)。东汉初平元年(190),董卓挟帝长安。幽州牧刘虞“欲奉使展效臣节”。众人议荐田畴。行前,畴曰“今道路阻绝,寇虏纵横”;“既取道,畴乃更上西关,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间径去,遂至长安”。胡注《通鉴》:西关,居庸关;北山,阴山(76)。据此,我们可知畴行路线:从居庸关向西北行,越长城,由塞外沿阴山西行,于河套平原西端南下,经朔方抵长安。可见,东汉特别是后期,由于北疆内缩和社会治安窳下,北边道多有阻绝,以致田畴奉命到长安,惟“期于得达而已”。为完成任务,田畴不仅精心选择线路,且需“循间径”,绕道朔方(此前的北边道由五原即秦九原而南下至关中)。因此,北边道的交通状况,东汉远较西汉为下。
2、飞狐道。《辞海》“飞狐”:①要隘名。今河北蔚县东南恒山峡谷口之北口,古为河北平原与北方边郡间交通要道飞狐道咽喉;②古道路名。东汉初筑,南自今河北涞源、蔚县之恒山峡口,东北通怀来、北京市的道路。对于历史上的飞狐道,王文楚曾有专门研究,深值借鉴(77)。“飞狐”一词较早见于《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汉三年(前204),郦食其建议刘邦距蜚狐之口,守白马之津;《汉书》郦传“蜚”作“飞”。郦生所说“蜚狐”,为飞狐关隘,非道路。不过,他要刘邦据守“蜚狐之口”,应有道路通过。有关“飞狐道早在楚汉之际,就已形成”(78)结论因此不虚。《辞海》称筑于东汉初、《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始标注“飞狐道”(79),都不准确。此后郦语以外涉及秦汉“飞狐”的事例有:《汉书·文帝纪》,后元六年(前158)冬,匈奴骑入上郡,汉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后汉书·王霸传》,建武时,卢芳与匈奴等连兵,寇盗尤数,缘边愁苦,王霸“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关于上述记载需弄清两个问题,即飞狐口所在、飞狐道起讫及走向。
首先,飞狐口所在,《史记》郦传“集解”引如淳语:“上党壶关”(80)。但颜注《汉书·文帝纪》则说“如淳曰在代郡”。壶关在晋南即今山西长治东南,而代郡在晋北,相去殊远。而云“上党壶关”仅一例,《史记》、《汉书》其他注家均称飞狐口在代郡。如《史记》“集解”在引如淳“上党壶关”.后按:“蜚狐在代郡西南”。《水经注·漯水》:“言在上党,即实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颜注《汉书》郦传:“臣瓒曰飞狐在代郡西南”,并云“瓒说是,壶关无飞狐之名”,否定了如淳“壶关”说;在注《汉书·匈奴传》后元六年汉使“赵屯飞狐口”时,颜氏又说:“险阨之处,在代郡之南,南冲燕赵之中”。飞狐代郡说也得到后人如宋元王应麟、胡三省等的肯定(81)。飞狐口具体位置,《水经·漯水》:漯水又东流,祁夷水注之。水出平舒县,东径平舒县之故城南泽中。魏《土地记》曰:代城西九十里有平舒城,祁夷水又东北,得飞狐谷。魏《土地记》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关水西北流,径南舍亭西,又径句琐亭西,西北注祁夷水;《史记》郦传“正义”:蔚州飞狐县北百五十里有秦汉故郡城,西南有山,俗号为飞狐口;胡注《通鉴》:《地道记》恒山在上曲阳县西北百四十里,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山岋,号飞狐口,北则代郡也(82);清初《大清一统志》:飞狐关,在蔚州南。魏氏《土地记》代城南四十里有飞狐关。《蔚州志》飞狐口在州东南六十里,北口在州南三十里(83)。
按:漯水,秦汉时治水,今桑干河;祁夷水,今桑干河支流壶流河;平舒,今山西广灵县西;代城,今河北蔚县东北;祁夷水支流飞狐关水,秦汉在交通关隘处设有关卡,飞狐关水可能因飞狐关之设而得名。飞狐关水呈西北-东南流向,在蔚县南;飞狐谷,郦注称即飞狐之口,有误,实际应是飞狐关水所在峡谷(84)。《史记》郦传“正义”飞狐县治今河北涞源,为隋改汉以来广昌县置。胡注《通鉴》引《地道记》之恒山,在今河北曲阳西北;曲阳,即今曲阳;“恒山岋”之“岋”,《康熙字典》引《正字通》“岋”本同“岌”。《说文》释岌为“山高貌”。胡注《通鉴》魏王“珪自邺还中山,将北归,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恒岭,恒山之岭”(85)。雍正《畿辅通志》引胡注云“恒岭即恒山山岋也”,将“岭”书“岋”。可知,《地道记》“恒山岋”即恒山岭。但清初《骈字类编》“山岋”引《水经注·白水》“隆山南有一小山,山坂有两石虎”,则将“山坂”作“山岋”(86)。坂,同“阪”,山坡、斜坡。又表明“山岋”为低矮山岭或山地。这和宋人韩拙“小山曰岋,大山曰峘,岋谓高而过”(87)之“岋”的界定相吻合。所以,“恒山岋”就是相对低矮的山地。正由于其地势相对低矮,故而飞狐口落位于斯。蔚州,治今河北蔚县(88)。由此可知:飞狐口应在蔚县或秦与西汉时代郡西南的恒山口,其所在地形乃恒山西北壶流河地区的低矮山地;飞狐关并非所谓的“亦即飞狐口”,因为二者方位不同:飞狐口在代郡西南,飞狐关则在代郡南流经飞狐谷的飞狐关水上,不可混淆;飞狐关水所在的飞狐谷应有一条道路,道上设有飞狐关、南舍亭、句琐亭,表明该道交通地位十分突出。
其次,飞狐道起讫和走向。有人认为,汉代飞狐道由洛阳至广阳郡驰道上的涿郡故安(今河北易县东南)西行,经广昌(今涞源)至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89),似不确。秦汉飞狐道具体路线的较早记载为《后汉书·王霸传》王霸“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一段文字。它透露两个信息:其一,治即整治、修治。王霸等“治飞狐道”,说明该道此前有之,殆因崩坏(90),王霸等对之加以修整;其二,整修后的飞狐道,则从蔚县东北到大同东北,总共300多里。但李贤注《王霸传》:“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飞狐县即今涞源,怀戎县为唐代妫州治所。《旧唐书·地理志二》:妫州,隋涿郡之怀戎县。贞观八年(634)改名妫州,取妫水为名。长安二年(702)移治旧清夷军城,天宝元年(742)改名妫州郡,乾元元年(758)复为妫州。旧领县一,怀戎,后汉潘县,属上谷郡,北齐改为怀戎,妫水经其中,州所治也。妫州,天宝后析怀戎县置今所。《文献通考·舆地考二》所载大体同此。汉上谷郡治沮阳,即唐怀戎县治所,在今怀来东南。如李贤所注为实,则:(1)李贤“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说明飞狐口为飞狐道出口。(2)王霸等“治飞狐道”,不仅修整了从蔚县到大同间300余里的道路、亭障,而且还打通了蔚县东北到怀来东南的飞狐道,直接沟通了河北平原与燕蓟一带的军事交通,加强了彼此间的联系(91)。
飞狐道东北通往上谷的线路,或据《水经注》进行了勾画:由蔚县代王城向东北,沿壶流河支流定安河河谷和涿鹿南桑干河支流岔道河(即《水经注》协阳关水)谷道东北行,经汉代潘县古城(今涿鹿西南),至涿鹿(汉下落县)后沿桑干河谷地东行,直达怀来(92)。《水经注》的记载,不仅提供了飞狐道从蔚县到怀来段的线路,还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李贤注《后汉书·王霸传》所云之飞狐道从蔚县“北通妫州怀戎县”的线路,或许就是王霸等所为。
至此,结合相关研究,飞狐路线清晰显见:该道以飞狐口即蔚县西南为中界点,一向北可达大同一带(秦汉平城);二向南沿飞狐关水可达涞源(汉广昌县),并南越倒马关,沿今唐河(秦汉寇水),进入河北平原(上述涞源至大同的线路,可能西汉前就存在);三向东北,从蔚县东北沿壶流河及其支流定安河河谷,以及岔道河河谷而行,中经汉潘县古城、今涿鹿,复沿桑干河谷地东行,抵今怀来。该道可能始辟于东汉初。由于是沟通河北平原与燕蓟、平城、太原间的交通要道,飞狐道在秦汉以降时期沟通上述地区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93)。
四、向南方向
燕蓟与南方的交通道路,两汉文献有诸多记载。如《史记》、《汉书》称邯郸北通燕涿、燕蓟南通齐赵等。故赵、齐两国都城为邯郸、临淄。从此记载出发,我们可将燕蓟通往南方的道路,从历史行政或文化区域方面,分为赵邯郸和齐临淄两个方向。
1、赵邯郸向。秦汉时,该道主要通往京师,属中央与地方间交通,其性质或功能以中央对所属郡国的政治、军事控制为主。该道主要沿太行山东麓南北高地而行,故被称为太行山东麓大道;秦汉时,该道连接燕赵两大城市:赵邯郸和广阳郡(国)蓟,故又被称为邯郸广阳道(94)。
数千年前蓟城始兴时,华北平原连接北京小平原只有沿太行山东麓一途(95)。史念海指出,春秋时的交通已有相当规模,但他并未提及太行山东麓大道及其在诸国政治、军事交往中的作用(96)。我们据此认为,战国以前,太行山东麓大道可能还没有完全形成;而到了战国时,随着燕蓟的兴起与强大,以及和中原事务交往日益频繁,该道在南北交流中的作用与意义日渐凸现。
战国群雄并起,形成了以各国都城为主的区域性经济都会。其中太行山以东(包括偏南)者有:温(今河南温县西南)、轵(今济源南)、野王(今沁阳)、朝歌(今淇县)、邯郸(今河北邯郸)、中山(今定州)、涿(今涿州)、蓟。这些都会彼此交通相联,如邯郸北通燕、涿,燕蓟南通赵地等。于是就形成了由洛邑向东北行的太行山东麓大道:经温或轵,过野王合为一途;复由野王东北行,经朝歌、邯郸,至中山而向北通往涿、蓟(97)。
学界对秦汉时的太行山东麓大道多有关注,认识基本一致(98)。但秦汉燕蓟通往河北等南方的路线不惟一途,此外另有一道,“特以其偏僻荒凉,不为世人所注意耳”。战争和巡幸是古代交通发达的二大原因。史念海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后汉书》之《光武帝纪》、《冯异传》、《王霸传》、《任光传》、《吴汉传》、《耿弇传》等,考证了秦始皇三十二年巡狩、两汉间光武北征和东汉初光武巡幸活动经过的地点,初步勾勒了秦汉燕蓟通往河北等地的2条道路:经涿郡西南行,以至中山、邯郸诸地;经饶阳南行,以至信都、魏郡诸地。笔者经对史著初步整理,条理出该2条道路的具体线径:(1)蓟—涿县—范阳(今河北定兴南)—容城(今容城北)—北平(今满城北)—卢奴(今定州)—新市(今新乐南)—真定(今正定南)—元氏(今元氏西北)—防(房)子(今高邑西南)—广阿(今隆尧东)—邯郸—邺(今临漳西南)—洛阳(秦和西汉则由洛阳至关中)。该线即太行山东麓大道(邯郸广阳道)。(2)蓟—安次(今河北廊坊)—易(今雄县西北)—饶阳(今饶阳北)—下曲阳(今晋州西)—临平(今晋州东南)—鄡(今辛集东南)—信都(今冀州)—清阳(今清河东南)—馆陶(今馆陶)—邺—洛阳(99)。该线北连蓟城,南通馆陶,可名馆陶广阳道。
2、齐地临淄向。从现有研究成果看,通往齐地的道路有2条:燕蓟-临淄道、并海道。前者即渤海西岸大道(100),后者则和由燕蓟通往东北的傍海道相联,故又称傍海道。燕蓟通往齐地的道路,秦汉时属区域间交通,功能或性质主要为区域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有研究者认为,渤海西岸大道迟至春秋战国时既成(101)。此间燕齐军事交往频繁,透过这些军事活动所经过的地点,可大体了解当时的交通路线:
(1)《史记》:燕庄公二十七年(前664),齐桓公救燕,伐山戎,至孤竹而还。燕庄公送之入齐。桓公以“非天子,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无礼于燕”而“分沟割燕君所至与燕”(102)。《燕召公世家》“正义”:《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沧州长芦县东北十七里,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与燕,因筑此城,故名燕留。唐长芦县治今河北沧州。高士奇《春秋地名考略·北燕》:燕庄公送齐桓处,在今沧州长芦县东北,号曰燕留城;乾隆《历代通鉴辑览》“齐人伐山戎”注:《史记》“正义”沧州长芦县有燕留城,即齐桓公分沟割燕君所至地。长芦,今直隶天津府天津县(103)。表明燕留城在今沧州东北。然雍正《山东通志》:乐陵,燕留城,在县北境。《郡国志》云即齐桓公割地与燕处(104)。今山东乐陵毗邻河北,距沧州百余里。把“燕留城”为长芦、乐陵二说相联系,很能说明沧州、乐陵应是燕齐交通所经处。
(2)《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前380年,齐起兵袭燕,取桑丘。“正义”:《括地志》云桑丘故城俗名敬城,在易州遂城县。唐代遂城在今河北徐水西南。
(3)《史记·燕召公世家》:燕釐公三十年(前373)伐齐,败于林营。林营,或作林狐。“索隐”:林营,地名。一云林地名,于林地立营,故曰林营。“林营”为何,已不可考。但其所在地,也应处于燕齐交通道上。
(4)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燕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大败齐愍王于济西,齐王逃至莒(今莒县)。燕军克齐70余城,并大掠临淄(今淄博东北)而归(105)。济西详细何指,不确。从胡注《通鉴》“济西,地在济水之西”(106)看,约在济水南—北流向的定陶(今定陶)—历城(今济南)一带;而聊城(今聊城西北)则在这一地带的北部,正好处在此次战争部队行经的道上。
将上述燕齐军事活动路线串联,可大致勾出燕齐交通道路:从今北京出发,南经河北徐水,东南折向沧州,南下至山东乐陵,西南可至聊城,在定陶—济南一带渡济水,沿泰山西北麓直抵临淄。史念海曾指出,平原津(今平原南)应为燕齐往来著名津渡(107)。因此,该道或由沧州南下从平原津渡河至聊城,再渡济而东北到临淄。因道经平原津渡,或名之为“平原道”(108)。
秦汉时,该道依旧为燕齐交通要道。结合史念海的研究,我们粗知秦汉平原道路线:经渤海(郡)(西汉郡治浮阳,今沧州东南;东汉郡治南皮,今南皮北亦即沧州西南)东南行,过平原、济南(郡或国)(今章丘西北),东至临淄,西至定陶(109)。史著不曾给出该道沧州以北的路线,根据前380年齐取燕桑丘即徐水史实,我们可推定秦汉时的平原道,可能仍经徐水。果如斯,则燕齐平原道就和燕赵邯郸广阳道、馆陶广阳道相交会,形成交通网。
秦汉时,临淄和定陶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贡品”“齐陶之缣”生产规模较大(110)。二者又是重要的商业城市,“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市租“日得千金,言齐人众而且富”(111)。《盐铁论》之《通有》、《力耕》亦载临淄“富冠海内”,为天下名都;“齐鲁商遍天下,故乃贾之富或累万金”。临淄富庶和齐鲁商人活跃,均以便利的交通为前提。
并海道的形成时间,可能主要在秦汉时,且与帝王出巡相关。王子今研究并海道,主要围绕帝王出巡展开(112)。按今之政区,秦汉并海道可分浙江、江苏、山东、河北、天津段。山东并海道,起自琅邪(胶南西南),经不其(今即墨西南)、成山(今荣成东北)、不夜(今荣成北)、之罘(今烟台北)、腄县(今福山)、黄县(今蓬莱西南)、徐乡(今黄县西北)、曲成(今招远西北)等地,始终与海岸并行;此后经卢乡(今平度北)、平望(今寿光西北)、巨定(今广饶北)、漯沃(今滨县西)、富平(今阳信东南)西行。河北、天津段并海道由今阳信西北至河北盐山南(秦汉千童)、黄骅(沧州东北)、天津静海、武清和宝坻一带(113)。天津以北的并海道,即通往东北的傍海道。不过并海道由富平西行,可能经乐陵,在此与渤海西岸大道相会,然后并由千童北上,于沧州东北分异,渤海西岸大道西北趋徐水,并海道则从今黄骅进入天津境。
综观秦汉燕蓟对外陆路交通路线,我们可得出以下初步认识:
第一,秦汉时的燕蓟,陆路交通十分便利,为朔方衢处。史念海认为,秦汉由广阳至各地道路约有7途(114)。而本文表明当时燕蓟通往四方之道至少有10条:卢龙道、无终道、傍海道(连并海道)、居庸关道和古北口道(平刚道)、北边道、飞狐道、太行山东麓道(邯郸广阳道)、馆陶广阳道、渤海西岸道(平原道)、并海道(连傍海道)。上述道路交会于燕蓟,形成一完整的交通网。通过该网络,从燕蓟可抵全国各地;燕蓟还是秦汉帝国通往东北交通干线的中枢地,燕蓟如渔阳郡及路县还因系交通要点得名(115)。
第二,道路的功能性质与其通行良窳状况息息相关。燕蓟对外陆道,通往东北者4条、西及西北2条、西南和南向的5条,以通向南方和东北地区为主,而西、西北向明显稀少。从道路的功能看,西南、南方通往京师的道路,主要服务于中央对地方的行政,其次为区域间(燕蓟与赵、齐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而通往东北的道路,除具有国家行政性质外,更因为秦汉时的燕蓟,一直是国家对东北和北方少数民族部族采取军事行动的基地,平刚等几条通往东北的道路,主要职能为服务于军事活动。由于道路的功能相异,彼此的通行状况也有相当差别。通往东北的道路,因与少数民族事务相关,随着国家一定时期内的民族政策调整和军事活动频度变化而呈现出相应的变迁与兴废。特别是东汉以来,随着北方少数民族内侵,边郡人口内迁,边地道路交通也随之逐渐寝荒;通往西南、南方的道路,由于是国家行政和区域经济交流之途,其功能具有长期性和客观必要性,道路不仅始终存在,而且因国家重视和有效维护,其通行能力一般较良好。秦汉中央通往燕蓟的交通速度可以说明其间道路的通行状况(116)。驿传的速度是以良好交通为前提。由于道路畅通,西汉才得以屡屡挫败发生在燕蓟一带的叛逆事件;两汉之际的刘秀也因此而雄踞幽冀、南指中原,最终取得政权。
第三,轮轨交错与朔方经济都会。《释名·释州国》:“小邑不能远通”。城邑的规模与其交通地位有相应的关系。都市规模的形成,本身也是以交通条件为基础(117)。秦汉交通发达、商贸活跃(118),极大地促进了位于交通枢纽上的城市之繁荣(119)。燕蓟的北国都市地位,早在战国时就已确立(120);秦汉燕蓟“载纵载横”(121)和无远弗近的陆路交通和以交通为基础的活跃之商贸,进一步巩固和保障了其一方区域都会的地位。马、班在描述当时燕蓟经济时,无不将之作为全国重要的商业“都会”之一。《盐铁论·通有》也载西汉士大夫称燕蓟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
第四,交通与社会风习文化。有学者认为,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看,交通网的布局、密度及其通行效率,决定了文化圈的范围和规模(122)。此语道出了交通之规模、质量与文化辐射、交流规模和程度的问题。孙毓棠对汉代交通与文化的统一性有所阐述。他说,便利的交通“使得汉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见,他们的见闻比较广阔,知识易于传达。汉代的官吏士大夫阶级的人多半走过很多的地方,对于‘天下’知道得较清楚,对于统一的信念比较深。这一点不仅影响到当时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够加强了全国文化的统一性”(123)。秦汉燕蓟通往京师的道路通便,为中原文化尤其是儒家正统文化对燕蓟文化,特别是地方风习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典型事例便是婚姻陋俗得以匡改。据《汉书·地理志下》,受太子丹影响,战国时期燕蓟存行“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这一被后世认定为“借妻婚”的习俗,西汉成帝时,此俗仍有较大的市场。后来由于国家的专门整饬和儒家文化的熏染,及至东汉,尽管与之相连的“嫁取之夕,男女无别”被保留下来并衍变成后来的“闹新房”习俗(124),而“以妇侍宿”的风习则一去不复返,代之以符合儒家礼制的婚姻形态。官方儒家文化的传播对燕蓟民风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但在中原文化对燕蓟文化产生积极影响的同时,由于和东北、北方异族之地交通较为方便,周边少数民族文化也对燕蓟社会文化形成了极大影响作用,这一点从两汉燕蓟地区的民习具有少数民族风习的特征得到充分的反映(125)。
点评意见:历史交通地理研究最基本的内容,是复原历史时期的交通网络结构,而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唐代以前特别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各地交通网络结构的复原,大多都还比较粗疏,并且还有许多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澄清,因此,亟待加强相关研究工作。该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全面重建燕蓟地区在秦汉时期的交通干道网络,所做梳理扎实细致,观点亦大多言之成理,为全面复原秦汉两朝的交通地理结构,做出了重要的基础工作。特别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研究秦汉时期各大区域的交通地理结构时,首先选择从燕蓟地区的对外联系通道入手,颇具学术眼光。这是因为由这一地区去往东北、正北、西北和西面,都要通过山地,地形的限制,再加上所毗邻地区民族结构的复杂性,以及中原地区东北门户的战略地位,使得对这一地区交通道路结构的研究,更具有典型意义。
点评专家:辛德勇,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注释:
①本文中的燕,即战国时的燕国,但比强盛时期燕国范围要小;蓟乃秦汉时广阳郡(国)治所蓟县。文中燕蓟大致相当于今北京地区。
②《汉书》卷51《枚乘传》。
③参见东北博物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④参见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⑤主要有王毓瑚《秦汉帝国之经济及交通地理》(《文史杂志》1943年第9、10期)、史念海《河山集》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劳榦《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国立中研院历史语言所集刊》第16本1册,1947年)、谭宗义《汉代国内陆路交通考》(香港新亚研究所1967年版)、孙毓棠《汉代的交通》(《孙毓棠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95年版)、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以及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秦汉时代的并海道》(《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2辑)等。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版)对此部分也有涉及。
⑥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⑦以下成果对秦汉燕蓟交通也有探讨:侯仁之《历史上的北京城》(中国青年出版社1962年版)、河北省交通厅公路史志编写委员会等《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1985年内印本)、山西省交通厅公路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山西公路交通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北京市公路交通史编委会《北京交通史》(北京出版社1989年版)、河北省交通厅运输史志编写委员会《河北公路运输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90年版)、王绵厚等《东北古代交通》(沈阳出版社1990年版)、内蒙古自治区公路交通史志编审委员会《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7年版)、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尹钧科《北京古代交通》(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侯仁之《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中国书店2001年版)。
⑧《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⑨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353页。
⑩《三国志》卷11《魏书·田畴传》。
(11)谭其骧:《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西汉时期图说”。
(12)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13、2页。
(13)《钦定热河志》卷56《建置沿革二·周秦汉》。
(14)参见《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9-10页。
(15)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2页;《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1页;《河北公路运输史》第1册,第26页。卢龙道走向,学界争论较多,参见左恩庆《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闭幕词》,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5页。
(16)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2页;《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1页。
(17)史念海:《河山集》4集,第573页。
(18)《后汉书》卷81《赵苞传》。
(19)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2页。
(20)《史记》卷110《匈奴列传》“集解”、“索隐”,《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集解”。
(21)《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20-21、31-32、41-42页;《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1-14页。
(22)《资治通鉴》卷6《秦纪一·始皇帝上》,三年。
(23)《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集解”、“索隐”;《逸周书》卷7《王会解》孔晁注。
(24)《逸周书》卷7《王会解》,孔晁注;鼎铉仝:《古音骈字续编》卷1《平韵·四支》。
(25)《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9-10、27-28、61-62页。
(26)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1《庄公三十年·山戎》。
(27)如石道全等《辽宁公路交通史》第1册(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3页)等等。
(28)《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集解”、“索隐”;《逸周书》卷7《王会解》孔晁注;《国语》卷6《齐语》韦昭注。
(29)《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颜注。
(30)《史记》卷4《周本纪》;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1《历代州域总叙上·四极》。
(31)《春秋地理考实》卷1《庄公三十年·山戎》。
(32)《水经注》卷14《濡水》。
(33)刘向著、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辨物》,中华书局1987年版。
(34)明代薛虞畿《春秋别典》卷2《鲁庄公》、彭大翼《山堂肆考》卷24《地理·见俞儿》均云齐桓公是渡河而“斩孤竹”。
(35)贾敬颜《东北古代民族古代地理丛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36)《钦定热河志》卷56《建置沿革二·周秦汉》。
(37)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北京历史纪年》,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38)《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辽宁省朝阳地区古代入中原道路考》,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3、45页;《辽宁公路交通史》第1册,第3页。
(39)《读史方舆纪要》卷17《北直八·永平府》。
(40)《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3页;《辽宁公路交通史》第1册,第3-4页。
(41)史念海:《河山集》4集,第573、594页。
(42)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秦汉交通史稿》,第31页。
(43)《史记》卷115《朝鲜列传》;《河山集》4集,第573、594页。
(44)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4页;《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闭幕词》、《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5、12页。
(45)或云傍海道路线是:经蓟县、玉田、丰润、卢龙,出榆关,由绥中而溯六股河,经建昌、喀左而达朝阳,再经义县过辽河,至辽阳(《辽西通往中原古道交通之考察》,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87-88页)。
(46)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2、5页;《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闭幕词》,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5页。
(47)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353页;尹钧科:《北京古代交通》,第5页。
(48)侯仁之:《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历史地理》第2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9)《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下》及颜师古注、《后汉书·郡国志五》;《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17-18、27-28、61-62页。
(50)《史记》卷11《孝景本纪》、卷108《韩长孺列传》、卷110《匈奴列传》,《汉书》卷6《武帝纪》,《后汉书》卷4《殇帝纪》、卷5《安帝纪》、卷6《顺帝纪》、卷85《东夷传》、卷89《南匈奴列传》、卷90《乌桓鲜卑列传》。
(51)《史记》卷110《匈奴列传》,《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卷48《应劭传》、卷73《刘虞传》。
(52)《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李贤注。
(53)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394页。
(54)《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河北公路运输史》第1册,第26页。
(55)参见《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第29页。
(56)《太平寰宇记》卷49《河东道十》。
(57)《关于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的报告》、《辽宁省朝阳地区古代入中原道路考》,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13-14、45-50页;《东北古代交通》,第163页;《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第18页。另有两种说法,参见《河北公路运输史》第1册,第26页;李廷俭《从两座古桥和出土文物看凌源古代交通和道路发展情况》,载《华北通往东北古代道路考察暨学术讨论会会刊》,第93页。
(58)史念海:《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1年第1辑。
(59)辛德勇:《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第2-3页。
(60)李文信:《西汉右北平郡治平刚考》,《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成立大会会刊》,1981年;《辽宁省朝阳地区古代入中原道路考》;《北京交通史》,第31页;《东北古代交通》,第24、181-183页。
(61)《中国历史地图集》第1册,第37-38页;第2册,第9-10页。
(62)史念海:《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
(63)史念海:《河山集》4集,第594页。
(64)《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
(65)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30页。
(66)《汉书》卷51《贾山传》。
(67)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
(68)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14页;《山西公路交通史》第1册,第11页;《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第21页。
(69)《内蒙古古代道路交通史》,第22页。
(70)《山西公路交通史》第1册,第11页。
(71)史念海:《河山集》4集,第594页。
(72)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31页。
(73)史念海:《河山集》4集,第540页;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秦汉交通史稿》,第29页。
(74)《后汉书》卷90《乌桓鲜卑列传》。
(75)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
(76)《三国志》卷11《魏书·田畴传》;《资治通鉴》卷60《汉纪五十二·孝献皇帝乙》,初平四年。
(77)王文楚:《飞狐道的历史变迁》,《古代交通地理丛考》。
(78)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255页。
(79)《中国历史地图集》第2册,第61-62页。
(80)郦道元《水经注·漯水》:“苏林据郦公之说,言在上党,……如淳言在代”,疑裴引“上党壶关”实为三国魏苏林语。
(81)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卷7《名臣议论考·郦食其画取楚之策》;《资治通鉴》卷10《汉纪二·太祖高皇帝上之下》胡注,三年。
(82)《资治通鉴》卷10《汉纪二·太祖高皇帝上之下》胡注,三年。
(83)《大清一统志》卷25《宣化府二·关隘》。
(84)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第3册,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2页。
(85)《资治通鉴》卷110《晋纪三十二·安皇帝乙》,隆安二年。
(86)《骈字类编》卷36《山水门一·山》。
(87)韩拙:《山水纯全集·论山》。
(88)李贤等:《明一统志》卷21《大同府》;《大清一统志》卷24《宣化府》。
(89)《河北公路运输史》第1册,第26页。
(90)《资治通鉴》卷43《汉纪三十五·世祖光武皇帝中之下》胡注,十二年。
(91)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256、257页。
(92)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256-257页。
(93)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第256-257页。
(94)侯仁之:《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353页;《北京古代交通》,第4页;《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第19页;《秦汉交通史稿》,第28页。
(95)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353页;《北京城:历史发展的特点及其改造》;《北京城的起源与变迁》,第19页。
(96)史念海:《河山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80页。
(97)史念海:《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
(98)主要如劳幹《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林剑鸣等《秦汉社会文明》(西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孙健《北京古代经济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林甘泉《中国经济通史·秦汉经济卷》(下)(经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等。
(99)《河山集》4集,第580、538、594、545、579-589页。
(100)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356页;《北京古代交通》,第9页。
(101)侯仁之:《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354页。
(102)《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卷34《燕召公世家》。
(103)《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4《周》。
(104)雍正《山东通志》卷9《古迹志》。
(105)《史记》卷34《燕召公世家》、卷80《乐毅列传》,《战国策》卷13《齐策六》。
(106)《资治通鉴》卷4《周纪四·赧王中》,三十一年。
(107)史念海:《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
(108)《河北公路运输史》第1册,第26页。
(109)史念海:《河山集》4集,第594页。
(110)《汉书》卷72《贡禹传》、卷9《元帝纪》颜师古注。
(111)《史记》卷52《齐悼惠王世家》。
(112)参见王子今《秦汉交通史稿》,第31页。
(113)王子今:《秦汉时代的并海道》。
(114)史念海:《河山集》4集,第594页。
(115)渔阳所辖路县,王莽时改为“通路亭”,“可能即因地当交通干道交会点而得名”(《秦汉交通史稿》,第301页)。
(116)参见王子今《〈九章算术〉汉代交通史料研究》,《南都学坛》1994年第2期;《秦汉区域文化研究》,第141页;《论汉代之陆运与水运》;郭沫若《“乌还哺目”石刻的补充解释》,《考古》1965年第4期。
(117)王子今:《秦汉都市交通考论》,《文史》第42辑,中华书局1997年版。
(118)《盐铁论·力耕》、《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19)孙毓棠:《汉代的交通》、《秦汉都市交通考论》。
(120)史念海:《战国时期的交通道路》。
(121)《艺文类聚》卷6引杨雄《冀州箴》。
(122)王子今:《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
(123)《孙毓棠学术论文集》,第367页。
(124)卢云:《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61—262页。
(125)陈业新:《两汉时期幽燕地区社会风习探微》,《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4期。
标签:卢龙论文; 史记·秦始皇本纪论文; 东北历史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历史论文; 汉朝论文; 地理论文; 秦汉时期论文; 武帝论文; 热河志论文; 秦朝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