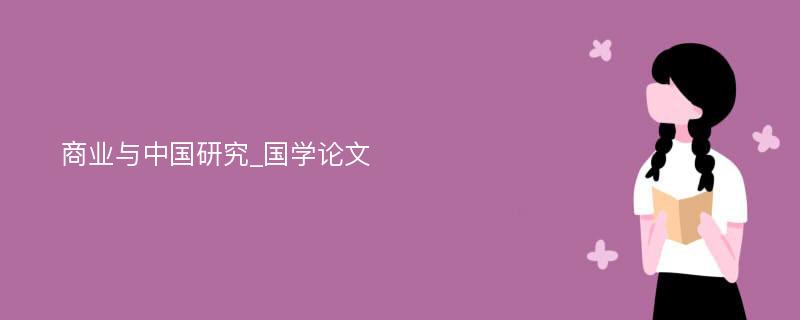
商业与国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学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突然间,很多跟国学有关的学院、学堂、俱乐部以及形形色色的国学培训班涌现出来,尽管它们出身各异,但几乎都热衷于为同一个目标群体服务——企业中高层管理者。
伴随着这一特殊群体的介入,以往在国学传承中一些不曾遇到的问题一下子成了人们争议的焦点,比如国学是否可以商业化?企业能否成为传承国学的基地?国学怎样和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传统文化是否能推动当今经济的发展?……
“其实所有争议的核心还是国学究竟该走什么道路的问题——是继续走专业化的道路还是在学术发展的同时在现实中发挥实际作用的问题。”清华大学思想研究所原所长、现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钱逊说。在他看来,近代以来,国学一直在走学术化的道路,已经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了,如何使之走向民间,走向生活,与市场融合,才是国学重焕生命力的关键,至于与商业相结合是否合适,则是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
国学传承的现实困惑
“国学是必须和现实应用相结合的,否则就只能沦为文化遗产了。”针对目前一些人主张国学应该回到书斋去的观点,钱逊说。在他看来,如果如今企业有这方面的需求,国学为企业服务也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但是目前涌现出的几种探索模式,都面临不同的争议。
2005年5月成立的人大国学院第一个被推上风口浪尖。这个最初在企业界的建议下,由人大校长纪宝成力推而设置的学校院系,被称为是“学院派”的代表,它的出现最先引发了2005年有关国学方面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一直持续到真正带有商业面孔的北大乾元教室和中国国学俱乐部出现才得以减弱,辩论的焦点由先前针对人大国学院的“要不要复兴衰微的国学”倏然转移到了“能不能靠国学牟利”。
“我们就是要看看靠国学能不能谋生。”在北京立水桥附近的一栋别墅里,中国国学俱乐部的创始人之一王正伦对记者说,他并不回避从中获利的问题,“我们坚信有价值的东西必定有价格。我们打动投资人或者说我们成立俱乐部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了实现从价值到价格转换的途径——这就是我们的商业模式。”这个筹备一年,初期融资2000万,在2005年11月份成立的俱乐部,这栋别墅就是其办公地点。
这样的办公设施对租住在北京大学西门外承泽园两间平房里的逄飞来说完全是一种奢望,他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创建的公益性民间团体——北大一耽学堂,是在这场争议中惟一没有受到公众商业化质疑,并且还一直受到各方人士褒扬的机构。但因他拒绝了很多商业目的很强的企业赞助,使得这个公益性团体从2001年元旦成立以来,就一直因缺少资金支持,时时面临生存的压力,总负责人逄飞更多的时间更是只能睡在学堂的厨房里,冬天靠白菜馒头过活。
逄飞的精神在同样从北大哲学系毕业的王正伦看来虽然可敬,但他还是坚持自己先安身才能立命的观点。他认为自己找到的才是一条集职业、事业和爱好三者为一体的道路,而且可能更容易实现一些。他颇有些得意的告诉记者,为和国学的氛围相吻合,这座具有浓郁现代气息的别墅将要改装得古色古香,其中楼上作为会馆,将来供会员们读经、休息和交流用。会员则主要是来自企业中高层的管理人员。
与这种豪华配置相对应的是其昂贵的学费,这也是所有商业培训机构最受争议的关键所在。北大乾元教室为每年12次课,每次课2天,一年学费是24000,另加资料费2000。中国国学俱乐部,每期培训费9800元,每期2或3天的培训时间。其他社会培训机构每年的培训费也是2到3万不等。
对普通百姓来说,国学成了奢侈品,一些商业机构也从中赢利颇丰。对此,很多学者认为这种举动与古代圣贤教导的“正其谊不计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友渔在《新京报》上发文质疑北大乾元教室说,“从成本计算,每月上一次课无论如何不应当是这种天价学费……从办学方来说,是在谋取不合理的、惊人的利益,从交费方来说,是用大把银子博得虚名。”他对国学俱乐部的批判则是更不留情面,认为其“搞的是‘文化搭台,利润挂帅’的俗套,明显是趁国学热火而打劫。”
关于“趁火打劫”
“既然市场有不同层次的需求,就应该有不同的主体介入来满足。”王正伦说。作为俱乐部核心团队中惟一有专业背景的成员,成为了徐友渔“趁火打劫”说的接招者。
2005年11月13日,也就是在徐先生发出质疑之后不久,同样在《新京报》上,他做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在这一回合的辩论中,由于“不惮于袒露自己的铜臭味”,使人们不但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国学俱乐部,而且王正伦通过媒体传递给公众的形象也是:即使算不上惟利是图的人,恐怕至少也应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商人。
不过后来出现在记者面前的王正伦却很让人意外,1973年出生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纪还要轻很多,长相文气、清爽,还有点瘦弱,似乎更像一个书生,言谈间还不时提及自己被现实击碎的一个个梦想以及对未来的憧憬,并且很多都跟金钱无关。
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后,对外界有关以国学为名造势捞取名利的质疑他已很释然:“好像国学一旦和商业沾边就是错的,是歪门邪道。既然大家目前还不知道哪种方式是最好的,为什么不宽容一些,让我们来做尝试呢?如果不适合,让市场和大众来淘汰我们不就行了吗?”
“国学可不可以商业化,哪部分可以商业化,有价值的部分如何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并且这件事具体由谁来做的问题。”王正伦总结说。在他看来,无论是针对人大国学院要不要复兴国学的争议还是针对自己和北大乾元教室谋取利益的质疑,以上这几个问题才是这场争论的实质所在。
并且在他看来,自己同北大一耽学堂没什么本质区别,做的都是为传播国学添砖加瓦的事情。但仍让他耿耿于怀的是现在一些学者还是拿清华国学院、一耽学堂来比较,“尤其是清华国学院,几乎成了复兴国学的一个标杆,学者们总是拿它来丈量我们,似乎只有那种复兴方式才是最正确的。”
王正伦所说的清华国学院兴起于1925年,停办于1929年,成为了近代众多国学复兴中至今仍被人们记住的不多的国学院之一。对清华国学院如今仍被记住的真正原因,钱逊认为是,“清华国学院当时采用了中西结合的研究方式,留下了大笔不可磨灭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国学研究院开办的四年中,毕业生共四届计70人,绝大多数后来成为知名学者,在文、史、哲等学科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
教企业家学什么
“我们常常在议论,过去儒学的传承是通过私塾、书院和家族祠堂等等,佛教的传承是通过寺庙,现在佛教的寺庙依旧,而儒学赖以传承的那些社会体制已不存在了,那么,现在儒学的传承靠什么?”
“要靠企业,企业应该成为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基地。”在国际儒联和北京中圣国脉管理咨询公司联合成立的“企业国学堂”开学典礼,钱逊应邀前往,针对企业在复兴国学中的地位问题,他在致辞中这样说道。
对于这个观点,在后来的采访中,他又做了补充和修正,认为商业参与到国学中来,这在以前是没遇到的问题,企业传承可以算是一种尝试,效果如何还有待检验。目前为企业界管理人员办相应的培训班,使他们了解国学,正是与现代社会企业界的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分不开的。至于备受公众质疑的高收费问题,他认为这都是探索过程中的微不足道的问题,没必要纠缠在细枝末节里。“关键是在现代企业追求与传统文化提倡的东西相冲突的情况下,如何把国学和经济活动结合起来。”
至于具体传承方式,他认为目前至少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学术上比较高端的研究和传承;一种是在民间的实际应用,企业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市场来满足是无可厚非的。
关于培训学员定位于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以及产生的相应收费问题,中圣国脉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梅霖认为,人们看到的还是表象。他解释说,在中国企业现在的发展阶段,企业家在企业文化中起到决定作用,他倡导的企业文化会影响到所有的员工,甚至还会辐射到员工的家庭成员,因此让对企业文化有决定作用的高层先接受培训,使他们在企业中由上而下产生影响,更有利于国学的传播。而相对于这个阶层产生的费用也是市场能接受的。
但是对这个有丰富实际管理经验的特殊群体,学者教授给他们什么的知识,才能使他们真正学以致用呢?
对这个问题,有很多培训机构声称,他们会从国学中总结出一些管理企业的方法教给企业家。“不要指望老师能给予企业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国学的价值主要还是对管理者价值观的改变,属于启迪层面,而不是具体的方式方法,否则就是对教育的误读。”
戚聿东,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院长,MBA教育中心主任。他认为力图从国学中提炼出具体管理方法的本身就是一个误区,因为越是低层次的管理越有规则可循,最高层次的管理则是无规则的,对企业高层而言,“并不需要教给他们具体的管理方法,关键是使他们从中受到启发。”
北大乾元教室在课程设置的理念上也印证了戚的观点。其负责人冀建中说,“我们不会教给企业家任何技术层面的东西”。乾元国学教室在开设之前,就摒弃了以往哲学系在开设这种课程时,往往先将国学内容用流行的“管理理念”、“商业思想”包装起来的做法,而是让企业家们能读到纯粹的“国学”。
能否走进商学院
在人们越来越抱怨西方的管理过分强调技术,缺乏人性化、艺术化,“术”的成分过多的情况下,那么管理中以“道”见长的国学,将来能不能真正走进商学院,和西方的管理教学取长补短,形成补充呢?
“其实国学走进商学院已经算不上是什么新鲜话题了。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商学院一直就是比较重视的,尤其是企业文化课程,一直是商学院的核心课程,而且讲这种课程也一定是要讲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戚聿东说。
至于以往这种课程发挥的作用一直不尽人意的原因,他分析说,最大的局限就是讲传统文化的时候就只是限于传统文化,而没有和实际应用相结合,讲现代企业管理则单纯是讲管理,没有把古代思想融会贯通到里面去。两者的具体整合工作都交给学生自己来完成,结果就存在传统文化和企业现代管理两张皮的现象。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为了促使两者融合,后来他有意识的邀请一些企业家或者学者到学院来做“国学和企业现代管理”一类的讲座,但基本不能使他满意,“学者有很深的学术研究,但不了解企业,企业家有一线的管理经验,但国学修养又相差甚远,讲来讲去还是改变不了国学跟管理学‘两张皮’的问题。”再后来有人希望到学校来试讲的时候,他基本都谢绝了。
根据自己管理商学院的经验,戚聿东认为目前国学教育中还存在很多问题,每一个都严重影响国学的正常发展。其中最主要的是,虽然知道东西方的各有优劣,却很难做到优势互补。2005年11月15日在北大开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儒学专家陈来对主张弘扬国学和批判性反思启蒙的学者提出一个建议:应该开出两张清单,明确罗列传统思想文化中不应该赞成的东西;在此之后再来讲传统中的精华,外来文化中的糟粕,这样就会有一个正确的前提,就可以避免许多误解。
无论高等院校开设的培训班还是社会上的培训机构,课程安排其实大同小异,基本都包括《易经》、《老子》、《庄子》、《论语》、《资治通鉴》,等等,但具体授课内容却相差甚远,授课重点往往就是授课教师自己研究的领域,因此出现即使同一门课程,讲授重点也是五花八门的现象,有的认为是必须重点讲授的,有的则认为是可以一笔带过,甚至批为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