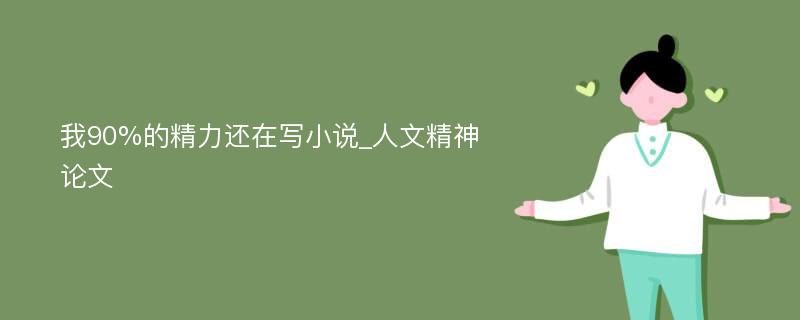
——我百分之九十的精力仍然是写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仍然是论文,精力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家自述
1995年8月22日下午,王蒙在石家庄市接受了省经济台记者的采访,采访涉及王蒙的写作是否由小说转向杂文随笔,以及对人文精神的看法等问题。
问:近些年您的杂文随笔的影响很大,您的精力是不是由小说转向了杂文随笔?
蒙:不是。最近五、六年我已发表三部长篇小说。由于大家都很忙,所以能塌下心来读长篇的人比较少。其实我百分之九十的精力仍然是写小说,主要写长篇。您所说的那些杂文一类,大多是在两部长篇之间为了休息,为了调剂而写的。
问:看来这是大家对您的一种误解。您的经历比较特殊,再加上您的智慧和才华,使您总是处在大家关注的焦点上。在去年的《读书》上看到了您写的《不成样子的怀念》,文中涉及到现代派的问题,您是不是认为中国艺术家的活动范围还不大?
蒙:不是。那篇文章提到了毕加索,他的创作方法应该说主要不是现实主义的。我想知道乔木同志对他的看法,想了解领导对毕加索这样的非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态度,看看这样的创作方法在中国存活的可能性有多大。
问:这个问题您今天有答案了吗?
蒙:我觉得我们的艺术空间处在不断开拓的过程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广阔。
问:今年的《东方》(1995-3)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对您的思想和观点作了一些分析,有肯定也有批评和反驳,对此您怎么看?
蒙: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不过有一点遗憾,刚才我说过我百分之九十的精力是写小说,但未必有人像读我二、三千字的文章那样去读我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问:您是否在暗示文艺界的人塌不下心来?
蒙:那倒也不能这么说,这不是文艺界的问题,而是整个读者的问题。大家都很忙碌是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对长篇来说,有时一时是看不出什么来的。而一篇千八百字的文章在报上一发表,看的人非常多。像上海的《新民晚报》发行量一百六、七十万,发在上面的文章很容易被大家知道。而一个长篇在情况不错的时候能印到一万多册,这无论如何不能和报纸的发行量相比。报纸的读者面大,反映也快,但它过去得也快;而一部书就比较有分量。报纸上的一些话题一年之后往往就没人知道了,忘掉了;而一部书出版后十年可能还会有人议论。
问:看来我也是受报刊的影响误以为您的精力由小说转向了杂文随笔,其实您的主要精力仍然是写小说。上海发起了人文精神的讨论,您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产生了一些争议。我读您的杂文随笔,感到您的文章也是在呼吁一种新的人文精神,是这样的吗?
蒙:问题是现在我对人文精神的定义不太清楚。现在至少有四、五种对人文精神的解释:有人强调的是“人”(我是这种看法),有人强调的是“文”,有人强调的是“人文科学”,有人强调的是“文人”,有人强调的是“精神”。实际上是各说各的,没有说到一块儿。一个年轻朋友给我来信,说人文精神就是要爱自己的母亲呀,岂可以调侃怀疑?其实,看懂我文章的人可以明白,我调侃的与其说是人文精神,不如说是那种排斥人文精神的遭遇。这是汉字的特点所造成的,因为汉字的信息量特别大,同时又很模糊。一听人文精神都觉得好得不得了,但它到底是什么却不知道。周介人同志在《文汇报》上写了一篇文章(人文精神最早是他在《上海文学》上提出来的),说上海的老作家徐中玉问他到底什么是人文精神?并说怎么越讨论人文精神我越糊涂了?所以周介人表示不得不和这个话题告别了——最初提这个问题的人现在给吓回去了。这也很有意思。
中国人很喜欢寻找一个终极的概念,比如说“道”,“朝闻道,夕死可矣。”你越研究这个道就觉得越深。比如说“仁”,“求仁得仁”,“仁者爱人”,儒家的一个“仁”字似乎把它的主要思想都概括进去了。又如“气”、“太极”,这玩艺儿你觉得太伟大了!因为你抓不着它,越抓不着就越觉得伟大,凡能抓着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又太又极,就把事物推向了顶端。这既是中国式思维的长处,也是它的短处。一方面它很灵动,很直观,很有弹性,深不见底,大可遮天;另一方面就是缺乏科学性,大而无当,模模糊糊。人文精神也是这样,从字面上看你是不能反对的,因为“人”、“文”、“人文”、“文人”、“精神”你怎么看都是很好的一些词汇,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文明与道德,它是先验正确的。它既是很美好,很终端的一个概念,又是很模糊的一个概念。一位很好的评论家,他是特别主张人文精神的,他说人文精神到底是什么?我也没有那个豪兴能提出几条来,我只知道我是在寻找,寻找的方向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觉得这很像诗了,一个朦胧诗人可以这样说——我在寻找/但我不知道在找什么/我在寻找/但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我在寻找/但我不知道为什么去找。这几句话完全可以当做诗来发表,但要是当做论文的话就令人不大满足,因为它表达的是一种直觉的内心的诉求渴望,不是论证。有人指出这种说法使“人文精神”带上了神学的意义,与科学精神相矛盾,因为科学精神要求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有明确的界定。现在显然对人文精神的讨论是各人在说各人的,争论了半天有时你觉得很奇怪,你是按你的理解说,他是按他的理解说,说的不是一回事。这是不是说人文精神这个词就不好?那倒不是,它是针对市场经济引发的物质压迫与物欲泛滥的有的放矢。只是这个矢还需要磨砺和充实。
问:您如何评价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蒙:它除了引起一场热闹之外,究竟能给我们的学术生活文艺生活带来些什么启示?还需要再看一看,现在还难以判断。
问:现在还有人在写像《青春万岁》这样的作品吗?
蒙:不知道。《青春万岁》是我最早的作品,并不是非常成熟的作品,但它是我的作品中卖得最多的,已经印了8次了。中学生比较喜欢这个作品,他们还没有完全长大,但又不满足于儿童文学作品了。
问:这也反映着年轻人特有的单纯和在精神上的追求,而现在这样的书已不多见,文学作品到底应把读者引向哪里?您能谈谈这个问题吗?
蒙:原则上说文学作品当然应该有助于提高人们,包括年轻人的精神品位,但这不是一个简单化的过程。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文学要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还有一个是生活要把文学引导到哪里去?历史要把文学引导到哪里去?因为生活毕竟比文学更强。中国正处在一个转变的时期,面临着许多新问题,但不管怎么样,由于有了文学,使我们的年轻人能在精神上得到更多的色彩,更多的体验和营养,这是无可怀疑的。
问:这涉及到读者、书、作者及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您有没有一个标准,达到这样一个标准就可以使这些方面良性互动?
蒙:我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我们希望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越来越丰富。生活的质量也应包括精神生活的质量。如果你让我说得更具体就很困难。我们必须承认价值标准并不是单一的,比如一个篮球运动员就是迷着打球,而他对看小说没有什么兴趣,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嘲笑和责备他。他把他的才华、能力、情感都投入到了体育运动中,他在体育中享受到的快乐与一个诗人在诗中享受到的快乐在精神的世界里没有高下的区别,你不能说诗人的快乐是伟大的、高级的,而运动员就是不高级的,不能这么说。如果能把篮球打到出神入化的程度,那确实是一种很高级的精神享受,观看也是一种享受。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一本成功的书发行到几十万、上百万册,它的影响和作用也是有限的。
问:也就是说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起主要作用?
蒙:是的。文学在社会生活中不可能占主要位置,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占主要位置的必然是生产活动、经济活动,教育的覆盖面也比文学大得多。现在青年在文化生活中的选择也多样化了,有人喜欢读诗歌、小说,这我当然高兴,如果谁也不读我就失业了;有人喜欢钻研电脑;有人喜欢钻研各种不同的艺术,如弹琴、跳舞、画画、写字等等;也有人热心社会活动、公关活动。我们不能随便谴责别人没有文化没有人文精神,只有抱着本诗集才算有人文精神,这是自己糊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