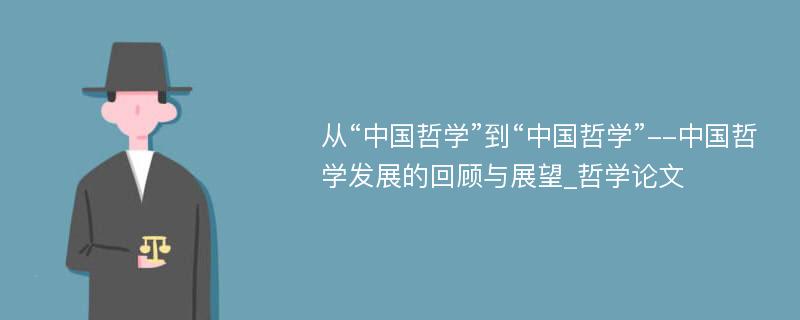
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中国哲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展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哲学论文,发展历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55-07
从20世纪初以迄于今,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已经历了百年的风风雨雨。在世纪之初的今天,重新反省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产生和发展的历程并对其未来的走势作出展望,对于面向21世纪更好地加强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更为充分地体现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特质,无疑是有益的。本文拟就此问题略陈管见,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出现了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不仅有论者提出了“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有论者进而认为中国哲学存在着“合法性危机”。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其产生和发展从始至终为西方哲学所笼罩,因此它只能被看作是“哲学在中国”,而不能成为“中国的哲学”。这场讨论关涉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对面向21世纪重新反省作为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如何在挺立民族文化精神主体性的基础上,建构更能充分体现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中国哲学,确乎具有积极意义。但是,讨论中出现了过分渲染所谓的“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对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已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注重不够的偏向,则是我不能同意的。本文将以胡适、冯友兰、牟宗三、成中英为代表,对不同时代中国哲学家的相关理论努力作进一步的梳理,以求对中国哲学在20世纪的整体理论进路予以更完整的把握。在我看来,如果用一句话概括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产生、发展的历程,那就是:从“哲学在中国”到“中国的哲学”。
作为中国哲学学科的实际开创者,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这部“具有划时代意义”① 之著作的问世,可看作是中国哲学这一现代学科确立的重要标志之一。概要而言,该书有两方面的基本特点:其一,由于胡著是在“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② 的情状下,按照西方哲学的价值系统、观念框架、问题意识乃至话语系统编织而成的,“以西释中”由此成为胡适书写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范式。其二,尽管胡著最大的弱点是没有能够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质,但其中却确实又包含了将中国哲学看作世界哲学主流之一的理论涵义。他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一起,称作是分别代表了东西方哲学传统可能通过相互接触、相互影响而“发生一种世界的哲学”的“两大支”③。由此,胡著从问世之日起就具有颇为复杂的含义:一方面,它标志着中国哲学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另一方面,由于它自觉地以源起于西方的哲学观念框架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相关内容予以取舍、梳理与诠释,也就必然包含了肢解、扭曲中国传统的“天人之学”、甚至使之面目全非的理论可能性。由此,胡适的有关工作对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演进而言,就成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成为了中国哲学确立的逻辑起点;另一方面,它开启了按西方哲学来形塑中国哲学的先河。
胡适开启的事业,在冯友兰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展。与胡适相比,冯友兰的哲学观与哲学史观不仅具有更强、更系统的理论形态,而且他对按照西方哲学的范型来建构中国哲学亦具有鲜明的自觉。在他看来,“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④。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在按照西方的理论形态“哲学”地建立中国哲学这一点上,冯友兰的确比胡适更具有理论的彻底性。但是,另一方面,冯友兰确实又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中国哲学独异的民族性特质。这在其“新理学”的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均有明确表现:在思想形式上,不仅构成新理学哲学体系基本范畴的理、气、道体、大全等概念均是源自中国哲学,而且只有在中国哲学传统中才得到充分发展的“负的方法”,在他的哲学方法论上得到了充分的凸显。在冯友兰看来,“一个完全的形上学系统,应当始于正的方法,而终于负的方法。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最后顶点”⑤。在思想内容上,冯友兰十分注重作为中国哲学区别于西方哲学之重要理论特质的“境界说”。在长达半个多世纪而又不断变异的哲学活动中,正是“境界说”构成了冯友兰哲学思想中最为稳定的内容。直至晚年,他还明确自认,“‘境界说’是新理学的中心思想”⑥。可见,冯友兰虽然自觉地以西方哲学为建构“中国哲学”的范型,但在哲学之为哲学的理论指归上,他却又是归宗于中国哲学之基本精神的。
这样,冯友兰有关努力的理论意义,就表现为表面看来南辕北辙的这两个方面。而在相当程度上,恰恰是这种相反而相成的奇妙吊诡,从两个不同的向度共同推进了确立中国哲学学科的工作。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是在“西方中心论”盛行的时代背景下、以西方哲学为样本建立起来的。这就使得它自建立之日起就处在左冲右突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中国哲学不能不师法西方哲学,否则就无从立足;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要想真正在学理上得以确立,又必须与西方哲学保持必要的张力,通过凸显自身的独特理论价值,来最终获得作为一种哲学形态而得以成立的“自性”。在一定意义上,冯友兰上述两方面似乎相互矛盾的努力,恰恰正适应了处于特殊境遇中的中国哲学的特殊的两重需要:一方面,更彻底地效仿西方哲学,使其整体学科框架得以体现更为完整、系统而深入的哲学素养;另一方面,对中国哲学理论特质的凸显,又使中国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身“哲学的”自性。借用金岳霖的话说,这一方面是以“哲学在中国”的方式确立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特定内容与哲学的正向联系,从而保证了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普遍性(亦即作为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又是在一定程度上以“中国的哲学”的方式凸显了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从而体现了中国哲学作为“中国的哲学”的特殊性。这显然是为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胡、冯等人之后,学界继续推进着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在这方面,牟宗三的相关工作颇具代表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牟宗三以颇具系统的理论形态,论说哲学的普遍性与具体哲学形态的特殊性及其关系问题,表现出了面向人类民族文化之林以确立“中国的哲学”的更为明确而深入的理论自觉。
牟宗三首先从“文化构成”的视角,肯认了中国哲学的存在。在他看来,“文化之范围太大,可以从各角度、各方面来看,但向内收缩到最核心的地方,当该是哲学。哲学可以做庞大的文化这一个综合体的中心领导观念”⑦。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呢?牟宗三的回答是:“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⑧ 在论证了中国有哲学后,围绕中国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牟宗三提出了颇具理论特色的“通孔说”。在他看来,中西哲学之所以具有自身的特殊性,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提出都是关联于作为有限存在的人,而作为有限存在的人(不论是个体还是民族),都不可能不受到“感性的存在形态”与“外部的存在环境”等内外两方面的限制,而“在限制中表现就是在一通孔中表现,所谓一孔之见。也就是《庄子·天下》所说的“‘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由于人各得一察焉以自好,于是“‘道术将为天下裂’”⑨。由于“道就在一个通孔上显现,并没有全体表现出来”⑩,以追求普遍性为宗旨的哲学之所以出现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等特殊形态,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有如冯友兰,牟宗三也十分关注中国哲学作为“中国”之“哲学”的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与新儒家“民族本位”的基本理论立场相关联,虽然牟宗三明确承认各民族哲学通过“通孔”所表现的特殊性是关联于普遍性的,但其理论落脚点则在论说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弘扬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构成了其整个哲学活动的中心意旨。显然,在胡、冯等较为彻底地引进西方哲学的学科框架、以初步确立中国哲学作为“哲学”的普遍性之后,如何在此基础上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特质,就成为进一步确立中国哲学学科的内在要求。在这个意义上,牟宗三着力于论说中国哲学之特殊性,与此前胡、冯更为注重凸显中国哲学之普遍性,堪称构成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整体过程中具有相互承接关系的两个必要环节。
与同为确立中国哲学学科重要代表人物的胡适、冯友兰相比,正是在牟宗三这里,中国哲学的书写方式发生了一个翻转:不再是如何更为彻底地接纳西方,而是如何更为充分地体现中国哲学自身的精神特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凸显中国哲学自身的学理特质是冯友兰与牟宗三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两者仍有一个基本差别:在冯友兰那里,凸显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质是服从于把中国哲学纳入以西方哲学为范型的“哲学”之普遍性框架这一更为根本的目的;对牟宗三而言,其整个理论活动的基本出发点与归属,恰恰是要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比,来反衬中国哲学之特殊性。从这个视角,可以把牟宗三终其一生的基本理论活动归结为三大方面:其一,在中西哲学对比反省的整体背景下,通过对中国哲学的系统梳理而揭示其自身的理论特质;其二,立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认识,哲学地揭示中国哲学何以具有这些理论特质;其三,在此基础上,力图会通中西哲学传统而达成在根本精神归趋上皈依于中国哲学的“新的综合”。迄今为止,牟宗三的有关工作已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于有人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也就关涉到如何消化牟先生的论著,如何超越牟先生理路的艰巨任务。”(11)
但是,牟宗三的有关理论亦有其内在限制。其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他在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中,走向了“华夏中心论”。这在他对中西方哲学的基本分判中可以清楚见出。在牟宗三看来,哲学本当是“生命的学问”,其基本使命是通过内省反求,以心、性、天相贯通的理路,来为人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托。由此,牟宗三认为,只有以儒家哲学为正宗的中国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而西方哲学则因为囿于向外在对象追寻的传统,归根结底只能是“见物而不见人”的“不透之论”。立足于这样的观念,牟宗三给西方哲学的未来走向下了这样的断语:“我看西方哲学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所成就的理想主义的大传统,最后的圆熟归宿是向中国的‘生命之学问’走,不管它如何摇摆动荡,最后向这里投注。”(12) 不难看出,牟宗三显然是以中国哲学的某些价值取向为基本标准,来论衡西方哲学。由于牟宗三表现出了过于亢进的民族意识和深层文化心态上的“华夏优位论”,因而其有关理论活动固然较为充分地凸显了中国哲学的精神特质特别是优长之处,但却很难被认为是持平之论,难免具有相当程度的独断色彩。这就不能不对确立中国哲学学科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一代中国哲学家逐渐登上了学坛,并在前辈有关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了中国哲学的学科建设。限于篇幅,这里仅以成中英的有关理论创获为例证,对这方面的新进路作一揭示。成中英的有关理论努力对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主要作了两方面的推进,从而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达到了将中西哲学作为人类哲学两个平等分支的理论定位。
第一,成中英揭示了中西哲学传统同为人类哲学之“殊相”的具体内涵。如前所述,前此的有关认识大体可归于两种基本立场:一种是从肯认西方哲学的优位性出发,为凸显中国哲学的普遍性,以西方哲学为范型来比附和论说中国哲学何以是哲学,由此呈现的中国哲学,要么是不具备充分的哲学特质因而是残缺的,要么是处在哲学的初步形态因而是肤浅的。这样,所谓的中国哲学就只能被看作是西方哲学的附庸。另一种则是从凸显中国哲学的特质出发,最终走入了“华夏中心论”,从而得出“只有中国哲学才是真正的哲学”的结论。这两者显然都很难被看作是持平之论。
成中英则表现出了不同的理论态度。在他看来:
哲学应该是自生命的肯定,产生生命的价值与知识,再进而对知识的反省来探讨价值,从价值的反省来寻绎知识,并从两者交互的反省中来彼此充实与重建。借此产生的一套价值哲学与知识哲学,以及衍生的文化哲学与人生哲学,才能提供人类以生命的智慧。(13)
这也就是说,哲学是关于生命的智慧,而知识与价值构成了这一“生命的智慧”的两个方面的基本要素。在他看来,中西哲学传统正好分别表现为价值哲学与知识哲学,代表了人类哲学的两种基本形态:“知识的灿烂蔚成西方哲学”(14);中国哲学则“本质上是价值哲学,是对于宇宙价值、人生价值、社会价值深沉的肯定与体验”(15)。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分化,在其根源性上是由于知识化与价值化的过程各具有动力。知识化的动源在理性,价值化的动源则在意志。虽然只有它们的共同作用才形成生命的整体存在,但它们之间相对的差异性与独立性,又为两者在生命过程中的偏倚提供了可能。不论是个人的生命存在,还是不同民族的文化慧命,“偏于知而失于志者,有之;偏于志而失于知者,亦有之;显于知而隐于志者,有之;隐于知而显于志者,亦有之”(16)。中西哲学传统的差异,正表现为偏失隐显的不同。但是,哲学活动立足于价值与知识之间的动态进程以及价值和知识之间的动态结构,由此,价值与知识应当不断走向新的和谐与平衡。这也就为中西哲学间展开良性互动揭明了现实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依以上的了解,中国哲学的问题与西方哲学的问题恰恰相反:西方哲学的问题是如何在知识宇宙中安排价值;中国哲学的问题则是如何在价值宇宙中建立知识,如何认清知识的重要。”(17) 他进一步论述道:
中国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对知的分析不精而引起的,正如西方哲学的许多问题都是因为对志的掌握不切而引起的一样。这种差异不但见之于个人行为、社会制度、价值规范,而且也造成中西文化传统历史性的对比。若能明白人类的知与志的内在统一性以及原始统一性,那么就必定能突破后天限制,追溯内在的知与志交融互用的原始点,并能导向知与志相互批评,以达到相互补足、相互彰显的理想圆融境地。这就是中西哲学发展的方向,亦为人类走向未来世界、以世界性融合历史性的必然趋势。这将是哲学理性内在的必然发展。(18)
尽管上述论述的具体内容不无可以讨论之处,但成中英的确突破了此前中国哲学家在中西哲学传统之间左冲右突的困局,给出了一个有一定理论系统与理论深度、等观中西哲学传统的理解框架。这对于更为确当地确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显然有积极意义。
第二,成中英具体揭明了中西哲学传统关联于人性本质的内在根据。他把哲学看作是关于人之生命的学问,而生命存在又包含了意志与理性两大层面:“综言之,人的存在可区分两个层面:一面是理性,一面是意志。”(19) 就两者的关系而言,理性与意志一如知识与价值,亦是相辅相成的:“理性与意志在生命的本质上不应相反相抵,而应相辅相成;理性与意志应有其相对的、内在的独立性,但也应有其内在的、整体的相对性。换言之,理性是意志的理性,意志是理性的意志,这是肯定生命的整体的内涵。”(20) 两者在生命发展过程中亦体现为一种动态的平衡。理性与意志在本体上所具有的内在和谐性,为人类文化与社会对知识与价值平衡与和谐的追求,奠定了形上基础。这其中,自然也就包含了分别表现为价值哲学与知识哲学的中西哲学传统走向平等对话与融会的理论必然性。
自中国哲学学科草创以来,虽然中国哲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肯认人生哲学是中国哲学独擅胜场的地方,但在人性本质的层面,为中国哲学确立形上根据的工作却一直没有完成。牟宗三等前辈新儒家虽然事实上是力图从人性本质的层面来论说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但由于他们往往把人的本质仅仅归结为“内在道德性”,因而难免陷入“华夏中心论”。他们在为中国哲学确立内在基础的同时,亦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去除了西方哲学在人性本质层面的内在根据,因而可以说事实上是要取消西方哲学存在的合法性。成中英则以具有一定理论说服力的观念框架,同时为中西哲学传统确立了内在于人性本质的形上根据,并进而揭示了两者走向平等对话与融合会通的理论必然性,从而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达到了将中西哲学传统作为人类哲学之两个平等分支的理论定位。
因此,我认为,尽管在起步之初,中国哲学学科不能不以西方哲学作为基本的哲学范型,时至今日也依然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的问题,但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它不仅已初步确立了学科框架结构,逐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而且在精神理念的层面,达到了将中西哲学传统作为人类哲学之两个平等的分支的理论定位。换言之,尽管在一定的意义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确立是以“哲学在中国”为逻辑起点的,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又是逐渐向着“中国的哲学”生成的。经过百年来的发展,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展示了一种不尽同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的哲学形态。西方哲学的主流传统是一种以客观认知自然与社会等外在对象为指归、以求“真”务“实”为目标的知识系统,人生问题在其中并不占主导地位。而正如有论者已注意到的,中国现代学界对哲学的基本理解,则是“把哲学当作一种人生的智慧,并认为这种智慧的根本意义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人生的烦恼,解除人生的痛苦,找到人生的归宿”(21)。以人生问题特别是生命意义的安顿问题为中心来展开学理系统,构成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存在形态。这种哲学系统与西方哲学主流传统之间显然有着相当的差异。因此,在比较文化的视野中,中国哲学的出现,可以说是在西方以知识论为中心的主流哲学传统之外,确立了一个新的哲学形态。
当然,我并不认为,经过百年来的努力,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已是完美无缺的。由于特定时代条件的限制,以往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论衡中国哲学的基本价值尺度源自西方,而非内在于中国哲学自身。在20世纪中国哲学中影响广泛的“以西释中”的理论范式,就是这种状况的一个明显表征。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中国哲学,毋宁说时至今日依然还是走在朝向“中国的哲学”的途中。为了更合理地推进自身的学科建设,面向未来的中国哲学必须根本改变迄今为止在相当程度上依然将西方哲学等同于人类哲学之共相的状况:一方面,还西方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本来面目,另一方面,通过深入而系统地开掘中国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智慧精神,以进一步丰富哲学的内涵,不仅凸显并涵容中西哲学之基本智慧精神、作为人类哲学之共相的哲学特质,而且在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上,确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平等齐一的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地位。换言之,使中国哲学成为在人类哲学之共相统领之下,而非依附于西方哲学的人类哲学的殊相之一,并最终在中国哲学与哲学之间达成殊相与共相的联结。为达此目标,中西哲学之间应当达成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以下对此略加论述。
世纪之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之所以再次引起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是与中国哲学一直存在着的“身份认同”之焦虑密切相关的。一方面,虽然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堪称无所不在,但中国哲学不仅事实上从来就不完全是“哲学(实际上是西方哲学)在中国”,而且越来越不安于主要以“哲学在中国”的形态存在;另一方面,中国哲学虽然一直是向着“中国的哲学”生成的,但却又没有能够充分地体现出自身的基本理论特质,因而也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的哲学”。正是有见于中国哲学的这一两难困境,认为“按照西方哲学来塑造中国哲学是中国哲学永远难以摆脱的宿命者”有之;力图完全消除西方哲学乃至西方现代学术的影响,按照中国传统学术的“本来”面目来重新书写中国学术思想传统者亦有之。
在我看来,这两种主张都不具有理论的可能性与现实的可能性。哲学诠释学已揭明,作为人类基本存在方式之一的理解活动,均是带着特定的“先见”或“前理解”,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理解者浸淫于其中的文化传统,构成了“前理解”的主体内容。理解是一个“视界融合”,即理解者立足于先在的“前理解”而形成的视野,与理解对象在向理解者打开自己的过程中所呈现的视野相互融合,以形成新的意义世界的过程。因此,在两个各自具有独异精神特质与深厚理论积淀的伟大文化传统之间所进行的理解活动,所形成的意义世界不可能只反映其中某一文化传统的精神特质,而只能是多多少少同时带有两者思想印记的“共在”。而在全球化时代,恰恰是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哲学”地思考世界与人生的先在的存在背景或曰“理解起点”。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的哲学之思不仅无法逃遁于中国文化传统,而且亦无法游离于西方哲学的影响之外。
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我认为,只有首先同时“进入”到中西文化与哲学传统之中,在中西哲学之间达成互诠互释、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中国哲学才能逐渐走出两难困境,最终确立自身的合法性。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哲学的确立过程本身就证明了这一点。以西方哲学为基本的范型来诠释中国文化以建立中国哲学,堪称是确立中国哲学不可规避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舍此,中国文化传统中并没有以一个独立的学科存在过的中国哲学就无从出现。但是,由于人之理解活动的具体性与历史性,即使是在这个“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交会处,也并不仅仅只存在以西方哲学诠释中国文化的单向度的关系,而是实际上就已在西方哲学与作为等待着被确立的中国哲学之资源背景的中国文化之间,构成了一个双向回流的“诠释圆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国人理解源自西方哲学不可规避的“先见”,在中国文化中出现的“哲学”,也就必定会或多或少带有中国文化自身的印记,因而体现出与西方哲学的差异。正是由于诠释过程所包含的“误读”的内在必然性,即使是力图完全按照西方哲学的标准来确立中国哲学,中国哲学也必然不可能完完全全地成为西方哲学的复制品,而是或多或少总要出现不同于西方哲学、而与自身文化传统具有正向联系的内容。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学术中的“哲学”不尽同于西方式哲学、而与中国文化自身的传统间保持某种内在一致性的根本原因。
由于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各自依托于不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其间的差别不可避免地会在各自的哲学系统中表现出来,并最终较为充分地体现为在各自思想文化背景基本精神特质的两种哲学系统间,呈现出相当的张力。因此,中国哲学学科不断得到确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中西哲学系统之间的差异逐渐得到更为充分凸显的过程。而同处在“哲学”这一精神理念之共性之中的两大哲学系统之间的差异互见,又正好为它们之间进一步展开对话与批评提供了现实可能性。这样,就学理系统的建立本身而言,中国哲学不断成长的过程,同时也就是一个不断以西方哲学来诠释、批评中国文化的过程。而与此同时,则是中国哲学逐渐具备了对西方哲学展开反批评的潜在可能性,从而不断推进中西哲学进入一个真正可以相互展开对话的更高发展阶段。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哲学家已经亲身参与西方哲学与文化的发展进程之中,就是这一历史进程的明证。
进而言之,与西方哲学不断展开互诠互释、并达成在人类哲学理念统领之下的“诠释圆环”,不仅是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之道,而且也是中国哲学面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之道。在今天,我们固然不能安于使中国哲学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但试图彻底割断与西方哲学的关联、确立“纯之又纯”的中国哲学,也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只有在更高的理论基点上,不断达成从中国哲学到西方哲学、再从西方哲学到中国哲学的“诠释圆环”,我们才有可能逐步做到既更为充分地体现中国哲学的自身特质,又不断推进中国哲学融入人类哲学的智慧长河之中,在破除将西方哲学视为普遍哲学之观念的基础上,通过差异互见的多元民族哲学的交流与融会,逐渐凸显出“哲学”所具有的一般共性。
回顾中国哲学学科的确立过程,应当说,在取得了相当理论成就的同时,亦存在着内在的问题。与“以西释中”范式的广泛影响直接相关,其中最根本的限制,就在于中国哲学虽或多或少具有了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色,但体现自身的“自性”仍不充分。这一问题的出现自有内因与外缘多方面的原因,但中国哲学的确立主要是在“西方中心论”的观念框架下进行的,因而自身的主体性意识挺立不够,恐怕是其中最基本的缘由。在我看来,在前此的中国哲学确立过程中,中国哲学的理论特色之所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固然与几代中国哲学家的自觉意识有一定程度的关联,但更为基本的,应当归因于前述理解活动的本性,即理解过程所包含的“误读”的内在必然性。就整体而言,前此中国哲学工作者的民族主体意识之豁显应当说是不够的。面向未来,中国哲学要成为一种既在理论形态上达到人类哲学之一般的高度、而又充分体现中国气派与中国文化之精神特质的学理系统,就必须在真正走出“西方中心论”并保持开放的文化心态的前提下,切实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意识,使之充分体现中国哲学之自性,不再以“自在”的形态而潜存,而是在明确的理论自觉中,成为“自为”的要求,在充分成就中国哲学之自性的自觉意识中,推进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所达成的“诠释圆环”在既相互批评又相互借鉴的互诠互释、互补互生之中,不断升进到更高、更深层次,既促使中国哲学更趋成熟,又通过将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融入当代人类文化之中,为人类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新的精神资源,从而推动人类哲学的一般共性不断得到进一步凸显。中国哲学的出现,打破了在西方哲学一统天下基本背景之下事实上存在着的一元哲学观,改变了前此人们只是停留在以西方哲学为范型来理解哲学的理论视野,不仅在广度上扩大了“哲学”的外延,而且亦在深度上丰富了“哲学”的内涵,开启了在多元哲学观的视野下,进一步思考宇宙、社会与人生问题的理论可能性。今天,以西方为主导的人类文化,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亦面临着深刻的问题乃至危机。作为具有自身特质之智慧形态的中国哲学,加入到人类哲学多元开展的大潮之中,应当能够对人类面向未来保持更为清明、理性与健康的思考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伴随着中西哲学之间互诠互释、互补互生之“诠释圆环”的不断升进,伴随着中国哲学与“哲学”之间殊相与共相联结的逐渐达成,中国哲学必将最终走出两难境地。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必将能够更为充分地融入人类思想文化之中,并作用于当代人类的社会与人生。中国哲学作为人类哲学“殊相”之一的历史地位,必将在人类哲学多元开展的现实中得到肯定。
注释:
①冯友兰:《三松堂自序》,第215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②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蔡元培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③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4页。
④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卷,第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
⑤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95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⑥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第22页,开封,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
⑦牟宗三:《中西哲学会通之十四讲》,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⑧(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第3—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⑨⑩牟宗三:《中国哲学十九讲》,第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11)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225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6。
(13)(15)(16)(17)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237、230、364、232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
(14)(18)成中英:《世纪之交的抉择》,第366、366页,上海,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
(19)(20)李翔海编:《知识与价值》,第301、31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
(21)方朝晖:《“哲学”范畴的中国化及其内在问题》,载《学术季刊》,2000(4)。
标签:哲学论文; 牟宗三论文; 冯友兰论文; 哲学基本问题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特质理论论文; 哲学家论文; 西方哲学论文; 成中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