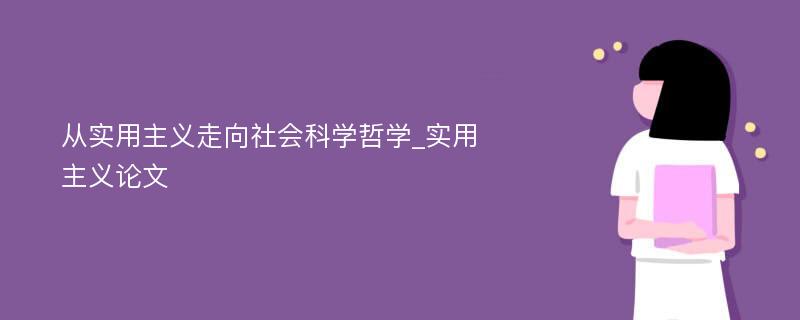
走向一种由实用主义所激发的社会科学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哲学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用主义哲学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影响受到各种各样的局限。当然,实用主义对社会科学在20世纪整个过程中展开自己的方式,有着一种实质性的影响,尤其在美国。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遗产是进步主义的、由实践所驱动的教育的发展,而G.H.米德(G.H.Mead)所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打破了与笛卡尔式的孤立的、非社会的自我概念的联系。二者对互动主义社会理论的建构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种互动论影响着目前的社会学、教育科学和社会心理学。也应该承认,芝加哥学派深深植根于美国实用主义之中,许多后来的社会科学家和批判性思想家,如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同样如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承认实用主义的社会科学不只是存在于北美,在实用主义与欧洲社会理论之间正在兴起一种富有成果的对话①。不过,这些例子仅限于社会科学和社会理论的实践领域;就整体而言,对实用主义的兴趣并没有扩展到社会科学哲学领域之中。除了一些例外(例如,哈贝马斯②),社会科学哲学家普遍忽视实用主义,甚至表现出明显的敌意(例如,巴斯卡③)。虽然罗蒂、伯恩斯坦等人对实用主义传统的重新发现,无疑对哲学和文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相形之下,这种实用主义传统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影响却并没有得到重视。本文意在填补这一空白,说明实用主义,尤其是其最新的发展,将对社会科学哲学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一)科学:方法论的多样性
对基础的哲学工程,我遵循实用主义的怀疑主义。许多实用主义者已经对那种认为在知识的获取和证明中存在着坚实的、不可改变的基础这样一种观点,表明了明显的敌意。他们拒斥以下观点,即哲学的洞见会打开一条秘密通道,最终可以导向这些知识基础(例如,伯恩斯坦和罗蒂)④。不过,我对范围广泛的哲学辩论不怎么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基础主义渗透到当代科学哲学中来的途径。它现在仍然存在于这样一些持续的企图中,也就是揭示科学的“本质”或“逻辑”——据称所有成功的科学活动都共同具有的探索的逻辑,我所拒斥的就是这种形式的基础主义。对科学在本体论上和方法论上的统一性的追求,曾经是维也纳小组的特点。本体论上的统一性的概念很快被放弃,但是,证伪主义者和批判实在论者进一步发展了对方法论统一的探求。虽然认识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但是,波普(Popper)和巴斯卡(Bhaskar)一直追寻这些研究领域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的东西。不过,自然科学史已经表明,任何这样的重构都是非常值得怀疑的。要认识到自然科学领域内的不同学科所共有的东西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这种困难的存在将使得无法用单一的方法把这些学科归属于单一的范畴⑤。在自然科学中不同的学科是按照非常不同的方法来发挥作用的。目前,与新实证主义关于自然科学的重构相反,人们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生物学并不适合关于物理学和化学的绝大多数方面的模式⑥。生物学的主题的性质似乎倾向于不适应“现代科学的形而上学”。新实证主义的自然科学观假定那种由规律所支配的、决定性的以及完全可以理解的结构的存在,而在生物学中我们要面对的是相反的情形,或如杜普雷所说的“物的无序”。生物的复杂性超越了我们的计算和认知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完善的说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此,毫不奇怪,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力图揭示自然领域的潜在结构,而生物学家是以一种更有实践性的、工具性的方式来操作的。如果生物学是如此不同,那么,所谓科学在方法论上的统一则完全是不可能的了。越来越明显,那些相信这种统一的方法论的人是错误地从少数几个分支学科(主要是物理学)中推导出来的,实际上,这些方法在这几个学科中适用,而在别的学科中却不一定适用。
摒弃对所谓科学本质的探求的另一个理由是: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支配所有科学活动的中性运算法则的信念,是建立在一种片面的和歪曲的科学观之上的,这种科学观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已经完成的和被整齐地加以划界的活动⑦。过去几十年科学社会学中的许多应用已经表明这一观点是多么荒谬。目前,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家的社会实践感兴趣,这种兴趣在所谓“科学社会学的强纲领”那里得到了最强烈的体现⑧。随着这种兴趣在关于科学的社会建构领域内不断增长,存在一种不变的科学概念这样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把科学与其他活动区别开来)引起广泛的讨论。我们看科学的距离越近,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区别也越模糊。我们越研究科学家实际上是怎么操作的,他们的成果呈现给我们的就越富有可争议之处。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说明科学家是怎样使用不同的把戏或修辞手段去说服别人的,使用“正确的科学方法”并不足以使科学家成名。他们必须在合适的杂志上发表成果,如果要设法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必须以适当的方式来写作,以同样是有争议的资料来支持他们自己的主张,进一步参考其他论文,等等。科学家在科学中不仅像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那样使用许多的修辞;他们自己的经验研究也远比新实证主义哲学家所承认的要杂乱。当研究成果最后在权威的科学杂志以优雅的论文出现的时候,它们可能看起来是无可争议的和权威的,但是,对通向“发现”的实际经验研究的详细人种志研究表明,原来这些发现可能是多么成问题的和虚假不真的东西⑨。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以一种相似的方式,表明教会最初对伽利略的反对并不是那样不合理。教会的意见部分地是科学的,部分地是伦理的,但是,相对于那个时代的背景及其假定来说,教会意见的任一方面都是有道理的⑩。可以从反面来进行辩论,说这些假定是错误的,但是,关键的地方是,如果不依靠更广泛的前提,就无法作出科学的判断,而大多数假定是不能由经验来加以评价的。
科学中缺乏方法论的统一,这不只是与学科之间的方法论差异有关。缺乏统一也渗透到学科之内。科学史家,诸如托马斯·库恩和保罗·费耶阿本德已经证明,例如,在物理学中,并不存在一套支配一切的规则来指导成功的科学研究。存在着这样一种模式:长时段的常态科学之后,是科学革命的短时期的爆发,库恩的研究尤其是因为他以如此庄严的方式所描述的循环图式而闻名。不过,不应该把这种模式与单一方法的循环使用相混淆(11)。就任何新的范式来说,方法论的规则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改变,在这样一种范围之内,我们才有可能谈论认识论的不连续性。这样说是合理的,即除了最乏味的和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命题之外,并不存在一套(可应用于所有范式的)支配一切的规则,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并没有适用于科学的中性的运算法则。依同样的道理,费耶阿本德说明,在某一个时期或语境之内非常成功的某一特殊的研究逻辑,在另外的时期和语境之下却可能并不这样。一种新的制度和社会环境的出现,可能使得曾经非常成功的某一研究策略变得不适用,而曾经被放弃的却可能突然成为一种非常好的策略。科学家的具体工作也表明科学研究的“地方性”:不同的文化、国家和实验室以不同的方式来操作。同样,人们对历史学家,如盖索(G.L.Geison)所最先提出来的“研究学派”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感兴趣(12)。即使在学科之内,这种经验的证据也表明,并不一定存在起作用的某一单一的方法。
(二)社会科学与方法论的多元论
从人们常说的那种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中来推论适用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规则是有问题的。这样做的任何企图都有可能成为少数几个逻辑上的缺陷的牺牲品。首先,存在着这样一种趋势,把构成社会研究之基础的多样的认识旨趣简化为这样一种单一的旨趣:可能实现预见的说明。正如哈贝马斯已经指出的,把知识简化为这样一种“经验—分析知识”的形式是几个作者所犯的一个逻辑错误,这种错误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相联系。当哈贝马斯证明社会科学的独特性质使得它可能去追求其他的认识目标时,他肯定是正确的。“认识旨趣”的概念比科学哲学家经常谈及的用于理论选择的所谓标准来说是更为基本的。例如,当库恩提到作为标准的准确性、一致性、范围、简单性和成就时,他仍然假定研究是为了说明外部世界,而标准表明这种说明有多好。社会研究的认识目标包括社会的批判(这与自我解放或解除过去的限制紧密相连)、理解(它赋予文本或实践以意义)以及正如我所强调的自我理解。其次,把社会科学放在仅仅适合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紧身衣中的这种倾向甚至是更成问题的。把自然科学当作一种角色模式来使用的做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定的基础之上的,即所有自然科学的分支都有某种同样重要的东西。正如我所证明的,如果这一假定是有问题的,那么,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格言就变成一个令人困惑的要求。第三,正如把性质不同的自然科学看成一个单一的实体这种做法是可以质疑的一样,把社会科学作为一项统一的事业来对待同样是有问题的。可能容易证明,就方法而言,比如,与语言学相比,人口统计学与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有着更多共同之处。即使在每一个分支之内,假定方法论上的统一也是危险的。缺乏这种统一性可能是非常有建设性的。社会学没有达到在当代经济学中所发现的那种方法论统一的水准,但是,这不一定是一个障碍。这使得研究者一直能够意识到构成他们工作之基础的那些明确前提,以及认识到能够加以描述的其他可以选择的研究方案。今天社会学的力量恰恰就在于它能够打破与以前所建立的假定的联系,并且经常在某一给定的课题上能够引入新的角度。方法论选择的多样性培植着一种自我意识,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
(三)社会研究是一种对话
我的第三个主张更广泛地影响着社会理论。我质疑史蒂文·塞德曼和杰弗里·亚历山大恰当地称呼的社会科学中的“基础主义”(13)。在哲学中,基础主义是指系统地探求据说构成认识(或伦理和审美)主张之基础的认识论(或其他基础)。实用主义的较早的形态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批判基础主义。同史蒂文·塞德曼和杰弗里·亚历山大一样,我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使用基础主义的概念。史蒂文·塞德曼和杰弗里·亚历山大谈到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内社会理论家构想他们的学科的占统治地位的方式。这些理论家力图揭示关于社会的囊括一切的框架或科学的不变的基础。基础主义可能在批判实在论那里找到其最纯粹的表达形式,但是,它也表现为许多其他的形式和形态: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和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到卢曼的系统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这样,基础主义就能假定个人的能动作用或结构的强制,采取一种政治上保守或激进的立场,成为实证主义的或是由解释学所激发的理论主张。基础主义的统一的特征是这样一种信念:理论为强有力的参考框架提供一个客观的基础,理论能被应用于不同的环境、文化和时代,即使不是所有的环境、文化和时代。在社会科学哲学中,基础主义伴随着关于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功能性说明与目的性说明等等孰优孰劣的持续不断的、分析性的辩论。这些哲学问题据说解决了不同基础主义方案之间的论争。
这里不适合详细阐述针对社会科学和理论中的基础主义的哲学论战,而且已经有人非常冷静地做了这一方面的介绍(14)。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更迫切的问题是,社会研究者的共同体已经从基础主义的方案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收获。答案是非常少。我们离问题仍然很远,这些方案或理论中的哪些可能更令人信服?实际上,基础主义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统一,其发展的结果之一是分化为不同的流派,以及在这些流派之间的堑壕和知识上的越来越明显的隔膜。大多数研究者仅仅谈论和依靠他们的学派中的成员,有些学派甚至有他们自己的杂志和丛书。简而言之,相互对立的阵营的成员往往不承认彼此的立场。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实际上使用的是伯恩斯坦所说的“对抗性的”或“遭遇性的”论辩风格(15)。在这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中,对立学派的言论往往是针对对方和批判对方,目的是摧毁对方。相互对立的学术部落成员的观点被表明是错误的、不一致的或没有意义的。参与这种形式的论辩的人并不想从其他观点中学习,他们也不想利用学术交往的机会去反思和质疑他们自己的某些前提。针对这样一种状况,我倡议一场超越基础主义时代的运动,把学术交往看作是一种“对话际遇”(dialogical encounter)(16)。在对话际遇中,人们并不希望靠千方百计地找出他人的弱点来得分;他们力图通过尽可能理解他人来聆听他人的意见。他们强化自己的论点,使它尽可能令人信服,并从他人那里学习。这样,学术交流就变得更像是一种恰当的对话,鼓励参与者以独特的方式思考问题。最终的目的不是为某一种具体的制度进行辩护或者为这种制度的完善服务,而是通过学术的对话来促进我们的想象才能。
(四)知识是行动
我们不应该把知识构想成表述性的,而应该把它看作是一种行动方式,看作是某种行动着的东西(17)。正如威廉·詹姆斯所正确地指出的,“实用的方法……是作为一种路径的指示而出现的,在这里,现存的实在是可以改变的”(18)。这样,知识与“认识的旨趣”相关联;社会科学哲学应当反思构成社会研究之基础的不同目标,思考如何才能够达到每一个目标。依据这一观点,没有任何认识旨趣能够取得对其他认识旨趣的先验的优先地位。所以,认真对待实用主义,就要避免“本体论的谬误”,这种错误的假定认为,方法论问题能被简化为本体论的问题(19)。针对这一假定,我证明,方法的问题总是涉及目的的问题,因此,所使用的方法至少部分地依赖于特定研究想要实现什么样的目的。不涉及社会的本体论也足以能解决社会方法论的问题;没有什么关于社会的本质的东西强迫使用某一具体的方法。不过,这不是说方法论就只是一个目的的问题。的确,当罗蒂说方法论根本不能建立在本体论的基础之上时,他似乎就犯了这种“工具主义的错误”(20)。与罗蒂相反,某一特定的方法论路径可能导向某一研究领域中的一个具体的目标,而不是属于另一个领域中的目标。同样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某一具体研究对象的性质使得我们不可能同时实现某一特定的目标。此外,社会理论家或哲学家也完全有可能确定社会的本体论特征,而这种本体论特征可以被用来进行同一类型的方法论的界定。简而言之,虽然方法论的选择总是有局限的,但是,我们也不是不可能去确定被施加于这种方法论选择的本体论限制。
(五)自我理解开辟了另一种局面
我认为,我们应该把自我知识作为一种认识旨趣来加以认真对待。这与以伽达默尔的方式来构想理解的诉求是联系在一起的(21)。我这么说的意思是,理解应当首先被看作是一种际遇,在这一际遇中,依赖我们的文化前提来接近正在被研究的东西。其次,通过这一际遇,我们表达和重新表达这些相同的前提。“解释学的循环”是一种回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假定既是理解的前提,也受到这种际遇的影响。伽达默尔主要是在本体论的范围内使用理解这个概念的。我建议也把理解这个概念作为一种方法论的策略来使用。的确,理解总是包含着对话的模式,但是,我认为,从积极地进行对话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的东西。对话的概念在伦理学和政治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富有成果的使用,这种情形可以从A.麦金太尔(A.MacIntyre)的有影响的著作中看到。对他以及其他使用对话模式的人来说,追求一种关于正义的普遍理论就是无视这样一个事实:伦理立场是与伦理传统相联系的。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试图置身于一种传统之外来获得一种中性的优势的观点,而是承认我们的观点的文化特殊性,并保持对其他传统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可以通过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来获得,这就是保持对其他传统的开放,并从其他传统中学习。这种开放性以及愿意向其他传统学习的意愿,对如何把对话模式应用到社会科学哲学中来说是关键的。
解释学循环的概念对于社会研究的方法论来说有三个重要的含义。这个回归概念的第一个含义是,它完全承认人们不可能获得不在某方面反映他们的旨趣和价值观念的世界观。正像实用主义者坚持哲学应该从尼采所说的“真的世界”中摆脱出来一样,解释学循环的概念认为,理解只有在日常或生活的情景中发生。正如斯坦利·菲什(Stanley Fish)令人信服地指出的:相信我们能够摈弃“解释性共同体”的力量并以某种方式“回归到文本”(back-to-the-text)是错误的,同样成问题的是,认为正确的解释方法会让我们触及“外部的实在”(reality-out-there)。其二,正如理解的概念是如此根本地与任何传统的符合概念相对立一样,依据是否最好地反映外部世界来判断关于社会实在的不同解释也有问题。不过,否定这种标尺的恰当性并不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任何标准。一个明显的标准是,一项研究是否使我们对正在被研究的东西产生了新的领悟——所谓新,也就是指与现存的意见的关系。其三,理解是与“自我理解”紧密相连的:相遇新的社会环境能使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的文化和环境进行重新描述和概念化。在这里,我的论述很明显也是与诸如把社会研究的初始目的看作是忠实地刻画外部社会世界的观点相对立的。受罗蒂关于“教化性”哲学的建议的启发,我的文章也提倡“自我指涉的”知识获取形式的重要性,在这种知识获取形式中,个体学会从一种不同的视角来看他们自己、他们自己的文化以及他们自己的假设,并且把这种重新解释与可供选择的生活形式相比较。换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自我指涉的知识试图表达和质疑那最先使相遇差异成为可能的相同的前提。
虽然罗蒂仍然仅仅关注哲学,我认为社会科学(而不是哲学)在这种自我指涉的知识类型中发挥着一种核心的作用。在社会科学中,相遇差异会以三种方式影响人们的自我知识。首先是“概念化的影响”。这是指相遇不同的生活方式会让人们对他们的文化进行表达和概念化。研究生活的不同形式会让个体表达他们的无意识的假设和他们迄今借以理解他们的环境的解释方法。其次是“解放性的影响”。相遇差异会让人们质疑某些有关他们自己的文化,或某些一般文化产物的根深蒂固的信念。例如,相遇一种不同的环境也许能使人们区别哪是必然的,哪是偶然的,哪是本质的,哪是历史的。虽然人们往往倾向于把他们的似乎理所当然的文化环境看作是普遍的,但是,事物总是具有差异性的意识会质疑或者削弱这种经验。第三是“想象性的成分”。正视差异会让人们构想可选择的未来。人们的期望和想象性的能力,往往可能被他们生活于其中的想当然的世界所形塑和限制。相遇一种不同的环境将使人们能够拉开他们与自己的文化之间的距离,从而探索新的世界。它使人们能够发展他们的想象性的能力,这样,他们就能够对不在场的东西产生构想。
(六)人类学的批判转向
这里关于由实用主义所激发的哲学所做的构想,不只是一种哲学的建构;它们与经验的研究有直接的关系。在社会科学中,依据这些理路来进行的研究越来越多。我将给出三个学科的研究例子,它们会具体说明我的观点。这些例子一个来自文化人类学,一个来自考古学,还有一个来自历史学和历史社会学。这些例子允许我示范如何应用我的由实用主义所激发的观点,说明这种观点的可能的理论和方法论缺陷,以及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些缺陷。
人类学中的批判转向最初是由马库斯和费希尔(1999)的《作为一种文化批判的人类学》以及克里福德和马库斯(1986)的《书写文化》所提出来的,这种转向表明人类学已经远离了关于知识的表述性的观点。它也预示着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在这里,人类学家不再被一种教条或理论的参考框架所约束。人类学中的批判转向意味着用推论性隐喻(知识是“文化诗学”,知识是一种相互影响的声音)取代视觉隐喻(知识是观察之眼)。在这样一种视角之内,研究不再只是对存在于外部世界的东西的一种描述或说明。与之相反,它把相遇差异看作是一种机会,首先是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某些假设,其次是反思在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中,人类学的立场在何种程度上影响它所产生的那种认知需要(22)。第一个目标在身份和人格的概念上由人类学研究作出了具体的说明。相遇完全不同的人格概念,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我们自己的想当然的概念,使它们变得清晰,并且认识到它们不一定是普遍的(23)。第二个目标,具体说来就是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人类学通过什么样的途径与殖民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内在的关联,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这种联系仍然可能影响今天默认的认识论假设。这两个目标都与批判的概念有联系,因为,在两种情形之下知识都涉及挑战和质疑我们自己的文化,包括人类学学科本身(24)。每一个目标也都与新实用主义的教化概念有联系。对实在进行系统描述的目的是达到“普遍的相同性”,而教化的描述意味着我们向新的经验开放,同时永不放弃对话(25)。
(七)后过程的考古学
利用亨普尔的演绎的—律则性的模式,过程考古学(或“新考古学”)试图把考古学建设成一门科学。过程考古学试图在复杂的统计方法、信息和系统理论的帮助下,寻求类似规律的概括(26)。与之相对照,后过程的考古学家则指向社会生活的有意义的性质,肯定自然主义的不可能性。他们与过去的关系在这里是尤为重要的。后过程考古学家重新思考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他们强调考古学能被有意识地用来挑战和批判现在,挑战我们根深蒂固的假定。虽然后过程主义者认识到,任何考古叙事都不可避免地与现在的旨趣和意识形态存在关联,而且依赖于这种旨趣和意识形态,但是,他们也相信考古研究者能够利用客体来审视他或她自己的文化假设(27)。这种视角构成了关于身份形成研究的基础,这一研究是在女性主义的后过程观念的羽翼下进行的,其目的是挑战今天俘虏着我们的一些二分法(28)。同样,后殖民的人类学也会表明被殖民社会的混血和混合的性质,从而质疑某些支配目前法律论辩的众所周知的假设(29)。这里尤其要注意与早先的论点的区别,相遇其他观点迫使考古学家重新思考他们的假设:现在他们有意识地用过去来质疑现在。因此,蒂利有这样一句格言,“考古学家到目前为止一直在解释过去;他们应该努力改变过去,以服务于现在”(30)。这说明了为什么后过程主义者对任何呼吁进行经验主义考古研究的尝试都充满敌意,这不仅是因为与理论无涉的观察这样一种安全港的观念只不过是一种幻觉,而且也因为这一概念把考古学家的职业简化为仅仅是寻找事实这个单一的使命。考古学远不只是简单地记录资料,它也与创造性地使用资料来面对现在有关。这也说明了为什么后过程主义者批评新考古学没有认识到过去的独特性,批评它把过去简化为现在的一面镜子。只有充分地意识到过去与现在的非连续性,前者才能被成功地用来挑战后者。批评现在可以在两个层次上来进行,一是在学科内部,一是在学科外部。它首先是指质疑考古学家自己所使用的关于理论框架的假设;其次是指质疑当今社会中的社会组织的某些范畴或原则。后过程主义者尤其关注其工作的社会意义。因此,他们最终更感兴趣的是社会层面而不是学科层面。
(八)系谱性的历史和社会学
福柯重新发现了尼采用于历史研究的系谱学方法的意义,受福柯的影响,许多当代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都采纳并广泛地应用这一系谱学方法,因而形成了许许多多复杂的历史分析,比如,关于“治理”(governmentality)的分析,关于现代人格概念的分析,以及关于治理贫穷的分析(31)。正如人类学中的批判转向和后过程的考古学一样,系谱学的目标也是自我指涉的知识获取。系谱学的主要目标不是简单地走向不熟悉的过去,而是清晰地说明和阐明我们所熟悉的现在。这样,过去就成了接近现在、根除传统的基础和挑战有关连续性的假定的手段。对于系谱学家来说,除非历史研究汇入“生活和行动”,除非它帮助我们摆脱自己所建构的东西的束缚,洞穿我们给自己戴上的精神枷锁,不然,它就没有什么价值:“知识的形成不是为了理解;它的形成是要用于斩断”(32)。历史,只有当它确实与现在产生关联时,只有当它切入或刺穿现在时,才有意义(33)。系谱学的过去之旅能够形成对我们现在状况的一种批判的距离。系谱学家证明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假设(例如伦理)或墨守成规的实践(例如惩戒),通常比我们想象的要具有大得多的历史特殊性。阐明在某一个特殊的时间点上这些假设或实践的历史呈现,会使我们证明它们与具体的历史偶然性或权力斗争的关系。这又进一步削弱了我们将这些假设或实践看作是自然给予的或必然进步的东西的倾向。尼采的系谱学与批判关于“起源”(ursprung)的形而上学追求有关。寻求起源就是试图恢复一种不为人知的本质,找回那些“先于由偶然和演变所构成的外部世界而存在的稳定的形式”(34)。系谱学研究认为,除了清醒地意识到本质并不存在的真理以外,不存在无时间性的和本质的秘密。格斯(Geuss)将系谱与家谱进行比较,家谱是使个人、家庭或其他实体合法化,展现某个被称为单一而高贵的血统得以产生的一个连续而久远的延续过程,而系谱揭示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发展线索,我们回溯的时间越远,那么,似乎存在着的起源也就越纷繁复杂(35)。与家谱概念的另一个区别是系谱学家追求不连续性,探索贯穿历史从而导致出现完全不同的思想和存在形式的那种历史断裂。尼采这里讨论的是效果历史(wirkliche historie),旨在引爆持续、稳定的本质这种虚幻而荒诞不经的结构(36)。
(九)本文的几点结论
这三个例子(人类学中的批判转向,后过程的考古学以及系谱性的历史和社会学)示范和说明了我的这一由实用主义所激发的观点的轮廓及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案的潜能。它们说明了一种自我指涉的知识获取形式如何能够应用在实际的研究中,以及已经有了怎样的应用,而不只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说明。它们表明了这一方法论观点的广泛的可应用性,的确,这种观点可以在多种多样的学科中付诸实施。但是,对于这些例子来说,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探讨。这些研究策略已经存在几十年了,因此,应当能够从这些研究策略中了解这一由实用主义所激发的方案可能承续的新的关注点是什么,以及如何处理这些问题。有三个问题是所有的研究者在追求自我指涉的知识的过程中都应当关注的,它们是他者的性质、相对主义的问题以及知识与政治行动的关系。
第一个问题涉及“他者”的地位,这个问题已经在广泛的学科中激起了热烈的讨论,从社会学和文化研究到历史和社会人类学。当代人类学家、文化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警告“他者”应当不被作为一种先验的同质而固定的实体来对待,他们这样做是正当的。对“他者”的性质的这种关注对于一般的社会研究来说也是有价值的。的确,这种关注在许多话题的辩论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性别到殖民和后殖民的经验。例如,拉康的女性主义的论点,即女人的经验与男人不同,已经被正确地批评为忽视了女人之间的经验的差异,非批判地袭用“妇女”这一范畴。这些经验不仅因为阶级和种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把女人作为一个统一的范畴来使用是有困难的,而且“妇女”作为与“男人”相区别(“男人”的概念也与“妇女”不同)的概念,已经表明是不稳定的和被政治化的(37)。在相似的文脉中,萨义德(Said)和霍米·巴巴(Homi Bhabha)已经指出,西方人对他者的不同解释,诸如对东方的解释,都是对实际上是某一完全不同的实体的“本质化”(38)。对某一特定的范畴进行本质化,就是假定属于那一范畴的所有或大多数的成员借助某些内在的品质而具有特定的共同特征。对于萨义德来说,东方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话语,它助长这种把“他者”看作一个统一的东西的这样一种歪曲的观点。这样,正如在“妇女”这个例子上,危险是这个范畴之内的不同的经验差异都被错误地抛弃了。正如上面的这些例子所表明的,如果研究就是要去面对这种差异,如果相遇差异是这种研究的一个关键的部分,那么,问题就更为紧迫。属于这种传统的研究者有必要确定不要把研究的对象作为一种统一的、不可区分的实体来对待。这样,追求自我指涉的知识获取,应该与有规则地重新评价“他者”如何被构想的任何假设携手并进。
第二个问题涉及的是这样一种指责,即这些类型的研究都是相对主义的。有些后过程的考古学家和反思性人类学家认为,任何对资料的重构都仅仅是一种解释的行动,是许多叙事中的一种叙事而已。尼采持相似的观点,他诉诸“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根据这种观点,任何历史都应该被描绘为仅仅是从现在的角度所看到的历史(39)。对尼采来说,“一个事实,一件作品对每一个时代的人来说,对任何新的类型的人来说,都以某一新的方式展现其动人之处。历史总是阐发新的真理”(40)。这种主张可以说含混到臭名昭著的地步;它们之所以被解释为相对主义的,毫不足怪,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弄巧成拙。不过,我认为不应该给它们贴上这些标签,对它们作出这种解释。这一立场存在的立脚点是不存在能够在不同的叙事之间作出比较和判断的中性的运算法则;这种类型的决策只有通过有经验的研究者之间的公开对话才能作出。如果这种立场意味着根本不能作出这种判断,因而任何叙事都像任何其他的叙事一样是有效的(或者是难以置信的),那么,它就是成问题的。后面所说的这种立场不仅与常识相悖,自相矛盾,而且与构成自我指涉知识的解放性效果的东西也是不相协调的。的确,任何叙事所持的立场都会严重地削弱我们质疑某些信念或假定的能力,这些信念和假定涉及特定概念的不变性或普遍性。这种立场与尼采的有关伦理的系谱学的关键角色相抵触。但是,我所提倡的立场则可能与它并不抵触。我所提倡的这种立场完全承认不可能先于人们之间的开放的对话而设定准则。这一立场与实用主义关于自我的社会性质以及任何形式的探索的公共性方面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种主张,“只有把我们的假设诉诸公共的批判的谈论,我们才能意识到在我们的主张中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无法经受批判的审查”(41)。
第三个问题与社会研究中所涉及的伦理有关。探求自我指涉类型的知识,对研究者提出了新的伦理关怀和责任。这在福柯的属于现在的历史的例子中尤其明显。在传统史学的范围之内,主要的目的是说明过去,因此,研究者没有在政治上如何采取行动的负担。福柯式的史学家则的确承担着这种责任。他们力图干预现在,因此,在他们身上就承担着一种责任,就是指明往后怎样继续下去。福柯对这一悖论的回应就是把自己说成是与“传统的知识分子”相对立的一种“新知识分子”。后者高高在上,鼓吹自己的观点,试图把自己的世界观强加于别人,而前者则只是提供工具让人们设定一种距离来审视他们的想当然的世界以及以不同的方式来看待事物(42)。从我的实用主义的视角来看,福柯的回应仅仅在部分的意义上是令人信服的。他怀疑把批判建立在无时间的基础之上的企图,以及那种认为任何变革都必然意味着进步的思想,这是有说服力的。不过,问题仍然存在着,一旦现在以福柯所期望的趋势受到干预,发生改变,那么,研究者就有责任对需要做些什么提供准则。不奇怪,福柯在政治上很活跃;他做出种种努力来改进法国的刑事制度。自我指涉的知识获取必须要求研究者对自己如何行动有着强烈的责任意识。当然,这一立场与实用主义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实用主义认为,知识不是像镜子似的反映外部世界,而是要产生一种影响和作用。
注释:
①参见H.Joas,Pragmatism and Social Theory,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P.Baert and B.S.Turner," New Pragmatism and Old Europe: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ragmatist Philosophy and Europea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 ,European Journal for Cocial Theory,2004( 7) .
②J.Habermas,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Cambridge:Polity Press,1987.
③R.Bhaskar," Rorty,Realism and the Idea of Freedom" ,in A.Malachowski( ed.) ,Reading Rorty,Oxford:Blackwell,1990,pp.198-232.
④参见R.J.Bernstein,The New Constellation: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R.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Oxford:Blackwell,1980; R.Rorty,Philosphical Papers Vol.1:Objectivity,Relativism,and Truth,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⑤R.Rorty,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Harmondsworth:Penguin,1999.
⑥J.Dupré,The Disorder of Things:Metaphysical Foundations of the Disunity of Scienc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 A.Rosenberg,Instrumental Biology or the Disunity of Science,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4.
⑦参见R.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Oxford:Blackwell,1980,pp.322-333; R.Rorty,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Harmondsworth:Penguin,1999,pp.67-69.
⑧参见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 H.Collins,Artificial Experts: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lligent Machines,Cambridge,MA:MIT Press,1990; Barnes et al.,Scientific Knowledge:A Sociological Analysis,London:Athlone,1996; K.D.Knorr-Cetina,Th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An Essay on the Constructivist and Contextual Nature of Science,Oxford:Pergamon,1996; H.Collins and M.Kusch,The Shape of Actions:What Humans and Machines Can Do,Cambridge,MA:MIT Press,1998.
⑨B.Latour,Science in Action,Milton Keynes:Open University Press,1987,pp.63-100.
⑩P.Feyerabend,Against Method,London:Verso,1998,pp.129-138.
(11)R.Rorty,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Harmondsworth:Penguin,1999,pp.175-182.
(12)G.L.Geison," Scientific Change,Emerging Specialities and Research Schools" ,History of Science,1981( 19) ; G.L.Geison( ed.) ,Research Schools:Historical Reappraisals,Osiris,vol.8,1993; E.F.Keller,A Feeling for Organism:The Life and Work of Barbara McClintock,San Francisco,CA:W.H.Freeman,1993; P.Galison,How Experiment End,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13)S.Seidman and J.C.Alexander," Introduction" ,in S.Seidman and J.C.Alexander( eds.) ,The New Social Theory Reader,London:Routledge,2001,pp.1-26.
(14)R.J.Bernstein,The New Constellation: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
(15)Ibid.,pp.336-337.
(16)Ibid.,pp.337-339.
(17)参见J.Dewey,The Quest for Certainty:A Study of the Rel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New York:Minton,Balch,1930.
(18)W.James,A New Name for Some Old Ways of Thinking,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07,p.45.
(19)R.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Brighton:Harvester Wheatsheaf,1982,pp.195-203; R.Rorty,Philosophical Papers Vol.1:Objectivity,Relativism and Truth,Cambridge:Camo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78-92.
(20)R.Rorty,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Brighton:Harvester Wheatsheaf,1982,pp.191-210.
(21)H.G.Gadamer,Truth and Method,London:Sheed and Ward,1975; R.J.Bernstein,Philosophical Profiles:Essays in a Pragmatic Mode,Philadelphia,PA: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6,pp.94-114; R.Rorty,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Oxford:Blackwell,1980.
(22)G.E.Marcus and M.J.Fis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7-44.
(23)G.Bowman," Identifying Versus Identifying with the ' Other' :Reflections on the Sitting of the Subject in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in A.James,J.Hockey and A.Dawson( eds.) ,After Writing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7,pp.34-50.
(24)G.E.Marcus and M.J.Fisher,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9,pp.137-164.
(25)N.Rapport," Edifying Anthropology:Culture as Conversation; Representation as Conversation" ,in A.James,J.Hockey and A.Dawson( eds.) ,After Writing 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7.
(26)A.Wylie,Thinking from Things: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Archaeology,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p.25-41.
(27)I.Hodder,Reading the Pas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p.180-181.
(28)L.Meskell," Archaelologies of Identity" ,in I.Hodder( ed.)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2001,pp.187-213.
(29)C.Gosden," Postcolonial Archaeology:Issues of Culture,Identity and Knowledge" ,in I.Hodder( ed.) ,Archaeological Theory Today,Cambridge:Polity,2001,pp.241-261.
(30)C.Tilley," Archaeology as Socio-Political Action in the Present" ,in D.S.Whitley( ed.) ,Reader in Archaeological Theory,London:Routledge,1998,pp.315-330.
(31)G.Burchell,D.Gordon and P.Miller( eds.) ,The Foucault Effect:Studies in Governmentality,Hemel Hempstead:Harvester Wheatsheaf,1991; G.Procacci,Gouverner La Misère,La Question Sociale En France 1789-1848,Paris:Seuil,1993; N.Rose,Governing the Soul,London:Free Association Books,1999.
(32)M.Foucault," 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 ,in M.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p.139-164.
(33)N.Nietzsche," On the Utility and Liability of History for Life" ,in E.Behler( ed.)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iedrich Nietzsch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83-167.
(34)M.Foucault," 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 ,in M.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142.
(35)R.Geuss," Nietzsche and Genealogy"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94( 2) .
(36)M.Foucault," 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 ,in M.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p.152-157.
(37)D.Riley,Am I That Name? Basingstoke:Macmillan,1988; M.Barret and A.Phillips( eds.) ,Destabilising Theory:Contemporary Feminist Debates,Cambridge:Polity Press,1992; J.Butler and J.Scott( eds.) ,Feminists Theorise the Political,London:Routledge,1992; L.Segal,Straight Sex:The Politics of Pleasure,London:Virago.Segal,1994.
(38)E.W.Said,Orientalism,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 H.Bhabha,The Location of Cul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
(39)A.Danto," Nietzsche' s Perspectivism" ,in R.C.Solomon ( ed.) ,Nietzsche: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Notre Dame,I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73,pp.29-57.
(40)N.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London: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68.
(41)R.J.Bernstein,The New Constellation:The Ethical-Political Horizons of Modernity/Postmodernity,Cambridge:Polity Press,1991,p.328.
(42)M.Foucault," 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 ,in M.Foucault,Language,Counter-Memory,Practice,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p.207-208.
标签:实用主义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论文; 自我认识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人类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 考古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