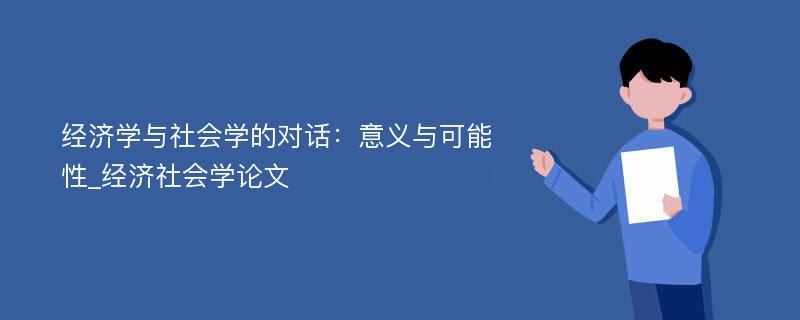
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学论文,经济学论文,可能性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话及其意义
提倡经济学与社会学对话不只在于这种对话既必要又有可能,更重要的还在于其不对话的现实。如果有经济学者谈论社会问题,十有八九会被社会学者斥为肤浅,而如果有社会学者指点经济问题,百分之百会被经济学者认为是谈论其不懂的东西。关于前者,我们可以从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S.Becker)早期对人类社会行为所作的经济分析在社会学界引起的反应中窥见端倪;至于后者,早在社会学的命名祖师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 )那里就已领教过经济学者的尖刻批评,当时的经济学者认为孔德讲经济学是在讲他完全不懂的东西。
对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人为筑就的学科藩篱的这种判断也许有失偏颇或夸大,但是,主流经济学与主流社会学之间从不试图沟通和对话,则是不争的事实。加里·贝克尔等人的人类行为经济分析,一向为主流经济学所拒斥,即使是在他于1992年因这一领域的杰出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时,仍有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不予接受;至于主流社会学,只要翻一翻那些流行的教科书就可知道,主流社会学的理论体系中并没有“经济”的一席之地。
这似乎说明,经济学与社会学之间并没有太多必然的联系,两者之间的拒绝对话也并不影响各自的学科发展。然而,这种看法是似是而非的,并且,两者之间的隔阂不仅造成了“公共”的问题,而且也影响了各自学科的发展。所幸的是,这种后果已分别引起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的注意。譬如美国经济学者斯坦菲尔德(R.Stanfield)就曾尖锐地指出:
“正统经济学——新古典综合派——已经进入不结果实的形式主义阶段。……主流经济学把经济过程定义为面对稀少进行选择,实际上其整个核心都依赖于对经济的逻辑演绎分析,忽视了对在历史上同生产和消费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行为分析。强调通过计算机得出来的选择很明显是同在制度上偏爱市场交易纠缠在一起的。交易过程能有效地控制个人价值的观念已经导致了市场价格和社会价值的实质差别,而这种差别又导致了失真的政策建议和政策评估。(注:参见斯坦菲尔德,“制度分析:经济学中即将到来的革命”,载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正统经济学这种把市场资本主义的特殊情况上升为一种普遍原则的做法导致了“经济学家的谬误”(economisticfallacy),而这种谬误的存在也是“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的原因之一。(注:参见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前引书,第13页。)同样,在社会学界,也有社会学者意识到这种学科藩篱的障碍作用,如美国社会学者特纳(R.H.Turner)就曾指出:
“有几个尚未解决的问题限制了社会学的完善和运用。其中之一是:由于重新找出从前的相关研究成果很困难,不同专业而从事同样或相关问题研究的人缺乏沟通,因而有些劳动都重复和浪费了。……不同词汇的使用,专业期刊的滥出及会议的频繁不仅导致了重复浪费,而且也使研究人员无从吸收其他学科的养料(这在新观念时代是非常必要的)。问题和题材惊人的同质现象时常被表面结果的殊异掩盖了。……我个人则相信,愿撇开细小枝节及在研究中探索问题时能跨过学科界限的有较独立意志的学者才能给社会学带来益处”。(注:特纳,“寻求认同的美国社会学”,载单天伦主编《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第4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显然的是,提倡学科对话,将有助于上述两个学科存在问题的解决。或许可以说,我们正处于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正如在每个学科的源头曾经融为一体那样,只有融合、交流和对话,才能求得创新和发展,从而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和革命。
二、经济学与社会学
寻求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自然是经济学者和社会学者之间的事情,然而,归根到底还是由两个学科的性质所决定的,也就是说,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对话的可能性,而探讨这种可能性,又不得不对其各自的学科定向历程作一检讨。
现代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一般公推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A.Smith),因为他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般简称为《国富论》)(1776)中所论述的经济问题构成了现代经济学诸领域的源头。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all,1842—1924 )在其著作中冠以《经济学原理》标题,被认为是首次使用“经济学”(economics )作为学科名称。如果说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的祖师,那么,马歇尔就是现代经济学的直接奠基人。之后,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建立了“厂商理论”,初步确立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凯恩斯则建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从此,主流经济学以其完整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大理论体系而确立了其社会科学中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地位。
相形之下,现代社会学的历史似乎要比现代经济学逊色一些。首先是作为其祖师的奥古斯特·孔德,不仅生年较晚(1798),没有赶上亚当·斯密时代,而且其著作主要的不是社会学著作,没有像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那样为后世的社会学者奠定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寻根体系。孔德之于社会学的最大贡献在于命名了“社会学”这个学科。按照英国《大英百科全书》的说法,是“为社会学研究争得了地盘,预告了社会学研究的到来,而并非创立了社会学”。(注:转引自刘豪兴主编:《国外社会学综览》,第5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虽然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经验的研究都起源于欧洲,但将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并加以发展的,最早也是最重要的还是在美国。第一次将社会学列为大学科目的是萨姆纳(W.G.Sumner)。他于1874年在耶鲁大学首次开设社会学课程。斯莫尔(A.Small)与人合编的《社会研究导论》(1894),被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学教科书。索罗金(P.Sorokin)不仅推动了社会学研究的发展,还直接影响了后来成为国际社会学界权威人物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之久的帕森斯(T.Parsons)。帕森斯的主要成就是创立了结构功能主义和社会系统分析。到1949年国际社会学会成立,社会学研究已确立了自己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此后的社会学研究基本上和先驱者的研究相对应而发展,如在马克思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冲突理论,在涂尔干基础上发展的结构功能理论,在斯宾塞基础上发展的社会变迁理论,在韦伯基础上发展的解释社会学及在齐美尔(G.Simmel)基础上发展的微观社会学等。
从经济学与社会学各自学科发展的定向历程中可以看到:
1.社会学的起源晚于经济学的起源。以各自的学科祖师而论,亚当·斯密要比奥古斯特·孔德早半个多世纪,斯密的《国富论》比孔德的《实证哲学教程》(以第四卷出版的1839年为准),早63年。这种起源的时间早晚对各自的学科发展是有影响的。
2.学科发展脉络和主流体系不同。经济学由斯密而始,经马歇尔的综合,发展为现代经济学,其学科发展脉络十分清晰,作为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经济学业已形成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相比之下,虽然许多研究领域上,现代社会学仍有其源流脉络,但并未形成一种统一的理论体系或范式。
3.学科界限的划分和清晰化。在社会学起源的19世纪乃至以前的历史,经济学与社会学并没有绝对的界限,如马克思既是经济学家又是社会学家,亚当·斯密也被认为是“社会科学家”;涂尔干研究的劳动分工问题是斯密理论的一个命题,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问题;马克斯·韦伯既研究社会又研究经济,等等。但本世纪以来,在非主流经济学中仍能看到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研究,但在社会学领域,在帕森斯之前,有关经济问题基本上被摒弃于社会学体系之外。究其原因,据说与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美国的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有关。社会学者试图和经济学者竞争大学的位置,结果遭到惨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社会学也因此而获得“剩余科学”的称号(注:参见李猛、李放春:“新经济社会学与中国”,载《社会理论论坛》,1997年第2期。)。
“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学”
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定向历程看,两者之间似乎颇有点竞争的意味。从孔德为社会学“争得了地盘”,到沦为“剩余科学”,一方面是社会学发展了自己学科,逐渐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另一方面与经济学的学科范围藩篱筑就,分界线就在于是否“剩余”。
然而,这种学科藩篱的筑就带有强烈的人为色彩,而且是学科体系化后相互敌视的结果。事实上,作为社会科学的两个分支,作为对人类行为进行研究的不同学科,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在古希腊的文化遗产中,两者之间难分你我,相互耦合,而即使是现在,仍有诸多共同或共通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正如熊彼特所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注: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9页、第41页、第48页, 商务印书馆,1991年。)。正因为有这层关系,所以,尽管作为两个学科,“自18世纪以来,两部分人在不同的道路上都在稳步发展,直到现在,典型的经济学家与典型的社会学家对于对方在做些什么都知道得很少,而且关心得更少;每一方都喜欢各自用他们自己粗浅的社会学与粗浅的经济学知识去接受对方专业上的成果——这种情况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由于相互咒骂而有所改善”(注: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9 页、第41页、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但是,仍有一些学者试图致力于两个学科的沟通、交融和对话,这使“经济与社会”领域得以形成,也使来自两个学科研究交叉的新学科——经济社会学与社会经济学——得以形成和诞生。
按照字面上理解,“经济社会学”(economic sociology)应当是一门社会学的分支学科,是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的学科;同样,“社会经济学”(social economics)应当是一门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是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社会问题的学科。然而,就学科名称的早期使用看,似乎情况并非如此,既有使用“经济社会学”的经济学者熊彼特,又有使用“社会经济学”的社会学家韦伯。熊彼特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经济分析史》中就使用了“经济社会学”这一学科名称;而韦伯则在其未完成的原著《经济与社会》中使用了“社会经济学”这一学科名称。(注:《经济分析史》是熊彼特在其人生的最后九年撰著并最终未完成而由其夫人伊丽莎白整理、编辑出版的多卷本遗著。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经济与社会》则是韦伯从1910年开始到1920年去世期间进行的《社会经济学》(Sozialokonomik)研究系统的未完成稿,由其遗孀整理于1922年出版。《经济与社会》也被认为是误置的书名,原名应为《经济、诸社会领域及权力》。参见甘阳,“韦伯研究再出发”,载韦伯著:《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第2页, 三联书店,1997年。)这与今天我们使用这两个学科名称时的理解恰恰相反,颇为耐人寻味。
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一词,是为了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按照他的看法,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有四门,分别为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熊彼特的“经济社会学”更类似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他所强调的仍是经济学的研究,即使是对社会学研究本身,他也是在“社会科学”意义上理解的。他说:“对社会学我们将采取狭义的解释,指一种单独的、但成分远远不是很纯的科学;……比较广泛地说,它指互相重叠、互不协调的整个社会科学而言——而社会科学是我们愿意采用的一个名词。”(注: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9页、第41页、 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也并非试图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问题,尽管在其《经济与社会》一书中,大量的篇幅讨论了社会学的问题(注: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7年。)。他之使用“社会经济学”可能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是“政治经济学”时代的后期,如前述,到19世纪末“政治经济学”开始为“经济学”所取代,这主要发生在英美。而在德国,则更多地并行使用另外一个名词,即“社会经济学”。而韦伯又被认为是“比较出力使它推广使用”的学者(注:参见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第49页、第41页、第48页,商务印书馆,1991年。)。
其实,无论是熊彼特还是韦伯,之所以使用和今天理解不同的学科名称,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同被誉为“社会科学家”的综合性特征。他们之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和今天的意义也是不同的。熊彼特的经济理论具有历史性,具有社会洞察力,是一位名符其实的“社会科学大师”;而韦伯因其宗教研究而被称为社会学家,但其背景却是经济学,还写过《经济通史》的巨著。
所以,尽管熊彼特和韦伯分别使用了“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的名称,但他们都是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
“经济学帝国主义”、“社会学帝国主义”与新经济社会学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之所以有“经济社会学”、“社会经济学”之名而难有其实,另外一个原因是,无论是经济学还是社会学均尚未形成足以作为方法来分析其他学科领域的独立的体系。而这一体系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基本形成或成熟。
到50年代,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学已经达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尽管在经济学内部,这时已分化为以萨缪尔逊( P. A.Samuelson )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或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和以琼·罗宾逊为代表的“新剑桥学派或凯恩斯左派”,但是,在经济学能解释社会经济现象或人类行为这一点上,看法并无不同。也正是从这时起,以加里·贝克尔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开始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于“非经济”领域。这样做的理由,如莱昂纳尔·罗宾斯(L.Robbins)的经典论述所阐明:
“人类任何一种行为都落在经济学的概念范围之内。因此我们不认为马铃薯的生产是经济活动而哲学的生产不是经济活动,相反,我们认为,就两者中任何一种活动都涉及到放弃其他合意的选择来说,都有其属于经济活动的一方面。除此之外对经济学的论题没有限制。”(注:参见L.Robbins,1930,The Nature and Signifisance of EconomicScience,London:Macmillan,P17.)
基于上述认识,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如贝克尔就先是分析歧视问题,后是分析人力资本问题、生育问题、婚姻家庭问题、时间价值问题、犯罪与惩罚问题、社会相互作用问题等。(注:参见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3年。)。这种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被称为“加里·贝克尔革命”(注:参见勒帕日:《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如果说“加里·贝克尔革命”是一种对“非经济”领域的经济学革命,那么,由凡勃伦(T.B.Veblen )等人的非主流制度经济学脱胎而来的新制度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70年代以来的崛起,则可看作是对经济学本身的革命。这种革命也被看作是“经济学的社会学化”。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学内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同时为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奠定了基础。
进入20世纪以后,社会学的研究中心开始由欧洲转向美国,而美国社会学,在30 年代以前以芝加哥学派的经验研究为主流。 当帕森斯于1937年发表了《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之后,美国社会学很快迎来了“帕森斯时代”。而恰恰是帕森斯本人,对经济问题颇感兴趣,早在1932年就曾著有《经济学和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一书,到50年代还和他的学生斯梅尔瑟(N. Smelser )合著了《经济与社会》(1956)一书(注: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在该书中,帕森斯试图应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来分析经济问题。后来,斯梅尔瑟又作了进一步发展,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注:帕森斯和斯梅尔瑟:《经济与社会》,华夏出版社,1989年。)。在该书中,斯梅尔瑟详细讨论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个方面,并试图形成“经济社会学”学科。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引起经济学者的积极反应。其原因可能与帕森斯等人采取的“社会学帝国主义”立场有关,即在其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中,经济只是其一个子系统。又由于分析的概念体系并不与主流经济学相一致,这样,也就很难取得平等的对话和沟通。即使是经济社会学内部,虽然有独立的学会,但参加者不多,活动也不够活跃,因而学科发展并不快,其原因是,帕森斯一开始已指出过,到富永健一时仍是主要问题的学者知识构成问题,即“大部分经济学者不懂社会学,大部分社会学者对经济及经济学既缺乏知识又不甚关心”(注:参见富永健一主编《经济社会学》,第5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
这种情况一直到80年代中期才开始改变。1985 年格兰诺维特(M.Granovetter )发表的“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一文(注:参见M. Cranovetter, 1985,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edness",American Jourral of Socialogy,(91).)既引起了社会学界的震动,又引起了经济学界的反应,并引发了以“新经济社会学”(new economic socialogy)为核心的研究热潮。格兰诺维特的论文实际上是对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一些前沿课题的社会学参与,这些课题包括:什么样的交易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在市场中实现的?什么样的交易被纳入根据等级制组织起来的厂商?等等。正是对经济学者关心的问题的直接参与,使得社会学者与经济学者的平等对话得以实现,并使新经济社会学在90年代成为国际社会学界最为活跃、 最富于成果的一个分支(注:参见 N.Smelser and R. Swedlberg, eds,1994,The Handbook of Economic Socialog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作为一种肯定的标志,经济社会学的先驱者之一斯梅尔瑟于1997年当选为美国社会学会的主席。
至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不仅必要和可能,而且正在成为现实。
标签:经济社会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社会学论文; 帕森斯论文; 理论经济学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微观经济学论文; 韦伯论文; 中国社科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