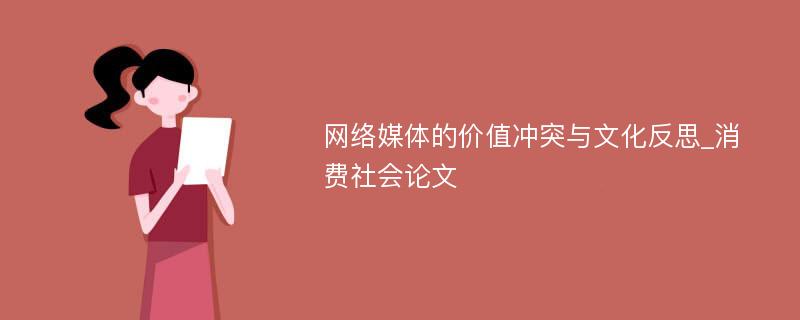
网络媒体的价值冲突与文化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网络媒体论文,冲突论文,价值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16)04-0098-08 DOI:10.15937/j.cnki.issn1001-8263.2016.04.014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高度结合,使网络文化成为社会文化最主流、最直接的表现形态,马克·迪由泽(Mark Deuze)将网络文化视为数码文化,他认为,世界从19世纪的印刷文化过渡到20世纪的电力文化,再到21世纪的数码文化。随着接入互联网的电脑普及,一种新的数码文化正加速和增强,数码文化被认为是一套正在崛起的观念、行为和对人们应该如何行动并与当代网络社会互动。数码文化已经在线上线下扎根,并且产生了即时的影响,特别改变了我们对网络环境的意义。①网络化生存所带来的巨大影响,已对整个社会的深层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随着媒介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加快,网络对传统媒介的兼容更为明显。由于网络生产与消费界限的模糊,对于一般网民而言,上网更多地体现为消费行为,网络消费与日常消费的融合趋势非常明显。尤其是随着网络购物、网络游戏的流行,网民更多地通过网络实现自己的消费意愿,网络消费对网民的消费观念、价值取向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日常生活的网络化势必对网民、群体和社会带来多重的影响,尤其是在价值观方面的冲击极为明显。网络社会所引发的诸多矛盾和问题,也主要体现为网络价值观的冲突与困惑。 一、网络主体与客体的矛盾 网络媒体尽管在技术上超越了传统媒体,但它仍然是一种先进的技术工具,是人类运用电子技术的集中体现,也是折射现实社会的基本客体。因此,网络文化本质上是当代文化的基本内容和载体。网络本身不能创造文化,网络文化的生成与传播离不开人,人是网络文化的主体。 然而,随着网络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网络化生存已成为网民证实自我的主要方式。人们进入网络空间时,物理上的身体并不需要随之移动,这样一来,人们在可见的物质空间之外,又觉察到一个多维度的心灵空间的存在。心灵摆脱了物质的束缚,找到了想象交互的新天地。②而网络文化则成为后现代文化的基本表征。网络信息泛滥不但没有使许多网民保持应有的理性,却让许多网民在对传统的消解中寻求信息崇拜。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与信息组成的无深度的网络世界中,“在破碎的符号与影像的轰炸下,个人的认同感垮掉了,因为这些符号将过去、现在和将来之间的连续感统统抹掉,并打倒了所有相信生活是一项有意义事业的目的论信仰。”③应该看到,网络社会中个体与网络的主客观关系具有很大的变异性。尤其是网民对网络高度迷恋和盲从的情况下,网络符号价值与人的价值之间的矛盾显得尤为突出。 按照麦克卢汉的说法,媒体是人体的延伸。人体则是媒体的生存前提。没有人的主体性存在,任何媒体的作用都无法发挥。在印刷媒体时代,书籍和报刊媒体是被“观看”的对象,人们读书看报以自我为目的,并与文字保持着适当的距离,阅读是一种具有逻辑性、连续性、记忆性的过程,阅读本身能够带来身心的愉悦和思辨的火花。因此,对于纸质媒体的翻阅具有回溯与反思的价值。但是,在网络浏览状态下,“我”是一个“流浪者”,在网络世界中,信息共享促进了消费民主,却使“我”的差异性存在遇到了极大困难。作为新型的“生产型消费者”,“我”生产并消费信息,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我”收集到海量的信息,但是,对于信息的“主人”却无须考究。“我”可以占有媒体的物质形态,却对信息本身无从把握。 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言,现代性是一个从起点就开始的“液化”(liquefaction)的进程。④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也是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网络信息的瞬息万变和漫无边际,使任何个体在信息的汪洋中都难以保持“恒定”。由于上网是一种“心情涣散”的行为,网民很难集中精力对信息进行精读和反思,更谈不上“沉思默想”。因此,网民在网络上的游走与飘移,表现出自我的“无根化”生存的状态,网络信息的轰炸与意义获取的困惑成为持久的矛盾。上网时自我的缺失与现实中自我的焦虑形成鲜明对比。生活在不确定世界中的人,在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在都市化、全球化的流浪、归属感的淡化中,在权威的不断消逝、身份感不断模糊中,深陷于“我是谁”的追问。⑤网络依存度与个体的围困感有着内在的关联,在网络消费欲望的刺激下,个体的身体被外界的诱惑所迷惑,变得焦虑而困惑。“身体,尤其是它的适应性,正经受着多方的威胁。然而人们却无法安全地加强自我以对抗这些威胁。”⑥ 在网络社会,个人价值与网络价值的分裂已成为突出问题。一方面,网民通过网络体现自我和发展自我的诉求非常强烈,在1990年代,网络提供的科技信息查询和学习功能较为强大,许多知识分子通过网络进行写作和研究,网络在传递知识和文化方面的功能得到了较充分的发挥。但是,随着Web2.0时代的来临,网络的互动和交流功能不断放大,网络娱乐、游戏、购物等方面的需求也日趋强烈,网络偏向于满足消费欲望和互动交流,这就极大地解放了网民的自我需求。由于网络消费主义的影响,传统礼仪难以发挥文化聚合和社会信仰的作用。对于消费主义者而言,网络购物天堂远比礼仪殿堂重要,人与物的关系远比人与上帝(神)的关系重要。在网络社会,仪式已改变了原初意义,其宗教信仰的功能正在日益缺失。霍尔(John R.Hall)和尼兹(Mary Jo Neitz)指出:从超时空的角度说,仪式定义最重要的内容是,它们是标准化的、重复的行动。在现代世俗社会,远离赋予传统仪式以意义的文化背景,仪式就不仅是标准化的、重复的,而且还是毫无意义的。⑦尽管网络社会将仪式赋予日常消费活动中,尤其是在商业文化礼赞中,各种网络庆典和消费场景极为壮观。但是,这类带有明显消费导向和功利目的的营销活动,已经远离了仪式的本质内涵,此类仪式难以让参与者得到精神洗礼和价值观的认同。从某种程度上看,这类经过商业包装的“伪仪式”恰恰是消费主义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 在网络社会,许多网民沉醉于自我享受,对公共生活和集体活动漠不关心,对“他者”缺乏应有的信任,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他们以不断“购买”和“消费“证实自身价值。他们以商品拜物教和信息拜物教寻求精神寄托,对日常仪式和文化传统视而不见,他们在自我解放中放弃了对“社会共同体”的追求。他们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好自我表现,伪装成饱学之士却没有公共关怀精神,这就是消费主义者与现代犬儒主义者的杂糅。贝维斯(Bewes,T.)指出,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有唯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背叛了崇高的价值,而对于这些价值领域而言,真理和诚实的抽象化比行为和想像的政治品格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⑧与魏晋名士沉溺宴饮、寄情山水的心境不同,现代犬儒主义者是在丰裕的消费社会中出现的,他们无处不在,如那些沉迷于肥皂剧、商品广告、汽车旅馆、子夜舞院、好莱坞B级电影、机场的平装惊险小说、名人传奇、浪漫小说的人完全可能是犬儒主义者。现代犬儒主义是新的拜物教形式,传统拜物教建立在行为者对自己行为意义的“非知”之上,是有待启蒙的幻想,而新的拜物教则是启蒙了的或后启蒙的意识形态。⑨在网络空间,现代犬儒主义者明知理想、信仰和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他们都接受了现代启蒙,但是,他们在行为上却在反启蒙,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方式,已成为他们构建犬儒主义意识形态的表征。⑩ 在网络世界,由于身体的不在场,这更使得原本就难以“相遇”或“重合”的心灵与身体之间的距离拉得更大了,从而降低了人际间身心近距离交流的频率。(11)网络上飘移的虚拟自我在脱离了身体控制之后,变得没有主张、没有中心、成为了一个情绪的多元体,是本能、欲望、权力、力量、激情、情感的混合。无深度感代替了形而上的追求,碎片化代替了整体性,颠覆代替了建构。(12)游走在网络之中的虚拟个体,由于孤单、焦虑和对自我呈现的迫切需求,将网络社交作为体现自我价值的最重要途径。在Web3.0时代,网络已经将社会引向大暴露主义时代。网络实现了对人的全天候监控,已经从一个非个人数据库转变为一个公开播报人类意向和个人品味的全球数字大脑,今天的网络产品和服务,让我们的朋友能够准确地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想什么、读什么以及看什么和买什么,它们正在为我们大暴露主义的超知名度时代提供动力。(13)显然,网民在网络上的展演和社交,是力图证实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但是,网络却将每个网民作为可以出售的数字化商品,对网民进行了全景监控。而网络上的虚拟自我与身体的分裂,使“凝视”成为一种稀缺资源,网民对现实交往的疏离加剧了网络社交的“伪装性”。许多时候,网民是在“向网络说话”,每个人都在喋喋不休,但是没有多少人愿意在网络中静心倾听。虚拟的身体离真实的情感越来越远,而虚拟的网络却对网民的控制越来越紧,人机对话已经演变为人机分裂,体现出网络社会主客体关系的悖论,“主体失落于外与主体封闭于内同时并存。”(14)一方面是网络实现了对人的支配,另一方面人却在网络化过程中进一步走向内心的孤独和封闭。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紧张和矛盾已成为网络文化建设中的一大突出问题,从而影响到网络价值的建构。 二、网络空间与时间的裂变 时间与空间是哲学的核心概念,也是哲学家所苦苦探求的意义所在。康德认为:吾人由外感(心之一种性质),表现对象为吾人以外之事物,且一切对象绝无例外,皆在空间中表现。对象之形状、大小及其相互关系皆在空间中规定……故凡属心之内部规定之一切事物,皆在时间关系中表现。(15)时间规定了先后,表明了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关系,是人确定存在的基本形式。海德格尔指出: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根植于这种时间现象。(16)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是已经发生的新闻”,便是从时间概念来说明新闻与历史的关系。对于一般媒介而言,都具有时间和空间两个面向。根据网络媒介的属性,它是偏向于空间的,而且是全球性的空间。对于由电脑组成的网络空间而言,每个机器之间的距离都一样,除了地球本身的范畴之外,电脑空间完全没有物理边界。(17)梅洛-庞蒂(Maurece Merleau-Ponty)甚至将身体本身视为空间,他指出:“我的身体在我看来不但不只是空间的一部分,而且如果我没有身体的话,在我看来就没有空间。”(18)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网络对批量信息的空间传播更是难以想象。由于网络传播的全球化和即时性,人们对“地域”的概念已经淡化,网络创造了新的媒介景观,“打破了物理场景和社会场景的传统关系”(19)。因此,网路媒介不仅仅是偏向于空间,而其本质上就是表现为“信息场景”,是以空间上的绝对优势而体现其存在的价值。 网络空间对时间的高度挤压,使时间的价值变得越来越边缘,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研究网络社会的特征时指出:在更深的层次上,社会、空间与时间的物质基础正在转化,并环绕着空间和无时间之时间(timeless time)而组织起来。……无时间之时间似乎是在流动空间的网络里否定时间的结果,不论是过去或未来。(20)网路空间的无限扩展与时间的高度浓缩形成强烈的反差和矛盾,对于网民而言,在网络空间的自由漫游固然是对身体的极大解放,但是毫无目的的浏览却使时间的价值被严重消解,网络时空的断裂现象较为普遍。 时间的价值在工业社会被高度重视,“时间就是金钱”意味着单位时间具有衡量效率的意义。芒福德(Lewis Mumford)认为,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不是蒸汽机,而是时钟。在时钟发展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是机器的出色代表,也是机器的典型符号。(21)正是有了时钟的记录,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才能保持正常秩序和纪律。在时钟的作用下,抽象的时间成了新的显示存在的媒体,它调节有机体本身的功能,何时吃饭,不必等肚子饿,而是让钟表告诉我们;何时睡眠,不必等困了,而是由钟表来加以确定。(22)时间规定了序列和先后,对个体的自我管理起到关键性作用。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在“时间中存在”这种意义上,时间充任着区分存在领域的标准。(23)在网络社会,由于网络空间的去边界化和去中心化,时间被打破社会实践的序列,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顺序可以逆转,通过打乱事件的序列并促使事件同时发生,流动空间消解了时间概念。(24)因此,网络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刻意让个体“忘记”时间,网络对时间的占有不仅体现在身体的“缺场”,更多地表现为个体对空间的盲从。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对工作、生活乃至娱乐都设定了时间,但在网络世界,个体却有意无意地抛弃时间,对时间的流逝没有“间距”上的关注,上网本身就是“此在”,至于“我”在何时何地,则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如果说,个体的过程性体现了存在与时间的关系,那么,与他人的共在则体现了存在与空间(社会空间)的关系。(25)无论是从时间还是空间的维度看,存在都是基于“生活世界”的“此在”。但是,网络空间将个体幻化为虚拟的自我,将“此在”转变为虚拟的存在。这就导致个体的身心分离,并过度依赖虚拟的“我”来表达存在。由于身体的不在场,网络空间的自我往往与思想分裂,对现实生活需要由时间限定的规则和秩序进行颠覆,虚拟自我过度依赖空间进行展演。尤其是随着社交媒体的普及,许多网民在多个社交媒体拥有不同的身份,以不同的“姿态”与“他者”交流,其交往动机体现出以我为中心的目的。网络空间充满了无穷的“邂逅”,与陌生人的虚拟交往可以抛开现实的道德和规则,个体在无限度的话语游戏中可以忘却现实,可以忽略时间,可以放纵身体。虚拟空间似乎可以容纳个体的一切,尤其是类似“精神走私”现象,体现出网络中个体展演的“伪善”,一些网络大V发表的各种言论,往往利用“仪式”的赋权功能对某些事件进行操作,引发网民的关注与参与,从而达到提高自身知名度和进行商业营销的目的。显然,网络空间虚拟自我的高度张扬,与对时间的挤压和身体的放纵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看,“所谓新自由主义的网络空间,是一个充满脆弱和剥削的高压空间。”(26) 网络空间对虚拟化生存的高度张扬,使网民往往容易通过脱域(Disembeding)进行无限穿越,相对于真实的存在,网民更愿意用符号化的象征标志(Symbolictokens)(27)来证实虚拟的身份。在以个体需求为导向的网络空间,每个人都在创造“真理”,每个人的“真理”都和其他人的“真理”一样正确,Web2.0革命不但没带给我们更多的知识、文化和共同体,反而带来了更多由匿名网友生成的不确凿的内容,它们浪费了我们的时间,欺骗了我们的感情。(28)网民以对网络空间的强烈欲求来抵制对现实时间的合理分配,网络空间的“任性”与现实生活中的“无聊”形成极为强烈的反差。在网络空间中,网络更多的是“说话”,而不是对话,而对话是捕捉人的心灵和思想的最好方式,“透过对话,我们得以用最接近实际心灵活动的方式呈现出我们的思想并与人沟通”。(29)但是,网络民主的口号培养了更多的“骂民”,“骂完即走”成为“发帖者”的常见心态。因此,尽管网络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但是,由于缺乏广泛的自律和协商精神,网络上很难产生共识,哈贝马斯式的公共领域更是难以建构。而网络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挤占,使网民面对面交流的时间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广泛使用,使许多网民宁愿“向网络说话”也不会对身边的人“开口”,在拥挤的人群中,大家都在赶时间,但是,低头看手机却意味着虚拟空间更为重要。对于“低头党”而言,眼神交流的时间不是没有,而是“不愿”。网络空间与现实时间的断裂已严重影响到网民的身心健康,也极大地消解了网络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 三、网络技术与伦理的冲突 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将文明分为三类,技术运用文明、技术统治文明和技术垄断文明。(30)而网络则是技术垄断文明时期的最重要的标志,网络技术以二进制信息处理技术为基础,融数字存储、数字编辑、数字网络和数字表现技术为一体,网络媒体是数字技术应用的最重要载体。中国从1994年引入国际互联网之后,数字技术对新闻传播业产生了一次深刻的变革。在1990年代,报刊媒体首先利用网络开拓新闻传播的新平台,传统媒体的网络版改变了读者的阅读方式,引发了阅读革命。而数字技术的商业化促进了商业网站的崛起。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就基本与全球保持同步,大致经过了互联网1.0阶段(Web1.0)、互联网2.0阶段(Web2.0)和即时网络的互联网3.0(Web3.0)阶段。在Web1.0时代,我们体验的是信息总量剧增之时,人与信息之间的连接。Web2.0时代,我们体验的是网络社会形成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推动了社交媒体的发展。Web3.0时代,我们要体验的是物质世界与人类社会的全方位信息交互,感受人与物质世界的联接。尤其是随着微博、微信的广泛使用,传统的人际传播已走向大众传播,自媒体的发展使数字技术无处不在,近年来,移动互联网、智能便携终端、云计算形成千姿百态的信息服务,改变信息交流的结构与模式,从而使新闻传播的提供方式、社会关系的经营方式、社会结构的演进方式发生革命性改变。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我国媒介融合的趋势不断加快。传统媒体利用网络、手机平台大力拓展发行渠道,强化内容生产和拓展传播业务,新旧媒体共享数字技术的成果,网络、媒体、通信三者“大融合”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化媒体、移动终端、大数据成为新媒体发展的趋势,全媒体技术强化了新闻传播的即时性、交互性与共享性,从网络新闻到数据新闻的发展,体现了新闻形态、内容和模式的巨大变化。全媒体、人与社会的互构一方面提高消费者作为“高贵的业余者”的主体地位,正是因为如此,人们对网络技术产生了膜拜的情结,将网络视为无所不能的机器。正如波兹曼所言:技术垄断是一种文明形态,也是一种思维状态。技术垄断在于对技术的崇拜和神化,即文明在技术之中寻找权威,寻求满足感,建立起自身的秩序。这就要求创建新型的社会秩序,并且必然导致与传统信仰相关的事物急速瓦解。最能适应技术垄断时代的人坚信,技术进步是人类的崇高成就,技术工具能够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最艰难的困境。这些人还相信,信息是一种纯粹的福祉,生成并传播连续不断、不受管控的信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自由、创意和心灵上的平静。(31) 由于网络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更加相信网络的全能作用,尤其是新经济形态对大数据、电子商务、移动终端的大力鼓吹,使“互联网思维”作为体现技术文明的新方式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现实生活的确定性不一样,网络技术容易让人产生“沉浸”感。正如莫斯可(Vincent Mosco)所言:网络空间不仅是迷思上演的地方,它同时也促进今天的迷思性思维方式。因为它体现了一种模糊意识(或者更正式的说,是文化理论家所说的阈限(Liminality)。它们表达了一种既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的意识,一种将某些事物抛在后面,但又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相关的意识,一种获得新事物,但又无法被清晰定义的意识。(32)然而,正是由于对网络新世界迷思的坚定信仰,许多网民不断寻找网络技术所提供的灵丹妙药,努力使自己在迷思中获得社会认同,因此,网络技术提供了新的“脱域”机制,使人们坚信在网络迷思中能够寻求价值的源泉。 网络技术对信息共享、公平自由理念的灌输,很容易让人们产生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对于芸芸众生而言,如果能够在网络空间摆脱现实的困惑,重建新的自我,这无疑具有宗教式的救赎作用。但是,资讯本身并没有启蒙的作用,因为在这个媒体主导的社会中,我们很难辨明什么是错误的资讯、反资讯或宣传。只注重资讯的结果是过度累积了意义愈来愈稀薄的资料片段,而不再寻求有意义的知识模式。(33)网民对网络技术和信息无所不能的盲目崇拜,并使网络进一步监控了网民的身心,凯文·凯利(Kevin Kelly)描述了网络技术盲从者的心态:“我们将听从技术,因为我们现代人的耳朵再也听不进别的。再也没有坚定的信仰。”(34) 显然,使人成为机器并不是人性的体现。当人被技术奴役之后,人的存在价值就无法得到体现。由于长期在网络环境下工作所导致的眼疲劳、手腕关节疼痛、精神焦虑、反应迟钝等慢性症状,却对网民的身体健康造成了极大危害。而网民对信息自由和信息价值的盲目追求,推动了博名效应的爆炸式增长,尤其是社交网络对一夜成名的宣扬,使许多网民将暴露隐私作为最大的卖点。无论是自己、家人、朋友还是陌生人,隐私已经成为可以公开出售的商品,且技术成本几乎为零。因此,寻求超级知名度便是网民社交的重要目的,网络“声望经济”已发展成为新兴的重要产业,商业网站对用户的需求了如指掌,网民的资料成为网络全景数据库的重要来源。在那些高呼平等自由、倡导公平开放的阵营里,声音最大、气势最强的正如谷歌、微软、百度、腾讯这些超级巨头。然而,往往被爆出侵犯用户隐私的、被指责思想保守不愿意公开自身数据的、被卷入反垄断调查的,也是他们。(35)网络技术的垄断巨头们将网民作为新兴的商品符号进行交易,但在技术符号层面,形式上的民主、自由、平等却充满了魅力。体现了网络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体面”与“装饰”。然而,其思维体系缺乏卓越的叙述手法,因此既无法提供道德支柱,也缺乏强有力的社会控制,以管制技术产生的“信息洪水”。(36)“大暴露时代”使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窥探和被窥探的对象,从而丧失了自我保护能力,也使整个网络社会的伦理秩序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但是,“我”者的存在如果连基本的隐私和安全感都没有,网络化生存又有何价值而言。 网络技术的无限制运用还对信息安全带来了极大挑战,计算机黑客行为造成的巨大损失和心理恐惧,尤其值得高度关注。由于网络技术的普及,当黑客也越来越容易,黑客们在缺乏道德约束的情况下,可以轻易地闯入计算机系统,肆意破坏系统的运用,窃取和损毁各种数据,造成电脑瘫痪。然而,这些破坏的行径往往是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的,黑客可以随处游走,不断制造入侵行为,却很难被发现,更难以遭到法律的惩罚。 由于许多网络技术的运用缺乏明晰的产权边界,网络产权的保护极为困难。许多网民对传统媒体环境的抄袭和盗版行为有一定认知,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复制、抄袭、转发和改编的现象已司空见惯,网民可以使用简易的技术手段便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收益,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网络作品的粗制滥造。许多“作者”不愿意去思考,也不想查阅原文的来源,随手可得的资料和软件,满足了使用者的私欲和私利,许多网民对各种偷窃和盗版行为津津乐道,却很少从道德层面加以反思,更不愿意对获取的知识进行深度“加工”。盗版、复制和抄袭的目的是满足当下的消费,在快速地获取之中,许多网民强化了对网络信息的“掠夺”心态。 值得指出的是,网络传播技术推动了“全息社会”的发展,全媒体消费社会极大提升了信息经济和传媒产业的作用和地位,媒介融合进一步推动了传媒业的转型升级和管理变革。但是,由于“新闻把关人”的逐步缺位,网络工具理性的高度膨胀,导致了新闻业价值理性的严重缺失。媒体与受众比较容易塑造“意见气候”,新闻真实性与客观性难以得到保障,网络消费主义的盛行导致网瘾、网络购物症、孤独症等问题较为突出,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缺失导致社会信任度下降和谣言的泛滥。网络自由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思潮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网络“伪公共领域”现象对公共价值观培育也极为不利。 可见,网路技术的传播全球化本身是一把“双刃剑”,它一方面促进了媒体文化的共享与互动,促进了传播技术的发展,也为中国新媒体新闻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文化殖民与文化堕距等问题。随着西方传媒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中国媒体内容建设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城乡、地区间的数字鸿沟不断加深,各种网络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观念不断流行,主流新闻价值和文化观念同时面临被各种亚文化“收编”的危险,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新闻商品化与产业化的趋势不断加强。西方文化尤其是消费主义文化日益流行,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与作用则有不断弱化和消解的趋势。因此,对于网络技术的进步,我们需要从其价值理性的角度进行全面思考。正如福山所言:技术能否改善人类的生活,关键在于人类道德能否同步进步。没有道德的进步,技术的力量只会成为邪恶的工具,而且人类的处境也会每况愈下。(37)从这个意义上看,网络技术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而网民的道德水准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和前提。 心理学家荣格(Carl G.Jung)认为,唯有对现代最具有感知的人才是现代人,唯有一个不但超越了属于过去的意识阶段,而且完全履行了世界所指派给他的义务的人,才可能达到充分现代的意识境界。(38)从这个层面上看,许多网民虽然掌握了上网的技术,但未必能够认识网络社会的基本特征,他们过分沉溺于自我的世界,只关注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将网络视为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展演舞台,对网络谣言、盗版、欺诈、色情等现象习以为常,不关心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权益,对社会公平正义和道德伦理置若罔闻,此类网民显然是“伪现代人”,与现代公民社会的要求格格不入。面对网络社会的价值迷思,网民应该以理性、科学、文明的态度进行全方位思考,不断提升自身的网络素养,在网络主体与客体、时间与空间、技术与伦理之间寻求价值理性,成为网络社会的真正主人。 ①Mark Deuze.Participation,Remediation,Bricolage:Considering Principal Components of a Digital Culture,The Information Society,Vol.22,2006,p.63. ②黄少华、翟本瑞:《网络社会学—学科定位与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③[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杨渝东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2页。 ④[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页。 ⑤吴玉军:《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7—58页。 ⑥[英]齐格蒙特·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道德》,郁建兴、周俊、周莹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34页。 ⑦[美]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周晓虹、徐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97页。 ⑧[英]提摩太·贝维斯:《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胡继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⑨汪行福:《从商品拜物教到犬儒主义——齐泽克意识形态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3期。 ⑩蒋建国:《消费主义文化传播、仪式缺失与社会信仰危机》,《现代传播》2012年第4期。 (11)唐魁玉:《网络化的后果—日常生活与生产实践的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页。 (12)吴玉军:《非确定性与现代人的生存》,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52页。 (13)[美]安德鲁·基恩:《数字眩晕》,郑友栋、李冬芳、潘朝辉译,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0—41页。 (14)杨国荣:《认识与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15)[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蓝公武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51页。 (16)[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2页。 (17)[美]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范海燕译,海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79页。 (18)[法]莫里斯·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0页。 (19)[美]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页。 (20)[美]纽曼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40页。 (21)(22)[美]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陈允明、王克仁、李华山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15、17页。 (23)[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21页。 (24)[美]纽曼尔·卡斯特主编:《网络社会:跨文化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25)杨国荣:《认识与价值》,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6)Kym Thome.Cyberpunk-web 1.0 "Oegoism" Greets Group-web 2.0 "Narcissism":Convergence,Consumption,and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Divide,Administrative Theory & Praxis Vol.30,No.3,2008 p.299. (27)象征标志和专家系统是脱域机制的两种类型,在吉登斯看来,象征标志指的是互相交流的媒介,它能将信息传递开来,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见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28)[美]安德鲁·基恩:《网民的狂欢: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丁德良译,南海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16页。 (29)(33)[美]理查·伍尔曼:《资讯焦虑》,张美惠译,台北时报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87、45页。 (30)(31)[美]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蔡金栋、梁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19、66页。 (32)[加]文森特·莫斯可:《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与赛博空间》,黄典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1页 (34)[美]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肖华敬、任平译,广州出版社2000年版,第225页。 (35)黄升民、刘珊:《“互联网思维”之思维》,《现代传播》2015年第1期。 (36)[美]波兹曼:《技术垄断:文明向技术投降》,蔡金栋、梁薇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第74页。 (37)[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页。 (38)[瑞士]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寻求灵魂的现代人》,黄奇铭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209页。标签:消费社会论文; 虚拟商品论文; 消费文化论文; 虚拟网络论文; 虚拟技术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网络空间安全论文; 文化冲突论文; 信息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