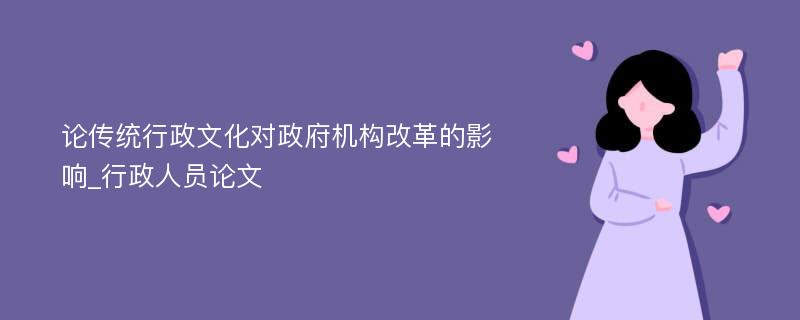
论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论文,行政论文,文化论文,政府机构改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行政文化是行政体制的深层结构,是行政管理的灵魂。行政文化通过行政人员的思想意识影响着行政实践。发轫于夏、商、周三代,定型于两汉,因袭发展于隋、唐、宋、元、明、清各代,横贯数千年经久不衰的传统行政文化,虽然在当代遭到西方行政文化的强烈冲击,但仍以坚韧的生命力固存于当代中国的行政文化系统中,对我国正在进行的政府机构改革发生着深远的影响。
一
传统行政文化的提法可以成立。古代中国没有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分立一说,一切由皇帝个人说了算,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管理职能也混为一体,统一于皇帝的政令。这种政治和行政的一体化状态,使人们难以发现二者之间的区别。但皇帝的决策和政令要得以贯彻,必须依靠各级官吏去推行,而他们的活动,就是今天通常所说的行政实践。故而古代中国虽没有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概念,但历朝累代的行政实践却是客观存在的。从文化发生的最终根源看,有行政实践必然有行政文化。由于文化在不同的领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因此,我们可以把行政文化界定为:传统行政文化是传统文化在行政领域里的表现形态。这一概念的内涵,从文化哲学的角度看,包括传统行政思想、传统行政心理和传统行政观念三个互为关联的方面。
传统行政思想是古代人们在行政实践中形成的主观想法和见解的总称,是理论化、系统化的行政认识。它是人们对社会生活中各种行政活动、现象以及隐藏于其后的各种行政关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自觉的、系统的反映。传统行政思想的内容较丰富,既有仍具现代价值的“民本”思想、仁政思想等,也有已落伍的“礼治”思想、“大一统”思想等,还有精华和糟粕并存的“无为而治”思想、“绝对无君”思想等。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行政思想,自被西汉的统治阶级采纳后,就上升为历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物化为等级森严的中央集权的官僚行政体制。体现到行政运行机制上,则表现为行政决策的“君权至上”性和行政执行的等级性,“事无大小,皆决于上”,皇帝的决策无论正确与否,百官唯有诚惶诚恐地服从;行政权力层层向上集中,等级森严,下级行政官员的自主性极弱。传统行政思想在历朝累代统治阶级高强度、长时间的宣传中,逐渐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内化为一种稳固的、持久的心理状态。这就是传统行政心理。
传统行政心理是古代人们在行政思想传播过程中形成的关于行政实践的稳固的行政态度、行政情绪、行政愿望、行政信念等集体心理现象。它是行政思想在人们心理层面上的积淀,是一种比行政思想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作用范围更为广阔的精神因素。传统行政心理包括“以吏为师”心理、“政治教化”心理等形形色色的心理现象。与传统行政思想有别,传统行政心理是一种不容易被改造、被抹去的感情、态度、信仰和潜意识。传统行政心理一经形成,就会对人们的行政行为产生持久的、稳定的、牢固的影响。传统行政体制在今天业已土崩瓦解,但传统行政心理经过代代相传,恰似一种遗传基因,沉淀在行政人员的灵魂深处,并成为民族心理性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对行政实践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不过,传统行政心理对行政行为的影响不是直接的,它需要通过一个中介,即传统行政心理要外化为一种思想意识,外化为人们对行政体制和行政实践的一种概括的映象——行政观念,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传统行政观念是传统行政思想、行政体制和行政心理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概括的映象。传统行政观念直接作用于行政体制和行政运行机制,影响着人们的行政实践。其内容十分复杂和丰富,既有仍然符合现代政治、行政发展需要的“民本”观念、“仁政”观念、“贵和”观念,又有阻碍市场经济进程和社会进步的“官本位”观念、“宗法”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人治”观念,还有良莠混杂、瑕瑜互现的“无为”观念等。从传统行政思想到传统行政心理,再到传统行政观念,构成了传统行政文化的内部结构,亦使传统行政文化呈现出专制性与统一性、封闭性与实用性、保守性和严密性、排异性和兼容性、重形式轻效率、重人法转法治、重权威轻民主、重集权轻分权、重经验轻制度等特征。在传统行政文化的规约、引导、控制和激励作用下,一方面,传统行政体制发挥了维护阶级统治,推动小农经济发展,促进文化繁荣的功能,使中国封建社会创造了农业文明的高峰;另一方面,传统行政文化又以其专制性、保守性、排异性和封闭性阻碍着现代行政文化的生成,影响今天的行政改革和行政发展。
传统行政文化到近代开始走向没落。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腐败的晚清政府无力抵御节节败退,使中国统治阶级中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发出了变革传统的强烈呼声,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都集中反映了这种要求和呼声,但这仅限于器物层面的变革。之后,人们对变革的认识又深入到制度层面,于是就有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再后来,变革的要求深入到社会的思想意识层面,从“五四”运动对民主与科学的呼唤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传统行政文化与整体的封建文化一起,遭到了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强烈冲击,发生了愈来愈深刻的危机。但由于种种原因,根深蒂固的传统行政文化,特别是化为“集体下意识”的深层的民族心理结构,始终没有分崩离析,反而以不同方式发挥着消极作用,出现了一次次帝制复辟、尊孔读经、一党专制、个人独裁这样的历史逆流。即使到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后,其影响也未尽除。虽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政治上、经济上消灭了封建主义,但在思想上、文化上却并没有完全挣脱封建主义的束缚。因而当我们在跨进社会主义大门时,不仅脚踏的是一片落后的自然经济土壤,而且四周环绕的仍然是浓厚的封建主义文化氛围。
二
作为一种行政领域里的“集体意识”,就其本质来看,传统行政文化的消极影响是主要的。它通过对行政人员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意识发挥作用而影响着行政实践,阻碍着政府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
1.阻碍行政职能的转变。行政职能是政府的职责和功能,即政府权力的作用范围和程度。我国行政职能的转变,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也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总的来说,行政职能的转变是要从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全能政府”转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政府的职能要转变到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但是,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全能政府”观阻碍着行政职能的转变。“全能政府”观是传统行政文化的产物。在传统行政文化中,君主的行政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可以无限制地侵入和管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存在君权不可以统治和管理的领域。“全能政府”观造成公民、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对各级行政组织的“依附”观念,使它们的自立、自主意识遭到泯灭。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一方面,政府不愿意放弃对经济、文化和社会事务的全方位的控制和管理,使政企分开、政市分开、政社分开难以实现;另一方面,由于自我组织能力较弱,公民、企业、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也不希望政府从许多复杂事务和矛盾中抽身出来,仍然习惯于与政府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仍然管着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事务。
2.阻碍行政人员的分流。行政人员的分流是行政职能转变和行政机构精简的必然要求,也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难点所在。人们之所以把人员分流看成是行政改革的难点,从行政文化的角度看,是因为传统行政文化的“官本位”观念、“宗法”观念、“特权”观念、“等级”观念的影响。“官本位”观念以不择手段地求官、保官为目的,以以官牟利、以官构名为归宿。“官本位”观念衍化出丑陋的“等级”观念,所谓“官有九品、人有九等”,官贵而民贱;内生出丑恶的“特权”观念,认为官吏可以享有特权,可以得到一般人不能得到的特殊利益。这些观念阻碍了行政人员的分流:一旦某些行政人员被划入分流的范围,在本人和他人看来,就必然是权力、利益和地位的丧失。这样,他们就会通过种种手段,运用种种关系来改变这种状况。“宗法”观念与“官本位”观念有着天然的粘连关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之间的关系是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血亲关系。在“宗法”观念的支配下,现代中国政府内部的人际关系仍以变种的宗法血缘关系居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较低的行政层次中,这种关系仍然支配着行政人员的录用和管理,维系着行政机构的运行。一旦某些行政人员被列为分流的对象,其所构建的以血缘关系为主导的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网络就会发生作用,阻挠行政人员的分流。而一些行政组织为了适应这种状态,或改头换面或真戏假做,设置一些“翻牌公司”和从属于行政组织的社会组织来缓解行政改革的冲击,使行政人员的分流有其名而无其实。
3.阻碍行政权力的调整。行政职能的转变和行政机构的精简实质是行政权力的调整。这种调整,从纵向上看,是要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进行自上而下的放权;从横向上看,则要求政府进行水平方向的分权,即政府要把本来属于市场、企业、社会中介组织和公民的权力交还出来。这样做的好处,一方面是政府可以从许多“管不了、管不好和不该管”的事务中抽身出来,把该管的事务管好;另一方面,则可发挥市场的作用,培养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培养社会中介组织的自我组织能力,塑造公民参政议政的民主意识。但是,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大一统”观念、“集权”观念阻碍着行政权力的调整,阻碍着中央向地方的纵向放权。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进行了三次大的调整,这三次权力调整虽对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仍然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划分不科学、不具体,权力划分和权力制约在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过于原则化,过于笼统、宽泛,操作性不强等弊端。这些弊端的存在,使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改革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循环之中。究其原因,仍然是在“大一统”观念和“集权”观念的影响下,我国采用单一制的国家机构形式,强调权力由地方向中央集中,使得行政权力的调整十分困难。
4.阻碍行政法制建设。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行政法制建设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行政法制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离市场经济的要求仍相距甚远。就目前而言,尚无一个完整的行政组织法体系,尚无一部完整的《政府职能转换法》和《行政机构编制法》,使政府机构改革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因此,在政府机构改革中加强法制建设已迫在眉睫。但是,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观念仍然阻碍着行政法制建设的推进。“人治”的本质是“礼治”、“德治”。传统行政文化中虽有“法治”,但更强调“礼治”,“礼”处于统帅地位,“法”以“礼”为纲。突出“礼治”的目的在于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人治”的另一层含义是“德治”。所谓“德主而刑辅”,把道德看作是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主要手段,法律只是次要手段,道德教化是目的,刑罚只不过是工具。由此,行政法制建设的目的不过是要对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实行道德控制,而不是要其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一旦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的道德素养有所提高,行政法制建设就变得可有可无。再者,传统行政文化中的“人治”观念,还体现在“法自君出”、“朕即法律”上,法是“帝王之具”,君主和某些统治阶级成员可以置身于法律之外,由此形成的“权法合一”、“政法不分”、“权即是法”的传统,反映到今天的行政法制建设上,就是有些行政组织和行政人员仍然认为法律仅是“治民”的手段,而不是也可以约束自己的工具。
三
传统行政文化对政府机构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这种作用主要表现为促进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实现,推动行政道德建设和行政关系协调上。
1.促进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实现。政府机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它内在地包括了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依存的价值取向,这与传统行政文化的某些民主性思想有相通之处,而这些在现代社会仍具价值的思想对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有着促进的作用:一是“民本”思想的积极影响。古代“民本”思想是指以民众为社稷之根本,并以民众为发政施治之基础与标准的政治和行政学说。“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既包括“君为民立”、“吏为民役”、“得其心,斯得其民矣”的民本价值观,也包括爱民、利民、保民、富民等实现民本思想的措施和手段,还包括察民情、顺民意、安定民生、体恤民疾和取信于民的方式和目的。古代“民本”思想与共产党的宗旨有相通之处: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此目的,必须走“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当前中国的政府机构改革,归根结底是要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本”思想的凸现和彰显,有助于政府机构改革目标的制定和实现。二是“仁政”思想的积极影响。古代“仁政”思想是同霸政思想相对立的,“仁政”思想是一种“以德行仁者王”的王道行政学说,它以“德治”为其运作基础,是一种将行政问题道德化的学说,“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制民以“恒产”,薄税赋,轻刑罚,救济穷人,保护工商等几个方面。这种思想至今仍有超时代、超阶级的价值。对政府机构改革而言,要实现民主和效率的改革目标,就必须精简机构,裁撤冗员,减轻纳税人的负担,同时又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惠顾在社会竞争中的最不利者”。由此来看,古代“仁政”思想对促进政府机构改革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2.推动行政关系的协调。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飞速发展和剧烈变动,使行政系统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压力,这就要求必须加强行政协调。这里的行政协调仅指行政系统内部关系的协调,既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之间、地方政府内部的各种关系的协调,又包括地方政府与职能部门条块关系的协调。行政关系协调是政府机构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传统行政文化中关于人际关系的某些有价值的思想和观念,可以作为行政关系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则,如“贵和”观念、“和而和同”的观念等。“贵和”观念是从中庸思想中生发出来的,最初是处理社会成员关系的准则,虽然其出发点在于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秩序,但到了现代,已成为我国处理国家关系和国内政府间关系的一条原则。在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调整地方政府内部利益关系的过程中,仍具有积极的意义。
3.促进行政道德的建设。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行政人员队伍,是政府机构改革的目的之一。为建立这样一支队伍,必须加强行政道德建设。现阶段我国行政道德的理论、措施、手段和方法的建设都可以从传统行政文化中找到可资借鉴的资源,例如,忠于国家,严守机密;依法行政,秉公办事;不谋私利,廉洁奉公;忠于职守,勤政负责;精通政务,高效行政;各司其职,团结合作等规范性内容,与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忠恕”观念、重义轻利观念等都有诸多相通之处。虽然,传统行政文化中的“忠恕”观念,本意是指忠于朝廷忠于君主,勤政也是为一家一姓的勤政,但剥去其封建性内核,其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形式仍然可用。再者,行政道德建设中的一些措施、手段和方法,如教育手段、监察手段、法律手段和制度手段等,与古代行政文化中传承下来的“教化”、监察、法治手段亦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这些,对行政道德建设都可以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