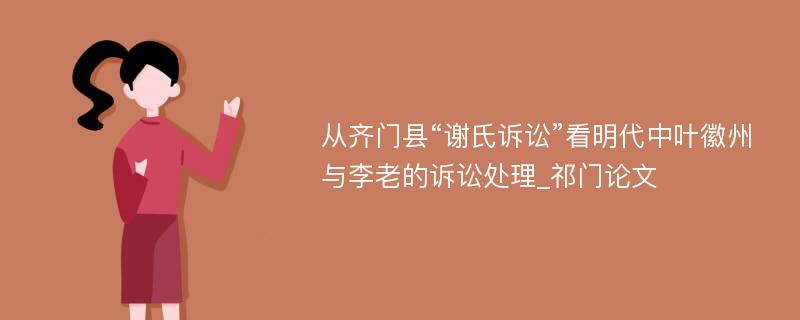
从祁门县“谢氏诉讼”看明代中期徽州的诉讼处理和里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祁门县论文,徽州论文,明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序言
对地方司法运用实况的分析不仅有助于了解地方社会本身,对掌握地方和国家权力间的关系也是有帮助的。但是对明代司法的全盘制度进行整理的研究并不是很多,一直以来都是着重于对个别制度的研究。至于对于诉讼解决的具体过程以及国家的统治理念和地方社会是怎样结合起来研究更少。(注:利用多种明代徽州文书分析包括民间的调解和地方官裁判的纠纷处理系统的中岛乐章的研究值得关注(《明代中期,徽州府下におげる〈值亭老人〉にっりこ》,《史观》131,1994;《明代前半期,里甲制下の纷争处理—徽州文书を史料として—》,《东洋学报》76—3·4,1995;《徽州の地域名望家と明代の老人制》,《东方学》90,1995;《明代徽州の一宗族をぬぐゐ纷争と同族结合》,《社会经济史学》62—4,1996;《明代后期,徽州乡村社会の纷争处理》,《史学杂志》107—9,1998等)。他强调里甲特别是里老人的存在和作用, 将焦点放在了乡村的纠纷正式向官方递交之前依靠地区社会自行解决的过程。因此他的研究也在掌握地方诉讼处理的整体上还是不足的。) 并且由于资料的局限性,研究对象多局限于清代特别是其中后期,出现了用这一时期资料研究得出的结果,去理解明清时代地方司法整体特质的倾向。虽然明清时代的基本制度在大的框架以及理念等方面有相同部分,但是决不能忽视时代变迁而造成的变化。因此,对于明代地方司法实况的实证性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在中国,明代编纂了《大明律》、《大诰》等各种法典,表明要大力开展司法运用,特别是企图通过对官吏的严格管制来促使诉讼的公正处理。其中乡村的诉讼处理完全委托给里长、里老人的乡村裁判。(注:与此相似的概念“基层诉讼制度”(杜婉言:《明代诉讼制度》,《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2期,83页),“乡诉讼”(尤韶华:《明代司法初考》,厦门大学出版社,1998,62页)也有。但不是单纯受理诉讼,而是在乡村里处理诉讼进行判决,因此本文中使用“乡村裁判”这一词。) 这既有利用旧有的乡村自身解决能力来谋求社会安定的一面,同时也减轻了官府的行政负担。[1]
但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诉讼更加频繁。诉讼的增加不只表现在量的增加上,案例也越来越复杂,仅靠乡村裁判难以解决的案例增多。当然,里甲制下的乡村裁判在制度上仍然是有效的,只是由于制度和现实之间的偏离,诉讼处理过程中开始出现了很多问题,致使国家不得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方案。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藏有明代《抄白告争东山刷过文卷一宗》(注:本案卷的原本是,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明档2—4》)。最近出版的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明朝档案总汇》第1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以下称《明朝档案》),38—52页中也有。),是围绕成化年间徽州府祁门县谢氏发生的诉讼资料。这是目前为止所知的明代诉讼案卷中时期最早、收录翔实,价值很高的资料。据此可以详细把握明代中期以后诉讼处理的实况。
一、明代成化年间“谢氏诉讼”始末
首先来看一下“谢氏诉讼”事件的过程
正式的诉讼是从成化八年(1472)十一月十四日祁门县十西都民里长谢玉清户所属的谢玉澄向徽州府递交诉状开始。在诉状中谢玉澄称:从祖上继承下来的东山土地北边的界限,和同一都内的谢道本等所有的山地南面界限相连。在永乐年间就曾因谢道本的长辈越界发生过争吵,在亲戚的劝解下双方划清界限,此后50年间没有再发生过事情。但是在成化七年(1471)九月谢玉澄等在山上伐杉树,却被谢道本等带人阻拦,不许伐木带走。在事件发生的九月到上诉的十一月间,虽然进行了调解和协商,但是最终失败。
十一月十五日徽州知府受理了谢玉澄的诉状,诉讼处理正式开始。
首先需要就诉状中的内容是否属实对相关人员进行审问。被告人住在祁门县,因此徽州知府就向祁门县发出帖文,“合仰本县当该官吏,速照帖文内事理,即拘后项人犯到官,审各正身,星火差人解府”,命令将谢道本等人传唤到徽州府。帖文中只说明由祁门县的有关官吏负责,没有标明具体的传唤负责人。十一月二十二日祁门知县下文“遣牌下该都勾使县令牌前去,仰速拘勾犯人谢道本等务正身,星火依限赴官,以凭解府施行”。“该都”指的是谢道本等有关人员住的十西都。从知县的其他批文来看,这一命令是下达给十西都里长的。由于传唤犯人发生了拖延,十一月二十五日徽州知府又下了督促文。接到文件的祁门知县在十二月四日也下了同一命令。(注:明代诉状递交后传唤有关人员的方式,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下命令给被告,让其自己来到官府,这叫做“传唤”。这一方式没有什么一定的法律规定,所以实际执行起来有好多方法。原告负责叫来或是官方将让被告出庭的命令书下达给原告带来。另外一种是“拘提(勾摄)”。人命、斗殴、强盗事件等被告逃跑的可能性大的重大案件的有关人员,下了命令后不来的话,派遣人员强制押送到官府。(见杨雪峰:《明代的审判制度》,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175—181页。)强制押送犯人的时候,执行衙门中要发给“拘票(牌)”,根据这个进行。为了防止连累无辜人员或迟到官府,要写上传唤人员的名字、地址、时限等。处理诉讼的时候采取什么方式要依据各个事件的情况和地方官的习惯。本案件因为递交诉状的地方和犯人的所在地较远,而且原告和被告是同一宗族,因此让原告带被告来的方式应该没有什么效果。)
不久,里长谢得延就以书面“申状”文书于十二月六日向祁门知县进行了回复,称已将除了生病的谢道忠以外的谢道本等犯人带到祁门县衙。
在知县确认是被告本人之后,又给里长下了如下批文:
直隶徽州府祁门县为强占山土印阻木植等事。承奉本府帖文,及蒙白牌,拾西都民谢玉澄状告前事除外,今差本役管解后项犯人谢道本等,定限本月初拾[红]日前,赴本府告交明白,守奉批回销照,在途毋缓。须至批者。
[府印一颗]
计开该犯人肆名 谢道本 王成 仕端 文瑜
[除将解到犯人谢道本等,随批带回本县,听候公文,至日另行外,本月十四日批回]
[县半印,祁字柒号][十四日到]
右批差 里长谢得延 准此
成化八年十二月初柒日 典吏 饶立 承
县(押) 附卷
这是有关从谢玉澄起诉一事接到徽州府的帖文和白牌后,派“本役”将谢道本等犯人截至十二月十日为止护送到徽州府衙门的命令。“本役”指的是里长,他的任务要等到徽州府的“护送好了”批示下来后才算结束。同时在此过程中里长谢得延在任务完成后要将印有护送命令的牌交回。这一般都是派遣衙门的差役时做的。(注:具体的程序参照黄六鸿:《福惠全书》卷11,刑名部,词讼,差拘。) 里长虽然不是官府衙役,因为他也履行了相同的任务,所以也有相同的手续。批文的尾部写有“典吏饶立承”,说明由县衙的胥吏饶立将知县的批文送达给里长。但是在知县的批文下面,还有一份十二月七日写的很短的文书:
西都里长谢得延,今当官领到批文壹道,管解后项犯人谢道本等,赴府告交明白,守奉批文,不致违误,所领是实。
一实领到批文壹道
成化八年十二月初七日 西都 里长 谢得延 号 领
滋贺秀三在介绍清末台湾地区淡新档案中的证据文书类时解释:如果只是“领状”的时候指的是接管身柄。接管东西的时候一般像“领契状”、“领银状”一样要加上东西的名字。[2](p.273—274) 但是从上面的“领状”标明“实领到批文壹道”来看,应该是对知县批文的一种回执。这一领状给了传达批文的胥吏,然后又转达给了知县。因为是按徽州府的指示护送犯人,出什么差错的话知县要负责任,所以有必要确认一下命令是否传达到。
在里长的护送下谢道本等人到达徽州府衙门,知府审问以后,发现原告和被告的说法不同,因为十二月五日,被告谢道忠也向徽州府递交了诉状,说是谢玉澄等人越过了界限,将他们的约900棵杉木强行伐走。这样在进行现场取证之前是得不到正确的判断的。所以知府又下了“仰本县勘判回报”的批文,命令将谢玉澄诉状的抄本和被传唤的四人送回祁门县,经有关官吏进行现场调查后。再将公正的陈述和保证文书递交给府里。这样,谢玉澄的诉状抄本和十二月七日知府的帖文一起又发给了祁门知县。
接到知府命令后,祁门知县首先审问了相关人员,听取了各自的陈述,然后知县下了如下帖文:
……一帖下该都排年里老使县令,将各人供词帖前连人帖发前去,仰速照二家情词,并奉府帖文内事理,拘集山邻保长人等,追出的本,堪信经理,照依各家四至,山亩多寡阔狭,逐号定立,疆界明白。先将二家所争互界山内杉木,照依原砍桩木点数桩管,毋许将无干之数一概混同。桩管其木植,听候断理明白,方许撑放。务将二家所争事情,取具各人不致供结,听候覆勘施行……
现场调查的具体内容在知府的帖文中已经提到。帖文中写着让十西都的排年里老来做,而不是县衙门官吏。“排年”与当年担任里长的“见年”不同,原则上没有处理行政事务的义务。但是有记录说“所司有清理军匠,质证争讼,根捕逃亡,挨究事由则通用排年里长焉”[3](卷31《制国用·傅算之籍》),为了进行现场调查,见年里长、里老人和排年里长一起参与的情况在文书中可以得以确认。对于知县的这一指示,和前面一样里长谢得延做了领状:
十西都里长谢得延,今当官领到本县帖文壹道,并原被告人谢玉澄等及状内一干人证,前到告争山,所听候查勘,所领是实。
一实领到本县帖文一道并供状三纸 原被告人 谢玉澄 谢道本
成化九年三月十八日 十西都里长谢得延 号 领
知县的帖文虽然是下给排年里老,但是写公文这样的事情是见年里长的事,所以收据是以“里长谢得延”的名义写的。
三月十八日,接到知县命令的相关人员历经约2个月调查后,以共同的名义作成如下文书:
十西都里老谢得延等,今于与执结为告争山土事。承奉本县帖文,据本都谢玉澄,谢道本告争前事。依奉前去会同比都老人汪思诚等到告争山,……勘得:谢玉澄见勘杉木,系是二千号,二千一号,原系玉澄栽苗老林界内杉木,应该玉澄等管业。勘得:见在山未勘杉木,系谢道本经理一千九百九十七,一千九百九十八,一千九百九十九号三号,嫩际界内嫩木,原系道本栽苗,应该道本为业。勘得:亩步多寡阔狭,系是二家祖父管业已定,中间即无扶同。不实如虚,得延等甘罪无词。执结是实。
成化九年 五月 初三日 十西都里长谢得延 号 状
排年里长谢彦荣 号 李秉隆 号 李文焕 号 谢彦修 号 李秉彝 号
老人李秉通号
比都老人汪思诚号 胡宽号
这一文书是排年里老现场调查后将了解的事实罗列出来,连带保证内容没有虚假并对此负责的结状。(注:根据滋贺秀三,在淡新档案中“遵依结状”、“指伤结状”、“甘结状”以外还有多数保证人的“保结状”(同文,272—273页)。笔者想本案卷的“结状”是属于“保结状”的。“结状”末尾使用的“执结”指的是对保证负责的意思,也作为向官府递交的文书的名字来使用。和同一用途使用的“具结”一样都是结状类文书。另一方面天启、崇祯年间休宁县发生的余氏和潘氏的诉讼案卷《不平鸣稿》(南京大学历史系资料室所藏)卷1中收录有对殴打事件的受害者的值日医生徐应新的“结状”。还有在《徽州文书》2卷中收录有隆庆年间的保结状。) 知府和知县的帖文中分别有“取是不扶供结”“取具各人不致供结”这样的字样,“供”是有关人员的供状,“结”是保证书。谢玉澄伐掉的杉木本来就是自己种的树,所有者是谢玉澄。而东山内还没有伐的小杉木,是谢道本种的,所有者是谢道本,这就是现场调查的最终结论。
结状的最后部分落有参与者的署名,首先是见年里长谢得延,接下来是5名排年里长。但是除了十西都的里老人署名外,还有两名“比都老人”的署名,虽然不知道是几都的老人,是附近十东都老人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是因为东山的界限和附近地区连接在一起。但是从见、排年里长和里老人的情况来看,都是和原被告一样的谢氏宗族或是有亲属关系的李氏家族的人。《教民榜文》中说:“本里老人,遇有难决事务,或子弟亲戚有犯相干,须会东西南北四邻里分,或三里五里众老人里甲剖决。如此则有见识多者,是非自然明白。”
见年里长附了保证书后向知县递交了如下文书:
十西都里长谢得延,承奉本县文书,为谢玉澄,谢道本告争山土事。依奉前去体勘得,唐字二千号,二千一号,系玉澄砍木管业。又唐字一千九百九十七,一千九百九十八,一千九百九十九号,三号山内嫩苗木,系道本长养管业。为此,今将不扶结状一样二本,合行申覆施行。须至申者。
一 缴不扶结状一样二本
成化九年五月初三日十西都里长谢得延号状
这是对前面保证书的调查结果进行了简单的概括。因为接到知县帖文的是见年里长,所以最终结果报告也得以谢得延的名义作。(注:地方官对里老下了调查指示,但报告文是以里长名义做成的事例,在《成化五年祁门谢玉清控告程付云砍木状纸》,《徽州文书》1卷,186页中也可以确认。)
里老的现场调查结果出来后,原被告人接受了亲戚李秉高等人的调解,于五月十九日达成妥协,由谢玉澄将伐下的老杉木搬走,小树木则由谢道本继续管理,并向祁门县递交了要求撤诉的告息状。(注:本诉讼虽然是以告状的形式报告了和解,但是也还有合同形式的文书(《嘉靖四十二年谢祖昌等息讼合同》,《徽州文书》2卷,314页;《崇祯四年黄记秋,谢孟义息讼清业合同》,《徽州文书》4卷,306页等)。即取消诉讼的文书没有什么一定的形式,是按照情况灵活做成的。) 从里老进行现场调查后双方即达成妥协,并且其协议内容也和里老的报告相符这一点来看,有可能是里老进行了劝解从而达成了和解。因为,现场调查后各自的所有情况都搞明白了,再到徽州府去审判对双方都是很麻烦的事。
但因为是由知府受理的案件,最终还要经过知府的允许才能取消诉讼。祁门知县将这一经过于五月二十四日报告给了徽州府,六月三日知府批复的文书下来,六月十三日祁门知县向当事人发送帖文,至此这一案件才算完结。
“谢氏诉讼”一案,从成化八年十一月十四日谢玉澄的状纸递交,到成化九年六月十三日祁门知县的帖文发送到当事人手中,约历时7个月,纷争的起因是界限不明的山地。这在山区的徽州是经常可以看到的案件。在这个案子里,比较特别的是相关人员之间的关系。
祁门县的谢氏在南唐末从金陵搬到了祁门,以谢诠为始祖,以后分为众多支派居住在祁门县各地。按照《王源谢氏孟宗谱》记载,谢诠长子的六代嫡孙谢芳在北宋末居住在王源村,南宋末出了两名进士,到了明初又通过农业经营和经商发家,成为地方上有势力的宗族。宗族内又分为利仁、贵和、俊民派。从族谱看,俊民派的人数最多,利仁派其次,贵和派只是处在维持血脉的状态。贵和派从始祖贵和开始就没有子息,收养了利仁的二儿子时佐做养子,时佐也没有后代,就又收养了弟弟富閠的二儿子允宪,允宪也没有子孙,收养了名叫乞安的,以后子孙们才慢慢多起来。
从族谱(注:笔者利用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中所保存的《王源谢氏孟宗谱》分析。21代以上世系收在卷4,21代以下收在卷5。) 上能找到的有关人员来看,诉讼文书中使用的名字,大部分都是字,不是本名。原告方面,谢珍瑛、珍瑺、玉澄均是谢能静的后代,是利仁派的第22代子孙。只有谢志华是贵和派的,但考虑到贵和派的先祖是从利仁派收养而来,两个支派间的关系应该是比较密切的。而被告方面的谢道本、道忠以及王成、仕端、文瑜都是俊民派的第21代子孙。进行共同调查的排年里长中,谢彦修是贵和派的第21代子孙,将有关人员押送到徽州府的里长谢得延在族谱上找不到,但是从谢道本等向同一派的亲戚谢用和委托现场验证时写的名字来看,应该是和俊民派有着密切关系。但不管如何,诉讼的有关人员几乎都是祁门谢氏的同一宗族。从宗族内部的问题不能自行解决,而起诉到徽州府的情况来看,可以说是明代中期以后宗族内部纠纷日益频繁的一个很鲜明的例子,而宗族处理这类纠纷的能力则在下降。
二、从“谢氏诉讼”处理看里老作用的持续和变化
综合以上的诉讼处理过程,可以看出明中期处理诉讼时官府不采取直接的措施。受理诉状的徽州知府为了押送有关人员和现场检验,不直接派遣衙门的官吏或差役。所有的都委托给祁门知县,但是祁门知县也不直接处理,而是向相关地区的里老下命令让其传唤有关人员,再护送到徽州府。不仅如此,进行现场调查的知府命令一下达,又委派给了排年里老,依据他们的调查结果向知府报告。
府和县衙门之间,知县和里长间的意思传达是通过递交帖文、批文、牌文及收据、报告等来进行的。从明初以来禁止官吏亲自下乡,因此地方官和里长间没有见面的机会。虽然很麻烦,但是这种文书的往来还是需要的。可以看出在徽州一直到明中期还是遵守太祖制定的祖法禁止“官吏下乡”的。(注:有关“官吏下乡禁止”的明初规定是,参照《大诰续编》17,官吏下乡;《大诰续编》18,民拿下乡官吏;《大诰三编》36,民违信牌;《大明律》卷3,吏律,信牌。)
在乡村,担当直接事务的就是里老。里老负责拘提犯人往祁门县再解送到徽州府,进行现场调查、验证判定事实。在清朝受理诉状的地方官发给差役令状,派其到当地进行调查、验证、传唤、逮捕等,根据情况,不同正官或佐贰官还亲自到纠纷地区。(注:有关清代的情况是,参考Tung-tsu Chu,Loc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the Ching,Harvard U.P.,1962;那思陆:《清代州县衙门审判制度》,文史哲出版社,1982;郑秦:《清代司法审判制度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吴吉远:《清代地方政府的司法职能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等。) 但是在徽州府的文书中一直到明中期为止,找不到官吏或差役被派到诉讼地区的例子。可以说成化年间祁门县“谢氏诉讼”中也是遵守了里老来处理乡村诉讼的基本原则。不仅如此,里老的事实调查带来了当事人间的和解,从结果上来看在解决这一诉讼中里老的影响力是较大的。
只不过在明初里老人的作用比里长更具有主导性,而在本诉讼处理过程中,里老人只是进行现场验证作为保证人署名的人群中的一个。官方的命令下达给里长,最终报告也是以里长的名义递交的。明中期里老人在诉讼处理中发挥影响力的事例虽然很多[4](第4章参照),但是应该说出现了诉讼处理的主导权逐渐从里老人向里长这方面转移的趋势。(注:明中期以后纠纷增多,所以里老人的处理速度和公平性随之降低。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变化,利害关系尖锐,诉讼变得越来越复杂,在里老人的主导下进行的教化、和解、调解为主的乡村裁判的效力发挥变得困难了,所以向官府诉讼的例子增多。这就是乡村内部调解能力出现问题的证据。因此以后诉讼处理过程中里老人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同时原告不先告诉里老,直接向官方特别是向知府递交诉状这一点也值得关注。通过以前的研究可以知道,这并不是只有本次诉讼这样。通过多种史料来研究明代纷争处理和里老人制度的中岛乐章曾经用表格形式介绍过从建文三年(1401)到正德十三年(1518)的43件纷争事例。[4](P130—135) 这里包括自行解决的事例。如果只考虑扩大到诉讼的事例,从成化年间开始表现出鲜明的差别。成化年间以后的事例是32件,这其中14件是由中间人或亲戚、耆老等调解的事例,打官司的是18件。这其中只有正德七年(1512)祁门县的郑良吴的事例是先向里老上诉的,其余的都是向县或府递交诉状。这种倾向通过休宁县《茗洲吴氏家记》中的《社会记》里收录的介绍茗洲吴氏和其他宗族间纷争的表中可以得以确认。[4](P187) 分析这当中截止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共计32件的事例,大部分都是有关山林盗伐或坟庙问题。这其中自行解决的有5件,先向里老起诉的有5件(这其中2件又再向府县起诉),此外的22件都是直接向县、府等官方直接起诉的。明中期以后虽然也向里老递交诉状,但是从相当数量向县官方起诉这一点来看分明和明初不一样(当然就算向官方起诉,实际调查验证也还是由里老来负责,并且在他们的调解下中途得以解决的事例很多)。到了明中期先向官方起诉的事例变多,说明有可能乡村裁判中里老担当的作用出现了问题。
里长和里老人对当地的情况非常了解,虽对处理诉讼非常有利(注:海瑞:《海刚峰先生文集》,卷上,参评,里长参评:“谁贫谁富,谁困苦,谁徒流,谁人钱粮多寡,谁人丁口消长,彼尽知之。”),但从“谢氏诉讼”来看诉讼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有着血缘、地缘关系,难以在第三者的立场上做出客观的决定。而且地方官不进行亲自处理,将传唤相关人员、现场调查等大部分委托给乡村有势力的里老,因此而带来的弊病也不少。对里老处理的诉讼的验证、调查、再审查过程中发生的弊病的指责很多,所以成化九年国家法司经过讨论后命令地方官不要贪图安逸委托给里长和里老人,要亲自审理诉讼。[5](卷116·成化九年五月辛卯) 但是仅就“谢氏诉讼”来看,国家的这一决定,并没有实际反映到乡村上,只是明中期以后里老人和里长在乡村发生的户婚田土等诉讼的解决上逐渐困难起来。
通过以上《抄白告争东山刷过文卷一宗》中收录的文书来看,明中期受理诉状的地方官一般不是向官员或差役,而是向里老发送帖文,指示其传唤犯人和验证调查。接受命令的里老要递交令状、结状、申状来报告结果,地方官允许其将处理内容发送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保证结果,这是在当时一般的诉讼处理过程。实际上诉讼处理非常多样化,既有像成化年间的“谢氏诉讼”这样在验证调查的过程中达成和解取消诉讼的情况,也有当事人不听从验证结果和地方官的决定向上级机关上诉要求再审的情况,但总体来说是按照这样的诉讼处理过程基本上保持了。只是到了明中期以后,里长和里老人的作用开始发生了变化。同时向官方直接起诉的事件也越来越多,因此可以认为里老像以前那样在诉讼中发挥绝对的影响力已经有些困难了。
三、结语
明中期以后,在社会诸多方面发生了大变化。当时有必要拉近变化中的社会现实和死板的法规条文之间的距离。在制定法律方面,到成化弘治年间进行了条例统一,中央政府也频繁地介入地方司法行为。而地方官频繁指责里长、里老人的诉讼案件调查、检证或办理弊害。当时通过对地方问刑衙门的监察强化,中央政府在试图介入地方司法的体制,采取限制里长、里老人诉讼处理的措施。不过这不是说中央否定了乡村裁判制度的原则本身。笔者认为,到了明中期,上疏的地方官还有在京法司,也不是主张废止里老的乡村裁判本身,而是议论如何改善情况。并且其措施也是对个别事例命令,所以一再反复议论,尚未到调整原则的阶段。
为了考察当时乡村里诉讼如何被处理,笔者剖析了成化八年在祁门县发生的“谢氏诉讼”。我们可明白这件在同一宗族间,因山地边界发生的案件,尽管当事者间经调解以取消诉讼,但因是徽州府下令祁门县调查的事件,所以还要得到府的最终承认,直到给当事者帖文以后才结束了。这一案件虽未到地方官审判,但刷卷御史检阅了关联文件。因此我能了解当时府县衙门的自理案件也是成为监督对象。从本案诉讼处理过程来看,到这时期,乡村裁判的基本精神本身还是维持下去。但通过许多诉讼事例,可以确认,明中期以后老百姓到官诉讼的情况渐渐增加。所以笔者认为,里老不像以前在乡村里诉讼处理,容易发挥绝对影响力。并且里长和里老人的分工也开始发生变化,相比里老人,里长的职责变得更重要。
总之,剖析成化年间“谢氏诉讼”的结果,我们可以确认,明中期地方司法与乡村组织有密切关系。明中期以后,因许多因素,诉讼越来越多,并渐渐复杂了。所以像过去在乡村内部解决问题遇到了不少困难,因而打官司自然增加起来。尽管乡村里打官司增加,考虑到当时地方衙门行政条件,处理诉讼过程中不能排除乡村组织的影响。不过在里老的权威越来越下降的情况之下,中央官府不能使他们专任像明初一样的乡村裁判。老百姓直接到官告状,里老在其处理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逐渐变化下去。以后到了明后期,里甲组织更不坚固,已不像明中期一样依靠乡村组织能专门处理,利用乡约、保甲以办理诉讼也不充分,因此有时借用族长或绅士的权威。所以,明中期地方诉讼处理当中呈现出里老作用处于过渡期的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