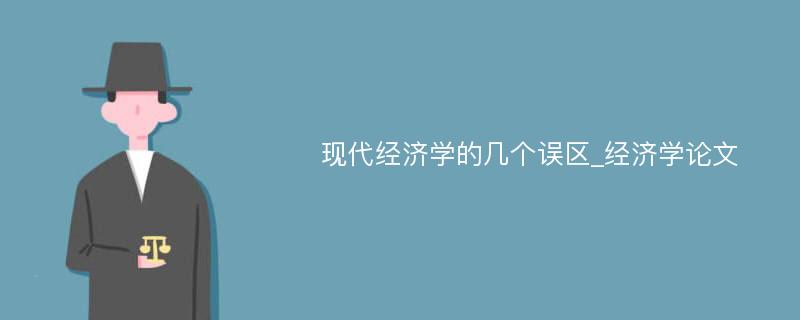
关于现代经济学的几个误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个论文,误读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06(03)-0001-06
一、市场经济是中性的吗?
在现代经济学的教义中,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自由”、“平等”,就是“资源优化配置”。从20世纪80年代起,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与现代经济学的教义相呼应,市场经济的本质在我国就逐渐被“中性化”,成为一种与生产关系“毫不相干”的工具。我注意到,极力回避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去观察市场经济,千方百计地抹去市场经济与生产关系的联系,这在今天我国学术界不仅代表着“与时俱进”,而且也具有“政治正确性”。令人遗憾的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并非现代经济学所描绘的那么“中性”:
其一,自由和平等并不是价值中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自由贸易,自由买卖。”[1]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中自由和平等的本质,他说:市场“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但是,“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庸俗的自由贸易论者用来判断资本和雇佣劳动的社会的那些观点、概念和标准就是从这个领域得出的,——就会看到,我们的剧中人的面貌已经起了某些变化。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萎缩不前,像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2] 对于弱者而言,难道强加的买卖(比如出卖劳动力,甚至出卖自己的肉体、色相和灵魂)是“自由”和“平等”的吗?如果说这里存在着什么“自由”、“平等”,那也只是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其本质则是买者(强者)的自由和平等。对于资本而言,所谓平等,就是平等剥削劳动力。其实,哈耶克所鼓吹的、正被现代经济学奉为圭臬的“自生自发”的市场自由,并没有为多数人带来普适性的自由结果,它只能导致强者的充分自由以及强者对弱者的专制——政治的、经济的专制。这已经而且仍在被市场经济的发展史所证明。
按现代经济学流行的教义,“平等的真义在于公民基本权利的平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机会的平等”。在经济地位不平等的条件下谈机会平等,未免太天真了。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背景下,机会只能是一个势利眼,它总是取悦于那些有权有势有钱者。不少人坚信“市场经济是多赢、双赢的经济”。然而,在资本和劳动的实力极不对等的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期望真正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双赢”,几近空想。资本的本性就是“弱肉强食”,就是不能让别人“双赢”。如果资本主义真能实现这种“双赢”,资本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
其二,至于“资源优化配置”,也并非如现代经济学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不包含价值判断的中性概念”。资源优化配置并不仅仅意味着物的关系的“变动”(重新组合),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人的利益关系的“变动”(重新组合)——这就必然涉及不同阶级、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和博弈结果,也就是说,它无法摆脱价值判断。
问题的要害在于,资源优化的评判标准其实并不是中性的,它内生着强烈的价值倾向。在表面上“自由、平等”的市场经济中,资源是否得到了“优化配置”的衡量标准,只能以强者的“效用最大化”为依据,绝不会也不可能以弱者的“效用最大化”为依据。如果按弱者的标准来评判,那么强者所期望的“优化配置”就很值得怀疑(比如有关下岗分流的争论,对国企改革效果的评判,关于MBO的分歧,以及有关医改和教育产业化的争论,精英和大众的认识几乎水火不容,郎顾之争就是很好的案例)。如果“优化配置”的结果仅仅是“优化”了少数精英,而大多数普通大众却被“劣化”(不幸的是,这恰恰是中国当下某些领域改革的真实情况,比如少数精英侵吞国有资产,大多数工人失业下岗),那么把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定义为“中性”的,恐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市场经济之所以不可能是“中性”的经济范畴,就在于它本身就内含着某种生产关系。正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张宇教授所说:“如果说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那么,这不仅仅是就它的物质内容而言的,而更重要的是就它的社会形式而言的。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商品不是物,而是被物的形式掩盖的人与人之间的一种特殊经济关系。资源配置归根结底是资源在相互存在利益差别以及利益冲突的不同人们之间的分配”。张宇由此得出结论:“因此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3]。值得注意的是,自我国理论界把市场经济的本质中性化以来,这是我现在惟一读到的敢于将市场经济与生产关系联系起来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本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只不过人们离这种常识已经渐行渐远)。
不过,在我看来,张宇教授的结论仍然是不够彻底的。张宇说:“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请注意,在“不仅是”和“也是”的判断中,“资源配置方式”与“社会形态”就成了二元并列的东西,好象“资源配置方式”本身是与生产关系无关的。其实,“资源配置”就是资源在不同人之间的配置,离开了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竞争、矛盾,资源配置又何以可能?何以成立?何以展开?因此,“资源配置方式”本身就是生产方式,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一个中性的工具。
有必要强调的是,承认资源配置方式的本质是生产关系是一回事,我们选择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又是另一回事。换言之,把市场经济看作一种特殊的生产关系,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能推行市场经济。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选择什么样的资源配置方式的依据,并非在于对生产关系的价值判断或好恶,而是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承认市场经济的“非中性”,与肯定市场经济是我们现阶段的必然选择,二者并不矛盾。我国今天选择市场经济,其依据并不在于它的本质是不是“中性”的,而是在于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
当然,仅从形式上或表象上看,说市场经济是一种中性的工具也并没有错。我想,邓小平把市场经济看作是工具,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用”,应当是就形式的层面来把握市场经济的,而且他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纠正以生产关系作为资源配置方式选择依据的传统流行观点,我们应当把邓小平的有关论述置入当时的语境下来理解。但是,“理论要说服人,就必须彻底”,不能因为市场经济内含着某种特殊的生产关系,我们就不敢正视市场经济的本质了,只是在市场经济的表象上兜圈子,甚至千方百计地把市场经济的表象当作本质。这种做法不仅不科学,而且十分愚蠢。因为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无助于为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提供合法性,反而会误导人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好象市场经济一旦与生产关系沾边就会有“难言之隐”。大家想一想,如果市场经济已经脆弱到只敢“说物”而羞于“见人”的地步了,这样的市场经济还能在现实中存在吗?
二、难道“过劳死”才是就业的题中之意?
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人类的智慧虽然可以缓解失业的压力,却没法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这已经并还在为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包括中国的现实所证明。其所以如此,倒并不是当代人类的智商不够,而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使然。个中原因,其实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看到了:雇佣劳动是失业的根源所在。雇佣劳动与市场经济是孪生兄弟,消灭了产业后备军(失业),也就消灭了市场经济。在这个问题上,知趣的主流经济学家要么三缄其口,要么闪烁其词。但也有不少自以为是的主流经济学家却并不知趣,极力炮制着“失业与市场经济无关”的鸿篇巨制。比如在寻找当下中国失业问题的根源时,我国某些主流经济学家一定忘不了重复这样的陈词滥调:“今日失业是昔日计划经济种下的恶果,是隐性失业显形化之结果”——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在失业问题上的全部智慧,就是终于发现了失业的“深层次”原因在于“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这简直是在给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丢人现眼:市场经济生的病,却要计划经济吃药(计划经济当然有自身的问题,但不能因此把市场经济的问题也强加在计划经济头上)。
为了证明其论点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在失业前面加上了“隐性”二字,以增强其“技术含量”。经过如此包装,“隐性失业”的说法居然成了经济学的“常识”。尽管如此,也并不能改变这个“常识”的荒谬:失业就是有人失去了工作,难道非要“过劳死”才是就业?难道两个人干了一个人的工作就不行,就非得让一个人“失业”不可?把“一个人干的活两个人干”等同于“失业”(隐性失业),这不是强词夺理又是什么?按此逻辑,则人类休闲时间的增加就只能是一种奢侈,缩短劳动时间就永远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其实,劳动时间的缩短和休闲时间的增加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过劳死”与失业大军并存的就业制度只是市场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正如恩格斯说:“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4],但它决不可能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当然有不少值得赞美的地方,但它在失业问题上的表现却实在是乏善可陈。
有趣的是,在现代经济学的经典教义中,失业的根源却并不在于计划经济。现代经济学把失业的原因归结为三个:(1)摩擦性失业;(2)结构性失业;(3)周期性失业。前两种失业“因其不可避免的性质”,又合称为“自然失业”。由此看来,那种把失业的原因归结为“都是计划经济惹的祸”的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显然连初级现代经济学的水平都不及格。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论西方主流经济学怎样对失业进行分类,其理论前提都认定市场经济是配置资源(包括人力资源)的惟一正确的方式。由这个前提引申出来的逻辑结论是:在不存在其他能替代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方式的条件下,失业的原因就只能在市场经济之外去寻找。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虽然以上三种失业在本质上仍是市场作用的结果,但通过将这三种失业“现象化”的转换,隐藏在这三种失业现象背后的本质——雇佣劳动关系,就被遮蔽和隔离了。人们看到的只是失业的三种表层原因——这种表层对失业的真实原因构成了一个保护带,使得市场经济这个内核不会因为对失业原因的追问而受到威胁。就如同把价值归结为价格一样,西方主流经济学如此解释失业的原因,再次证明它的确是一种现象经济学罢了。正如马克思当年所言:“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现象背后的本质。
不过,在既定的市场经济制度中,如此“现象经济学”也并非没有意义。虽然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现代经济学对于缓解失业问题却也有某些“具体”和“可操作”的功能。比如针对周期性失业可采用宏观经济政策(逆调节),针对自然失业可采用降低经济活动成本的措施,等等。
马克思把失业的根源归结为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雇佣劳动制度: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垄断,以利润为指向的生产目的决定了就业人数的上下限——由此提供了产业后备军的必要性。这种分析不再把市场经济看作人类社会配置资源的惟一合理方式,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从而颠覆了市场经济的神圣性。换言之,市场经济并未穷尽人类配置资源的方式,一旦生产目的不再指向利润,一旦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被消除,一旦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不再被资本家阶级控制,一旦雇佣劳动制度被消灭,产业后备军就会成为历史(对于将市场经济看作是永恒不变的现代经济学来说,这四个“一旦”显然是无法理解的)。
当然,把握了失业的真实原因并不等于就能立刻彻底解决现实中的失业问题。在市场经济存在的背景下,马克思的失业理论并没有为解决当下的失业问题提供立竿见影的“可操作”对策。但尽管如此,马克思主义却是真正揭示了失业本质原因的科学理论。它的意义在于,使人们能用历史的、本质的眼光来看待失业问题,于是我才能够明白:只有当市场经济退出历史舞台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否则,对任何自称能够根治失业的万灵药方,我们都应当表示怀疑。
三、“调整分配”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吗?
近年来,面对市场经济下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的现状,经济学界终于呼吁应“调整收入分配”,连唯“效率第一”的主流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收入分配结构出了问题。“调整收入分配”的动机是好的,良苦用心是值得称道的,但认为由此就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在理论逻辑上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期望在不触动生产关系的前提下,通过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就能够改变两极分化的结果,是一种极为幼稚的空想。正如马克思说:“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4]。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不调整生产关系,调整收入分配的效果就极为有限,并不能根本解决两极分化问题。这个常识究竟正不正确?近几年来在市场经济关系的约束条件下,我们在“调整收入分配”上究竟做了多少事,究竟能做多少事,效果究竟有多大,看看基尼系数的变化和两极分化的趋势就清楚了。问题并不在于在现有经济关系的培育下,两极分化的发展势头如何强劲,也不在于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和措施有多大效果,而是在于现代经济学把分配关系与生产关系完全割裂开来,根本就不承认今日的收入分配问题与市场经济的内在联系:
比如,在扩大内需的问题上,经济学界逐渐认识到“分配结构失衡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但分析也就到此为止了。至于分配结构“为什么会失衡”,则要么三缄其口,要么语焉不详,或是归结于分配政策,或是归结于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总之与市场经济无关,是自外于市场经济制度的原因造成的。
再如,有学者认为:对于两极分化问题,“关键不在所有制,而在分配制——关键在政府如何作为”,因为“私有制不是贫富悬殊的决定性条件”,“如果共同富裕可以通过政府宏观调控第二次分配来达到,则真正达到了改革的目的”。[5]
改革的最终目的当然是指向共同富裕的,但以为仅靠“第二次分配”就可以实现“共同富裕”,我真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天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问题是有不少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学人也加入了“自欺欺人”的行列。总之,他们不是把当今两极分化的症结归结为人性的堕落上,就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
自“和谐社会”提出以来,两极分化的问题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于是解决分配领域的问题成了大家的共识。至于怎样解决,其“正版”的措施无非是“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扩大中间收入阶层、救济低收入者”云云。其实,收入分配问题只是表象,背后的生产关系才是本质,分配关系是生产关系的反面,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就必定有什么样的分配关系。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生产成果的分配“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4] 23。实事求是地讲,不论你愿不愿意,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分配原则必然是“按要素分配”,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法则。“按要素分配”的灵魂就是“按资分配”,资本的所有权决定了分配必然呈现向“两极”运动的趋势。正如恩格斯说:在雇佣劳动关系中期待出现“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氢。”[4]
因此,“保护合法收入”固然正确,资本家的收入只要不是违法的,当然应当保护,但我实在不明白,这种保护与解决两极分化有何必然联系?假冒伪劣、制黄贩毒当然是非法的,必须在狠狠打击之列,但打击了就解决了两极分化了吗?至于“扩大、救济”云云,怎么扩大?如果“扩大中产阶级”的动力来自于市场的优胜劣汰,13亿中国人中能有多少人胜出?怎么救济?每个月救济几百元就能改变穷人的地位?如果救济增加到几千元,且不说政府有没有这个财力,仅就市场化改革的内在要求看,就有违背市场经济“政治正确性”的嫌疑,这不是在与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规律对着干吗?按市场经济的要求看,这个“救济”说白了恐怕只能是“活命钱”,只能“救急”而不可能“救穷”。活命钱或许能保证穷人不闹事(机会成本太高,毕竟好死不如赖活),但离真正的和谐恐怕还远着呢!我并不是说“保护合法收入、打击非法收入”,“扩大中间收入阶层、救济低收入者”等一系列措施没有意义——这些措施不仅有重要意义,而且非常必要,我举双手赞成。但我认为没有必要把这些措施的意义上升到那样不着边际的高度。
两极分化是市场经济背景下的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转型中的我国而言,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无疑是符合现阶段国情的正确选择(在没有最优选择的约束条件下,调整分配至少是一种次优选择),甚至可以说对于当下的社会稳定具有十分紧迫的必要性。但必须明白:(1)今日的两极分化与市场经济的确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2)在既定的市场经济的制度背景下,任何调整分配的措施都只能是“缓解”而不可能“解决”两极分化问题。如果说市场经济是符合现阶段经济规律的客观趋势,那么对于由此带来的两极分化问题,我们当然只能是积极地并不断地“调整收入分配”,尽最大努力加以缓解。但是我们不能违背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以为这种调整就可以从此把人们带入“共同富裕”的天堂。窃以为,这是我们在应对两极分化问题时,应当具备的起码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四、现代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吗?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代经济学就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历史和运行规律的理论体系。由于该理论体系与现实生活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今天大多数国家均实行市场经济),因而在今天的经济学界,它已然被看作是亘古不变的永恒真理,并由此被认定为“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然而在我看来,这个“认定”其实是很可疑的。比如,与马克思把人性看作历史范畴不同,现代经济学把人看作是非历史的和抽象了具体社会关系的人,眼睛里永远只有孤岛上的鲁滨逊先生,并进而把孤独的鲁滨逊先生压缩成理性的“经济人”先生(马克思说:“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逊一类的故事”。[6])。在我看来,即便“经济人”可以解释小商小贩的经济行为,但如果以此观察人类社会的整个历史变迁,如此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实在是迂腐的很。
从孤独而又理性的鲁滨逊先生出发,自视甚高的现代经济学因其“经济人”假设和数学工具的运用,自以为引领和代表了真正的“科学”。一段时期以来,现代经济学在教学和研究中成了不容置疑的“圣经”,而嘲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成了很时髦的事情,比如有人不能容忍对现代经济学的怀疑,甚至已经发展到不能允许别的流派自称是某某经济学的垄断心态(除了现代经济学有资格称为经济学之外),在他们看来:“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我很敬佩西方主流经济学“海纳百川”的宽阔胸襟,但我很怀疑在现代经济学所谓“不同的经济理论”中,是否还包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按他们对“现代经济学”的界说,恐怕只有西方主流经济学才是“经济学”。如此狭隘的心胸,未免愧称“现代”二字吧。
我曾经纳闷:现代经济学为什么对自己的主流地位如此不可一世?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后,我才恍然大悟。恩格斯说:“在他们看来,新的科学(指18世纪的古典经济学——引者注)不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关系和需要的表现,而是永恒的理性的表现,新的科学所发现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不是历史地规定的经济活动形式的规律,而是永恒的自然规律:它们是从人的本性中引申出来的。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个人就是当时正在向资产者转变的中等市民,而他的本性就是在当时的历史地规定的关系中从事工业和贸易。”[7] 190—191在批判杜林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时,恩格斯说:“在他看来,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历史的发展规律,而是自然规律,是永恒真理。”[7] 比较一下历史和现实,令我感慨不已的是:当今现代经济学的认识水平与100多年以前的杜林先生竟是何其相似乃尔!
在主流经济学者看来,经济学之“科学性”应当像自然科学一样纯正,如果说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什么“不同”的物理学的话(因为我们人类所处的物理环境总是相对稳定的),那么说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学”岂不荒唐。换言之,羊就是羊,没有什么“山羊”和“绵羊”的区别。
山羊和绵羊当然都是羊,然而,牧人或许可以不去关心山羊与绵羊的区别,但把握这种区别却正是学者和教授的份内之事。明摆着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难道是“相同”的经济学吗?
就算自然科学的“同一性”的确是一个很强的客观存在,也不能由此证明经济学已经达到了“天下大同”的境界。为什么?因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极大的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相对客观和相对稳定的,社会科学研究对象是人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这种不同决定了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主观能动性”和“非稳定性”的特征,由此也就决定了社会科学的范式、理论框架、方法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历史时空、制度安排、利益趋向的制约。
现代经济学虽然对自己的主流地位感觉不错,但对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却总是缺乏自信,以为自然科学的方法才是科学。这也正是现代经济学殚精竭虑地要将经济学形式化的原因所在。不幸的是,自从经济学越来越形式化以来,这种所谓的科学也就成了“黑板经济学”,甚至被人讥讽为“狗屎经济学”(想想坊间盛传的两个经济学博士吃狗屎的故事吧)。比如在数学化的问题上,我们可能进入了一个误区:理论经济学喋喋不休地强调数学的局限性,而应用经济学则不容置疑地强调数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很有可能一直都在各自不同的语境中自说自话,根本就没有对话的基础。对于应用经济学来说,数学的必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比如金融和财会,我们总不能用“生产关系”之类的抽象概念来描述各种资金平衡表和账目吧?但是,对于理论经济学来说,数学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一点上,政治经济学尤为明显: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可能精确数量化。因此,对于数学作用的认识离不开特定的语境,换言之,当我们认定数学作用时,一定要看针对什么对象而言,离开具体的对象谈数学的作用,是无的放矢。应用经济学强调数学的必要性一万个正确,但一旦它把这个必要性扩展到理论经济学,就成了谬误;同样,理论经济学强调数学的局限性也是一万个正确的,但如果它把这种怀疑扩展到应用经济学,就大谬不然了。
恩格斯说得好:“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谁要想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那末,除了最陈腐的老生常谈以外,他显然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因此,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7]
经济学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社会科学,极而言之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我敢打赌,只要机器人不能取代人类而成为地球的主人(成为人类的仆役是可能的),那么你就别指望人的行为必然是“1+1=2”;那么期望把经济学“形式化”为自然科学的一切努力,其良苦用心或许值得尊重,但注定它是徒劳的。说句让现代经济学的教头们不高兴的话:一旦认同了经济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之后,从此就再也不会相信现代经济学代表着“永恒科学性”之类的神话,当然对于守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的、辨证的和唯物的方法论,也就有了更为坚定的信心。
标签:经济学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两极分化论文; 劳动经济学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论文; 市场经济地位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失业证明论文; 数学论文; 科学论文; 收入分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