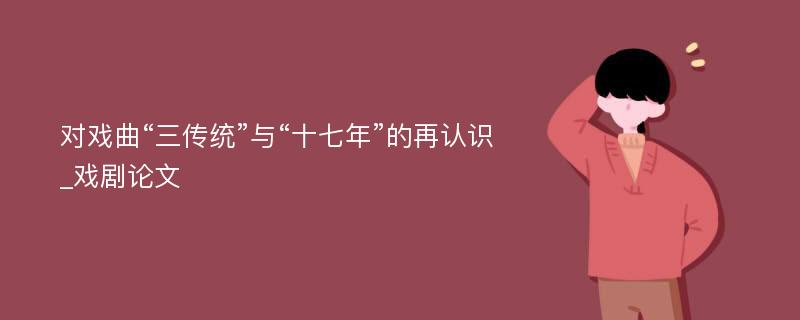
戏曲“三种传统”与“十七年”的再认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再认论文,三种论文,戏曲论文,传统论文,十七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J8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40X(2015)03-0032-07 贾志刚先生发表在《民族艺术研究》2014年第1期的文章《选择传统 贯通古今》,通过对中国戏剧传统的思考与梳理,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文章指出,戏曲从古到今至少有三种传统,即五千年的传统、近代百年改良与改革的传统、1949年至“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戏改”传统。文章中所说的“三种传统”,来源于何怀宏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整体分析并有所修正,但仍可表述得更为精细和准确。戏曲在中国文化长河中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拥有“十七年”形成的“第三种传统”,所谓的“第一种传统”,与大文化的传统脉络也并不同步。整体上说,我高度认同贾志刚提出的戏曲有“三种传统”的论断,略有补充,我觉得戏曲的三种传统分别是:从宋元至今一千年形成的古典戏剧传统、20世纪上半叶在都市剧场演出中形成的现代戏剧传统、1949-1966年的“十七年”里形成的当代戏剧传统。这三种传统虽然有共通性与延续性,然而其表现形态和内在的艺术追求又有明显的差异。它们对当下的戏曲创作演出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因而,笼统地说“继承传统”是不够的,理论家们还需要更清晰地认知,我们要继承的是什么“传统”。 我这里主要想提出与贾志刚先生讨论的,不是“三种传统”的划分与差异,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意见大致是一致的,分歧只是枝节。我想提出讨论的是如何认识十七年时期形成的“第三传统”,这里既涉及对“十七年”戏曲发展历史、尤其是对“戏改”的认识,涉及对该时期戏曲发展的基本归纳与评价,更涉及贾志刚先生所在、并且一度主持所务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十七年”的主要贡献。 诚然,“戏改”是“十七年”期间戏曲领域说得最多的词汇。张庚先生在1956年曾经呼吁放弃用“戏改”笼统地指代整个戏曲工作的习惯,认为戏曲工作应该回归常态,①不过他的呼吁没有得到正式的回应,而“戏改”及其思想方法,仍然在这个历史时期的中国戏剧界,占据着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但是“十七年”的戏曲行业发展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曲折,实难以用“戏改”这个词汇完全概括和容纳,即使在实际的“戏改”过程中,不同的思想方法和艺术取向,也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历史作用。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十七年”形成的戏曲第三传统确实与“戏改”有密切关联,这个第三传统复杂丰富的内涵,也需要加以重新厘定。 “十七年”与戏曲领域形成的新传统相关的工作,至少有三个重要且具有本质差异的方面。我希望在这里具体阐述这三个方面,冀可与贾志刚先生和戏曲理论界的同行们,一起思考与总结戏曲当代传统的定位与描述。 无可怀疑,“十七年”留下了丰富的戏剧遗产,尤其是留下了大量经典剧目。贾志刚的文章充分肯定“戏改”“收获了丰硕的成果”,因为“我们今天所观赏的绝大部分活跃在舞台上的剧目都是经过‘戏改’洗礼的优秀作品。”确实如此,今天戏曲各剧种的舞台上所演出的所谓“传统剧目”,大部分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戏改”过程中定型的。或者说,尽管除京昆之外,各剧种今天舞台上演出的“传统戏”,多数都是历史上长期大量演出,并且为各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剧目,但是它们大多数在“戏改”时期经过程度不同的修改,很少完全原封不动地保留至今。在所有剧种里,唯京剧和昆曲是其中的例外,至于京剧和昆曲的“传统戏”何以在“十七年”较少被改,我们或可以在其他场合单独讨论。 在这个意义上,“十七年”形成的第三传统之所以拥有截然不同于此前时代的特殊性,就是由于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戏”,实际上多数都经过了“戏改”时期的整理、加工和修改。经过十年“文革”,改革开放之初大量重新搬上舞台的传统戏,也基本上是这些整理、加工和修改之后的文本,而不是、或主要不是1949年前通行的剧目以及当年舞台上呈现的模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新一代戏剧演员所接受的表演艺术训练,以及他们所学习演出的传统戏,就大致局限于这个第三传统之内;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演员,更难以越过第三传统,直接从第一和第二传统中获取艺术营养。在这个方面,京剧同样成为例外,李瑞环主导的“音配像”工作的主体,就是努力接续第二传统的尝试,部分因为“音配像”的影响,许多新一代京剧演员得以熟悉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京剧保留剧目及其表演,可惜这样的大型文化工程,没有机会在各剧种普遍推广,所以对于京剧和昆曲之外的地方剧种而言,戏曲舞台上唯一仍在延续的就只有第三传统。 “戏改”之初衷,是要全面改造传统戏剧。其中最表层的是对传统戏剧思想内容层面的改造,其中,传统戏里大量以忠孝节义、三从四德这样的“旧道德”为主题和包含因果报应之类“封建迷信”思想的剧目,都是涤荡的对象;舞台表演形式方面的改造也是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被认为是色情、暴力和危险残忍的表演,要尽可能清除;至于演出制度的改造,从剧院经营方式到戏班内部的分配模式,均在其内。 当然,即使局限于思想内容方面,“戏改”也不只是消极地清除传统戏剧中与新社会的意识形态理念不相吻合的部分,还包括更积极的方面,那就是让传统剧目更趋于精致化的修改,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整理、加工、提高”。如果仅仅从美学的角度看,大量的传统戏经过“戏改”过程中的整理、加工和改造,确实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至少在文学的层面上,“戏改”不仅为中国的传统戏剧注入了更多新的文学化的表达,而且多数剧种的保留剧目,经过整理、加工与修改之后,在情节结构、人物关系和历史叙述的合理性上,尤其是戏剧的完整性上,都有更多可圈可点之处。如果说基于意识形态的改造,在一个短时期是否确实为人们所接受还难以肯定的话,如果只论对传统剧目的精致化改造,经过“戏改”时期的加工改造的传统戏很快为戏剧表演者和观众充分认可,确实有其艺术上足够的理由。 戏曲传统剧目文学性的大幅提升,最直接的原因,是大批比艺人有更好教育背景的文人参与到“戏改”的进程中。客观地说,各地方剧种传统剧目的水平参差不齐,原因也很简单——大部分剧种的保留剧目,多数是在明清以来的实际戏剧演出过程中逐渐成形的,而不是艺人按照现成的文人创作的剧本演绎的结果,所以,这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传统戏的创作主体主要是艺人而不是文人。由于传统社会中艺人处于社会边缘,一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因此这类在艺人的实际演出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剧目,在文字表达上难免有欠缺和粗陋之处;至于说到美学趣味,有时质朴与粗鄙的界限实难以区分。因此,即使那些最为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保留剧目,从文人的立场看,在文学上也并不见都很完美。以艺人为中心建构的戏剧传统有其与生俱来的这一缺陷,恰恰成为“戏改”时期传统戏被全面改造最理直气壮的理由和“戏改”的前提。 至于“戏改”时期之所以有如此之多受过较好教育的文人参与戏剧,当然是政府主导的结果。由于戏剧工作在20世纪50-60年代的特殊重要性,在“戏改”过程中,各地各级政府调动大批社会精英参与其中,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社会资源(包括具体表现为大量知识分子参与的优质的知识资源)最集中地被倾注于戏剧行业中的前所未有的现象。一批受到更好教育的人才深度参与和介入戏剧行业,对提升戏曲剧目的文学水平和美学高度的作用显而易见。 因此,对传统戏系统的、大规模和大范围的整理、加工和修改,是“十七年”留给今人的戏剧文化遗产中最明显的特点,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那批高水平、并在舞台上保留至今的优秀剧目,包括这些剧目因成熟而相对凝固化的表演形制,就构成了中国戏剧第三传统的核心部分。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充分肯定“戏改”过程中形成的戏曲第三传统在美学上的成就。然而衡量与评价戏曲的第三传统的成败得失,还需要引进更多的视角。经过“戏改”干部的“整理、加工、改造”之后的经典剧目,或许在新文学的视野中确实明显“提高”了,然而,假如把这些剧目回置于传统文化的格局中,评价结论也许会截然不同。假如我们只是静态地、孤立地看待这一时期留下的戏剧作品,局限于当事者的立场去感受判断它们在艺术上达到的高度,显然既不客观也不全面。换句话说,对任何艺术作品的评价,都需要引进历史的维度,评价第三传统,始终要将它们的第一传统与第二传统相比照,方可获得理性与公正的认识。 首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戏改”过程中形成了戏曲第三传统,但这并不是戏曲艺人和观众在各种不同形式和不同性质的剧目及演出的自然竞争中留下的。这个新的传统不仅是在政府强势推动下实施的,而且更是“戏改”最初的主导者要求斩断在此前形成的传统的特殊背景下形成的,这使得戏曲的第三传统与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第二传统的关系,缺乏第二传统和第一传统之间的自然接续与过渡。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只拥有这个传统,就想当然地以为这就是历史的选择,甚至以为这是历史唯一的选择;因为“戏改”最初的主导者对历史持有几乎完全否定的态度,并且据此实施了一系列严厉禁戏的政策。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50-60年代,在当局管理成效不彰的区域和演出场所内,那些未经修改的传统戏的竞争力,决不下于经过“戏改”工作者“整理、加工、提高”之后的作品。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政府需要推进相当严厉的行政措施,通过完全封锁传统戏的存在方式,为“戏改”的成果腾出生存空间,否则“戏改”就难以推进。这样的行为在“文革”期间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我们可以承认“样板戏”取得了某些艺术成就,但要看到“样板戏”之所以深入人心,是由于在长达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其他的戏曲形态与剧目都被打入冷宫,所以它的传播与普及的效果是通过文化上极其粗暴的极端手段取得的,而不是艺术创作中自然竞争的成果。②所以,简单化地以为“戏改”对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就是对它们的“提高”,以为那些未曾留传至今的作品,都是因观众不喜欢而被自然淘汰的,恐怕十分片面。 “戏改”通过政府的力量,开启了中国戏剧的一个新阶段,如同当年的“戏改”工作者所称,它可以称为“定腔定本时代”,其实这也是中国戏剧的第三传统中最具特点的方面。传统戏中大量的经典剧目因为是在不同的地区、剧种和不同的戏班、演员的实际演出过程中发展形成的,所以几乎每个经典剧目都有数不胜数的不同演出本。中国戏剧传统因此拥有令人骄傲的丰富性,更因为“演活戏”的传统,而让戏剧本身充满活力。但是“戏改”中意识形态优先的政策制定者们,不接受这样的丰富和活力,而更希望通过严格的管制让每部剧目的表达方式均归于一统,以维护它们在政治上或艺术上的纯正性,当然,这里所说的“纯正”只是他们理解中的“纯正”。“戏改”中所提倡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这一领域显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执行。 还需要指出的是,今天包括在戏曲第三传统里的那些“传统戏”,实际上只不过是各剧种原有的剧目体系中很有限的一部分。相关的历史资料说明,从1947年华北人民政府成立戏剧音乐委员会到东北地区人民政府的戏剧主管部门,还有北平和平解放后的军管会,都陆续下达大规模禁戏的行政命令,这一趋势蔓延到全国各地,禁演剧目中很多是各地各剧种影响深远的保留剧目。几乎所有地方剧种,原来都拥有艺人和戏班奉为经典的所谓“江湖十八本”“江湖三十六本”等自成体系的保留剧目,它们不仅代表了各剧种最具特性的舞台叙述方法,而且更是每个剧种独特的表演手段的汇聚。这些剧目原本就是传统社会中人民群体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伦理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的载体,因而和“戏改”年代倡导的意识形态诉求,难免有相龃龉之处。其中固然有一部分经过修改之后被认为可以继续存在且也确实经整理、加工和改造后留在了舞台上,但各剧种的剧目体系中相当大部分的传统剧目,或因未及修改,或被认为难以修改,或者仅仅由于“戏改”干部关注度或能力的欠缺,就一直被束之高阁。甚至常有报刊发表某人一篇批评文章,一出经典剧目就被禁演、停演的现象,《戏剧报》1956年的一篇社论称之为“一言以毙之”[1]。大量优秀剧目被禁演、停演,“戏改”至今已经几十年过去,舞台上的表演者历经几次代际转换,这些剧目的演出形态早就失传。 戏曲的第三传统是对第一传统、第二传统严格筛选之后的再造。这一筛选与再造,从出发点到实施的过程,都很难说完全吻合中国的戏剧传统。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批“戏改”干部所接受的教育,更侧重新文化领域,并不在中国戏剧得以滋生的传统文化的有机系统范畴内,因而他们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才有可能获得对中国戏剧传统的认识与理解。所以,他们并不是在理性和感情两方面接受了这个传统的内在价值体系之后再来实施对传统戏剧的“加工、整理”的,相反,他们从外部进入来“改造”传统。尽管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化部门就一直强调充分发动艺人,要“依靠老艺人”,但是在“戏改”实际过程中艺人群体始终处于被动地位,是不争的事实。其实,文化部门之所以需要反复强调对老艺人的尊重与依赖,恰恰就是由于在“戏改”过程中老艺人的积极性和参与感一直十分欠缺。这当然是由于“戏改”所遵循的原则,完全在老艺人们的知识与经验积累之外,而且这些复杂抽象且远离戏曲实际的理论,也不是参加了文化部门开办的几次学习班就能理解,更遑论认同。 因此,“十七年”的戏曲事业既有成绩,也有教训。我们不能只看到“戏改”的成就,忽略了问题。我们固然要看到“戏改”留下的剧目的优秀和精彩,但不能忘记有太多同样优秀甚至更优秀的作品丢失了,同一部作品的更多种精彩的表达被舍弃了。各地方剧种的传统戏经历改造之后,文学性固然有明显提升,但传统戏剧为之付出了沉重代价,而这当然也正是民族艺术经受的巨大创伤。所以,我们需要全面、完整地认识与把握“戏改”时期形成的戏曲第三传统的得与失,给它更公允的评价。 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其实只有1957年上半年的大约8年时间里,“戏改”才是戏曲领域发展变化的主轴。如前所述,20世纪50年代初的“戏改”运动对传统剧目采取的是“剔除糟粕、汲取精华”这种价值模糊的态度,充分说明“戏改”主导者面对中国戏剧的第一和第二传统时首鼠两端的矛盾心理。当大批“戏改”干部受政府指派,几乎完全接管了戏剧事业的主导权时,他们中的多数人最初都自信满满,然而对传统戏剧接触越多,了解越深入,就有越多人被激发出崇敬与迷恋之情。在这个时期,文人不只是参与“戏改”,更是在接受戏剧传统的熏陶,并且逐渐改变了原先歧视传统戏剧的立场,最终尽可能地保留了传统剧目的生动、精彩、深刻与魅力。经过“戏改”时期整理、加工和改造的保留剧目中主要的精华,大多数恰恰是从第一传统和第二传统中继承来的。这是在“戏改”过程中,中国戏剧的伟大传统最终并没有完全断裂的主要原因。评价戏曲的第三传统时,如果只看到“戏改”工作者对传统的改造,看不到传统的继承,那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文化的悲哀。 而且,我们不仅要看到“十七年”对传统戏剧的改造,同时必须看到对“戏改”的纠偏,尤其是“纠偏”中体现的继承与保护传统的努力。早在大规模的“戏改”运动开启之初的1950年,如何防范与纠正持极左观念的“戏改”干部们对中国戏剧传统粗暴的打击,尽最大限度确保戏剧传统的延续性,就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戏改”时期最耐人寻味的现象,就是中央政府文化部所扮演的角色。由田汉主持的文化部戏改局(其后并入艺术局,局长仍是田汉)在“戏改”事务中最初的重要举措,不是经过周密的考虑,确定并颁布一系列普遍适用的原则,而是将“禁戏”权限收归中央。从1950年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直到1956年、1957年两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从田汉到中宣部、文化部领导的讲话,都反复强调不允许地方政府擅自禁戏。政务院1951年颁布的“五·五指示”里非常明确的指示,“对人民有重要毒害的戏曲必须禁演者,应由中央文化部统一处理,各地不得擅自禁演”,[2]《人民日报》也发表社论,强烈批评地方上那些“对民族戏曲的优良传统,对民族戏曲中强烈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毫不理解;相反地,往往借口其中含有封建性而一概加以否定,甚至公然违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不经任何请示而随便采用禁演和各种变相禁演的办法,使艺人生活发生困难,引起群众的不满”[3]的戏曲工作干部。而用周扬的话说,“有人要禁戏,我们必须禁止他们禁戏”[4]这里的所说的“有人”,除了他的下级机关及其所指派的“戏改”干部之外,实在找不到另外的所指。而这些由高层通过不同的形式反复强调且言辞激烈的批评,充分说明在全国各地,极左倾向在“戏改”运动中很有市场,而地方政府与“戏改”干部们无端禁戏的现象也决非个案。 如果说中央政府以及宣传文化领域的高官们最多关注的各地普遍存在的禁戏过多的现象,那么,在1950年到1957年的“戏改”期间,以张庚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为主的学者群体,他们承担着另一方面的重要工作,那就是从理论上努力张扬和维护传统戏剧的价值及其存在合理性。更直接地说,他们同样在旗帜鲜明地反对“戏改”中的极左倾向,但是表达的方式以及所针对的具体对象另有侧重。 在20世纪50年代初,张庚、郭汉城等前辈学者在不同场合,通过对《蝴蝶杯》《秦香莲》《斩经堂》等剧目的分析,强调传统戏剧中许多优秀剧目包含丰富的“人民性”。如同这个时代的戏曲理论家强调传统戏曲的表演符合“现实主义”原则一样,“人民性”也是从苏联文艺界搬运来的范畴,而且,如同当年意识形态倾向相对温和的苏联文艺理论家运用“人民性”为帝俄时代优秀作家的价值辩护,有效地制止了“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倾向,“戏改”时期的优秀戏曲理论家巧妙地借用了“人民性”这一重要概念,为传统戏里大量包含“忠孝节义”之类“封建思想”且以为之主旨的剧目,争取到了在新社会继续存在的理由。肯定大多数传统戏具有“人民性”,将戏曲非写实的表演划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不仅不是理论上的突破,还充满了美学的误读和附会,但是历史地看,假如没有这种基于政治智慧的借用,中国的戏剧传统在“戏改”年代完全断裂,并不是没有可能。 张庚1956年在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的专题报告《打破清规戒律,端正衡量戏曲剧目的标准》,③更是运用“人民性”的范畴批驳“戏改”时期戏曲剧目甄别与衡量中流行的极左思想的范本。张庚明确指出,“我们在衡量剧目,特别是传统剧目方面存在一些思想上的混乱。这些混乱是造成目前戏曲舞台上剧目贫乏单调的原因之一,甚至可以说是主要原因之一;而剧目贫乏单调,又是目前戏曲艺术向前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在衡量剧目的看法方面有混乱的情况,就造成了一些衡量剧目的不成文的清规戒律,使得剧目的上演、特别是传统剧目的上演和整理、改编以至发掘都受到许多不必要不应有的限制。”④[5](P244)张庚先生在报告中,详细分析了这些“清规戒律”,打破这些清规戒律的呼吁,更是他这一长篇报告贯穿始终的内容。 在“戏改”时期,以张庚为代表的戏曲理论家们为纠正“戏改”中的错误观念,针对各地“戏改”过程中大量存在的极左思想和粗暴做法,展开了系统、全面与集中的批评。1954年之后的几年里,批评和纠偏的立场更直接坚定。张庚发表了题为《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的长文,批评“粗暴地禁戏改戏,片面强调配合当前政治任务而不注意、甚至完全不注意戏曲艺术本身的发展;不顾实际情况脱离传统地强调改革;不依靠艺人,而用包办代替的办法进行工作等等”,并且认为“这种情况带有普遍性。”[6]文章尖锐指出,正是由于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影响和对苏联文艺政策的机械搬用,导致了脱离中国戏剧传统、几乎全盘否定中国戏剧传统的“教条主义”思想与态度。就在这篇文章里,他提出要取消“戏改”或“戏曲改革”的说法,避免用“戏改”取代戏曲事业。他提出“发展民族艺术必须反对洋教条”,对那个时代流行的“迷信外国人从外国的艺术实际中所总结提升为理论的条文,以为可以逐条运用在我国艺术实际上面,成为衡量我国艺术的绝对标准”[7]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毫无保留的批评,他的这些见解的针对性,当然也非常之明确。他还明确反对机械地将戏曲表现现实题材等同于强调作品的思想意义,在华东区戏曲观摩大会上提出“诸如京剧、绍剧、梨园戏、莆仙戏……这些比较古老,基础较形态较固定的剧种,我们从事改革,从事表现现代生活问题上就须要慎重。”[8] 张庚先生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50年代公开提出这些重要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正是由于他深刻认识到“我们必须继承传统。新戏曲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不能撇开传统从新另搞一套,而是要在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与发展。因之,首先就是必须把传统继承下来。”[9]因此,我们固然要看到“戏改”时期对传统戏剧的“改”,同时还必须看到以张庚为代表的戏曲理论家和包括田汉、周扬等人在内的文化官员还在呼吁与实际推动传统戏曲的“守”;张庚1956年明确提出要“取消”的,也绝不仅仅是“戏改”这个词汇,其深层含意早就已在其中。所以,“十七年”是有其复杂性的,绝不是“戏改”的铁板一块。看不到其中的复杂性,我们对“十七年”,尤其是对1957年之前戏曲行业的全貌,就不可能有准确和完整的把握与认知。 诚然,从1949-1966年,在大多数年份和大多数场合,左的思想与理念都占据上风,对支撑着“戏改”的所有政治观念的质疑,都很难真正出现,更遑论形成气候。田汉说要把禁戏的权限收归中央,但地方上仍然有无数种手段禁戏;周扬说要“禁止他们禁戏”,然而实际上大量的戏还是被“他们”禁了;张庚说要打破“戏改”中的“清规戒律”,但在1957年“反右”和1966年开始的“文革”期间,类似的“清规戒律”发展到了极点,张庚本人为自己辩护的机会也不复拥有。在这样的大环境中,即使周扬、田汉这样有艺术情怀的官员、张庚这样勇敢与智慧的理论家,以及梅兰芳这样著名的表演艺术家,都不得不说很多趋时的违心话,只能迂回曲折地表达他们的观点。但是他们对待中国戏剧传统的立场与态度依然十分清晰,同时为后人树立了很好的榜样。我们不能忘记他们在“十七年”为戏曲传统的赓续所做的不懈努力与杰出贡献,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简单地将“十七年”归纳为“戏改”。而且,在1949年之后艰困的政治环境里,戏曲界上述种种“纠偏”的理论与措施,实为这个时代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戏曲理论遗产。这份遗产,或许比“戏改”更有现代性,更具文化价值。 确实,中国戏曲的传统有独特的丰富性,“十七年”中国戏剧形成了不同以往的第三传统,这段历史无法改变。我们要打破对“戏改”的迷信,赋予“十七年”形成的第三传统更丰富与更积极的内涵。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中国戏曲的三个传统——宋元以来形成的古典戏剧传统、20世纪上半叶形成的现代戏剧传统和“十七年”形成的当代戏剧传统,相互关联,不绝绵延。这就是我对中国戏曲三种传统的一点认识。 注释: ①张庚:《反对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来“改革”戏曲》,《文艺报》1956年第13期。这段话出现在文章的注释中,在后来的各种文集里,不知为何注释均被删去。 ②“文革”结束后,劫后余生的周扬在文章中感慨地反思当年“戏改”的粗暴,他说,“粗暴倾向,发展下去,可以走向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和虚无主义。三十多年戏曲改革的历史告诉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和克服粗暴的现象。”(周扬:《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戏曲艺术》,《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从“戏改”到“文革”,有很多现象可以印证他这段有明确针对性的经验之谈。 ③这份报告在《文艺报》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完全没有了原报告的标题的锋芒。张庚先生在编选自己的文集(包括《张庚文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时所用的是公开发表版,但是报告较原始的版本早就在各地戏曲界流传。 ④这份报告在《文艺报》公开发表时,标题改为《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完全没有了原报告的标题的锋芒。张庚先生在编选自己的文集(包括《张庚文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时所用的是公开发表版,但是报告较原始的版本早就在各地戏曲界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