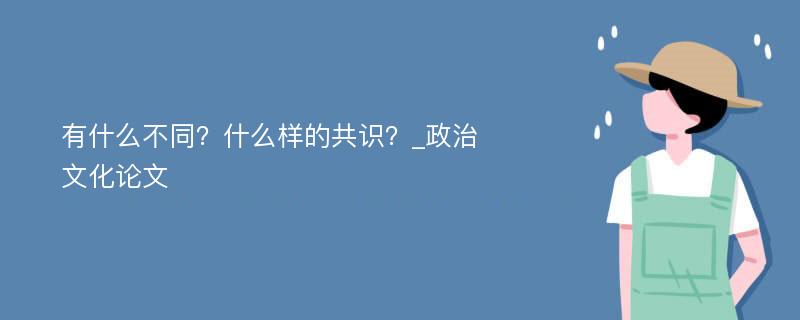
哪些差异?何种共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共识论文,差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10)05-0001-05
自麦金太尔的《谁的正义?何种合理性?》1988年出版以来,多有学者采取类似其提问的方式,本文也是如此,但基本取向则有异。和麦金太尔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正义观念的差异是不可通约的,没有公度性的,或者说是无法对它们形成共识的,而是认为恰恰在正义的问题上形成某些最基本的共识是可能和必要的。问“谁的正义”预示了正义总是某种主体的正义,而现代“正义”不能不预设某种普遍的、一视同仁的观点,虽然从“一国的正义”到“国际的正义”会有一种范围上的缩小,这种缩小是和“权责相应”的原则相关的,但有一些最基本的价值内核是共同的。而人们在形成共识的过程中,也可以努力诉诸一种公共理性(但我心里虽然对问题的回答是有某种倾向性的,我还是在提出问题,因为我心里还是有许多的困惑)。
当今世界,愈是承认和尊重差异,也就愈是需要寻求共识。差异是事实,而共识也有某种客观的根据。只是我们需要分析,究竟是哪些差异被人们挑出来认为不仅是重要的、而且是相当根深蒂固的,我在这里特别想指出一个今天容易被遮蔽的差异——民族乃至种族的差异。而如果要保持合理的差异,保持“和而不同”,在如何对待这些差异上恰恰可以形成某些共识。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共识呢?在多元的背景下是否可以有这样一种共识呢?我同意一种根本性的共识就其范围而言是一种政治领域内的共识,但就其性质而言,我认为也是一种道德共识。而如果连强调多元和冲突的思想者也承认有这样一种道德共识,那么寻求它就的确不仅是有必要的,也是有可能的。
一、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征:全球化与多元化共存、差异与平等并倡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生活相当一体化的时代;又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是一个“道为天下裂”的时代。从现实状况讲,我们有联系极其密切的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交往、但却没有全球化的道德、政治和信仰①。或者说,人类在物质的、有形或形而下的方面越来越接近,越来越趋同;而在精神的、文化的、形而上的方面却越来越分离,越来越有一种求异的倾向②。有一种“语言”所有民族都能够懂,都挺会用或不得不学着用,那就是金钱的“语言”、交易的语言;但文化、价值、信仰的语言却千差万别。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强烈要求平等的时代,又是一个特别强调差异的时代。这是矛盾的吗?抑或是相互包含的?要求平等正因为存在差异,各个阶层、各个群体、各个个体之间不那么平等,所以才要求平等;人其实并非“生而平等”,所以才要求与生俱来的“平等对待”。而存在差异也恰被一种形式平等的要求所彰显。要求差异也同样是时代的一种要求,一方面似乎有无数的差异,但另一方面又似乎只有不多的几种差异。价值追求从事实存在来说是多元的,从主要差异或矛盾来说又常常呈现为二元的;从实际的主流和支配趋势来说又常常是一元的。也许所涉及的这一切差异和平等的问题都是一个范围和程度的问题?但我们又可发现一些根深蒂固的、无法泯灭的、甚至注定要发生冲突的差异。
世界似乎一方面越来越“趋同”,同时也越来越要求“认同”。但这两个“同”并非同一个“同”。“趋同”是在外的、自然的事实;“认同”是向内的、内心的要求。或者说,一方面是所有文明、民族、甚至个人的某种“趋同”,尤其在物质生活方式方面;另一方面,“认同”是指对全人类之下次级文明、文化、团体的“认同”,实际上是强调乃至扩大差异。在精神文化上,愈是强调对一个群体的“认同”,这世界的文化价值也就愈加不同。这种“不同”不仅是事实上的,也是现代价值认可和要求的,即认为差异应当被视作“正常”。差异在要求得到承认,也要求相互之间有一种平等。人们一方面要求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另一方面又要求扩大平等。或者说,许多人要求一种物质状态上的平等,同时拒斥精神状态上的平等?
其实,人们的生活追求与其说是求“同”,不如说是求“异”,而且只要有可能的话,会追求一种向上或居上的“差异”,但是,即便只是为了这种求“异”,为了保障这种求“异”能够正常进行,他也必须求“同”,即他必须努力和其他人形成某种共识,以不至于在追求自己所理解的幸福时互相妨碍或互相拆台。这种“同”也就是有关其行为、手段的某些具有政治范畴和道德性质意义的基本规范的共识。
也许人类面临的形势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乐观而又悲观:人类所掌握的物质和军事力量极其强大,而使人类能够联系起来的精神和文化纽带却极其薄弱。这里甚至潜存着某种凶险:这是人类第一次面临这样的处境——多元化使人类在遇到“全球浩劫”时不容易有真正的全球权威。甚至不会有时间让人类形成真正这样的权威;而全球化、人类的一体化使人类的文明如果有衰落或灭亡就不再能够像过去的历史文明那样“此伏彼起”,而是命运共担。的确,脱离了“冷战”时代,人类进步了,面对差异甚至对立,人们不再优先考虑诉诸武力,用武力解决冲突,而是学会了使用经济手段,学会了谈判和妥协。但基本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在一个存在差异、甚至认为这种种差异的存在不仅是合理和正常的,而且是合德和正当的情况下,还是不是要寻求某种共识,以使差异必然要导致的矛盾和冲突不致造成大难,不致使社会分崩离析甚至人类文明毁灭?
二、哪些差异?
对人类世界,从各种各样的角度观察,几乎可以说有无数种差异,就像蒙田所说,人与人之间是多么的千差万别。差异最后都会落实到个人,但个人又是有各种不同传承和身份的,是结为各种不同群体的,亦即对人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观察,也可以从某一“类”即群体的角度来观察、概括、辨认和区分。这就涉及到了“同”:某些种族、国籍、信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相同或类似的人们被归到了一起,从而与其他群体的“同”有所“不同”,于是形成了群体的差异。
我们这里自然只谈群体的差异。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的大的差异有政治性的乃至法律明文规定的社会等级的差异,有马克思揭橥的以经济为基础的阶级差异,这些差异往往被认为是巨大的、根本性的,乃至构成一种对立、一种历史的主要动力,其对峙性的冲突需要通过不断的流血斗争、暴力革命或者一个阶级的专政来解决。
究竟是看重和强调哪一些差异,反映出一个时代或社会的变迁。今天,我们更经常谈到的是“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是一个比较温和、也比较包容和广泛的概念,对之仍然可以有很多的观察角度,比如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等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谈到一种重要的由质量引起的数量差异,即一种少数与多数的差异,如果承认这是一个真实的差异,“解放”就要成为问题,“启蒙”也要碰到它的限度。
不过,在这里,我想进一步限定自己只谈一种文化差异,但或可说是一种最重要的文化差异,即一种和历史文明与民族国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文化差异,比如说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差异、中国文化和美国文化的差异。虽然我们说,这种差异也是可以独立观察的,我们有时会直接说文明、国家、宗教、民族或种族之间的差异。它们不像是从属的概念,而是交叉的概念,而在交叉的时候,就有了一种互相限定。
那么,就说一种广义的“文化差异”,这种差异中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文化差异”中,其中有两种最为重要的差异:一是宗教的或信仰的差异,这是最高和根本追求的差异,或者说“高端的差异”;二是民族或种族在生理体质、性格气质、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差异,这或可说是“底部的差异”,是属于这个群体的个人与生俱来的、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被积淀和决定了的差异。其中有些差异几乎可以说是无可改变或很难改变的,比如说肤色、体质乃至语言。我们现在就主要来讨论这后一种差异。它涉及到一些根深蒂固的差异,然而在今天却几乎不谈、讳莫如深,尤其是族群和种族(ethnicaily and racially)方面的差异。
我想在这里重温一段梁启超在一百多年前的论述,即他在1903到1906年写成的《新民说》中第四节“就优胜劣败之理以证新民之结果而论及取法之所宜”中有关种族或族群差异的论述。在他看来,若比较世界的黑、红、棕、黄、白五色人种的差异,白种人最优;而在白种人中比较,条顿人又最优;在条顿人中比较,盎格鲁撒克逊人又最优。因为,在五色人种中,白种人最为好动和进取;在白种人中,条顿人的政治能力、自治能力、结成团体的能力最强;而在条顿人中,盎格鲁撒克逊人之所以最优,则主要是因为其能在团体中保持个性,最能够独立自助③。
梁启超的论述有如下特点:第一,他是从人种立论,但是并非注重种族之间的体质特点,而是强调它们的性格气质能力方面的特点,是否在这两种自然与文化的特点和能力之间存在联系,他没有谈到,但也可以说隐含了一种联系;第二,他不仅是毫不忌讳地谈种族差异,而且是从优劣的角度谈这种差异,且自认本族为劣④;第三,当然,他认为本族为劣并非是全面的论述,他后来也谈到过中国人的优点,但是,他讨论的主要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所观察的中国人的特性,在这方面,他自然是视中国人为弱势的,但他并不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他希望着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世界上达到优胜,希望中国能够臻于富强⑤。
而这也不仅是梁启超一个人所言,也是其时相当占主流的思想气氛,只是梁启超作为当时“言论界巨子”,他的影响自然更大些。上个世纪之交的中国士人感觉有“亡国危种”的危险,希望“保国保种保教”,所以特别注意种族的分别、尤其是优劣的分别,由此还产生国民性的分析和改良国民性的急迫愿望。此风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中叶,比如潘光旦译述《优生原理》,一个比较根本的变化是发生在二战之后,这自然和“第三帝国”的覆亡有关。的确,此前尚没有这方面的政治禁忌,而即便有这种政治禁忌,由弱小民族提出这种差异似乎也要比强大民族提出较不易触犯这种禁忌。今天的西方世界,像美国的思想学术界,一种“政治正确”的约束使诸如种族的差异不便提及,尤其是优劣方面的比较更几乎无人敢去触及,但这样的差异是否就不存在呢?或者说,即便存在,也还是不提、“不争论”为好。就像有人批评亨廷顿,说他的“文明的冲突”的预测就像是一种说出来或说多了就会自我实现的预期(self-fulfling expectation)。当然,对这样一些差异的认识可以隐藏在诸如“文化的差异”或“文明的冲突”之下。无论如何,如果意识到这些差异的存在并且根深蒂固,如果意识到这些差异至少在可见的未来并不能够融合或者泯灭,或将使人们更加迫切地寻求一种共识,寻求一种如何对待这些差异的共识。
三、何种共识?
就像有多种差异一样,也有多种范围内的共识,比方说在国际政治的领域内,有两国或多国之间对某些问题达成的协议或共识。这些共识可以说都是政治共识,它们不仅是政治范围内的共识,甚至也可以说是纯粹或狭义性质的政治共识——如果将政治理解为必定要有妥协、“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的话。当然,追溯下去,一种不纯粹是制胜策略(即并非最终的目的还是一定要吃掉对方)的妥协也还是具有某种道德意义。
但共识肯定不能仅仅是一些临时性的、权宜性的妥协和协议,我们还希望寻求一种更具有根本性的持久共识,本身就具有一种目的意义的共识,如此才能真正保障合理的文化差异,保证和平的列国共存。如此,就还需要寻求一种道德性质的政治共识。这种道德性质的政治共识应是对一些具有根本重要性的政治价值的共识,也是具有普遍性和恒久性的政治共识。
这种共识的范围是政治的,而性质是道德的。这样一种有限的范围也是显示其重要性,即我们需要、或首先需要、且特别需要在涉及权力、暴力这样的强制力量的地方达成共识。这方面一个最好的说明就是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这种政治自由主义实际也就是政治范围内的、或以政治为对象的道德哲学,或径直说“政治哲学”——就像伯林将政治哲学视作伦理学的一个分支一样⑥。
罗尔斯认为他的政治自由主义的目的,就是寻求一种作为独立观点的政治正义理念。这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有三个特征:作为一种应用于政治领域的道德观点;作为一种独立于广泛理论的道德观点;通过某些隐含在民主公共政治文化中的政治理念来表达。他谈到政治的正义观是一个道德观念,但是是用于一个特殊领域内的道德观念:即是用于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道德观念。说这一观念是道德的,是指该观念的内容是由某些理想、原则和标准给定的,而这些规范明确表达了某些政治价值。但这种道德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广泛的道德理论,这种政治的正义观念与其他道德观念的分别,乃是一个范围的问题,也就是说,两种观念的区别乃是一种这一观念所应用的对象范围与一种较广范围所要求的内容之别⑦。
所以,我理解罗尔斯所说的政治正义观念,或他希望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的“公平的正义”理论,其对象范围是政治的,而其性质是道德的。罗尔斯强调,“重叠共识”绝非一种临时协定、绝非政治上暂时妥协的权宜之计,这也就表明了这种共识的道德性质,这种共识是根本性的原则规范,它之所以有可能成为人们的共识,因为其核心内容本身是具有一种客观普遍性的根据的。
谈到这种共识的内容,罗尔斯提出了他的两个正义原则。的确,我们可以从《正义论》出版近四十年来围绕着它的批评、讨论和反应观察到,一个民主社会的大多数人大致不难在他的平等自由的第一正义原则和第二正义原则中的机会平等上达成共识,但在第二原则中的“差别原则”上却存在较多争议。而罗尔斯自己也认为,虽然可以在一个政治社会的内部采用最照顾最弱者利益的“差别原则”,这一原则却不宜推广到国际政治的范围内采用。而孔汉思等学者主要针对国际政治提出的以“四不戒律”为核心的“全球伦理”,则是在这方面更加缩小范围和降低要求的,也渴望达成更大范围内的共识的道德文本。只是人们可能不屑于此,会有更高的抱负和期望,追求更高或更多的东西。但是,在我看来,随着群体范围的扩大和强制性的增加,道德要求的高度或强度也应该是递减的,或者说道德要求的范围需要相应缩小。
总之,要使根深蒂固的、并更加强力地固定在国家形式中的种族、民族的文化差异不致变成血与火的、两败俱伤的、甚至同归于尽的冲突,就有必要寻求一种道德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如何对待文化差别和民族差异的根本态度的共识,就是如何与他族和他国和平共处的基本共识。这种国际正义共识的核心是一种生命原则,是一种对生存平等的共识,从否定的方面来说,就是不杀戮、不抢掠等。我以为这种共识只可能在这样一个基本的层次上形成,在一个缩小的范围内形成。这个范围基本是在政治或法律的范围之内,这个层次是基本的道德规范的层次。只有这样的共识才有可能为各种在价值和信仰追求方面迥异的文明、文化所认同,因为它们实际已经包含在各种文化的核心规范之内,自身也具有一种客观的可普遍化的逻辑根据。
这样一种共识是可能达到的吗?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但在这里,我不再仔细地讨论“如何可能”⑧,而只是展示两个相当强调(或者说承认)差异和冲突的思想家的观点。一个是伯林,他是非常强调价值多元论和文化多元化的,但他也还是认为,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渲染各种价值的冲突,“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人们早已有过大量的广泛的共识。当然,不同的传统、看法、态度或有合情合理的差异,人的需求无穷尽,然而基本的原则可以超越其上”。“归根结底,这并不纯粹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普遍的价值即便不多,最低限度总是有的,没有它,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今天,很少会有人为了追求快乐、利益、甚至是政治的优良,去为奴隶制、杀人祭神、纳粹的燃烧弹或者肉体的刑讯辩护;不会再像法国和俄国革命时所主张的那样,赞同子女有公开抨击其父母的责任;更不会认可无情的杀戮。在这一问题上妥协,是没有正当理由的”⑨。
提出“文明的冲突”一说,对文明(或文化⑩)的融为一体不怎么抱希望的亨廷顿也写道:“文化是相对的,道德是绝对的。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指出的,文化是‘深厚’的,它们规定体制和行为模式以引导人们走上一条对某一特定社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然而,高于、超出和产生于这一最高标准道德的,是‘浅显’的最低标准道德……也存在着最低道德的‘否定性戒律,最可能的就是反对谋杀、欺诈、酷刑、压迫和暴政的规则’。人们共有的‘更多的是共同的敌人(或罪恶),而不是对共同文化的责任感’。人类社会是‘普遍的,因为它是人类的,特别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然而,‘浅显’的最低道德的确产生于人类共同的状况,而且‘普遍趋向’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文化的共存需要寻求大多数文明的共同点,而不是促进假设中的某个文明的普遍特征。在多文明的世界里,建设性的道路是弃绝普世主义,接受多样性和寻求共同性。”(11)亨廷顿这里所说的要“弃绝”的“普世主义”是指文化价值追求上的普遍主义,即以一种文明模式或其价值统一世界;而他所说的要“寻求”的“共同性”则是一种基本的规范伦理。
这样,或许我们最后可以不无揶揄地说,如果在最难达成共识的知识分子中间也能初步形成一些这样的道德共见(12),那么,我们的确有希望在范围远比这更广大的人们中达成类似的共识。
收稿日期:2010-05-28
注释:
①或如孔汉思所说,我们有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但没有一种全球性的伦理。
②今天要当一个隐士是很不容易了。在物质生活方面,要完全不借助现代物质和技术手段也几乎不可能。比如最近一个尝试“极简生活”的西方人,还是不得不保留手机等联络手段。
③见《新民说》第四节,梁启超写道,盎格鲁撒克逊人即英美人“其独立自助之风最盛。自其幼年在家庭,在学校,父母师长,皆不以附庸待之。使其练习世务,稍长而可以自立,不倚赖他人。其守纪律循秩序之念最厚,其常识(Commonsense)最富,常不肯为无谋之躁妄举动。其权利之思想最强,视权利为第二之生命,丝毫不肯放过。其体力最壮,能冒万险。其性质最坚忍,百折不回。其人以实业为主,不尚虚荣。人皆务有职业,不问高下。而坐食之官吏政客,常不为世所重。其保守之性质亦最多,而常能因时势,鉴外群,以发挥光大其固有之本性。以此之故,故能以区区北极三孤岛,而孳殖其种于北亚美利加、澳大利亚两大陆。扬其国旗于日所出入处,巩其权力于五洲四海冲要咽喉之地,而天下莫之能敌也。盎格鲁撒克逊人所以定霸于十九世纪,非天幸也,其民族之优胜使然也”。
④梁启超以下言论甚沉痛:“吾观我祖国民性之缺点,不下十百,其最可痛者,则未有若无毅力焉者也。其老辈者,有权力者,众目之曰‘守旧’。夫守旧则何害,英国保守党之名誉历史,岂不赫赫在人耳目耶(现内阁亦保守党)?然守则守矣,既守之,则当以身殉之。顾何以戊戌新政一颁,而举国无守旧党者竟三阅月也。义和团之起也,吾党虽怜其愚,而犹惊其勇,以为排外义愤,有足多焉。而何以数月之力,不能下一区区使馆也?而何以联军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顺民旗,不复有一义和团;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复有一义和团也!各省闹教之案,固野蛮之行也。虽然,吾闻日本三十年前,固常有民间暴动,滥戕外人之事。及交涉起,其首事者,则自戕于外国官吏之前,不以义愤贻君父忧。而吾国民之为此者,何以一呼而蜂蚁集,一哄而鸟兽散,不顾大局,而徒以累国家也。”见《新民说》“论毅力”一节。
⑤梁启超说“使黄人能自新以优胜于白人”,则他日能“代之以兴”。
⑥伯林:“政治哲学,也就是应用于社会的伦理学。”见《扭曲的人性之材》,岳季坤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⑦见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万俊人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4页。
⑧“如何可能?”的一个主要理据就是它是一种最低限度、最小范围内的基本规范。我在“全球伦理的可能论据”中讨论了相关论据,在《伦理学是什么》中讨论了论证的三种可能方向。
⑨见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岳季坤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22页。
⑩亨廷顿认为:文明实际只是放大了的文化。
(11)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369页。当然,我认可沃尔泽在《厚与薄——道德论证的内与外》(1994)一书中所论“底线道德”(minimal morality)的意义,但不同意他所认为的“充量道德”(maximal morality)与“底线道德”的关系,此可另外再论。
(12)思想者或观念人本就富于个性和特异,而今天远比古代扩大了、但仍是少数的“现代知识分子圈”似更强调标新立异,但也可能因此容易脱离常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