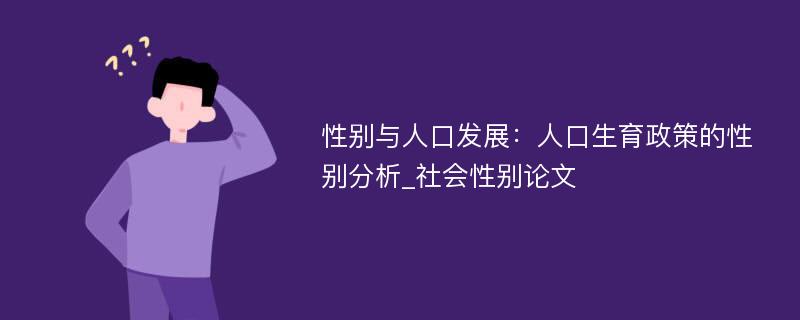
社会性别与人口发展笔谈——人口生育政策的社会性别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性别论文,人口论文,社会论文,笔谈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637(2007)03-0022-03
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我国现行生育政策,考察其中社会性别意识的体现以及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推进性别平等的对策措施,有利于充分发挥人口政策的调控作用,更好地为人口发展目标服务。在人口生育政策中体现社会性别意识,一是要体现性别平等,即消除性别歧视;二是要体现性别公正,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充分考虑两性的不同需求。此外,还应考虑政策实施对男女两性产生的实际影响,通过赋权和资源分配,创造有利于两性平等、和谐发展的社会环境。
一、生育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行30多年来,在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基本上考虑到了社会性别差异问题,不仅做到了尊重和保护女性权益,而且也提倡男性参与,较好地体现了社会性别公正。
首先,我国从法律上确立了男女平等的社会地位,赋予了妇女生育自主权,妇女在生育问题上自主性增强,基本上实现了男女两性平等地享有生育决策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他人既不能干涉妇女的生育行为,也不得歧视不生育的妇女。
其次,我国法律提倡和保障男女共同参与计划生育。《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第十七条规定:“公民有生育的权利,也有依法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这就排除传统社会剥夺妇女生育决策权、把生育的责任完全推给妇女的观念和做法。而且我国还强调男女两性共同参与计划生育,关注男女两性的生殖健康,从而改变了我国计划生育工作中长期以来“重女轻男”、把避孕的责任主要推给妇女的局面。这是我国生育政策中社会性别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
第三,我国生育政策中体现了对女性的认同与尊重,即鼓励无性别偏好的生育,这对于提高妇女地位、推进男女平等具有重要意义。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写道:“女孩长大一样劳动,有些专业劳动可以干得很好,更会做家务劳动,还可以让丈夫住在女方家里。新中国的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一定要克服重男轻女的旧思想,如果只生了一个女孩,同样要把她抚养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妇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决定》第九条规定:“对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特别是只有女孩的家庭,在分配集体经济收入、享受集体福利、划分宅基地、承包土地、培训、就业、就医、住房及子女入托、入学等方面给予适当照顾。”《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同样做出了鼓励无性别偏好生育的规定,如第二十二条规定:“禁止歧视、虐待生育女婴的妇女和不育的妇女。禁止歧视、虐待、遗弃女婴。”第三十五条规定:“严禁利用超声技术和其他技术手段进行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严禁非医学需要的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无性别偏好的生育政策,是社会性别平等的体现,有利于改变女婴生存困境和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局面,对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至关重要。
第四,生育政策中还充分考虑了女性的特殊需求,对妇女给予特殊保护和照顾,包括对妇女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的特殊保护,以及在离婚问题上对怀孕及生育妇女的照顾。例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和《女职工劳动保护规定》明确规定:妇女在孕期、产期和哺乳期间享受特殊劳动保护,并可以获得帮助和补偿。《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妇女权益保障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女方按照计划生育的要求中止妊娠后的,在手术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第四十六条规定:“离婚时,女方因实施绝育手术或者其他原因丧失生育能力的,处理子女抚养问题,应在有利子女权益的情况下,照顾女方的合理要求。”对怀孕妇女的特殊保护,充分考虑了女性在特殊生理时期的特殊需要,是社会性别意识在生育政策中的具体体现。这对女性顺利渡过特殊生理时期,并使其在特殊生理时期的特殊要求能够得到满足,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生育政策执行中的社会性别问题
虽然生育政策本身较好地体现了社会性别意识,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因种种原因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女性生育自主权被打折扣,在生育问题上女性参与为主,重男轻女倾向仍较普遍,部分女性因生育而受到歧视或遭受不公正待遇。
第一,女性生育自主权被打折扣,自愿不育妇女遭受社会舆论压力。虽然政策规定了妇女享有生育的自主权,包括自主选择生育或不生育的权利,但不生育的权利往往因与社会常理相违背而遭受社会舆论压力,从而被变相地剥夺。自愿不育是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出现的一种客观现象。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影响,自愿不育者群体却普遍遭受着沉重的社会舆论压力,尤其是自愿不育的妇女。
在女性的多重社会角色中,社会性别赋予女性最主要的社会角色就是社会人口再生产的承担者。女性和母亲,这是一个概念的两个方面,似乎是不可分割的。如果仅仅是女性而不能成为母亲,这与公众意识中的社会性别角色是不一致的,是不能被接受的。这正是自愿不育女性遭受社会舆论压力的深层原因。
第二,现实生育问题上的女性参与为主。虽然政策和法律规定了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计划生育的义务,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计划生育直接的和主要的承担者仍然是广大妇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男性避孕方法普及率低,采取男性避孕方法的少。调查发现,大多数男子赞成计划生育,1/4到2/3的男子不想生育更多的孩子,但在避孕方法选择上只有不到1/3的夫妇使用男性方法或需要男性配合,男性绝育率远远低于女性,计划生育以女性为主。二是女性在生育过程中的投入和付出远远大于男性。虽然政策规定了夫妻双方在生育问题上共同的责任和义务,但女性往往要承担较多的责任,她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比男性多得多,支付的机会成本和身心痛苦也比男性大得多。至于那些因工作、学习原因,丈夫不能陪伴左右的,妻子的付出就更多了。
究其原因,一方面,传统的男尊女卑的性别观念根深蒂固;另一方面,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模式在现实生活中仍占主流地位,“男主外,女主内”是多数家庭的性别分工选择,男人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外面打拼事业,而女性则承担了更多的家务事,包括生儿育女。
第三,现实生育中的重男轻女现象。从政策上说,是鼓励无性别偏好生育的,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传统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男轻女现象,出生婴儿性别比持续居高不下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自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来持续偏高的原因固然有诸多方面,但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是其深层原因。
第四,女性因生育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主要表现在就业领域。一些单位的招工信息或劳动契约中充斥着或变相存在着对女性的歧视性条款,特别是对怀孕和生育的妇女尤其如此。
我国台湾地区一些企业的劳动契约中就有“单身条款”和“禁孕条款”[1]。即规定在职场工作的女性必须是单身;女性一旦怀孕,便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要么被解雇,要么自动辞职或被迫辞职。这些条款或明或暗地存在于劳动契约或劳资双方的默契里。我国大陆的劳动契约中,虽未见明文规定的类似条款,但一些企业的女职工却面临着同样的遭遇。如有的企业有着严格的业绩考核制度,每隔一段时间就对员工进行一次考核,不合格者即面临被解雇的危险。这使得员工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女职工更不敢也没有时间安排自己的生育。
女性享有与男性平等的劳动权利,不能因生育而被剥夺或受到影响。更何况,女性生育不仅仅是其个人的事情,更是在为国家和社会尽义务、作贡献。社会不仅不应该剥夺其工作的权利,而且应当对其生育给予一定的补偿。因此,劳动契约中的这些规定,与国家制度相违背,侵害了妇女的合法权益,阻碍着性别平等的进程。
三、对策探讨
针对生育政策执行中存在的社会性别问题,特提出以下对策:
第一,强化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积极推动男性参与。社会性别强调两性性别关系的平等,在计划生育问题上应做到男女两性共同参与。为此,应当开发研制更多、更好的男性避孕用品,鼓励男性采取节育措施,提高男性避孕方法使用率。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应把男性参与纳入到政策规划中,营造良好的男性参与氛围,使男性参与计划生育成为人们的普遍共识。
第二,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消除生育中的性别偏好。社会性别主流化作为提高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战略,其最终目标是实现男女平等,要求在各个领域的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纳入性别公平意识,消除不利于女性发展的因素,使男女两性都能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使公众能够正视两性的社会性别差异和不同的社会性别角色分工,认识到男女都一样,都能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消除生育中的性别偏好。
第三,正视社会性别差异,实行生育社会补偿。女性承担生儿育女的主要责任,是其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不仅仅是妇女自己的“私事”,也不仅仅是个体家庭的“家庭事务”,而是“国家大事”,是社会人口再生产不可或缺的。同物质产品的生产具有价值一样,生育也具有价值。承认生育的社会价值,对妇女的生育给予一定的社会补偿,是消除生育性别偏好、提高女性地位、推进性别平等的重要环节。生育补偿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经济补偿,二是机会补偿。关于经济补偿,我国目前已经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生育保险制度,但在执行环节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加以保障,使制度上的平等和公正真正得到落实,实现社会生活中的性别公正。关于机会补偿,制度上基本上还是空白,现实中不仅没有对女性的生育进行机会补偿,反而是女性因生育而丧失了很多机会,这是有失公正的。应通过制定《工作平等法》或适合女职工特点的工作制,尽量降低女性的生育机会成本,或通过赋权和资源分配,给予女性一定的机会补偿,使她们能够享有与男性平等的权利、资源和机会[2]。当然,要做到生育政策中的社会性别平等和公正,还需要其他相关社会政策的配套和完善,如社会保障政策的健全和完善、劳动就业政策的公平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