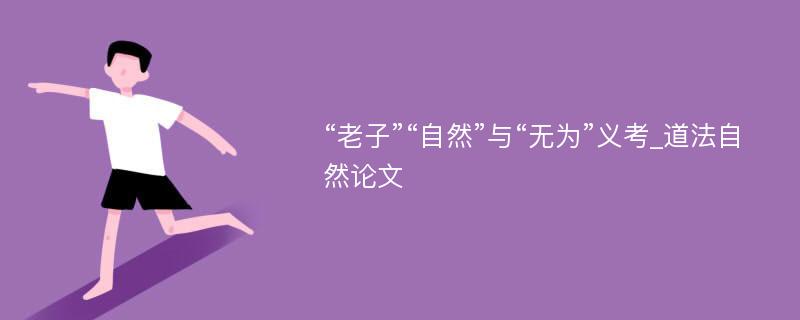
《老子》的“自然”与“无为”义考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老子论文,自然论文,义考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7511(2009)05-0034-07
《老子》中共有五处提到“自然”一词:
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言贵。功成事隧,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
希言自然。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第二十三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
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五十一章)
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第六十四章)[1]
《老子》中出现的这些“自然”一词,一般都可以理解为本然、天然、自然而然的意思。朱谦之注曰:“黄老宗自然,《论衡》引《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此即自然之谓也,而老子宗之。二十五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五十一章‘夫莫之命而常自然’,二十三章‘希言自然’,六十四章‘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观此知老子之学,其最后之归宿乃自然也。故《论衡·寒温篇》曰:‘夫天道自然,自然无为。’”[2][P71]所以,在他看来,《老子》的“自然”就是顺其自然之意。陈鼓应转引蒋锡昌注云:“广雅释诂:‘然,成也。’‘自然’,指‘自成’而言。”他自己也认为:“自然,自己如此。”“不加以干涉,而让万物顺任自然。”[5]这些都是解释《老子》之“自然”一词的颇具代表性的观点。
从字面的意义上看,《老子》的“自然”与“自然而然”无甚差别。但是,《老子》的“自然”一词的含义,根源于其整个的宇宙观和本体论。因此,对《老子》之自然义的考察,必须从它的宇宙创生论说起。
我们知道,在《老子》中,“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然《老子》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明确提出了“道”与“自然”的关系。对此,历代学者看法相近。河上公注本曰:“‘道’性自然,无所法也。”董思靖注:“‘道’贯三才,其体自然而已。”吴澄说得更明确:“‘道’之所以大,以其自然,故曰‘法自然’。非‘道’之外别有自然也。”童书业说:“所谓‘道法自然’就是说道的本质是自然的。”陈鼓应注曰:“‘道’纯任自然,自己如此。”[3](P168)冯友兰也认为:“道之作用,并非有意志的,只是自然如此。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4](P219)
我也认为,《老子》的“道法自然”并非意指在“道”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实体。所以,“道法自然”的实质就是“道即自然”。那么,这里的“自然”的含义是什么呢?是否就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的意思呢?从《老子》思想的整体来看,对这里关于“道”与“自然”的解释,可能还不应如此简单。因为这涉及到《老子》与上古思想的关系。
现代治老学者对《老子》与上古思想的关系有很多论述,但诸家说法稍有不同。胡适认为:“老子哲学的根本观念是他的天道观念。老子以前的天道观念,都把天看作一个有意志,有知识,能喜能怒,能作威作福的主宰。……老子生在那种纷争大乱的时代,眼见杀人、破家、灭国,等等惨祸,以为若有一个有意志知觉的天帝,决不致有这种惨祸。万物相争相杀,便是天道无知的证据。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老子这一观念,大破古代天人同类的缪说,立下后来自然哲学的基础。”他又说:“老子的最大功劳,在于超出天地万物之外,别假设一个‘道’。这个道的性质,是无声、无形;有单独不变的存在,又周行天地万物之中;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又却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很明显,胡适看重的是《老子》对于上古思想的发展与超越,在这个基础上,他强调《老子》的“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是一个‘自然’。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5](P45-46)
当代学者余敦康先生认为:“在西周天命神学中,天这个概念包含着三种不同的意义,一是指有意志的人格神,一是指自然之天,一是指义理之天。这三种不同的意义在西周的天命神学中是混合在一起的。西周的天命神学由原始的自然崇拜宗教发展而来。原始的自然崇拜宗教是一种万物有灵论,认为每一种自然物都有一个主宰着它的神灵。”而《老子》则打破了这种自然宗教的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道家的创始人老子第一次把道凌驾于天之上,哲学的整体观才算摆脱了宗教的桎梏,有了自己独立的理论形态。”所以,余敦康先生认为:《老子》的“道,则是自然而然,本来如此,所谓‘道法自然’,不仅意味着道以自身为法,而且也意味着人、地、天这三个低于道的整体都处于道的支配之下,效法道的纯任自然。”[6](P215,217)
上述观点虽然论述了《老子》与上古宗教的关系,但其强调的是《老子》对上古宗教的突破与超越,认为《老子》的“道”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自然而然。然而,与此不同,另一些学者的看法则更强调《老子》所传承的上古思想。这就像魏源说的:“老子道太古道,书太古书也。”[7]
吕思勉先生认为:“古书率以黄、老并称。今《老子》书皆三四言韵语(间有散句,系后人加入);书中有雌雄牝牡字,而无男女字;又全书之义,女权率优于男权;足徵其时之古。此书决非东周时之老聃所为,盖自古相传,至老聃乃著之竹帛者也。今《列子》书《天瑞篇》有《黄帝书》两条,其一文同《老子》,又有‘黄帝之言’一条。《力命篇》有《黄帝书》一条。《列子》虽伪物,亦多有古书为据,谓《老子》为黄帝时书,盖不诬也。”[8](P14)
冯友兰先生虽然也说过“道法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但他认为,《老子》与古代宗教的联系颇为密切。这是因为“(《老子》的作者)李耳为楚人”。据《汉书·地理志》:“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民……信巫鬼,重淫祀。”因此,《老子》与上古宗教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4](P217)
近年来,有学者对《老子》与上古氏族文化和神话的关系进行了专门研究,认为《老子》与远古的创世神话有着比较亲近的关系。王博先生认为:“与创世神话相比,老子的道论固然采取了哲学的形式,但它们之间仍然有共同关心的问题:天地万物是如何形成的?创世神话主要采取了月神创生的形式,在老子哲学中,道则取代了月神的位置成为天地万物包括人类的本原。”他认为,《老子》中关于道的论述和描写,很多与月亮非常相似。比如:“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忽兮其若晦,望兮若无所止。”“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等等。这里突出了《老子》与上古文化的直接关系。[9](第五章)
以上各家对于《老子》与上古文化的关系的看法,均有所据。不过,我认为,吕思勉、冯友兰、王博等先生的观点更具有一种历史的意识。下面从《老子》的文本出发,对它与上古原始文化的联系再进行谨慎的辨析。
这里的中心问题仍然是“道法自然”。《老子》既然说“自然”是一种可以让“道”去“法”的东西,那么,也可以说它也是世界的一种法则。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自然即道”。“道”与“自然”在这里是一样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老子》的宇宙创生论,我们也许对“自然”会另有一些感受。
我们知道,在《老子》中,这个法“自然”的“道”被认为是不可说的,并且是被神秘化的: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第二十五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第四章)
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第十四章)
道之为物,为恍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第二十一章)
在这里,虽然《老子》说“道”是“无状之状,无象之象”,但《老子》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只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抟之不得名曰微。”很明显地可以看出,“道”在这里被表述为一种“物”。①而且,“道”本身还处在一种运动之中:“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当然,《老子》对这个“道”“不知其名”,不过,我们不能排除“道”是一种“物”。当然,《老子》说过:“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第四十章)那么,《老子》的“道”和“无”是什么关系呢?陈鼓应解释说:“‘无’、‘有’是指称‘道’的,是表明‘道’由无形质落实向有形质的活动过程。”[3](P55)如果说《老子》的“无”是一个逻辑前设,那么,“道”则不能说没有实体性的含义。由此可见,我们不能否认在《老子》的思想中,具有一种在宇宙万物生成之前,有一个实体性的“道”存在的观念。
对于这个不可言说的、神秘的“道”,《老子》又有一种什么样的看法呢?他说: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其致之。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发,神无以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高贵将恐蹶。(第三十九章)
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网恢恢,疏而不失。(第七十三章)
“一”即是“道”,它的力量是人力所无法抗拒的。无论你有什么计谋或物质力量,若与它对抗,将会有灭顶之灾。而且,这个“自然”并不具有像人类那样的情感或同情心:“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第五章)但是,如果你能顺应它,它也会庇护你、保佑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第七十九章)在一定程度上说,它也能够主持公道:“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第七十三章)能知这个“常”就是“明”。“不知常,妄作,凶”。(第七十七章)故“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第十六章)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能说“天之道,利而不害”。(第十六章)
不难看出,《老子》的“道”(法“自然”之“道”)具有一种超现实的、甚至是超出想象力的力量,人力是无法与之抗争的。因此,在《老子》中,对于“道”存在着一种敬畏甚至惶恐的心理,②这就明显表露出一种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的色彩。一般来说,宗教神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目的论,即万事万物的生成、发展、死亡,都是由一种超现实的上帝、神灵或理念安排的。而一种纯粹的哲学自然观的标志,应该把事物的生成、发展、死亡看作是按照自身的目的实现的,事物的这种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或逻辑,才真正是自然的。《老子》显然没有达到这种自然观。
从本体论和认识论来说,《老子》的“道”还是一种法则和规律。“道法自然”,“反者,道之用”(第四十章)等,都是就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律和法则而言的。不过,这个法则和规律在《老子》看来也是神秘而难以言说的:“明道若昧,进道若退。”(第四十一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第七十三章)即使是圣人,对于这个法则和规律也感到困惑:“天之所恶,孰知其故?是以圣人犹难之。”(第七十三章)《老子》还说:“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第四十一章),而知识与这个“道”是不相干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第四十八章)这样,我们对于客观世界万事万物的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就只能靠一种神秘的体验了。故而从根本上说,《老子》的知识论与宇宙论是一致的。可以看出,《老子》中关于知识和真理问题的表达,常被一种神秘的体验所代替。
因此,从《老子》对于“道”的描述到他全部思想的表达,大都是采用比喻、隐喻、格言警句以及寓言等方法。例如: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第三十二章)
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第三十二章)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第八章)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动。(第六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五十八章)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第五十八章)
道之为物,为恍为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第五十八章)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第五十八章)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第二章)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第二章)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第五章)
这些表述及其思维方式,与《老子》的全部思想和观念是一致的。
现代人类学家一般都认为,原始人类或处于早期蒙昧时期的人类,在语言和思维方式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使用具体事物进行比喻和想象,而很少运用概念进行抽象的表达。18世纪的意大利人维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1668-1744)就曾提出了原始人类的语言和思维问题,认为早期人类的思维和语言大多都具有具体形象的特点,词汇中很少有抽象的表示概念的词。他把早期人类的这种思维特征称之为一种“诗性智慧”。当代法国人列维-布留尔(Levy-Bruhl,1857-1939)在其名著《原始思维》中说:“在原始人那里,思维、语言则差不多只具有具体的性质。一个精细的观察者说:‘爱斯基摩人的推理方法给我们一种非常表面化的印象,因为他们不习惯于保持我们叫做推理的确定路线的那种东西或者一个单一的孤立的主题;换句话说,他们的思维没有上升到抽象化或逻辑公式的程度,而是固守着一些观察或情势的图景,这些图景的变化规律是我们所难以捉摸的。’简而言之,我们的思维首先是‘概念的’思维,而原始人的思维则根本不是这样的。”[10](P414)
《老子》的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述方式,无疑具有人类早期的思维特征。虽然《老子》的思想中含有许多很深刻的哲理和辩证法,但这与思维和表达上运用概念抽象的思辨方法则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在原始人的语言表达中,也含有辩证法思想,但这与哲学本体论具有本质上的不同。哲学本体论的思考不同于一般现象描述的实用性智慧。《老子》的思想还没有成为一种纯粹的哲学本体论。例如,《老子》的“道法自然”在实用的智慧层面上,无疑是很深刻的,但作为一种严格理论意义上的本体论,则是很贫弱、乏力的,甚至会导出逻辑的循环:自然——道——自然。“自然”一词的意义,在这种本体论的追问中,立刻被消解了。从“道法自然”这种思想的表述方式可以看出,《老子》对于抽象概念的追问,实质上采取的是消解的办法。由此可以看出,《老子》在概念抽象和理论思维上,至少是表述上的无力或无能。③这也可以证明,《老子》的思想和观念与上古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很直接、很亲近的关系。
在对《老子》之“自然”一词的解释中,人们常常又把它和“无为”一词相混淆。例如,车载说:“老子书提出‘自然’一辞,在各方面加以运用,从来没有把它看成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界,而是运用自然一语,说明莫知其然而然的不加人为任其自然的状态,仅为老子全书中心思想‘无为’一语的写状而已。”“老子提出‘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的见解,说明万物是在无为自然的状态中生长的。”[3](P131,262)
“无为”当然也是《老子》的重要思想。《老子》中直接提到“无为”一词不下数十处,例如: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
为无为,则无不治。(第三章)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第三十八章)
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第四十八章)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第五十七章)
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第六十三章)
是以圣人无为,故无败……(第六十四章)
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老子》中,“自然”与“无为”之义很相近,但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不能完全等同。魏源说:“老之自然,从虚极静笃中,得其体之至严至密者以为本,欲静不欲躁,欲重不欲轻,欲啬不欲丰,容胜苛,畏胜肆,要胜烦,故于事恒因而不倡,迫而后动,不先事而为,夫是之为自然也。岂滉荡为自然乎?其无为治天下,非治之而不治,乃不治以治之也。功惟不居故不去,名为不争故莫争。图难于易,故终无难。不贵难得之货,而非弃有用于地也。兵不得已用之,未尝不用也。去甚去奢去泰,非并常事去之也。治大国若烹小鲜,但不伤之,即所保全之也。以退为进,以胜为不美,以无用为用,孰谓无为不足治天下乎!”[7]不难看出,魏源大致把“自然”解释为个人的处世手段,把“无为”解释为君主的南面之术。很显然,这种观点可备为一说。
应该说,《老子》中除了“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中的“自然”有无为而治的意思外,其他几处的“自然”都不同于“无为”的含义。从字面的意思上看,“自然”主要是指事物的一种状况,“无为”则是人们对待事物的一种态度。当然,这种区别不是绝对的。在《老子》中,“自然”与“无为”之间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即它们与“道”都有着一种直接的关系。而它们之间的区别,也根源于“道”。
上面论述了《老子》中的“自然”不仅仅只是自然而然的意思,它还带有对自然的原始崇拜的意味。“道法自然”也不仅仅只是顺其自然的意思,还带有对自然力量无可奈何的认可。于是,“顺自然”是人们最聪明的对待世界的态度和办法,即所谓“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就是“无为”的思想。由此可见,“无为”的态度和办法,在这一意义上当然是消极的。这里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道”(“自然”)的力量太强大了,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人类无法与之抗拒、抗争。所以,在顺应自然的“无为”之中,同样含有敬畏和无可奈何之意。而在《老子》看来,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与自然的运行法则是一样的:“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第八十一章)因此,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运行法则,也不能进行抗争,只能顺其自然,无为而治。“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宾”。(第三十二章)“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第三十七章)《老子》由此而得出了“无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并提出了“无为而治”、以退为进的社会政治思想,以及顺应自然、守素抱朴的处世态度和人生哲学。
与此相一致的是,《老子》认为,与大自然万事万物相对的一切人为的政治制度和伦理秩序,都是违反自然的,因而这种制度和秩序最终不会给人们带来安宁和福祉。所以,他抨击儒家的礼治思想,认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第十九章),提出“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第十八章)。他的理想社会是“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第八十章)的人们无知无欲的远古自然社会。故而从历史观来说,《老子》的思想无疑是复古倒退的。
“无为”的观念,可以说是《老子》对自然、社会和人生的深刻认识,反映了《老子》的深刻思想和卓越智慧。因此,我并不否认“无为”的积极意义。但是,从另一角度来说,“无为”的观念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无能为力的消极含义。因此,不管以后历代对于《老子》之“无为”思想的理解和运用有何不同(比如,汉代初期的黄老之学与后来一般道家对于“无为”的理解,应该与《老子》文本的原义有很大的不同),在《老子》本来的“无为”思想中,应该具有这两方面的含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老子》作为一本哲学著作是毫无疑问的,《老子》在思想观念上实现了对上古原始宗教的突破,亦标志着一次思想史上质的飞跃,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老子》的思想和观念与上古的原始文化之间,有着一种很亲近的关系。虽然它已经是哲学而不是神话传说,但它仍然带有浓厚的原始神话、宗教等文化色彩。人类早期哲学所带有的直观、朴素以及神秘的特点,其仍然未能摆脱。同时,在理论上,它经常用一种神秘的体验来代替日常经验的描述和论证,这表明《老子》对于客观外在世界的认识,还处于早期人类的直观和猜测阶段。因而,我们不能完全以现代人的观念标准,把《老子》看作是已经具有现代人的认识观念和水平的哲学著作。④
因此,我们不能像有的学者所解释的那样,把《老子》中的“自然”说成“是强调不受干扰、悠游自得的意思”。[11]在对外在自然具有敬畏的观念时,“悠游自得”是不可能的。由于《老子》的“自然”中含有一种对于超现实的,甚至是超出想象力的、人力无法与之抗争的力量的敬畏甚至惶恐的心理,因此,《老子》的“无为”思想实质上也包含了一种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无能为力的消极含义。笔者认为,指出这一点并不会掩盖《老子》的重要价值,相反,这不仅有助于我们对《老子》中的“自然”和“无为”思想有一个更加清醒的认识,还有助于对《老子》整体思想的真正意义有更进一步的理解和把握。
注释:
①刘大杰先生认为:《老子》的“道是‘夷’、‘希’、‘微’这些原素构成的。正如欧美人说的原子、电子一样,这些东西看不见、听不到、触不着,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所以名之为恍惚或是混成。虽是耳目不能见闻,虽是惚兮恍兮,但内面还是有象有物,这就是道,就是宇宙的本体。”(刘大杰:《魏晋思想论》第4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②先秦哲学中这种对于自然力的敬畏,在《荀子》之“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中才完全消失。孔子也说过:“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论语·季氏》)
③中国哲学直到魏晋时期的王弼提出了以“无”为万物本体的思想,即体用一如、即体即用的思想时,才出现了一种思维水平很高的本体论。参见章启群:《论魏晋自然观——中国艺术自觉的哲学考察》第二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④在王弼的哲学中,《老子》的这种自然观念发生了本质的转换。王弼的哲学已经彻底摆脱了早期哲学中的原始宗教和神学的影响,达到了一种纯粹本体论的哲学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