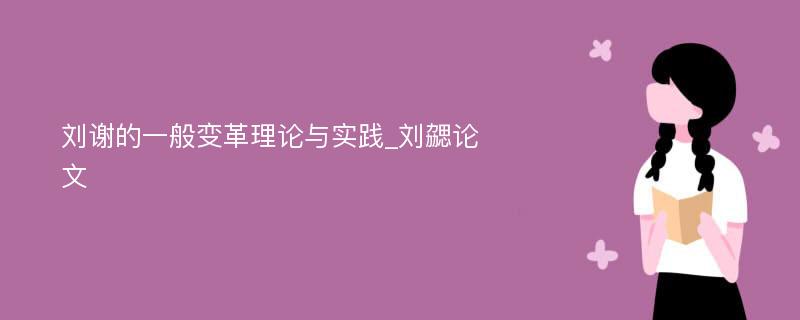
刘勰的通变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纵观文学史,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是根据时代需要,通过不断地继承和创新而发展变化的。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刘勰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通变理论论述了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他的通变理论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主张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强调文学的创新是其通变论的主旨,并且主张既要在形式上创新,也要在内容上创新。刘勰不仅提出了通变理论,而且以其《文心雕龙》成功地实践了他的理论,其中的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包括通变理论本身等都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而成的,做到了既有通又有变。
一
(一)通变的辩证关系
所谓“通”,就是文学不变的常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通变》)诗赋书记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尽管它的体制形式不一,而“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即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在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即“序志”)和表现时代(即“述时”)这一根本问题上,是有共同点的。刘勰认为: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能从“变文之数无方”“明其然”,也就是从纷繁的、各式各样的体制和风格中看到它们的基本点,正因为文学在它的基本点上是有规可寻的,所以就必须继承遗产,借鉴前人的经验,即所谓“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创作才不至于匮乏(即“通则不乏”)。例如在《时序》中,刘勰认为楚辞之大放异彩(“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前代的影响,同时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爰其汉世,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明乎在。”这是所谓“通”的一面。
仅仅有“通”,而没有“变”是不行的。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文学艺术也必须勇于革新创造,例如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过:“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刘勰更加强调这一点,要求“酌于新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刘勰认为这一点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不断地革新创造,文学才会不断发展,即所谓“变则其久”;而要革新也就必须继承,即所谓“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继承的,不然就会“虽获巧意,危败亦多”(《风骨》)。只有“通”、“变”结合,文学才能够“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才会有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刘勰在《物色》中说的“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的道理。
刘勰认为,变有两种:一种是不要通只要变,完全违背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的变,如《通变》所说的那种“竞今疏古,风味气衰”的变;《定势》说的“逐奇而失正”的变。对于这种表面上是创新,“跨略旧规,驰鹜新作”(《风骨》),而实质上是形式主义的“逐新趣异”(《声律》)的变,刘勰是坚决反对的。这也是刘勰所反对的当时的文风之弊病,他在《定势》中说“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求也,反正而已。”在《明诗》中更对形式主义的“穷力而追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另一种变是在通的基础上的变,就是在继承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的前提下,用新的方式来发扬传统精神,灵活地运用历代承传下来的方法,充分地体现文学创作的独创性。这种变就像他在《风骨》篇中所提出的:“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也是《定势》篇中所提出的“执正以驭奇”的那种变,这是刘勰所提倡的。简言之,刘勰反对“竞今疏古”、“习华随侈”的新变,而主张“资故实”、“酌新声”的通变。
因此,在文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刘勰强调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刘勰认为:一方面,“体必资于故实”,即要学习古人各种文体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另一方面,“数必酌于新声”,即要凭着自己的气性才情,用今天的语言,创作今天的时文。他反复强调“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就是告诫我们:继承必须革新,革新不废继承,因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唯其如此,文学才具有不朽的生命,永久的魅力。刘勰要求于作家的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要学习借鉴古人的作品,根据今天时代的要求,创作出有特色的脱颖之文。他清楚地认识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学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可以积极倡导文学要“酌于新声”。由此可见,他对文学继承与创新的见解是精到而深刻的。“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等等都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文学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二)变即创新是刘勰通变论的主旨
刘勰在论述通变的过程中,其主要着眼点在论变,即强调变,变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容易被人忽略。其实,变才是刘勰通变论的主旨所在,因为要强调变,所以有一个怎么变的问题。要怎么变才是正确的,这是刘勰提出通的前提,他是要说明正确的变应当是在通的基础上的变,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的变。
《通变》篇赞词可说是全文的总结,刘勰的通变思想表达得最为集中和明显。“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不断发展的文学规律,就是“日新其业”,这是刘勰对文学发展的最可贵的认识,倒退是一条绝路,也不可能倒退。“日新其业”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的规律,而“通变”就是使文学创作能长远发展的必然道路,因此,刘勰鼓励作者大胆果敢地去创新,只要不忽略“有常之体”的基本原理,在“望今制奇”的同时,还应结合“参古定法”,极分明地概括出了通变的出发点,要求从学古中创新。“变通者,趋时者也”,于此可见,发展创新确是刘勰通变论的主要思想。
刘勰虽以“师乎圣、体乎经”论文,却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取其“衔华佩实”之义,其所本之道又非儒道,而是言必有文的“自然之道”。他不仅对纬书的“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予以肯定,更大力赞扬“自铸伟辞”而“惊采绝艳”(《辨骚》)的楚辞,其列论楚辞的《辨骚》为“枢纽论”之一,主要就是取“变乎骚”之义。这个“变”,就指对儒家经典的变。楚辞由儒家五经发展变化而为文学作品,在刘勰看来,这并不违背儒家圣人的旨意。《征圣》曾明确讲到:“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既然随时适变是圣人之文的特点,既然要师圣宗经,当然就不能固守五经而无所发展变化。于此可见,刘勰强调征圣宗经,并非为了坚守儒道,不是为了复古倒退,从来没有要求作家照搬照抄“古昔之法”,而是从文学本身的特征出发,注重于文学的发展新变。之所以借重于儒经者,主要是为了“矫讹翻浅”,以图遏制“从质及讹”的发展趋势。不论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不会为“古”而“颂古”,“好古”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今”。正如鲁迅所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
刘勰论作家,非常重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首创的功劳和独创的成就,这也可以说明刘勰通变论的主旨在于变。屈原的《离骚》在辞赋中是首创的作品,在历史上是独创的现象。刘勰以前的人都未曾对其独创的特点予以评价,刘勰则指出它是独创的文学,在《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此外,如《杂文篇》中谈到宋玉的《对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都重视了首创的功绩。说宋玉之“始造《对问》”是“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说枚乘之“首制《七发》”是“腴辞重构,夸丽风骇”,又说“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说扬雄之“肇为连珠”也是“覃思文阔,业深综述”,又说“其辞虽小而明润”。相反,刘勰对模拟的作家作品总是否定多于肯定,这又从反面说明了他强调创新的主旨。刘勰在《辨骚》和《事类》等篇中指出扬雄基本上是一个模拟的作家,作品大多是模拟的作品后,除了对他的少数篇章某些表现和若干言论有所肯定外,对扬雄的为人和作品大都是否定的。如提到扬雄的为人时,他说:“扬雄嗜酒而才算”,“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程器》)。论及其作品时,则说:“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诔碑》),“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味文略,故辞韵沈膇”(《哀吊》),“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逐辞,故兼包神怪”(《封禅》),“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娈彼洛神,既非罔两;……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夸饰》),“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才略》)。
(三)兼有形式和内容的变
刘勰强调变,不仅仅在形式上,还包括在内容上的创新,这一点也常被人忽视。不断发展变化的“文辞气力”涉及到了内容方面。因为刘勰讲的“气”是和“情”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情与气偕”(《风骨》)都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气质而言。他说的“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都是以作家的“情”和“气”作为通变的依据的,刘勰说过“文变染乎世情”(《时序》),即是着眼于“世情”而观“变”。刘勰既主张在形式上变,也主张在内容上变,还体现在《辨骚》和《正纬》篇中。在《辨骚》篇中,刘勰认为《楚辞》是通过“夸诞的”“异乎经典”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来体现其符合经典“同于风雅”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的,《楚辞》就是用这样的“夸诞”“奇意”“自铸伟辞”,从而“取熔经意”于其中,成为“词赋之莫杰”的。从刘勰所举的“异乎经典”的四事来看,主要见于《离骚》《天问》《九章》《招魂》,而对于这些作品,刘勰的评价都是很高的。他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丽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楚辞》这种合乎原道征圣宗经原则的新变,刘勰认为是文学发展中的通变的典范。它从文学的独创性方面来说,是足以后人效法的,它既不违背《诗经》的传统,又能做到“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所以刘勰赞美它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难矣。”由此可见,刘勰所说的变,决非仅仅指文辞形式,而是首先包括了文学内容方面的变革的。《正纬篇》中刘勰认为纬书的内容是荒诞虚妄而不可信的,他引用前人对纬书的批评,指出其“虚伪”、“浮假”、“僻谬”、“诡诞”,抛弃了圣人经典的传统,因此这种变是不值得肯定的。不过,刘勰认为纬书中的某些次要方面,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他指出纬书在“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方面,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而且可供“后来辞人,采摭英华”,也还起过一定积极作用。这也说明刘勰主张的变,是包括了内容(“事丰奇伟”)和形式(“辞富膏腴”)两方面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违背道圣经的原则,那么文学的具体内容和文辞形式都需要变,通则主要是在基本思想倾向和写作重大原则方面和圣人保持一致。
(四)通变的必要性和如何通变
文学是在继承和创新中发展变化的,文学发展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通变篇》说:“是以九代咏歌,志合文则。黄歌《断竹》,质之至也;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至于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这里有继承有创新,不过,主要指创新而言。“广”、“文”、“缛”、“丽”等词都说明文学的新变化,这些变化都产生于“序志述时”的基础上,所以是正常的。至于“楚之骚文,矩式周人;汉之赋颂,影写楚辞;魏之篇制,顾慕汉风;晋之辞章,瞻望魏采。”(《通变》)这里也是有继承又有创新的,然而主要指继承而言。前代影响后代,后代继承前代,陈陈相因,互相沿袭,这是人所共睹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继承现象。显然,刘勰从继承和创新两方面证明了文学发展中继承和创新的必然性。
文学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正如刘勰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时序》)。而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特色,形成新的时代风俗:“……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刘勰认为,从远古的质朴到近代的诡异,时代越近,作品的滋味越淡,其原因是人们争着模仿现代而忽视学习古代,即《通变》篇所指出的:“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要纠正这种偏向,刘勰认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样,在质朴和文采之间斟酌去取,在雅正和通俗之间考虑得失,就可以讲继承和创新了。既要通又要变,这样“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作家的作品就会日益刚健而立于不败之地。作家怎样把“通变”贯彻到文学创作中去?怎样继承和创新?刘勰作了这样的回答:“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光若长离之振翼,乃脱颖之文矣。”(《通变》)在这里作者直率而满怀自信地向我们提供了一把文学创作的钥匙:“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即以自己的情感去体会历代佳作的要领,这才是真正的“通”,进而结合自己气质才能的实际去革新,这才是有意义的“变”。这样的变,显然既有对古代优秀传统的继承,又能适应当前的需要,所谓“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如何把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刘勰一则喻之曰:“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再则直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沐浴时代阳光,开出奇异花朵,或曰制当代诗文之奇,其义一也;植根古代经典,使诗人异代而同质,或曰以古代经典为法则,其义一也。他要求作家一方面“趋时必果,乘机无怯”,一方面“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针对当时文坛的“风味气衰”,刘勰提出这个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论断,使文学“日新其业”,“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是高瞻远瞩的。
(五)通变论的局限性
封建的时代和儒家的立场给刘勰的文学思想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关于通变的见解,在根本上也就不能不受到他的宗经征圣等观点的制约。由于从宗经的立场出发,刘勰对于后代文学发展的认识是不足的,对它们的批评也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他认为,从“九代”的作品来说,由黄帝时代的“质之至也”的《弹歌》,发展到宋初的作品“讹而新”,其趋势是“弥近弥淡”,原因则是“竞今疏古”“刻意学文”。他还认为,从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发展变化来说,“青生于蓝,绛生于蓓”,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变化,然而变化至此就已“不能复化”,即到了顶点不能再有新的变化了。从文学的发展来说也是这样,“夸张声貌”即作品中对声音形貌的夸张描写,刘勰举枚乘、张衡、司马相如、扬雄、马融五位赋家为例,认为到了汉初已达极点。从此只能“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也就是再也不能有新的发展变化了。这里刘勰既把汉初当作“夸张声貌”的极点,又对文学的发展作出每况愈下的消极结论,暴露了明显的保守性。
刘勰对楚汉以至宋初的文学发展表示了不满,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了一个“通变之术”的药方,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即必须“宗经”:“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宗经》)。他关于“名理”“故实”的强调,同样是如此。这就是说,刘勰是主张通变的,但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却不能违背“宗经”的原则,必须以“经典”或“经诰”为旨归。在这里表现出他的尊经复古思想,从而反映出他的局限性。纪昀对通变篇眉批道:“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奇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通变”条说:“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其要语曰: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此则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矣。……明古有善作,虽不变者不能越其范围,知此,则通变之为复古,更无疑义矣。”纪黄二人都阐明了刘勰的复古思想,但两人异口同声地断定“通变”就是复古,也有商榷之处。刘勰在要求会通时,他说既要“资故实”,又要“酌新声”,“还宗经诰”是就“资故实”而言的,这是他宗经思想局限性的反映,但是他认为文学必随时世而变,主张不割断文学历史继承性的创新乃是他的通变理论的主导方面。强调征圣宗经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的,企图以此来达到“正末归本”的目的,所以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又具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他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变的前景看不清楚,因而也说不清楚,充其量他只能提出一些改良意见。二
刘勰不仅在理论上对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上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继承了儒家思想,特别是荀子、扬雄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思想,提出了《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下面主要从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三方面来论述。
(一)文体论
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当时流行的八种体裁和它们的基本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心雕龙》那种把两种近似的文体合为一篇的分类方式,如“颂赞”“祝盟”“铭箴”等,则是受了曹丕《论文》的影响的。但对曹丕的理论,刘勰又有一定发展,如对“书论宜理”,彦和在《文心·论说篇》更明确指出:“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支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故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对“铭诔尚实”,《文心·铭箴篇》曰:“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及“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就是“尚实”思想的进一步延伸。
但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多本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文心雕龙》上编用二十篇的篇幅讲各种文体的源流区分,并对每种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这种体例就是从《文章流别论》继承来的。《文章流别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后来多为《文心雕龙》所本。诸如:“王泽流而诗作”,《文心·明诗篇》云:“自王泽殄渴,风人辍采”。“成功臻而颂兴”,《文心·颂赞篇》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德勋立而铭著”,《文心·铭箴篇》云“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嘉美终而诔集”,《文心·诔碑篇》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文章流别论》中叙述了“颂”的流变,刘勰《文心·颂赞篇》中对颂这一文体的看法,与挚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刘勰“敷理以举统”,阐述某一文体是为了指导写作,如《颂赞篇》中“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惧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惟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弘,如斯而已。”却是他的创制,为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不及。刘勰的文体论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各种体裁的创作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如论赋时讲“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论论说时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支碎”的要求;论骚时讲到写实与幻想的结合;论诗时讲到四言要求“雅润”,而五言要求“清丽”等等。刘勰对形式技巧的津津研究和他对新的审美原则和新的审美思想的提出和阐发都是他在文体论方面所做的“变”。
总的来说,文体论由曹丕开其端,经陆机、挚虞,刘勰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文体论,成为文体论的集大成者。
(二)创作论
刘勰的创作论部分本于陆机《文赋》,这和文体论多本于挚虞《文章流别论》一样。在构思上,陆机用了一些形象的比喻来描写创作构思过程中想象的飞腾,他指出文思酝酿过程中,情感越来越鲜明,物象越来越清楚,然后才用巧言妙语来表达,这说明创作构思过程中非但离不开物象,而且伴随强烈的感情。他更进一步体会出在创作过程中,思路有“通塞”。思想通畅的时候,文思如泉涌;思路堵塞的时候,文思变干涸了。《文赋》着重谈文思产生的情况,但没有详谈文思如何能产生,并自叹“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不知道思路的通塞是怎么造成的。刘勰在写《神思》、《养气》时直接受到《文赋》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培养文思使其通畅的途径。在文思与才学关系问题上,一再强调后天的“积学”、“酌理”、“研阅”、“驯致”,而且强调这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神思》),“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其反其习”,“学慎始习”,“功在初化”(《体性》)。在创作技巧上,《文赋》里十八个“或”字,主要是讲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分析入微,但都是分别就具体问题而言的。而《文心雕龙》则进一步提出了“术”的概念,不但在《神思》、《附会》等篇中分别有所阐述,而且还特立了《总术》一篇,“执术驭篇”“乘一总万”。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文赋》只是初步接触到,陆机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把意理当作“质”“干”,把文辞当作枝叶,表明以意为主,以辞为辅。但是《文赋》在后半部分用了大量的篇幅,细致地讲文章形式和创作技巧,他详细论述的“作文之利害所由”,主要也是从形式方面讲文章的优点和缺点。他重视谋篇法,讲究文章的组织结构,但认为内容繁富的文章,只要有警句,就可以显示要领,而把全文统率起来。《文心雕龙》的《熔裁》、《附会》等篇,一方面继承了他的谋篇术,一方面更进一步讲究剪裁,来弥补《文赋》的不足。在形式方面,陆机提出“尚巧”“贵妍”的主张,不仅注重文章的色采,还强调声音的优美。刘勰在《情采》、《附会》中发展了《文赋》的理论,而且更加突出内容的重要性。如《情采》:“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他把情理看作经,文辞看作纬,认为写作必须先内容而后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又说:“夫能设谟以位理,……彬彬君子矣。”所谓“文不灭质,博不溺质”,正是思想与艺术得到恰当统一的作品。在《文心雕龙》的下编里,立了《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等专篇,分门别类地分析了各种表现手法和修辞技巧,这都显示出比《文赋》更加条理分明了。
刘勰的创作论显然吸收了陆机《文赋》的精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详细最精采的文学创作论。章学诚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论,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确实如此。
(三)批评论
刘勰关于文学欣赏和批评方面的思想渊源: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其实质正是要求批评家要比较客观地评论作品,避免断章取义的那种主观主义的文学批评,以免曲解了诗歌的本意。同时孟子也指出了要按照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去理解作品,而不能局限于字面上的一知半解。这些对刘勰的文学批评论的提出是有很大启发作用的。刘勰在《夸饰》篇中还特别提到对文学夸张描写的意义,就应当按照孟子所说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原则去理解。
王充《论衡》中批评“贵古贱今”。《案书篇》中说“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而实际上,“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不能以古今来论高下,而应当以客观存在的作家的实际才能、作品的实际水平来评论优劣。刘勰继承这一观点,并以秦皇汉武为例尖锐地批评贱同思古,贵古贱今这一错误倾向。说他们如好龙之叶公,“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思古”,“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马轻。”敢于把矛头指向两位皇帝,斥责他们的罪过,说明他批判的尖锐性和勇气之大。《齐世篇》中说:“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有人于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为文书者,肯载于篇籍,表以为行事乎?作奇论,造新文,不损于前人,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而垂意观读之乎?”主张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这是王充论文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它对刘勰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王充是非常重视批评家要有真知灼见的,优秀作品毕竟是少数,“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超奇篇》)合众心顺人意者不一定是好作品,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常常是“谲常心,逆俗耳”(《自纪篇》)的,只有能识深鉴奥者方能成为其知音。其《自纪篇》又云:“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卡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畔者五人。盖独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愚者欣颂,贤者逃顿。”这不正是刘勰所说的“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意思吗?王充在《佚文篇》中说:“孟子相以眸子焉。心清则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这个道理刘勰在《知音》中说过:“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曹丕提出“文人相轻”。《典论·论文》一开篇就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体。’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善备,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曹丕认为产生“文人相轻”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善于自见”、“闇于自见”,对自己的长处“善于自见”,对自己的短处“闇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善备”,必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以己之长轻人之短,总是有可轻之处。解决办法是“审己以度人”。刘勰对曹丕“文人相轻”的观点深表赞成,并作了新的论证,如“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体’。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知音》)从而作出了“崇己抑人”的概括。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葛洪在《抱朴子》中对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的有关论述对刘勰的影响。《抱朴子·辞义》篇中指出:“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因为人们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飞鸟睹西施而惊逝,鱼鳖闻九韶而深沉。故衮藻之粲焕,不能悦裸乡之目;采凌之清音,不能快楚隶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辩,不能释系马之庸。”欣赏者和批评者各有自己的标准,因此对文学作品优劣的评价也难于取得一致。本来,“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然而,“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其《尚搏》篇指出,“夫赏其快者必誉之为好,而不得晓者必毁之以恶,自然之理也。”只凭主观爱恶,就必然会丢掉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可能对文学作品作出正确的公正的评价,许多批评家由于自己的识见的浅薄,不能认识真正优秀的作品。“若夫驰骋于诗论之中,周旋于传记之间,而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虽始自髫龀,讫于振素,犹不得也。”(《尚搏》)为此,葛洪也强调批评家本人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水平,有广博的见识,善于比较和鉴别。《广譬》篇云:“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觌虎豹之彧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刘勰反对以主观好恶去武断地评论作品,批评世俗之人不辨真伪,“以雉为凤”,“以夜光为怪石”。如《知音》篇中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而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他提倡批评家要有“博观”之能,要“识深鉴奥”,善于“见异”。可以说都与葛洪的上述主张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联系。所以,刘勰的文学欣赏和批评论,也是总结前代有关的历史经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
批评论无论孟子论诗还是曹丕论文,都是片言只语,到刘勰,不但详论批评方法和原则,还进行具体的批评。除在各文体论中评论作家作品外,还在《才略》、《体性》、《程器》中专论作家。刘勰论作家,对于前代的关于作家的评论坚持了不肯雷同也不苟立异的精神。他在《序志篇》说:“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就是说,对于古今的旧说,有所继承,也有所批判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集旧说之大成,有可能提出新的结论。例如在《宗经》篇里,刘勰就采用过王粲的成文,在《颂赞》和《哀吊》篇里,也采用了挚虞的旧说,此外像论刘歆和扬雄,又采取过桓谭的看法。《通变》说:“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看刘扬言辞,常辄有得。”又如论孔融和徐干,也采取过曹丕和刘桢的成论,《风骨》说:“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有逸气”,又说:“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念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如此等等,都是以前人旧说为基础而加以阐述的,刘勰于前人的旧说,或引申,或借用,或补充,态度相当谨严。有所因袭,却非雷同。
因为对旧说不肯雷同,也就能够创立新说。在评述作家特长的时候,刘勰发展了曹丕《典论·论文》里的一些见解。《论文》指出“文人相轻”的不当,从而指出建安七子于各体文章各有专长,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刘勰则进一步指出“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程器》)于是刘勰对于某些作家虽然批评十分严格,但也不是责备求全,只要作家在某一方面有所贡献,刘勰都给以应得的评价。例如关于屈原的评论,刘勰别具新的见解。在刘氏以前,或褒或贬,主要从思想方面立论,而刘勰则更注意了艺术的方面;而且即使在思想方面,刘勰也比前人分析得更加具体。譬如《辨骚》在列举了刘安、班固、王逸等人的分歧的看法之后,便对作品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认为在《离骚》里面,既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又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既有“同于风雅者”,也有“异乎经典者”,内容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这比前人那种片面地“举以方经”或“谓不合传”的观点全面多了。此外,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关于曹植和曹丕的评论,关于班固和班彪、刘歆和刘向的比较,刘勰都有自己新的见解。
总之,刘勰的批评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既有通又有变的。
刘勰提出了全面系统的通变理论,而《文心雕龙》本身又是其通变理论最好的实践证明。刘勰主张通,于是他吸收了他的前辈在文学理论批评各方面的成果;他又强调变,在继承前人的同时进行了新的创造,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做到了通与变的辩证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