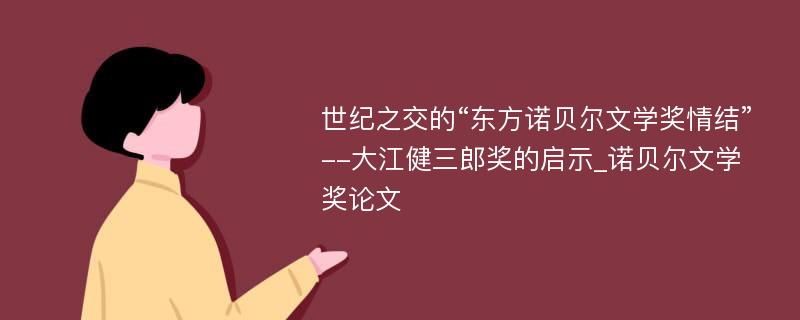
世纪之交的“东方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大江健三郎获奖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诺贝尔论文,世纪之交论文,情结论文,文学奖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世纪之交回顾二十世纪外国文学,有的人说它是“诺贝尔文学”。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能否在本世纪剩下的四年内一解、再解为快?日本作家两度获奖,尤其是大江健三郎近年来的夺魁,在作家作品、推荐战略、评奖政策诸方面都颇有启迪。
二十世纪文学与诺贝尔文学奖
文坛复杂多变的二十世纪即将过去,文学走势难以猜测的二十一世纪就要到来,在世纪之交回顾、总结本世纪的外国文学,因角度、标准或参照系的不同,而有各种不同的提法。有人着眼于东、西方文学的融合趋势,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已进入“世界文学”的时代;有人鉴于文学向内转即注重心理描写的趋向,从文学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是一种“心态文学”;有人强调文化人类学对文学的冲击,从文化寻根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是“神话回归”的文学;有人注意到文学的回归文本与重视形式现象,从文本学、叙述学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是“寻求形式”的文学;有人概括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无产阶级文学)三分天下的现实,从文学思潮、创作方法的角度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是“三足鼎立”的文学;也有人根据越来越显著的多种方法、流派、思潮、风格、倾向相互影响、并存和更替的五花八门的文坛现状,联系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经济、多元化文化的趋向,而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是“多元化文学”,等等。然而不应忘记,还有特别重视诺贝尔文学奖的巨大作用和贡献,以此为参照系而提出二十世纪文学是“诺贝尔奖文学”,因为尽管获奖名单中遗漏了许多一流大作家,“但全面地看,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作品还是基本上代表了20世纪文学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探求,绝大多数作品无愧于20世纪世界文学遗产。”[①]
确实,二十世纪全世界文学界的最高荣誉和大奖,非诺贝尔文学奖莫属。有人恰当地将其比喻为“文学奥运会”的“金牌”。对之作家自然情有独钟,就是一般国人也视为国家荣誉而心向往之,形成“情结”。从1901年第一次颁奖到1995年,全世界共有92位作家获此殊荣,其中西方(欧美)作家85人,占92.4%,而东方(亚非)作家只有7人,占7.6%。以东方的人口、面积和文学历史、成就等来衡量,这个比例太不相称了。特别是文学大国中国,居然至今无一位作家名列其中,无异在“文学奥运会”上的“金牌”纪录还是零。这不能不令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遗憾和深思。
究其原因,我们首先不能排除长期以来世界政坛和文坛上的“欧洲中心主义”偏见的影响,因为诺贝尔文学奖毕竟是西方人设立的奖项。其次,文学的影响力与经济实力关系极大,亚非各国除了日本,在经济实力上尚难与欧美各国比肩,日本迄今已有两位作家(1968年川端康成,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奖,为东方国家之仅见,不能不说其经济实力起了很大的作用。再次,从文学本身来说,东方文学从近代以来落后于西方文学的局面并未彻底改变,加之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没有好的译介,再好的东方作家和作品也难以交流到西方而造成世界性影响。如此说来,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情结”,恐怕难以在短时期内解开了。
随着世纪之交的临近,久已郁结的“东方诺贝尔文学奖情结”愈加强烈。屈指算来,本世纪只剩下四个席位(1996-1999年)可供竞争了,东方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还有可能在剩下的四届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中取得突破吗?难度无疑是很大的,我们知道,每一年都要由世界各国推荐提名几百名候选人来竞争这项世界级的荣誉,评选委员会几番严格的筛选之后,剩下五名,再投票表决,票数最多者就是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1993年之前,评选委员会中甚至无人懂中文,直到1993年,才首次增选了一名汉语教授,但也仅有一名而已。不过,日本“梅开两度”是颇有启迪意义的,特别是大江健三郎的再次获奖,从作家作品、推荐战略、评奖政策诸方面留给我们很多值得深思、探讨、借鉴、改进的地方。下面着重对此作一粗浅分析。
评选标准与大江健三郎其人其文
在诺贝尔的遗嘱及由此而制定的诺贝尔奖颁奖规章中,文学奖的评选标准是:不论国籍,但求对全人类有伟大贡献,且具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文学作品。不难看出,这个标准太过笼统,也太死板。因此在具体操作中,评委会会在不同的时期将标准作出相应的变通,以适应文学不断发展的实际情况。如瑞典诗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成员埃斯普马克曾于1987年说过:“三十年代,得文学奖的人是高尔斯华馁、辛克莱·路易斯、赛珍珠等,因为他们是世界公认的作家,文学奖是奖给对全人类有益的人。当时许多人都喜欢看他们的作品,大战以后发生了变化,年轻的读者喜欢看现代作品,年轻的评委会倾向于艺术上有创新的人。艾略特、福克纳等被推上来了。他们的作品的读者范围虽然在当时还不大,但质量是上乘的。采取这样的标准完全是一种新的做法。……到底怎样评文学奖,现在又有新的标准,把未出名的作家推向世界。当法国作家西蒙获奖时,有人问:“干嘛给西蒙?这个人连我们法国人也不知道。’‘他的作品棒极了!’我只能这样回答。现在他的作品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仅是法国。”[②]
同样,当大江健三郎得知他继泰戈尔(印度,1913)、阿格农(以色列,1966)、川端康成(日本,1968)、索因卡(尼日利亚,1986)、马哈福兹(埃及,1988)、戈迪默(南非,1991)之后,成为第七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东方作家时,他也感到很偶然,甚至谦虚地说,他属于日本文学流派中的“少数派”,虽说向世界文学学习,但“正在没落,似将绝种,基于此才授我以诺贝尔文学奖”[③]。日本读者也感意外,据说在获奖消息传开后,电视台播放了一则报道,表明他母校东京大学的大多数学生都没有读过他的作品;节目主持人竟脱口而出,要是吉本芭娜娜(日本青年女作家吉本真秀子的笔名,作品在欧美非常畅销)得奖就好了,言下之意是大江的名声还不及吉本芭娜娜,真想不到会得这么大的奖。
但是,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及不同时代的变通情况来衡量,我们不得不承认评选委员会是有眼光的,大江健三郎可以说是当年度的最佳人选,他的获奖完全是必然的结果。他始终怀抱并坚持不懈地在作品中表达一个人道主义的理想。如他所述,“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人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④];“我认为面对另一形式的全部毁灭的可能性,必须提出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文学典型。”[⑤]大江对现实黑暗的揭露、对社会罪恶的谴责、对人性弱点的嘲讽,都是基于人道主义理想的,并以存在主义作为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不可缺少的补充。他的两部长篇小说代表作《个人的体验》(1964)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1967)完美体现了他创作中的两大民族性与国际性相结合的题材--“人类痴呆弱智儿及其父亲的痛苦和再生体验”与“人类面临核威胁的死亡体验”,从而控讨了人类永恒的“死和再生的主题”[⑥];这与他一生为之奋斗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两大社会政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他的创作方法溶现实主义基础、心理体验特色、变异怪诞风格为一炉,独创性地将这三大要素整合成为“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方法,在当代世界文学中独树一帜、独领风骚[⑦]。他以引人注目的创作理论与实践,很好地解决了东西方文学中都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四大课题--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相结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小宇宙与大宇宙相结合、现实与神话相结合,从而得到世界文坛的公认与崇敬,奠定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国际性文学地位。在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已经先后得到国内外的“芥川文学奖”(1958)、“新潮社文学奖”(1964)、“谷崎润一郎奖”(1967)、“野间文艺奖”(1973)、“读卖文学奖”(1982)、美国“巴克雷校特别功劳奖”(1983)、“伊藤整奖”(1989)、欧洲共同体“犹罗帕利文学奖”(1989)、意大利“蒙特罗文学奖”(1993)等。他的作品已被译为世界上的八十六种文字出版。到1994年,瑞典文学院对大江的评价已经非常之高,其授奖理由为:“大江凭着诗的想象力,创造了使现实与神话紧密地凝缩在一起的想象的世界,夸张地描写了现代人的形象”;“在他自己创造的想象的世界里,他努力发掘个人的体验,成功地描绘出人类共同的追求。这在他成了残疾儿的父亲之后的作品里有更充分的体现。”[⑧]
评选程序与日本举国推荐战略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一般由5-6人组成,均为瑞典文学院院士,每位评委任期三年,但可以连任。评委会每年秋天从几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由具备资格的人或团体所推荐”的文学家中选出五名候选人,把名单和报告交给瑞典文学院。虽然瑞典文学院可以不受这张名单的限制,但每年的得奖人几乎都是从这五个人中选出,而且往往是他们推荐的头一名。
每个星期四下午,这几位评委就聚集在斯德哥尔摩老城王宫后面瑞典文学院的图书馆里,进行两、三个小时的讨论,互相介绍各国的文学作品,有时也约请其他专家翻译、介绍评委会所缺门的语种的文学作品。在长方形的桌子边上排满了从全世界各地来的书籍和推荐材料、初审报告等,供评委们参考。讨论中大家都互称“先生”和“您”,以使气氛显得庄重和客气,避免过于火气大的争论。到晚上八点钟左右,他们就结束讨论,到附近一家中世纪起开设的“金色和平”饭馆去吃饭休息,这家饭馆的二楼上有专为他们设立的雅座。到这里大家的神态就完全变了,互相称起“你”来,甚至兴之所至,还会弹钢琴唱歌曲呢。
他们的工作从选拔到定出名单,再缩短名单、最后作出决定,对任何人(包括政府在内)都是保密的。其间,他们要尽可能地抵制各国大使馆、各国政府或学术团体机构、甚至新闻媒介的压力和意见。这是很不容易的,既要鼓励人家申请、推荐、介绍,又要坚持主见、排除干扰,甚至还要自己去慧眼识珠。这里面,遴选工作跟推荐者的名望、游说以及初审报告都有着微妙的关系。
日本人深谙此道。第一次获奖的川端康成,就有日本评论家指出,他虽是个好作家,却不是一位与诺贝尔文学奖相称的作家。于1968年,日本政府为了他的夺魁,特意在日本举行国际笔会,把瑞典文学院的院士都邀请来,颇有“感情投资”的味道。当年,除了川端,另一个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也曾被日本推荐作为候选人,所以他在得知川端获奖后,慨然长叹道:“今后至少十年,我不用想拿到这个奖了,政府不会为我再去做什么了。”这说明川端获奖,日本政府确实是作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努力的,并且考虑了足够的“保险系数”。川端获奖之后,也曾公正地承认:“我之所以获奖,主要归功于日本文坛,其次归功于我的作品的翻译者。”这也是由衷之言。川端的成功,使日本人兴奋不已,随即期望三岛由纪夫再接再励,再摘桂冠。不想,三岛剖腹自杀了。后来,日本文化界又陆续推出安部公房、井伏鳟二、井上靖和大江健三郎等,大量翻译他们的作品并介绍到欧美,期望再造辉煌。然而,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泥牛入海无消息。前面三人已先后作古,只剩下最年轻的大江了。谁料二十六年后,大江真的不负众望了,了却了日本人多年来的心愿。这一次,日本人巧妙地利用举办广岛亚运会的时机,出动不下五、六个权威学者,力荐描写“反核”、“呼唤和平”的大江。日本笔会会长、文艺评论家尾崎秀树在谈到这次大江获奖时,透露了一点内幕情况:“我也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了。怎么推荐的不能说,怎么运动的也不能说。日本有五、六个推荐委员哩!”从此不难看出日本全面而严密的举国推荐战略和积极主动的“金牌意识”。
在这方面,不少其它东方国家也急起直追,尽管它们大多数目前还未取得“零的突破”。以近邻韩国为例。韩国首都汉城有家著名的大型书店“教保文库”,它的入口处醒目地悬挂着历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肖像画。最近,这些肖像画的中间增挂了一张印有韩国国旗的白纸,纸的空白处写着“等待主人的出现”。这是日本作家大江再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出现的新现象,说明对日本文学在亚洲独领风骚而耿耿于怀的韩国人立志要向“诺贝尔”进军了。在1994年底,到瑞典采访大江获奖仪式的韩国记者一致认为,把韩国文学大力推向世界才是问题的关键,具体的做法可以有:由企业出资赞助及由政府财政资助出版社,在瑞典皇家科学院所在地斯德哥尔摩设立韩国文化中心和购书中心,让评选委员会和欧洲读者有机会接触和了解韩国文化及作家群,等等。可以预料,以韩国的雄厚财力,它必将成为东方国家中角逐诺贝尔文学奖的后起之秀和佼佼者。
评选政策与东方文学的代表性
从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来说,也在不断地注意调整政策,以使这项世界性大奖更具地区和国别的代表性,更注意在敏感的各种世界关系中保持平衡性。如文学与政治关系密切,奖金颁发给谁有没有政治因素在起作用呢?曾有一位评委隆德克维斯特博士绝对否认他受政治的任何影响,但同时又承认:“我并不认为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大艺术家。他写起作品来有点象托尔斯泰。不过我们帮助了一个有重要的话要说,而处境又十分危险的人。他得奖后就有机会把他要说的话向全世界说了。当然我们还给了肖洛霍夫文学奖。这样就比较平衡了,因为他是苏联政府所推崇的作家。《静静的顿河》是他唯一的一部重要作品,他后来的著作完全不够资格。”[⑨]再如文学与语言和翻译的关系,获奖者的遴选是否受到评委会成员根本不懂某些语种像东方的阿拉伯语、汉语等的严重局限呢?当然不可避免,但在宣布颁奖给埃及作家马哈福兹后,瑞典文学院负责人阿伦就说:“瑞典文学院确实没有人懂阿位伯语,但是,如同往年那样,我们利用了翻译版本作出了我们的决定。”[⑩]所以,对于中国作家为什么一直没能获奖的问题,曾任评委会执行主席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教授作过这样的解释:“主要是没有传神的翻译。中国有好几位作家,许多作品是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但是中国的优秀作品往往翻译得不好,不懂中文的外国读者从翻译中看不出这些作品的文学价值。”(11]对这种解释,很多作家和学者给予批评,认为不成其为理由。当然,后来评委会中增加了一名汉学家,说明它的工作还是有改进的,政策还是在逐步调整的。
正因如此,如果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欧洲中心主义还占统治地位,获奖者除印度的泰戈尔、美国的刘易斯等人外,基本上都是欧洲人,那么,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就有阿格农(以色列,1966)、阿斯图里亚斯(危地马拉,1967)、川端康成(日本,1968)获奖,七十年代有怀特(澳大利亚,1973),八十年代有索因卡(尼日利亚,1986)、马哈福兹(埃及,1988),九十年代有戈迪默(南非,1991)、瓦尔克特(圣·卢西亚,1992)、莫里森(美国黑人作家,1993)、大江健三郎(日本,1994)等人获奖。可以说,最大的空白区只剩下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了,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特殊而又特殊的情况,颇值得再次提及。据瑞典驻日本大使透露,1968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本来是要授予中国作家老舍的,而且他是中国作家中截止1992年唯一进入前五名候选人圈内的。鲁迅先生活着时,曾进入候选人名单,但他明确表示不要,后来巴金、冰心、艾青等也曾入围,但他们都没有进入前五名。唯有老舍先生,在1966年评选委员会开始决定考虑一个中国作家时,就逐渐看中了他。因为他的作品早已在西方流传,其中也有瑞典文版的,尤其是他的小说《猫城记》,寓言化地描写了人际关系复杂,嘲讽了人类中性恶的人的劣根性,具有超越时空的艺术价值。这本《猫城记》,解放后的中国没有出过单行本,也没有收入《老舍文集》。而在苏联,全苏作协的杂志《新世界》连载后,又出版单行本,发行量竟达七十万册。那时中苏关系正紧张。老舍先生仿佛是个预言家,他预言到会有把图书馆烧了的一天。在那时的形势下,老舍先生根本不知道诺贝尔文学奖已拍板定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自尽的道路。而诺贝尔文学奖从来不授予已去世的作家,无论他生前多么声名显赫、著作等身。于是,在1968年评选委员会得到老舍先生已去世的确证之后,把在五名候选人中排名第一的老舍注销了,按常规在剩下的四名候选人中再投票一次,原则还是照顾东方作家,这就使日本的川端康成成为幸运者了(12]。当然,也就使得中国遗憾地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了。
往事不可追,中国人都愿意向前看。那么,在二十世纪剩下的四年中,中国人能不能一解郁结了几十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情结呢?笔者大胆地预言:事在人为,能!因为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有着历史悠久、成就卓著的丰富的文学遗产,且在当代也拥有世界文坛公认的优秀作家群。早在二、三十年代,曾有梁启超、鲁迅、林语堂、闻一多等人被提名角逐诺贝尔文学奖;近年来,又有巴金、沈从文、丁玲、冰心、艾青、钱钟书、王蒙、姚雪垠、北岛等人获得推荐。目前,在改革开放的中国,文学正扩大对外交流,加快走向世界的步伐,加之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越来越重视汉语文学的积极恣态,这些条件都预示着中国人离诺贝尔文学奖是越来越近了。
不过,条件再好,大奖也是等不来的。日本的大江健三郎的获奖,说明自身努力争取也是必备条件之一。既然我们把诺贝尔文学奖看作是“文学奥运会”的“金牌”,我们文学界也不妨借鉴体育界的“奥运战略”,树立文学的“金牌”意识。“当然,关键还是要有更为良好的文化环境,要有真正伟大、深厚、优秀的作家、作品不断出现,并且大家配合着一道来,做很多具体细致的准备工作。哪一天中国果然实现了这一‘零的突破’,相信不仅是文坛,而且也是全国全民族的一大盛事”。(13]
注释:
①孟宪忠、邹广文:《诺贝尔文学奖之得失--兼论20世纪文学参照系》,见《社会科学报》1990年11月22日。
②《用燃烧的语言沟通心灵--访瑞典诗人、学者埃斯普马克》,见《文学报》1987年6月4日。
③《大江健三郎谈日本文学与世界文学》,见《文汇读书周报》1994年11月5日。
④大江健三郎:《我在暧昧的日本》,见《个人的体验》附录,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第307、309页。
⑤大江健三郎:《生的定义》,见《广岛札记》,光明日报出版社,1995年,第236-237页。
⑥同上,第325页。
⑦参见拙作:《大江健三郎:怪诞的心理现实主义》,见《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6年第2期。
⑧见《个人的体验》附录,第278页。
⑨转引自亢泰:《诺贝尔文学奖金种种》,见《读书》1981年第3期。
⑩路透社斯德哥尔摩1988年10月14日电讯稿。
(11)引自《文学报》1986年11月20日。
(12)摘自《炎黄春秋》1994年。
(13)徐中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精华集成·序》。
标签:诺贝尔文学奖论文; 文学论文; 日本作家论文; 诺贝尔论文; 大江论文; 艺术论文; 个人的体验论文; 作品推荐论文; 作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