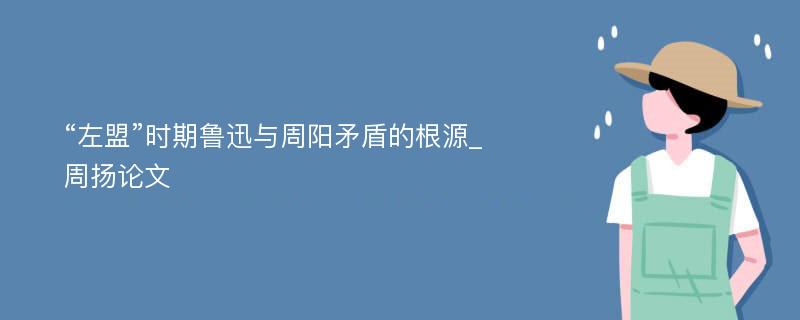
“左联”时期鲁迅与周扬等人矛盾的由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等人论文,由来论文,矛盾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左联”内部的公开论战
1934年8月,由曹聚仁主编的《社会月报》1卷3期, 刊登了鲁迅《答曹聚仁先生的信》一文。此文是关于大众语问题给曹聚仁先生的回信。同期上,《社会月报》还刊登了杨邨人(中共党员,1928年加入太阳社,后来叛投国民党)的《赤区归来记》一文。这便引起田汉的警觉,并以此为由进一步发起对鲁迅的论战。
就在这期《社会月报》发行后不几天,田汉便在《大晚报》副刊“火炬”发表题为《调和——谈〈社会月报〉八月号》的文章,称鲁迅“极善调和”,“替杨邨人氏打开场锣鼓”。显然,这是明指鲁迅为杨邨人捧场。鲁迅对此极为震怒。11月25日,他借答覆《戏》周刊关于改编《Q》戏的问题, 写了一篇《答〈戏〉周刊编者信》(田汉是该刊主编之一)。第一次对田汉的挑战作出公开回答。鲁迅在信中称:自己没有权力“禁止别人将自己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指《社会月报》发表鲁迅给曹聚仁的回信),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但“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从而澄清了“为杨邨人打开场锣鼓”之嫌。至此,信中鲁迅便将田汉(笔名绍伯)和此前廖沫沙的文章连贯一起评说:“这倒并非个人事件,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先生可以施展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所说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鲁迅在信中还写道:倘若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们的憎恶和鄙视,是明显在敌人之上的”。这化了装的“同营垒中人”,当然指的是“左联”内部。这说明鲁迅和周扬、夏衍、田汉等人的矛盾,已经发展到了难于调和的地步。
此间,鲁迅还多处对周扬流露出极为不满,其中有:1935年1 月26日,致曹靖华的信中对“左联”党团组织高层表示不满,称“这里朋友的行为,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出过一种刊物,将去年为止的事情,听说批评得不值一文,但又秘密起来,不寄给我看”;1935年6月25 日,在给胡风的信中,对周扬“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的行为表示不满;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 又披露“左联”领导层内部纷争:“一到里边去(加入“左联”),即酱在无聊的纷争中,无声无息。以我自己论,总觉得缚有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的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真令我手足无措”。
另外,鲁迅对周、夏、田等指称胡风是国民党特务而又不能提出实据也很气愤。1935年8 月他在《答徐懋庸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称:“……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指夏衍)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外两个人(即夏衍、阳翰笙,此即‘四条汉子’最初之说)。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的穆木天口中(穆1930年入左联,1936年被捕)。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便奉为圣旨,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矛盾的双方中似乎周扬一方看得更开一些。他曾想方设法缓和同鲁迅之间的紧张关系。据徐懋庸回忆说:周扬曾要求我和胡风谈话,希望同胡风合作,但为胡风所拒绝。任白戈称:周扬很尊重鲁迅的意见,周扬自己说过,曾着沙丁、欧阳山和胡风往来,希望能消除双方的歧见。显然,周扬是想通过缓和同胡风的关系,进一步达到缓和同鲁迅之间的紧张关系。文人笔战,当与战场上敌对双方有别。
这中间确实牵涉到胡风这个人。胡风和鲁迅原来并不认识, 只是1933年下半年起, 胡风作为“左联”和鲁迅之间的汇报人之后他们才认识的。从此胡风便有机会同鲁迅接触,并且成为鲁迅所信任的人。其间随着鲁迅和周扬等人的关系不断恶化,因而从夏衍到田汉、茅盾等人,都指胡风从中挑拨离间所至。其实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鲁迅毕竟是当时中国思想、文学战线上公认的领袖,他同周扬等人矛盾的发生、发展以及他的处理方式,都不是当时还是一位文学青年的胡风的言论所能左右的。事实上,鲁迅和周扬因《文学月报》长诗事件发生矛盾时,胡风这时还未认识鲁迅。但公平地分析以后的情况,倘若胡风跟鲁迅要好之后,他的心胸更宽阔一些,有意转达对方的诚意,也许真的能缓解双方之间的一些误解。
分道扬镳
1936年初,鲁迅和周扬等分道扬镳了。
事情是由解散“左联”引起的。那是1935年11月8日, 共产国际总部的“左联”代表萧三来信,提出解散“左联”,组织新的文艺团体的建议。这是当时中共在共产国际的代表王明和康生的决定。萧三被迫写了这封信。信是由鲁迅转达“左联”组织的。当时“左联”的上级组织“左翼文化总同盟”(简称“文总”)执行了这个决定。所以说这正如1929年决定组织“左联”一样,此时决定解散“左联”,也是中共上级组织的决定。“左联”党团负责人也只是负责执行罢了。
据“左联”后期党团书记及鲁迅的联络人徐懋庸的回忆,鲁迅对共产国际解散“左联”的决定持反对的态度。鲁迅称:组织新的团体,我是赞成的,但以为“左联”不应解散。我们“左联”作家,虽说是无产阶级的,实际上幼稚得很,同资产阶级作家去讲统一战线,弄得不好,不但不能把他们统过来,反而会被他们统过去,这是很危险的。如果左联解散了,自己的人没有一个可以商量事情的组织,那就更危险。不如“左联”还是秘密存在。鲁迅的担心也曾对冯雪峰说过:我不是别的,就是怕共产党又上当。
“左联”党团组织在讨论“解散”之前,也只是象征性地征询了鲁迅的意见而已。对于鲁迅既赞成组建新的团体,又要保存“左联”的主张,当时以“文总”身份参加讨论会的胡乔木认为,如果一个群众团体内存在另一个团体,这会造成宗派主义的条件。这样鲁迅也便无可奈何。过后他表示:既然大家同意解散,我当然也只能同意。
鲁迅遂要求发表解散“左联”的“宣言”,声明“‘左联’的解散是在新的形势之下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文艺团体所必须的”。“假若这样无声无息地解散,会被人误认为禁不起压迫而溃散”。但最后这个意见也被否了。1936年2月18日, 当徐懋庸将“文总”的最后决定正式告诉鲁迅先生时,“鲁迅当时脸色一沉,不发一言”。
鲁迅显然对这样的结果深为痛心和失望。过后他曾私下对冯雪峰说:就这么解散了,毫不重视这是一条战线。由此看出,尽管鲁迅对“左联”部分成员有种种不满,但对于组织本身,却是极其关切和重视的。
由于萧三给“左联”的信是寄给鲁迅转交的,所以,鲁迅应是看到萧三来信的第一个人。鲁迅对于解散“左联”的提议最初虽然持反对态度,但当“左翼文化总同盟(即‘文总’)和“左联”党团领导层作出相应的决定之后,鲁迅最后只坚持发表解散宣言。鲁迅的这个意见得到“文总”一定程度的尊重。据胡乔木的回忆,最初曾决定以“文总”的名义发表解散宣言,但下属各联(包括“左联”在内)不发表,但后来“文化界救国会”接着成立,如再以“文总”的名义发表宣言,会使国民党把“文救会”看作是“文总”的替身,遂又决定一律不发表宣言。由于“左联”的同志没有及时对鲁迅解释,以引起了鲁迅的严重对立情绪。由此可见,这是由于主管“左联”工作的夏衍、周扬及“左联”的党团书记徐懋庸等人没有充分尊重鲁迅,深入地向他解释而造成的,这应是工作方法的一种过失。
据冯雪峰在《回忆鲁迅》一书中披露:党员作家只简单的征询一下他的意见,而没有和他深刻地研究。林淡秋称:“左联”常委会没有认真讨论过鲁迅的意见,根本漠视了鲁迅在“左联”的领袖地位。胡乔木也指出:“左联”的同志没有郑重地征求和听取鲁迅的意见,“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这样认为只是说造成在“左联”解散问题上和鲁迅不应有的对立,周扬等人起码在工作方式上是有可检讨之处的。由于这样的过失,从而加剧了新的对立的形成。就在“左联”宣布解散,新的统一战线团体成立之时,鲁迅本人拒绝参加,并且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表明自己的立场。一时上海文艺界原先属于“左联”的阵营一分为二,互相对立,爆发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大论战。这样,因1932年底《文学月报》事件而暴露的周扬和鲁迅之间的矛盾,至此便形成了文艺理论根本路线上的全面冲突了。鲁迅和周扬等便这样分道扬镳了。 (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