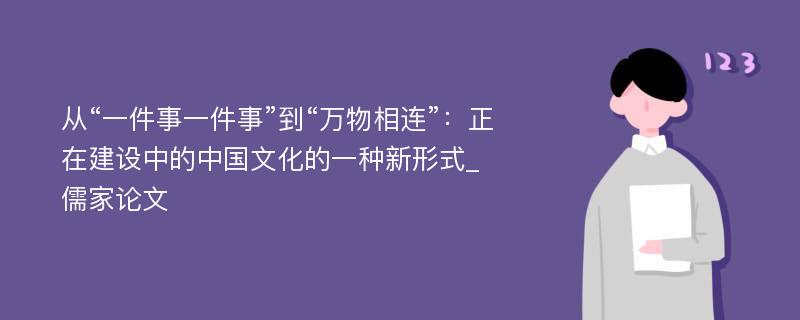
從“萬物一體”到“萬有相通”——構建之中的中國文化新形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萬物一體论文,新形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19世紀中葉的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文化形態可以粗略地概括爲“天人合一”或稱“萬物一體”(此形態綿延幾千年,並非一成不變的)。這一形態顯露出的弊端是,人與人,人與物,皆彼此不通。因此,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後,中國文化在人與自然的關係方面不斷克服傳統中將個性自我湮沒於自然整體之中的思想,在人與人的關係方面不斷克服傳統中將個性自我湮沒於封建社會群體之中的思想,取得了不小的進步,但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未來中國文化應當進一步走出傳統的、原始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形態,達到一種“萬有相通”之境,也就是達到不同萬物之間(包括所有獨立性自我之間)相通相融的狀態。 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或者說“萬物一體”,其特點可以歸納爲原始性、樸素性。具體而言,主要是缺乏“主客二分”的思維模式,缺乏個性自我。由此,在古代社會呈現爲三個特征: 其一,個體性自我被湮沒於社會群體之中,一切都依賴個人所屬之社會群體,思想言行都聽命於父母、家族以及最後唯專制皇帝之命是從。孔子(前551—前479)所說的“克己復禮爲仁……爲人由己”①,雖然有從自我真情出發而爲仁的思想因素,值得珍重,但歸根結底,還是要人自覺地服從貴賤等級社會群體之“周禮”。這就造成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民主自由思想極難伸張的現象。傳統的“天人合一”或者說“萬物一體”觀念,還把個體性自我湮沒於自然整體之中,缺乏自我作爲主體,以自然爲客體和對象,從而認識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這就造成了中國古代不重視自然科學研究的現象。正如梁啓超所總結的:“我國數千年學術,皆集中社會方面,於自然界方面素不措意。”② 其二,人與人之間少有相互往來、相互理解、相互溝通。由於每個個人都衹有其所屬社會群體的共性,少有自己獨特的個性,所以,人與人之間也少有相互往來、相互溝通、相互理解的必要,少有個性交流的內容;至於人與君王之間,更是鴻溝一道,互不相通。也由於缺乏科學技術,缺乏相互交流的客觀條件,遠古社會因此而成爲一個“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③的社會。另外,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在傳統的“天人合一”或者說“萬物一體”中,更明顯的是人很少認識自然,很少理解自然。 其三,人們平常所說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中人與人之間的“一體”、“融通”,不是指不同個性的自我之間的相互交流、相互理解,而是指沒有人我之別的“人皆有之”的人性之同一性,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惻隱之心,仁之端也”④。孟子(前372—前289)所謂“四端”,即“人皆有之”的同一性。當然,孟子思想的可貴之處在於,強調超越此種原始的同一性,而將此“四端”擴而充之,成爲仁義禮智之“四德”,亦即發揮“心官”之“思”的功能,使人能成爲其“所以爲人”的“大人”。孟子引顏淵說:“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⑤其重視自我個性,由此可見一斑。但孟子在這方面的思想仍然顯得極其簡單樸素。在古代封建等級社會的群體裏,即使將此“四端”擴而充之,以達於“人倫之至”的“聖人”⑥,亦難違君命而盡展自我之個性。不過,無論如何,孟子多少還是指出了一條伸張自我個性的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⑦孟子這裏所謂“大丈夫”者,即“不移”、“不屈”的特立獨行之人也。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也許就是人之由屈從“天人合一”之原始同一性走向孟子所謂“大丈夫”的一條漫長而曲折的發展過程。孟子在原始的“天人合一”佔主導地位的時代(他自己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而言,也是此種“天人合一”的思想)說出了超越“天人合一”的遠大理想,實屬難能可貴。 就人與自然的關係而言,所謂“天人合一”、“萬物一體”中人與自然之間的“合一”、“一體”,也不是指人作爲主體,以認識作爲客體的自然,從而達到主客對立統一之後的一種通透的精神狀態,而是一種朦朧模糊的混一景象。在原始的“天人合一”中,人不理解(不認識)自然,故不能說與自然相通。人們在日常語言中有時也把原始“天人合一”中的“合一”說成是“人與自然相通”,這種所謂“相通”實際上是指人與自然間的一種無意識的不可分離的聯繫。這衹是一種自然現象,而不是指人對自然有了認識、理解和領悟之後的通曉、通透——“靈通”。 與古代原始“天人合一”、“萬物一體”的文化形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現當代正在構建的“萬有相通”文化形態。其特點有二: 首先,自我的個性日益從社會群體的束縛中獲得解放。自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各種個性解放的社會現象,尤其是中國大陸19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中國人的“自我”,從做服從權威和社會群體的“螺絲釘”到有自己獨立的生活訴求,做一個能以人本身爲目的之人,這一自我覺醒過程,是一個從量到質的變化。目前,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變,更使中國人的“自我”得到伸張,社會生活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個性化。現在,人們大多都嚮往以“自我”爲中心來設計自己的世界;微博、微信、微電影之類的“微”現象,已經把人們帶入一個儘量滿足個人當下生活的“微時代”,人在各種“微”生活中表達自我當下的、片段的情緒和感受,以至即興的創作,從而大大擴展了自我表現的領域,分享豐厚的世俗生活的意義;儘管這裏不免有思想性較弱、內容不夠深厚等缺點,但畢竟讓中華民族的文化向着個性伸張、多元共生的方向前進了一步。當前,在經濟生活方面,人們不斷發現個性的“自我”,發現嶄新的“世界”,其伸張程度甚至到了引起人們警惕“個人主義”膨脹的地步,不少人開始抱怨以至於譴責“個人物欲擴張”、“跟着(我的)感覺走”等現象。客觀地說,這種抱怨或譴責是合理的,但同時也應認識到,此種現象是對幾千年來原始“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思維模式下個性“自我”被湮沒和禁錮於封建社會群體之中的文化形態的一種反彈、反動,有其產生的歷史必然性。相對而言,此種現象有解放“自我”的積極作用。 其次,“萬有相通”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是原始“天人合一”、“萬物一體”形態下的那種互不相通——互不理解的關係,而是相反:互相理解——互相融通。當今社會生活中特別是經濟生活中的每個個人,既是獨立的,有個性的,又不是孤立的,與他人隔絕的,而是與他人、與遠在天涯海角的人,甚至與陌生的人,或直接或間接地聯繫在一起的。互聯網、手機、電腦的信息交流最具體地、最明顯地說明了這一點。現在,整個宇宙已形成了千千萬萬、無窮無盡的網絡聯繫的有機整體,“萬有”亦即每個物、每個人,都是這一整體中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相互依存的一個交叉點;每個個人,既有其是某一交叉點的特點、個性,又與其他個人——其他交叉點息息相關:互聯網、手機、電腦不過是此種“息息相關”中的一種具體表現方式;人們由此而產生的經濟生活方面的“相互理解”,則更是深層的。人與人之間在日常生活方面相互理解到當今這樣廣泛的程度,主要是靠互聯網造成的。這種相互理解,既是虛擬的,又是現實的。“萬有相通”在這裏有了非常具體的體現。在經濟全球化形勢下,國與國之間相互依存的現象已越來越頻繁,開放、包容、對話的全球意識已是大勢所趨,這也是“萬有相通”之一例。顯然,現代科學技術的發達,既造成了人對自然的認識和瞭解,也是人與人之間相互理解、相互融通的條件之一。 “萬有相通”的整體,既是真,又是善,也是美。就一人一物之真實面貌衹有在此整體之中、在此無盡的普遍聯繫之中纔能認識(“知”)到而言,它是真;就每個人在此整體之中相互支持、相互愛惜,從而使人有“民吾同胞”之同類感(“意”)而言,它是善;就此整體給人以無窮無盡的玩味、領悟(“情”)而言,它是美。“萬有相通”之整體,集真善美於一體,堪稱萬有之源。 “萬有相通”之“相通”,其實是一種“靈通”。也就是說,“萬有”因人而相通:因人而美(因人而有美醜),因人而真(因人而有真假),因人而善(因人而有善惡),借用王陽明(1472~1529)的話來說,“人心一點靈明”是萬有一體的“發竅之最精處”⑧。若無人心,則天地萬物是不開竅的、無意義的漆黑一團,談不上有意義的相通。這樣來看,“萬有相通”之“相通”,乃是一個發展的過程,它隨着人的認識、審美、道德意識之逐步深入而逐步加強:認識、審美、道德意識愈深入,“萬有相通”的程度便愈強。從原始的“萬物一體”到“萬有相通”,也是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華幾千年的文明史,從一人獨斷專制到個人自由的逐步放開,從“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到今天之一機在手、雖相距萬里亦能互訴衷腸,從愚昧無知的巫術迷信到今天現代科學技術的繁榮發達,都很清楚地說明,從原始“萬物一體”到“萬有相通”是一個宇宙萬物愈來愈“靈通”的發展過程。 “萬有相通”的“整體”與傳統的“萬物一體”(“天人合一”)之“一體”(“合一”),表面相似而又大有區別:“萬物一體”(“天人合一”)之“一體”(“合一”)是無區別、無個性的簡單同一;“萬有相通”之“整體”是有個性的千差萬別之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物、自然物與物之間的相通相融。簡單同一衹講相同,必然抹殺不同的個性,也就談不上彼此,談不上彼與此之間的相通;衹有承認了有個性的差別或不同,纔有可能談不同的兩者間的相通。“簡單同一”與“不同相通”是兩個不同的概念,有高低階段之分:一個是原始的,一個是現當代的;一個是混沌蒙昧的,一個是靈明清晰的。由“萬物一體”到“萬有相通”,由簡單同一到不同相通,其所經過的歷史發展過程既漫長又曲折。如果把由“萬物一體”之“一體”到“萬有相通”之“整體”稱作一種“回歸”,那乃是一種高級的回歸,一種否定之否定的回歸。軸心時代以前的部落意識,可以說是嚴格意義的“萬物一體”意識,個人的自我完全融爲自然的一部分,融爲部落集體的一部分,沒有獨立自主性;是軸心時代開始把人帶入了“個人意識”和“理性意識”,而在西方文化史上,主要是經過文藝復興、啓蒙運動至19世紀中葉幾百年間以“主客二分”式的自我主體性思想爲主導的否定階段,又對這種否定階段再加以否定,纔發展到19世紀中葉以後現當代的不同自我間的“對話文明階段”⑨,即一種具有“全球意識”和“整體意識”(不同於“個人意識”)的“萬有相通”的文化階段。但西方人受“主客二分”式的思想傳統的影響太深,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一直束縛着他們而難以超越,他們欲學彼此融通的思想亦非易事。“萬有相通”在西方現當代文化狀態下,還有待完善和發展。 在中國文化史上,自軸心時代開始,伸張自我的思想雖時隱時現地綿延着,明清之際稍有較多的表現,但“主客二分”式的自我主體性思想直到19世紀中葉鴉片戰爭以後纔明確地由西方輸入。上述“否定之否定”過程中的中間階段——第一次否定,亦即伸張自我的階段——也衹是從那時纔真正開始,比起西方來落後了幾百年,而且從那時以來的一百多年時間裏,自我個性的解放不斷受到阻擾。作爲當今文化發展的一種趨向,一種文化理想,目前中國的“萬有相通”正在構建之中。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萬物一體”)思想是中國文化童年時代的精神狀態,它的“天真”的詩意境界仍然可以對今人產生一種類似於古希臘藝術、史詩所留給人的“永恆魅力”。例如,傳統“天人合一”中所蘊涵的那種渾厚、淡遠的神韻和胸懷,至今都值得人們深思玩味。因此,對古人的這一思想應當採取珍重的態度,絕不能因爲時代的變遷而簡單蔑視。再者,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形態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它在數千年的緩慢發展過程中也有進步的東西。例如,宋明時期的“天人合一”就比先秦時期的“天人合一”進步得多,雖然那些進步的東西仍未脱離“天人合一”的總範疇,但卻值得今人去汲取。同時,今人也需要認識到,童年時代的東西,其產生的社會基礎已經消失,不能與今天成年時期的互聯網等先進科學技術之類的東西相提並論,不能把原始的“天人合一”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今天來“拯救危機”。 之所以說“萬有相通”在中國衹是“正在構建”中,其最關鍵之處在於,中國的自我之個性解放現象主要還是體現在經濟領域和科技領域,遠未達到在思想意識、觀念形態領域的個性解放,而後者的個性解放卻是“萬有相通”的必要環節。如果在思想、學術方面依然是心理學家朱瀅所說的“中國人依賴他人”的“互倚型自我觀”⑩,不敢越雷池一步,那麽,實現獨立創新、“萬有相通”的理想就必然漫長而遙遠。 思想意識、觀念形態領域裏缺乏自我個性,追根溯源,在於長期受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簡單同一觀念所束縛。強求一致(簡單同一),不容異見,其實質是同而不和,相同而不相通。孟子在批評戰國時的農學家許行(约前372—前289)主張“巨屨小屨同賈”時說道:“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11)因爲,許行的主張,正是抹殺物之不齊(不同)而強求簡單同一、“比而同之”的思想表現,所以,孟子斥之爲“亂天下”和“相率而爲僞”之道。 美國語言哲學家蒯因(W.V.O.Quine,1908~2000)的“整體論的檢驗理論”告訴人們,在整個知識或信念的體系中,各種命題構成一個圓圈,居於中心的是內容玄遠的命題,其普遍性最強,距離中心最遠的感性命題最少普遍性。後者與經驗的接觸最直接,兩者之間的衝突首先引起距中心最遠而距經驗最近的命題的調整和改變,最後纔引起居於中心的命題的調整和改變。這就是說,距中心愈遠和愈接近邊界經驗的東西,其改變的速度愈快,愈靠近中心的東西,其改變的速度愈慢,而中心則不輕易因周邊的改變而等速改變,但即使是居於中心的命題也不是不可改變、不可調整的。借助於蒯因的這一理論加以分析,可以發現,經濟、科技與思想、觀念形態的變遷關係,也類似於蒯因所說的周邊變速與中心變速的關係。經濟、科技與思想、觀念形態實可以概括爲一個由中心與不同層次的周邊構成的圓圈:粗略地講,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思想、觀念形態是中心,經濟、科技是周邊;具體地講,思想、觀念形態居於最中心的地位,生產是邊緣,器物、金融、科技等則是這個圓圈所包含的不同層次的周邊(這裏且不談器物、金融、科技這些層次的具體的遠近程度和次序)。經濟、科技的變化和進步“推動”思想、觀念形態的變化和進步,但經濟、科技是一個民族、國家與外界(即其他民族、國家)最直接接觸的方面,其變化的速度也最快,而居於中心的思想、觀念形態雖有變化,但變速甚慢。換言之,經濟、科技是比較敏感、比較靈通的領域,而思想、觀念形態則是比較遲鈍、比較固執的領域。就個人來說,經濟生活的外貌上的改變和科技的進步,相對而言,也是比較容易的,而思想、觀念形態的改變和進步卻是困難的。思想、觀念形態的變易性往往滯後於經濟、科技方面的變易。這也可以解釋,爲什麽中國在經濟生活方面已由原始“天人合一”那種閉塞和缺乏個性的狀態迅速轉變爲如此廣泛的個性化和開放狀態,在科技方面的獨創性進步已達到中華文明史上空前的地步,而在思想意識、觀念形態方面卻仍保持傳統的一元化,缺乏自我獨創性。它表明,思想、觀念形態方面的個性解放(民主、自由、多元化),衹能是逐步逐步、緩之又緩地進行的。 “萬有相通”除了伸張“自我”個性這一必要環節外,還必須進而超越自我,超越“主客二分”,達到萬有之間、千千萬萬個“自我”之間的相通相融。否則,就會重走西方“主客二分”式的“自我專制主義”(12)老路——唯我獨尊,極端的個人主義。西方現當代思想家對這種舊傳統大多持批評態度。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的“互主體性”學說,批評西方傳統的“主體性哲學”,反對唯我獨尊的“主體”,便是一例。當前中國經濟生活方面的個人主義膨脹現象,也是此種“自我專制主義”的表現。因爲它衹承認一己之“自我”,而抹殺他人之“自我”,所以要明瞭每人每物作爲宇宙這一大網絡整體中的一個交叉點,都因“相互隸屬”(海德格爾語)、相互支援、相互融通而存在,故“民吾同胞,物吾與也”(13),人皆需要尊重、愛惜他人之“自我”。也因爲這個緣故,應特別提倡包容、寬容的品德。包容、寬容,就是能容納他人之“自我”的個性,也就是能容納他人之“不同”——不同的聲音,不同的意見,不同的風格,等等。當今的社會,既是伸張不同“自我”個性的社會,也更需要恢宏大度,海涵“他人”的不同個性,這正是“不同而相通”的重要內涵。(14)“萬有相通”的哲學,正是追求此種寬闊、高遠的人生境界之學。 “萬有相通”的哲學,一方面是要伸張自我,另一方面又要超越自我。借用中國經典語言來說,就是要求人既不能無我,做“喪己”之人,又不能執著於我,而應進而“忘我”。這樣,此種哲學又可稱之爲“忘我之學”,或者更全面一點說,是“物我兩忘之學”——針對中國思想、觀念形態領域中缺乏自我個性,提倡個性解放,提倡“有我”;針對當前經濟生活領域中的個人主義氾濫現象,提倡人皆以“民胞物與”的胸懷和精神境界爲追求目標,提倡“忘我”。但正如辯證唯物論所講的,“存在決定意識,意識卻又可以反作用於存在”;同樣,居於上述圓圈之中心位置的思想、觀念形態,雖由居於周邊位置的經濟、科技的推動而緩慢變化、前進,但思想、觀念形態卻又可以“反作用”於經濟、科技。此種“反作用”可以是順勢的,也可以是逆勢的。如果思想、觀念形態領域的主導力量逆勢而動,屬意於抑制自我的個性解放,則連經濟、科技領域裏個性解放的進程以及與之相聯的獨創性也會受到阻滯和壓抑。所以,在上述兩方面中,當今更應着重於提倡思想、觀念形態方面的個性解放,提倡“有我”。 既曰“萬有相通”,則“相通”的方面遠不衹人與自然之間的相通和人與人之間的相通,它還包括自然物與自然物之間的相通,如有生命之物與無生命之物之間的相通,植物與動物之間的相通;包括人生的各個方面之間的相通,如人生諸種精神境界(欲求境界、求知境界、道德境界、審美境界)之間的相通,各種社會活動(經濟活動、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等等)之間的相通,工農商之間的相通,以及中西兩種不同文化之間的相通,等等。與這些相應的,還有各種學術研究領域之間的相通,如植物學與動物學之間的相通,生命科學與無生命科學之間的相通,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相通,哲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相通,倫理學與美學之間的相通,政治學與經濟學之間的相通,所有這些“相通”,與原始的“萬物一體”(“天人合一”)之“一體”(“合一”)相比,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徵,既重彼此之“不同”(區分、分明)又強調“相互融通”,強調相互結合成一靈通的有機整體。從原始的“萬物一體”(“天人合一”)之“一體”(“合一”)到現當代的“萬有相通”,是一個由混沌不分,經逐漸區分,逐漸分明,到超越區分而達到有機結合,融通爲一整體的過程。人與自然的關係以及人與人的關係,已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即就社會分工來說,“分工”乃近代文明特別是西方近代工業社會的產物,而非古代社會的特徵,也同樣能說明這一過程;再看各種學科研究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在原始“天人合一”、“萬物一體”佔主導地位的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學科的研究多重混合,而很少重視分門別類,自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以後,已陸陸續續地走出傳統的“萬物一體”的思維方式,學習西方的分析式(包括“主客二分”),在學術研究方面更多地重視專科研究,分科越來越細,如今又認識到了片面運用分析式的弊端,近些年來強調交叉學科研究的呼聲也越來越強。西方現當代(或稱“後現代”)學者也已認識到他們非此即彼的分析式傳統(包括“主客二分”)的弊端,而提倡彼此融合、相通的思維方式,在學術研究方面實踐交叉學科的研究中開創新的學科。 凡此種種均表明,“萬有相通”的哲學是一種既要求重視萬有之各自的個性,又提倡萬有之間的交融共生、平等對話的哲學。此種哲學思想,在中國當代文化的各個方面已有了不同程度的體現。由“萬物一體”(“天人合一”)到“萬有相通”,是中國文化歷史發展的大道,“萬有相通”的哲學應是中國文化走向未來的路標。 注釋: ①《論語·顏淵》,北京:中華書局,2012。 ②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第50頁。 ③《老子》,第18章,北京:中華書局,2012。人們一般都以小農經濟社會的原因來解釋這種現象,我完全同意;我這裏衹是從科學和思想意識的角度來做點說明。 ④《孟子·公孫丑上》,北京:中華書局,2012。 ⑤《孟子·滕文公上》。 ⑥《孟子·離婁上》。 ⑦《孟子·滕文公下》。 ⑧《王陽明先生傳習錄》卷下,合肥:黄山書社,2011。 ⑨[美]列奧納德·斯維德勒:《從軸心文明到對話文明》,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3,第43~59頁。 ⑩朱瀅:《文化與自我》,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 (11)《孟子·滕文公上》。 (12)猶太裔法國哲學家萊維納斯,E.Levinas,1906~1955,批評西方傳統文化的用語。 (13)《張子正蒙·乾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14)關於“尊重他者”的問題,還可以參閱復旦大學孫向晨《面對他者——萊維納斯哲學思想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