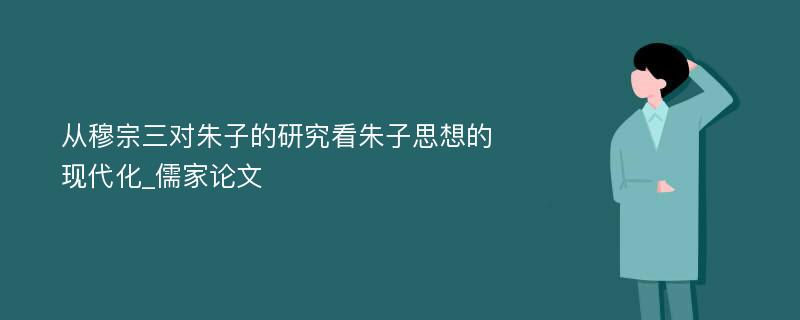
从牟宗三的朱子研究看朱子思想的现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子论文,现代性论文,思想论文,宗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中国儒学的开山祖师当然是孔子,但因为他自谦“述而不作”,不但引起了抬举他的汉学家对他有不同的封号,或尊为“素王”,或称为“先师”,在学术思想上也引发一场今古文经学的论争。而晚於孔子一千八百年的朱熹,虽然只是为孔子《论语》作注解,而且声明他注解的每一个字都如在天平上称过,即孔子怎么说,他就怎么注,不轻一点,也不重一点;不高些,也不低些。这说明,朱子自信只有他才真正懂得孔子,也最有资格做孔子的传人。他不但用同样的方法注解四子书,而且注遍群经,其成就与贡献遂得到了极大的肯定。
牟宗三先生在《心体性体》一书中,推崇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其所反映投射之颜色,沾满一切,吾人虽不能以为标准,实不能不以为中心(焦点)〔3〕。牟先生肯定朱子对儒学的贡献, 既提醒吾人研究儒学不能以朱子为标准,又不能不以朱子为中心,此话看来十分吊诡。其实正因为牟先生对朱子之学看得透彻,才把握到朱子思想的真义,才得出此一结论。他首先批评朱子的心态根本不宜于讲《论》、《孟》、《中庸》与《易传》,因为对於由《烝民》诗所统系之心、性、仁一面,与《维天之命》诗所统系之“於穆不已”之天命之体一面根本不能有生命、智慧上之相呼应。而且以“心之德、爱之理”的方式去说“仁”,既不能尽孔子所说仁之实义,以“心、性、情三分”之格局去理解孟子,尤与孟子“本心即性”之本心义不相应;以“理气二分”之格局去理解《中庸》、《易传》“生物不测”之天道、神体、乃至诚体、尤觉睽违重重。因此若以朱子为标准,根据其讲法去理解先秦旧典,与儒家的基本义理实不相应。唯一相应的是《大学》,虽不必完全合《大学》原义,然毕竟是相应,故能顺格物穷理的认知方式,重视“下学”与“道问学”的层面,而开出另一重知识的系统。就先秦儒学之正宗言,固是一步歧出,但就儒学思想之发展言,不但是一步突破与创新,且与现代重知识的思潮相衔接。而本文即根据牟先生此一判别为基础,尝试探讨朱子思想中之现代性。
(二)朱子舆道统
⑴朱子在道统中的地位。首先就客观地位言,朱子乃儒家道统的建立者,且自任为道统之传人,如门人黄榦撰朱子行状,即谓“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得统之正,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其后《宋史》的《道学传》也称“朱夫子承宋儒的正宗”。当今朱子学专家陈荣捷先生在论朱子的贡献时更下结论说:“朱子已建立新儒学之整个建构于坚固基础上,在此一意义上,朱子实‘集’新儒学整个系统之大成。”〔4〕但牟先生卻提出相反的看法,说朱子为“别子”而非“正宗”与儒家道统无关,实际是另外开出一传统。其言曰:“朱子固伟大,能开出一新传统,其取得正宗之地位,实只是别子为宗也。〔5〕
其次就学问内容言,《中庸》指出的“尊德性”与“道问学,一直被公认是支撑儒学规模的两大支柱,或比喻为车之二轮。朱子也认同此义,在《答项平父书》云“大抵子思以来,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问学两事为用力之要。今子静所说专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论却是问学多了。”显然朱子已察觉到自己在两者之中有所偏差。但钱穆先生在《朱子新学案》中却赞美“朱子精神充满,气魄恢宏,故能立大规模而兼斯两者,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四通六辟,成此一家”。而牟先生却提出相反的看法,批评朱子与《中庸》,甚至《论》《孟》《易传》等先秦儒家旧典根本不相应。牟先生说他原来也是接受传统的看法,认为宋明儒都是继承先秦儒家,既“尊德性”又“道问学”,认为象山阳明,与朱子及朱子之后学互相争论对尊德性与道问学孰轻孰重的问题,无多大意义。直到他认真去处理内部之义理问题,才发现其中争论并非全无意义,也不完全是门户意气之争。即两者之间实有义理之根本差异处,不可不作进一步之分辨,而终于判定双方为两个不同的系统。象山阳明才是继承道统之正宗,而伊川是礼记所谓“别子”,朱子则是继别子为宗者〔6〕。
⑵朱子非正宗而是“别子为宗”。牟先生一再表示他整理疏解北宋四家与朱子为一艰钜的工作,不仅因为朱子著作分量最多,而且朱子是由遍注群经,讲遍北宋四家而形成系统者,是故其要点之确义颇不易把握。思想的脉胳亦不够凸显。所以很多研究朱子者,很难一探究竟,常觉冲突百出,矛盾重重。而牟先生说他是用坚壁清野的办法,即在双方的比对剔剥中将朱子所反映投射的颜色一一剔剥开来,还其本来面目,而双方的眉目自然郎现,而彼此的思路也就清晰可辨了。例如他将朱子对孟子心、性、情、才之理解,或“尽心知性”之理解;对《中庸》“中和”之理解,以及对于濂溪、横渠、明道等所讲的诚体、神体、仁体的理解,发觉皆不相应;而且朱子力斥象山为禅。这才发现真正的关键在对“道体”一义了解不透,因而影响工夫入路完全不同〔7〕。
牟先生解释这不透的一点,即在:对于形而上的实体只理解为“存有”(Being,ontological being)而不活动者(merely being but notat the same time activity)。但在先秦旧义以及濂溪、横渠、 明道之所体悟者,其形而上的实体,或称天命不已之体,易体、中体、太极、太虚、诚体、神体、心体、性、仁体等乃是“即存有即活动”者。至于朱子则不能讲诚体、神体、心体。因为朱子所言的实体“只存有而不活动”,这是两者之差别,也是系统之所以分的原因〔8〕。
所谓“即存有即活动”的实体,就统天地万物而为其体言,曰形而上的实体(道体Metaphysical reality),此即是能起宇宙生化之“创造实体”,就其具于个体之中而为其体言,则曰“性体”,此则是能引起道德创造之“创造实体”,而由人能自觉地作道德实践以证实之,此所以孟子言本心即性也。客观地、本体宇宙论地自天命实体而言,万物皆以此为体,即潜能地以此为性,但不能像人一样能自觉地作道德实践,故只有能以此为性〔9〕。
牟先生认为宋明儒的正宗应与《论》《孟》《中庸》《易传》精神相继承相呼应,其目的是在豁醒先秦儒家的“成德之教”,是要说明吾人之自觉的道德实践所以可能超越的根据。此超越根据直接地是吾人之性体,同时即通形而上的实体,即由“尽心知性知天”而渗透至“天道性命通而为一。”本心是道德的,同时也是形而上的,具有绝对的普遍性。心体充其极,性体亦充其极,心即是体,故曰心体。自其“形而上的心”言与“于穆不已”之天命实体合而为一,则心也而性矣。自其为“道德的心”而言,则性始有真实的道德创造(道德行为之纯亦不已)之可言,是则性也而心矣。是故客观地言之曰性,主观地言之曰心。自“在其自己”而言,曰性;自其通过“对其自己”之自觉而有真实而具体的彰显呈现而言则曰心。客观地自“于穆不已”之天命实体言性,其“心”义首先是形而上的,自诚体、神体、寂感真几而表示。若更为形式地言之,此“心”义即为“活动”义(Activity),是“动而无动”之动。此实体、性体,本是“即存有即活动”者,故能妙运万物而起宇宙生化与道德创造之大用。与《论》《孟》通而为一而言之,即由孔子之仁与孟子之心性彰著而证实之。是故仁亦是体,故曰“仁体”,与孟子的心性,皆是“即活动即存有者”。这就是由《论》《孟》《中庸》《易传》通而为一的主要内涵,牟先生即根据此一中心观念作为判教根据,依“只存有而不活动”说,则伊川、朱子之系统为:主观地说,是静涵静摄系统;客观地说,是本体论的存有之系统,简言之,为横摄系统。依“即存有即活动”说,则先秦旧义以及宋明儒之大宗,皆是本体宇宙论的实体之道德地、创生的直贯之系统,简言之,为纵贯系统。系统既异,含于其中之工夫入路亦异。横摄系统为顺取之路,纵贯系统为逆觉之路〔10〕。
以上的分判,乃是义理上的必然,牟先生决不是意气地在争论孰为道统,也不是要打压朱子在儒学中的权威,反而是表扬了朱子另开一系统的伟大处。而且纵贯系统正需有横摄系统来作补充,两系统一纵一横, 一经一纬, 恰似西方之柏拉图传统与康德传统之异。 前者海德格(Heidegger)名之曰“本质伦理”,后者海德格名之曰“方向伦理”。拿儒家来说,则先秦旧义及宋明儒之大宗,孔孟、濂溪、横渠、明道、陆王等属于方向伦理。所依据的形而上的实体是超越的、动态的,“即存有即活动”从上而下直贯,吾人可以由反身而诚,自证其道德的本心自发自律定方向自作主宰以为吾人之性体(本心即性),故为自律道德。而伊川、朱子则属于本质伦理,其形上实体,虽是超越的,却是静态的,“只存有而不活动”,即此实体(性体)只是理,并无心之活动义,即非本心即性,心从性体上脱落下来,只成为后天的心气之灵之心,故人之实践之为道德的,是一种他律道德,盖理在心之外律之也。
故两系差异,是横摄系统与纵贯系统之异,是他律道德与处律道德之异,是本质伦理与方向伦理之异,由此可见伊川朱子所开出的确为一新的系统。在西方是先有本质伦理的出现,而柏拉图所代表的希腊传统又是西方的大宗,而在中国,本质伦理虽然后出现,但却建立起一与孔子传统相抗衡的朱子传统,而且此一新系统,重知识,近常情,与现代精神相契合,也更易为人所接受〔11〕。
(三)朱子与《大学》
牟先生说朱子惟一相应者为《大学》,此相应开始完全是不自觉的,因伊川、朱子之言道体、性体,简之为性理,原本亦源自中庸、易传、与孟子。只因对于“于穆不已”之体不能有相应之体悟,对于孟子所言之性体不能有相应之体悟,故只简化汰滤而为“只存有而不活动”之“存在之理”,然后顺“理”之存有义想下去,遂与原初之义相反,偏向重视下学,重视知识,重视渐教的“道问学”的系统。牟先生认为这都是由于伊川、朱子言道体性体之根本转向而来的结果〔12〕。
牟先生说《大学》并不是继承孔孟之生命智慧而说,而是从教育制度而说,乃是开端别起,虽为儒家教义之所以函摄,实际只是列举道德的纲领与范图,而其解释(所谓传)也只是现象学地平说,如朱子所谓“大学诸传有解经处,有只引经传赞扬处,其意只是提起一事,使人读著常惺惺地”。宋儒自伊川著重《大学》之致知格物,朱子继承之,并援引孟子以迁就《大学》,以《大学》为定本,而将孟子之本心拆为心性情三分。而心只讲成认知义,非是。表示朱子对孟子之无相应之理解〔13〕。
⑴认知心与道德心。牟先生说:朱子注《大学》欲将大学纳于孔孟之生命智慧中而一之,因此遂将“明德”就德行向里推进一步视作本有之心性,此义若依陆王之讲法,本心即性(此承孟子说)则“明德”及“明明德”之意义皆极单纯、确定而顺适。“明德”即是本心之明,既是昭灵不昧又是光明正大,此即吾人本有之自发、自律、自定方向之性体,亦即道德创生之实体。“明明德”即是复其本心明,此纯是自觉地作道德实践言,盖只是明体以起用也。依朱子“明德者,人之所得予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大学》注语)。牟先生说大抵朱子初见“明德”,欲安顿“明”字,但想到“虚灵不昧”,如是便不自觉地以“虚灵不昧”之心觉为综主词以说“明德”,而于性理则只以“具众理”说之。“具从理”与“应万事”俱系于此虚灵不昧之心觉,如是“明德”即是此心觉。顺此语法下去,若不知其系统之详,一直可以讲成是陆王之讲法。但朱子所想的心只是心知之明之认知的作用,其本身并非即是“心即理”之实体性的心。彼虽亦常言“心具万理”,但其所意谓之“具”,是认知的、管摄的、关联的具,并非是“心即理”之实体性的心之自发自律的具〔14〕。
故“虚灵不昧”是就心知说,而“明德”之实只在性理,而“虚灵不昧”之实,只在说“明明德”所以可能之内在的认知根据。(此内在即指人本有心知之明说)所以牟先生说依朱子说,统其在《大学》中关于明德所作之注语实当修改为‘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可以由虚灵不昧之知之明以认知地管摄之’之光明正大之性理之谓也。”,如此修改,不以“虚灵不昧”为首出主词,省得摇摆不定,而亦与朱子之思想一贯,若如原注语,则易令人误会为承孟子而来之陆王之讲〔15〕。
牟先生为了分辨朱子“认知心”与孟子所说“本心”及阳明“良知之心”的不同,进一步解释说:朱子所说“本心”非孟子所谓的“本心”,朱子讲心、性情三分,曰“心统性情”,心之统摄“性”,是主观地认知地统,心之统摄情,是客观地行为的(激发)统。因朱子所说只是实然的心气之心,心并不即是性,并不即是理,心只能发其认知之用,并不能表示其自身之自主自决之即是理,而作为客观存有之“存在之理”(性理)即在其外而为其认知之所对,此即分心为能所,而亦即阳明所谓“析心与理为二者也”。至于孟子所说“本心”,则并非朱子心、性、情三分之心,亦决非只是心知之明之认知作用的心。本心是实体性的,立体创造的本心,是即理即情之本心,情是以理说以心说,不是以气说,心是以“即活动即存有”之立体创造说,不以认知之明说,理即是此本心之自发自律自定方向之谓理,不是心知之明之所对。而王阳明(舆与孟子思想相应)也说良知之心昭灵不昧,但此良知能自知是非,是顺其“知”向里看,是单在说良知之自成决断,自定是非,自定方向之神用,故良知即是实体性本心,即是天理,即是明德。但朱子不是如此,朱子是顺“人心至灵”之“知”向外看,单注意其认知作用,而以理为其所对,是则心具众理,是认知地具,而不是其本身即是理,故亦不能即以此“人之至灵”为明德也。“人心至灵”之心知之明只能认知地带出明德来,认知地提挈明德而令其显现,而其本身非即明德,此则必须注意者,否则必讲成陆王而不自知〔16〕。
⑵泛认知主义的格物论。牟先生说朱子论格物对虚层义的格物与实层义的格物不加分别,是一种泛认知主义。因朱子的心是认知心,故曰知是人心之灵,心之灵本有认知事物之理之明的,只为物欲所蔽,其明便发不出,故须要格物以致知。致知是藉格物一方面推致,扩大并恢复其心知之明;一方面推致其穷究事物之理之认知作用令“到尽处”,即“知得到”,知得彻底,知得到家,此之谓“知至”。格物愈多愈至,其心知之明愈明愈尽。及到“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达至知“太极”之境,则“吾心之大用无不明矣”。此即朱子所谓格物的实义(“基础意义”是就事事物物之存在之然而究其超越的所以然〔17〕。
但依朱子之说“格物者,如言性,则当推其如何谓之性;如言心,则当推其如何谓之心。只此,便是格物。”(《朱子语类》卷十五。〈大学二,经下〉),朱子认为心知之明是属于“气之灵”,亦可以视为一“存在之然”,故亦可以究知其所以然之理。但“性不是一存在之然,吾人并不能就“性”再推究其所以然之理。因“性”是存在,而无所谓存在不存在,然则视“性”亦为一物,此物与“存在之然”之为物并不同此物并无实义与“道之为物”之物同。因此只有文法上的意义,并无实义。性之为物既如此,则“推其如何谓之性”亦是格物,此格物亦无实义。“推其如何谓之性”,如说“性只是理”,或性只是“存在之然之所以然之理”,此种推究实不是格物,只是一个名称之定义;而且只是一种“名目式的定义”,重言式的定义。于此说格物,此只是格物的虚层义,只是对于所知之理自身之反省〔18〕。
牟先生批评朱子于此虚实之异不加分别,一律视为格物,未见其当;而且把仁体、性体,俱视为存在之然之所以然,而由格物之就“存在之然”以推证而平置之,此已是泛认知主义矣。然此犹是格物之实义,犹是就存在之然说,而今复进而说“推究如何谓之性”,亦是格物,混虚实而为一,此则真成泛滥之泛认知主义矣。故其缺失是既未能成就知识,又减弱了道德的力量。原因是:朱子说格物主要目的是在就存在之然以推之证其超越的所以然,至于存在之然自身之曲折,则是由“即物穷理”拖带出来,非其目的所在,故未能成就积极的知识。又因为朱子将一切皆视为格物工夫之所对,纳于“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之格范下,如孟子所讲恻隐羞恶等之心即是吾人道德本心,亦即是吾人之内在道德性之性;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即是仁义礼智,此中并无然(情)与所以然(性)之别。所谓求放心,所谓操存,所谓存心养性,尽心知性,并不是即物而穷其理的格物问题。但朱子也一律平置而为存在之然(物)以究其所以然,此显然非孟子本义。盖如此,即将孟子所说之本心拆散而不见,推出去平置而为然与所以然,只剩下心知之明与在物之理间之摄取关系,而真正的道德主体即泯失。先秦儒家,除孟子讲的心性,还有孔子言仁,《中庸》言慎独、致中和、言诚体,以及《易传》的穷神知化,凡此似皆非“即物而穷其理”之格物问题,而朱子必欲以泛认知之格物论处理之,故终不能相应也〔19〕。
⑶哲学的与科学的。朱子讲“格物致知”,讲“即物穷理”,是否即能成就知识成就科学呢?牟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朱子的目标却不在此,故只是成为穷性理的道德学家而非科学家。牟先生分析说:朱子之“穷在物之理”,就其所穷者是存在之理言,虽是以认知方式穷,亦无积极的知识意义。因为光只是“存在之然”之所以然之理,即必然而不可移,当然而不容己之理,是空无内容者,不管节节推上去,是那一节之存在之理,皆是如此。节节推上去,每节所穷至之存在之理,其实皆是同质的,并不构成理之异质、不同类。只是因“存在之然”之不同而有不同的名字,因而有受局限的“存在之理”而已。此如动之理之对动,静之理对静,爱之理(仁)之对爱,宜之理(义)之对宜。……等等,实皆只是局限的存在之理,而其为存在之理则一也。此处即函理之一相与多相之确切意义之透示。即表里精粗无不到,穷至极复杂、极微细,一毛孔、一毫端,而就其为“存在之然”言,其所以然之理亦仍是如此。所以然之理至单纯、至齐一,并无曲折之内容,亦不表象存在之然之曲折。是以光知此存在之理,并无积极的知识之意义。积极知识是在“存在之然”之曲折之自身处,并不在此存在之理处〔20〕。
而朱子之“穷在物之理”,其目标是在穷其存在之理,并不是穷其存在之然之曲折本身。穷存在之理是哲学的,穷存在之然之曲折本身是科学的。科学式的积极知识或特殊的专门知识是在其穷存在之理时接触物,因而成其为泛观博览,所谓道问学,通过此泛观博览,道问学之过程,而即在此过程中拖带出来的。而朱子的重点与目标固不在此。
朱子之穷在物之理,对此分别未能自觉,或至少未能自觉地清楚地予以分别规定(此或即以前所谓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之别),遂使人有混杂之感。实则原则上可以分开,即依朱子之思路与目标亦可以分得开。惟其表示的词语不甚够,遂令近人有不清楚之感。因可以客观地从“然”与“所以然”之两层上(只要知道“所以然”是超越的所以然。只是存在之理即可)予以原则性的分别:单穷超越的所以然这存在之理者为哲学的、德性的,无积极知识的意义;单穷存在之然之曲折本身者为科学式的、见闻的、有积极知识意义的。前者是朱子之本行,后者则是其通过道问学之过程而拖带出的。朱子对此后者兴趣甚浓,依其理气之分之清楚割截也实有可以引发此种知识之依据。此如《朱子语类》卷第二,理气下,论天地下,卷第三论鬼神,此两卷所论者皆是就存在之然(气本身之曲折)而说,故其所穷知者虽未进至科学阶段,然亦实是科学式的积极知识,因其基本观点是在就气本身曲折说,根本上是物理的故也,此即引发此种知识依据。朱子大弟子蔡季通尤见此种知识之兴趣,而且甚见此方面的才智,虽是前科学的、老式的,然实是科学家之类也。故可另换一词语表示此种分别;就气上建立者是积极的知识,是科学的;就理上建立者哲学的,德性的,无积极知识的意义,而朱子之目标在后者,故成性理家而非科学家也〔21〕。
(四)结论
以上根据牟先生对朱子的研究,并根据牟先生的语言,来解说他为何念念不忘孔孟传统,其心思可谓完全是正统派的朱子说他非儒家之正宗。因在根本思想上发生了歧出与转向,故判定他为“别子”为旁歧,并谓朱夫子的头脑不能讲《论语》,也不能讲《孟子》、《中庸》、《易传》,而只能讲《大学》。另外加上《荀子》,因为他的头脑是荀子的头脑,是实在论的头脑,他们都重视客观存有都讲本质伦理,都重道问学,重客观知识。但荀子在先秦并未取得正宗的地位,宋明儒也不喜欢他,朱子也不是从荀子那里继承;由于头脑相近,心态相近,终于开出了此一重智的传统,补足了重德传统之不足。但因为将知识问题与成德问题混杂一起讲,既于道德为不澈,不能显道德之本体,复于知识不得解放也不能显知识之本性,而科学的积极知识也并未建立起来。但其具有现代性的价值,却是不容忽视的〔22〕。
牟先生煞费苦心,花了十年工夫去研究北宋四家舆朱子,一方面固然是他所说“求是”之心之不容己,逼迫他非为此不可,弄不明白,不得一谛解,实无法下手讲此期之学术。但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对儒家的使命感。他在《从儒家的当前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讲稿中即强调说:“中国从清末民初即要求现代化,而有人以为传统儒家的学问对现代化是个绊脚石。因此,似乎一讲现代化,就得反传统文化,就得打倒孔家店。事实上,儒家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我们说儒家这个学问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积极地负起它的责任,即是表明从儒家内部的生命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所以儒家的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23〕。他认为,儒家当前的使命就是“开新外王”,要求民主政治乃是新外王的第一义;另一方面就是科学,而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亦即新外王的材料、内容。科学的精神即是事功的精神。科学乃是与事功精神相应的理性主义之表现,所以科学可以与儒家的理性主义相配合,而科学也正是儒家的内在目的所要求者,牟先生并比喻说儒家讲良知、讲道德,乃重在存心动机之善,然有一好的动机却是无知识,则此道德上好的动机也无法表达出来,所以良知、道德的动机在本质上即要求知识作为传统的一种工具〔24〕。是以每一致良知行为自身有一双重性:一是天心天理所决定断制之行为系统,一是天心自己决定坎陷其自己所转化之了别心所成知识系统。此两者在每一致良知之行为中是凝一的。经过良知的坎陷转化,则逻辑、数学、纯几何,乃至一切知识方法、知识条件也都得到安顿〔25〕。
当然有关阳明“良知的坎陷”说,与朱子乃“别子”为宗之判定,早已在学术界引起过争论,但牟先生此一提法,证明他是积极在为儒家的新外王找寻有效的理论基础。因为无论科学也好,民主政治也好,必须在中国文化中去寻根。有与其相近的头脑心理,才能开出这方面的学问内容,否则永远是从外面移植。或中体西用,或西体中用,而不能建立起自己的体用,这个文化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注释:
〔1〕:钱穆著《朱子新学案》册一页1。
〔2〕:陈荣捷著《朱子新探索》(台湾:学生书局),页808。
〔3〕:牟宗三著《心体舆性体》(台北:正中书局)册一, 页55。
〔4〕:陈荣捷著《朱学论集》页13、22。
〔5〕:朱子继承道统之争, 请参拙文〈朱熹在传统儒学中地位之批判与认定〉(《鹅湖月刊》15:9)。
〔6〕:《心体与性体》册一,页55。 牟先生说:什么叫“别子”呢?这是根据礼记而来的。譬如说有弟兄两人,老大是谪系,是正宗,继承其父;老二不在本国,迁到他处,另开一宗,而成另一系,这就叫做“别子为宗”。(见《中国哲学十九讲》415页)。
〔7〕〔8〕〔9〕〔10〕〔11〕〔12〕:仝上, 页56;58;40;41;42、59;86、87。
〔13〕〔14〕〔15〕〔16〕〔17〕〔18〕〔19〕〔20〕〔21〕:《心体与性体》册三,页369、369、370、374、378、384、385、 385 、386、386、391、393、365、365、366。
〔22〕:牟宗三著《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 页401。
〔23〕〔24〕:牟宗三著《时代与感受》(鹅湖出版社),页300;313。
〔25〕:牟宗三著《从陆象山到刘蕺山》,页254、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