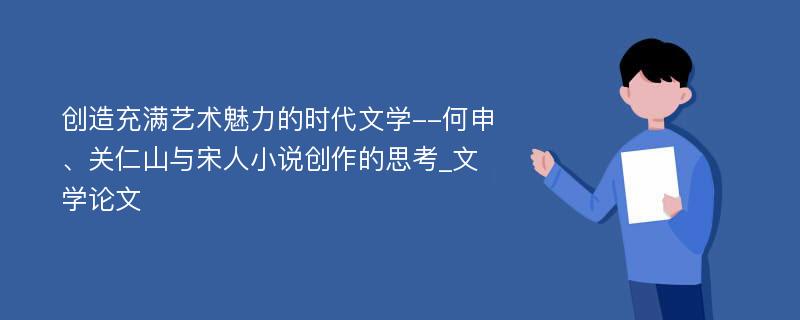
创造富有艺术魅力的时代文学——何申、关仁山、谈歌小说创作给我们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给我们论文,魅力论文,艺术论文,时代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时期文学走过了将近18个年头,及至本世纪末期,首都文坛上召开了以河北作家群体形式出现的小说研讨会,我想这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可能它不仅仅是文坛圈子里一般意义上的学术活动,从深层的动因来看,也可以说是反映了时代对文学的某种选择,人民群众对文学的某种期待。是否可以这样说,何申、关仁山、谈歌的小说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时代文学的品位呢?
文学,特别是现实主义文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都存在着一个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血脉关系问题。这种血脉关联正是文学的精魂之所在。新时期文学在各种思潮相互撞击、叠涌交织的曲折发展态势中,其所引发的正反两种效应,都再次证明了这个绝对不容忽视的道理。文学,自有其本身的价值法则,它可以而且必须要有自己的种种探索和多元追求,作家进入创作状态后可以是充分个性化乃至个人化的,但不管怎样的探索和追求,不管是怎样的个性化个人化,都绝对不可冷漠了时代,不可拒绝人民群众的需求。冷漠的结果最终将会受到互动法则的惩罚,并将导致文学生命力的枯萎。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将以什么样的姿态和质地面对时代,面对人民群众,这个基本走向问题不能不被重新提了出来。近一个时期,河北三位中青年作家何申、谈歌、关仁山的小说被各方看重,特别是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我想正是与这根神经有直接关系的。河北三作家共同以他们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品格,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时代气息,以及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深深感染了读者。广大读者从何申《年前年后》等乡镇干部系列中,从关仁山“雪莲湾风情”系列中,从谈歌的《大厂》、《年底》表现城市企业职工生存命运的系列中,看到了他们自己的身影,闻到了他们最熟悉最亲切的生命气息,听到了令他们怦然心动的声音,小说走进了他们,他们又走进了小说,这种文学与读者息息相通的情景,不是纯粹出于观赏,而是出于命运的共鸣共振性获得读者的喜爱,已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比较淡薄了。很显然,正是这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共同体现出来的积极入世的现实主义品格,构成了他们创作上最招人眼的一个亮点,反映了深受广大读者称赞的发展趋向,这才是我们今天举办这次研讨会的契机和基础。
然而,“入世”又有博大与狭隘,高尚与卑琐,深刻与肤浅,丰富与单调,创新与守旧之分。文学创作从较高的审美层次上感应时代的脉膊,写出现实主义力作并非易事,此中有许多道理值得仔细探讨。就河北作家而言,不是指单个人而是从群体来看,新时期以来就走过了一段相当艰难的路程,经过坚持不懈的上下求索,才在今天的一些中青年作家身上取得了相应的成果。回顾过去,我国新时期文学的灿烂成就中,先后有所谓湘军、晋军、鲁军、楚军、陕军的纷纷崛起,各自以其独特的光辉为推动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引人瞩目的贡献。相对来说,在全国能产生广泛影响且成梯队阵容的冀军却迟迟未见形成,以致我们在面对自己的现状时,不得不把八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一个阶段称为“低谷”状态。即使在今天,我们业已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一定影响的作家,也还应该有勇气承认,我们确实曾经落伍时,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的弱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正是聪明而能有所作为的表现。河北当代文学创作,本来有着老一辈作家梁斌、孙犁、徐光耀等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一直是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命运血肉相关的。但历史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后进者的乏力,很长一段时间未能成功地找到优良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新的时代精神的契合点,没有从内容到艺术表现形式上对老的传统有所拓展和创新。而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对于文学创作来讲,绝对是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须臾或缺的。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好多小说都呈现出老面目、老状态、老的叙述套路、老的语言格调的陈旧平庸境况,习惯的思维定势曾经成为我们的桎梏,使我们的作品与广大读者新的审美需求拉开了相当长一段距离,时代大大向前发展了,而我们未能艺术地向读者提供新的生活内容。另一方面,极少数作者出于浮躁和投机心理,又良莠不分地盲目追逐新潮泛起的泡沫制作出一些不伦不类的膺品,更倒了读者的胃口。几此种种是想说明,缺乏哲学思想和艺术修养的充分的准备,特别是缺乏独到的识见,使他们身在生活中却难以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发现,不能以审美的眼光把握生活,加之小说语言的陈旧,叙述手段的单一老套,这几乎是相当一大部分河北作家的通病,使他们难有振耳发聩、夺人眼目的创新之作。深入探讨此中人文背景和历史文化上的原因,并非本文的任务,回顾这种情况只是为了突显何申、关仁山、谈歌具备了怎样新的特质,才使得他们的创作在某些方面改变了河北小说往日的面目而取得了目前卓越的成就。
首先,我以为何、关、谈三位作家都能以开放性的眼光将笔下的人物放在新时期的种种机遇与挑战面前,在他们的精神状态自由放逐的态势下,充分展示其真实而隐秘的心灵世界,紧紧抓住人生价值观念、价值取向激烈碰撞这个枢纽,以非常精彩的笔墨为我们提供了独属于这个时代的新的矛盾冲突,新的时代语言,新的故事中所演绎出来的新的人物。众所周知,新时期是以思想解放为其根本的时代特征的,国人精神状态的主动性、放松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互相挤压制约性,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姿多彩、鲜明强烈过。本来,这为作家的艺术表现提供了空前未有、无限丰富的良好客观条件,就看你的感觉与发现能力了。何、关、谈三作家所以能得到群众的认可,就在于他们以自己的艺术笔触将广大读者带进新的时代生活的二次体验中。在这方面,谈歌的《大厂》、《大忙年》都有令人叫绝,十分出色的表现。特别是《大忙年》,简直称得上一幅极具概括力的时代风俗画。这部中篇小说以主人公陈浩正月初一携妻带子回爸家及岳母家、单位领导和亲朋好友家一连串的拜年活动为轴线,有声有色地展开了一幕幕苦辣酸甜的故事情节,以此为巧妙的聚焦点,将当今社会建筑在利害关系基础上的亲情与种种复杂莫测的人际关系,通过高度浓缩的手法写了个淋漓尽致,毕现无遗。年轻的知识分子陈浩努力以靠本事吃饭、清正做人的处世原则闯荡社会,却遭到物欲化十足的岳母家及“一担挑”的白眼和冷遇,其热心助人的情肠也受到昔日为同学,今日为暴发户的嘲弄与人格上的颠覆。金钱与权利的占有急剧地改变、乃至打破了往日的人际关系,即使在亲情之间这个魔鬼也无所不在地肆虐扬威,荡涤着一切温情脉脉的传统。《大忙年》把素日里形成的人际关系放在表面上充满喜庆气氛的春节拜年活动中,更集中、更深刻、也更剧烈地搅动着人的情肠,把种种价值取向的磨擦冲突充分展现出来,让人们感受和思考,去做出自己的评判与选择。《大忙年》的精彩描写使人不禁油然想起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个入骨三分的论断。《大忙年》的构思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我疑心谈歌是受了传统故事的触发,才找到了这样一个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姑爷几个登门给老丈人拜年来展示世态民情的一系列民间故事,提供了绝妙的窥察人心灵的窗口和契机,谈歌巧妙地借用了这种形式并加以改造与拓展,成为表现社会转型期人际关系变动着的一个大舞台,让读者感应到时代的神经。这部小说将生活流与意识流浑然一体结合起来,并不着意去揭露什么,只是在自然本真的状态下提供大量密集的生活信息,避免了说教气,让运动中的现实自身去显示生活的内涵,小说写得很聪明,应该说,比五十年代的一批作家在艺术表现手法上要高明些。此中,我以为作家能以开放的眼光观察生活、把握时代是非常重要的。何申为中国文学增添的乡镇干部系列艺术画廊,就是这种开放心态、开放眼光的发现。是否可以这样说,从打何申的小说开始,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党政干部才不那样拿腔捏调、假里假气、故做姿态?中国的干部队伍在政治上是个非常敏感的特殊阶层,他们要面对党和国家的政策,面对事业和分管的具体工作,面对集体和群众的利益,无可讳言,也同时面对自己职位的升迁荣辱,尤其是直接领导对自己的评价更是经常让他们牵肠挂肚的事情,他们处于种种利害关系夹击的官场上,既要冠冕堂皇地做好工作在政治上不断地赢分以增强晋升资本,又要机警地躲避各种暗算、排挤以及可能有形无形对自己的伤害。一事当前,对“利害”关系的层层审度对他们尤为重要。可以说,“为人民服务”是通过处理好复杂的人际关系后最终才得以实现的。每一个乡镇干部都有自己处理各种微妙关系的一套,那里面包藏着“人情世故”的百科全书。何申虽还不能说把这套活的百科全书全部吃透了,起码是一页一页地打开了。因此,他写给我们的不是书本中的干部形象,而是实际生活中活生生有血有肉、有长有短、被七情六欲燃烧着的干部形象。他们每抓一项工作,既有表面上严肃的一套,也有和方方面面打交道时胡扯蛋打哈哈的一套,既有桌面上工于心计、讲究韬略的一套,也有背地里委屈求全、迂回退让、伺机再起的一套,既有真心实意干好工作的一套,也有深藏私欲、步步为营求得个人发展的一套。乡镇干部们鼻子和脑瓜儿都灵得很,各有自己的一套人生“小九九”,那“小九九”让人可爱可笑可怜有时也可憎。何申从长期的交往中把他们的“心脉”摸准了,吃透了,既没有故意回避他们身上的什么,也没有故意拔高什么,就在价值观念的左右驱使中,活灵活现地写出了这很有思想很有本事很有手段也很有特点的一群。特别是北方乡镇干部那非常幽默、非常俏皮、非常朴实又非常生动极富生活哲理的语言,简直令人捧腹令人叫绝。他们在群众中笑着骂着亲热着挖苦着抬举着奚落着就在与乡里乡亲的无拘无束中把原本是很棘手的工作干了,这是一本正经的知识分子一辈子也难以学到的本事。“人情”就是他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乡镇干部都是些地域生活中的能人。在他们那一亩三分地儿上,称得上是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难怪《年前年后》让我们满腹经纶的高手王蒙先生也读得那样开心,那样过瘾,连用了几个“极”予以称道。可见何申对于新时期乡镇干部丰富而复杂的心态以及他们思想感情的表达方式取得了何等得心应手的把握程度。
其次,几位作家都有较为深厚的生活根基和文化根基,在他们所熟悉的一方沃土上形成了让灵魂飞扬的精神家园,这是他们坚持深化现实主义创作的生命之本。作家们各有自己的追求和兴奋点。有的热中于文体意识的拓展和创新,有的在叙事语言上不断弄出些新的花样,有的完全面向作家自身的内心体验、内心感怀,迷恋于所谓“个人化”的写作。应该说,他们各有所获,从不同的侧面对整体的文学事业都献出了各自的果实,致于合不合读者的胃口,只有靠实践过程本身来检验了。哪怕是并不成功的极为短命的探索和试验,作为新时期整个的文学发展过程也是不可或缺的,就算是化为腐植土吧,也算是对文学机能的另一种营养。我不太同意某些批评家在时过境迁之后,站在今天较为成熟的认识高度对过去曾出现过某些偏颇的实验性创作主张过分苛责,脱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与过程的阶段性,那种居高临下的训令性批评对于文学的健康发展是不可取的。一切都是在相比较中存在,在相比较相斗争中发展的。历史会做出过滤和选择。新时期的文学创作经过种种曲折现在已经表明,文学要加强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血脉关联,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然是最广阔、最具生命力的通道。而现实主义的写作,要求作家们应该具有较雄厚的生活根基、文化根基,这已经为多少优秀的创作成果所反复证实。直白地讲,这也算是文学创作上的一种国情吧。十分明显,何申写不尽的承德山区的乡镇干部,关仁山的“雪莲湾风情”系列,谈歌的国营企业和城镇职工题材,都是他们多年来耳濡目染、呼吸与共的最熟悉最有感情的生活,里面维系着他们的生活之根、生命之根。如果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熟悉生活,还难以从历史纵深的宏大背景下去把握好笔下人物性格中更为隐秘更为凝重的东西,难有精神上的超越。而何申等三位作家有意识地加强了自身的文化涵养,从历史文化的动因上加强了对生活的观照,这在他们作品的面貌上已经有所反映。如关仁山对“渤海文化”意蕴的理解:“我觉得没有哪一本书能像大海这样丰富。海是一个格外热情的老人,交往久了,他用另一种原色还原你,于是,我们便有了穿透海水的海眼,看啥都是蓝色的,一个辽阔而奇妙的蓝色世界,甚至连自己的脉管里殷红的血液也变成了蓝色。蓝色世界给我多种多样的文学启示。下海,即使是苦难,对我也有着妙不可言的诱惑。海即人、人即海,每当我提笔时,总有一种错觉。海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那蹲在海滩上吸烟的渔佬即是一个写不尽猜不透的海。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就是一张揉皱的海图。我想,人与海的沟通,最终将发展为人类自身对生命意义及生存方式的诘问和探寻。”对人与自然关系如此地把握和观照,这样的主体意识,显然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家当时难以具备的,都是熟悉渔民生活,层次与深度显然大不相同。唯其如此,关仁山的雪莲湾系列才显示出浓郁的文化底蕴,对人类生存史的概括显得更为厚重而透彻,像老扁、老满、黄老爷子、单五爷等人物形象都有历史的长河流经他们的生命中,其间包含的生活信息量与历史的暗示当然要大得多,作品的韵味也醇得多。每一个人物身上都“存在着两种敌对的原则之间无时无刻不存在的对立和斗争”(雨果语)。这种着重表现人物性格内在因素的对立冲突,作为小说艺术来讲,当然较之过去单纯着眼于人物的外部关系描写要深刻得多,也丰富得多了,大大加强了形象的立体感。
在这里,我想强调一句,在谈歌的二百来万字的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及若干笔记体小说中,写得最简洁、最机智、最深刻、最耐人寻味的还要算是若干以“绝”字命题的笔记小说。那在各种特殊人生境况下对于“绝处逢生”精神现象的抒写,极具越轨的笔致和震撼心灵的哲学蕴涵,表现了相当高的文化品位。
第三,我想从探讨问题的角度提出一点很不成熟的见解,即文学对时代感应的深切程度,不仅取决于作家艺术手段的丰富与娴熟,而且更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修炼。特别是表现在作家对时代生活的整体把握上,哲学思辨能力尤显重要。由于自己的工作特点,我在阅读一些作家的初稿和业已出版的作品时,常常不无遗憾地感到,许多作家整体把握生活的能力暴露出不少局限性。谈歌在一部表现革命历史题材内容的中篇小说《山毛榉》的“作者题记”里有这样一段话:“我渴望真实,但又害怕真实,于是我便痛苦。在万里逶迤的长城下,在波涛滚滚的大江边,都曾留下我伤痕累累的思索。”应该说,这不仅是谈歌一个人的苦恼,它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许多作家都曾面临既“渴望真实”而又“害怕真实”的矛盾心理。有的成功地超越了这种矛盾而写出了警世之作,有的则在作品中表现出这种困惑与无奈。诚如谢冕先生所言:“这个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百年来的痛苦与焦灼的历史记忆,作为遗产,梦魔般地使他们无法逃避和摆脱,他们不得不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宣战”。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实在是太沉重、太复杂、太变幻莫测而令人眼花缭乱了,作为作家单是有渴求真实的勇气还是远远不够的,一旦客观真实以其本来面目无情地展现在你面前时,你将作出怎样的梳理呢?一旦精神准备不足极可能又会陷入“害怕真实”的惶惑境地而茫然失措。这不仅是创作的课题,我们的编辑与文艺理论家又何尝不经常面临这既老又新的问题呢?新时期以来,由于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相对宽松的创作环境,使得作家们在展现历史的真实图景上取得了相当大的自由度,但与此同时,剖解历史与把握历史向度的能力却也严峻地考验着作家们。我以为,谈歌在《天下荒年》中对一些精神现象的思考与追问是十分可贵的,而暗示给读者的评断却不免过于简单,带有作家自身情绪驱使的片面性与偏激性。《天下荒年》贯注了作家对共和国那段饥苦年月极为动情的理性思考。作家本意是运用历史与现实相贯通相对比的手法,弘扬在国难当头饥饿与死亡威胁着每个人生命安全的严峻时刻,那种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气节与情怀。其中确有些令人荡气回肠的章节。特别是由于作家敢于面对令人眼晕的历史真实,作品的前半部分写得十分精彩,无论是崇高或者愚昧,把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某方面的精神状态表现得维妙维肖,颇有些当时的历史气度,虽然他是以对另一方面的删削与舍弃为代价的,但生活本身客观内涵的丰富性已经颇具张力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然而,当作家试图从那种历史现象中引发出普遍的结论,将那段特殊年月所曾有过的精神原则过分神圣化、极端化,持完全礼赞的态度,特别是与新时期社会大变动过程中所出现的物欲横流道德沦失现象做出机械对比时,从而发出了在精神领域中今不如昔的慨叹,这就出现了某种偏颇。众所周知,三年困难时期,我国社会生活中确实存在着如《天下荒年》所描绘的那样哪怕饿殍累累饥民们也不曾抢劫粮库的动人情景。但那“动人”的背后,也并非完全出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自我道德约束,更有着无产阶段专政强大控制力量的深层背景。脱离开一定的历史条件,孤立地考察道德现象是不可取的。建国之后,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曾有那个时期的道德文明问题,只不过表现的侧面与价值内涵不同罢了。把当年广大群众消极被动地忍受饥饿过分地理想化,作为新时期的精神大旗予以呼唤张扬,真的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么?何况,造成《天下荒年》的历史动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就有各级领导干部头脑发热瞎指挥搞浮夸风的因素,让人民群众心甘情愿地以生命为代价承受这种后果就一定是完全合乎道德的吗?艺术表现的分寸感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过与不及都会带来损伤。物质的问题最终还是要靠物质来解决,精神不能代替一切。弘扬道德文明是非常必要的,但作家亮起的旗帜必须是真正能在社会实践中引导人们前进的号角,不能有乌托邦色彩。读罢《天下荒年》我不无遗憾地想,如果作家只客观真实地叙写当年的历史图景,本身的内涵就极为丰富,读者自会做出多种思考,而实际上作品的后半部分却过多地将历史与现在的两种精神现象作对比,作者直抒胸臆地予以评判,反倒限制了作品的张力,偏偏作者对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又缺乏成熟的思索,硬塞给读者的结论是难以经受住历史的检验的。这使我再次联想到,多年来在我们的思想领域中存在着一种远比“左”和“右”为害更烈、更难以被人觉察的过于简单、过于片面、好走极端的思想方法,往往由此而改变了事物的本来面目,导致一系列的行为失误。很可惜,包括我们的一些作家在内,今天仍未能彻底走出极端化认识怪圈的阴影。指出这一点是想说明,本世纪的“历史难题和这个社会百年来的痛苦与焦灼的历史记忆”对于中青年作家的思想造诣是个异常严峻的挑战。建设优秀的时代文学离不开作家要有较为成熟的思想这个必备条件。我们千万不可因思想上的乏力给读者制造虚幻的图景,对种种社会现象不能降低到一般街谈巷议的水准。
新的历史条件给我们提供了表现真实的相当宽松的自由度,而能否恰当地运用好这个“自由度”则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修养。十年前,当时还非常年轻的铁凝就讲过一句十分精彩的话:“作家要特别重视营养自己的心灵”。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宽泛而深刻的,假如我们的作家既重视坚持不懈地深入生活,开掘生活,始终保持与时代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又具有博大丰富的心灵世界,具备足够的能力去把握人生,把握世界,我们必将会创造出深刻反映时代变革的优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