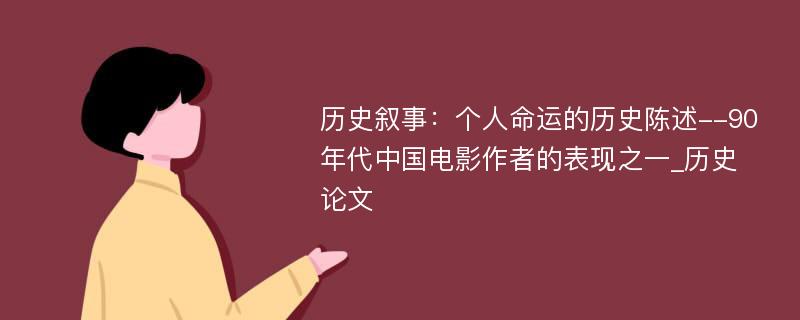
历史叙事:个人命运的历史陈述——90年代中国电影的作者表述之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中国电影论文,命运论文,年代论文,作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一词在早期的用法里,是一种事件的叙事记录,即记述想象的事件或记述被认定为真实的事件。因此,历史与叙事之间有重要的关系,或者说历史就是用话语加以表述的各种“文本”。美国文学理论家蒙特洛斯说文本与历史之间是“文史互相交错”的,包括“文本的历史性”和“历史的文本性”,其中“文本的历史性”是指“个人体验的文学表达总是具有特殊的历史性,总是能表现出社会与物质之间的某种矛盾现象”。①这一概念同样适用于电影,也就是说电影也具有历史性,它指电影作者从个人体验出发进行的关于历史的电影叙事。
就20世纪90年代的电影文本而言,电影作者的历史叙事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在对个人命运的描述中表达其历史观念,其电影文本对历史的叙述正是基于对人的经历或命运的叙述而展开的。90年代中国电影创作群体中的一个主力是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极大成功的“第五代”导演们,个人命运与历史命运的深刻联系在8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创作中被普遍割裂,因而其历史叙事显得符号化、抽象化和空洞。进入90年代,“第五代”导演的反叛激情已经褪色,在继续批判历史的束缚力、肯定人的生命力的同时他们转为注重电影的叙事性,意识到故事和人物的重要性,因此他们不再用《黄土地》和《红高粱》中黄土地、红高粱那类空洞、抽象的文化符号来图说中国历史,而是通过个人的命运来叙说历史,90年代的电影文本反映了这一时期“第五代”导演在历史叙事上的变化。
在这里,所谓历史叙事,是指作者通过描述历史境遇中个人的种种命运来言说其历史观,批判历史对生命力的束缚,90年代的电影文本中凡以历史为叙述对象、以个人命运阐说历史事件或历史变迁的“作者表述”皆被归于历史叙事。本文将以《大太监李莲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蓝风筝》等电影为个案,论述90年代中国电影中以“作者表述”的方式呈现出的三种历史叙事形态:禁锢人的历史、遮蔽人的历史和捉弄人的历史。
一 禁锢人的历史
90年代中国电影关于历史的书写多集中于晚清至文革,这个时间段落是中国经历从古老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国历史进程中风云波诡、充满变动的时代。在本节讨论的电影文本中,无论是处于不同社会身份的各色人物,还是拥有不同性别身份的男人或女人,个人均陷入历史的泥沼,在动荡、逼仄的历史场景中个人被历史禁锢,本章关于历史叙事的“作者表述”形态中最具有悲剧色彩的一类正是这类被历史禁锢的个人,他们包括《大太监李莲英》中的清官大总管李莲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陈府四姨太颂莲,种种暴力将这些人物禁锢在历史中,使人物无法听从自身的驱遣,人物命运的结局只有死亡或疯狂:李莲英成为清王朝的祭品,颂莲则被扼杀在森严的性别秩序中。
1、向一个朝代进献的祭品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覆灭也意味着中国历史一个场次的谢幕。田壮壮导演的影片《大太监李莲英》中描述的清朝末年的宫廷生活也仿似古老中国的舞台缩影,李莲英这个人物就是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毫无疑问,李莲英是一个悲剧性人物,从个人意义上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是多重的,从肉体的阉割到精神的压抑,无处不是对个人的抛离;但影片更着重的是将人物视作畸形而没落的王朝的缩影,从李莲英的悲剧命运来叙说这一历史时期的国家的悲剧命运。
《大太监李莲英》以李莲英为中心视点,以皇宫为主要影像空间,叙述了1873年至1909年清朝最后一段风雨飘摇的历史。这段历史在很多电影文本中都有过表述,大多是关于民族国家命运的书写,和以往不同的是这部影片在李莲英个人的苦痛中渗透了历史的厚重感。作为历史叙事的一个类型,李莲英被作者叙述为被历史禁锢的个人,李莲英身上承受的诸多暴力阉割以及人性的复杂反应和历史的变动密切相关,这种关于个人的书写具有历史叙事的寓言性,即从李莲英的悲剧命运映射这一时段民族和历史的变动。影片中,关于李莲英的“历史”书写可构成这样一个序列:被遗弃者→庇护者→祭品。
作者以阉割主题作为历史与个人的连接点,李莲英是慈禧太后专宠的太监,被阉割者这一身份意味着极度的残酷性,太监身份要付出的惨痛代价是身体的阉割,切割了作为男人生存的维系,也剥去了作为人存在的根基,身体阉割必然导致精神上的扭曲和变异。作者之所以选择李莲英这个人物来表述中国历史上某个时段的悲剧性,正是因为李莲英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是被抽离了正常人生轨道的非常态者,这个被禁锢、被扭曲的人物反映了历史本身的非常态。
太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特殊的群体,负载了太多历史赋予的、个人不堪承受的重负。按照拉康的观点,儿童在镜像阶段是与想象的秩序相对应,在俄底浦斯阶段则与象征的秩序相对应。太监们大多在成童期被父母送入宫廷,成童期始于五岁左右,此时儿童处于拉康所说的俄底浦斯阶段,在这个时期父亲是权威的根源,正是在这一时期太监脱离了常态的父子关系和温婉的家庭生活,失去“父”的秩序引导和限制的同时也失去了“父”的庇护,他们在经受了残酷的肉体阉割之后被扔进了冷酷森严的、等级分明的、禁锢个人欲望的宫廷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太监既要成为服侍被置于深宫之中的女性(另一种意义上的被阉割者)、等级低下的人,又要避免成为对皇帝造成性威胁的人,这是对个人的二次放逐,不但在社会等级上处于最低层,而且因丧失了性能力而被常态社会疏离,这给个人的命运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作者的叙述中,李莲英身上就存有这种深刻的自我放逐特性,他谨小慎微地周旋在皇室和朝臣之间,时时刻刻充满忧惧、缺乏安全感,李莲英以“这个地方不把咱当人”这句话总结了他在宫廷中的处境,他对这种处境既感到痛苦又无法摆脱。
在作者的历史叙事中,李莲英的被遗弃者身份映射着中华民族同样的被遗弃者身份。和李莲英一样,在清王朝面临西方列强进逼的危机时刻,整个民族又何尝不是遭“父”遗弃的“子”一代?自视为“华夏”中心的古老中国一贯以泱泱大国自居,而1793年乾隆皇帝接见英国公使事件标志着中国的“父”秩序遭遇颠覆的危机,这样一个有着盲目优越心理的民族陡然面临被殖民割地的危机,才惶然发现提供庇护的“父”早已不在,自己却被抛进一个陌生、危险、充满竞争的世界里,这和李莲英的遭际何其相似。影片中清王朝的权力操控者慈禧听到轰隆的炮声弃宫而逃,丢下皇宫和跪送的臣民,这一场景象征着走向末日的帝国和最高统治者已然丢弃了他的子民。失去“父”(尽管这个“父”本身并不称职)的倚靠的世界是充满忧虑和缺乏安全感的,和李莲英一样,整个民族也由此成为被遗弃者,成为被历史禁锢的对象。
作为被遗弃者,李莲英的情感放纵让观众体会到他内心深刻的绝望、不可逆转,影片展现了被禁锢的人内心的苦痛。李莲英与自我的抗争被作者着意刻画,描写被禁锢的个人的价值就在于这种个人的挣扎,通过个人的挣扎和无奈显出历史对于个人的强大的主宰力量。作者对李莲英被禁锢状态的描述,首先是表现其在非常态境遇下的人性欲望。太监被阉割的只是肉体,人性的欲望并没有伴随肉体的戕伤而湮灭。很难说被剥去性能力的人是否还存有性欲望,影片中李莲英娶亲的情节却无疑具有心理代偿作用。电影在常规叙事中多次打破线性时间的叙事、“非常规”地插入晚年李莲英的镜头,在这些片段里李莲英为慈禧陵寝守陵,他的身边有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作者有意设置的一个寓意符号。在这些片段里多次出现男孩的阳具,喻指李莲英对缺失的性器官的迷恋,阳具意象说明了李莲英被剥夺却渴望满足的欲望,这也是导演试图说明的人最根本的欲望,它的缺失是压在李莲英精神上最沉重的负担。作者对李莲英被禁锢状态的另一层表现就是对权力的欲望、对财富的欲望,这是上述人性欲望无法满足时向权力和财富转移的结果。影片中,李莲英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出巡北洋水师,后因接受贿赂被革职去顶。此外,影片中还叙述了李莲英处心积虑地安排侄女菊花接近光绪皇帝,并请求慈禧赐给菊花名号,这是李莲英对于权力和财富欲望的表现。无论是对性欲望的代偿,还是对性器官的迷恋,还是对权力和财富的索取,都可归因于由于“父”遗弃带来的安全感的匮乏,安全感的缺失使得李莲英更加纵情于对这种外在对象的索取。可是这些外在对象的获得并不能减少和平复他的心理苦痛,于是李莲英转而寻求能给他带来一定安全感的庇护者,也就是慈禧。
慈禧在文学、电影、戏剧等各种文本中通常都是背负了历史骂名的负面人物,在这部影片中也多处表现了她的阴狠、不可一世和心胸狭窄。可是在这部电影中,慈禧却让李莲英感激涕零、至死跟随。这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天然敌对好像无故就消失了,事实上等级敌对在这里被作者转换成一种情感力量——对李莲英来说,慈禧充当了拯救者和庇护者的身份,她取代了宗亲关系的部分功能在李莲英的生活中成为庇护者,充当了李莲英被割离的“父”的角色,而这是他极度渴求的。作者用几个段落表现了慈禧的庇护者身份:1885年,李莲英任钦差大臣,与醇亲王一同巡视北洋水师,因监军、干政、纳贿罪名被除去顶戴、革职待审。这体现了慈禧和光绪之间的政治矛盾,光绪是为了向慈禧示威而惩罚李莲英,慈禧为此与光绪交锋。随后,慈禧亲自看望李莲英,并为其四十岁生日赐点心、复职、赏银,李莲英号啕大哭。哭声中不乏委屈,但更多的是对慈禧的感激,对庇护者的感激。慈禧不但以李莲英的庇护者自居,也是以“大清”的庇护者自居。的确,慈禧不但是李莲英的庇护者,作为一个王朝的最高权力掌控者,她还充当了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庇护者的角色。但是,和李莲英的庇护者身份相比,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庇护者她是不合格的,她是一个不能提供庇护的庇护者,是一个遗弃者。影片结尾,因为庇护者的离去使被遗弃者无从依附,这是某种意义上再度地被遗弃,被遗弃者的命运又堕入不可知的深渊,因此慈禧死后李莲英主动选择充当祭品。
关于李莲英的死亡,作者给出的解释是被阉割者为庇护者殉葬,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见死亡意象与个人的苦痛、欲望和挣扎有直接关联,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影片描述了李莲英个人的悲剧命运。但是,从叙事结构、影像风格和阉割主题以及细节的分析来说,影片更试图描述慈禧、清王朝乃至中国历史一个阶段的完结,作者将李莲英视作历史大叙事的侧影和旁证,视作一个朝代覆灭的祭品。作者通过表述对个人的理解来阐释历史的意图,虽然最终落脚在历史的图说上,但对个人的关注贯穿了影片。个人和历史的关系在影片中从外在结构到内在主题纠结在一起,作者试图用个人体验来完成对历史的叙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本文对李莲英的定位是“小写的人”,李莲英的徒劳挣扎和最终的死亡结局说明他是历史叙事中“被禁锢的人”。
2、性别秩序中的疯女人
对于历史和个人问题的关注,张艺谋早期的电影如《红高粱》就已充分而明确地表现了以“对历史、文化、人生的感悟与寄意”为主的主体性,进入90年代后张艺谋意识到这一主体性对“人”的问题的忽略。从《菊豆》开始,张艺谋转向对“人及人的命运”这个基本哲学命题的关注,菊豆、秋菊等人物从根本上区别于“我奶奶”这个人物,她们不再只是某种民族精神的化身,更具有了“人”的特征。但是,关注“人”并不表示关注了“个人”,在张艺谋那里“人”仍然是具有“类”特征或者说单一特征的扁平人物,缺少真正的个人性,《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颂莲也是其中的一个,但这个人物在“类”的意义上,或者说表现女性问题上具有独特的价值,是作者从女性的角度阐说历史叙事中被禁锢的人。和男性相比,在中国传统电影中真正从女性的角度来彰显女性自我的历史叙事是不可见的,在历史的重重帷幕中女性总是被囚禁在性别秩序之中。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历史的禁锢中显影了一个“不可见”的女性,尽管这个女性有着“知识”赋予的桀骜不驯,但这并非是作者对女性性别身份“神话的建构”。这个关于女性抗争主题的影片始于一个有别于传统女性的新的女性身份——女大学生,但迥异于传统模式的是,这个“新”女性并未进入反秩序的行列,反而退缩至秩序森严的旧式庭院,最终被困锁在这个象喻性的囚笼中。于是,张艺谋的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成为一个成功的反第三、四代中国导演建立的“大叙事”的例证。作者没有重复女性“出走”以及“出走后又怎样”的“五四”以来的女性抗争主题,而是试图叙述:如果一个女性具备了“出走”的身份和权力,不出走又会怎样?正是设置了这样的问题,张艺谋给自己的作者表述拓展了空间;《大红灯笼高高挂》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从历史视角重新探讨女性问题的文本,并且引发我们对抹灭了性特征的个人和历史归属关系的思考,颂莲这个人物的意义也在于此。
故事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女性话语的一大主题是出走,娜拉这一经典女性人物似乎为女性的出走构筑了美好的图景,但是接下来必然有一个设问:女性出走后到底怎样呢?事实上,女性出走后的命运是极其复杂的,既有萧红式的极端渴望自立却又因各种原因无法自立的命运,也有丁玲式的投身革命却被革命洪流裹胁的命运。总之,她们各自的遭际证明女性出走的美好初衷并未获得满足。女性选择“出走”后虽然并非如预想中的坦途,充满坎坷,但是毕竟以获得相对的独立和自由作为回报,当然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出走的可能性。那么,如果选择另一条道路——不出走又怎样呢?颂莲的命运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影片有一个清晰的情节序列:序幕—冲突—规训—臣服/反抗—惩罚—疯狂,在这个情节序列包含了两个福科式的主题:规训与惩罚、反抗与疯癫。
颂莲“闯”入陈府的情节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登场,她制造了一系列的冲突:和迎亲队伍“擦肩而过”、和丫环雁儿的冲突、新婚第二天拜见几位太太表现出的颇不情愿,这和一个本该低眉顺眼的姨太太形象大相径庭。究其原因,是预设的身份使然,影片将颂莲设置成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相对独立性的“知识女性”,但这个身份陡然被置换成依附他人、毫无独立性可言的“姨太太”,她制造的冲突就是可理解的了。只是人物本身并未意识到,随着身份的置换,身份所赋予的独立人格、自由空间也同时被剥离了,追求背离秩序的个人自由是等级森严的“家规”不容许的,因此规训不可避免。和原著不同的是,影片通过仪式化的影像来表现规训这一主题,作者用仪式来说明深宅大院对女性的禁锢。影片的规训仪式——点灯和捶脚的寓意十分明显,高高挂起的灯笼悬置在院墙上,红色的视觉意义在于警示规矩不可逾越,仪式化本身也意味着权力的不可知和神秘性。福科在论述规训的手段时说:“检查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技术结合起来。它是一种追求规范化的目光,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个人。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实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②如果把点灯看作“规范”的仪式的话,它就是一个类似于检查的规训手段,它的作用正是用于制造个人的“能见度”,个人成为规训的对象。
在影片中规训的首先是肉体。正如福科所说,肉体是驯顺的,可以被驾驭、使用、改造和改善。规训具有强制性和矫正性,新婚之夜通过点灯仪式权力各方的身份指认在影片中已尘埃落定。接下来的段落是进一步强化规训的过程。新婚第二天,大太太训话、管家陈百顺教规矩,颂莲即便是不情愿也必须接受这一强制性的规训手段。权力指向最明确或者说强制性最明显的是傍晚时分各院太太等候宣布点灯的场景,四个女性站在院门口,被迫列入站立序列的颂莲正式加入争夺一个男人的战场,执掌生杀大权的统治者则用灯笼这一意象来统领这个序列,性别秩序由此完成了规训的历程,女性成为驯顺的肉体。在这个段落里,影片还暗示了规训之下个人为何臣服的一个理由,在获得性权力的同时,点灯的女人也获得了点菜的权力,在众人之中取得的某种具有象征意味的优先性满足了颂莲被激活的权力欲,只是这样的优先性必须在规则的允许下才能获得满足。被激活和期待满足的欲望以及规训的强制性导致了女性的臣服,点灯和捶脚的仪式对颂莲来说从新奇、抗拒变成内在需求,最终无法摆脱。
规训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惩罚。在老爷和颂莲这对权力关系中,颂莲任何“偏离准则的不规范领域”的行为同样都受到制裁。第一次的惩罚显得有些漫不经心,老爷回来听说颂莲在三太太屋里打麻将,便埋怨颂莲不老实呆在屋里,转身去了二太太卓云那里。第二次的惩罚比较柔和,起因于颂莲从家里带来的笛子,老爷疑心笛子和某个男人有关,便命人烧了。第三次的惩罚则是具有毁灭性的、也极具象征性——封灯,福科曾说“一切规训系统的核心都有一个小型处罚机制”,在这个院落里封灯就是惩罚机制中比较严厉的一种。由于不满二太太和雁儿的暗中敌对,颂莲假装怀孕,获得了长期点灯、捶脚以及在房间吃饭的权力,随着假象的揭发被规训系统施以封灯的处罚。
影片中颂莲的结局是“疯”了,表面原因是颂莲在死人屋发现三太太被杀,真实的原因则是性别秩序的禁锢所致。颂莲刚发现死人屋的时候,院里所有的人都要她不要再说、再看,这是因为死人屋里掩藏着关于等级秩序的所有真相:死人屋是性别秩序的规训和惩罚的象征,在死人屋里死亡的人都是被囚禁在性别秩序中的女性——陈府历代的姨太太们。福科说:“禁闭将非理性隐匿起来,从而泄露了非理性的耻辱。”③秩序系统为了将“耻辱”隐匿起来,必须掩盖死人屋的真相,颂莲看清了真相却又不肯承认那不是真相,只有被认定是“疯”了。对权力制度而言,疯癫的发作是对安全的威胁,是对等级序列的篡越,于是老爷宣布颂莲“疯”了,使她真正成为“阁楼上的疯女人”。影片中,性别秩序用疯癫捆缚住了颂莲“自由的灵魂”,避免它威胁到“野兽的、吃人的世界”。
影片以仪式化的影像书写了一个关于女性的影像寓言,即中国历史的性别秩序传统对女性的禁锢。从表现性别秩序中的“人”的角度来说,影片的仪式化起到了抽离具体人物及其命运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颂莲属于表现“被禁锢的人”这一“类”特征的扁平人物,其命运的寓言性就是她的“类”特征——解释不出出走与毁灭、规训与惩罚、反抗与疯癫之间的因果关系。
二 遮蔽人的历史
通过人物的离奇命运讲述故事是90年代电影的一个特点,这类电影文本中的人物被编入历史进程,提供作者对历史的认知。本章关于历史叙事的“作者表述”形态中的另一个重要类型就是“遮蔽人的历史”,在对历史的描述中进行关于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探讨,具体说就是历史事件对个人的遮蔽。和上一种历史叙事类型相同,这一类型的历史叙事也是描述个人命运,但在这里作者赋予个人的命运的意义更加抽象,也就是说,个体意义上的“人”的命运和整体意义上的“人”的命运构成内在的关联性,历史叙事也因而更具有符号化的特性,这里以张艺谋导演的影片《活着》为例进行分析。
在作者的表述中,这种“仪式化的集体行为”通过影片中具体的个体对象,如《活着》中的福贵来表现,其目的不是他们难测的命运,而是作为整体、群体意义上的“人”的命运的探索。人物的坎坷经历远离人的日常生活,影片正是通过这种不无极端的叙事方式来进行一种集体表达,即个人的命运被纳入历史轨道,使历史对个人命运的主宰力量清晰可见,这样的人物无疑是历史叙述中被遮蔽的人。
影片《活着》以时间为线,对福贵一家的生活进行了历史性的描述,在历史的轨道里,因主观或客观原因富贵的亲人们一个个死去。在影片的叙述中,历史的命运和人的命运产生了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影片中,人们所看到的历史是由很多重要历史事件构成的,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炼钢铁运动、文化大革命等,而在这些历史事件中活动的个人往往被历史事件所遮蔽,更不必说像福贵这样“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了,叙事的焦点虽然始终对准福贵,但历史事件的遮蔽力也始终笼罩着人物的命运。
然而,对于个人来说“活着”是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只有在对他的“活着”发生影响时才变得有意义,这也是影片将历史事件同小人物的“活着/死亡”扭结在一起叙述的动机,即在历史事件的背景下展示出小人物的“活着/死亡”的状态,以让人浮出历史事件的方式,使观众看到被历史遮蔽了的人。因此,尽管死亡的命运不断降临在影片中的人物身上,作者表达的却是关于活着的思考,即探讨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影片作者试图表述的正是这种关于活着的“意义和意识”的内涵,即通过充斥着死亡事件的历史叙述来阐述“活着”的意义。
要说明作者表述的历史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必须将影片和原著小说进行比较。和余华的小说《活着》相比,影片的死亡叙述有所节制,叙述者的情感基本上是克制、平淡的。在小说里,除了福贵,福贵的亲人——爹娘、有庆、凤霞、家珍、二喜和馒头都相继死亡,这个不无极端的故事在福贵对牛的叙述过程中娓娓道来。小说中人物的死亡是偶然性、突发性、彻底性的,这样的死亡事件只能解释为偶然和宿命。小说通过福贵讲述了整个故事,其叙述带着舒缓的节奏,语调带着幽默和达观,心理带着平静的距离,这是克制而隔离的个人回忆。小说叙事的目的在于通过在人物身上发生的死亡事件来解说关于活着的人生哲理,突出一种人生境界——孤独与达观。它远离了社会、远离了历史,有意淡化时间特征,仅仅要叙说死亡和活着本身的问题。
电影的叙事目的则不同。张艺谋此前的作品也大多根据文学作品而改编,如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等,在这些影片中作者的“表述”往往并未脱离原小说的“表述”原意,只是在小说作者的“表述”中集中某个“点”来加以视觉化的放大,给人以深刻印象,《红高粱》就是典型例子。与之相比,影片《活着》的上述多层面的“大不相同”表明作为“作者”的张艺谋不再是在原小说的表述范围内进行重复性的表述,而是借苏童的故事“另有表述”。
和小说相比,电影蓄意突出的叙事时间反映了作者独特的历史观念。小说的时代特征在“个人”叙述中显得模糊,因而系列死亡事件仅仅是用来表现福贵个人的遭际和人生体悟。而影片的时间被严格区隔为“40年代”、“50年代”、“60年代”以及“以后……”,并以字幕形式予以清晰地标示,影片从春夏秋冬的自然时序变为历史时序,个人命运由此被作者纳入线性的历史时间中。影片中的历史时间是一种集体时间,对应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死亡时间于是成为和中国历史发生关联的连接点。每个年代都对应着死亡事件,40年代是福贵爹和福贵娘的死亡,50年代是儿子有庆的死亡,60年代是女儿凤霞的死亡,死亡事件是以累积的形式来表现历史和个人的联系,死亡不仅仅是福贵个人的事件,也表现了历史对个人的遮蔽力量,因此影片中长达几十年的叙事时间不是以福贵个人命运为线索的时间史,而是一个社会性的时间史。
除了叙事时间上的差异外,影片和小说在叙事视点上也存在差异。小说基本上以福贵的主观视角进行叙事,是限知叙事;影片则是以客观视角进行的全知叙事。90年代已趋分散的“第五代”导演似乎不约而同地回避着意念、造型、表意、抽象等“第五代”电影的共同特点,而归于平实,归于写实主义的叙事传统,但张艺谋对写实主义的“回归”并非是真正从写实主义的立场来进行叙事,而是从反“传统”的立场转向平实地叙事,用张艺谋的话说就是:“第五代的电影喜欢玩不说话,用电影语言替代,弄得好像很深刻似的。咱们这部片子不走这条路,该说话时就得说,只要说的是人话。我们的电影就是戏剧性电影,所以要保持戏剧性的张力。”④张艺谋的所谓“戏剧性的张力”是相对于“第五代”导演的“传统”,即注重造型、仪式化的电影形式而言的,作者已明确意识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电影的造型特性对叙事而言已显狭隘,因此急需从电影形式向电影内容上的叙事转化,而张艺谋追求的“戏剧性的张力”在《活着》中的表现就是改变夸张的语言形式转而侧重表述“意义”的叙事方式,因此《活着》的叙事恰恰是反戏剧性的。影片虽然具有明显的以时间为轴的线性结构,但影片的叙事没有根据线性结构来制造戏剧冲突,叙述基本上是克制的和反戏剧性的。
总之,从小说到电影,叙事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在情感上,由个人的平静回忆和内在体悟变为外在描述,并通过皮影、幽默等方法来外化了活着主题。在视点上,由主观地叙说历史变为客观地再现历史事实及人物经历。由此可见,电影《活着》以宽阔的历史时间来俯阅人生,和小说纯粹探讨活着的意义有所不同,电影的叙事是从历史的角度来展示的死亡和活着这一“人”的基本命题,因此作者叙述的是一段社会性的时间史,其间个人为历史所遮蔽。
作者通过死亡事件让人浮出历史,使观众看到被历史遮蔽了的人,死亡事件由是成为作者描述历史与个人的关系的中介。和死亡事件相对照的是人物对活着的达观态度,如果说死亡叙述是用以说明历史对个人的遮蔽的话,那么对活着的态度则可视作作者对这一遮蔽的回应。影片结尾处,福贵对馒头说:“鸡长大了就变成了鹅,鹅长大了就变成了羊,羊长大了就变成了牛。”这就是影片讲述的关于活着的素朴的道理,活着就是生命的延续,在延续的过程中不断涌现新的变化。活着从潜入福贵无意识的生物性生存变成“有意识”的觉悟,尽管福贵的命运是悲剧性的,但和无意识相比,福贵(或者说作者)对活着的有意识体悟和积极态度才是活着的“基本事实”。《活着》书写的既是福贵个人的命运,也是人类的群体命运。作者表明了对“活着”这一问题的思考,人不应该浑浑噩噩的活着,人必须在与外在环境和内在自我不断抗争的过程中意识到活着的意义,生命延续的过程中都会面临到种种荒谬的事实,但活着意味着用激情和坚韧来抗争死亡,用幽默和达观来对付荒谬,由此来战胜历史对个人的遮蔽,这就是影片《活着》从福贵个体命运的框架内对人类群体命运作出的“作者表述”。
三 捉弄人的历史
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个稳定模式——集体永远高于个人,抹杀个人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的弱化。在90年代电影的历史叙事中,历史对个人的控制力量如同高悬在个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剑,使得个人的命运被历史操控,历史叙事的第三种类型就是此类捉弄人的历史。《蓝风筝》里的铁头母亲、爸爸和继父就是这样的人物,他们或与政治运动、或与历史事件发生错位,其结果往往是个人为历史让路。历史之“重”、个人之“轻”让人产生荒谬感,个人的命运在此成为作者书写历史的中介,在这一历史叙事中表现的是历史对个人的重压和捉弄。
田壮壮导演的《蓝风筝》是一部“描述性的”的电影,它的人物和人物身上发生的事件之间并不具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它是由历史变迁中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来勾勒人物的命运,蓝风筝是作者设置的关于铁头和亲人们命运的抽象符号。从“描述性”电影的特征来说,这部影片首先引人注意的是它的叙事方式,它以儿童铁头的视角来观照从1953年至1967年间儿童眼中的中国历史。在电影中用孩子的视角来叙述故事并不少见,如吴贻弓的电影《城南旧事》就是采用这种叙事方式,这是因为孩子的世界纯净无暇,所以孩子往往成为影片中极为特殊的叙述者。孩子的视角和成人的视角有较大差别,孩子象征着身心的纯洁及道德的纯粹,但是在各种文本中孩子的出现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表现“纯洁”、“纯净”或“纯粹”等美好的方面,他们常常被用于作者某种意念的表达。譬如“由于人们认为孩子是未受到(或较少受到)成年世界中族群偏见影响的人,所以,在许多艺术作品中,孩子往往被想象、描述为超越偏见和冲突的存在……不论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少,人们对这样的情景的热情想象本身其实反映了成年人自身在现实中的某种无力感。”⑤《蓝风筝》正是一个符合这种特点的电影文本,用人的“无力感”反衬历史对于个人的力量。
在《蓝风筝》中,母亲树娟与儿子铁头是事件建构出的历史变迁的中心人物,由此影片形成典型的以时间为轴的线性叙事结构。影片以铁头眼中母亲的三次婚姻连接起影片的三段式结构,分别以铁头的视角命名为“爸爸”、“叔叔”和“继父”三个部分,这三个命名虽然都是对“父”的称谓,但生活中始终与铁头相伴、并担当守护者角色的却仅仅是母亲。因此,在铁头的世界里,母亲是最重要的情感维系所在,在铁头的叙述中一直在影片中回响的是母亲树娟教唱的童谣《乌鸦歌》。这个童谣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母子之间动人的人伦传统,乌鸦“母子”之间亲密互助、相互支撑的关系是铁头与母亲关系的诗化表达,童声唱出的歌谣在日后苦难的岁月里成为铁头生命中最有力的精神支柱,在影片中歌谣和蓝风筝一样成为人们度过那段历史的见证和慰藉。在“爸爸”部分,爸爸在劳改农场去世后,铁头对母亲的依恋和《乌鸦歌》中乌鸦对母亲的依恋极其相似,对铁头来说,失去父亲庇护后母亲就是他的全部世界,但是连母亲都随时有丧失的可能,童年铁头不断的追问表明他内心的危机。在“叔叔”部分,叔叔因病去世母亲再嫁后,铁头对继父充满敌意。母亲因阻止红卫兵批斗继父而被抓,铁头拿起一块砖头砸破红卫兵的头,被红卫兵打倒在地。在这一连串的悲剧事件后,母亲还是无可奈何地离他而去,铁头的世界也因此全部塌陷。在铁头的世界里,社会和历史的可怕摧毁力量似乎随时威胁着他和母亲,最终还是使他们分离。
在铁头童真的目光里,有关那个年代的“集体记忆”显得格外沉甸,也格外荒谬,影片从铁头的视角叙述了大量的荒谬情节:
(1)由于斯大林逝世,树娟和少龙延迟结婚,铁头因此延迟出生;
(2)爸爸少龙因上厕所而被无辜摊派了一个右派名额,最终死在劳改场;
(3)大舅舅树生是国民党投诚空军,反因眼疾在政治运动中安然无恙;
(4)树生的女朋友朱瑛因不愿陪首长跳舞而被转业至工厂,后被宣布为反革命分子入狱;
(5)大姨忠诚革命,却被挂牌批斗;
(6)小舅舅树岩是美院学生,上山下乡后娶了成分好的农村女民兵排长。
对上述事件的因果关系加以对比会发现,除了树生的命运以外以上这些情节的共同主题是惩罚,但这些情节之所以会产生荒诞感是因为惩罚的因果关系不具备合理性,影片中的人物没有辩护和寻找过错的权利,就如同铁头的生命一样无法自己控制,历史和个人之间形成了摸不着、却实实在在产生了结果的关系,历史操控并无情地捉弄着个人。树生情节的原因最有理由带来惩罚的结果,但恰恰没有,作者在树生情节设置的因果关系构成了进一步错位,这就产生了进一步的荒诞,使得荒诞性格外醒目而突出。当然,作者的意图不是讲述儿童铁头的故事,而是通过描绘铁头的外部世界的荒谬来进行历史叙事,指出历史对个人的捉弄和个人对自己命运的无能为力。
影片以蓝风筝为题,可见蓝风筝是作者赋予影片的重要意象,是作者对人物命运的符号化和形象化表述。风筝是一个优美的意象,但是又是那么轻薄难以附着,靠一根细细的线固着在土地上,飘摇在空中的风筝的命运却不是能靠一根细线就能够掌控的。影片中的风筝就是如此,风筝的蓝色和时代呼应,也暗示了风筝的命运:爸爸给铁头放飞的风筝又高又远,引起同伴们的羡慕,风筝破了以后爸爸能够随时再糊一个,提供给铁头源源不断的满足;爸爸离开以后风筝一直挂在床头墙上,可铁头不再放风筝,除夕夜和玩伴玩耍,但叔叔为铁头点的灯笼却被烧了,铁头在黑暗中茫然四顾;在继父家,继父的孙女妞妞看见铁头床头的风筝,请求和铁头放风筝,风筝被挂在树上,两个人望着窗外树上的风筝无语;影片结尾,铁头被打倒在地,仰面望着树上的风筝,风筝已是破烂不堪,地上的铁头、在风中飘摇的破风筝以及童声的歌谣叠加出作者喷薄而出、急欲诉说的话语——对历史的感受和判断。风筝因此成为作者表述其“意义”的重要符指,是作者表述其观念的视觉化呈现。不但是风筝,影片中还充斥了广播、标语口号、服装、会议、打斗等各种与时代密切相关的符号,人物在这些符号构成的场景中经历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可以说,这些符号集体构成了作者赖以表述的工具和话语,为作者的表述提供了影像和声音上的支撑。
风筝是人物的抽象化符号,因此《蓝风筝》的主题仍然是集中在历史与个人的书写上,作者通过影片明确表示在历史面前个人的不可为,个人的悲剧性皆来自于此。这也许是对个人的贬低,但在不可抗拒的历史运动面前,个人只能是不可为的,也因而是悲剧性的,如同飘摇欲坠的蓝风筝,影片中的人都是作者在其历史叙事中叙述的被历史捉弄而无奈的个人。
结语
历史叙事是90年代中国电影“作者表述”形态之一,作者关于历史的叙述是其历史观在电影中的反映。从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来说,历史叙事的历史远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派电影”,近可推及80年代以来“第五代”导演的文化批判和历史反思,这是中国电影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一传统在90年代得到延续,进入90年代后,电影作者的历史叙事不再如80年代那样摒弃个人,而是借重个人来抒发对历史的认知。本文分析的三类“历史中的个人”,包括李莲英、颂莲之类被历史禁锢的人,福贵之类被历史遮蔽的人,铁头父母之类被历史捉弄的人,通过这三类个人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作者对历史宰制个人的批判。在叙事中,尽管这些人物仍旧被遮蔽,但是不再像“我奶奶”、“顾青”、“翠巧”等80年代电影中的人物那样,人物自身的特性完全被作者抽离,人物成为空洞的文化符号,90年代电影中人物的困顿、罹难既是个人自身的命运,也是历史的映射,“个人”因此和80年代相比较为丰富、与此同时,作者的历史叙事也因这丰富的个人不再显得空洞、抽象,电影文本中沉重和压抑的历史形态更具有“说服力”,这是90年代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转变。
注释:
①引自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第182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
②[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20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8月。
③[法]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第63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
④引自王斌:《张艺谋这个人》,第97页,团结出版社,1998年1月。
⑤陈映芳:《图像中的孩子——社会学的分析》,第32页,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1月。
标签:历史论文; 李莲英论文; 电影叙事结构论文; 红高粱论文; 张艺谋论文; 慈禧论文; 古希腊论文; 历史故事论文; 历史学论文;
